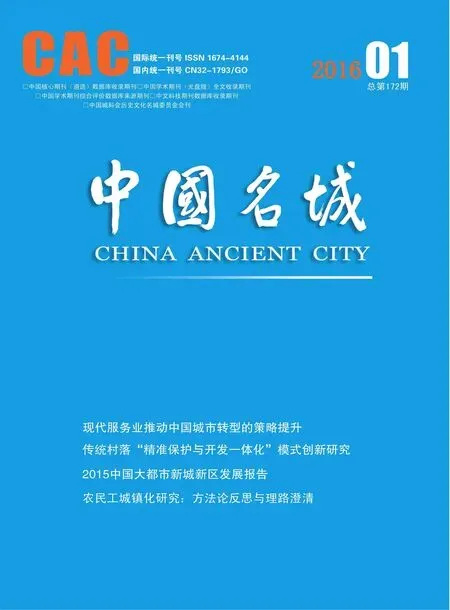農民工城鎮化研究:方法論反思與理路澄清*
曹志剛
農民工城鎮化研究:方法論反思與理路澄清*
曹志剛
目前農民工城鎮化研究領域的研究中,因為對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缺乏足夠的思考,導致研究中出現了經驗研究與理論探討相脫節的現象,影響了研究積累和質量提升。在對農民工城鎮化研究需要解釋的現實問題和西方移民研究所解釋的現實問題進行比較分析的理路澄清中,概括出了兩者之間的三個相似點和三個不同點。這三個相似點分別是遷移的動因、移民的文化屬性對其流入目的地的影響作用、基于流入地利益而非社會公正的制度結構安排。不同點則是土地制度、戶籍制度和中西文化差異。基于這些相似點和不同點的整體性理解上的差異,可以歸納出后續研究在兩種截然不同方法論立場下的不同發展方向。相信這一問題的明確,不僅對于這一領域的理論提升,而且對于這一領域的政策設計,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農民工;城鎮化;方法論;理路
1 引言
自2012年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報告中“新型城鎮化”的提出,新型城鎮化這一問題越來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重視。之后,2014年李克強總理所作政府工作報告中關于“三個1億人”的提法,①使農民工城鎮化研究在理論界、實務界的工作日程中更加緊迫起來。
而從筆者對這一領域研究進展的把握和理解來看,近十年以來,社會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業已有了相當積累。目前研究中存在的突出問題不是對這一問題的理論關注和實地調查不足,反而是因為缺乏對這一研究領域方法論的高度自覺和提升,使得這一領域的研究缺乏系統性地梳理和整合,很難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逐步推進,研究的“碎片化”傾向嚴重,很難從對實地問題的調查研究走向理論自覺,嚴重制約了這一研究領域的發展前景和突破性可能。只有在方法論層面對這一領域的相關研究進行系統性反思,并對相關研究理路進行澄清,明確它與西方移民研究理論之間的關系,這一研究領域才有可能從“量”的積累真正走向“質”的提升,也才有可能使理論提升和實踐對策更具高度和層次。
2 農民工城鎮化研究方法論反思的涵義
方法論,概括而言,關系到研究者如何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具體而言,方法論是指人們用什么樣的方式、方法來觀察事物和處理問題。在早期西方社會學的發展歷史中,迪爾凱姆倡導的實證社會學和韋伯主張的理解社會學就貫徹了截然不同的方法論立場。在中國社會學的早期發展歷程中,對西方社會學理論的簡單移植和社會學本土化的不懈努力也體現了兩種不同的方法論立場。[1]方法論意味著,對同一事物的客觀理解和認知有可能產生多種并行不悖的解讀方式,甚至,這一“客觀”在部分研究者的方法論立場上,本身就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妄想。在具體的研究中,方法論的立場和選擇,制約著研究的選題,所采用的資料收集方式和如何理解這些研究資料。換言之,方法論的選擇往往意味著研究路徑的迥然不同走向甚至包括研究結論的提出。這也就意味著,方法論問題不僅在某一項具體的研究中非常重要,在某一領域的研究中更是重要。研究者在整個研究過程中,都必須對方法論的重要性保有高度自覺,才能使具體研究更具研究質量和理論內涵。但目前國內農民工城鎮化的諸多研究中,卻未能對方法論問題作出很好回應,制約著該領域的研究進一步向前拓展,使該領域目前已有的大量實地調查面臨低水平重復性勞動的風險。[2]不僅有損于該領域的理論提升,也會使該領域的實踐對策缺乏頂層視野,[3]淪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一孔之見。
關注農民工城鎮化研究的國內社會學研究者,普遍使用了國外同行較為常用的社會認同、社會融入、社會適應、社會融合、遷移意愿等相關比較相近的學術概念,[4]運用了一般線性回歸分析、因子分析、Logistic回歸,結構方程等不同的數理模型,探討不同的自變量指標,如個體人力資本、客觀社會地位、社會網絡狀況、制度壓力等,對不同的因變量指標,諸如社會地位認同、群體認同、文化認同、地域認同、職業認同、地位認同、經濟適應、文化適應、心理適應、社會適應、文化融合、心理融合、身份融合和經濟融合等的影響作用,[5]對農民工在流入地城鎮的社會狀況進行了描述和分析。也有學者基于上述結論,提出了“農民工——工人——市民”的農民工市民化路徑的策略性思考,[6]應當來說,這些經驗研究的成果積累,體現了社會學研究者關注時代重大問題,響應社會現實需求的工作倫理。也為理解、分析作為城市外來者的農民工的社會狀態和農民工城鎮化社會政策的提出,奠定了相當現實基礎。
雖然目前這一領域的研究已有相當數量的積累和一定程度的推進,但是,當系統性梳理這一領域的研究現狀時,其對方法論反思存在的缺陷卻又一覽無遺。它體現在,前述研究中出現了若干相近的核心概念,不同研究者的用法存在側重點差異,甚至同一學者在不同時期使用了不同核心概念,那么,這些核心概念的使用究竟是出于同一英文詞源,只是在翻譯中使用了不同漢語詞匯,還是研究者出于核心概念背后的深層含義具有針對性地使用了自己主張的獨特概念。這些問題,在相關研究中并沒有得到明確交代和說明,后續研究者面臨無法明確在何種對話基礎上繼續研究的尷尬處境——因為他極有可能選擇一個不太高明的研究作為自己的研究起點從而使自己在研究中花費的精力、時間都毫無價值可言。
更為致命的是,研究者們普遍使用的這些核心概念,在西方移民研究中出現頻率較高且出現較早。這就意味著國內社會學研究者是在借用西方移民研究的“成形”概念來理解和分析中國農民工城鎮化的相關問題。這一“借用”本身并無問題,體現了后發國家在吸收先發國家研究進展的必要性,也表明后發國家除了經濟生產、社會發展之外,在理論闡發中仍存在的巨大挑戰。但是,如果不對這一借用——也就是研究的方法論立場作一清晰交代,既有可能使具體的研究面臨南轅北轍的風險——在此一方法論立場下選擇彼一研究方法和分析方式,也有可能使具體的研究似無頭蒼蠅——只探討具體的經驗現象中這一指標與另一指標的關系而不具深厚理論內涵。
概括而言,農民工城鎮化研究中的方法論缺陷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如果說研究者大量使用西方移民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來解釋我國農民工城鎮化中的若干重要具體問題,是不是也就變相承認了農民工的城鎮化只是“移民研究”的一種亞類型。因此,自然而然的,這些核心概念的使用就有了天生的合理性。但是,農民工的城鎮化可以被視作移民研究的一種亞類型應當不是不證自明的,研究者仍需在具體研究中交代,這一類屬關系劃分的依據——也即是農民工城鎮化研究所要解釋的現實問題與西方移民理論已經解釋的現實問題的高度相似性的邏輯所在。其二,如果說研究者大量使用西方移民研究中的核心概念的方法論基礎在于,是認為目前在這一領域的經驗研究積累還不足以豐厚到足以進行理論生產和方法論對話,只能暫時性地將這一方法論問題加以“懸置”,等到這一領域的經驗研究達到能夠進行理論生產和方法論對話的時候再來討論這一問題。那么,研究者有必要交代自己目前所使用的核心概念是存在一定適用性風險的。遺憾的是,筆者基本很少看到這種交代。而且,筆者認為,以目前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展狀態似乎還不能說,該領域作為一個新生研究領域,還來不及反思方法論立場這一重大問題。恰恰相反,筆者認為這一領域的發展現狀正到了必須正視方法論立場的關鍵時期。其三,如果說研究者認為,可以在方法論層面“改造性”地使用西方移民研究中的這些相關核心概念,對這些核心概念的使用是在技術層面的,那么,也需要交代農民工城鎮化研究與移民研究在哪些地方存在重大差異,以至于必須改造性地使用這些核心概念。這樣,才能使研究者能夠更好的遵守學術倫理——在某一理論概念能夠適用的具體情境下使用它而不是相反。
遺憾的是,筆者上文所提及的這些方法論的缺陷問題一直未能得到高度重視,更逞論得到妥善解決。這其中既有我國社會學早期傳入過程中對實證社會學較為偏重的歷史原因,也有當前我國社會學教育和研究現狀中的重經驗調查、輕理論闡發傾向的現實原因。既有該研究領域問題研究難度的客觀困難,也有研究者或對方法論的忽視或主動回避困難的主觀問題。不論造成問題的原因有多么復雜,在目前的研究現狀下,只有主動彌補這一方法論缺陷,這一領域的研究積累才能從經驗調查的積累走向理論闡發的提升。而要想實現這一較高的研究期望,就必須對該領域的研究理路做一整體性澄清,理清在該領域的研究中可能有哪些不同的方法論立場。這一工作目標,對于這一領域的后續研究者在不同的方法論立場上展開充分充分探討和對話,從而實質性的推動該領域的研究,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而要想實現這一工作目標,就必須在理路中澄清哪些因素會對農民工城鎮化的方法論立場造成重大影響,從而影響其走向不同的研究立場的。這一工作目標,有必要從對我國農民工城鎮化研究產生重大影響的西方移民研究的方法論及其關注展開。
3 西方移民研究的理路關注
社會學史上的不同抽象理論,依其來源大體可以分為從一定的社會現實領域產生或者從既有的研究范式產生兩種路徑,前者如青年研究、婦女研究等,后者如社會沖突論中分化出來的功能沖突論等。依據這種思考,西方移民研究的既有理論應當可以歸類為從一定的社會現實領域產生。那么,從研究的理路中分析西方移民研究已經解釋的社會現實,并在此基礎上分析這一社會現實與我國農民工城鎮化研究想要解釋的社會現實之間的相似點和不同點,就成為本文對農民工城鎮化研究方法論反思的核心內容。它尤其體現為從方法論上對這些相似點和不同點的整體性理解,將會產生農民工城鎮化研究截然不同的理論提升和實踐對策。因為方法論的具體作用展現,是通過方法論對具體研究的全過程統領實現的。
具體而言,如果能夠在理路層次上論證西方移民研究理論已經解釋的社會現實問題與目前農民工城鎮化研究需要解釋的社會現實問題并無二致,我們就沒有必要在方法論層次重新提出新的方法論思考,借用西方移民研究的相關理論來指導相關理論提煉和對策實踐將是更為便捷、可行的途徑;而如果西方移民研究理論所解釋的社會現實問題與目前農民工城鎮化研究需要解釋的社會現實問題實際上存在重大區別,對目前這一領域的方法論審視就是非常必要的,它有助于我們防范和避免盲目套用西方移民研究理論來解釋其并不適用的社會現實問題的風險——即削社會現實問題之足適既有理論之履的風險。這一方法論的反思,不應視為可有可無,而是應當成為這一領域研究的基石。沒有這一基石,后續研究在相當程度上都只能被視為無本之木。
下文首先來分析西方移民研究理論已經解釋的社會現實問題與目前農民工城鎮化研究需要解釋的社會現實問題之間可能具有的相似點,接著再分析兩者可能的不同點,以便在理路上澄清影響農民工城鎮化研究方法論不同走向的關鍵點所在,筆者認為,這也是本研究的核心貢獻所在。
無論是對西方移民研究具有開創性貢獻的W·L·托馬斯和F·茲納涅茨基對波蘭移民在美國工作、居住和生活、心理狀況的經驗研究,[7]還是在西方移民研究中占據重要位置的克雷夫科爾(Crevecoeur)的“熔爐論”、特納(Turner)的“邊疆熔爐論”、肯尼迪(Kennedy)的“三重熔爐論”、斯圖爾特(Stuart)的“變形爐論”等的研究,[8]其關注的核心問題指向的是流動人口(強調短時期地理空間位置的變動)或遷移人口(強調長時期地理空間位置的變動)從流出地到流入地的工作、居住和生活、心理狀況。“跨國”是他們關心的內容之一,但他們更關注的是流動或者遷移人口的地理空間位置變動的“動因”和“后果”及其影響因素等。為敘述和理解的方便,筆者試圖分要點將西方移民研究理論所解釋社會現實問題的基本理路做一澄清,并試圖分析它與農民工城鎮化研究所需要解釋社會現實問題的相似點如下:
3.1 從流動到遷移,從流動人口到遷移人口
在西方移民研究中,以薩斯塔(Larry Sjaastad)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理論、斯塔克(Oded Stark)為代表的新經濟移民理論、農戶風險決策機制理論、托達羅(Todaro M.P)的托達羅模型、哈里斯(J.R.Arris)對托達羅模型進行修正后的哈里斯-托達羅模型,都將移民的外出動因主要理解為移民出于個體理性或者家庭理性的經濟計算,從而形成遷移的動因,[9]他們試圖解釋為什么有的移民選擇短期的流動,成為流動人口,為什么有的移民選擇長期的遷移,成為遷移人口,以及流動人口在什么條件下會轉變為遷移人口。這也就意味著西方移民研究理論對移民“從流動到遷移,從流動人口到遷移人口”這一地理空間位置的短期變動到長期變動,給予了相當的重視。
西方移民研究理論所揭示的“從流動到遷移,從流動人口到遷移人口”這一規律與農民工城鎮化現象之間具有相當的共性之處。經濟理性是我國農民工是否進入城市務工的重要動因是不可爭辯的基本事實,但國內有研究已經充分注意到了老一代農民工與新一代農民工代際差異的種種表現,[10]其中之一就是新一代農民工并不像老一代農民工僅僅出于經濟理性來計劃他們的城市務工行為,而是在社會理性的綜合考量下,對他們城市生活未來之路作出了更具策略性的籌劃,[11]當前城鎮農民工群體的分化,已經出現了西方移民所具有的一大重要特征——基于經濟理性但不僅僅出于經濟理性對個人或家庭的流入目的地的謀劃。以往,國內研究者認為區分農民工城鎮化研究與移民研究的理由之一即是老一代農民工相對于西方移民而言,城市在他們未來生活預期中的重要性是有重大差別的,農民工往往“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在外務工的基本著眼點在于為了“讀書、娶妻(兒媳婦)、建房、辦大事”而賺錢,很少想到在流入目的地或其它城鎮中定居。新一代農民工則明顯有了差別,雖然他們也像他們父輩在不同城市流動遷移,但其主要目的中增加了在不同城市尋找定居機會這一選項。而且,他們的最后落腳地意向除了流入目的地城市,配偶所在地城市、家鄉所在省會城市、家鄉所在地級市、家鄉所在縣、家鄉所在鄉鎮也成為了優先選擇,作為流出地所指的鄉村,已經不是一個葉落歸根的歸宿地,而是一個“不得已而為之”的無奈選擇。這就意味著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工消失了——新一代農民工成為了力圖改變定居地、實現城鎮生活的移民。
3.2 移民的文化屬性對其流入目的地的影響作用
以往的西方移民研究中發現,南歐移民、東歐移民、墨西哥移民、泰國移民、中國移民等在流入地漫長的遷移歷史中形成了各具特點的移民傳統,來自不同流出地國家的移民往往選擇不同的流入目的地國家。甚至在這些地區或國家內部,來自不同區域、省份的移民也會形成不同的移民傳統。[12]例如,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區域、省份的移民往往會在流入地國家的特定區域城市聚集、定居,甚至會在這些特定區域的城市選擇特定的行業尋求謀生之道。這體現了語言、民族、來源地區域等文化屬性對跨國移民流入目的地的影響作用。
類似的,已有大規模問卷調查、深度訪談的研究中,研究者業已發現來自不同地域、省份、區域的農民工也在長期的流動經歷中形成了特定的遷移路徑。東三省、西北地區、西南地區、江浙地區的農民工對津京唐、長三角、珠三角各經濟帶大中城市的選擇性偏好往往具有明顯的特點。如客家人往往選擇珠三角城市作為落腳地的首選城市,而江西撫州市資溪縣人的面包店、福建三明市沙縣人的小吃店、湖南婁底市新化縣人的打印復印店、廣西天等縣人的桂林米粉店、重慶開縣人的成都小吃店等則在全國各個大中城市中都占據了各自行業的龍頭壟斷地位,這些都表明了農民工與跨國移民一樣,出現了流出地的文化、語言、籍貫對流入目的地的影響作用。
西方移民研究中發現的“少數族裔經濟”在城鎮農民工中也存在相似情況,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民族政策影響,我國國內各個民族的差異性得以凸顯而不是趨于消失,[13]民族的差異性這一變量的影響,使得少數民族的農民工在特定流入地城市中往往選擇了“小聚居”的形式,這種并非四處分散的務工形式,反過來又強化了他們的民族意識,增加了他們在城鎮化過程中“被標簽”的可能,這對他們同時存在著有利和不利的影響:有利之處是他們在流入地城鎮中作為群體的存在使得城市政府必須回應他們的某些呼聲,幫助他們解決一些現實問題;不利之處是他們始終被視為“外來者”這一外來群體,而不是很快消失在城里人的視線之中成為“城里人”。這一尷尬處境,與非洲移民、墨西哥移民等有色種族移民在美國、歐洲等移民流入地國家的情形是相似的,與流入地的“差異性”成為他們實現移民的雙刃劍——差異性既幫助他們取得一定特權又使他們成為永遠的“侵入者”。
3.3 基于流入地利益而非社會公正的制度結構安排
跨國移民在其遷移行動中,受到流入目的地國家社會政策、流出地與流入地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的經濟結構影響,因此遷移行動面臨種種約束和限制。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型”,費景漢和拉尼斯對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模型”的發展,唐納德·博格提出的人口轉移“推-拉”理論,多林格爾和皮埃爾提出的“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等,[14]都關注到了社會政策、經濟結構對移民遷移行動的影響。在具體的個案中,無論是1882年5月6日美國政府針對華人勞工頒布的《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Law)》,還是2012年6月18日美國眾議院全票表決通過,正式以立法形式就當年通過的《排華法案》道歉,它反映的一個基本規律就是流入地優先因其利益需要,選擇性地放寬或者加重對外來移民的限制政策,反映的是外來者在流入地政策設計中處于劣勢地位的既定事實。
在國內農民工流動與遷移的相關政策中,無論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南方各省為了預防民工潮大規模涌入城市,而和農民工流出地各省一起加強對“外出務工人員就業登記表”和“暫住證”的審查,[15]還是20世紀90年代末期放寬對農民工外出務工的限制,以及廣東省《關于開展農民工積分制入戶城鎮工作的指導意見》和佛山、深圳、東莞等地制定的“積分入戶”的具體細則,反映的也都是農民工流入地城市對流入農民工有選擇性的利用(本文中,筆者并不打算從社會公平的角度詳細探討這一問題,而只強調這一既存的社會事實)。
遷移者——包括跨國移民和國內農民工——在流入目的地這一相似的社會境遇,引起了極其類似的連鎖反應。2011年8月6-10日,主要由愛爾蘭裔移民在英國倫敦引發的社會騷亂[16], 2012年11月26日,中國籍巴士司機因為與馬來西亞籍巴士司機同工不同酬,以及背后的勞工身份不能申請親屬長期探親簽證,引發的在新加坡極其少見的大罷工,[17]2011年6月10日晚,因四川籍孕婦與治保會工作人員沖突引發的四川籍、江西籍、湖南籍農民工與廣州市增城區新塘鎮當地村民及警方的大規模對抗,[18]都說明了作為外來者在流入地所遭遇到的“天花板效應”——他們雖然與當地市民一樣工作和生活,但因為制度身份、所處勞動力市場等種種結構性限制,他們或許從進入流入地的一刻開始,就已經注定因為身上帶有的這種“外來者”的標簽,而永遠難以擺脫這種相對劣勢的境遇。
4 農民工城鎮化研究中的理路困境
如果僅僅只是看到上文中農民工城鎮化研究與西方移民研究之間理路關注的三個重大相似點,似乎本文的結論將走向如何將西方移民研究的已有理論指導于我國的農民工城鎮化研究的現實問題。實則不然,筆者認為,農民工城鎮化研究與西方移民研究之間的理路關注之間同樣存在三個重大不同點,它恰恰也是導致目前農民工城鎮化研究中存在理路困境的原因所在。這三個重大不同點的存在,對于農民工城鎮化研究的未來走向,將會產生重大影響作用。概括而言,在理路上我們可以同時發現農民工城鎮化研究與西方移民研究的理路關注的相似點和不同點,但如何整體性的理解這些相似點和不同點,是農民工城鎮化研究的方法論中必須回答的問題。同時,必須意識到,在方法論立場中對這些相似點和不同點的整體性理解差異,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方法論走向。下文,筆者先對三個不同點逐一進行分析。然后,在本文結論性的部分,再來展開對從方法論的整體性理解分析。
筆者認為,目前農民工城鎮化研究中存在的理路困境所在,也就是在農民工城鎮化研究中借用西方移民研究的理論框架未能妥善解釋的三個不同點分別是:土地制度、戶籍制度和中西文化差異。這三個不同點又存在一定差別。土地制度的特點在于其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中的核心構成部分,來區別于資本主義土地私有制。它在社會變革中的操作性難度相對不大,但是變革帶來的震動可能最大。戶籍制度在三者之間恰好處于中間,它相對于土地制度而言,變革帶來的震動較弱。但是因為這一制度束而非單一戶籍制度牽連的廣泛性,其在變革中的操作性難度比農村土地變革的操作性難度要大。中西文化基礎的差異,則是看上去變革帶來的社會震動最小,不需要動用強制力量推行,但實際上變革操作性難度最大。以下試分別展開分析:
4.1 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度對農民工城鎮化的兩面性影響
與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實行的土地私有制明顯不同,目前我國農村的集體土地所有制度,約定了農民以家庭為單位可以擁有一定面積的宅基地,同時還可以以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形式,承包一定面積的土地、山林、池塘、草原等賴以謀生。改革開放之后的這一在原來政策基礎上給予農民更大勞動激勵的政策安排,在三十年后的今年,遭遇了更為復雜的現實情境,顯現出了其對農民工未來走向的兩面性影響。它到底是給農民工的進城務工以一種類似“托底”式的在流出地的最后保障,還是給予流入地城市和農民工兩者以一定“借口”抑或“理由”來忽視農民工城鎮化的政策安排?對于前者來說,農民工在流出地的自我保障顯然地降低了他們對農民工群體的政策安排緊迫感,對于后者來說,則是在另一角度而言增加了他們流動遷移而不是永久性遷移的可能性。
堅持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度是農民工城市化減震器觀點的學者認為,對農村土地流轉和農村土地規模經營的積極倡導是錯誤的,因為“農村土地流轉和農村土地規模經營應該是農民工轉移進入城市后的自然而然的結果,而不能反過來”,[19]因為目前這樣的土地制度安排,農民工在城市的務工生活,才能沒有后顧之憂。而亦工亦農的靈活就業安排,既給予城市以巨大的勞動力供給,也免除了他們在使用勞動力時的巨額社會成本支出,能夠減少出現社會動蕩的風險。
而持相反觀點的學者則認為,我國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等一系列農村土地制度變革中貫穿的基本思路是給農民以越來越大的土地權利,而不是相反。只有給予農民以更大的土地權利,包括給農民工參與土地流轉或規模化經營的權利,才有可能激發農民群體的生產效率,[20]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當前我國工業化率遠高于城市化率的現狀。與此對應的,跨國移民的重要流出國家(地區)的墨西哥、泰國、臺灣,其農村土地制度都早已是私有化的制度。
筆者認為,造成學界對農村土地制度與農民工城鎮化兩者關系不同觀點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以何種視角來理解農民工的城鎮化。認為現有農村土地制度是農民工城鎮化減震器的學者及相反觀點的學者對農民工城鎮化的前景預期產生了不同的判斷。比較而言,前者更多的是出于整體主義視野下農村社會和城市社會的社會穩定中去分析農民工的流動和遷移;后者則更多的是在個體主義的視野下從農民工個體權利(分享城鎮化進程的收益)如何實現的角度去分析農民工的流動和遷移。很難判斷兩種觀點的對錯,但這種社會學方法論中的整體主義——個體主義的分歧影響著不同的理論研究和對策實踐也已是不爭的事實。但制定相關實踐對策的迫切性,也在呼喚其所遵循的理論方向指南的明確化。
4.2 戶籍制度在農民工城鎮化中的深刻影響
脫胎于蘇聯人口管理體制的我國戶籍制度,在事實上已經遠較蘇聯時期的人口管理更為嚴厲,[21]它既是我國城鄉二元體制的伴生物,也是維持這一體制的重要支撐。而以通常所說戶籍制度所涵蓋的內容,與其說戶籍制度制約著農民工的城鎮化,毋寧說,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束制約著農民工的城鎮化。因為城市戶籍和農村戶籍的差別所指向的并不僅僅在于人口登記的地理差別,它指向的是身份、就業、失業、工傷、教育、醫療、養老、政治參與等一系列重要權利差異,因此本文所指的戶籍制度,并不僅僅單指戶籍制度本身,而是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構成的制度束。這一制度束在城鎮居民和農民工中所造成的影響是:它在城鎮居民與農民工個體的層面是一系列現實權利不平等及在此基礎上的優越感和歧視問題,在城市居民和農民工群體的層面是群體利益博弈的問題,在宏觀城市社會政策的層面則是社會公平正義的理想規范與社會成本的現實核算問題。
目前,在數目龐大的城鎮農民工群體中,真正實現城鎮化的少之又少。即使他們中有少部分人通過自身的努力獲取了足夠的經濟收入以支付城市生活的各種開支,但是因戶籍制度束造成的種種權利差異,又極大增加了他們的經濟負擔——他們必須以更大的經濟開支如購買藍印戶口、購房落戶、借讀費、商業保險等來彌補自身與城鎮居民之間的權利鴻溝,而甚至在此之前,還必須彌補因為受教育程度較低在城鎮勞動力市場中的不利地位。顯然,從農民工成為城鎮居民,他們所要跨越的制度結構帶來的區隔,甚至可能要大大強于跨國移民在其遷移行為中面對的制度區隔,這一點,在農民工城市認同的研究中業已得到體現[22]。
跨國移民在流入地國家需要跨越國籍、語言、文化、種族等區隔來實現真正的移民。來自于不同流出地的移民,如中國移民、波蘭移民、韓國移民、日本移民、越南移民、墨西哥移民、西班牙移民、非洲移民在流入地國家實現了不同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在美國的中國裔移民往往具有較高的文化資本,經濟地位也相對較高,但政治地位則處境堪憂。越南裔移民、韓國移民的文化資本也在逐漸提高,并且經濟地位也處在上升趨勢。非洲裔移民、墨西哥移民雖然文化資本、經濟地位較低,但因其種族特點,在美國社會的政治議題中卻享有相對優先的優越權利,有時候甚至還會因此出現社會政策中對白人的反向歧視這一特殊的情形。這些現象,都說明了跨國移民的跨國遷移相對于農民工城鎮化而言,即使不能說是明顯受到的制度區隔制約較少,但確能顯示出國內農民工城鎮化受到以戶籍制度為代表的制度束的深刻影響。
4.3 個體為本與家庭為本的中心文化差異
無論是費孝通所說的“差序格局”所描繪的中國社會尤其是農村社會中人們以自身為原點,發展出類似波紋結構的、可以伸縮的社會關系網絡,從而與西方社會中從個體主義出發的、界限分明的團體格局相區別,[23]還是梁漱溟所說的“中國逐漸以轉進于倫理本位,而家族家庭生活乃延續于后。西洋則以基督教轉向大團體生活,而家庭為輕,家族以裂,此其大較也”的中西社會文化基礎的差別,[24]都指向了中西社會的文化差異。筆者認為,這一文化差異意味著,在以移民研究既有理論來解釋農民工城鎮化問題時,尤其需要得到重視。因為它指向了兩者之間可能存在的不能兼容之處。
文化差異及其蘊含的意義,并不意味著這一差異的不可轉換性,但這一觀點,落腳在文化變遷的緩慢性這一特性上卻有著重要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文化,相對于國家體制、社會制度、法律條款、社會心態等而言,顯然其變革的周期相對更長,轉變的可能性更小。它蘊藏在社會有機體的各個部分之中,雖難以言狀但卻時時處處發揮著實際的影響作用。這一差異的影響,也可能同樣體現在國內農民工的城鎮化與跨國移民的遷移中。
國內農民工往往依賴于其血緣關系、親緣關系、地緣關系為核心連接形式建立起來的社會關系網絡,在流入地城鎮尋找工作、解決住宿、幫忙解決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尋找情感支持等,并因此在流入地城鎮中形成了小聚居的生活格局。這一特點,在一個角度來看,有利于他們在流入地的生活轉換,但在另一個角度卻極其容易導致他們在流入地復制鄉土生活的社會網絡結構,影響著他們真正的城鎮化,因為與此同時流入地的城鎮居民也會因為這種文化特性,在流入地社會中形成另一種社會網絡結構,“本地人”與“外地人”的這兩種社會網絡結構之間相互隔離,彼此之間很難、也很少溝通,在一定程度上甚至還會增加兩個群體發生群體間產生對立和沖突的可能。
而在流向西方國家的跨國移民的遷移中,來自不同國家的移民雖然和農民工一樣,也會利用血緣關系、親緣關系、地緣關系等社會網絡實現其遷移行為。但在流入地國家中,他們面臨的社會空間結構卻相對明顯更為開放,因為不同文化特性帶來的社會網絡差異,我國農民工在流入地社會空間中需要通過多重社會網絡的“中介”,實現與城鎮居民“弱關系”的連接,來解決他們在城鎮中面對的種種問題,西方移民在流入地國家面對的處境則沒有這么困難,他們只要在經濟收入、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實現成功,與當地居民的隔閡沒有國內農民工碰到的情況那么深,在流入地的生活轉換相對會比農民工的城鎮化相對順利得多。
5 結論與討論
時至如今,正如斯蒂芬·卡斯特爾斯所言,“移民現象既不單純是因,也不單純是果,是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一個互動性變量”,[25]同樣,農民工城鎮化既是一個結果、又是一個原因,新一代農民工在流入地城鎮的目標出現了復合化和多元化的特征,它成為當下整個社會系統變遷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而不僅僅只受到其它變量因素的影響。同時,農民工城鎮化研究所蘊含的政策涵義,表明它將繼續處于最近一段學術研究的中心領域,但目前的農民工城鎮化研究往往與短期而非長期的政策關注相關,既不能前瞻預見性地對農民工城鎮化進行政策設計,又存在被政策利益和偏見驅使下“問題化”的可能。這些理論問題和現實困擾,都意味著當前我國農民工城鎮化研究需要在方法論層面加以澄清,以明確在什么立場和什么角度來分析農民工城鎮化。
前文筆者已經試圖在理路中澄清了農民工城鎮化研究需要解釋的現實問題與西方移民研究已經解釋的現實問題之間的相似點和不同點,這絕不意味著研究的結論分別強調這些相似點或不同點的“是”或“否”。特定的理論往往由一定社會現象或現實問題的解釋需要而產生,因此往往只能對它所涵蓋的社會現象具有更好的解釋力。但與此同時,理論內部的邏輯結構意味著它向外擴展解釋力的可能性,這是抽象理論相對于經驗歸納的優越性,也是抽象理論的生命力所在。它意味著既不能將特定理論僵硬的應用于解釋它所適用的社會現象,也不能僵硬的認為特定理論只能解釋它所適用的社會現象。有時候,理論內部邏輯結構的局部微調甚至會帶來它解釋范圍、解釋力的巨大變化,經濟學領域赫伯特·西蒙對傳統經濟學中的“理性人”假設的局部修正和社會學領域杰弗里·亞歷山大對塔爾科·特帕森斯結構功能主義的改造即是這一規律的最好注腳。但是這些仍然不能回答的問題是,什么是特定理論擴展的邊界?
這一問題具體到農民工城鎮化研究的方法論探討中,則是,在前述理路中澄清了農民工城鎮化研究需要解釋的現實問題與西方移民研究所解釋的現實問題之間的相似點和不同點后,對這些相似點和不同點的整體性理解而非片段式理解,有可能導向不同的結論。
結論之一是,既然西方移民研究和農民工城鎮化研究都需要關注作為“外來者”的社會群體在流入地的社會處境,并由此延伸到遷移行為為什么產生,移民在流出地和目的地又受到什么結構性因素的制約等。這就意味著西方移民的既有理論是完全可能移植到農民工城鎮化研究中去。此時,我們只需要將土地制度、戶籍制度和中西文化差異作為其中技術性的前置部分加以重點解決,這樣,農民工城鎮化研究需要解釋的社會現象就成為了移民研究中的亞類型,在相關研究中對這些核心概念的運用就完全可以是不假思索的。這一更具“規范研究”色彩的方法論立場在帶來理論運用便捷性的同時,也有存在“削足適履”的風險。
結論之二是,相反的,如果繼續堅持土地制度、戶籍制度、中西文化差異的根本性,強調目前社會現實的發展路徑而不是從已有成型的理論出發,則可能導向農民工城鎮化研究的另一種思路——生發出另一種社會學理論與西方移民理論相區別,它朝向社會學本土化、中國化這一宏大設想前進。它在重視理論建設的本土性資源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的連鎖效應,這主要體現在不需要視土地制度、戶籍制度、中西文化差異為理解農民工城鎮化問題的前置性部分的同時,也可能剝奪了目前處于相對被剝削地位、需要從社會公正角度加以彌補的這部分農民工尋求權利救濟的理論合法性資源。
筆者本文,并不能完全回答農民工城鎮化所應持有的方法論立場問題,但卻在理論澄清中指出了影響這一領域研究走向截然不同方法論立場的關鍵因素。這一立場,并不期望目前在農民工城鎮化研究能夠貫徹其中某一類型思路。而是提醒相關研究者,在進行具體的經驗研究前應明確該研究的不同方法論立場,從而避免研究中的方法論立場與具體的研究理論、方法相矛盾甚至混亂的問題。
農民工城鎮化研究想要避免淪為狹隘的“經驗研究”,研究者就需要將其置于更為深厚的理論框架和寬大宏觀歷史視野的關懷之中,如農民工的代際變遷、城市社區重構、社會發展階段等的考量之中。[26]否則,研究極有可能存在“失之毫厘、謬之千里”的風險。在具體的研究中,方法論立場與理論選擇、研究策略、資料獲取等應構成宏觀、中觀、微觀的整體性解釋框架鏈條,而不是僅僅沉迷于數字統計相關之中。與此相對應的,農民工城鎮化的政策設計中,政策設計者們也需明確其基本的理論立場,否則,這些政策設計極有可能出現“碎片化”的特點,在邏輯關聯上很難互相呼應,最終造成的后果之一即是目前農民工的相關政策設計中出現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且多有反復,既浪費了社會資源又增加了未來改革的社會成本[27]。
更廣泛而言,本文提出的這一問題,背后涉及的是農民工城鎮化這一具體中國現實問題遭遇既有西方社會學理論這一經典社會學命題,本文未能完全回答西方移民研究理論能否適用于國內農民工城鎮化研究的問題。但相信筆者對這一領域的理路澄清,對農民工城鎮化研究需要解釋的問題和移民研究所解釋的問題之間的相似點與不同點做出的基礎性分析,對其融合性和分歧性也作出了初步預判。未來這一領域的研究或可沿此而推進,在理論升華和經驗對策中形成更具說服力的研究成果。
注釋:
①主要是指“促進約 1 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改造約 1億人居住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引導約 1 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
[1] 趙旭東.超越社會學既有傳統——對費孝通晚年社會學方法論思考的再思考[J].中國社會科學,2010,(6).
[2] 曹志剛,雷洪.對當今社會學庸俗化風險的討論[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14,(3).
[3] 劉愛玉.城市化過程中的農民工市民化問題[J].中國行政管理》,2012,(1).
[4] 王毅杰,倪云鴿 .流動農民社會認同現狀探析[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5,(2).
劉傳江,周玲 .社會資本與農民工的城市融合[J].人口研究,2004,(5).
田凱 .關于農民工的城市適應性的調查分析與思考[J].社會科學研究,1995,(5).
任遠,鄔民樂 .城市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 : 文獻述評[J].人口研究,2006,(3).
[5] 張文宏,雷開春.城市新移民社會認同的結構模型[J].社會學研究,2009,(4).
張文宏,雷開春.城市新移民社會融合的結構、現狀與影響因素分析[J].社會學研究,2008,(5).
孟祥斐,華學成 .被動城市化群體的轉型適應與社會認同——基于江蘇淮安市失地農民的實證研究[J].學海,2008,(2).
王春光.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與城鄉融合的關系[J].社會學研究,2001,(3).
悅中山, 李樹茁,【美】費爾德曼, 農民工的社會融合研究 : 現狀、影響因素與后果[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2.
羅遐,流動與定居 : 定居農民工城市適應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1.
[6] 劉傳江,程建林,董延芳.中國第二代農民工研究[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2009.
[7][美 ]W·L· 托馬斯,[波蘭 ]F· 茲納涅茨基.身處歐美的波蘭農民[M].張友云,譯.南京:譯林出版社 ,2000.
[8] 李明歡.20 世紀西方國際移民理論[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0,(4).
[9] 曹志剛.人口流動與遷移//載蔡禾.城市社會學講義[C].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 :103-114.
[10] 王興周 .兩代農民工群體的代際差異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 (英文版 ),2008,(3).
[11]羅霞,王春光.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外出動因與行動選擇[J].浙江社會科學,003,(1).文軍 .從生存理性到社會理性選擇 :當代中國農民外出就業動因的社會學分析[M].社會學研究,2001,(6).
[12] 周敏.唐人街——深具社會經濟潛質的華人社區[M].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5.
曹志剛.社會網絡與城市化意識——以珠三角農民工為例[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36-48 .
Peter Karpestam and Fredrik N. G. Andersson, Economic perspectives on migration, Chapter in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Migration Studies,Edited by Steven J. Gold & Stephanie J. Nawyn, Routledge Press, 2011:pp 12-27.
[13] 馬戎.關于當前中國城市民族關系的幾點思考[J].西北民族研究,2009,(1).
馬戎.對當前中國民族政策的反思[J].青海民族研究,2013,(4).
[14] 曹志剛.人口流動與遷移//載蔡禾.城市社會學講義[C].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36-48.
[15] 劉愛玉.城市化過程中的農民工市民化問題[J].中國行政管理,2012,(1).
[16]http://zh.wikipedia.org/wiki/2011%E5%B9%B4%E8%8B%B1%E5%9 B%BD%E9%AA%9A%E4%B9%B1,2013-12 -24.
[17]http://news.ifeng.com/world/detail_2012_11/27/19573494_0.shtml,2013 -12 -24 .
[18]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2%9E%E5%9F%8E%E5%B8%82%E6%96%B0%E5%A1%98%E4%BA%8B%E4%BB%B6,2013-12-24 .
[19]賀雪峰.地權的邏輯—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向何處去[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10:301.
[20]周其仁.公民權利的城市化[J].資本市場,2013 , (4).
[21]王海光.移植與枳變—中國當代戶籍制度的形成路徑及其蘇聯因素的影響[J].黨史研究與教學,2011,(6).
[22]曹志剛.農民工的城市認同及其影響因素[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9,(1).
[23]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24-30.
[24]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57-74.
[25]Stephen Castles,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hodology and methods, Chapter in Handbook of Research Methods in Migration,Edited by Carlos Vargas-Silva,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12:pp 7-25.
[26]Stephen Castles,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hodology and methods, Chapter in Handbook of Research Methods in Migration,Edited by Carlos Vargas-Silva,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12:pp 7-25.
[27] 曹志剛.新型城鎮化道路與農民工遷移意愿[J].廣東社會科學,2014,(5).
曹志剛.新型城鎮化與農民工的梯度轉移[J].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4,(6).
責任編輯:王凌宇
There is a big crack between empirical study and theory discussion in current research of migrant workers’ urbanization because of lack of enough attention to related methodology issues, so it affects both the accumulation of research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in research.
Based on a specific clarification in the study of practical problems need to be explained in research of migrant workers’ urbanization and in the study of which practical problems that western immigration theory wants to explain, we can summarizes both the similarities in three aspects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hree aspects between them. These similarities in three aspects are motives for migratio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affecting the destination of migration, a similar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focus on the benefit to migration destination but not social justice of all the people in the destination place. These different points are the land system, the Hukou system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We can develop different direction based on the different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thes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different methodology viewpoints. We think this clarification in methodology and logic line can bring great benefit to the theory sublimation and policy design in this field.
migrant worker ; urbanization ; methodology ;framework
C912
:A
1674-4144(2016)-01-49(9)
曹志剛,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員,社會學博士。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農民工社會網絡對其遷移意愿影響研究”(編號:12CSH030);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項目“社會網絡視野中的農民工遷移意愿研究”(編號:11YJC84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