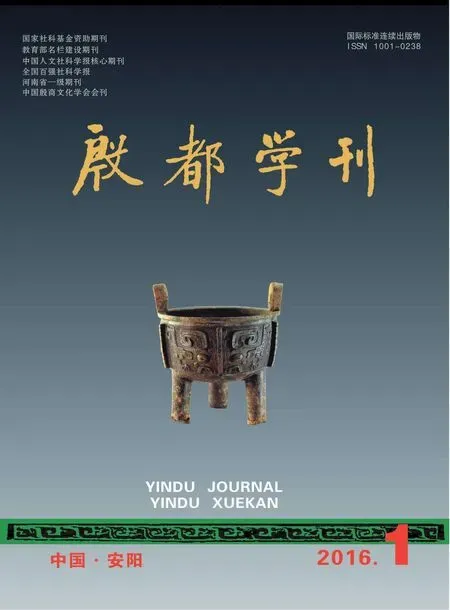司馬貞生平考辯
牛巧紅
(鄭州師范學院 文學院,河南 鄭州 450044)
?
司馬貞生平考辯
牛巧紅
(鄭州師范學院 文學院,河南 鄭州 450044)
摘要:《史記索隱》為《史記》三家注之一,后世多以其成就在其他兩家之上,然其作者司馬貞的生平一直是學界的一樁懸案。通過探尋新的文獻支持,鉤稽考索,考證出司馬貞出生于唐高宗顯慶六年與咸亨二年之間(660—671年),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年為國子博士,開元七年(719年)為弘文館學士,開元八年(721年)出任潤州別駕,不久后辭世。《史記索隱》成書應在開元之初,不晚于開元八年。
關鍵詞:史記索引;司馬貞;生平考辯
司馬貞,唐人,字子正,《史記索隱》作者。《史記索隱》是《史記》三家注中惟一有完整單行本流傳至今者,其精于校勘,勇于立言,深受后人推崇,后世多以其成就在其他兩家之上。但由于新舊《唐書》皆未為司馬貞立傳,《史記索隱》前后序言中也沒有明確的時間記載,因此司馬貞的生平身世一直是學界的一樁懸案。近代學者雖然也有一些討論,但各家觀點相去甚遠,定此從彼,良難間焉,深有重新探討的必要。
一、司馬貞生卒年月考
司馬貞生于何年?卒于何時?學界先賢大多依據《高祖本紀·索隱》“貞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碑文,其字分明作‘溫’字,云‘母溫氏’,貞與賈鷹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沈嘆古人未聞,聊記異見,于何取實也”[1]和《史記索隱后序》“然古今為注者絕省,音義亦稀……前朝吏部侍郎許子儒亦作注義,不睹其書。崇文館學士張嘉會獨善此書,而無注義。貞少從張學,晚更研尋,初以殘缺處多,兼鄙褚少孫誣謬,因憤發而補《史記》,遂兼注之……”[2]兩條史料中所涉人物的任職經歷以及生卒年代加以演繹推證。清代著名經史學家錢大昕認為:
《高祖本紀》:“母劉媼”。《索隱》云:“近有人云母溫氏,貞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碑文,其字分明作‘溫’字,云‘母溫氏’,貞與賈鷹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沈嘆古人未聞,聊記異見,于何取實也。”“鷹復”當是“鷹福”之訛,先天二年為右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以預太平公主逆謀誅。見《唐書·公主傳》。今河內縣有“大靈寺碑”即鷹福書也。徐彥伯卒于開元二年。見《唐書》本傳。貞與賈、徐諸人談議當在中、睿之世,計其年輩蓋在張守節之前矣。《唐書·藝文志》又稱貞開元潤州別駕,蓋由文館出為別駕,遂蹭蹬以終也。[3](P122)
錢先生依據《高祖本紀》中《索隱》注文,并佐以《唐書·公主傳》、《唐書·藝文志》中的相關材料,推證出司馬貞“蓋在張守節之前”,“蓋由文館出任別駕,蹭蹬以終也”。當代學者朱東潤、張玉春、應三玉等皆依其觀點。然而由于所見史料有限,錢先生的考證過程及所得出的結論皆稍嫌簡略。在錢先生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挖掘史料,并得出新的結論的應屬程金造先生和李梅訓先生。程金造先生在《史記索隱引書考實自序》中據上述《史記索隱后序》中的材料考證曰:
案《文獻通考·職官考》十四,唐崇文館屬門下省,原名崇賢館。高宗上元二年,立沛王賢為太子,避名改曰崇文館。是則張嘉會為學士,當在高宗儀鳳之后。若此際小司馬從張問學,年當在二十歲以內。上推其生年,應在顯慶、龍朔(656—661)之時也。[4]
李梅訓則認為:
至上元二年(675)八月二十七日改崇賢館為崇文館。據此,張嘉會為崇文館學士之年當在上元二年之后,即司馬貞師從張嘉會之年亦必在上元二年之后。但在這之后多少年呢?兩《唐書》不載張嘉會其人,今無從考起。但司馬貞本人既稱許子儒為“前朝”之人,又“不睹其書”,則是司馬貞師從崇文館學士張嘉會時,許子儒必已前卒,故不見其人其書……許子儒亦以學藝稱,長壽(692—694)中官至天官侍郎,弘文館學士……其自注曰:“字文舉,叔牙子也,證圣(695)天官侍郎……”準此,則司馬貞入文館當在證圣之后。古人八歲入崇小學,十五歲入太學。司馬貞自云“少從張學”,則其師從張氏之年,必在弱冠之前,假設為十八歲入文館就讀,則司馬貞之生年當在高宗儀鳳末年(676—679)。[5]
程金造、李梅訓兩位先生的考證過程皆較詳贍,也得出了更具體的結論,然而程先生認為司馬貞生于高宗顯慶、龍朔之時,即公元656—661年之間;李先生則認為司馬貞當生于高宗儀鳳末年,公元676—679年間,兩家之說相差近20年,哪一種說法更接近歷史真相,學界尚無定論。鑒于此,下文將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探求新的文獻支持,爬梳比對,鉤稽考索,以期對兩種觀點有所案斷取舍。
據上文所述,司馬貞曾經與賈膺復、魏奉古、徐彥伯等人一起以班固泗水亭長古碑文“執對反覆”,證明《高祖本紀》中的“母曰劉媼”應作“母曰劉溫”,“媼”是“溫”字誤寫。四人中的“賈膺復”,據錢大昕考證,乃《索隱》誤寫,本應作“賈膺福”,武后久視元年(700)為太子中舍人,唐睿宗景云二年(710)任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等職,玄宗先天二年(713)七月,因為與太平公主共同謀逆被誅[3](P122)。徐彥伯,據《舊唐書·徐彥伯傳》載,兗州瑕丘人,少以文章著名,武后圣歷(698)年間任給事中,唐中宗神龍元年(705)官至太常少卿,兼修國史,后出為衛州刺史。因其善理政務,不久入為工部侍郎,后又除衛尉卿兼昭文館學士。景龍三年(709),中宗李顯親拜南郊,景云初(711)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右散騎常侍、太子賓客,仍兼昭文館學士,玄宗先天元年(712)以疾乞骸骨,開元二年(714)卒[6]。魏奉古,據李梅訓考證,“開元(713)初為給事中,開元十一年(724)為長史,終官兵部侍郎。”[5]
根據徐、賈、魏三人的任職經歷及各任職階段的起始時間可以推知,徐彥伯在神龍元年(705)后不久出外任職,景云元年(710)又入京為官。這一時期,賈膺福、魏奉古也在京為官。先天元年(712),徐彥伯以疾辭官歸鄉。那么四人談論班固泗水亭長古碑文之事應在景云元年(710)與先天元年(712)之間,以景云二年(711)為宜。此時,徐彥伯、賈膺福分別為左右散騎常侍,官至從三品,[7](P459)兼任昭文館學士;魏奉古為給事中,官至正五品上。[7](P458)又徐彥伯“先天元年(712)以疾乞骸骨,開元二年(714)卒”,可見在與司馬貞等討論古碑文時其年歲已較高。司馬貞彼時與此三人交游,應該在年齡、職位、資歷方面相差不多。司馬貞在《史記索隱序》中自題為“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其中,國子博士屬國子監官員,為正五品上,司馬貞與徐、賈、魏交游時應至少已任此職。參照程金造、李梅訓上文所闡述的古人求學的一般年齡及仕宦晉升的一般過程,此時司馬貞的年齡應該不低于40歲,由此可推算出,其生年應不晚于高宗咸亨二年(671)。
另據《新唐書·劉子玄傳》載,司馬貞曾因《孝經》鄭注的行廢與劉知幾有所論辯:
開元初,(劉知幾)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為正……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8](P4520)
《唐會要·修撰》對此亦有記載:
開元七年五月左庶子劉子元上議:“今之所注《老子》,是河上公注……《漢書·藝文志》注《老子》者有三家。河上所釋,無處聞焉。王弼義旨為優。請黜河上公,升輔嗣所注。司馬貞亦注云:“《漢書》實無其人,然所注以養神為宗,以無為為體。請河王注令學者俱行。”從之。[9](P658)
據此可知,這次論辯的時間為開元七年(719)五月,論辯的結果以司馬貞為勝。《唐會要·貢舉下》載有司馬貞奏議的詳細內容,司馬貞在奏議末注明“臣等國子博士司馬貞、太學博士郄嘗通等十人對如前。”[9](P1407)可見,在開元七年(719)前后,司馬貞正處于人生得意之時,鑒于此后他又被貶出為潤州別駕一職,則司馬貞此時的年齡應不超過60歲,由此可推知,其生年應大致在高宗顯慶六年,即公元660年之后。
結合上文所述,我們認為司馬貞的生年當在高宗顯慶六年與咸亨二年之間(660—670)。
二、司馬貞求學任職考
上文有言,司馬貞在《史記索隱后序》中提到“崇文館學士張嘉會獨善此書,而無注義。貞少從張學,晚更研尋”,程金造據此推斷“是則張嘉會為學士,當在高宗儀鳳之后。若此際小司馬從張問學,年當在二十歲以內。”李梅訓也認為“司馬貞自云‘少從張學’,則其師從張氏之年,必在弱冠之前,假設為十八歲入文館就讀,則司馬貞之生年當在高宗儀鳳末年。”程、李兩位先生皆據“崇文館學士張嘉會獨善此書……貞少從張學”推測司馬貞師從張嘉會應在張任崇文館學士之間。實際上,這種推論并不充分,司馬貞寫后序時張嘉會正擔任崇文館學士一職或其官職止于崇文館學士皆有可能。筆者在拙作《司馬貞籍里考辨》中已有論證,張嘉會、司馬貞皆為吳(今江蘇與浙江一代)人,[10]在張嘉會入為崇文館學士之前,張、司二人已有淵源也是極有可能的。司馬貞以《史記》為家傳之書,自小研習,因此他所說的“少從張學”指的應該并非弱冠前后,而是更年少的階段。而司馬貞是否曾入文館就讀,恐怕還需要新的文獻支持,不能僅憑“崇文館學士張嘉會獨善此書……貞少從張學”一句妄議。
關于司馬貞生平任職經歷,前賢已有零散論述,下文將作進一步的梳理。司馬貞在《史記索隱序》中自題為“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11],《新唐書·藝文志》又載:“司馬貞《史記索隱》三十卷,開元潤州別駕”[8](P1457),可以確定,司馬貞一生曾歷任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潤州別駕諸職。需要注意的是,《唐會要》卷七十七《貢舉下》有稱司馬貞為國子祭酒者,應屬誤稱,原因有二:一,《唐會要》之外并無其他文獻稱司馬貞為國子祭酒,《冊府元龜》兩次提到司馬貞,皆作國子博士;二,據《文獻通考·職官考》載,國子博士中“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為祭酒”[7](P515),可見相比于國子博士,國子祭酒更為榮耀,然而司馬貞《史記索隱序》自屬官職時并沒有提到國子祭酒,惟一的可能就是其生平從未出任此職。
司馬貞任職的具體時間文獻也無明確記載。上文已證司馬貞在景云初與賈膺福、徐彥伯等人討論班固泗水亭長古碑文之時應已任國子博士一職,朝散大夫官職不及國子博士,司馬貞《序》中又列朝散大夫于國子博士之前,因此,任朝散大夫自然應在景云初年之前。關于其出任弘文館學士的具體時間,李梅訓有較為詳細的考證:
《新唐書·百官志二》弘文館下本注:“武德四年,置修文館于門下省,九年,改曰弘文館。……神龍元年,改弘文館曰昭文館,以避孝敬皇帝諱;二年曰修文館。……開元七年曰弘文館。”《唐會要》卷六四明書:“開元七年九月四日,依舊改為弘文館。”國子博士為正五品上,故司馬貞此時已經具備做學士資格。而弘文館名在此時亦已恢復,故司馬貞為學士殆在此時。[5]
據李梅訓先生以上推斷,司馬貞任弘文館學士不晚于開元七年(720),今從其說。至于司馬貞為何由弘文館學士出為潤州別駕,李梅訓認為與宋璟罷相有關:
新、舊《唐書·宋璟傳》載:“先是(開元七年),朝集使每至春將還,多有改變,率認為常,璟奏請一些勒還,絕其僥幸之路。又禁斷惡錢,發使分道檢括銷毀之,頗招士庶怨。俄授璟開府儀同三司,罷知政事。”據《玄宗紀》及《資治通鑒》卷二一二,宋璟罷相在開元八年正月。又如上引《新唐書·百官志三》弘文館本注,宋璟時亦為“館主”,對學士之員自有推選之權。宋璟罷相,亦必同時罷去“館主”之職。《新唐書·劉子玄傳》又謂司馬貞頗“阿意”宋璟,則司馬貞由博士出為外任,自與宋璟罷相相關。[5]
李梅訓據《新唐書·劉子玄傳》載司馬貞“阿意”宋璟,與宋璟頗有私交,推測司馬貞出為潤州別駕可能受宋璟罷相牽連,應在開元八年(721),是有一定道理的。上文有述,開元七年(720)司馬貞曾和當時的國子祭酒劉知幾有今古文之爭,根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孝經正義》記載,“開元七年今古文之爭后迨時閱三年,乃有御注太學刻石,署名者三十六人,貞不預列。”[12]司馬貞當時應該已由京官出為潤州別駕,因此不在石刻署名之列。
三、《史記索隱》成書考
唐初,在結束了魏晉至隋末的動蕩之后,統治者“鑒前代敗事以為元龜”的愿望非常強烈,十分重視史書的修撰,《史記》作為紀傳體史書的鼻祖在唐代備受推崇,在唐修《隋書·經籍志》中位列史部之首,朝野上下,為《史記》做注漸成風氣,這對司馬貞撰寫《史記索隱》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此外,司馬貞嘗自以為遷之后人,在《史記索隱》前后序言中多次申明“家傳是書,頗事討論”“家傳是書、不敢失墜”,對《史記》有著特殊的情感,自年少之時便開始研尋,終其一生未有停輟。司馬貞又曾任弘文館學士一職,掌管校正圖籍,得以接觸弘文館內所藏的大量的古籍文獻,飽覽群書,積累下扎實的史學素養,為其能夠最終完成《史記索隱》奠定了基礎。正是唐初有利的時代背景和司馬貞個人對《史記》的熱愛及其深厚史學素養的完美結合,最終成就了《史記索隱》,也成就了史注大家司馬貞。
關于《史記索隱》成書年代,程金造認為在開元初年[13],李梅訓則認為“在開元二十年左右為宜”[5],筆者認為程金造之說更接近事實。從司馬貞在《史記索隱序》中的題名來看,《史記索隱》成書之時,司馬貞已經是,而且仍然是弘文館學士,因此《史記索隱》的成書必然不會晚于開元八年。另外,史記三家注中另外一注《史記正義》在《序》中言明“開元二十四年八月,殺青斯竟”,可知《史記正義》成書在開元二十四年。雖然其作者張守節在文中并未明確提到司馬貞《史記索隱》,然而通過爬梳其具體內容可知,《正義》確有疏解《索隱》之處。則張守節作《史記正義》時,《史記索隱》已流布較廣。考慮到古人信息傳播的不便利,我們有理由認為此時距《史記索隱》成書應已有一段時間。因此,李梅訓先生認為其成書“在開元二十年左右”之說似不合情理。加之司馬貞景云初年(711)與賈膺復、魏奉古、徐彥伯等討論班固泗水亭長古石碑文時,《史記索隱》尚未完成,則可推定《史記索隱》成書應在景云初年(711)以后,開元八年(721)以前,因此程金造之說蓋得其實。
至于司馬貞卒于何時,由于文獻資料缺乏,不得其詳,錢大昕先生認為其“蓋由文館出為別駕,遂蹭蹬以終也”[3](P122),今姑且從之。
四、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司馬貞生于高宗顯慶六年與咸亨二年之間(660—671)。曾任朝散大夫一職,睿宗景云二年(711)前后為國子博士,開元七年(719)為弘文館學士,開元八年(721)受宋璟罷相所累出為潤州別駕,之后不久辭世。司馬貞以《史記》為家傳之書,少從張學,晚更研尋,一生未有停輟。在唐代統治者以“鑒前代敗事,以為元龜”為指導思想的學術背景下,司馬貞集其畢生所學為史做注乃成《索隱》。《史記索隱》前承《集解》,后啟《正義》,代表了我國古代《史記》箋注的最高水平,其成書應在開元之初,至遲不晚于開元八年(721)。
[參考文獻]
[1]司馬貞.史記索隱.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342.
[2]司馬貞.史記索隱后序.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10.
[3]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
[4]程金造.史記索隱引書考實自序[M].北京:中華書局,1998.
[5]李梅訓.司馬貞生平著述考[J].安徽師范大學學報,2000,(1):109-111.
[6]劉昫等.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2005.
[7]馬端臨.文獻通考[M].北京:中華書局,1986.
[8]歐陽修,宋祁.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9]王溥.唐會要[M].北京:中華書局,1955.
[10]牛巧紅.司馬貞籍里考辯[J].大家,2012,(20):6-8.
[11]司馬貞.史記索隱序.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7.
[12]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M].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646.
[13]程金造.史記管窺[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5.181.
[責任編輯:康邦顯]
中圖分類號:K2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0238(2016)01-0117-04
[作者簡介]牛巧紅(1977-),女,鄭州師范學院文學院講師,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國古典文獻學和語言學。
[收稿日期]2015-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