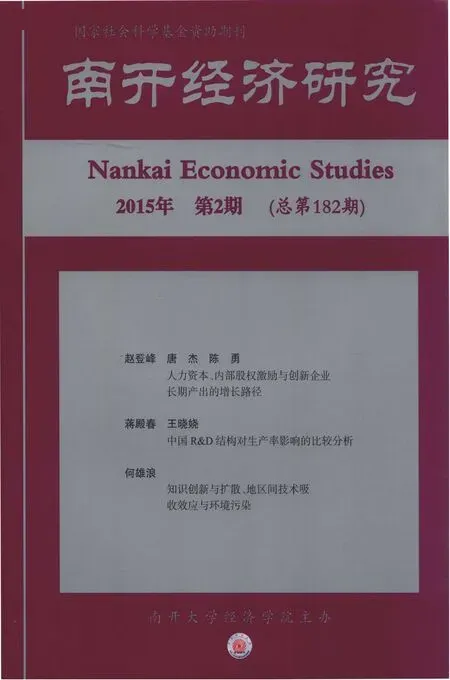腐敗與企業創新:潤滑劑抑或絆腳石
李后建 張 劍
一、引 言
腐敗是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問題。通常地,在經濟學研究中,腐敗是一種政治腐敗或官員腐敗,它是指政府官員“為牟取私利而濫用公共權力或權威”的行為(Rodriguez 等,2006)。盡管大量的文獻研究已經證實,控制腐敗有利于促進外商直接投資(Lambsdorff,2003,a;Mauro,1995)、提高生產率(Lambsdorff,2003,b;Rivera-Batiz和Democracy,2002)和拉動收入增長(Kaufmann 和Kraay),但有關腐敗與企業創新之間的關系在現有研究中并未引起足夠關注。
腐敗究竟是企業創新的潤滑劑還是絆腳石?厘清這一問題對推動中國經濟成功轉型具有重要意義。對照中國的發展實踐可知,自改革開放以來,雖然中國經濟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被世人譽為“增長奇跡”,但造就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主要因素并非技術創新,而是建立在“政治晉升錦標賽”激勵機制下的高儲蓄和高投資(周黎安,2008)。從長遠來看,這種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絕非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不竭動力,相反地,它不僅造成中國自然資源的嚴重透支,使整個社會背負高昂的環境代價,而且加劇了中國經濟結構的失衡。由此可見,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從“要素驅動型”向“創新驅動型”的轉變已是大勢所趨且迫在眉睫。然而,當前中國正式制度并未完全確立,市場運行機制尚存在明顯的分割與扭曲,企業創新缺乏有效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特別地,政府主導的資源配置方式為權力尋租和消極腐敗提供了生存空間。毋庸置疑,企業創新成果排他性弱。如果政府相關部門不能在短期內全面改善當前的制度環境,那么企業創新成果極易被競爭對手復制模仿而使得創新所帶來的壟斷利潤被侵蝕殆盡。由此可知,在當前的制度環境下,理性的企業通常不會將創新作為其獲得市場競爭優勢的占優策略。一旦將創新作為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一項重大的戰略決策,那么創新企業便有強烈的動機通過非正式支付等各種方式尋求政府庇護,以減少市場機制不完善對企業創新的傷害(Chen 等,2011)。不僅如此,非正式支付還可以幫助企業規避一些無效率的政府管制(例如行政壟斷),減少繁文縟節(red tape),提高了企業創新效率。同時,腐敗官員既是索賄受賄行為的主體,也是出售政府庇護的壟斷者。出于理性,他們只可能為賄賂額度最高的企業提供政府庇護。值得說明的是,建立在賄賂基礎上的政府庇護協議并不具有強制執行的法律基礎,這使得收受賄賂的腐敗官員極有可能不兌現事先的承諾(事后機會主義行為),反而索要更多的賄賂。因此,腐敗也可能是企業創新的“絆腳石”,從而阻礙中國經濟轉型的步伐。更為重要的是,在當前的制度環境下,理性的企業更樂意通過賄賂等腐敗活動來享受腐敗官員授予的市場壟斷特權,這勢必壓制企業創新精神(Aidis 等,2008;李后建,2013)。此外,現有文獻指出,腐敗有可能阻礙了對企業的知識產權保護,降低了企業研發投資的效率,弱化了企業創新激勵機制的作用(Claessens 和Laeven,2003)。
以上論述表明,在轉型的經濟體中,對于企業創新而言,腐敗很有可能同時扮演了“潤滑劑”和“絆腳石”的角色,究竟哪種角色占據主導,目前鮮有文獻對此進行恰當評判(Goedhuys,2008)。為了深入考察腐敗與企業創新之間的關系,我們利用2012年世界銀行關于中國企業運營制度環境質量的調查數據,以企業非正式支付占年銷售額的比例衡量腐敗程度,以新產品或服務占年銷售額的比例衡量企業創新,我們得到了以下結論。第一,腐敗與企業創新之間是一種倒U 型曲線關系,即一定程度的腐敗有利于企業創新,而更高程度的腐敗則抑制了企業創新。第二,不同企業產權性質下,賄賂等腐敗活動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具有顯著差異。第三,我們揭示了腐敗影響企業創新的兩種渠道:政府擔保(政府訂單)和銀行信貸。
本文的研究從以下幾個方面豐富和拓展了現有文獻:首先,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本文的研究豐富了經濟學者關于制度質量影響內生經濟增長的文獻,有助于我們解開中國的“腐敗與長期經濟增長共存之謎”。對腐敗影響企業創新渠道的分析表明,腐敗客觀上有助于企業獲得政府庇護和爭取金融機構貸款,從而為企業創新提供了便利。與此同時,我們的研究也表明,更高程度的腐敗會抑制企業創新。我們的研究揭示的是腐敗與企業創新之間有著顯著的倒U 型曲線關系,與現有的兩種觀點:腐敗是企業創新的“潤滑劑”抑或“絆腳石”都不相同,即腐敗并非絕對有害,也非絕對有利,它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取決于腐敗的渠道。其次,我們探討了不同企業產權性質下賄賂等腐敗活動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有助于進一步理解在所有制歧視的狀況下,賄賂等腐敗活動對企業可持續發展重要性的差異。最后,本文從腐敗的角度加深了對中國經濟轉型的理解,為我們正確理解在正式制度缺位的情況下,腐敗對中國經濟轉型的作用機制提供了經驗證據。
二、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設
(一)腐敗與企業創新:潤滑劑抑或絆腳石
為了追求利潤,企業無論規模大小,都渴望通過引進新產品、服務或技術來獲得市場競爭優勢。這使得企業持續地進行創新,從而推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而企業創新便成為一種社會價值活動(Boldrin 和Levine,2004)。這也是“企業追逐私利的過程提高了全社會福利”的經典案例。對于發展中國家,尤其是處于經濟轉型期的新興發展中國家而言,市場機制不健全不僅增加了企業創新的制度成本,而且還為機會主義盛行開了方便之門。李后建(2013)針對中國30 個省級區域1998 年至2009 年的面板數據利用門檻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發現腐敗對企業創新的打擊力度會隨著市場化進程的推進而呈現出非線性的變化。Aidis 等(2008)的研究表明,在市場機制并未完全確立的經濟體中,在位企業通常會通過伴有非法支付的尋租行為獲得市場特權,從而壟斷市場,并抑制企業創新,最終損害社會福利。由此可見,在上述經典案例的背后,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唯有健全的市場機制才能保證所有企業在追逐私利最大化的同時也能實現全社會福利的提升。在本文中,我們主要關注的是在市場機制不健全的經濟體中腐敗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幾項經典的研究針對不同環境下腐敗與企業創新的關系展開了理論論證。Murphy 等(1993)認為公共尋租活動(例如腐敗或游說)限制了企業創新。這是因為公共尋租活動使得創新面臨著更高的風險、不確定性和脆弱性。然而,上述情景是基于以下兩個關鍵的假設:首先,創新僅僅局限于潛在競爭者;其次政府官員擁有賄賂需求的壟斷權力。Blackburn 和Forgues-Puccio(2009)的研究放松了上述基本假設,他們的研究結論表明腐敗對創新的影響取決于實施尋租行為的政府官員間的協調程度。因此,有組織腐敗網絡的國家很可能出現腐敗與創新共同繁榮的景象。從理論和實證的結果來看,針對腐敗與企業創新之間關系這一研究主題,經濟學家們形成了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腐敗是“潤滑劑”,有助于企業規避無效率的政府管制,提高企業創新效率(Aidt 和Dutta,2008);第二種觀點則認為腐敗是“絆腳石”,會扭曲資源配置,阻礙企業創新(Mauro,1995;Aidis 等,2008)。以下就這兩種觀點分別進行闡述并據此建立本文的研究假設。
1. 腐敗是企業創新的“潤滑劑”
在本研究中,我們使用失范和制度理論來發展研究假設,因為這一理論強調了制度環境和規則對企業戰略的重要性,例如企業的創新戰略(Martin 等,2007)。失范理論(Durkheim,1897)表明成功的壓力能夠取代規范的控制機制,并提供用于驗證企業倫理和戰略決策是否平衡的重要工具(Martin 等,2007)。制度理論被用于為企業戰略提供見解(Mike 等,2009)。此外,腐敗很有可能是現存制度環境的一種均衡結果(Vaal和Ebben,2011)。
失范描述的是一種扭曲的環境,而在這種環境中,個體通常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失范理論假定個體和企業都以目標為導向,并且在監督機制缺失的情況下,個體和企業都傾向于使用非法手段獲得成功(Merton,1938)。在社會層面上,失范為制度對這種扭曲行為的影響提供了一個經典的社會學解釋。從本質上而言,失范是各類社會經濟活動偏離整個社會普遍認可的社會規范、規則和慣例而導致的后果。當賄賂成為企業成功的先決條件時,企業將面臨著當地失范的壓力(Martin 等,2007)。為適應市場經濟秩序的失范,越來越多的企業致力于應對失范,這也使得通過賄賂來獲得成功的企業也越來越多,此時腐敗便可能成為企業生存的重要法則。轉型經濟體為我們探索失范和制度發展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實驗環境。尤其對處在經濟轉型的中國而言,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都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變化,可以預知,這些變化將會導致社會價值與目標發生深刻的變化,而這種深刻的變化需要新的系統、流程和基礎設施來匹配社會結構的變化。
Leff 首次識別了失范經濟體中,腐敗可能影響企業創新的機制。他認為,在失范的經濟環境中,經濟和政治派系之間有著密切的長期關系,而這種關系會破壞正常的市場競爭環境。腐敗有助于企業應對主要由政治因素導致的不確定性和風險(Leff,1964)。考慮到體制變化的頻率和政策的不連貫性,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政府行為對投資者而言是一個主要的潛在風險(Acemoglu 和Verdier,2000)。因此,如果企業致力于創新,那么它們愿意支付賄賂來確保它們未來的事務免受不利干擾(Leff,1964)。在市場機制不完善(失范)的經濟體中,當腐敗有助于企業規避繁重的監管要求時,它通常被視為一種次優選擇(second-best option)。腐敗的“潤滑劑”假說指出,賄賂等腐敗活動雖然增加了企業的交易成本,但有助于企業規避官僚體制中的繁文縟節(red tape)(Leff,1964)。Lui(1985)在其提出的排隊模型中指出,在企業和官員的非合作博弈過程中,賄賂額度與企業機會成本有關,更高效的企業更愿意提供較高額度的賄賂來規避繁文縟節。因此,賄賂通常被視為“速辦金”,它可以節約企業為獲取許可證和辦理相關手續所需的大量等待時間。Qian 和Xu(1998)認為,政府官員為了有效地抽取租金,傾向于故意延遲(deliberate delay)許可證頒發,當企業為了盡快地獲取許可證而向官員提供的賄賂額度超過其最大化的賄賂預期值時,政府的故意延遲行為才能得到緩解(Acemoglu 和Verdier,1998)。正如拍賣一樣,建立在賄賂額度基礎上的許可證授予或官方授權能夠實現帕累托最優配置。因此,腐敗使得政府官員在經濟體中引入了有效率的制度安排(Acemoglu 和Verdier,1998),也即賄賂提供了一種有償服務的制度安排從而改善了企業創新效率。對于處在轉型時期的中國而言,由于相關市場機制并不完善,再加上創新成果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故而企業創新面臨著巨大的風險,包括創新成果被當地政府征用的政治風險以及被競爭者競相復制模仿而致使創新活動收益流失的風險等。這使得致力于創新的企業更傾向于賄賂當地官員以盡快獲得政府提供的許可證和官方授權。由此可見,企業賄賂通常是對正式制度缺失的一種彌補,它有利于企業通過非正式的方式尋求政府庇護,規避正式制度缺失給企業創新帶來的諸多風險。毋庸置疑,企業創新是一個長期過程,它始于一種理念或智慧,經過幾輪投資周期,最終形成提升消費者幸福感的新產品或服務。在企業創新這個漫長的過程中,企業難免與公職人員進行互動(包括審批、許可和執照等)。由此推測,在失范的經濟環境中,這一互動過程必須有足夠的賄賂保證,才能使得企業的相關業務得以順利開展。
此外,由于信貸市場并不完美,企業創新通常受限于融資約束。其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將企業創新成果轉化為產品,從而實現商業價值,需要經過較長的孕育期,再加上其固有的風險,這使得外部投資者很難識別出企業創新項目的優劣;第二,企業外部融資需要給外部投資者提供更多更準確的信息,而有關創新戰略實施信息的披露可能會導致其他企業模仿,提高創新成本,這使得創新企業信息披露并不充分,且無法獲取外部融資(Bhattacharya 和 Ritter,1983);第三,為了減少信息不對稱問題,投資機構通常的做法就是要求借款人提供相應的抵押品。對于創新企業而言,這樣的要求似乎并不現實。因為在企業創新活動中,大部分研發支出的形式都是工資薪金,而非可以作為抵押品的資本物品(Hall 和Lerner,2010)。因此,在信息嚴重不對稱的情況下,企業創新活動的風險規避和私人信息會引發道德風險問題,這會使得謹慎的外部投資者對企業創新活動的投資失去興趣,從而使得企業創新活動陷入嚴重的融資困境。然而,致力于創新的企業可以通過賄賂的方式與當地官員建立起紐帶關系(包括政治關聯、金融關聯等)。這種紐帶關系不僅是企業創新獲取各種資源的重要渠道(余明桂和潘紅波,2008;Adhikari 等,2006;Yeh 等,2013),而且還是一種重要的聲譽機制和企業擔保貸款的重要資源。因此,與當地政府有紐帶關系的企業通常能夠分享到政府部門的外部網絡資源,從而獲得數量更多、成本更低的信貸資源,能緩解企業創新所面臨的融資約束。換言之,在市場機制不完善的經濟體中,腐敗可以起到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即腐敗是對市場機制運轉不暢的一種市場反應。其結果是將相關資源轉移至最需要的流動部門,從而提高了企業創新效率。基于上述探討,我們認為賄賂等腐敗活動對企業創新具有積極影響。因此,建立研究假設H1。
H1:賄賂等腐敗活動對企業創新具有積極影響。
2. 腐敗是企業創新的“絆腳石”
首先,如果腐敗能夠起到潤滑“商業車輪”的作用,那么腐敗可以減少政府與企業之間垂直交易的交易成本。然而,愈來愈多的理論與實證證據傾向于支持相反的觀點,強調腐敗會抑制企業創新,即腐敗是企業創新的“絆腳石”(Rose-Ackerman,1999;Svensson,2003;Shleifer 和Vishny,1993)。其主要觀點是普遍存在的腐敗可能扭曲了資源配置,這是因為相對于企業創新等生產性活動而言,腐敗增加了非生產性尋租活動的回報(Baumol,1990)。同樣地,腐敗也會影響企業家才能的配置。在腐敗水平較高的環境中,企業家可能更致力于謀求寶貴的許可證和優惠的市場準入條件,而非生產率的提高(Murphy 等,1991)。當企業家才能直接配置到生產性活動時,企業創新活動的可能性會增加,同時也會伴隨著企業生產率的提高。相比之下,當企業家才能配置到政府抽租行為(rent extraction)時,企業家才能回報則通過挪用財富而非創造財富實現最大化(Murphy 等,1993;Acemoglu 和Verdier,1998)。在腐敗水平較高的環境中,既得利益者通常會反對競爭者采納新技術,因為他們將競爭者采納新技術的行為視為對他們特權地位的一種威脅和挑戰,這使得他們極力推崇其掌控的舊技術,而刻意壓制競爭者新技術的采納(Krusell 和Rios-Rull,1993)。由此可見,腐敗會形成事實上的進入壁壘,從而破壞公平有序的市場競爭環境,打擊企業家精神(李后建,2013;Alesina 等,2005)。此外,政府官員的自由裁量權會增加征收風險的概率,從而降低企業創新活動的投資回報(Alchian 和Demsetz,1973)。這會進一步降低企業家創新行為的激勵水平,強化低效企業致力于腐敗活動的動機。更為重要的是,腐敗有利于在位企業獲得市場特權并對新生企業進行打壓,從而壟斷市場,抑制企業創新活動(Aidis,2008)。同樣地,也有大量研究對腐敗的“潤滑劑”假說提出了質疑(Lien,1986;Beck 和Michael,1991)。盡管賄賂等腐敗活動能夠使得制度成本內部化,但它并未考慮到制度剛性的內生性(Ahlin 和Bose,2007)。事實上,Tanzi(1998)認為當規則被用于抽取賄賂時,更多的規則便會接踵而至。Guriev(2004)強調賄賂會給腐敗官員提供制定更多繁瑣規則的足夠激勵,這顯然妨礙了資源的有效配置,提高了企業創新的交易成本。Ahlin 和Bose(2007)提供的理論證據表明,如果妨礙資源有效配置的規則是內生的,那么企業賄賂只可能導致更多低效的規則,從而妨礙資源的有效配置,提高企業獲取相關資源的交易成本。同樣地,賄賂對企業創新的影響也如此。因為,在沒有賄賂的情況下,政府官員會根據事先制定的審批條款對企業創新項目進行審批,從而確定資源配置結構,此時企業創新所需資源配置的交易成本取決于當前制度安排的質量。然而,在企業競相提供賄賂的情況下,腐敗的政府官員有足夠的激勵制定更多繁瑣的審批條款以抽取更多的賄賂。此時,創新項目存在巨大風險的企業為了躲過政府的審批程序會通過更高額度的賄賂來競取政府資源配置的機會。如此下去,那些潛在價值巨大的創新項目通常較難獲得資源配置的機會而被迫終止,因此有強烈創新意愿的企業會由于賄賂等腐敗活動對資源配置環境的破壞而遭受巨大的打擊。
其次,由于建立在特定額度賄賂基礎上的資源配置協議是腐敗政府官員的事后承諾,它具有強烈的事后機會主義性質。這是因為賄賂等腐敗活動是非法的,因此建立在特定額度賄賂等腐敗活動基礎上的非正式契約并非法律保護的需要強制執行的條款,即上述非正式契約缺乏法律保護的基礎,這也使得上述非正式契約并非穩定和持久有效。正如Shleifer 和Vishny(1993)所言,建立在腐敗基礎上的協議能否事后兌現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因此,在腐敗的環境中,即使腐敗政府官員利用有關資源配置條款的自由裁量權向相關企業索取了特定額度的賄賂,也不能保證他們就能立即兌現事后承諾。尤其是在多重利益約束機制之下,這些受賄的政府官員很有可能在事后難以實現先前達成的提供有關資源或政府庇護的非正式契約。由此,賄賂被視為“速辦金”的假說也遭到了諸多學者的質疑(Andvig,1991)。他們認為,政府官員在收受賄賂之后可能并不會信守承諾,反而會延緩工作效率,從而索要更多的賄賂,即表現出“敲竹杠”的行為。由此可見,腐敗通常具有任意性(Rodriguez 等,2006)和事后機會主義性質(Luo,2004)。因此,企業在創新活動過程中如何規避腐敗帶來的諸多風險就變得更加困難和昂貴(Anokhin 和Schulze,2009)。由此可知,腐敗就如同一種不可預見的隨機性稅收,它不僅提高了企業創新活動的交易成本,而且分散了企業家實施創新戰略的精力(Anokhin 和Schulze,2009)。
最后,賄賂等腐敗活動會阻礙資源配置市場化改革的進程,妨礙資源配置的市場有效性,增加企業創新的交易成本。由于資源配置市場化制度的確立會導致“租金耗散”,因此在既得利益的誘惑下,收受賄賂的政府官員必定會抵抗關鍵資源配置市場化制度的確立。更重要的是一旦當前低效的市場制度可為其帶來賄賂,他們則希望有更多類似的低效市場制度能夠出現。進一步地,當政府官員意識到延遲資源的配置可以為其帶來賄賂時,其會為了收受更多的賄賂而傾向于更長時間的資源配置延遲,并減少政府庇護的提供。這顯然會阻塞企業創新獲取關鍵資源和政府庇護的正常渠道。正如Murphy 等(1993)所言,若將賄賂等腐敗活動歸于競租活動,那么賄賂等腐敗活動將會破壞正常的市場運作秩序,從而扭曲市場對資源的有效配置。事實上,建立在賄賂等腐敗活動基礎上的資源配置和政府庇護并不必然將相關資源和庇護配置到最具創新能力的企業,這是因為根據“贏者的詛咒”(winner′s curse)理論,愿意支付最高額度的企業并不必然為致力于創新的企業,而是最成功的尋租者。一個重要的觀點是建立在賄賂等腐敗活動基礎上的資源配置增加了企業創新的成本負擔,有可能將致力于創新的企業排斥在關鍵資源配置的對象之外,而使得致力于非生產性活動的企業掌握豐富的資源,極大地扭曲了資源配置的路徑,妨礙了企業創新活動。基于上述探討,我們認為賄賂等腐敗活動對企業創新具有消極影響。因此,建立以下研究假設H2。
H2:賄賂等腐敗活動對企業創新具有消極影響。
(二)腐敗與企業創新:所有權的影響
企業創新通常被視為一種動態交互學習與積累的過程(Lundvall,1998)。制度因素通常決定著新技術創造所需資源的配置效率,從而對企業創新活動有著深刻的影響。在推動企業創新活動的過程中,政府部門往往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Haggard,1994)。眾所共知,一些國家的政府針對科學與技術的發展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以激發企業參與學習與創新活動的積極性。這些政策工具包括戰略性產業R&D 投資便利化、政府對研究機構的資助計劃、專利法律法規體系的建立與完善、國外先進技術的引進計劃以及國家戰略項目發布計劃等。
國有控股企業,憑借與政府的天然聯系更容易優先享受國家給予的相關政策優惠,從而獲取企業創新活動所需的各種資源,有助于企業創新活動的順利開展。與政府有著天然聯系的國有控股企業能夠優先獲得政府支持,強化企業創新成果的競爭性和排他性,降低企業創新活動成果被復制和盜取面臨創新收益被嚴重侵蝕的風險。國有控股企業通常與政治有著緊密的關系,相互信任和有效溝通有助于企業順利地通過研發立項、審批以及研發活動中的報批和審批手續,減少了政府和執法部門的頻繁檢查和刁難,有助于降低企業創新活動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由此可見,國有控股企業這些天然優勢可以減少其通過賄賂等腐敗活動這種非正式手段來推動企業創新(唐清泉,2011)。
從另一方面而言,在國有控股的情況下,實際控制人通常為企業高級管理人員,他們的任免過程并不是從人力資源市場競爭產生而是通過政治過程決定,由政府任命,任期較短,變數較大,并且領取的是固定薪酬,剩余索取權由國家所有。作為理性的“經濟人”,他們的目標函數更多地體現在職務待遇和晉升機會上,力求短期內業績穩定,而不是歷經數載的企業創新,最終釀成“前人栽樹,后人乘涼”的“悲劇”,從而錯失升遷之機會。這會促使國有控股企業高管理性地選擇風險厭惡策略,排斥企業創新活動。更重要的是,國有控股企業通常將社會和政治目標界定為企業的最終目標而并非是利潤最大化。因此,國有控股企業承擔了更多的政策性任務。在當前的制度環境下,政治晉升競標賽使得大量的政策性任務具有急功近利的特點,這客觀上要求國有控股企業將投資目標集中于見效快的政績項目,而放棄孕育周期長、風險大的研發項目。
對非國有控股企業而言,復雜的市場環境給它們的生存帶來了極大的挑戰,若不通過創新來抓住市場機會,適應競爭環境變化,非國有控股企業恐難生存下去。Choi等(2011)認為非國有控股企業致力于創新活動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非國有控股企業為了致力于企業的穩定和持久的競爭優勢,它們更傾向于投資R&D 這樣的長期項目,而不是利潤最大化的短期項目;其二是非國有控股企業的員工希望通過技術創新與企業建立長期穩定的勞動關系。由此可見,非國有控股企業通常對市場動態更加敏感,但是它們對來自政府的制度壓力缺乏敏感(Peng,2004)。相對而言,非國有控股企業通常很難獲得政府提供的大量資源和扶持,因此在轉型經濟體中,它們的運營通常面臨著緊張的預算(Tan,2002)。更重要的是,在轉型經濟體中,非國有控股企業面臨著最糟的制度環境。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正式的規則和良好的商業慣例(Ju 和Zhao,2009),非國有控股企業創新面臨著巨大的風險。為了規避風險,非國有控股企業需要通過賄賂等方式獲得政治身份,希望通過政治身份這一渠道獲取政府提供的大量資源和扶持,以便為創新活動提供必要的物質條件。同樣地,非國有控股企業也具有通過賄賂等腐敗活動來尋求政府庇護的強烈愿望,以防創新收益被競爭者侵蝕殆盡。由此可見,在轉型經濟體中,非國有控股企業由于缺乏天然的政治優勢,再加上正式制度的缺失,這使得賄賂等腐敗活動可能成為這些企業順利開展創新活動的重要因素。基于上述探討,我們提出研究假設H3。
H3:相對于國有控股企業而言,腐敗對非國有控股企業創新的影響更加強烈。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樣本與數據來源
我們使用的數據來源于2012 年世界銀行關于中國企業運營的制度環境質量調查。這次共調查了2848 家中國企業,其中國有企業148 家,非國有企業2700 家。參與調查的城市有25 個,分別為合肥、北京、廣州、深圳、佛山、東莞、石家莊、唐山、鄭州、洛陽、武漢、南京、無錫、蘇州、南通、沈陽、大連、濟南、青島、煙臺、成都、杭州、寧波、溫州。涉及到的行業包括食品、紡織、服裝、皮革、木材、造紙、大眾媒體等26 個行業。調查的內容包括控制信息、基本信息、基礎設施與服務、銷售與供應、競爭程度、生產力、土地與許可權、創新與科技、犯罪、融資、政企關系、勞動力、商業環境、企業績效等。這項調查數據的受試者為總經理、會計師、人力資源經理和其他企業職員。調查樣本根據企業的注冊域名采用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獲取,因此調查樣本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在本研究中,有效樣本為1748 個,這是因為我們剔除了一些指標具有缺失值的樣本,例如就腐敗指標而言,選擇“拒絕回答”和“不知道”的樣本分別178 個和255 個,同時還有60 個樣本就腐敗而言沒有作任何反饋,因此我們在研究過程中將這些樣本予以剔除。需要說明的是,在回歸過程中,我們對連續變量按上下1%,的比例進行Winsorize 處理。
(二)計量模型和變量定義
為了考察腐敗以及其他因素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我們遵照相關文獻的經驗做法(Goedhuys,2007;Lederman,2010),將本文的基本的計量回歸模型設定如下:

在模型(1)中,innovi表示第i 個企業的創新行為。由于企業創新活動是一項領域非常廣泛,內容非常豐富的實踐活動,因此要完整地測量企業創新行為并非易事。早在20 世紀30 年代,熊彼特就列舉了五類創新活動:(1)生產新產品;(2)引進新方法;(3)開辟新市場;(4)獲取新材料;(5)革新組織形式等。Lin 等認為評價企業創新行為之前必須首先區分創新投入和創新產出(Lin 等,2011)。關于創新投入,廣泛使用的指標是R&D 投資決策和R&D 強度(Coles 等,2006;Chen 和Miller,2007)。主要是因為這些指標較容易從企業財務報表中摘取,且易于理解。不過,這些指標的潛在缺陷是它們無法捕捉到企業的創新產出。基于此,使用企業創新產出指標可以彌補這一缺陷。關于創新產出指標,應用得比較廣泛的有專利授權量(Argyres 和Brain,2004;Lerner 和Wulf,2007)、專利前向引用(Hall 等,2011;Lerner 和Wulf,2007)和新產品銷售比例(Lin 等,2011;Czarnitzki,2005;Cassiman 和Veugelers,2006)。在本文中,我們運用創新產出來度量企業的創新行為。遵循Chen 和Miller 的做法,創新產出被度量為近三年內企業是否引入了任何新產品或服務,若引入了新產品或服務,則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其次創新產出被定義為2010 年內企業引入的新產品或服務銷售額度占年度銷售總額的百分比(Chen 和Miller,2007)。新產品和服務是企業生存的基礎(Smith et al.,2005)。引入新產品或服務提高了企業滿足新市場需求的能力并助其在新技術競爭的格局中確立地位(Li et al.,2013)。為此,大量文獻將企業引入新產品或服務作為度量企業創新的關鍵指標(Li et al.,2013;Smith et al.,2005)。這是因為企業引入新產品或服務是企業產品創新的一種表現形式,是企業創新活動的重要體現,也是熊彼特所定義的企業創新類型之一。
bribei表示第i 個企業的腐敗程度。腐敗本是道德與法律上不容許的行為,因此腐敗具有隱蔽性和非公開等性質,這使得腐敗的準確度量顯得非常棘手(Banerjee 等,2013)。早期的研究文獻通常采用腐敗評價指數來衡量腐敗程度,例如腐敗感知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CPI)、行賄指數(Bribe Payers Index,BPI)、行政腐敗指數(Administrative Corruption Index,ACI)、國家俘獲指數(State Capture Index,SCI)等,而這些評價指數可能會受到文化、心理因素的影響而容易產生腐敗信息偏差。后來,部分研究者建議采用貪腐瀆職涉案人數占當地公職人員數的比例(人/萬人)來衡量各地區的腐敗程度(李后建,2013;陳剛和李樹,2012)。由于腐敗行為是一種隱蔽性和非公開性行為,因此該指標也就無法真實反映出各地區的腐敗水平①因為當年的貪腐案件數并不意味著這些貪腐行為是當年發生的,而有可能是多年前(跨省)發生的,而只不過是這些腐敗行為在當年被查處出來了,因此用貪腐案件涉案數并不能準確反映出本地當年的腐敗水平。。為此,我們使用企業非正式支付(informal payment)的總額占年度銷售額的百分比來度量企業的腐敗水平。Lewis 認為非正式支付是指在正式渠道以外向個人支付的金錢以及提供的禮品或服務等。他同時指出非正式支付與賄賂、灰色支付、腐敗活動、酬金等描述的是同一類現象(Lewis,2001)。當然,在不同的情境下,非正式支付定義并不相同,然而它被公認為是一種腐敗,這是因為非正式支付通常是直接向公職人員付款以獲取某種權利,因此它在某種程度上也屬于“公職人員追逐私利”的范疇(Lewis,2007)。世界銀行提供了一套衡量腐敗直接成本的指數,即The Graft Index。該指數的具體含義是指企業為了順利開展相關生產經營活動,向政府官員提供的非正式支付,這項指數可以作為衡量市場中腐敗的指數。事實上,大多數學者將非正式支付視為腐敗的一種表現形式(Bardhand,1997),即雙方關系中只包含物質利益,并以直接且即時的非正式支付為特征,這種交換則被歸于賄賂行為的行列,同時也被視為一種流行的腐敗行為(Yang,1989)。喬爾·赫爾曼等(2009)也用該指數定義和分析了行政腐敗。通常而言,企業非正式支付包括禮物、宴請和贈送現金等項目,這些項目的目的包含著物質利益,是企業為了達到某些眼前的目標而采用的一種非正式競爭手段,從表面來看它可能遵循了禮物的形式,但它的內容是一種賄賂而非禮物交換。由此可見,在本文中,非正式支付實際上是對企業賄賂額度的度量,直接體現了企業層面的腐敗水平。我們在模型(1)中加入腐敗的二次項,這樣不僅可以度量腐敗對企業創新的平均效應,而且還可以度量腐敗對企業創新的邊際效應。εi表示的是誤差項。
Zi表示控制變量向量,包括企業層面和企業所在城市層面兩個維度的控制變量。企業層面的控制變量包括:
(1) 企業規模(lnscale)。與以往研究文獻一致的是,我們仍使用企業員工人數的自然對數作為企業規模的度量指標(Abdel-Khalik,1993)。之所以將企業規模納為控制變量,其原因在于以往研究認為企業規模是影響企業創新的重要因素(Cohen 等,1987;Jefferson 等,2006)。通常而言,企業規模越大,企業的規模效應和聲譽優勢就越明顯,則企業越有可能獲得創新所需具備的各種條件,同時更有能力應對創新所帶來的諸多風險。
(2) 企業年齡(lnage)。企業年齡定義為2012 年減去企業創始年份并取其對數。關于企業年齡對創新的影響,目前的文獻對這一問題并未達成一致(Huergo 和Jaumandreu,2004)。因為年輕的企業和成熟的企業在創新上各有優劣勢,年輕企業的優勢在于它們易于接受新的思想和方法,而劣勢在于它們創新失敗的風險可能要大于成熟企業,這是因為相對于成熟企業而言,年輕企業的市場經驗顯得相對不足,且要面臨著各種資源的約束。
(3) 國有股份比例(soe)。國有股份比例定義為所有制結構中國有股份所占的比例。由于國有企業的實際控制人通常是各級政府機構,國有企業與地方政府之間有著天然聯系。“政府庇護”理論表明,地方政府官員能夠對國有企業施加更多的影響,從而獲取政治收益和私有收益(Shleifer 和Vishny,1993)。因此,國有企業必須附庸地方政府,并助其實現相應的政治和社會目標。這意味著國有企業的相關行為被限定在地方官員政治偏好之下。由此,控制住國有股份比例,有利于我們捕捉地方政府政治偏好對企業創新的干擾效應。
(4) 市場競爭程度(compet)。市場競爭程度定義為企業就非正式部門競爭者的行為對其營運影響的評價,根據影響程度的高低,依序賦值為0 至4。以往研究表明,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中,企業若要鞏固市場地位或擴大市場份額,那么企業必須持續地進行產品改進和過程創新,這將激勵企業進行更多的創新活動(Boone,2001)。
(5) 企業出口(export)。企業出口定義為若企業所有的產品都在國內銷售,則賦值為0,否則賦值為1。近些年來,出口與企業創新之間的關系得到了諸多學者的廣泛關注。事實上,最近的理論文獻顯示,出口與創新之間有雙向因果關系(Aw 等,2008)。由于企業創新和出口活動都需要進入成本,因此企業將對這兩種活動產生基于生產力特征的“自我選擇效應”。總而言之,通過企業生產力的變化,企業創新與出口的雙向因果關系可能存在。這是因為出口能夠提高企業的生產力,從而使得企業傾向于自主選擇創新。同樣地,企業也可以通過創新來提高生產力,從而使得企業傾向于自主選擇出口(Aw 等,2009)。
(6) 銷售收入利潤率(ros)。銷售收入利潤率定義為企業的總利潤對同期銷售收入的比率,即利用2010 年的總利潤/銷售收入。銷售收入利潤率是用來反映企業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標,這項指標越高,說明企業銷售收入獲取利潤的能力越強。毋庸置疑,利潤空間越大的企業通常有更多的資源來進行創新活動。
(7) 企業高層經理的工作經驗(exper)。企業高層經理的工作經驗定義為企業高層經理在特定行業領域里的從業年數。Ganataki(2012)認為,創新活動是一項高風險的復雜活動,它對環境的敏感性較高,需要有工作經驗豐富的高層管理人員對創新項目進行評估,才能有效地控制創新活動風險,從而推動企業創新。因此,企業高層經理的工作經驗越豐富就越有利于促進企業創新。
(8) 正式員工的平均教育年限(edu)。正式員工的平均教育年限用于反映企業的人力資本質量,通常而言,平均教育年限越高,人力資本質量越好。Shane(2000)認為正規教育能夠使人獲得識別商業機會的技能。更重要的是對于企業創新而言,提高具有高等教育學歷的員工比例有利于提升企業的吸收能力(Roper 和Love,2006),從而有效地推動企業創新活動的開展。
根據2012 年世界銀行關于中國企業營運的制度環境質量調查,我們還控制企業層面上其他有可能影響企業創新的因素(Goedhuys,2007;Lederman,2010)。首先,我們構建了企業對員工是否有正式培訓計劃的虛擬變量(train),將其定義為若企業對員工有正式培訓計劃則賦值為1,否則為0。利用這一虛擬變量我們可以捕捉到正式培訓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其次,構建企業是否具有透支額度的虛擬變量(overdraft),將其定義為若企業具有透支額度,則賦值為1,否則為0,利用該虛擬變量來捕獲融資約束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最后,我們還控制了城市層面有可能影響企業創新的變量,例如該城市的市場規模(marketsize),按照該城市的人口規模分為四個等級,人口少于5 萬的賦值為1,5 萬至25 萬的賦值為2,25 萬至100 萬賦值為3,100 萬以上賦值為4;該城市是否是重要的商業城市(business),若是則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除此以外,由于以往的研究結論顯示不同地區和不同行業的企業創新具有較大的差異,因而我們納入了城市和行業的固定效應。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1 所示。

表1 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表
四、計量分析
(一)腐敗與企業創新
1. 基準規范分析
本研究采用的截面數據要求考察橫向截面的動態變化,因此需要將內生性和異方差等問題充分考慮。為此,我們控制了行業和城市的虛擬變量,并且估計了聚合在行業性質層面的穩健性標準誤。由于企業創新為非負的連續變量,因此我們首先采用Tobit 方法對計量模型進行估計,它比OLS 回歸模型要更加穩健。
在表2 中的列(1)只考慮了腐敗的一次項(bribe)與企業創新之間的關系,其結果顯示腐敗的一次項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意味著在市場機制不完善的經濟體中,腐敗可以為企業適當地減少行政干預,在時間上為企業贏得競爭優勢以及獲得公共部門較為短缺的資源配置,如獲取相關許可等等,這為企業創新營造必要的前提條件。在表2 中的列(2)和列(3)匯報的是Tobit 回歸結果。在表2 的列(2),我們首先只考慮腐敗與企業創新的關系,發現腐敗的一次項(bribe)系數和二次項(bribesq)系數在1%,的水平上分別顯著為正和負。這一研究結果表明,一定程度的腐敗對企業創新有
正效應,但更高程度的腐敗則對企業創新有負效應。在表2 的列(3)中,我們將所有控制變量加入,發現腐敗的一次項和二次項系數的絕對值并無明顯變化,且符號仍然分別顯著為正和負。作為對比,我們在第(4)列和第(5)列報告了Probit 的回歸結果,發現腐敗的一次項和二次項的系數符號仍然不變。這一發現與現有文獻截然不同,現有文獻或者發現腐敗是企業創新的“潤滑劑”(Acemoglu 和Verdier,1998)抑或腐敗是企業創新的“絆腳石”(Anokhin 和Schulze,2009)。本文的結論表明,腐敗與企業創新之間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而是一種非線性關系,即某種程度的腐敗是企業創新的“潤滑劑”,而更高程度的腐敗則是企業創新的“絆腳石”。

表2 腐敗對企業創新影響的實證檢驗結果
為進一步明確腐敗與企業創新之間的關系類型,我們對這個二次函數的拐點進行計算(列(3)的估計結果),并將其與腐敗的分布進行比較。根據模型估計結果,易得其拐點為14.863,6+0.195,8=15.059,4。該值略小于腐敗的99.8%,分位數(20),這表明有超過0.2%,的腐敗數據位于該點的右方。再考慮模型的幾何圖形是一條開口向下的拋物線(腐敗的二次項系數為負),我們于是可以判定企業非正式支付總額占年度銷售額的百分比在15.059,4%,以內時,腐敗對企業創新具有正效應,而當這一百分比超過15.059,4%,時,腐敗對企業創新具有負效應。對于上述結果,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市場機制并未完全確立的經濟體中,政府過多干預造成層級節制和繁文縟節,這種低效率的制度安排在某種程度上妨礙了企業創新項目的實現。活躍于當前市場上具有強烈創新需求的企業迫切需要有關部門能夠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以保證企業創新的順利開展。因此,賄賂等腐敗活動便為相關政府部門引入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提供了足夠的激勵。由此,賄賂可以視為特定企業從相關政府部門手中購買有效制度安排所需支付的費用。然而,在這一交換關系中,買方和賣方的地位并不是對等的。因為,特定企業履行相關非正式支付后,并不能立即獲得有效的制度安排,而可能僅是相關政府部門的事后承諾,而這一承諾并無強制執行的法律基礎,這使得相關政府部門違約的成本很低。在事后承諾沒有兌現的基礎上,相關政府部門反而向企業索要更高額度的賄賂,這顯然加重了企業創新的交易成本,抑制了企業創新。另外,我們還注意到,企業除了向相關政府部門購買有效的制度安排以利其創新的順利開展外,它們還有可能通過更高額度的賄賂從政府部門手中購買市場特權,以壟斷市場,同時極力推崇自身掌握的舊技術,壓制企業創新,并將潛在競爭型企業創新視為對自身地位和權力的一種挑戰。
除了關鍵解釋變量腐敗程度以外,控制變量的符號也基本上符合理論預期。在第(3)列的Tobit 回歸中,國有股份比例(soe)系數顯著為負,表明隨著國有股份比例的增加,企業可能越傾向于守舊。按理說,國有企業有著天然的政治關聯或擔保,這使得國有企業在當前的制度環境下具有較強的免疫力,以保證其創新行為免受不完善市場機制的傷害。因此,國有企業在創新能力上應更有優勢。然而,本文的實證研究結果正好相反。對此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國有企業雖然可以通過天然的政治關聯或擔保優先獲得各種資源,但國有企業這種天然的政治關聯或擔保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決定了企業的投資取向。我們認為,從20 世紀80 年代開始的地方政府官員之間圍繞GDP 增長而展開的“政治晉升錦標賽”是理解國有企業與創新的關鍵線索之一。“政治晉升錦標賽”是由上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推行和實施,行政和人事方面的集權是其實施的基本前提之一。政治錦標賽則可以將關心仕途的地方官員置于強力的激勵之下,這種強力激勵雖然有利于推動當地經濟增長,但更重要的是這種激勵模式產生了一系列的扭曲性后果(周黎安,2008)。尤其是在財政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向上級爭取資源的機會受到限制(Coles 等,2006),在地方政府財政預算不足的情況下,地方官員傾向于將政治和社會目標推向轄區企業,其中國有企業首當其沖。在這種情況下,國有企業通常背負著沉重的“政策性負擔”,這些政策性負擔擾亂了企業創新計劃,造成企業過度投資和員工冗余。由此,我們可將政策性負擔視為國有企業獲取各種資源所要付出的代價之一。需要強調的是,在晉升激勵之下,官員需要在短期內向上級傳遞可置信的政績信號。那些孕育周期長、投資風險大的項目通常難以迎合地方官員的政治偏好,為了配合地方政府的政治和社會目標,國有企業也只能將大量的精力放在短期內能夠促進當地GDP 增長和降低失業率的項目上,擠出了企業創新所需投入的精力。此外,在國有控股的情況下,實際控制人通常是企業高級管理人員,他們的任免由政治過程決定而不是由人力資源市場競爭產生。并且他們領取的是固定薪酬,剩余索取權卻歸國家所有。作為理性的經濟人,他們的目標更多的體現為職務待遇和提升機會,需要的是短期業績穩定,而不是歷經數載的企業創新。
企業市場競爭(compet)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市場競爭越激烈,企業越傾向于創新。這與Nicholas 的研究結論是一致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熊彼特假說”,即市場力量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企業創新的傾向(吳延兵,2007)。企業規模(lnscale)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企業規模能夠有效促進企業創新。這與吳延兵的研究結論是一致的,即規模大的企業通常能夠獲得企業創新所需的各種資源(Prashanth,2008)。我們并沒有發現企業年齡(lnage)對企業創新具有顯著的促進效應,對此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雖然年長的企業具有較強的市場分析能力,能夠快速地洞悉市場規律,把握創新項目投資機會,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企業可能越發擅長執行原有的慣例,并對企業先前的技術能力表現出過度自信的狀態,以致企業陶醉于原有的技術優勢,而陷入“能力陷阱”。因此,年長的企業由于惰性的原因又可能會減少嘗試創新的機會。企業出口(export)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出口企業更傾向于創新。這可能是因為出口企業可以獲得“出口中學”效應,較快地吸收了國外研發的技術外溢,促進了企業創新。銷售收入利潤率(ros)的系數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企業銷售收入利潤率越高,企業創新活動的強度就會越激烈。這是因為企業創新是一項耗資巨大的活動,豐厚的利潤才能為這項活動提供物質基礎。企業高層經理的工作經驗(exper)的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意味著企業高層經理的工作經驗越豐富,企業創新活動的強度就越激烈。這與Ganatakis(2012)的研究結論是一致的。正式員工的平均教育年限(edu)的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意味著正式員工的平均教育年限越長,企業創新活動的強度就會越激烈。這與Roper 和Love(2006)的研究結論是一致的。通常而言,較高的教育水平能夠幫助員工提高認知復雜性,從而獲得更強的能力來掌握新觀念、學習新行為和解決新問題。由于創新項目通常是復雜和不確定的,而具有較高水平的員工可能更容易接受創新和忍受不確定性。此外,較高教育水平還能幫助員工消化和吸收新的知識和技術,有利于推動企業創新活動的開展。企業員工培訓(train)系數顯著為正,表明企業員工培訓能夠有效地促進企業創新。對此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培訓有利于促進員工吸收新的知識,從而有利于企業創新活動的開展。企業是否有透支額度(overdraft)系數顯著為正,這表明企業的透支額度對企業創新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對此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企業的透支額度有利于緩解企業創新所遭遇的融資約束,從而有利于企業創新活動的開展。最后,城市層面有關市場規模(marketsize)和商業城市(business)等變量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并不明顯。
2. 工具變量回歸分析
已有相關文獻在研究賄賂等腐敗與企業創新之間的關聯性時,都面臨著一個難題,即未能使用有效的策略識別出腐敗與企業創新之間的因果關系(Prashanth,2008)。這是因為不僅賄賂等腐敗活動能夠影響企業創新,同時在當前的制度環境下,具有創新動機的企業也有強烈的動機通過賄賂等腐敗活動尋求政府庇護,以確保創新成果收益的獨占性。為此,我們必須使用工具變量的方法來識別腐敗與企業創新之間的因果關系走向。因為工具變量回歸可以產生合適的估計量來克服現存的內生性問題。但是利用工具變量回歸的一個難題是尋找出有效的工具變量,并且這一變量與內生解釋變量強烈相關且滿足排除限制(exclusion restriction)。參照相關文獻的經驗做法(Fisman和Svensson,2007;Reinnikka 和Svensson,2006),即企業所在城市的特征變量經常作為企業內生變量的工具變量。Fisman 和Svensson(2007)使用企業所在地區相關經濟變量的平均值作為工具變量。基于此,我們將使用企業所在城市同行業(location-industry average)非正式支付比例的平均值作為賄賂等腐敗活動的工具變量,利用這些工具變量,我們使用了IVTobit 和IVProbit 回歸,分別報告在表2 中的第(6)和第(7)列,回歸結果顯示,Wald 外生性排除檢驗都拒絕了原假設,表明腐敗是內生的,同時弱工具變量的穩健性檢驗拒絕了原假設,表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在表2 的列(6)中,腐敗的一次項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二次項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沿用前述分析方法,我們計算得到模型的拐點為7.193,6+0.195,8=7.389,4。該值略小于腐敗的99%,分位數(8),表明有超過1%,的腐敗數據位于該點的右方。再考慮模型的幾何圖形是一條開口向下的拋物線(腐敗的二次項系數為負),我們于是可以判定企業非正式支付總額占年度銷售額的百分比在7.389,4%,以內時,腐敗對企業創新具有正效應,因此研究假設H1 獲得支持,而當這一百分比超過7.389,4%,時,腐敗對企業創新具有負效應,因此研究假設H2 獲得支持。作為對比,在表2 的列(7)中,IVProbit 回歸結果顯示,腐敗的一次項和二次項系數分別在1%,和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和負,這意味著本文研究結論具有較強的穩健性。從工具變量估計的結果來看,腐敗對企業創新具有非線性的影響,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與普通的Tobit 和Probit 回歸估計的結果基本吻合。值得注意的是,工具變量估計的結果與普通的Tobit 和Probit 回歸估計的結果相比,表2 中列(6)和列(7)的腐敗一次項和二次項系數提高較大。這表明,腐敗的內生性使得普通的Tobit 和Probit 回歸估計產生向下偏倚,從而傾向于低估腐敗對企業創新的作用。
3. 不同產權性質下腐敗對企業創新的影響
根據前文推論,設定回歸方程如下,方程(2)用于檢驗企業產權性質和腐敗對企業創新的交互影響。

在方程式(2)中,soei×bribei表示企業產權與腐敗的交互項,soei×bribesqi表示企業產權與腐敗平方的交互項。上述方程式的設定主要用于檢驗不同企業產權性質下腐敗對企業創新行為的影響。表2 中的模型(8)~(9)檢驗了企業產權和腐敗對企業創新的交互影響效果。模型(8)首先考慮的是企業產權與腐敗的交互項對企業創新的影響,結果顯示,企業產權與腐敗的交互項(soei×bribei)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這意味著相對于非國有控股企業而言,國有控股企業腐敗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更弱。其次模型(9)同時考慮了企業產權與腐敗的交互項以及企業產權與腐敗平方的交互項對企業創新的影響,結果顯示在5%,的水平上,企業產權與腐敗的交互項(soei×bribei)對企業創新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而企業產權與腐敗平方的交互項(soei×bribesqi)對企業創新的負面影響并不明顯。這意味著國有控股企業創新對賄賂等腐敗活動的敏感性降低了①由于腐敗與企業創新是一個顯著的倒U 型曲線關系,而企業產權對這一倒U 型曲線關系具有負向調節效應,這導致倒U 型曲線的頂點向右移動,此時,相對于移動之前,企業創新對腐敗影響的敏感性降低了。,由此本文的研究假設H3 獲得支持。
Frye 和Shleifer(1997)針對上述現象提供了相關解釋,即在缺乏政府問責制的制度框架下,國有控股可以作為抑制本地政府尋租活動的次優承諾機制(second best commitment mechanism)。對于國有控股企業而言,其是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為彌補市場失靈,在制度、目標和管理諸方面具有特性的現代契約組織。對于這類組織,政府會委托職業經理人進行代理。為了鼓勵這些職業經理人和提升企業的收益,政府部門向職業經理人抽取租金的偏好通常較弱。通常地,政府部門會向國有控股企業主動伸出“扶持之手”,比如對這些企業進行減稅和補貼。在這種情況下,國有控股企業并不需要賄賂政府部門便可優先獲得企業創新所需的各種物質條件以及立法保護,這顯然弱化了國有控股企業的賄賂動機,削弱了國有企業賄賂等腐敗活動對企業創新的影響。相對而言,當企業為私人所有時,政府部門更傾向于向私有制企業的代理人抽取租金,因為政府部門并不是這些企業的直接利益相關者。更重要的是,在與國有控股企業競取政府資源配置的過程中,私有制企業通常處于劣勢,為此,私有制企業有更加強烈的動機通過賄賂等腐敗活動來獲取各種資源以利業務活動的順利開展。由此可見,私有制企業的各種活動通常要仰仗于賄賂等腐敗活動所換來的各種資源。尤其對于開展企業創新的私有制企業而言,其就更需要通過賄賂等腐敗活動的方式獲得政府扶持和保護。因此,相對而言,私有制企業的創新活動對賄賂等腐敗活動的影響具有更強的敏感性。
(二)腐敗與企業創新渠道
為何腐敗對企業創新反而有利呢?腐敗是通過什么渠道影響企業創新的?我們接下來分析腐敗影響企業創新的兩種渠道,具體如圖1 所示。我們首先考慮腐敗活動→政府擔保(政府訂單)→企業創新這條影響路徑。在當前的制度環境下,創新成果極易被競爭者復制模仿,會使企業創新的所有努力付之東流。若企業能夠獲得政府擔保,那么政府將有動力采取各種措施使得企業規避創新風險。因此,政府擔保會強化企業創新激勵機制。另外,毋庸置疑,市場在短時間內較難認知企業的創新產品,因此企業試圖尋找各種有效的方法加速市場對創新產品的認知,否則有可能面臨創新失敗的巨大風險。Granovetter(1985)認為經濟行為通常嵌入在社會環境之中。社會傳染(Social contagion)影響了潛在消費者,同時相對于其他個體而言,政府的購買行為會對消費者的購買決策產生更加深刻的影響(Iyengar 等,2011)。由此可見,政府訂單有利于消化企業大部分的創新產品,緩解企業創新產品的營銷風險。同時,政府訂單產生的“示范效應”有利于加速市場對企業創新產品的認知,提高企業創新成功的概率。既然政府擔保(政府訂單)有利于企業創新,那么企業如何獲得政府擔保(政府訂單)?在相關制度并不完善的經濟體中,賄賂等腐敗活動有利于企業與政府建立起牢固的紐帶關系,并使得企業優先分享到政府提供的各種政策性優惠。由此我們可以斷定賄賂等腐敗活動有利于企業獲得政府擔保(政府訂單)。

圖1 腐敗對企業創新影響的路徑圖
為了驗證上述邏輯框架的正確性,我們采用結構方程模型中的路徑分析技術來檢驗圖1 中各個變量之間的關聯性,之所以用結構方程模型中的路徑分析技術是因為路徑分析技術是多元回歸分析技術的一種拓展,它能夠同時估計各種多元回歸模型或方程,從而提供了一種更有效的方法來估計建模過程中的中介、間接效應以及其他變量之間的復雜關系。
在檢驗過程中,首先,我們利用企業是否獲得政府擔保或政府訂單來衡量政府擔保或政府訂單,若企業獲得政府擔保或政府訂單,則賦值為1,否則為0;其次,我們利用企業是否從融資機構獲得信貸來衡量金融機構貸款,若企業從融資機構獲得信貸則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具體結果如表3 所示。由表3 的結果可知,結構方程模型整體擬合優度為0.751,4,穩定性指數(stability index)幾乎接近于0,表示結構方程模型滿足穩定性條件。從單個的路徑系數來看,政府擔保(政府訂單)有助于企業創新(β=0.051,6,p<0.01)。這表明政府擔保能夠降低信貸機構獲取信息的成本,從而使得信貸機構能夠更好的評估、選擇和監督企業創新投資項目。由此可見,政府擔保的作用在于正確地引導資金流向,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促進了企業創新。這正如King 和Levine(1993)所強調的一樣,中介機構有利于減少資源配置成本,并成為金融發展促進企業創新的重要渠道。在本研究中,政府正是扮演著中介機構的作用(King 和Levine,1993)。同時,賄賂等腐敗活動有利于企業獲得政府擔保或政府訂單(β=0.012,8,p<0.05),這與黃玖立和李坤望(2013)的研究結論是一致的。即賄賂等腐敗行為發揮著特殊的資源配置功能,能夠為企業獲得政府訂單提供便利。這些結果表明我們的預測是正確的,也說明了政府擔保或政府訂單是賄賂等腐敗活動積極影響企業創新的重要渠道之一。

表3 腐敗對企業創新影響的結構路徑系數表
我們還要考慮腐敗活動→金融機構貸款→企業創新這條影響路徑。在市場經濟不完善的經濟體中,為了防止和減少貸款風險和損失,金融機構通常會針對私營企業貸款制定出更多的約束條款并執行更加嚴格的監督,這顯然增加了私營企業的貸款成本(Firth 等,2009)。這樣,賄賂等腐敗活動有助于企業規避官僚體制中的繁文縟節(red tape)(Leff,1964)。因此,它可以被視為提高私營企業貸款效率的一種次優選擇(second-best option)。同樣地,賄賂等腐敗活動有利于減少私營企業貸款審批所需等待的大量時間,有利于這些企業把握有效的投資機會,因而賄賂等腐敗活動可以視為私營企業獲得銀行信貸的“速辦金”(Lui,1985)。更為重要的是,金融機構的貸款具有較強的制度剛性和約束力,這使得某些不符合金融機構貸款條件的私營企業被排斥在正規金融系統之外,致使它們失去良好的投資機會。賄賂等腐敗活動能夠有效地軟化制度剛性,使得不符合金融機構信貸條款的私營企業有獲得正規金融機構信貸的可能。Lien(1986)將腐敗視為一個科斯議價過程。在科斯議價過程中,信貸機會被視為拍賣的標的物,金融機構將信貸機會出售給賄賂額度最高的競標者。在這個過程中,金融機構的信貸配置效率仍維持不變,這是因為在競拍過程中,通常只有成本最低的企業才能支付最高額度的賄賂。這也意味著建立在賄賂等腐敗活動基礎上的信貸配置機制使得唯有成本最低的企業才能獲得正規金融機構提供的信貸機會。因此,我們可以預見,賄賂等腐敗活動有利于企業獲得金融機構貸款。同樣地,金融機構貸款也有助于推動企業創新。這是因為,在信息不對稱的情境下,企業創新活動會因為規避風險和私人信息引發的道德風險而陷入融資困境。銀行機構貸款有利于保證企業創新的融資來源,緩解企業創新活動所面臨的融資約束,激發企業創新的活力。由此,我們有理由期待金融機構貸款有助于企業創新。表3 的結構方程模型回歸結果顯示,賄賂等腐敗活動亦有利于企業獲得金融機構貸款(β=0.016,8,p<0.05)。同時,銀行機構貸款(β=0.062,3,p<0.01)也對企業創新具有顯著的積極影響。這些結果表明我們的預測是正確的。這也說明了金融機構貸款是賄賂等腐敗活動積極影響企業創新的重要渠道之一。
最后,我們考慮腐敗活動→政府擔保(政府訂單)→金融機構貸款→企業創新這條影響路徑。在這條邏輯鏈上,我們主要關注政府擔保(政府訂單)對金融機構貸款的影響。當前中國正處在經濟轉軌的關鍵時期,資本市場體系并不完善,且企業上市條件苛刻,因而大部分企業難以借助資本市場平臺以股權的形式獲得企業創新項目融資。為了能夠解決融資困境,企業需要通過賄賂的方式來獲得政府擔保。因為具有政府擔保的企業更加容易取得國內銀行融資認可,從而獲得更多的低成本銀行信貸(余明桂和潘紅波,2008)。事實上,政府擔保對于企業獲得銀行機構貸款方面存在著三大優勢:第一,在經濟轉軌時期,銀行機構的貸款行為通常是基于國家政策傾向的考慮,因而在同等條件下,他們會將貸款機會讓給獲得政府擔保的企業;第二,政府擔保是一種重要的聲譽機制和企業擔保貸款的重要資源,因而獲得政府擔保的企業通常能夠分享到政府部門的外部網絡資源,從而獲得成本更低、數量更多的信貸資源;第三,獲得政府擔保的企業可以獲得政府的救助,即使在企業面臨財務困境時,政府仍然會出手相救(Faccio,2006)。這三大優勢降低了銀行機構對獲得政府擔保企業道德風險的擔憂。本文的實證結果表明,政府擔保有利于企業獲得銀行機構貸款(β=0.130,6,p<0.01)。這意味著政府擔保是一種重要的聲譽機制,并向金融機構傳遞“軟信息”,有助于企業獲得金融機構貸款。
從整體的路徑系數來看,賄賂等腐敗活動通過政府擔保和銀行機構貸款等對企業創新具有顯著的積極影響(β=0.001,8,p<0.01)。這意味著政府擔保和銀行機構貸款是賄賂等腐敗活動影響企業創新的有效渠道。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具有“新興加轉型”雙重制度特征的經濟體而言,相關正式制度并未完全確立,政府依然掌控著重要資源的供給,銀行機構信貸亦隨政府導向而為(Sapienza,2004)。為此,與政府建立牢固的政治紐帶(political connection)關系就成為企業獲得重要資源的關鍵手段。因為這種政治紐帶關系是企業獲得各種政策性資源的“通行證”。在這個過程中,賄賂等腐敗活動便有可能成為諸多企業建立政治紐帶關系的行為模式,并演化成為企業慣例。事實上,這種大多數企業采取的行為模式是一種“進化穩定均衡”。企業若偏離這種行為模式,則可能蒙受巨大損失。Djankov(2008)通過研究發現,企業家偏好通過賄賂等腐敗活動來改變當地政府制定的規則,從而推動企業發展。本研究表明,政府擔保(政府訂單)和銀行機構貸款是賄賂等腐敗活動影響企業創新的兩個重要渠道。這也意味著在市場機制并不完善的經濟體中,腐敗對企業創新的潤滑劑作用在于它有助于企業獲得政府擔保和銀行機構貸款,有利于減少市場機制不完善對企業創新帶來的傷害。由此可見,賄賂等腐敗活動是企業在非正式經濟體中尋求替代保護的一種重要手段,并被企業作為慣例來遵守。

表4 腐敗對企業創新影響的間接和總效應
(三)腐敗與不同類型的企業創新
以上結果表明腐敗與企業創新產出之間有著顯著的倒U 型曲線關系,那么腐敗對不同類型的企業創新又會有怎樣的影響呢?本部分我們分別將是否引入新技術和設備(newtech)、是否引入新的質量控制程序(newqual)、是否引入新的管理/行政流程(newmana)、是否為現有產品或服務增加新的特征(newfeat)、是否采取相關措施降低生產成本(redcost)以及是否采取相關措施來提高生產靈活性(impprd)等作為被解釋變量來考察這一問題。由表5 可知,賄賂等腐敗活動對企業引入新技術和設備、引入新的質量控制程序、引入新的管理/行政流程、為現有產品或服務增加新的特征、采取相關措施降低生產成本以及采取措施提高生產靈活性等有顯著的倒U 型影響。上述結果說明本文研究結論具有較強的穩健性。事實上,在缺乏法律保護等制度因素的情況下,企業創新成果容易被競爭者模仿和抄襲,這會降低企業創新活動對企業價值的影響。由此可見企業創新活動的收益預期在某種程度上取決于外部的制度安排。在缺乏有效制度安排的情況下,企業可能需要通過賄賂等腐敗活動來獲得政府的政府庇護,以確立創新成果的所有權,從法律上保護創新企業免于被模仿和抄襲。因此,我們可以將某種程度的腐敗活動視為正式制度缺失的一種非正式性的替代機制。此時賄賂等腐敗活動對企業創新具有“潤滑劑”的作用。當政府官員所要求的賄賂額度超過特定水平時,賄賂等腐敗活動會給企業創新帶來巨額的交易成本,加重了企業的負擔,此時腐敗對企業創新具有“絆腳石”的作用。

表5 腐敗對不同類型企業創新的影響結果
(四)廣義傾向得分匹配估計
為了更好地反映賄賂等腐敗水平對企業創新力度變化的因果影響,我們采用Hirano 和Imbens(2,004)所發展的基于連續性處理變量的廣義傾向得分匹配方法(Generalize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GPSM)進行實證分析,以進一步刻畫不同腐敗水平對企業創新力度的影響差異。一般而言,運用廣義傾向得分匹配法來實現因果關系估計有三個步驟:首先,我們計算出處理變量(bribe)的廣義傾向匹配得分①此處沒有列出所有匹配變量的估計值,感興趣的讀者可以通過E-mail 的方式向作者索取。。其次,以企業創新力度變化作為被解釋變量,以腐敗水平作為關鍵解釋變量,并將處理變量的廣義傾向得分作為控制變量,然后通過OLS 法進行估計。具體結果匯報在表6。由表6 的結果可知,各變量及其平方項和交互項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我們將這一步的估計系數作為第三步估計的基礎。在第三步估計之前,我們刻畫了不同腐敗水平下企業創新力度的趨勢走向,具體見圖2。由圖2 的處理效應函數估計圖的趨勢走向可知,隨著腐敗水平從低分位點向高分位點的逐漸升高,賄賂等腐敗活動對企業創新的正向處理效應逐漸弱化,超過特定分位點(20)時,賄賂等腐敗活動會對企業創新產生抑制效應,且抑制效應逐漸強化。從劑量響應函數估計圖的趨勢走向來看,腐敗與企業創新之間呈現出了明顯的倒U 型曲線關系。

表6 OLS估計結果

圖2 不同處理水平下的劑量響應函數和處理效應函數估計圖
最后,我們將企業腐敗水平按照其取值范圍劃分為多個區間,然后估計不同腐敗水平對企業創新力度的效應。其具體的估計結果如表7 所示。從表7 可知,當腐敗水平小于0.03 時,腐敗則是企業創新的“潤滑劑”,而這種潤滑作用卻越來越弱,而當腐敗水平大于0.03 時,腐敗則是企業創新的“絆腳石”,并且這種抑制效應越來越強。

表7 腐敗水平對企業創新力度的影響
(五)穩健性檢驗
為了保證本文研究結果的穩健性,我們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了穩健性檢驗,穩健性檢驗結果經整理后匯報在表8 中。
1. 基于產業類別的回歸分析。表8 中列(1)至列(2)的結果分別顯示,不管是制造業(industrial)還是零售和服務業(retail),腐敗與企業創新之間始終呈現一種倒U 型的曲線關系;
2. 將企業運營過程中所感知的腐敗障礙作為腐敗的替代變量①在2012 年世行調查問卷中,該題的設置是貴公司運營過程中所遭遇的腐敗障礙程度如何。答題項按照李克特五點尺度進行設置。0 表示沒有障礙,1 表示較小障礙,3 表示一般障礙,4 表示較大障礙,5 表示非常嚴重的障礙。。表8 中列(3)的結果顯示,在5%,的顯著水平上,腐敗與企業創新之間仍舊是一種顯著的倒U 型曲線關系。

表8 穩健性檢驗結果
3. 尋找企業創新的替代性指標。毋庸置疑,企業研發水平一直用于測度企業創新努力程度的重要代理指標之一。這一代理指標的優勢在于它是一個相對容易理解的學術術語,并且它提供了可以測度的幣值(a dollar figure)用于后續分析。有鑒于此,我們將企業研發投入決策作為企業創新的指代變量,具體定義為在過去的三年時間內,企業是否有研發支出,若有則賦值為1,否則為0;同樣地,我們將研發投入強度也作為企業創新的指代變量,具體定義為在過去的三年內,企業平均每年在研發活動上的支出額度,為了消除規模效應的影響,我們將平均每年的支出額度除以企業正式員工總人數。回歸結果經整理后匯報在表8 中的列(4)和列(5),回歸結果顯示在1%,的水平上,腐敗與企業創新之間依舊是一種顯著的倒U 型曲線關系。由此說明本文研究結果具有較強的穩健性。
4. 納入制度質量作為控制變量。良好的制度被視為決定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Djankov 等,2002)。這是因為良好的制度能夠確保契約的執行并保護公民的財產免受征用之風險,同時也為企業發展提供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商業環境。同樣地,為了制定和執行規則,制度必須發揮配置、表達和問責的功能。當這些功能能夠有效地發揮出來時,良好的制度會更加強調公眾對制定和執行規則之政府機構的問責,從而形成一個相對最優的商業規則。進一步地,良好制度的存在增加了腐敗政府官員向企業抽租的成本(Acemoglu 等,2002),同時也使得既得利益集團很難通過賄賂等腐敗活動來破壞規則或放松規則約束,以謀取犧牲社會利益為代價的私利。規制俘獲理論也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觀點,并將腐敗與制度質量聯系起來。Stigler(1971)最先提出規制俘獲的方法,他認為典型的政府失靈是因為特殊利益集團俘獲了制定和執行規則的國家機構。根據Laffont 和 Tirole(1991)的觀點,既得利益集團能夠通過賄賂制定和執行規則的腐敗官員來對規則施加影響。此外,企業家也能夠通過賄賂與政府官員建立起良好的關系以獲取各種政策性的資源。由此可見,在正式制度并未完全確定的環境中,既得利益集團通常會致力于游說政府官員(Austen-Smith,1987)。良好的制度環境表現為它能夠抵抗規制俘獲并防止既得利益集團從私人部門抽取租金的行為。
由上述結論推之,良好的制度環境能夠弱化賄賂等腐敗活動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基于此,我們納入了制度質量(law)、制度質量與腐敗的交互項(bribe×law)以及制度質量與腐敗平方的交互項(bribesq×law)。在度量制度質量時,我們根據2012 年世界銀行關于中國企業營運的制度環境質量調查問卷中設置的問題:“法院系統是公正、公平和廉潔的”,將其作為制度質量的度量。同時,企業管理層可以選擇的答案為“非常不同意”、“傾向于不同意”、“傾向于同意”和“非常同意”。根據這些答案,我們依次賦值為1、2、3、4。并利用IVProbit 和IVTobit 對計量模型重新進行回歸,回歸結果經整理后匯報在表8 的列(6)和列(7)。其結果顯示,制度質量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意味著正式制度質量對企業創新具有顯著的積極影響。進一步地,正式制度質量與腐敗的交互項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這意味著隨著正式制度質量的提升,賄賂等腐敗活動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會逐漸弱化。此外,正式制度質量與腐敗平方的交互項雖然為正,但在10%,的水平上并不顯著。需要說明的是,交互效應的檢驗并非完全取決于交互項的統計顯著性,而是可以通過交互效應圖來反映調節變量的邊界效應,否則我們可能會低估調節效應的真實效力。為此,我們繪制了正式制度質量與腐敗對企業創新交互影響的效應圖(具體如圖3 所示)。

圖3 正式制度質量與腐敗對企業創新的交互影響圖
在圖3 中,橫坐標表示的是賄賂額度比例,縱坐標表示的是企業創新強度。它們反映了賄賂額度比例每變化一單位的標準誤,將會導致企業創新強度的變化幅度。首先,我們將正式制度質量根據其中位數分為兩類,若大于或等于中位數的正式制度質量定義為高司法質量,而小于中位數的正式制度質量則定義為低司法質量。其結果顯示,在高司法質量下,賄賂等腐敗活動對企業創新強度的影響程度更弱。
五、結論與政策內涵
本文運用2012 年世界銀行關于中國企業營運的制度環境質量調查數據實證分析腐敗水平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可以看出,一定程度的腐敗有利于企業創新,而更高程度的腐敗則會抑制企業創新。腐敗與企業創新之間呈現出顯著的倒U 型曲線關系,這是因為在正式制度缺失的情況下,對于創新企業而言,腐敗很可能是企業尋求政府庇護的一種代價,但是當這種代價超過企業創新所得收益時,腐敗則會抑制企業創新。進一步地看,腐敗可以通過以下兩種渠道來促進企業創新,即腐敗有助于企業獲得政府擔保(政府訂單)和銀行機構貸款,從而推動企業創新。
當前,我國正處在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能否有效推動企業創新直接決定了我國經濟轉型的成敗。遺憾的是,目前不完善的市場體制成為制約企業創新的掣肘。在市場機制不完善的經濟體中,由于信息不對稱問題所引發的道德風險問題,再加上創新成果的非競爭性和無法回避的非排他性,企業創新活動通常會遭受嚴重的融資約束并伴隨著巨大的收益風險。為此,企業必須找尋一種替代性的保護機制以減少由于市場機制不完善給企業創新帶來的負面沖擊。本研究結論表明,某種程度的腐敗有利于企業獲得政府擔保(政府訂單)和銀行機構貸款,從而推動了企業創新。這說明在轉型經濟體中,特定程度的腐敗是企業克服市場機制不完善對企業創新造成負面沖擊的有力武器之一。但另一方面,我們發現更高程度的腐敗有礙于企業創新。更高程度的腐敗既可能源于腐敗官員“敲竹杠”,即腐敗官員并未兌現事先建立在賄賂額度基礎上的承諾,反而索要更高的賄賂,給企業運營帶來巨額的交易成本,抑制了企業創新;也可能源于低效企業以高額賄賂額來換取市場特權,從而打壓競爭對手,抑制企業創新。進一步研究發現,在不同企業產權制度下,賄賂等腐敗活動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并不一致。其中,國有控股企業的賄賂等腐敗活動對企業創新影響的敏感性要顯著低于非國有控股企業。基于上述經驗,本文所蘊含的政策意義如下:
(1) 在當前的制度環境下,賄賂等腐敗活動與企業創新之間的關系顯得異常復雜,從本文的研究結果來看,賄賂等腐敗活動對企業創新的“潤滑劑”作用占據主導。但是在當前的制度環境下,容忍高水平腐敗只會抑制企業創新,因此嚴厲打擊高水平腐敗的滋生和蔓延是當務之急。同時,我們堅信當前的賄賂等腐敗活動是市場機制不完善下的必然產物,也是相關資源配置的次優選擇方式,隨著市場機制的進一步完善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賄賂等腐敗活動也將隨之消失。
(2) 毋庸置疑,完善的市場機制是實現相關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方式。由于建立在賄賂等腐敗活動基礎上的資源配置無疑是市場機制扭曲的后果,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掣肘了企業創新的步伐,分散了企業創新的精力,增加了企業創新的成本。就當前的經驗來看,完善市場機制的第一步就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即轉變政府職能,政府要從競爭領域配置資源的角色中退出來,市場能夠管好的領域,政府不應過度干預。政府的職能在于配合市場為主的資源配置機制,正確地引導資源流向,解決市場失靈對企業創新造成的不利影響。
[1] 陳 剛,李 樹. 官員交流、任期與反腐敗[J]. 世界經濟,2012(2):120-142.
[2] 黃玖立,李坤望. 吃喝、腐敗與企業訂單[J]. 經濟研究,2013(6):71-84.
[3] 李后建. 市場化、腐敗與企業家精神[J]. 經濟科學,2013(1):99-111.
[4] 喬爾·赫爾曼,杰林特·瓊斯,丹尼爾·考夫曼,周軍華. 轉軌國家的政府俘獲、腐敗以及企業影響力[J]. 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9(1):1-12.
[5] 唐清泉. 企業R&D 創新投入的風險與有效性研究——我國企業轉型升級的內在機制[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1.
[6] 吳延兵. R&D 與創新:中國制造業的實證分析[J]. 新政治經濟學評論,2007,3(3):30-51.
[7] 余明桂,潘紅波. 政治關系、制度環境與民營企業銀行貸款[J]. 管理世界,2008(8):9-21.
[8] 周黎安. 轉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員激勵與治理[M]. 上海:格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9] Abdel-Khalik,A. R. Why Do Private Companies Demand Auditing? A Case for Organizational Loss of Control[J]. Journal of Accounting,Auditing and Finance,1993,8(1):31-52.
[10] Acemoglu,D. Verdier,T. Property Rights,Corruption and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A 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J]. The Economic Journal,1998,108(9):1381-403.
[11] Acemoglu,D.,and Verdier,T. The Choice between Market Failures and Corrup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90(1):194-211.
[12] Acemoglu,D.,Johnson,S.,Robinson,J. Reversal of Fortune: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2,117:1231-94.
[13] Adhikari,A.,Derashid,C.,Zhang,H. Public Policy,Political Connections,and Effective Tax Rates:Longitudinal Evidence from Malaysia[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2006,25(5):574-95.
[14] Ahlin,C. and Bose,P. Bribery,Inefficiency and Bureaucratic Delay[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2007,84(1):465-86.
[15] Aidis,R.,Estrin,S.,Mickiewicz,T. Institutions and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in Russia: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8,23(6):656-72.
[16] Aidt,T. S. and Dutta,J. Policy Compromises:Corruption and Regulation in A Democracy[J].Economics and Politics,2008,20(3):335-60.
[17] Alchian,A. A.,and Demsetz,H. The Property Rights Paradigm[J].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73,33(3):16-27.
[18] Alesina,A.,Ardagna,S.,Nicoletti,G.,and Schiantarelli,F. Regulation and Investment[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05,3(4):791-825.
[19] Andvig,J. C. The Economics of Corruption:A Survey[J]. Studi Economici,1991,43(5):57-94.
[20] Anokhin,S. & Schulze,W. Entrepreneurship,Innovation and Corrupt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9,24(5):465-76.
[21] Argyres,N. S.,Brain,S. S. R&D,Organization Structure,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Technological Knowledge[J]. Strategic Management Review,2004,25(8-9):929-58.
[22] Austen-Smith,D. Interest Groups,Campaign Contributions and Probabilistic Voting[J]. Public Choice,1987,54(2):123-39.
[23] Aw,B. Y.,Roberts,M. J. and Xu,D. Y. R&D Investments,Exporting,and the Evolution of Firm Productivi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8,98(2):451-56.
[24] Aw,B. Y.,Roberts,M. J.,Xu,D. Y. R&D Investment,Exporting,and Productivity Dynamics[R].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Cambridge,MA,2009.
[25] Banerjee,A.,Hanna,R.,and Mullainathan,S. Corruption[A]. In Robert Gibbons and John Roberts eds.,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Economics[C].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2013.
[26] Bardhand,P. Corruption and Development:A Review of Issues[J]. Journal of Economics Literature,1997,35(3),1320-46.
[27] Baumol,W. Entrepreneurship:Productive,Unproductive,and Destructiv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893-921.
[28] Beck,P. J.,and Michael,M. The Impact of the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on US Exports[J].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1991,12(4):295-303.
[29] Bhattacharya,S. & Ritter,J. Innovation and Communication:Signalling with Partial Disclosure[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83,50(2),331-46.
[30] Blackburn,K. & Forgues-Puccio,G. F. Why Is Corruption Less Harmful in Some Countries Than in Others?[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2009,72(3):797-810.
[31] Boldrin,M. and Levine,D. K. Rent Seeking and Innovation[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4,51(1):127-60.
[32] Boone,J. Intensity of Competition and the Incentive to Innovat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2001,19(5):705-26.
[33] Cassiman,B.,Veugelers,R. In Search of Complementarity in Innovation Strategy:Internal R&D and External Knowledge Acquisition[J]. Management Science,2006,52(1):68-82.
[34] Chen,S.,Sun,Z.,Tang,S.,and Wu,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1,17(2):259-71.
[35] Chen,W. R.,Miller,K. D. Situ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Firms′ R&D Search Intensity[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7,28(4):369-81.
[36] Choi,S. B.,Lee,H. S.,Williams,C. Ownership and Firm Innovation in A Transition Economy:Evidence from China[J]. Research Policy,2011,40:441-52.
[37] Claessens,S.,& Laeven,L. Financial Development,Property Rights,and Growth[J]. 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3,58(6):2401-36.
[38] Cohen,W. M.,Levin,R. C.,and Mowery,D. C. Firm Size and R&D Intensity:A Reexamination[J].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1987,35(4):543-65.
[39] Coles,J.,Danniel,N.,Naveen,L. Managerial Incentives and Risk-Taking[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6,79(2):431-68.
[40] Czarnitzki,D. The Extent and Evolution of Productivity Deficiency in Eastern Germany[J].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2005,24(2):209-29.
[41] Djankov,S,La Porta,R.,Lopez-de-Silanes,F.,and Shleifer,A.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Self-dealing[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8,88(3):430-65.
[42] Djankov,S.,La Porta,R.,Lopez-de-Silanes,F.,Shleifer,A. The Regulation of Entry[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2,117:1-37.
[43] Durkheim,E. Suicide:A Study in Sociology [M]. (Spaulding JA,Simpson G,Trans). New York:Free Press,1897.
[44] Faccio,M.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96(1):369-86.
[45] Firth,M.,Lin,C.,Liu,P.,Wong,S. Inside the Black Box:Bank Credit Allocation in China's Private Sector[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09,33(6):1144-55.
[46] Fisman,R.,Svensson,J. Are Corruption and Taxation Really Harmful to Growth? Firm Level Evidenc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7,83(1):63-75.
[47] Frye,T. and Shleifer,A. The Invisible Hand and the Grabbing Hand[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1997,87(2):354-59.
[48] Ganotakis,P. Founders′Human Capital and The Performance of UK New Technology Based Firm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2012,39(2):495-515.
[49] Goedhuys,M. Learning,Product Innovation,and Firm Heterogene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Evidence from Tanzania[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2007,16(2):269-92.
[50] Goedhuys,M.,Janz,N.,and Mohnen,P. What Drives Productivity in Tanzanian Manufacturing Firms:Technology or Business Environment[J].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2008,20(2):199-218.
[51] Granovetter,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3):481-510.
[52] Guriev,S. Red Tape and Corruptio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 2004,73(2):489-504.
[53] Haggard,S. Business,Politics and Policy in Northeast and Southeast Asia[A]. In:Maclntyre,A. (Ed.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in Industrializing Asia[C].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NY,Ithaca. 1994.
[54] Hall,B. H.,Lerner,J. The Financing of R&D and Innovation[A]. In:Hall,B. H.,Rosenberg,N. (Eds.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Innovation[C]. Elsevier-North Holland,Amsterdam,2010,609-39.
[55] Hall,B.,Jaffe,A.,Trajtenberg,M. The NBER Patent Citation Data File:Lessons,Insights,and Methodological Tools[R]. NBER Working Paper,No. 8498,2001.
[56] Hirano,K.,and G. W. Imbens. The Propensity Score with Continuous Treatments[A]. In Applied Bayesian Modeling and Causal Inference from Incomplete-Data Perspectives[C].England:Wiley InterScience,2004.
[57] Huergo,E.,and Jaumandreu,J. How Does Probability of Innovation Change with Firm Age?[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2004,22(3-4):193-207.
[58] Iyengar,R.,Van den Bulte,C.,& Valente,T. W. Opinion Leadership and Social Contagion in New Product Diffusion[J]. Marketing Science,2011,30(2):195-212.
[59] Jefferson G.,Huamao,B.,Xiaojing,G.,and Xiaoyun,Y. R and D Performance in Chinese Industry[J].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2006,15(4-5):345-66.
[60] Ju,M.,& Zhao,H. Behind Organizational Slack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China:The Moderating Roles of Ownership and Competitive Intensity[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9,26:701-17.
[61] Kaufmann,D.,Kraay,A. Governance and Growth:Which Causes Which? [R]. The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s. World Bank,Washington,DC,2003.
[62] Kim,E. M. Big Business,Strong State:Collusion and Conflict in South Korean Development,1960-1990[M]. 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7.
[63] King,R. G. and Levine,R. Finance,Entrepreneurship,and Growth: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3):513-42.
[64] Krusell,P. and Rios-Rull,J. V. Vested Interests in A Positive Theory of Stagnation and Growth[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6,63:301-29.
[65] Laffont,J. J. and Tirole,J. The Politics of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A Theory of Regulatory Capture[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1,106(4):1089-127.
[66] Lambsdorff,J. G. How Corruption Affects Persistent Capital Flows[J]. Economics of Governance,2003,a,4(3):229-43.
[67] Lambsdorff,J. G. How Corruption Affects Productivity[J]. Kyklos,2003,b,56(4):457-74.
[68] Lederman,D. An International Multilevel Analysis of Product Innovatio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0,41(4):606-19.
[69] Leff,N. H.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Bureaucratic Corruption[J]. 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1964,8(3):8-14.
[70] Lerner,J.,Wulf,J. Innovation and Incentives:Evidence From Corporate R&D[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7,89(4):634-44.
[71] Lewis,M. Informal Payments and The Financing of Health Care In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Countries[J]. Health Affairs,2007,26(4):984-97.
[72] Lewis,M. Who Is Paying For Health Care in Ea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R]. World Bank,Washington,D. C.,2001.
[73] Li,Q.,Maggitti,P.,Smith,K. G.,Tesluk,P. E.,Katila,R. Top Management Attention to Innovation:The Role of Search Selection and Intensity in New Product Introduct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3,56(3):893-916.
[74] Lien,D. H. D. A Note on Competitive Bribery Games[J]. Economics Letters,1986,22(4):337-41.
[75] Lin,C.,Lin,P.,Song,F. M.,Li,C. Managerial Incentives,CEO Characteristics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in China′s Private Sector[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11,39(2):176-90.
[76] Lui,F. T. An Equilibrium Queuing Model of Briber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5,93(4):760-81.
[77] Lundvall,B. A. Why Study National Systems and National Styles of Innovation?[J]. Technology Analysi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1998,10:407-21.
[78] Luo,Y. An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 of Corruption[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2004,1(1):119-54.
[79] Martin,K. C. J,Johnson,J.,Parboteeah,K. Deciding to Bribe:A Cross-level Analysis of Firm and Home Country Influences on Bribery Activit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7,50(6):1401-22.
[80] Mauro,P. Corruption and Growth[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10(3):681-712.
[81] Merton,R. K.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38,3(5):672-82.
[82] Mike,W. P.,Li S. S.,Pinkham,B.,and Chen,H. The Institution-Based View as a Third Leg for a Strategy Tripod[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2009,23(3):63-81.
[83] Murphy,K.,Shleifer,A. and Vishny,R.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Implications for Growth[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1,106(2):503-30.
[84] Murphy,K.,Shleifer,A. and Vishny,R. Why Is Rent-seeking So Costly to Growth?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3,83(2),409-14.
[85] Peng,M. W. Outside Directors and Firm Performance During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4,25:453-71.
[86] Prashanth,M. Corruption and Innovation:A Grease or Sand Relationship? [R]. Jena Economic Research Papers,2008,017.
[87] Qian,Y and Xu,C. Innovation and Bureaucracy under Soft and Hard Budget Constraints[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8,65(1):151-64.
[88] Reinnikka,R.,Svensson,J. Using Micro-Surveys to Measure and Explain Corruption[J].World Development,2006,34(2):359-70.
[89] Rivera-Batiz,F. L. Democracy,Governance,and Economic Growth:Theory and Evidence[J]. Review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2002,6(2):225-47.
[90] Rodriguez,P.,Siegel,D. S.,Hillman,A.,and Eden,L. Three Lenses on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Politics,Corruption,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6,37(6):733-46.
[91] Roper,S. and Love,J. H.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Absorptive Capacity[J].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2006,40(2):437-47.
[92] Rose-Ackerman,S. Corruption and Government Causes,Consequences and Reform[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93] Sapienza,P.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Ownership on Bank Lending[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4,72(2):357-84.
[94] Shane,S. Prior Knowledge and The Discovery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J]. Organization Science,2000,11(4):448-69.
[95] Shleifer,A. and Vishny,R. W. Corruption[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108(3):599-617.
[96] Smith,W. K.,& Tushman,M. L. Managing Strategic Strategic Contradictions Contradictions:A Top Management Model for Managing Innovation Streams[J]. Organization Science,2005(16):522-36.
[97] Stigler,G. J.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J].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1971,2(1):3-21.
[98] Svensson,J. Who Must Pay Bribes and How Much?[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3,118(1):207-30.
[99] Tan,J. Impact of Ownership Type on Environment,Strategy,and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02,39(3):333-54.
[100] Tanzi,V. Corruption Around the World:Causes,Consequences,Scope and Cures[J]. IMF Staff Papers. 1998,45(4):559-94.
[101] Vaal,A. and Ebben,W. Institutions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Corru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1,15(1):108-23.
[102] Yang,M. The Gift Economy and State Power in China[J].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89,31(1):25-54.
[103] Yeh,Y.,Shu,P.,and Chiu,S. Political Connections,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Preferential Bank Loans[J].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2013,21(1):1079-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