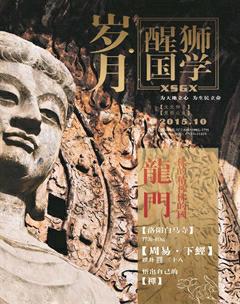負經白馬 踽踽東行
楊雪瑾
如果我是劉莊,我一定不會忘記永平七年所做的那個夢。
那一晚,我夜宿南宮,在夢里,我掀開重重疊疊的帷幕,赤腳踩著冰涼的地面,一路走向殿門口。當厚重的曲裾拂過門檻,我看到了一個身高六丈的金人自西方飛來,他的頭頂有圓月般的光暈,他身著五彩寶衣,他身后滿天花雨、神鳥鳴啼。
醒來時,望著金帳頂繁復的繡花,金人的身影在我腦海中久久不能消散,他像是一個夢,卻又清晰的如此真實。早朝上,我將夢境中的內容告訴大臣們,博士傅毅啟奏告訴我,那是西方的神,那里的人稱他為佛,和我夢中的金人分毫不差。
后來我才知道,那滿天花雨是曼陀羅花,那神鳥鳴啼是迦陵頻伽的佛國歌唱。我向往西方諸佛的世界,他們的誦經的喃呢跨越遙遠的時刻在我耳邊浮起。我派遣信任的臣子出使西域,去替我帶回夢中的佛經、佛法。
永平八年,蔡音、秦景等十余人帶著我的期許,離開了洛陽,踏上了漫漫求索的取經之路。這一路,或許是坎坷艱辛的吧?西行,約莫是黃沙萬里的征途,飛沙走石的蜿蜒路上,昏黃的天穹低如垂暮,長河落日圓,地平線那邊的落日把使者隊伍的影子拉的細長,悠長的駝鈴聲亦被朔風攪碎,但他們依然堅持著前行。
風塵仆仆的取經者,裹著滿身風沙,一腳深一腳淺,用一個個腳印丈量著巨大的時空的差距。然后,于某個黃沙蔽日的清晨或黃昏,他們抵達了大月氏國(今阿富汗境至中亞一帶)。月氏本是世居我國河西、祈連山一帶的游牧民族,秦時他們為匈奴所敗,西遷伊犁河、楚河一帶,后來輾轉傳來消息又敗于烏孫,于是月氏西擊大夏,占媯水兩岸而建立大月氏王國。
我從未想到,這樣一個地方,會是我的使臣最先接觸佛法之地。在大月氏國,他們遇到印度高僧攝摩騰、竺法蘭,見到了佛經和釋迦牟尼佛白氈像,于是便懇請二位高僧東赴中國弘法布教。
距離金人飛舞的夢已經過去三年了,終于在永平十年時,攝摩騰、竺法蘭和我的使者一道,回到了帝都洛陽。與他們一道而來的,還有馱載佛經、佛像的白馬。我親自接待了兩位印度高僧,以最高禮遇邀請他們住下。官署“鴻臚寺”不足以彰顯我的歡喜,永平十一年,我為他們在洛陽城東興建新的僧院,為紀念白馬馱經,取名“白馬寺”。
《尚書中侯·握河記》曰:“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于河。”龍馬負圖,始生八卦,伏羲觀之,始作八卦。而我的佛經,也是白馬負之而來的。作為和龍一樣神異的生靈,也只有這樣通靈性的白馬才會騰空西來,繞塔哀鳴吧。我亦愿意亦白馬悲愴雄壯的蕭蕭長嘶來向世人明道,顯示佛法的來之不易。
攝摩騰和竺法蘭在白馬寺譯出了《四十二章經》,為現存中國第一部漢譯佛典。在攝摩騰和竺法蘭之后,又有多位西方高僧來到白馬寺譯經,在之后的一百五十多年時間里,有一百九十二部,合計三百九十五卷佛經在這里譯出,白馬寺成為當之無愧的中國第一譯經道場。
白馬寺,這樣一個滄海遺珠般的佛國重地,如星子,如珍珠,熠熠生輝,光華滿溢,精美得讓歷史的旁觀者睜不開眼。太過美好的東西,總是要經歷他不應承受的過多磨難。盡管白馬寺如此之重要,可在東漢末年的軍閥混戰中,他還是第一次遭到了破壞。東漢初平元年,以渤海太守袁紹為盟主的各地聯軍,對洛陽形成了半包圍的陣勢。為防止人民逃回,袁紹便把洛陽城周圍二百里以內的房屋全部燒光,白馬寺被燒蕩殆盡。
東漢建安二十五年,曹丕自稱皇帝,即位于許昌。在東漢洛陽廢墟之上,重新營建洛陽宮,也包括重建白馬寺。曹魏嘉平二年,印度高僧曇柯迦羅來到白馬寺。此時佛教也從深宮走進了市井民間。隨后,曇柯迦羅在白馬寺譯出了第一部漢文佛教戒律《僧祗戒心》。同一時期,安息國僧人曇諦,也在白馬寺譯出了規范僧團組織生活的《曇無德羯磨》。至此,戒律和僧團組織章程都已齊備,一條中土有緣人出家持戒修行的道路鋪就,為中土戒律之始。
曹魏甘露五年,一場受戒儀式在白馬寺舉行,這是一個注定要深深印刻在中國佛教史上的事件。這一天,朱士行依《羯磨法》登上戒壇,長跪于佛祖面前,成了中國漢地第一位正式受過比丘戒的出家人。自此,儒家“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古老傳統被打破了。
佛教在中國扎根、傳播最初的二百年,整個過程都與白馬寺息息相關。這里是中國第一次西天求法的產物,是最早來中國傳教弘法的僧人的居所;這里誕生了第一部中文佛經和中文戒律,產生了第一個中國漢地僧人……總之,白馬寺是與中國佛教的許許多多個“第一”緊緊聯在一起的,這讓它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佛教的祖庭和釋源。
然而之后的白馬寺,仍舊無數次在戰火中被損毀,又無數次在百廢俱興中重建——
西晉永安元年,司馬颙部將張方攻入洛陽,燒殺虜掠,在長期的戰亂兵火中,白馬寺再一次遭受嚴重破壞。
北魏末年的“永熙之亂”,洛陽城又一次殘遭破壞。在遷都鄴城之后,洛陽僅余寺421所,其中,尚有白馬寺。大約在“永熙之亂”中,白馬寺雖難于幸免,但還是殘存下來了。
唐武周垂拱元年,武則天敕修白馬寺,這是白馬寺歷史上的黃金時代。
唐代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對東都洛陽的破壞甚為嚴重。白馬寺當亦然。
唐代末年,洛陽長時期陷入戰亂兵火,白馬寺再次遭受戰亂的破壞。
宋代淳化三年,宋太宗敕修白馬寺。
明代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太祖朱元璋敕修白馬寺;景泰年間,明政府曾規定各地寺觀產業限制為六十畝。
嘉靖三十四年,身為朝廷司禮監掌印太監兼總督東廠之職的黃錦,又一次大規模整修白馬寺。由黃錦撰文的《重修古剎白馬禪寺記》石碑,保存了關于此次重修的詳細資料。此次重修,大體上奠定了今日白馬寺的規模和布局,在白馬寺沿革史上意義重大。
明代末年,洛陽又遭戰亂破壞。
清代同治元年,立佛殿(接引殿)被焚燒;光緒九年復被重建。清代宣統二年,又重修清涼臺之毗盧閣。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南京國民黨政府決計遷都洛陽,見那時的白馬寺墻敗宇塌,庭階荒蕪,便委請上海佛教會德浩法師住錫白馬寺,重行營建。
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州大地處于戰亂兵火之中,白馬寺兩度敗落,墻頹殿傾,野草沒膝,一片荒涼景象,一直持續到解放前夕。
新中國成立后,白馬寺先后于1952年、1954年、1959年多次撥專款重修。1961年,國務院確定白馬寺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文革”之時,白馬寺也慘遭破壞。佛像被砸,經卷被燒。相傳為攝摩騰、竺法蘭二高僧帶來的極為珍貴的三十余片“貝葉經”也化作灰燼。
1972年對白馬寺的全面修復,這一次重修,前后持續十年,用款數十萬之多,翻修主要殿閣,彩繪天棚、梁、架、斗拱,油漆門窗、殿柱,廣騁新老藝人塑造佛像,貼金涂彩;培植花木,徹階修路。使千年古剎,面貌為之一新。
1973年,正式成立了文物保管所。
1984年,移交洛陽市佛教協會和僧人管理。一些在“十年動亂”時被迫還鄉的僧人也先后返寺。國家對他們進行了妥善的安排,使其誦經有所,衣食有靠;還為僧人的佛事活動而配設了多種香案、供器、七珍八寶,在大殿內懸掛幔帳,蓮臺前擺列蒲團,逐漸恢復了這座千年古剎固有的宗教氣氛。
1987年3月,寺院的山門、大佛殿、天王殿得到維修加固。
1990年,齊云塔院得到擴建。
……
如今的白馬寺不知經歷了幾世幾劫,亦不知還有幾分當初明帝初建時的樣貌。清晨伴著朝陽的響起鐘聲,傍晚時分和著薄暮遠遠送出的鼓聲,還有青燈下佛陀誦經的呢喃,交相呼應,共同奏出一曲梵唱,消弭在清心禮佛的背景中。暴雨將歇,厚重的云層日益稀薄,金色的陽光穿云而過,以佛光普照的姿態灑向大地,為萬物鍍上一層迷人的金色。檐角的青苔,仍有宿雨滴下,瓦當上的痕跡仍依稀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