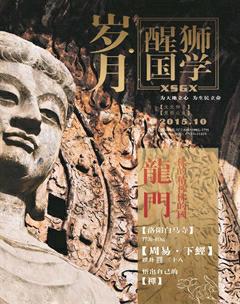全真道士的詞意境
倪博洋
對于今天的讀者來說,除了元曲,元代其他文學幾乎是完全陌生的。文學史到了元代似乎產生了一個斷層,唐宋時期昌盛發達的詩詞在此時統統失語,成為不為人注意的背景點綴。后人不僅以氣格卑弱形容元詩,還做出了“詞衰于元”的判斷。就后者而言,真令當代讀者舉出一位元代詞人,恐怕是一件難事。而若說活躍于金庸先生《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等小說的全真道士也能如蘇軾柳永一般填詞,那就更出乎我們的想象了。實際上全真道士不僅會作詞,而且愛作詞,著名的《全金元詞》一書竟然有二分之一弱的篇幅都是全真詞作。這實在使人驚訝。而問題也就來了,全真詞水平如何,元代文人又如何看待這些詞壇上的“不速之客”?
客觀的說,全真詞多是談道說理的枯燥之作,但并非沒有佳什。我們來看一首馮尊師詞。馮尊師是一位全真高道,其詞有二十首《蘇武慢》收于《鳴鶴馀音》一書,這里選擇其一:
夢斷槐宮,倚天長嘯,勘破物情今古。擔簦映雪,射虎誅龍,曾把少年身誤。金谷繁華,漢苑秦官,空有落花飛絮。嘆浮生、終日茫茫,誰肯死前回顧。 爭似我、玉麈清談,金徽雅弄,高臥洞天門戶。逍遙畎畝,肆任情懷,閑伴蓼汀鷗鷺。收拾生涯,紫蟹黃柑,江上一蓑煙雨。醉歸來、依舊蘆花深處,月明幽浦。
與我們對全真道士固有印象不同,這闋詞著實令我們驚異。從藝術看它有不少可稱道之處,整體結構上則上下兩片構成精妙對比,上片氣勢豪放悲涼,下片情致清幽寂雅,具有較強的藝術性。作者首先從“夢斷槐宮,倚天長嘯”下筆,“槐宮”指的正是南柯一夢中的大槐安國。然而既然已經勘破了世事繁華,然而偏偏要倚天長嘯,這種矛盾來自何處呢?且看作者描繪出一個射虎誅龍,氣吞山河的少年豪俠形象。本來這位少年應有一番作為,但最終空有屠龍之技,不得施展。不僅其身被誤,就連其所屬的時代象征:西晉金谷,秦宮漢瓦,都化為一片荒原。這樣作者就從個體的人反思到整個歷史。而最后的結句尤其加深了這一思考,把無窮的時間、無常的生死與有限的個體交織起來,由人生而家國,由家國而存亡,這使我們不得不再三深思人生的意義與歷史的無常。而正當我們感慨于作者筆墨勾起的波瀾時,下片的勾勒安排卻又好像恬淡無波的湖面。作者彈琴高臥,逍遙快活,在鷗鷺煙雨中逍遙自遂。這里作者是個手持紫蟹黃柑的隱士形象,而非悟道打坐的道人形象,文學的形象美感壓倒真實的社會身份,給人的是審美享受。其節奏之舒緩,文字之從容,似乎和上片長嘯高歌的氣氛不協調。但我們知道,沒有少年時的喑啞叱咤,沒有少年時的慷慨悲歌,就沒有老來的平淡自在。上片是積累,下片是升華。作者精致的筆墨就給我們展示出一片有別于傳統儒家事功選擇的人生圖景。
那么這類詞是否存在態度消極的一方面呢?我們先來看看當時人的選擇。元代有個叫虞集的著名文人,既是理學家,又詩詞文皆善,被譽為有元“一代文宗”今存虞集詞中恰有數篇和馮尊師的《蘇武慢》,且看他的追和:“老矣浮丘,賦詩明月,千仞碧天長劍。雪霽瓊樓,春生瑤席,容我故山高宴。待雞鳴、日出羅浮,飛渡海波清淺。”恰好和馮詞趣味一致。而另一位元末明初理學家凌云翰也和了馮詞,他的“世事浮云,人生大夢,歧路漫悲南北”的領悟也與馮酷肖。元代的理學大儒都喜歡馮詞,不是因為他們選擇了消極的人生態度,而是將道家或道教的隱逸追求作為儒家修齊治平的一種補充。當代我們津津樂道的儒道互補其內涵正是如此。但還有一點需要注意,傳統文化具有包容性,儒道互補不代表反對“純儒”或“純道”,馮尊師的《蘇武慢》完全是道家語,但不妨礙儒家大儒虞集凌云翰等對它的喜愛。
回到馮尊師的這首詞,“小詞雖小,意義俱全”。它至少給我們三個方面的啟示,一是元詞未必“衰”,有不少平日忽視的作者為之努力。二是元代未必是一段百年的文化荒漠,在相對貧瘠的土壤也能開出艷麗的文化花朵。三是對當代整個國學復興來說,我們疏漏忽視的文化精華還很多,小到一篇詞,大到一個文人,一個時代,都有我們繼續值得努力探索的必要。“路漫漫其修遠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