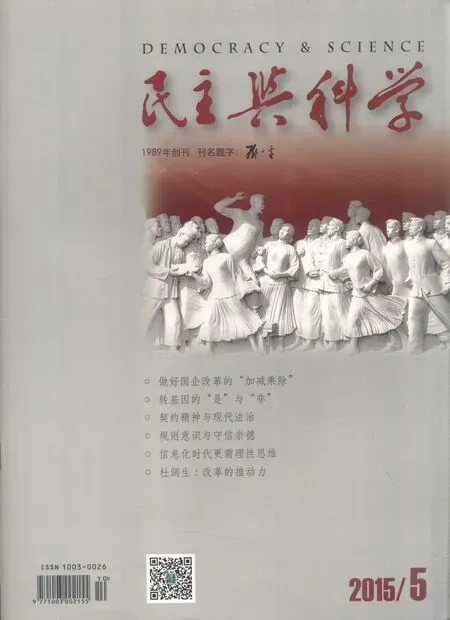契約精神與現(xiàn)代法治
■ 徐愛(ài)國(guó)
契約精神與現(xiàn)代法治
■ 徐愛(ài)國(guó)
契約精神是現(xiàn)代的產(chǎn)物。古代法律注重人類社會(huì)的共同利益,強(qiáng)調(diào)個(gè)人對(duì)于社會(huì)的身份依賴;現(xiàn)代法律倚重個(gè)人權(quán)利,突出意思自治的契約自由。歷史學(xué)家稱,進(jìn)步社會(huì)的運(yùn)動(dòng)是一個(gè)從身份到契約的演變。所謂從身份到契約,是指法律本位從家族到個(gè)人的發(fā)展。在古代社會(huì),所有人都依附于家族——妻子依附丈夫、兒子依附父親、仆人依附主人。依附者沒(méi)有獨(dú)立法律人格,不能為自己私利以個(gè)人名義做出法律上的決定。現(xiàn)代社會(huì)下,個(gè)人逐漸脫離家族束縛,也就是擺脫了身份,能夠按照自己意愿處理人身和財(cái)產(chǎn)。個(gè)人之間的合意,可以概括為契約。法律從身份到契約的發(fā)展,便是古代法向現(xiàn)代法的過(guò)渡。
契約精神物化為具體法律,可以稱為以法治為目的的行為規(guī)范。財(cái)產(chǎn)法的現(xiàn)代精神是個(gè)人自決地取得、占有和處分個(gè)別財(cái)產(chǎn)。而在古代社會(huì),個(gè)人并不能取得和享有私人財(cái)產(chǎn),財(cái)產(chǎn)實(shí)際上為家族或村落共同所有。私有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神圣性乃是現(xiàn)代法治的體現(xiàn)。一個(gè)人將自己的財(cái)產(chǎn)按照意愿轉(zhuǎn)讓他人,雙方合意通過(guò)等價(jià)交換達(dá)成互惠互利,是財(cái)產(chǎn)契約的基本屬性。古代社會(huì)財(cái)產(chǎn)交換注重財(cái)產(chǎn)轉(zhuǎn)讓的外在“儀式”,現(xiàn)代則注重雙方當(dāng)事人內(nèi)在的合意和協(xié)議,有了自由意志和個(gè)人自決,契約法才從古代發(fā)展到現(xiàn)代。繼承法的現(xiàn)代意義是,個(gè)人可以按照自己意愿立遺囑處理自己財(cái)產(chǎn),繼承人只繼承權(quán)利而不承擔(dān)無(wú)限義務(wù)。而古代繼承則是“概括繼承”,繼承人同時(shí)承擔(dān)被繼承人的權(quán)利和義務(wù)。這意味著,死亡者的肉體人格雖然死亡,但是他的法律人格依然存在,毫無(wú)減損地傳給繼承人或共同繼承人。現(xiàn)代婚姻以兩性生育和撫養(yǎng)子女為基本特點(diǎn),婚姻是男女兩性的結(jié)合,是神法與人法的結(jié)合。婚姻是一份契約,男女雙方合意共同生活、生育撫養(yǎng)后代。因?yàn)殡p方平等契約,所以夫妻有平等對(duì)待的權(quán)利和義務(wù),有相互扶助的義務(wù)和責(zé)任,夫妻存續(xù)期間所得歸夫妻共有,離婚時(shí)男女均分共有財(cái)產(chǎn)。與此不同,古代婚姻目的有二,一是家族延續(xù),二是通過(guò)聯(lián)姻擴(kuò)展政治權(quán)利。婚姻權(quán)歸家父,而非男女雙方,于是才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說(shuō)。
契約理念與個(gè)人自治和自由競(jìng)爭(zhēng)的現(xiàn)代觀念一致。19世紀(jì)歷史學(xué)家與18世紀(jì)理性主義者對(duì)法律現(xiàn)代化的認(rèn)識(shí)相同。不同的是,19世紀(jì)法律史學(xué)家把研究課題從現(xiàn)代追溯到古代,探討古代法律如何歷史地過(guò)渡到現(xiàn)代,展現(xiàn)了西方社會(huì)亦即他所謂的“進(jìn)步社會(huì)”的法律發(fā)展史。簡(jiǎn)練的“從身份到契約”的口號(hào),成為19世紀(jì)后法律界廣泛認(rèn)可的法律名言。英國(guó)人梅因考察了以羅馬和英國(guó)為代表的西方法律和以印度為代表的東方法律。在他那里,西方社會(huì)是少數(shù)和進(jìn)步的社會(huì),東方社會(huì)則是多數(shù)和停滯的社會(huì)。在法律發(fā)展模式上,法律自發(fā)的發(fā)展東西方?jīng)]有差別,都經(jīng)過(guò)了從宗教意味的個(gè)別判決到貴族壟斷的習(xí)慣法最后到法典的過(guò)程。此后,東西方法律發(fā)展發(fā)生分野,少數(shù)和進(jìn)步的西方社會(huì)經(jīng)過(guò)“法律擬制”“衡平”和“立法”完成從古代向現(xiàn)代法律的轉(zhuǎn)型。
當(dāng)西方社會(huì)在近代興起時(shí),東方社會(huì)開始由興盛轉(zhuǎn)向衰落,其中原因,就是東方人喜歡靜止和抗拒變化的本性。歷史學(xué)家的判斷總會(huì)有相似之處,梅因“少數(shù)與進(jìn)步”社會(huì)的法律進(jìn)化論,與后來(lái)德國(guó)人韋伯“唯有新教倫理才能產(chǎn)生資本主義”及“法治只是西方社會(huì)特有的偶然現(xiàn)象”命題,同出一轍。在1922年發(fā)表的《法律史解釋》中,美國(guó)人龐德承認(rèn)梅因“從身份到契約”的著名論斷“為英美法律思想所普遍接受,并一直統(tǒng)治到19世紀(jì)末。它現(xiàn)今仍在美國(guó)憲法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將個(gè)人契約上升到國(guó)家制度層面,可以說(shuō)現(xiàn)代法治國(guó)家的基石就是社會(huì)契約論。盧梭的《社會(huì)契約論》是傳入中國(guó)最早的政治法律著作之一。從他的社會(huì)契約論,中國(guó)人開始知道“人民主權(quán)”“公意”“自由”和“平等”,甚至“法治”這樣的名詞術(shù)語(yǔ)。18世紀(jì)的盧梭不是社會(huì)契約論的發(fā)起人,而是社會(huì)契約論集大成者。政治權(quán)力源于人民授權(quán);通過(guò)主權(quán)者與人民之間的契約,人類社會(huì)從野蠻的自然狀態(tài)進(jìn)入文明的現(xiàn)代社會(huì);政治和政府的任務(wù)應(yīng)該是保護(hù)人民生命、自由和財(cái)產(chǎn);法律是人民意志的宣告。這些現(xiàn)代法律精神在17至18世紀(jì)的學(xué)者那里屢見(jiàn)不鮮,其中有人們熟知的格勞秀斯、普芬道夫、霍布斯、洛克、狄德羅和孟德斯鳩等。社會(huì)契約論與其說(shuō)是哪一個(gè)人的思想成果,還不如說(shuō)是整個(gè)17至18世紀(jì)世界性的思想啟蒙運(yùn)動(dòng)。
近代社會(huì)契約論是講,人類進(jìn)入文明社會(huì)之前,沒(méi)有公共權(quán)力,也就沒(méi)有法律,他們按照自己本性過(guò)著野蠻生活。當(dāng)人民感到自然狀態(tài)無(wú)序和混亂所導(dǎo)致的孤獨(dú)、貧困、卑污、殘忍和短壽的時(shí)候,想到一種相互結(jié)合方式,利用集體力量來(lái)保護(hù)個(gè)人權(quán)利,于是就通過(guò)社會(huì)契約方式聯(lián)合起來(lái)。人民把在自然狀態(tài)下的自然權(quán)利轉(zhuǎn)讓出來(lái),把個(gè)人權(quán)利組合成一種公共權(quán)力,這個(gè)權(quán)力讓一個(gè)凌駕在個(gè)人之上的主權(quán)者掌握,這個(gè)主權(quán)者可以是一個(gè)君主,一個(gè)代表機(jī)關(guān),也可以是一個(gè)抽象人格。因?yàn)楣矙?quán)力來(lái)自人民授權(quán),因此君權(quán)民授或者主權(quán)在民;因?yàn)橹鳈?quán)者與人民有契約,因此主權(quán)者行使政治權(quán)力時(shí)候要保護(hù)人民利益;因?yàn)榇蠹叶甲袷刈约褐Z言,因此就有了共同意志之下的法治。從這個(gè)意義講,社會(huì)契約論實(shí)際上是一種公共權(quán)力起源理論,即國(guó)家與法律的民主起源說(shuō)。
社會(huì)契約論在實(shí)踐上發(fā)生了革命性影響。法國(guó)人特有的浪漫、激情和博愛(ài)打動(dòng)了歐洲人,最后通過(guò)殖民活動(dòng),自然權(quán)利、社會(huì)契約和人民主權(quán)理論傳遍世界。法國(guó)《人權(quán)宣言》稱,人生而平等自由,主權(quán)源于國(guó)民,法律是公共意志表現(xiàn),自由、財(cái)產(chǎn)、安全和反抗壓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權(quán)利。這些語(yǔ)言基本上來(lái)自盧梭的《社會(huì)契約論》。美國(guó)《獨(dú)立宣言》稱,人生而平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是人們不可轉(zhuǎn)讓的權(quán)利。這些內(nèi)容基本上都來(lái)源于洛克的《政府論》。即使是孫中山的“一國(guó)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ài)之精神”和“共和國(guó)之根本在法律,而法律之命脈在國(guó)會(huì)”,乃至他的“五權(quán)分立”,也無(wú)不有著洛克、孟德斯鳩和盧梭理論的影子。社會(huì)契約論擺脫了人類歷史包袱和羈絆,讓人民容易直接將自己的理想轉(zhuǎn)化為政治與法律現(xiàn)實(shí)。
當(dāng)代學(xué)者在設(shè)計(jì)社會(huì)公平理想制度時(shí)候,也會(huì)回到社會(huì)契約論。羅爾斯社會(huì)公平論的核心是,自由優(yōu)先、平等糾錯(cuò),他的論證方式還是契約論。他的“無(wú)知之幕”和“原初狀態(tài)”的理論前提,不過(guò)是社會(huì)契約論中“自然狀態(tài)”和“權(quán)利轉(zhuǎn)讓”的一個(gè)現(xiàn)代翻版。德沃金聲稱自己不是一個(gè)傳統(tǒng)自由主義者,當(dāng)他提出“認(rèn)真看待權(quán)利”口號(hào)的時(shí)候,他所呼吁的“自由和尊嚴(yán)的不可侵犯性”和“社會(huì)弱者的保護(hù)”,他所倡導(dǎo)的法律原則優(yōu)先于既定法律規(guī)則的法律帝國(guó),都從17至18世紀(jì)社會(huì)契約論的遺產(chǎn)中得益頗多。
中國(guó)社會(huì)進(jìn)入現(xiàn)代法治社會(huì),必定要經(jīng)過(guò)從家父權(quán)到共和國(guó)的過(guò)渡。一方面,動(dòng)態(tài)上考察,中國(guó)實(shí)行法治,必定要以現(xiàn)代個(gè)人自治取代家長(zhǎng)制觀念;另一方面,靜態(tài)上考慮,必定要樹立民主觀念,國(guó)家公共權(quán)力來(lái)自人民。這個(gè)過(guò)程經(jīng)過(guò)百年,但是任務(wù)依然艱巨。
中國(guó)古代社會(huì)基本結(jié)構(gòu)為家庭,小家庭有家長(zhǎng),大家族有族長(zhǎng)。家長(zhǎng)對(duì)外代表家庭承擔(dān)家庭成員的法律責(zé)任,對(duì)內(nèi)享受家父權(quán)。瞿同祖說(shuō),每一家族能維持其單位內(nèi)之秩序而對(duì)國(guó)家負(fù)責(zé),整個(gè)社會(huì)秩序自可維持。親親相隱、留養(yǎng)存嗣、子孫違反教令、一夫一妻多妾、親屬相犯與相奸,都是濃厚中國(guó)特色的法律制度。
對(duì)于中國(guó)古代法律特質(zhì),法律史學(xué)家有各種各樣的描述,不過(guò),公認(rèn)特質(zhì)便是法律上的家族主義和等級(jí)特權(quán)制度。社會(huì)基本單元是家庭,男性長(zhǎng)者為家長(zhǎng)。家長(zhǎng)既握有家庭成員的懲戒權(quán),同時(shí)也是對(duì)外法律責(zé)任承擔(dān)者。若干同宗之家,推選同族族長(zhǎng),族內(nèi)糾紛的處斷者便是族長(zhǎng)。家族是最初級(jí)的司法機(jī)關(guān),家族內(nèi)的糾紛先由族長(zhǎng)仲裁;不能夠調(diào)解處理,才由國(guó)家司法機(jī)構(gòu)處理。親屬間的殺傷、盜竊和奸非按照親屬遠(yuǎn)近服制懲戒,一般原則是尊犯卑減免處罰,卑犯尊加重處罰,完全不同于常人間的犯罪與懲罰。親屬間的容隱既是家庭成員間的權(quán)利,也是法律義務(wù)。
西方現(xiàn)代法律起源于啟蒙學(xué)者對(duì)封建法律的批判,從理論角度看,18世紀(jì)的社會(huì)契約論戰(zhàn)勝了古代社會(huì)的君主主權(quán)論,法律人道主義戰(zhàn)勝了法律暴虐主義。19世紀(jì)后,西方各國(guó)在政治和法律制度層面確立了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權(quán)。到中國(guó)清修律的19世紀(jì)末期,西方各國(guó)已經(jīng)完成法律的人道主義改造,而當(dāng)他們殖民到東方世界的時(shí)候,遭遇東方專制主義。清末修律的象征意義,就是要在中國(guó)對(duì)野蠻的法律進(jìn)行人道主義改造。百年過(guò)去了,家族制基本上在法律層面消失,但是人民當(dāng)家作主尚未實(shí)現(xiàn)。官僚主義、等級(jí)特權(quán)和家長(zhǎng)遺風(fēng),在社會(huì)中依然存在且根深蒂固。這是中國(guó)當(dāng)下法治面臨的艱巨任務(wù)。十八屆四中全會(huì)提出依法治國(guó)的目標(biāo),實(shí)現(xiàn)這個(gè)理想,中國(guó)法治才有希望。
(作者為北京大學(xué)法學(xué)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