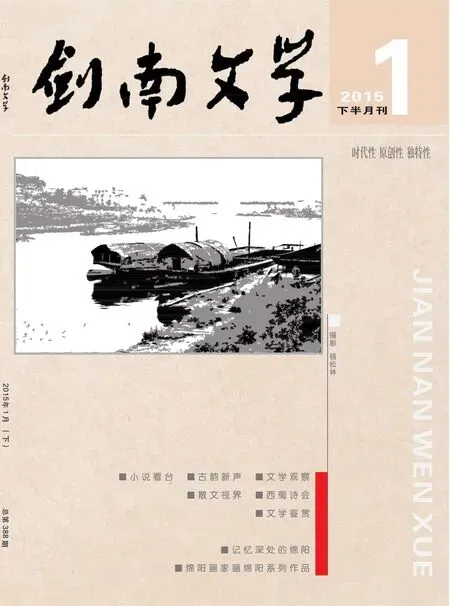論殘雪小說中的意象
■呂 晗
引言:殘雪是蜚聲海內外的新時期先鋒派作家,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文學創作以來,一直堅守著與現實對抗,與傳統對抗的創作原則。她筆下的純文學,既因為晦澀、惡心而令人“不忍卒讀”,也因為直達靈魂深處而令人折服。長期以來,殘雪文本在國內的解讀都充滿了爭議。從意象分析入手研究殘雪的中短篇小說,能夠理解作者如何將大眾眼中的日常現實變形為她筆下的那種癲狂狀態。
20世紀80年代中期興起的先鋒派小說,早已由如火如荼轉為悄然寂寞了,如今只有有限的幾位作家仍在先鋒派領域筆耕不輟,殘雪便是其中耀眼的一位。
二十多年來,殘雪小說的內在精神不斷提升,思想追求日漸清晰,直指無窮盡的人的心靈世界。初涉殘雪的小說世界,可能會因其錯亂、壓抑、焦慮、緊張以及對被害的臆想而止步,但當你深入其中,就會被作者對靈魂的深刻認識而震撼。殘雪正是運用與眾不同、含義深刻的意象來表現人性中癲狂的一面。
一、意象內涵
意象是中國古典文學的一個審美范疇,也是中國古代文藝美學和詩歌美學的重要概念,是中國文藝理論的固有元素。我國作為意象理論的發源地,長期把意象藝術運用于文學創作之中,形成了系統的認識。
意象是客觀物象經過創作主體獨特的情感活動而創造出來的一種藝術形象,是作家的主觀情感和客觀景物交融互滲的產物,是作家傳達情感、表現思想、升華意志的基本方式。它包括兩方面因素:一是主觀的情、思、意、志,即審美主體;二是客觀的景、象、物、境,即審美客體。一個完整和諧的意象,是意和象兩個要素通過語言這一媒介進行感應、交流、契合的結果。殘雪在創作過程中,充分把握意象內涵,廣泛采用并列、對比、通感和荒誕等意象構建手法,使其作品呈現出無窮的魅力。
二、殘雪小說中的意象
殘雪小說堪稱意象的世界。作者賦予一個個或和諧美好、或令人作嘔的事物與眾不同的含義,在提升作品思想深度的同時,增加了文本內涵的多義性,無意中給讀者接受設置了障礙,給予讀者廣闊的理解空間,使各不相同的個性化解讀有了意義。
(一)動植物意象
殘雪的小說中經常出現植物類意象,樹、花、果等等都很常見。如《蒼老的浮云》中,“楮樹上的大白花含滿了雨水,變得滯重起來,隔一會兒就‘啪嗒’一聲落下一朵。”《天窗》中,“在冬夜里,我將細細地傾聽那些腳步聲,把梧桐樹的故事想個明白。”《天堂里的對話(之一)》中,“那是一棵銀杏在湖心水的深處搖擺,樹上滿是小小的鈴鐺,鈴鐺一發光,就燦爛地轟響。”殘雪筆下的植物多得不勝枚舉。
在《蒼老的浮云》中,作者寫楮樹意在寫其花和果,花和果是貫穿全文的一條微妙線索。如小說開頭寫到花香對人的影響:“一通夜,更善無都在這種煩人的香氣里做著夢。那香氣里有股濁味兒,使人聯想到陰溝水,聞到它人就頭腦發昏,胡思亂想。”這種意象一直貫穿全文,使人無法擺脫:“楮樹的花香弄得人心神不定……”“那些花兒開得人心惶惶的。”花香擾人的感受多次從不同的人物口中說出,每個人都深受其害。小說中的人物對果子的關注也很明顯:“好久以來,他就盼望著樹上的那些果子變紅,因為他對她說過,等樹上結出紅漿果,大家就都能睡得安穩了。”在這部小說中,主要的植物意象是樹,其中突出樹的開花、結果等發展變化過程,以及這種自然過程中花香、紅果與人物情緒的關系。
動物也是頻繁出現在殘雪小說中的一類重要意象,殘雪筆下的老鼠尤為出彩。《蒼老的浮云》中,老鼠頻現,“天花板一角有許多老鼠在穿梭,爪子撥下的灰塊不斷地打在帳頂上。”《黃泥街》中,老鼠大舉入侵人們的生活:“果然有一天,一只大老鼠爬到了床上,將她男人的耳朵咬穿了。”而在《母鼠》中,老鼠更成了主角,成了一家人生活的中心:“它靜靜地躲在我的鞋柜里頭,根本就不危害誰的利益。不錯,為了它,我常把地板弄得油跡斑斑,它的糞便也遺留在墻角,但嫂子并沒有對我埋怨什么啊。不但不埋怨,她好像還很支持我養這只母鼠呢。”
在殘雪的小說中,主要表現了鼠與人的三種關系。一是老鼠與人平等,動物與人作為平等的主體共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互不干涉。如《蒼老的浮云》中,“他不敢回頭,像小偷一樣逃竄。一只老鼠趕在他前頭死命地竄到陰溝里去了。”這里的老鼠是更善無性格中卑微膽小因素的外化,他“像小偷一樣逃竄”,老鼠與他的動作一致,也是“竄”,生動形象地表現了更善無鼠一樣怯懦的性格特征。二是人仰仗鼠,人們在精神上或生理上依賴老鼠,如虛汝華要依靠老鼠的咬嚙聲來緩解神經的劇痛,她自己也不停地咀嚼。三是鼠主宰人,人們對老鼠的存在敬畏不已。
殘雪說:“不論小說中出現的蟲還是動物,決不是現實中生存的蟲和動物。因為那是我空想的東西。”殘雪文本中的蟲子、老鼠、蛇并不是先驗地被設定為“丑”,它們只是一種單純的客觀存在,隨機出現在作者的潛意識建構的環境中。殘雪曾多次強調孩童的眼光:“我就是用一個兒童的眼光來看這個世界。兒童的眼中沒有所謂美丑,也沒有社會化的世俗的東西。”“寫這些動物是表現一種意境,寫的時候無所謂美丑,用小孩的眼光,覺得奇特、有意思。”這說明了作者運用所謂的“丑”意象時的原則:只為遵循潛意識中的意境更好地表達思想、主題,而不管意象本身所傳達的、早已被世俗規定的傳統含義。
(二)器物意象
殘雪小說往往以日常器物作為意象,鏡子便是其中之一。《蒼老的浮云》中,“我已經在后面的墻上掛了一面大鏡子,從鏡子里可以偵察到他們的一舉一動,方便極了。”《公牛》中,鏡子更是頻繁出現:“我從墻上的大鏡子里看見窗口閃過一道紫光。”《布谷鳥叫的那一瞬間》中,鏡子十分詭異:“我建議和他玩一種游戲,就是兩人手牽手走進那些鏡子里面去,我們把青蟲打落在地上,朝著鏡子外面吐口水。”
殘雪在與文學評論家林舟進行書面訪談時說:“鏡子的設置就是為了來審視自我的。”作者為每個人都設置了一面審視靈魂的多棱鏡,在窺探別人的同時,也反射出自己的心靈。殘雪文本也因此多了一柄直搗人類靈魂世界的利劍。
意象使殘雪作品帶上了寓言的特征。寓言式的作品能夠打破文本在封閉狀態下意義的確指,使寓意成為待挖掘的不確定物,讓讀者成為文本的主人。讀者享有高度自由,反過來也賦予了殘雪文本豐富的多義性,讓閱讀更有趣味。
三、殘雪小說中的“意象”與“審丑”
殘雪小說往往讓讀者強烈地感受到壓抑、焦慮甚至極度的緊張。這既是因為她沒有采用傳統的寫作手法,淡化或拋棄了情節,放棄了對因果關系的交代,也是因為她使用過于繁密、奇特的意象讓人難以理清頭緒,更是因為她叛離傳統的審美方式太遠了。隨著西方現代派思想廣泛傳播,大眾對人性的理解愈加深刻:人性具有兩重性,美丑并存、相互斗爭,人的靈魂處于痛苦的撕裂狀態。殘雪的寫作就處于這撕裂的空間之中。殘雪將她的每個人物都視為一個矛盾著的個體。她說:“中國傳統文化認為‘人之初性本善’,可是人性并非善惡兩極,人性是一個矛盾,每個人身上都有善有惡。”受到這種思維的影響,殘雪的作品難免會描寫人性惡。
殘雪用荒誕的意象、特異的寫作手法與陌生的語言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神秘且奇詭的世界。她的小說仿佛一面鏡子,反映出世界的荒謬、滑稽與可笑。事實上我們每個人都很弱小,沒有能力去改變生存的環境,那些崇高的、美麗的理想只是理想而已。這種對命運的終極關懷,充滿了悲傷與憂慮,但我們從中可以感受到殘雪的內心是那么熱烈地渴望美,那么迫切地呼喚美,那么執著地追求著人類走出自身困境的嶄新開始。小說對丑的大量描寫正是對美的饑渴,小說中的荒誕正是對美好生活的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