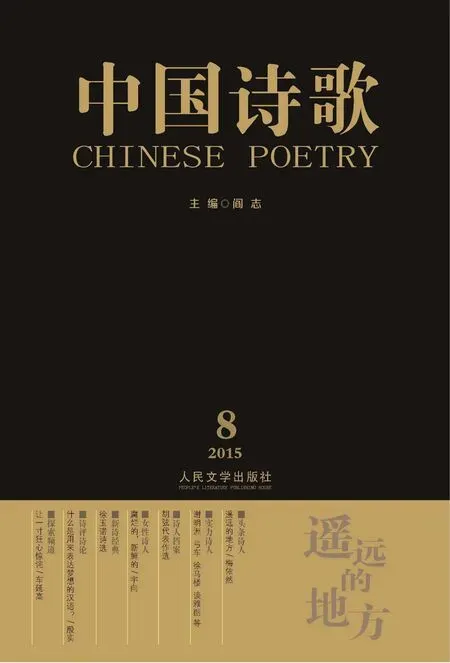“千萬不要把寫詩當個事兒”
——楊獻平訪談
□桫欏楊獻平
“千萬不要把寫詩當個事兒”
——楊獻平訪談
□桫欏楊獻平
桫欏:去年你的《生死故鄉(xiāng)》影響甚廣,“百度”一下能得到一千多個結果。你不要得意,今天先不談散文,聊聊詩歌。記得之前跟你說過,我喜歡你的詩——盡管一個做理論的這樣暴露個人好惡不太好,但我還是忍不住表達一下心情。其實,在我看來,詩才是你的“文學”,散文只是你的“職業(yè)”。你自己認為呢?
楊獻平:《生死故鄉(xiāng)》不是我最得意的一本散文集,但是“效果”最好的一本散文集。此前的《沙漠之書》也不錯,盡管其中沒有特別驚艷的作品。
對我個人來說,在文學這條路上,詩歌可能真的是我的主業(yè)和最強項,而且是無意之中得來或修來的。剛開始寫東西的時候?qū)懺姡液苌闲摹懥藥啄曛笤倏矗约旱脑姼璨皇瞧渌娙说膶κ帧T僬撸X得詩歌這東西是有些限制的。“體量小”導致的麻煩是,你必須回旋著去表達。盡管這是詩歌的強項。詩歌也是文學體裁中的“塔尖”建筑或者建構,但當下的詩歌,尤其是近十年來的詩歌,倘若細讀下來,我相信每個有眼光的人都是失望的。
必須要說的是,魯院幾個月,我個人最大收獲,大抵是重新開始寫詩。
我自己也認為我的詩歌要比散文好,批評要比小說強。散文我最用心,但效果可能最差;小說是剛開始寫著玩。當然,詩歌也是玩。我認為,玩是文學出其不意、登峰造極的不二法門。這就像我相信文學天才就在我們中間一樣。
桫欏:看似云淡風輕的背后,其實隱藏著無名的秘密。你我都是“70后”,我感覺這個代際的人都曾經(jīng)是文學青年。你的文學夢是從詩歌開始的嗎?假如不是,你是怎么想起來寫詩的?你還記得你發(fā)表的第一首或第一組詩嗎?
楊獻平:每個好作家都是詩人。賈平凹也寫過詩。但我不是說賈平凹就是當今最好的中國作家。從本質(zhì)上說,凡是從鄉(xiāng)村走出來的當代中國作家,身上和骨子里都有點“賈平凹”。作家按出生年代劃分是你們批評家為了言說方便而生造出來的一個“含糊的,不講理的概念”。我本人不反對,但也不贊成。因為,批評和寫作是兩套話語系統(tǒng)。批評家和作家、詩人最好的狀態(tài)是各干各的,各說各的。交叉時候就交叉了,不交叉那就相安無事。
我第一首詩歌發(fā)在《河北文學》,責編是王洪濤老師。一直想報答他,卻沒想到,他在2000年去世了。痛心。第一組詩歌是劉立云老師發(fā)在《解放軍文藝》上。這兩位詩人對我的鼓勵巨大到無法形容的程度。
桫欏:好編輯的伯樂作用不言而喻。因為你沒有詩集出版,我只能在網(wǎng)上找到你近幾年的部分詩作。早期的詩是什么樣子的?詩風與現(xiàn)在相比,有什么變化沒有?
楊獻平:除了九十年代中期那三四年,把詩歌當回事之外,直到現(xiàn)在,我對詩歌絲毫不當回事。想寫的時候就寫,不想寫就拉倒。沒有使命感,也沒有功利心。沒有宏偉目標,也不想和誰比試高下。“華山論劍”、“美人谷論爭”一類的事兒是浮在面上的幾個半吊子詩人所熱衷的。我就是寫點詩。而且覺得,自己的詩歌完全可以秒殺現(xiàn)在于詩歌界混得人模人樣、風生水起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所謂詩人。
我早期的詩歌抒情是必須的。看看九十年代多數(shù)詩人的詩歌作品,就知道我的詩歌了。那時候耽于抒情和想象,當然也耽于美。對社會視而不見,對廟堂江湖也懶得搭理。就是自我的抒情,美好,鐵血,純正,有愛,略微疼幾下,如此而已。現(xiàn)在的詩歌,從態(tài)度上是一種游戲的,不正經(jīng)的,不裝逼的多。記得2010年左右,我一個人剛到成都工作,沒事寫了幾個詩歌,搖滾式的,有點嬉皮和江湖混子的感覺。有一次和朋友聊起,忽然想創(chuàng)立一個“搖滾詩派”。仔細想了想,還覺得真可以。可到現(xiàn)在,覺得搞流派沒意思。詩就是詩。流派都是自我標榜的,充其量一個符號而已。真正的詩人,根本不需要什么鳥流派和團體來“站臺”和當“背景”。
2013年在魯院,再寫詩歌,也是想告訴其他人,詩對我來說,不在話下。我要寫詩,也應當是一個好手甚至高手。只是我不把詩歌當成一個事兒,至少不是主業(yè)。誠如你所言,我的詩是可以自視甚高,自感牛逼的。只是我不愿意去爭,懶得去爭罷了。
說起來這三個階段,變化是有的。九十年代中期寫詩是苦大仇深,掏心扒肺地當個事兒去干,干到一定程度之后,發(fā)現(xiàn)自己真的無力突圍。盡管那時候有幾位詩歌前輩對我的詩歌非常看好,但我還是毅然決然地轉向了散文寫作。現(xiàn)在回身去看,九十年代中期的詩歌一般,有幾首還行,大多數(shù)是可以稱之為“標準垃圾”的。2010年寫的詩歌,倒是有點意思。其中多了反抗意識,也更切身,尤其是時代中的個人經(jīng)驗的強度引入,是我九十年代詩歌所沒有的。再就是2013年在北京的詩歌。說實話,多年不寫詩忽然再拿起,卻發(fā)現(xiàn)自己修煉了幾年的詩歌技藝丟失了。所幸,很快又找了回來,而且越來越像模像樣,還與前幾年所寫的詩歌截然不同,無論語言還是技術,思想還是經(jīng)驗,都有新的拓展和進入,這是我沒有想到的。
桫欏:你再次強調(diào)魯院的學習,看來這段經(jīng)歷對你我都是重要的,讓我更深地理解了文學,也讓你我相識,更讓你重新找回了詩歌。促使你的詩風產(chǎn)生變化的原因是什么呢?你覺得人生的閱歷和文字的訓練哪一個更主要呢?這個問題也可以算作你的經(jīng)驗總結,供后來者參考。
楊獻平:就是當回事兒和不當回事兒的原因。當回事兒的話,你是詩歌的奴才,被它綁架和統(tǒng)治;當然不會有好的詩歌出來。不當回事兒,你就是詩歌的王。它是你的臣下和奴婢。這樣說,估計很多人會罵我冒犯繆斯。且不管他們。人生的功課人人時時都在參詳,作為寫東西的人來說,苦難、疼痛、失敗、愛著、寬恕、自由的不可能、生命在時間中的被摧毀感、靈魂也時刻被復雜的人心、人性凌遲和震撼著。人生是一門系統(tǒng)課程,文學也是,詩歌更是。生命本身就是詩。詩其實就是人與神的對話,是人與獸,善與惡的“接壤”那部分的植物和云霓,風雷和雨。
桫欏:很詩化的總結。最近楊克先生出版了《楊克的詩》,其實我也一直在說你應該出詩集。盡管詩人和詩人之間是不能比較的,但是我還是想說,楊克先生的詩我也很喜歡,所以我在跟一些詩人交流的時候,數(shù)次推薦“二楊”的詩。在我看來,他和你的詩有某種共通之處,就是離生活現(xiàn)場近,即所謂有“煙火氣”,即所謂“及物”,他的比你的“煙火氣”還重。你曾經(jīng)說“散文是離生活現(xiàn)場最近的文體”,你怎么看待詩和生活的關系?
楊獻平:楊克先生的詩歌我也拜讀過,好詩。這幾年,他把《作品》雜志也辦得很好。在這里向他致敬。你推薦我的詩歌,算是有眼光的行為吧。哈哈。盡管這話很多人不以為然,甚至會嘲笑我。不過,那些嘲笑我詩歌的人,再過十年二十年,他們會向我致敬。這話說得不著調(diào),但可能是有的。
散文隨筆我覺得就是寫當下之事的一個文體。前事前人做了,做得比我們好。未來自有后來人去干。當代人就是要寫當代,哪怕是臨摹,照搬,仿寫,也比趴在前人典籍和尸體上吸血要強上一萬倍。說實話,我挺可憐那些圍著歷史“施法”的散文隨筆寫作者。他們以為找到了歷史真相的大門,卻不料,到頭來還是一場空。所以,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你連自己親身經(jīng)歷的事情,特別是個人在時代中的生存、生命、精神和思想經(jīng)驗都寫不出來,去寫隔了幾十年,幾百上千年的時代,那不是隔靴搔癢是什么?因此,對于真正的作家、詩人來說,如何更好地書寫“此時我在”這個命題,是一個巨大的考驗。
桫欏:我贊同你的觀點,對當下生活本質(zhì)的把握確是有難度的。這也說明你的詩歌創(chuàng)作是重視生活經(jīng)驗的,對經(jīng)驗的重視或許保證了你的詩歌寬度,但也許更重要的是讓你獲得了上述的自信。的確,你在詩中能夠“所見即所得”、“所想即所寫”,你有馳騁縱橫的野心,但是很多時候,你還是不想天馬行空,你有更多的腳踏實地的寫作。你也寫自己的沉思,比如在北京的那一組,《失眠之書》、《不被挪移的名牌》等,但它們顯然也不是漫無邊際的“妄想”。這是你的自主還是無意識?
楊獻平:寫作就是掠地飛行,有塵埃泥土,也有風聲彩虹。現(xiàn)實生活和現(xiàn)場的經(jīng)驗是“觸發(fā)器”,半人半神才是爆破點。文學寫作,不就是從大地上來,到精神里去嗎?沒有哪一種文學憑空臆想構成,虛構也必須建立在現(xiàn)實的經(jīng)驗之上。因為,現(xiàn)實之中某個“場景”和“細節(jié)”就是一個導火索,就是空中武器“點火系統(tǒng)”,寫作本身就是“精確制導”的過程,盡管誰也難以精確地“命中目標”,但每個寫作者都會朝著這個目標費盡周折且不遺余力。
桫欏:記得魯院畢業(yè)前,你和高鵬程發(fā)起“離別賦”的同題寫作。你的作品中有兩句我記得特別清楚:“來到以后,你像鉆石,在靠近心臟的骨頭/一手捧著玫瑰,一手把持小刀”。就像黑澤明說的,“沒有比一部電影更能說明導演的了”,看上去生活中的你那種放達、豪邁,其實在你的詩面前完全可以判定是虛張聲勢的“偽裝”,這是一種矛盾嗎?你自己怎樣解釋?
楊獻平:魯院是一個有意思的地方,對我來說,人到中年,再恬不知恥地“任性”幾個月,也是人生之幸事。我和鵬程是一對好搭檔,在魯院有“基友”之名。但落實到詩歌上,我覺得我們那一屆有幾個很好的詩人,除了他們詩歌組的,還有蘇瓷瓷、孫學軍等寫小說的。發(fā)起那樣的一個活動,其實是想大家都寫寫詩。寫詩我覺得對任何文學創(chuàng)作都是有益的。偉大的作品本身就是詩。你可以沒有詩意但不要沒有詩性。
具體到我個人,我是非常矛盾的一個人,也是一個多面體。我玩是玩,沉默就是沉默。有時候各種情緒和表現(xiàn)轉換還非常快。這一點,我自己知道,但沒法克制和預料。我惟一的優(yōu)點就是很真誠地對待某個人某件事,但是我發(fā)現(xiàn)某個人某件事有點讓人“不爽”就會起戒心,而且這個“戒心”會持續(xù)很久。這不是記仇。我還覺得,人的品性好壞,是與生俱來的。我也覺得,搞文章的人,都應當是放達的通透的,他對世事人心有著精密的觀察,也有著天性的敏感與近乎科學的分析。
文學就是探究復雜的人心人性的,作為作者,本身也是很復雜的。惟其自己復雜,才會與這個復雜的時代和人性人心相銜接。
桫欏:透過你的詩,我知道你的真。你有一首寫父親病故的作品:《失去父親的夜晚》,或許是相同的經(jīng)歷引起我和這首詩的共鳴。從詩歌到散文,你的“南太行”敘事不脫對親人、對鄉(xiāng)鄰、對故鄉(xiāng)的懷念。你長期的軍旅生活使你遠離故鄉(xiāng),“鄉(xiāng)愁”一直是支撐你寫作的動力嗎?
楊獻平:我還有一首《父親》,比較長,也口水,純敘述。我覺得那個更好。將一個農(nóng)民的命運與他所經(jīng)歷的時代鏈接起來,目的是讓人看到時代這架重型機器在具體人,尤其是一個農(nóng)民身上碾壓的痕跡。此外,我還寫了一首《給兒子的詩》,一百多行,也寫到了時代對一個孩子成長的影響。就我個人而言,我不認為一個作家可以真正地胸懷天地,即使他有囊括寰宇的境界,但在實際的寫作當中,他也只能專注于具體人群和具體人來完成。
鄉(xiāng)愁其實是一個很空茫的詞語。鄉(xiāng),其實就是生身之地;故鄉(xiāng),就是一個人在人世間首次扎根的地方。很多時候,我們對故鄉(xiāng)的依賴,不是地域在起作用,而是親人。尤其是在這使人越來越孤單的當下時代。很多人對世界失去了信任,進而對周遭也沒有了依賴。每個人都必須為自己找一個安妥之地,不管是精神的還是情感的,因此,故鄉(xiāng)便成為了我們的不二之選。當然,故鄉(xiāng)也是我們根脈所在,任何人一生都必然與之發(fā)生關聯(lián)。
桫欏:你基于故鄉(xiāng)建構起的“南太行”文學地理學遼闊而深切,其背后的圖景中深含對傳統(tǒng)的回望和敬畏。你的很多詩作都在探究傳統(tǒng)與當下生活的關系,以及你基于這種關系之上的生命感受,《回鄉(xiāng)》、《悲歌》、《關于母親的饑餓記憶》、《在故鄉(xiāng)的城市給你寫詩》,從中我甚至看到古代士子的倫理道德,即所謂“士必以詩書為性命,人須從孝悌立根本”,詩書孝悌,你覺得你當下的生活有否受此影響?
楊獻平:“南太行”更多的是一個文學的地理,完全是我杜撰出來的。它的實際疆域為太行山東部,即山西左權、潞城、和順,河南林州、浚縣、安陽,河北沙河、武安、邢臺等地。這一帶雖然不屬于同一個省份,但其風習是非常相似的。盡管武安等地的方言與河北河南其他地方相差甚遠。
每個人都是傳統(tǒng)的產(chǎn)物,只不過,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文化“混血”的成分更大,時代賦予他們的特征也更顯著一些罷了。像你我這樣的人,本質(zhì)上只能算是農(nóng)民知識分子。再本質(zhì),其實還是農(nóng)民,只不過讀了點書,稍微開明和通達一些而已。
每次回鄉(xiāng),我都感到悲傷。這個悲傷一方面來自親人的逐漸稀少乃至迅速老去;一方面來自鄉(xiāng)村傳統(tǒng)文明日漸崩潰和被篡改。稍微考察一下,其實鄉(xiāng)村才是我們民族乃至中國文化的根脈,在急速變革和轉型的年代,鄉(xiāng)村也在調(diào)整自己,只不過混亂一些,盲目一些罷了。其“此時的狀態(tài)”與城市的本質(zhì)相同。
我們強調(diào)平等,自由,民主,其實一個字,還是愛。大愛是由小愛組成的。我不相信一個天天說胸懷天下的人只泛泛地去愛國家和世界。愛,是要從具體人入手的,是要在具體行為和人事上體現(xiàn)的。
而孝義也是愛的一種表現(xiàn)。讀書人,必然是明理的,寫作者,也必然是有情義的。
當下的現(xiàn)實生活已經(jīng)對我們每一個人都形成了強大的裹挾力量,誰也無法逃避。作為寫作者,寫當代,寫“此時我在”的現(xiàn)實生活與精神困境,我覺得是一個使命,也是一種能力。
桫欏:沒錯!我一直認為我就是一個農(nóng)民。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的返鄉(xiāng)愿望也越來越強烈。從農(nóng)門到校門再到機關門,我覺得自己就是另一個陳奐生,只不過面對新生活麻木了自己。你與我不同,你是一名軍人,而且長期在大西北服役。除了故鄉(xiāng),西部獨有的自然風物和人文地理也成為你筆下常見的書寫。在你的作品中,“西部”與“南太行”構成了你生命中的兩翼,成都或許是一個“中心點”。你關于西部的詩歌我稱之為“新邊塞詩”。你怎樣把握個人與土地、與人文傳統(tǒng)和與自然之物的關系?
楊獻平:關于西北,我起初是排斥的;但待了多年之后,儼然覺得西北也不錯。在中國,凡是邊疆之地,其混血成分越大,文化和文明相對內(nèi)地更為斑斕多彩。我前些年所在的巴丹吉林沙漠、河西走廊和阿拉善高原就是。它們雖然是沙漠戈壁,天如深井,地如瀚海,風沙連綿且摧枯拉朽,但夏天的沙漠是很美的,秋天也是。每一塊地域都是神奇的,對人的籠罩和影響深重而真切。多年之后,我發(fā)現(xiàn),西北那地方其實和我個人的秉性很吻合,放達、渴望自由、真誠,不妥協(xié),胸襟大等等,當然,我也希望安定和穩(wěn)定。這一切,西北都給予了我,而且還給予我愛情和家庭。
南太行鄉(xiāng)村作為出生地,就是生命的胞衣,靈魂的暖床。那里山峰林立,四季分明,裸露的巖石和草木一樣多,也一樣的堅硬和葳蕤。對于我來說,無論我去鄉(xiāng)多遠,南太行鄉(xiāng)村都是我的烙印和歸宿。
成都這個地方,我有點喜歡,主要是它的生活方式。慢生活。這只是成都給人的一個顯著印象。但實際上,成都的生活壓力一點都不比北京小。成都的消費我估計可以排在廣州之后。這個城市很復雜,一方面向往安逸,隨遇而安;一方面又盡顯奢侈。這可能也是大時代背景下的一種城市通病。
對于具體的地域,每個人都只有適應的權利,無法篡改。地域可以影響到一個人的品性,但一個人之力絕對無法撼動一個地域的傳統(tǒng)。這就是地域文化及其人文傳統(tǒng)。西南地區(qū)的自然環(huán)境,夏季的時候和我老家南太行有相同之處。這是我夏季回老家的時候忽然發(fā)現(xiàn)的,空氣濕潤,草木競發(fā),夜雨闌珊,清風輕揚。這使得我時常有一種恍然此地彼地的感覺。但在成都幾年之后,我發(fā)現(xiàn)我自己還是有些改變,具體怎么變了,變得如何了,我自己都難以表述。
桫欏:剖析一下你的詩觀,在你看來,詩歌的本質(zhì)是什么?你又如何實踐這個本質(zhì)?
楊獻平:詩無達詁!我覺得,詩歌就是你對這個世界的細微感知,你對所在時代的現(xiàn)實與精神的多種考察;是一個人生活經(jīng)驗和時代經(jīng)驗的并行與融合;是一個人被時代生活碰傷之后的嚎叫,也是一個人在溫暖中的呻吟,悲哀之中的自我療救。如此等等。在我看來,凡事皆可入詩,只要有所觸動,與人與自然與生活與精神和靈魂相關,都可以作為詩歌寫出來。
詩歌絕不是到語言為止。韓東的那句話誤導了很多人。我讀一些人的詩歌,基本上就是詞語的起承轉合,一種情緒的排放,還有一種現(xiàn)象和語言的堆砌。我很奇怪,這樣的詩還是詩,這樣的詩人還被眾人簇擁。詩歌,是妓女,還是貴婦;是奴婢,也是王者。每個人對詩歌的理解都不同,但詩歌應當有一個基本的道,那就是:時代中的個人經(jīng)驗詩化表達,時代經(jīng)驗的個人性體現(xiàn)。
關鍵在于:有沒有氣象和境界。
我是這樣想的,我也這樣做。但效果如何,自己不得而知。
桫欏:當然,“詩到語言為止”這個口號一樣的說法,當時新鮮,隔了時空現(xiàn)在來看,當初有點“標題黨”的意思,只不過那時沒有這個詞。一般情況下我不太愛附和你的說法,但這個我還是認同的。所以跟你對話我曾經(jīng)有所顧慮,因為怕打起來。記得在魯院上學,你我始終對各種文學之外的問題有分歧。我覺得你是個不老的“憤青”,這是否表示了你對生活的敏感呢?這種敏感度是不是你詩歌創(chuàng)作的“有力武器”?
楊獻平:你我不會打架。其實我蠻喜歡你的性格。能拒絕喝酒的人,一定是個評論家。酒是屬于詩人的。小說家太陰沉。詩人的敏感更強于小說家。敏感,就是神經(jīng)質(zhì)。我這方面的問題較大,往往會從一句話,一個字,一個細節(jié)和行為之間,發(fā)現(xiàn)一些自以為是的傾向和變化。我知道這對于寫詩是很好的,但在做批評的時候,寫散文和小說的時候,卻又顯得輕忽與不成熟。
如果我還是那么敏感,那么,我就還可以寫詩。
如果我不敏感,木訥了,麻木了,那我只能向你學習。
桫欏:離開你的詩歌作品,回到詩歌現(xiàn)場。當下的詩壇一直充滿傳奇性,像世界上的某些地區(qū),熱點不斷。最近有一個熱點是關于余秀華,你怎樣評價余秀華的詩?同時,你能不能評價一下當下的大陸詩歌創(chuàng)作?為什么我要單提出大陸,因為我覺得港臺文學有與我們不一樣的生態(tài),你還是談眼前的事。——請注意,是創(chuàng)作,不是詩壇現(xiàn)象。
楊獻平:詩歌必須制造熱點才能引起群體性狂歡和效仿。詩人是不甘寂寞的。另一個,中國本就是一個詩歌國度。在所有文學體裁當中,詩是吃水最深的。當下的詩歌,我覺得有五個現(xiàn)象。一個是以敘述為能事,類似散文詩的微縮版。所不同的是,大多數(shù)散文詩是抖小機靈,這些敘述性的詩歌,搞大機靈。擁簇者多,獲獎也無數(shù)。另一個是口水詩。也有一大群的效仿者和崇拜者。口水詩好不好?好,好在口語和口水詩解決了詩歌的一部分難度,寫作和閱讀層面的都有。以沈浩波的詩歌為例,我還是覺得他以前的下半身詩歌更好,現(xiàn)在的詩歌,雖然“正經(jīng)”了也深刻了,切身及物了,但過于直白,已經(jīng)算不得詩了。再一個,就是政治意見或者意識形態(tài)過重的詩。反抗、傳播和啟蒙都是對的,無可厚非,但要把詩歌做成純粹的口號和理念闡發(fā),我覺得就過了。第四個是按照八十年代以來的詩歌路數(shù)走。這些詩人不能說不夠優(yōu)秀,但是自我變革和調(diào)整的能力顯然不足。第五個是說家常話、堆砌語言、端架子,其實空空如也,識見、思想、技術、語言等能力長時間上不去,不開竅的那一類。
余秀華的詩歌,我認為是極好的,她的詩歌一出現(xiàn),就秒殺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詩人,尤其是女詩人。我曾經(jīng)說過,余秀華的詩歌有著“瓦藍色的歌唱、疼到靈魂的輕度與切入生命的真切與嘹亮”。我還覺得,對于上述的一些詩人來說,余秀華的詩歌再次證實了詩歌的抒情本質(zhì),特別是情感的濃度、生活和精神的寬度,還有詩歌與詩人、與生活的那種天然關系。這方面,關于余秀華及其詩歌文章,評論家張莉有一篇文章甚好。好像是發(fā)在《文匯報》上的。我覺得比較到位,也公正、切實。
桫欏:網(wǎng)絡時代,或者叫作“自媒體時代”,詩歌面臨與過去完全不一樣的發(fā)表、傳播方式。有人說網(wǎng)絡成就了詩歌,也有人說網(wǎng)絡毀了詩歌,你的意見呢?
楊獻平:好詩人都是自毀的。好的詩歌也是自毀的。毀不毀,與網(wǎng)絡和紙媒,其實都沒什么關系。我倒覺得,很多時候,網(wǎng)絡這個平臺起碼是對紙媒的一個補充,甚至校正。是的,因為版面所限,紙媒忽略和錯過的好詩太多了。再者說,相當一部分紙媒詩歌編輯,有時候充當了劊子手的角色。好詩出頭是一個艱難過程。歷來如此。
桫欏:你在朋友圈里推薦俄裔美國詩人、散文家布羅茨基的《小于一》,你也曬出你的大量藏書。所謂“讀書人”,就是“藏書、讀書、寫書”,你做到了,名副其實。你的閱讀更傾向于哪類書籍呢?
楊獻平:布羅茨基的《小于一》十多年前就在傳,很多人讀。這個不是新鮮的。我買書多,以前讀得多,現(xiàn)在則少。我覺得買書是一個習慣,也是一個毛病,其實有相當一部分書注定買回來是不看的,但還是要買。
我讀書的興趣多與思想學術類有關,文學作品占的比例極少。我愿意看一些地方志,一些田野筆記、調(diào)查研究一類的作品。當代中國文學,其實有很多不錯的。但失望的居多。這里面的原因,其實很有意思。以后有人再寫文學史,估計會從其中淘出很多文學之外的東西。是的,這個時代的文學相當一部分屬于文學之外的。
時間會證實我說的這一點。
桫欏:閱讀在你的生活中占有怎樣的位置?你怎樣看待閱讀與人生的關系?你的閱讀動力來自于哪里,或者說你為什么要閱讀呢?
楊獻平:很多時候,我拿一本書在手里,覺得充實;坐在書架前面,我覺得有很多的目擊和敦促。閱讀對于一個人來說,是生命的一部分,也是靈魂所需。任何人的作品,一旦成為書籍,流通開來的話,那就是他們的靈魂。無論健在還是逝去的作家詩人。
桫欏:在你的經(jīng)驗里,閱讀和寫作的關系是什么呢?你怎樣處理大量閱讀與保持自我的關系?
楊獻平:我很多時候讀書不求甚解,滿足于讀過。好書太多,一個人不可能一網(wǎng)打盡。讀自己喜歡讀的書,才是正道。我慶幸的是,我讀書,但從不模仿,我讀書,絕不跟著跑,我有我自己的判斷和寫作要求,即,不要跟隨大流去博取一時名利,盡量沉下心來,做自己旁門左道的事。因為,寫作者太多了,要想與人形成區(qū)別,難啊!但不管如何,獨立于眾,哪怕小一點,也都是屬于自己的。
桫欏:網(wǎng)絡時代的碎片化閱讀,對你的閱讀影響大嗎?你平常用手機看文章嗎?你覺得你有沒有對手機閱讀上癮?
楊獻平:我這個人自律性還可以,手機常用,碎片化閱讀也是跟風。但用一段時間,就覺得索然無味了。這說明,我這個人還是朝三暮四的人。微博、微信之類的工具,都是一陣風,一陣風之后,還會有新的類似工具出現(xiàn)。之所以跟風,是因為,不能落伍于時代。你要感知時代,就必須要在各方面與之同步,盡管你做不了更好,但你一定要敏銳,善于發(fā)現(xiàn)和領悟。
桫欏:除了詩歌之外,你能否推薦幾部你喜歡的書?假如讓你給高中生或大學低年級的學生推薦你喜歡的書,是哪幾部呢?當然也包括詩歌。
楊獻平:我覺得,長篇小說還是那些經(jīng)典,如《悲慘世界》、《巴黎圣母院》、《戰(zhàn)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迷宮中的將軍》,納博科夫的《洛麗塔》等等。中國本土的還是五四時期的那一批。當然還有四大名著和《金瓶梅》,以及后來的《白鹿原》。散文的話,還是魯迅、沈從文、伍爾夫、孫犁、汪曾祺、阿爾貝·加繆他們那些人的。詩歌有博爾赫斯、艾略特等西方詩人的,國內(nèi)的還是八十年代出現(xiàn)的那一批詩人的作品。不過,我還是喜歡像蘇珊·桑塔格、蕾切爾·卡森、哈耶克、本雅明、西蒙·波伏娃等等這樣的學者的作品。
桫欏:前幾天在《文學報》上看到“在場主義”散文獎的復評結果,你的大名赫然在列,祝賀你。雖然你也不大看中什么獎項,但大家都知道你是散文家,所以咱倆對話,散文必談。去年的《生死故鄉(xiāng)》之后,你最近有什么大的創(chuàng)作計劃沒有?
楊獻平:我比較安心的是,獲獎都沒有活動過;自然而然,聽“人”由命,沒玩過花招。再說,目前的文學獎,貨真價實的沒幾個,稍微公正一點就算是“萬幸”了。對我個人來說,這個年齡,早應當看淡了,一個人不可能萬事通達,好事都暴雨一樣落在自己頭上。做一個微笑的旁觀者或者干脆面對青山,不干其他,也未嘗不是好事。“在場主義”散文獎我覺得也是在為散文做事,很難得。對真心為文學做事的人,我覺得他們很有心。這就夠了。關于南太行鄉(xiāng)村,算上《生死故鄉(xiāng)》,一共四本。這四本基本上耗盡了我對南太行的積累和經(jīng)驗。再寫,就得再回去待一段時間了。所幸的是,這一系列有望在2015年內(nèi)出版。今后的想法主要有三個,一個是寫一部長篇小說,想了很多年,還是不夠成熟。再一個是會繼續(xù)寫南太行鄉(xiāng)村,尤其是近些年來的變化,尤其是時代背景下的北方鄉(xiāng)村文化變遷和經(jīng)濟、信仰等方面的。第三個是,詩歌會斷續(xù)寫一些,但要考慮路子。是的,要變。寫成順溜子,就沒什么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