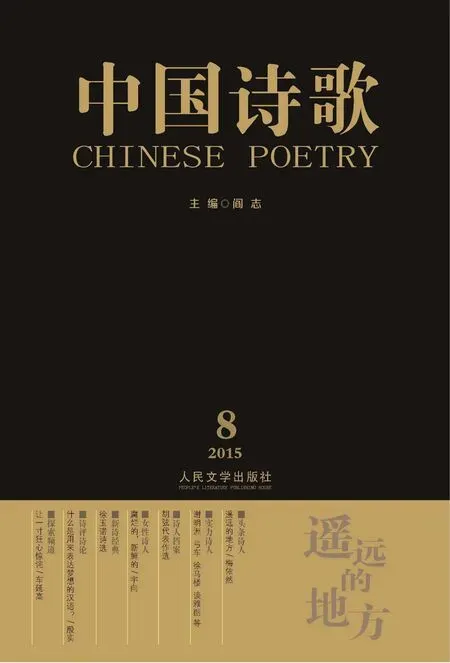詩學觀點
□李羚瑞/輯
詩學觀點
□李羚瑞/輯
●孫德喜認為,面對當下詩歌的不景氣,有人提出建立新詩的形式規范的設想,試圖通過具體的詩歌形式規范來約束詩歌,從而讓詩歌在形式上像詩歌的樣子,葉櫓并不贊同這樣的主張。他認為詩歌的本質不在具體的形式,而在其中蘊涵的詩質,而規范不僅不能解決詩歌的不景氣的問題,而且還可能因其“限制”而形成對詩歌創作的“約束”,進而“會成為對創造性和可能性的遏制”,但這并不是說葉櫓否定詩歌的形式。他提出了詩歌的形式感問題,認為詩歌不應該有統一的形式規范,而應該根據各自抒情感和表達思想的需要,進而建立起相應的詩歌形式,因而詩歌的形式感所體現的就是形式上的自由。
(《論葉櫓的詩歌批評》,《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
●方長安認為,從前有人將譯詩視為自己的白話新詩作品,主要原因一是以詩歌是不能翻譯的觀念為認識前提,將翻譯看成創作,也就是高度肯定譯者的創造性勞動;二是以外國詩歌尤其是西洋詩歌支持中國的白話新詩運動,賦予中國的詩歌革命和白話新詩創作以世界潮流性、進步性,也就是賦予中國白話新詩存在的合法性。但實際上這暗含著中國白話新詩的不自信,其隱患就是肯定那時中國詩歌一味地去民族化傾向,忘記自己還有幾千年悠久的詩歌傳統,肯定那時詩壇盲目地向國外詩歌學習的傾向,其結果是使白話新詩逐漸失去民族詩歌個性,失去民族文化神韻。
(
《對新詩建構與發展問題的思考——〈新詩年選(一九一九年)〉的現代詩學立場與詩歌史價值》,《文學評論》,2015年第2期)
●楊林認為,詩歌要有詩性,才能成其為詩歌,而詩性的實現,最為重要的就是意象經營的獨一無二。詩性意味的深邃性、哲理性與本質性,是通過獨特的意象來構建意境,通過這意境來引領讀者進入思考,使得個體生命的個性體驗上升到共性共鳴的藝術審美境界。沒有獨一無二的意象構建,就缺乏共性共鳴的真實性,就缺乏個性感受的感染力。從螞蟻這一獨一無二的意象經營中,感受到螞蟻與詩人獨特個體的卑賤與堅忍,感悟到人的卑微的生命意義,體驗到詩歌詩性意味的完美的藝術享受。
(《楊林讀詩之特朗斯特羅姆與南鷗》,《湖南文藝》,2015年4月號)
●張宇剛認為,馬永平的詩樸素,平實,沉穩,舉重若輕,字里行間總有一種明朗的憂傷和柔韌的堅強;其追懷往昔,摹寫事象,往往不拘形跡,而自能抵達內心,彰顯精神,于時代層云之上,勾勒出一顆不屈靈魂的高蹈。他的詩歌觀察細致,手法地道,摒棄了隱喻和象征,每以白描行事,下筆如同在說話,如同在生活;在一派不疾不徐中,必備的修辭、技巧亦巧焉隱于其間,情懷沛然——他的詩分明超越了修辭、技巧,超越了俗世的物象,不尚奢華,直抵本體。他的詩苦澀而輕松,無招勝有招,表象的簡單與內里的繁復,達成奇異的張力,彰顯對人生、對命運、對宇宙的本真性體悟。
(《不像詩人的詩人,及其詩》,《文學自由談》,2015年第2期)
●王攸欣認為,中國詩歌具有強大的抒情詩傳統,形成了豐富多樣的風格和技巧。情感表達的微妙、蘊藉,意境營構的超曠、悠遠,意象選擇的自然、恰切,語言運用的準確、凝練,音律琢磨的細密、謹嚴,章法構思的完整、流轉,是歷代名作的主流特征,其典雅含蓄、空靈深切的審美風格非西方詩所能媲美。卞之琳在自己的詩中承接并創新了這一傳統,吸納了西方最新的詩學經驗,在詩中融入、化入中國傳統,顯露了中國精神、中國風度。卞之琳的詩真正穩固建立了中國新詩的審美基質。
(《卞之琳詩作的文化-詩學闡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5年第3期)
●楊匡漢認為,現代詩似乎不必過多考慮“新詩”與“舊詩”。雙水分流,雙峰對看,朝著“現代”的同一方向,在高處匯聚,有何不可、不好?我們曾經以“啟蒙”與“救亡”之變奏為背景討論現代新詩的“合法性”,并予以歷史化。但同時對另一個“活性因子”——抒情傳統及其在新變中的滲透,不應忽略不計。在古典傳統文化落幕的“詩界革命”時代,有沒有古典詩詞的現代生產?有沒有以舊體詩詞為骨干的抒情傳統對新詩“歷史化”的頑強抗拒?有沒有古典所展示的抒情主體性在現代情境下書寫的脈絡和意義?答案是肯定的。所以我們要重視中西詩歌觀點的交集和差異,新舊詩歌理念的越界潛能,歧異與故常的流動性和相對性,守成與新變在同一位詩人身上多重曖昧的呈現。我們也正是從“新”“舊”互滲互動中,把握現代詩暗涌的脈搏。
(《堂郡絮語》,《詩選刊》,2015年4月號)
●羅振亞認為,新世紀文壇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走出邊緣化低谷的詩歌境遇逐漸好轉。大多數詩歌自覺回歸詩歌本體,致力于各種藝術可能性的挖掘和打造,提升著詩歌的品位,尤其是“及物”策略的明智選擇,將詩歌和現實之間的關系調整到了相對理想的狀態。詩人們不完全拒斥超驗、永恒的情思元素,可是已注意講究“及物”對象選取的穩妥、恰切,在典型、多維的日常處境和經驗的有效敞開中,更接地氣地建構詩歌的形象美學,與當代生活的聯系更為廣泛。一些詩人沒將現實因子直接搬入詩中,進行黏滯泥實的恢復與呈現,而是依靠能動的主體精神和象征思維等藝術手段的支撐,在呈象過程中充滿靈性,獲得一定的精神提升,甚至有時還能提供出某種新的精神向度。
(《“及物”與當下詩歌的境遇》,《光明日報》,2015年4月13日)
●蔣登科認為,詩學是以理解為基礎的學科。在詩學研究中,最根本的是對詩人的精神世界以及為了表達這種世界而采取的藝術方式的研究。在中國傳統詩學中,大多數詩論都是優秀詩人通過自己的創作經驗總結出來的,具有明顯的感悟性、經驗性特征,甚至是以詩的方式寫出的詩話。在現代詩歌研究越來越走向學術化、技術化的時候,梁平以一個詩人的身份,從經驗、感悟的角度談詩,而且是張揚一種符合詩歌歷史與現狀的“正”的觀念,對于詩歌創作、研究都提出了很多具有價值的觀點,這對于矯正詩學研究中出現的越來越離開詩歌本身的那些現象,對于人們全面、準確地理解詩之本質、作用等,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價值。
(《詩人的詩之思》,《人民日報》,2015年5月5日)
●于堅認為,真正好的詩就像塔一樣,塔基廣大,語言直接、簡單,讓很多人有感覺,被打動,可以進入,但詩真正的核心,它要表達的最隱秘的部分,是一層層往上升的,讀者經驗的深度不同,對詩的領悟也就不同。不是說只有作者才有精神性的東西,讀者只是像學生那樣一一接受。詩是對無的召喚,如果讀者心中對“無”毫無感悟,滿腦袋都是如何占有,他就無法進入詩。現在一個不太好的現象是,一個安靜的詩人一旦被網絡注意,被媒體發現,馬上就會變成新秀,喧囂起來,浮躁起來。在微博微信帶來詩歌傳播的“百花齊放”的時候,如何樹立和建立寫詩的“金字塔”,恐怕是我們應該關注的問題。詩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平易近人,這不是對詩的要求,是對世故的要求。
(《真正好的詩就像塔一樣》,《人民日報》,2015年5月5日)
●王志清認為,當下散文詩創作的同質化問題突出,經典缺席,重要原因出在語言上。換言之,當下散文詩突出的弊端是:語言僵化,缺乏體溫,思想稀釋,缺乏鮮活生動的個性和銳氣。散文詩的語言應該是詩性的。何謂詩性?即盡可能弱化其寫實性,不以再現為主,而強化其表現性,激增其情感含量與美感因素。或言之,散文詩的語言難就難在要不斷地解決再現和表現之間的矛盾。對于散文詩作家來說,作品中的“語言”絕非一般性意義的“詞匯”。散文詩的語言,應該已是一種意義,一種形象,一種詩人的靈感,一種詩性的活性載體,而具有詩性所特有的飽滿彈性,發生形態的變異與喻指的暗示,因此也具有真正的詩才有的豐富性和不確定性。
(《散文詩:語言決定命運》,《文學報》,2015年4月30日)
●任白認為,祭司也好牧師也罷,詩人都被看成是溝通被日常生活所蒙蔽的深邃世界的某種靈媒。他有異于常人的感知能力,能夠先于我們的哭泣看到淚水之海,能夠透過墻上巨大的陰影察覺到身后無名災難的咻咻鼻息。他是此岸的他者,甚至也是彼岸的他者,因為生活在別處,靈魂永遠不可能在現實的懷中安睡。詩人不可或缺,或者說詩歌不可或缺,再或者說我們對心愛之物的愛不可或缺。特別是在今天這個“貧困到以至于無法感知其自身的貧困”的年代,我們被自己和他人的恐懼與狂熱一起驅趕著,不知所終。這個時候我們需要有人失聲痛哭,有人大聲呼喊,或者,干脆轉過身去,用他落寞的背影來發布一個艱難的選擇和狂妄的判決。
(《為什么——〈耳語〉后記》,《作家》,2015年第4期)
●葉櫓認為,詩歌的抒情性日漸式微而智性因素卻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滲透其間,或許正是社會發展過程中人們的思維和感情方式受到潛移默化的表現。在當下的社會,人們似乎很難找回曾經有過的那種純情和稚性,因為彌漫在我們生活周圍的氣氛已然被雜色的物質侵入和浸染,所以我們不能指望詩人像生活在真空中那樣作純情的歌唱。但是,身處當下物欲橫流人情淡薄之現實而許多詩人已然孜孜以求地力圖表現人性中的真情,正是詩人作為社會良知的載體的一種現身。所以詩歌創作中不管是主情還是主智的作品,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主情乎?主智乎?》,《揚子江》,2015年第2期)
●譚五昌認為,吉狄馬加成功地超越了其特定的“彝族詩人身份”和“彝人意識”的命名與表達,詩人已從本土化、民族化立場的詩歌書寫與姿態固守中突入到更為開闊的世界性精神文化視野,表達著更為深刻而普遍性的憂患意識和人類情懷。在當下的全球化語境中,吉狄馬加并未盲目地以“世界性”詩人的身份自居,很多時候他反而持守自身的民族詩人文化身份,這使得他的寫作富有根性,而不飄在虛無、時尚的文化浮塵中,因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世界性寫作”其實是可疑的。作為一個彝族人,吉狄馬加在現代文明和傳統民族文化沖突中,在人類的精神困境和靈魂陣痛中幾乎別無選擇地渴望突圍。這是一種精神的宿命。
(《雪豹的詩性呼告,或關于自然環境的生存憂思錄——對吉狄馬加近作〈我,雪豹……〉的一種解讀》,《文藝爭鳴》,2015年4月號)
●耿林莽認為,想象力是從生活中來,是詩人在現實人生的體驗中,長期積累而得,是他創作倉庫中的“庫存”。生活經驗越豐富,想象力馳騁的空間就越廣闊。就我的創作實踐而言,局限于一時一事的具體之實構思的作品很少,而且往往效果欠佳,從宏觀視野、廣闊空間汲取素材,調動細節,展開思考,浮想聯翩的構思方式,常能取得更大的自由,獲得豐富的構思資源。所以,散文詩不是再現,也不是表現,而是創造,是藝術的創造、詩美意境的創造:“美而幻”,便是她的“完成式”。
(《散文詩,美而幻》,《散文詩》,2015年4月上半月刊)
●陳仲義認為,好詩是用生命、淚水、疼痛去結晶的。生命體驗的本真、自然質樸,經過語感的催化,外化為紙上的分行建筑。余秀華的一些詩作具備好詩的基本質素,具備迅速進入“召喚結構”的響應條件(只差導火線)。她的特殊遭際縮小文本生成與接受的落差,她的傳達方式容易讓“性情美學”或“情靈美學”(自撰),迅速抵達接受心理中的“動容”部位。悄然心動或怦然心動,所帶來的溫暖、澄明、撫慰、照亮,是好詩接受的一般“體征”。正是余秀華詩歌里的基本盤面,呈現出詩歌基本品質與質素,釀成的總體“感動”效應,符合接受的審美尺度與需求,她最終才得以自己的先天“短板”,反倒收獲了一場詩歌的“嘉年華”。
(《好詩的接受品質及其“附加值”——“余熱”觸探》,《詩歌月刊》,2015年第4期)
●楊慶祥認為,詩歌,尤其是現代主義詩歌,必須有“我”,這已經成了一種陳規式的設定。但正如阿蘭·巴丟所尖銳質疑的,如果割裂了“我”和“我們”的有機關系,這個“我”還有創造性嗎?他真的能代表“我們”嗎?這也許是現代主義詩歌面臨的最大的合法化危機。而要破除這個危機,就必須重新理解“我”和“我們”之間的關系,不能因為“我們”不夠理想或者“我們”曾經以各種主義之名對“我”實施了壓迫,就不承認這個“我們”的存在或者徹底割裂這兩者的聯系,從而讓現代主義詩歌寫作變成一個內循環的,擁有虛假的個人主體和語言能指的游戲。這是一種寫作和思考上的惰性,這種惰性的蔓延,讓我們當下的詩歌寫作沒有力量。
(《重啟一種“對話式”的詩歌寫作》,《詩刊》,2015年4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