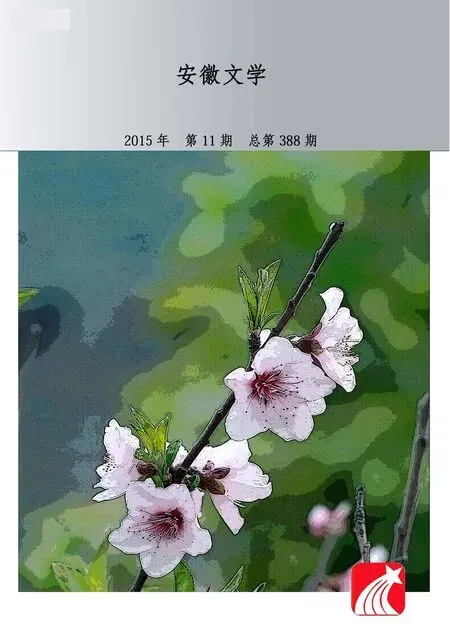異化、瘋癲與幻滅——《李爾王》的現代主義萌芽特征
徐顯靜
上海理工大學外語學院
一、引言
創作于1605年的著名悲劇《李爾王》被稱為莎士比亞所著最慘烈,最黑暗的悲劇,同時也是一部叫好不賣座的悲劇。幾個世紀以來,圍繞著它的爭議從未間斷。比如,正是李爾王三分其國交由女兒們分而治之的決定直接促成了整個悲劇,但是幾百年來無論是專業評論家還是普通觀眾,對于這種有悖常理、略顯荒唐的情節設計質疑不斷。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觀眾之所以不買賬,首先自然與其悲劇的巨大容量大大超出普通觀眾的信息解碼能力和接受能力有關。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其結局之慘烈令即便是鐵石心腸之人也為之動容,為之扼腕嘆息。理論上看,新古典主義戲劇創作大都遵循“詩的正義說”,即其結局必定是“善必賞,惡必罰”。因此,從習俗上,從感情上,甚至從理論上觀眾均無法接受代表正義一方的柯苔莉亞慘死的安排,更不能接受風燭殘年的李爾王面對痛失愛女轟然倒地而亡的悲壯結局。因此,莎士比亞敢于冒著失去票房的風險,無視習俗,顛覆傳統,充分展示了其敢于打破常規的非凡勇氣和超前的現代性。《李爾王》悲劇的慘烈,在于莎士比亞對深刻異化的人性一針見血的揭露,在于其對于理性和瘋癲悖論關系的展示,以及對封建君主專制政體幻滅感的刻畫,其之所以備受詬病不過是由于迫于時代的局限性觀眾及批評家們無法深刻體會其中的深意罷了。在經歷了后現代劇作家尤涅斯庫的《禿頭歌女》、塞繆爾·貝克特 《等待戈多》洗禮的現代觀眾看來,《李爾王》并沒有那么地不可思議,不能接受。當代評論中有一定代表性的波蘭評論家揚·柯特就認為《李爾王》作為悲劇來說是登峰造極的,表現的是悲劇中更本質的東西,其實質和當代貝克特的《最后一局》、《等待戈多》等荒誕戲劇完全一致,以此推理說荒誕派脫胎于莎士比亞。[1]258本文試圖從現代主義角度重新審視該劇,對于其廣受詬病的諸多矛盾之處提出新的解讀方式,筆者認為該劇初步展示了異化、瘋癲和幻滅的現代戲劇特征。
二、異化
不顧一切地反映現代西方人的異化感、焦慮感和絕望感構成了現代主義文學的一個共同特征。[2]29社會的種種危機和嚴酷的現實往往導致人性的嚴重扭曲,人的異化感便與日俱增。在《李爾王》中這種異化首先表現為人的物化,人性異化為獸性。有人做過統計,在該劇中莎翁先后提到了64種不同的動物,動物意象不僅增加了一種兇惡殘暴的氣氛,而且20世紀意象派評論家斯珀津認為這些動物的意象 “給予我們的感覺是‘人類’是‘正在退化的野獸’”。[3]436這種動物性突出地反應在貢納莉和瑞干的恣意作惡上。她們在家中對自己的父親和同胞姐妹刻薄無情,對自己的丈夫也毫無信義感情可言,對別人就更是殘忍無情了,隨便給別人上刑,鞭打殺害仆人,挖掉葛樂斯德的眼珠,還放在腳下踩……奈茨分析道:“這兩個女兒以她們的行為,她們的言論,以及與她們緊密相聯的吃人野獸的意象,再現出一種殘暴的動物性。 ”[3]440
無獨有偶,荒誕派戲劇大師愛德華·阿爾比的《動物園的故事》同樣戲謔了從人到獸的蛻變。在阿爾比筆下,人類社會就是一個動物園,每個人都有如一頭困獸。大家各自生活在自己的領地上,以柵欄相隔就相安無事。一旦籠門洞開,人們就開始為了蠅頭小利,如一張公園的長椅開戰,甚至不惜為此置對方于死地。李爾大權在握時,舊的統治暫時保持著應有的秩序。君臣、長幼、主仆之禮也得以遵從。國權三分其實是打開動物園籠門的一把鑰匙,頓時各種野獸爭相出籠,為爭奪權勢、利益勾心斗角、互相殘殺。于是乎天下大亂,正如葛樂斯德所言:骨肉至親,翻臉無情;朋友絕交;兄弟成了冤家;城里騷動;鄉下發生沖突;宮廷里潛伏著叛逆;父子的關系出現了裂痕。[4]24無論時代怎樣變化,人性始終如此。可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只不過在異化的程度上有所不同罷了。所以后來的荒誕派劇作家卡夫卡在《變形記》中干脆把人直接變成了大甲蟲。難得莎士比亞在前工業社會就這么深刻地洞悉了人性異化為獸性的現實。
那么又是什么導致了李爾個性的異化呢?答案只能是:王權。張君川認為,《李爾王》的主題就是權欲對人的腐蝕作用。[5]117李爾也曾經是一位明君,例如他尚能重用敢于直言相諫的坎特伯爵便是證明;殘暴專橫也并非其本性。但是在王位上的李爾即是封建王權的象征,王權使他不能客觀地看待自己和周圍的一切。一直以來形成的“朕即國家”的外部環境導致李爾的深度異化,以至于晚年的他不辨善惡,不分忠奸,濫用權威,為所欲為。簡言之,長期地以絕對權威自居,缺少有效地監管和制約機制的環境,造成了李爾個性的扭曲和變異。天性扭曲的國王勢必會禍國殃民,個性異化的父親勢必會使家破人亡。李爾的悲劇不僅是個人的,更是社會的。苦苦思索卻不能指出路在何方的莎士比亞,只好讓大部分劇中人物都在舞臺上死去,僅留下優柔寡斷的奧爾巴尼公爵和愛德加收拾殘破河山。因此,《李爾王》的悲劇性是壯烈的,徹頭徹尾的。作為一個在世時就大獲成功的劇作家,莎士比亞不是不懂得人們出于本能的對皆大歡喜結局的盼望,而且他早期的戲劇作品也以完美的結局為多。但是此情此景中的他似乎鐵了心的要讓這部悲劇來得更慘烈悲情,從中透露出的是莎翁對人類本性的質疑以及對人類命運的悲觀失望。
三、瘋癲
看似荒謬,卻有深意。這句評論用在李爾王的弄人身上是再恰當不過了。關于弄人有各種各樣的解讀。卜阿說:典型的(宮廷中的)傻子只知道一味逗笑打趣,“可是在這個悲劇里的傻子卻負擔了一項特殊任務。他反復不斷地唱著一個調子,那就是李爾王錯盡錯絕:把王冠送人,把自己的脖子套在貢納莉和瑞干的牛軛下。他跟其他戲劇中的同行弟兄不同,他沒有名字,只有這么一個簡單的稱號:傻子。他簡直不是血肉之軀,他是一個漂游的聲音——李爾王的心聲,附在一個奇形怪狀、臉帶哀容的形體上。這兒是一個深沉激動的靈魂戴著小丑的臉罩……他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具有奇特的洞察事物的能力。”(F.Boas,1908)(轉引自方平譯本評注第196頁)弄人表面看來癡癡癲癲,胡言亂語,但是癲狂背后是理性。透過現象看本質不難發現他時刻都表現出了世人皆醉我獨清的睿智,他的智慧不僅隱含在他與李爾半真半假的調侃當中,更反映在他時刻吟唱的無韻歌里。
和癲狂扯上關系的不僅有弄人,更有在暴風雨中嬉笑怒罵的李爾本人,以及淪落街頭的愛德加。他們或者把瘋癲當做一種生存或者斗爭策略 (愛德加),或者從瘋癲中痛苦思索最終獲得重生(李爾),或者在瘋癲的保護下道出了常人不敢說的人生至理(弄人)。莎士比亞對瘋癲這種極端情感體驗似乎極為偏愛,筆下的人物越是瘋癲,說出的語言越是精辟,啟發讀者也就越是深刻。縱觀莎士比亞的戲劇(尤其是悲劇),瘋癲之人和瘋癲話語出現過多次,如《哈姆雷特》里的哈姆雷特和奧菲利亞,《麥克白》里的麥克白。因此有人甚至認為“莎士比亞喜劇的情感高峰是 ‘癡迷’,而悲劇的情感高峰就是‘瘋狂’。[6]61
四、幻滅
俄國偉大作家托爾斯泰對《李爾王》的情節安排頗有微詞,他說:“李爾沒有任何必要和原因而必須退位。同樣的,他跟女兒們活過一輩子,也沒有理由聽信兩個大女兒的言辭而不聽信幼女的真情實話;然而他的境遇的全部悲劇性卻是由此造成的。”(轉移自方平譯《李爾王》代序“生活中不能沒有愛”)如是,悲劇的起因是荒誕的,不符合現實主義原則的,因而是不足信的。從現實主義角度講這種批評入情入理,但是筆者仍然認為在了解創作該劇的歷史背景之后,人們或許會有不同的感受。《李爾王》(1605)寫作時期是英國女王伊麗莎白逝世、斯圖亞特王朝詹姆士一世登基(1603)之后。這時候資產階級與封建階級聯盟破裂,專制王權成為社會上一切反動勢力的中心,這正是莎士比亞寫作的“悲劇時期”。[5]83《李爾王》不僅創作于悲劇性的歷史時期,更創作于莎士比亞本人的成熟期。他這時已脫離了富有幻想的青年時代,進入冷靜而敏銳地思考的中年,目光更犀利了,他對現實的觀察更深刻了。他的哲學思想也更豐富。[7]123
現在我們做出一個大膽揣度:在如此背景下,是否可以設想莎士比亞就是想借此來說明封建君主專制才是一切荒謬的起因呢?首先,一個荒謬的設想:李爾王要三分其國,免得日后有什么爭執。[4]5其次,就在即將付諸實施時,他又突生變故,為著一個荒唐的理由:三女兒未能如其所愿用甜言蜜語表達對他的敬愛;繼而一切悲劇開始上演。莎翁及其時代的人對政局的不滿是不言而喻的,但政治畢竟是一個敏感的話題,即便是對于戲劇家而言。于是乎,莎士比亞巧妙地利用了一個流傳已久為人熟知的故事框架,并嵌入了葛樂斯德輔線,加上其精心設計的看似荒唐的情節,既反映了自己的政治觀點,又引發觀者深入地思考,可謂以詩言志,一舉兩得。
封建社會人們一般的觀點是:好王當朝,任用賢能,國家一派正氣,就可把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5]92莎士比亞本人也曾是這一觀點的擁護者,例如在歷史劇《亨利五世》中他就塑造了自己心目中明君的光輝形象。在創作《李爾王》時,他對君主專制政體的態度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通過《李爾王》,莎士比亞明確地表明了這一觀點:即使是以“善始”繼位的明主,也很難有“善終”的結局,因為極端的權勢勢必造成統治者的驕橫跋扈,他們年輕時也許還有清醒的頭腦,可是到了年老昏聵之時,卻不免要嚴重地危及國家的政治生活。[3]159因此,當李爾王像古希臘英雄奧德修斯那樣歷經磨難終于認識到為人治國之道時,莎士比亞卻沒有給其機會,而是安排了其在絕望中死去的結局。似乎是要其為先前的荒誕行為付出代價,又似乎是說明封建君主制政體在當時只能是個悲劇。從某種程度上可以猜測,莎士比亞本人對“好王當朝”的美妙幻想產生了質疑,對人性是否本善產生了懷疑,對人類社會的未來也抱有深深的憂慮。
這一點還可以從其對柯苔莉亞的命運安排得以佐證。本來埃德蒙的陰謀已經敗露,雖然從政治角度看柯苔莉亞率領的法國軍隊戰敗有其合理性,但也大可不必非要置柯苔莉亞于死地。柯苔莉亞這一坦率正直、堅持自己做人原則、不讒言獻媚的正面人物形象承載著人們對正義公理的訴求,她的死意味著最終莎士比亞把這一線希望也抹殺了。于是,《李爾王》充滿了人的異化感和幻滅感,正如荒誕派戲劇里所再三揭示的那樣,一切的抗爭都是枉然,人類始終逃脫不了悲劇性的命運,而死亡是再自然不過的結局了。
五、結語
用現代主義去解讀一部創作于文藝復興時期的現實主義的悲劇,乍一看多少有些匪夷所思。但是對于現代主義或現實主義的劃分從來都不是絕對的,現代主義作品中可以有現實主義的成分,反之亦然。筆者從《李爾王》中發現了萌芽的現代主義因素,比如人的異化感,幻滅感以及人類命運的悲劇性和荒誕性。這些顯然與現代主義文學作品特別是荒誕派戲劇有著相通之處。我們必須強調這些還只是萌芽,還遠未發展到后現代戲劇中所展現的程度。如貝克特《劇終》所塑造的坐輪椅的主人,能走卻不能坐的仆人,這時人高度異化為蟲豸。
當然其淵源關系還不止于此。例如,現代主義作家重視主觀世界,不遺余力地揭示人物的感性生活和意識領域。[2]27雖說不可能在該劇中尋得類似意識流、蒙太奇的創作技巧,但《李爾王》的確對人物的精神世界給予了足夠的重視,特別是在塑造愛德蒙和李爾兩個人物形象時。其次,現代派作品的主人公往往發生身份認同危機,連自己的身份、地位都無法弄清,給讀者一種即可憐又可悲的感覺。[2]10“誰能告訴我我是什么人?”的困惑不正反映了李爾對于自我身份認同的危機嗎?再次,莎士比亞在該劇中大量使用了象征的藝術手法,使這部悲劇具有了詩歌的特質,即戲劇語言的詩歌化,這與現代主義作品中頻頻出現小說詩歌化的創作傾向如出一轍,突顯了莎翁作品的現代主義元素。
李維屏用“新”“晦”“悲”三個字概括了現代主義文學的藝術特征。[2]9-10雖然在《李爾王》中看不到后現代荒誕派的典型藝術手段,但是筆者認為《李爾王》對情節的頗有爭議的安排本身就體現了其創新之處,這個已在前文有所論及,此處無需贅述。至于“晦”,該劇以人物眾多,場面宏大,劇情復雜而著稱,搬上舞臺的《李爾王》很容易使觀眾感到雜亂無章、晦澀難懂。閱讀劇本雖可減少這種隱晦的程度,但莎士比亞劇中大量使用的俗語、俏皮話、隱喻及雙關也經常使人如墜霧里,不得要領。被認為莎士比亞最慘烈,最黑暗的悲劇《李爾王》其“悲”的特征不言而喻。如此,有論者奉莎士比亞為現代主義文學的鼻祖也不是空穴來風啊。
[1]張麗.莎士比亞戲劇分類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2]李維屏,戴鴻斌.什么是現代主義文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1.
[3]張泗洋,徐斌,張曉陽.莎士比亞引論(上)[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9.
[4]莎士比亞,方平,譯.李爾王[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
[5]張君川.時代的風暴—論《李爾王》[C].莎士比亞研究(創刊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6]周敏.莎翁筆底的“狂歡”——理解《李爾王》藝術上不協調的一把鑰匙[J].安康學院學報,2009,21(3).
[7]鄭敏.《李爾王》的象征意義[C].莎士比亞研究(創刊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