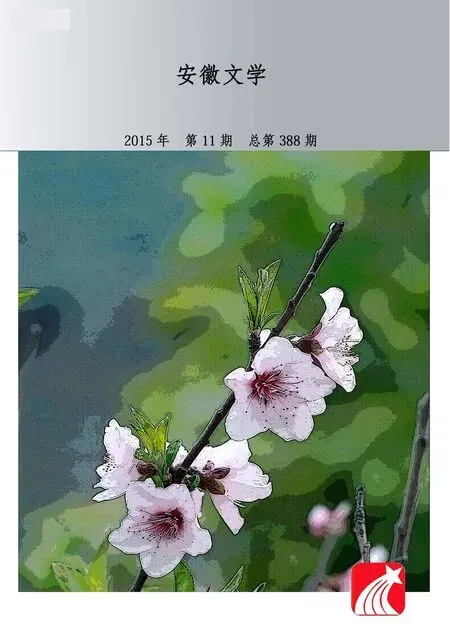論《占卜者》中的女性書寫
蔡奐 劉珊
云南民族大學
論《占卜者》中的女性書寫
蔡奐 劉珊
云南民族大學
加拿大女作家瑪格麗特·勞倫斯小說《占卜者》是當代加拿大文學中的經典。小說對敘事主題和敘事形式的突破,體現了作者對女性追求自由平等權利的思考。本文運用法國女性主義理論家埃萊娜·西蘇的“女性書寫”理論,分析小說中的身體寫作和非線性敘事所構建出的多元、發散、流動的女性主體文化,揭示作者反對性別兩元對立,提倡性別身份及社會文化多元的觀點。
瑪格麗特·勞倫斯 《占卜者》 埃萊娜·西蘇 女性書寫
一、引言
瑪格麗特·勞倫斯(Margaret Laurence,1926-1987)被譽為“加拿大的托爾斯泰”,在加拿大文學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她以自己的成長地尼帕瓦為原型,虛構了西部草原小鎮“馬納瓦卡”,創作了“馬納瓦卡五部曲”:《石頭天使》(1964)、《上帝的玩笑》(1966)、《火中人》(1969)、《屋中小鳥》(1970)、《占卜者》(1974)。其中《占卜者》是壓軸之作。該小說文筆洗練,優美雅致,講述了主人公莫拉格從底層少女到實現灰姑娘之夢,又從“錫安圣殿”的金絲雀到“娜拉”出走,最后成為了一名作家,用心去審視生活,占卜人生。
小說自問世以來受到國內外研究者的積極肯定。國外的評論主要從敘事學及多元文化等角度出發。例如,斯托弗在其專著中,從“元小說”角度,分析了《占卜者》中莫拉格所寫的五部小說,并指出《占卜者》這部小說也完全可以命名為《一個中年女作家的畫像》。[1]格林則稱贊瑪格麗特勞倫斯是現代四大主要作家之一,主要探究了《占卜者》中有關蘇格蘭和梅蒂斯人的民間傳說。[2]國內研究相對緩慢,評論界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小說中的意象和邊緣人物。其中也不乏關注小說中女性主義的研究。本文試圖在前人經典解讀的基礎之上,從埃萊娜·西蘇的“女性書寫”“會飛的語言”理論出發,對《占卜者》進行解讀。
二、女性書寫之身體書寫
埃萊娜·西蘇(Hélène Cixous,1937-)是當代法國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學理論家,她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提出“女性書寫”這一概念。“女性書寫/陰性書寫”指的是女性作家以表現自我、挑戰父權制文化傳統為目的的一種女性寫作方式。西蘇的女性身體書寫強調一種更親切、更豐富地情感表達,所表達的是女性獨有的生命感悟。女性書寫旨在解構男權意識形態對女性身體的控制,顛覆男性中心主義二元對立思維范式,建構女性新的文化向度與書寫空間。[3]借助女性書寫敘述策略,勞倫斯在其小說《占卜者》中成功地刻畫了一位顛覆男權社會、男性話語,大膽追求愛情與激情的女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改寫了女性被凝視及被書寫的命運。
身體書寫是西蘇女性寫作理論的核心。“身體書寫”中的身體是一種對抗菲勒斯中心主義的文化策略,是作為一種解構策略而存在和起作用的。西蘇的身體書寫理論可以從兩個方面理解:第一,身體書寫是女性作家用自己的身體感受和書寫女性自己的身體和身體感受;第二,身體書寫有女性政治的意味。西蘇認識到在父權社會,女性被迫與她們的身體分離,被教導要忽視它們,賦之以性的謙和與節制。[4]1907對此,西蘇倡導女性通過“身體寫作”這一寫作樣態,改寫其被凝視、被書寫的命運。[5]她指出,“幾乎一切關于女性的東西都有待于婦女來寫:她們的性特征,即她無盡的和變動著的錯綜復雜性,關于她們的性愛,她們身體中某一微小而又巨大區域的突然騷動。”[6]201
勞倫斯在其作品中關注女性身體描寫,作品中小說主角多為女性。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審視女性,她筆下的女性散發出美麗的神韻,形成了不同于男性作品中的女性群像。《占卜者》中對女性身體和欲望的大膽描述可以視為是對男權社會的有力反抗。勞倫斯獨特的女性敘事視角為《占卜者》帶來了強烈的敘述張力。例如,記憶庫電影:山谷下,第二幕中,“莫拉格很驚愕地發現自己并不害怕……她一點都不覺得害羞……她的軀體、胸脯、修長的雙腿和平坦的小腹,在她眼里忽然變得格外美麗,她想把自己呈現給他”。[7]188可以看出,在《占卜者》中,女性身體和欲望都得以解放,這里的身體概念擺脫了女性身體一直以來所處的被描摹的客體地位,成為表達意義的、能動的主體。除此之外,傳統小說中女性身體總是被放在觀淫男性凝視對象的位置上,但本小說中卻剛好相反——莫拉格處于凝視者的位置,被凝視的對象是男性身體。小說中有多處關于男性身體的描寫:“腹部寬廣,褐色的皮膚溫暖光滑……”[7]141“修長的身軀結實寬廣,肌肉發達,皮膚下的肋骨隱約可見……”[7]205。勞倫斯借助身體書寫策略改寫了女性被凝視的命運。
三、女性書寫之非線性敘事
二十世紀是語言的時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身處這種大氛圍中,自然會受到影響。西蘇認為,語言是控制文化和主體思維方式的力量,顛覆父權制必須從語言批判開始。女性要想獲得自由和解放,就必須形成一套不同于男性作家的敘述技巧和敘事語言。就如她在其代表作《美杜莎的笑聲》一文中,直言不諱地宣稱:“寫你自己,必須讓人們聽到你的身體。”[6]194書中提出“會飛的語言”這一概念,指出“飛翔是婦女的姿態——用語言飛翔也讓語言飛翔,我們都已學會了飛翔的藝術及其眾多的技術。”[6]201“婦女必須通過她們的身體來寫作,她們必須創造無法攻破的語言,這語言將摧毀隔閡、等級、花言巧語和清規戒律。”[6]201西蘇所說的無法攻破的語言不同于男權社會的象征語言。男權社會的象征語言是建立在邏輯和理性基礎之上的線性敘述,而西蘇認為女性寫作應該是修辭的、詩性的,所編織的語言應是“會飛的語言”即一種能夠掙脫牢籠,顛覆父權制中心話語的“新”語言。她主張女性作家創作要形成一套不同于男性作家的敘事形式和敘事語言即詩意的語言以徹底擺脫并摧毀禁錮她們的“清規戒律”的束縛。
通過細讀發現,勞倫斯作品中的多元敘事和詩意語言與西蘇“女性書寫”中對女性作家創作中獨特敘事形式和詩意語言的主張不謀而合。其作品《占卜者》在語言運用上對男權社會的語言及寫作方式進行了大膽的顛覆。勞倫斯在《占卜者》中運用獨特的敘事方式和語言技巧,她所編織的正是西蘇所描述的“會飛的語言”。首先,小說運用了元敘述的寫作方法穿越小說的不同層次,打破連貫的敘事流。小說一開始,就講述了莫拉格所遇到的兩大問題,一是女兒的叛逆離家出走,一是自己正處于寫作瓶頸期,文思枯竭。莫拉格的作家身份,使《占卜者》具備了元小說(metafiction)的特征——關于寫作的寫作,展現了小說的創作過程。而小說結尾“莫拉格轉回屋里,把構思好的小說的剩余部分寫完,并記下小說的題目”[7]466,暗示當莫拉格完成她的小說時,她同時也講述完了自己的人生經歷。其次,小說中勞倫斯用“快照”“記憶庫電影”等反傳統的敘事技巧,通過時空交錯的敘事方式使主人公在回憶與當下時空中穿梭。人物,場景及歷史故事隨著莫拉格的講述如電影蒙太奇一樣,不停地切換。再加上敘述聲音的交替、意識流技巧的應用使小說敘事呈現女性主義小說“碎片式的”、“非線性”的敘述特點。從敘述形式上解構了男權中心的語言和文化,構建出多元、發散、流動的女性主體文化。這種語言是對男性語言的挑戰和突破。
四、結論
埃萊娜·西蘇在《美杜莎的微笑》中提出的“女性書寫”理論對女性作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瑪格麗特·勞倫斯《占卜者》無論從身體書寫還是敘事形式和詩意語言方面都是對西蘇所提倡的“女性書寫”的典型再現。本文運用了西蘇的“女性書寫”“會飛的語言”相關理論,為小說闡釋提供了一種獨特的女性主義視角。此外小說中的馬納瓦卡的小鎮生活其實體現了一個時代、一種生活方式。而小說中塑造的女性形象鮮活真實,讓眾多女性讀者感同深受。勞倫斯的小說文本提供了一個能夠重新審視女性地位的全新視角,呼吁女性應擁有自己的空間,掌控自己的身體,發出自己的聲音。
[1]Stovel,NoraFoster.DivingMargaretLaurence—A Study of Her Complete Writings[M].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8:245-264.
[2]Greene Gayle.Changing the Story:Feminist Fiction and the Tradition[M].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
[3]林樹明.身/心兩元對立的詩意超越[J].外國文學評論,2001:2.
[4]Hélène Cixous.The laugh of Medusa.Trans.Keith Cohen and Paula Cohen[M].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9:1097.
[5]謝納.空間生產與文化表征—空間轉向視閾中的文學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232.
[6]張京媛.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7]瑪格麗特·勞倫斯著.占卜者[M].邱藝鴻,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