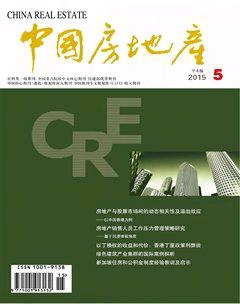以丁換權的收益和代價:香港丁屋政策利弊談
摘要:丁屋(Small House)是香港新界的特殊房屋形態。盡管丁屋的屋宇屬于私人,但政府仍然保留了土地所有權,即凡轉讓給非原住民的丁屋,都需在對外轉讓的時候按照市場價向政府補足地價。政府的這種置換安排有一定積極意義,即在保留政府很大一部分土地權利的同時,有效降低了管治成本,而同時丁屋的發展仍處在可控范圍,即在今后涉及到城市更新時,政府仍可以以較低成本重新買回這些屋宇。當然,有得必有失,丁屋政策也不是全無代價,由于政府嚴格限制了這些屋宇的尺寸,使得丁屋容積率偏低,在香港寸土寸金的大環境下,這些屋宇在占地方面就顯得超額,而這樣的資源搭配就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福利損耗。同時,丁屋政策轉移給原住民一定的租值,這使得很多原住民選擇不再工作,成為食祿階層,在一定程度上浪費了香港本就稀缺的勞動力。更重要的是,考慮到村民子子孫孫都享有這種丁權,這種約定使得政府不得不保留大片土地用于應付未來的丁權行使,這使得可供政府自由發展的土地過少,從而導致市區過于擁擠。討論香港以丁換權的收益和代價,嘗試分析丁屋的歷史權利界定對香港地政民生所產生的深遠利弊,并以史論今,通過對比香港丁屋和內地城中村發展的差異來為內地制定相應政策提供參考。
關鍵詞:香港土地史,權利置換,產權和制度,土地政策,法律與經濟
中圖分類號:F293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1-9138-(2015)05-0018-24 收稿日期:2015-04-16
1 丁屋緣起
1841年,清政府戰敗,被迫和英國簽訂了《穿鼻草約》,將香港島割讓給了英國政府。同年,英國軍隊占領了香港島,作為遠東英軍的駐扎基地。清政府最初以琦善無權割地為由,拒絕承認《穿鼻草約》。不過割地一事在第二年清政府再次戰敗之后成為事實。1842年,清政府和英國政府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正式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1860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再次戰敗,于是重蹈覆轍,被迫簽下《北京條約》,把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割讓給了英國。而英國人獲取九龍的主要目的則是為了建立戰術緩沖地帶,以維護香港島上駐軍的安全。
與割讓港島和九龍不同,英國人獲取新界的方式是通過租借。1898年,英國政府以香港的防衛需要加強為由,逼使清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將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北到新界深圳河以南地區(除九龍城寨),以及附近200多離島一并租給英國,為期99年。
因為新界并非割讓,英軍占領了新界之后,發現無法像從前一樣簡單地宣布所有土地屬于英國女王。而當時在新界散布的原住民手中所持的,乃清政府頒發的永久地契,明確規定了土地的私有性質,并且沒有限制土地用途,因此殖民地政府若強行占地則會面臨輿論和實際操作兩個難題。1905年殖民政府采取了折衷的辦法,將新界土地產權變為承租官契,即土地甲方為英國皇室,而原居民變為承租乙方,必須每年繳納地稅。這種方式的實質還是剝奪了原業主的土地所有權,但這名義上的權利變化并不影響當時村民對土地的實際使用。新界當時還是農村,村民所需的只是耕種以及本戶居住的權利,而轉讓和開發在當時并不普遍,因此這種承租契約雖然侵犯了原住民的產權,但在操作中并未產生太大的問題。
1972年,當港英政府決定開發新界的時候,土地權利的矛盾沖突就到了必須解決的關頭。即便之前簽訂了承租條約,村民仍然有抗拒征地的理由,因為他們原本擁有的就是永久地權。因此若要獲得村民的支持,殖民政府必須給予村民一定的權利置換,使得抗拒征地的凈收益低過承認承租條約的凈收益。1972年12月,政府出臺了《新界鄉村小型屋宇政策》,規定凡當年參與簽約的新界居民,年滿18歲的男丁,一生都可獲取一次特權,修建1棟屬于自己的小型屋宇。這樣的屋宇被嚴格控制在每層700尺大小,一共3層不超過25英尺高。因為限于男丁,這種屋宇被稱之為丁屋。丁屋政策給予村民的好處是世襲的和可擴展的,可擴展性源自對于丁權數目的不限定性,即子孫中男丁越多,則可獲取更多的丁權。遠大于村民抗拒征地的好處,因而獲得了推廣,下面會詳細討論這一政策的具體內容。
2 以丁換權的權利界定
在英國政府參與前,新界的地權是永久的私人地權,持有地契的權利人可以自由使用其所擁有的土地。而在英國政府參與后,新界土地變為承租性質,即殖民政府為甲方,擁有處置權,而村民變為乙方,獲得的只是土地的使用權利,并且有用途限制。丁屋所處的土地,也受到該承租契約的限制,即村民獲準修建總面積2100平方尺,不高于25英尺的3層小樓。
丁屋政策是政府為減小地權轉變過程中的執法成本而做出的妥協。作為對于強制村民讓出永久地權的補償,政府給予了一定優惠政策,即丁屋在村民自己居住期間可豁免差餉,而差餉原本是任何私有土地都需承擔的費用。更重要的是,丁權屬于世襲和可擴展權利,即如果該原住民家庭生育了多個男丁,那么就可以拿到更多的丁屋土地,這等于是將村民現有的固定大小的永久地權拿走,但置換成對將來更多土地的丁權,即便這些只是使用權,但畢竟權利所轄面積可隨人口增長而擴大,政府也必須預留大片丁權土地以應付將來的人口增長。因此這些權利置換使得丁屋政策在當時更容易推行。
除尺寸限制外,丁屋的轉讓受到嚴格控制,在轉讓時,新業主必須按照市價向政府繳納一定的土地費用,俗稱補地價。這一措施排除了非原住民染指丁權的可能性。當然,如果村民并不出讓其丁屋,只是永久用來收租,那么政府的補地價部分就拿不到,也會一并被村民收走。
丁屋政策以未來的丁權置換新界原住民現有的私有土地,因此獲得了成功推廣。這一政策的權利界定基本是明晰的,政府給予每個新界男丁的只是三層小樓的使用權利,這權利包括自己住和出租的收益,并且通過補地價政策(即丁屋在對外轉讓的時候按照市場價向政府補足地價)排除了非原住民染指的可能性,這樣一來丁屋引起的糾紛有限。但丁屋的一個悖論在于丁權的世襲性和擴展性,即子子孫孫都有這樣的權利,那么隨著人口的增長,所需土地無窮無盡,而政府將來并無這么多土地用于行使丁權。
合理的解釋在于這一權利安排在港英政府期間是可行的,因為考慮到99年的新界租期,港英政府的此項置換安排實際上是將便利留給了自己,問題則留給了將來香港回歸后的中國香港政府,因為在港英執政期間,考慮到人口繁殖所需時間,行使丁權所需的土地并無可能在99年內發展到無法想象的地步。
事實上,這一權利安排引起的問題在1997年香港回歸后已經開始凸顯。據新界鄉議局2003年的估計,香港有24萬新界男丁擁有丁權(劉敏莉,2013),即便以0.5的建筑覆蓋率計算,不考慮人口增長,都需要超過3700公頃的土地來安置。而根據最新統計,預留的政府鄉村發展土地只有3147公頃(香港規劃署,2012),遠遠不夠。一方面是土地的緊缺,另一方面政府則必須預留大量土地以供未來村民的子孫行使丁權。政府也在考慮修改丁屋政策,考慮將丁權中的三層小樓改變成高層建筑中的一定面積,但修改政策成本很高,在政治上并不討好,因為新界居民必然反對。
3 丁屋政策利弊談
丁屋政策對香港的地政民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這影響源自于特定的合約安排對經濟結果可能產生的決定性作用。這符合真實世界中經濟學的一般結論,即在非生產性成本大于零的時候,經濟結果只可能是收入轉移,福利損耗,或二者兼備。
對當前權利的索求和對未來權利的放棄為港英政府的丁屋政策的實行帶來了便利,這減小了丁屋政策的早期執行成本,即早期的社會成本,為港英政府發展新界帶來了契機。當然這一便利的背后則是未來的無窮無盡的丁權問題。
就收入分配而言,丁屋政策以期權換權利,減小了當時的執法成本,丁屋的發展在政府可控范圍,因此對當時的香港經濟有利。但從長遠來說,則有一系列的問題。第一,該權利的置換是否是等價?從短期來看,一部分權利及其附屬收入是從村民手中轉移到了政府手中,因為政府是獲取了新界原住民手中永久地權的一部分。但從長期看,政府是用無窮盡的期權去換取當時的權利,因此最終仍然是村民及其子孫獲取了更多權利,當然,在1997年之后契約甲方改變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因此最后負擔損失的并非是英國政府。這一權利置換盡管無法計算具體數額,仍可以簡單描述為土地權利從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轉移到村民手中,然后從村民手中轉移到了港英政府手中。或者用權利相欠來描述更為清楚,即港英政府借取村民土地權利,而還債人需要用超額權利去償還,這個還債人卻變為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假如現在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當時亦可參與政策制定,那么這政策必然不能通過,但因為當時并不存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而中國政府當時亦未參與政策討論,因此這一權利轉移是在權利最終移出方并未參與的情況下制定的,對于參與政策的港英政府以及新界居民來說則是皆大歡喜,因此政策獲得了成功推行。
從對地政民生的影響而言,丁屋政策并非一定會導致社會福利損耗,其實際產生的損耗則源于城市垂直發展的需求,即當新界城市化進度加快之后,三層小樓的尺寸安排損耗的是本可以修建的超過三層部分的租值。根據統計(劉敏莉,2013),自1972年到2011年,政府批出的位于鄉村發展區內的丁屋數量總計為36912個,按照香港市場此類住房每層每月租值為1萬元港幣計算,若以最高可建33層為標準,則每月損耗社會福利最高可達110.7億元。這一損耗并非是政策之過,而源于時間變化帶來的預測誤差,其損耗也只是暫時的,因為將來政府可以考慮征收丁屋并重建為高層住宅。而將村屋控制為三層小樓可能也包含了政府這一重建考慮,即這會使得重建的補償問題較為簡單。當然,這一過程并非一帆風順,實施起來會有重重阻礙,所以,即便丁屋政策的權利界定清晰,要維護三層以上空間的政府所屬權利仍然不容易(名義權利和實際控制權分離,并且變動合約的成本高企),而實際損耗難以避免。
除尺寸過時導致的損耗之外,為應付未來丁權而預留的大片土地,則損耗當期福利。參考前段的計算,以預留的3147公頃土地可供修建20萬棟丁屋為標準,這些損耗最高每月可高達600多億元港幣(按前文提到的如建非丁屋平均可建33層為標準計算)。當大量香港市民擠在狹小空間里蝸居之時,新界的大量可建設用地卻一直閑置,無法用于建設,村民未來的子孫還未出生,政府無法同村民未來的子孫談判達成任何合作,談判成本無窮大。這種權利約定對于土地資源緊缺的香港來說是一種極大的浪費,亦解釋了香港市區規劃得極其擁擠,而郊區土地卻大片閑置這一畸形城市規劃的形成原因(這種畸形城市發展從很長時間段看都難找到解決方案)。與此同時,新界原住民享受的這一特權,亦導致食祿階層的產生,這也浪費了香港本來就稀缺的勞動力資源。
當然,除此之外,丁屋政策并未賦予婦女丁權,因此在歷次女權運動中備受詬病,這引起的社會沖突,也可計算為福利耗損的一部分。
4 和內地城中村的對比
不同的產權厘定,使得香港丁屋的發展有別于內地城中村。換言之,為減小執行成本所作出的權利置換安排,其導致的收入轉移和福利損耗本身就是政策的一部分,是政策的主動安排。而內地城中村的不明晰產權,則導致了城中村發展的失控,即城中村的發展偏離了權利設定的初衷,造成了事實上的權利轉移和損耗。
在聶致鋼和黃國俊(Nie and Wong,2012)的文章中談及,內地城中村不完整和不明晰的產權導致宅基地上著建筑的密度失控,形成了握手村,即城中村的超建,并導致了社會福利損耗。這一結果建立在城中村和非城中村小區的租值對比之上,也證實了城中村中缺失的城市規劃管制對于非城中村經濟效率而言有正面效果。超建導致的損耗加上政府的部分地權以及較小的協商成本,則給城中村建筑帶來了較短的壽命(相比正規產權建筑的超過20年的經濟壽命,城中村建筑的經濟壽命大約10來年左右)。
這些現象在丁屋中都沒有出現。丁屋是受到政府嚴格管控的產物,因此違建雖有,卻并不普遍。很多時候,所謂的違建只是村民在樓頂搭了一個簡易的雨棚而已。相比內地城中村,丁屋的執法成本更低,這源于事先的明晰產權。村民因為對未來的丁權很滿意,所以對于承租契約的認可度很高,他們也擔心若不執行契約會損失掉未來的丁權,因此違法成本高企,這也減小了政府的執法成本。而相比于三層村屋,政府執法的動力也來源于保護自己的更多的可收回的租值,即執法能給政府帶來更高的租值回報,遠超過執法成本。試想,拆掉一棟三層小樓而代之以55層的高層建筑可能獲取的租值,怎不會遠超過執法的成本?即使政府未必有拆遷計劃,但潛在的高租值也可能是支撐政府執法的動力。不僅如此,香港有相比內地更充足和高效的常備警力,人口約700萬的香港的常備警力有36535人(香港警務處警方統計數字,2012),占人口比例約千分之五,而人口過千萬的深圳的常備警力則只有1萬余人(Nie,2014),只占人口比例的約千分之一,而且深圳關外警力尤其薄弱,警員占總人口比例只有約萬分之五。這也有效降低了額外的執法成本。
而反觀內地城中村的發展,由于事先權利界定不清楚,政府能對村民施加的法律成本有限,執法有困難,因此城中村的高度和建筑密度都不容易控制,這形成惡性循環,即越不容易控制則違建越多,則可回收的可能租值更少,則更難控制。這在警力不足,而租值也不夠高的深圳郊區尤為明顯,即十幾層的違法建筑在深圳郊區比比皆是,而政府則無能為力。
5 結論和啟示
綜合上面的討論,香港的丁屋政策起源于1898年新界租讓給英國政府之后租權與原住民的永久地權的權利沖突。而作為一種解決沖突的合約安排,港英政府以未來的丁權置換當時的地權,即所謂的“以丁換權”,減小了當時的執法成本,這對于港英政府推行香港新界的城市化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別于內地城中村的例子,其影響機制較為簡單,即權利的轉移是從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到村民,再到當時的殖民地政府。 機制雖然簡單,但其影響卻很深遠,整個香港的地政民生都因之而改變,按照上文中的估算,每月的影響總值可達將近1000億元港幣。這只是影響總額,并非是凈損耗,估算后者會更復雜,因為還需減去居住現狀所能挽回的殘值。除執法成本和社會沖突所產生的社會損耗外,這些影響主要來源于三個途徑:一是丁屋尺寸過小帶來的丁屋上部空間的浪費,損耗社會福利;二是為保障未來丁權而荒廢大量新界土地,導致社會福利損失;三是形成了食祿階層,造成了勞動力閑置。這些都是其政策本身能預料到的產物。而內地城中村的發展,則偏離了權利設定的初衷,政府的一部分租值被強行轉移到了村民手中,而政府在特定條件下挽回租值的辦法則僅僅限于對城中村的更新改造,而伴隨著改造的則是浪費,比如十年的新建筑也被推倒。因此,內地城中村的社會損耗則主要源自超建和拆遷,而其經濟結果往往更為激烈,其對內地地政民生的長期影響雖然還未完全浮出水面,但可以預期到同樣會很深遠。
香港丁屋政策的發展歷史以及同內地城中村的比較帶給我們的啟示主要有幾點。
第一,權利在法律意義上的清晰界定是經濟效率的保障,因此當權利界定不清晰或者兩種權利起沖突的時候,經濟結果就可能偏離最優。丁屋政策作為解決港英政府租權和原住民地權沖突的產物,其最終結果仍然帶來了權利轉移和社會損耗,而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這一政策帶來的麻煩仍將深刻影響香港的城市規劃、土地政策以及土地市場。當然,這并非是說清晰的權利界定一定不會帶來收入轉移或社會損耗,而只是說清晰的產權對經濟效率有一定的正面效果。
第二,執法成本對經濟結果的影響。香港新界的租權和地權的沖突,帶來了丁屋政策,這是一種新的產權安排,同時也是對于執法成本這一非生產性成本的一種適應(比如港英政府為了減小執法成本而犧牲未來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權益)。而其經濟結果也同樣受到各種非生產性成本的影響(比如名義權利和實際控制權分離導致丁屋三層以上空間無法有效利用)。同樣,內地城中村的發展,也反映了高額執法成本對于經濟結果的影響,即政府對城中村的超建違建的放任本質上源自高額的執法成本,這里有產權不清晰的作用,也有警力配比的影響(比如前段所述的深圳郊區警力配比失衡導致大量違建的例子)。當然,其他類型的非生產成本也必然對經濟結果產生影響,而對于其中之一的執法成本的強調并不否認其他成本的作用,也不否認產權明晰的重要性。因此,香港丁屋政策以及和內地城中村發展的對比帶來的啟示延伸了科斯定理(Coase, 1960)的具體涵義,即產權和交易成本都適用于成本分析,都對經濟過程和結果產生影響。而從一般意義而言,對丁屋政策的成本分析,不但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香港城市擁擠,郊區土地浪費背后的苦衷,也可給內地正在進行的保障房安居房建設提供決策分析參考,這啟發我們在制定政策的時候要謹慎。不僅如此,這些分析也有助于我們思考如何才能制定合適的法律以降低執法成本,達到現實約束條件下的社會最優。
第三,以丁換權有利有弊,這提醒我們在制定政策的時候要審慎。當年港英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時候,因為代價無需自己承擔,因此更多的是考慮到當期收益,這給香港回歸后的土地政策帶來了深遠的負面影響。而內地政府在制定土地政策的時候,收益和代價的承擔方都是自己,因此制定政策時更加應該審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前期的詳細利弊分析就必不可少。
參考文獻:
1.Coase,R.H.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60.3
2.劉敏莉.小型屋宇政策II:最新發展,思匯政策研究所研究報告.2013.http://www.civic-exchange.org/wp/wp-content/uploads/2013/04/SHP_cn.pdf
3.Nie,Z.A and Wong,K.C,Why Build More to Earn Less:Property Rights Implications of Urban Villages.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2012.12
4.香港警務處統計數字.http://www.police.gov.hk/info/doc/2012_police_in_fig.pdf.2012
5.香港規劃署.審核2012-13年度開支預算,答復編號DEVB(PL)223.http://www.pland.gov.hk/pland_tc/press/exam12/pdf_c/223-3491.pdf.2012
作者簡介:
聶致鋼,香港大學房地產與建設系博士,現為南京財經大學城市發展研究院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房地產經濟、價格理論、土地產權以及制度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