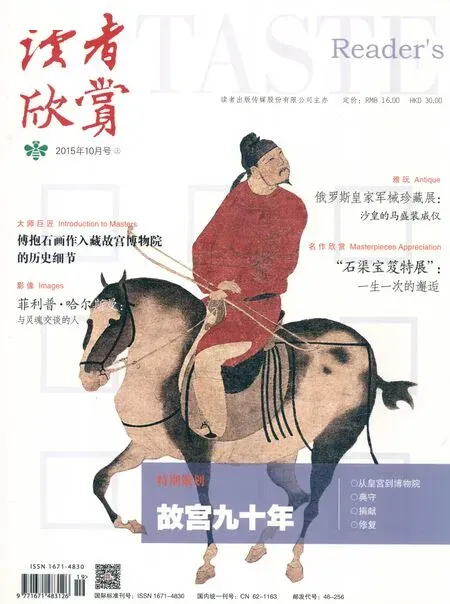《聶隱娘》與文青的讀圖時代(上)

在戛納獲得最佳導演獎的《聶隱娘》,在大陸上映后成為一個文化現象,但這不是侯孝賢的勝利,甚至不是文藝片的勝利,而是圖像時代的勝利。《聶隱娘》中那些“唯美意境”的圖像,恰恰符合了這個讀圖時代的文青和小資對圖像審美的最高想象。《聶隱娘》在各種社交媒體上的刷屏,在各大文化媒體上的爆紅,與其說是觀眾對侯氏美學堅持多年的鼓勵,不如說是讀圖時代的文青與小資對流行圖像的致敬。
作為著名的好萊塢敘事的反對者,侯孝賢在《聶隱娘》里繼續輕故事、重鏡頭的侯氏美學。侯孝賢的作品一向不著迷于營造沖突與刺激的戲劇感,故事的推進完全依賴畫面的空間和景深長鏡頭,而不是緊張、刺激的故事情節。
作為著名的冷靜而疏離的旁觀者,侯孝賢一向喜歡藏在長鏡頭背后,不動聲色地看著他的主角。從《戀戀風塵》里阿云的離別他嫁,到《悲情城市》里熱血青年的慷慨陳詞,再到《風柜里來的人》幫派青年的群毆。這一回,導演一如既往地藏在長鏡頭后觀看一個唐代女子的傳奇。只不過這一回因為主角形象的單薄蒼白,侯導內斂而疏離的招牌長鏡頭顯得有點可笑而裝腔。長鏡頭固然可以保留時間的完整和空間的統一,但是被剪輯得支離破碎的情節,讓時間與空間的完整失去意義。
在以往的侯孝賢作品中,導演喜歡用遠景固定長鏡頭來拍攝稻田、山川、原野、河流、海浪,表現東方田園詩的寧靜悠遠。在《聶隱娘》中,依舊有峰巒疊嶂的遠山、輕煙籠罩的樹林、碧波起伏的河流,只是這一回,破碎的故事和模糊的人物讓堆砌其上的唯美圖像顯得生硬乏味。虛弱與蒼白的主題讓長鏡頭更加冗長,空鏡頭更加空洞。
侯孝賢講述過許多“尋找身份”的故事。《悲情城市》講述新政權下臺灣知識分子對祖國憧憬的失落與對身份認同感的破碎。《冬冬的假期》講述主角告別童年、尋找青少年身份的故事。《童年往事》講述兩代大陸移民在臺灣尋找不同的文化身份。《聶隱娘》同樣是一個講述尋找身份的故事。但是片中的人物模糊、動機曖昧、細節破碎,既沒有動人的情感,也沒有感人的價值觀,女主角在貴族、刺客、俠士、隱士各個身份中的糾纏失敗,仿佛也折射出導演的失敗。
以往的侯孝賢作品仿佛一顆青橄欖或一杯淡茶,口感淡而回味悠長。“二·二八”事件中臺灣知識分子的命運,鄉鎮青年在大都市中的闖蕩,現實的關懷與人性的發掘,都值得我們通過冷漠的長鏡頭和詩化的空鏡頭去細細體味。那些關于青春的叛逃與成長的迷失,那些鄉土情結與家庭歸屬的情感救贖,值得我們忍受(或享受)導演的弱敘事和慢節奏。但是《聶隱娘》并沒有給出一個充分的理由,讓我們放下視聽享受和敘事快感去熬上一個半小時。
除了“反主流”與“理想主義”的贊美之外,在對《聶隱娘》的支持聲中,我們幾乎看不到對電影語言的分析,也看不到《聶隱娘》與侯導舊作的對比,只有一片“詩意”和“浪漫”的單調鼓噪聲。
事實上,《聶隱娘》引起刷屏和爆紅的最大原因,就是那些明信片一般的古建筑和山水圖像。曖昧的暖色調、華麗典雅的布景映襯出藩鎮府衙的奢靡與大唐的繁華,遠山白云的橫移空鏡頭滿足了觀眾對中國水墨畫的最高想象,每一幅畫面都取悅著觀眾的眼睛,但是也僅此而已。
我們要知道的是,今天雖然屬于圖像時代,但是圖像的美與豐富并不僅限于那些“唯美而有意境”的流行文化圖像。
人類最早只有語言和圖像兩種表達能力。隨著文字的出現,圖像從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隱退,蛻變為工匠或藝術家才掌握的技巧。19世紀攝影的發明觸發了圖像時代卷土重來的契機,20世紀,在流行文化和消費文化的裹挾下,圖像重新征服了世界,我們再次邁進圖像時代。(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