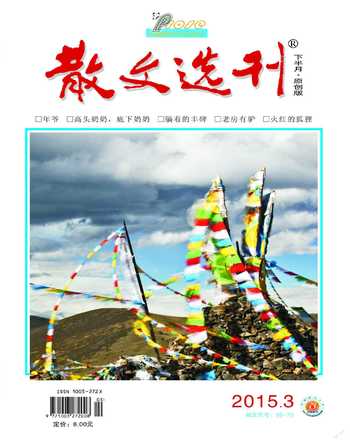山中聽鳥
孫江月
君若問我:“花鳥二物,造物生之以媚人者也,你喜愛誰?”我必答日:“二者皆喜皆愛,但鳥之喜愛更切。”固然古人愛拿“嬌花嫩蕊”以代美人,但“鳥啼聲脆”我則日可代管弦絲竹,百聽不厭矣。
我之家鄉地處長江中上游的一個鄉間僻野,那里風光綺麗,鳥類眾多,是鳥的世界。每值花柳爭妍之日,山坡、林間、房前屋后便是一派飛鳴斗巧的景象。當黎明時,你還未起床,窗外就不斷有鳥兒來啼喚。那啼喚聲真精神,是裹了陽光和希望的精髓的,又像是從音樂學堂受了基礎專業訓練出來的。你只需稍加細聽,就會覺得這來自大自然的天籟聲,有時是單音,有時是重音;有時是獨唱,有時是合唱,有時又是爭唱;大有目不暇接、耳不暇聽之勢,使你感受到獨唱中獲得個性的解放,合唱中獲得生命的和諧,爭唱中獲得自由與奮進!它們發白肺腑的聲音,常常是以時序的不同而變化著的。若是清晨,鳥們特喜繃起嗓門,引吭高歌,那唱腔多半是亢奮明亮的,是飲了興奮劑的。所以,它們在樹梢與天空間,時而輕靈振翅,時而摶扶搖直上,時而低落回巡。若是黃昏,鳥們的嗓音則變得平和、孤矜,那種“婉轉弄芳辰”的美聲唱法的熱情,隨著夕陽西下而不再延續,在幾聲如風搖銀鈴般的輕抒低吟后,便各自為伍,梳理著羽毛,咕咕嚶嚶互擺著一天的見聞,然后靜靜地歸巢而去。
這淡遠靜逸的生活,我永不忘懷。
來山中待不多久,你就會學得“以聲識鳥”的本領。如果聲音聽來是婉轉的、圓潤的,那一定是俊俏的畫眉、白靈,如果聲音聽來是清脆的、嘹亮的,那一定是批了金蓑的黃鶯兒或是八哥,如果聲音聽來是哀婉、凄絕的,不用說那一定是遠歸客愁的杜鵑了,且讓你一時想到“望帝”“杜宇”的分兒上去。山中的鳥聲就是如此地恬然、純凈,它充滿著無限美好的詩意,像潺潺的瀑流,在大地上呦呦回應著,有時還像是在拋磚引玉,一聲飛抵過來達六七個音階。這個時候,各類鳥們的歡鳴聲最愛接踵而起,一浪高一浪,形成歌的海洋。簡直是一派和諧的交響樂了。霎時,你心里會由衷地感到快活,且覺得你是一個自由的、純粹的人了,甚至是一個充滿了高尚境界的人,一切人生的煩惱都拋置于腦后。
也許是因性情所驅,見了這飛翔的美麗,聽了這動聽的歌喉,有時你真天真得像三兩歲的孩子,要去追蹤這些自由、浪漫的精靈。鳥兒們真有靈犀呀,見了你它可高興,一會唧唧喳喳,像是在逗你,一會忽隱忽現,又像是在與你捉迷藏,當你追它到了山頂,它們卻機靈地拐一個彎,從山頂飛下了山腳,當你白山頂追到出腳來時,它們則迅速地轉向另一個山頭去了。嗨,你怎么追得上它呢?那是長了靈翅的鳥哇!終于,你追它不上了,累了,于是你靠著山道,或是林間的一方空地坐下來,抽一支煙,免不了要作一些或大或小或近或遠的思考吧,那思考的課題我想多半是人與自然的!是啊,鳥是沒有時間和空間差的,它白窠巢脫離出來,造物主就注定它是一名自由的、抒情的、浪漫的歌手——云游四方,成為人間與天堂的訊音者!因而,我們人類在為其白身的享樂時,絕不能有任意捕之、獵之、牢之的行為與思想!
由此,我又想到都市人的養鳥來。
古代有“玩物喪志”的說法,而現代人不然,以為養鳥是一種“修身養性”的好方法。可為其享樂,給鳥——這天地間的訊音者帶來的卻是怎樣的痛苦和不幸呢?例如黃鶯,它的性情就特別暴躁,一旦關進籠子里便孑立不安,亂蹦亂跳,甚至撞擊樊籠,往往不到一天工夫就急死了。有這么一天,我去逛公園,見有一人提著鳥籠,那鳥籠確是精巧,竹木棍兒編之,并以生漆漆之,一只鳥就在里面孑立不安,且不時撞擊著竹籠,暴跳著欲死也。據有經驗的人講,這是剛從山林中捕來的。于是,我向前朝提鳥籠的人說:“‘鳥之性情唯在林木,樊籠之與林木有天淵之隔,放了它吧,你看它撞得頭破血流的樣子,好可憐嘍!”那人把我嘹了幾眼兀自走了。我看著那人走去,腦子里突地記起清人鄭板橋說過的話:
“……所云不得籠中養鳥,而予又未嘗不愛鳥,但養之有道耳。欲養鳥莫如多種樹,使繞屋數百株,扶疏茂密,為鳥國鳥家。將旦時,睡夢初醒,尚輾轉在被,聽一片啁啾,如《云門》《成池》之奏,又披衣而起,洗面漱口啜茗,見其揚暈振彩,倏往倏來,目不暇給,固非一籠一羽之樂而已……”
鄭板橋的這番話說得實在好,他不僅為我們樹立了一個愛鳥者的光輝形象(典范),而且還提出了護鳥的行動方案。這是怎樣的先賢者的偉大思想啊!這樣眷懷著,思考著,身子不知幾時已離開了喧囂的城市,回到了親近的故鄉。于是,輕輕地我推開自然的門,一群樊籠之鳥從我的心里飛了出來,向山中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