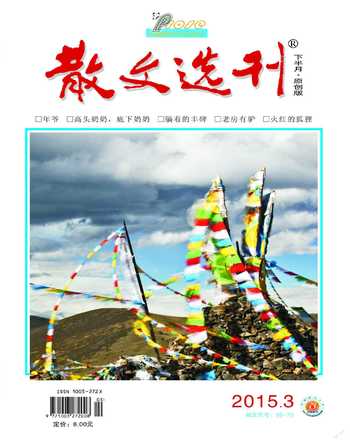南雁的箴言
施立松
與南雁蕩山做了多年鄰居,有事沒事,到山中去,就像到鄰居家串串門。
秋風乍起,一池秋水,皺了平,平了皺,像心底的微瀾,起起落落,頗不平靜,便想,到南雁去。
人還未到,早有雁鳴聲聲,報告客來消息;早有溪澗潺潺,烹茶煮酒等你;早有煙嵐裊裊,如炊煙四起,遨你推杯換盞,飲風啜露。石天窗邊,早有一樹楓紅憑窗而望。窗在那溪邊的大懸巖上,宋人項桂發說:“深游南雁見名山,石洞天窗夜不關。”石天窗早早就聞名遐邇了。
南雁的門扉,是一道清溪,淺淺的,溪石清晰可數,柔柔的,宛如一襲碧綠的錦。挽起褲腳涉水也能過的,但撐一桿竹排去輕扣南雁柴扉,更顯風雅,更富童趣。竹排上三五張竹椅,三五人坐著,都不老實,赤了腳劃水的,扯起嗓子唱山歌的,擺弄相機企圖收了水光山色去的,還有伸手撩水潑人的,相熟不相熟的,挨了潑也不生氣,回不回擊,都一樣笑臉盈盈。竹竿一撐,竹排一蕩,人就到山水里了,和鳥、石頭、樹、溪,融為一體,光陰的小舟,就從凡俗人世撐到了世外桃源。
南雁一挑門簾出來迎你。那門簾是一掛青石,巧手的人繡了“東南屏障”字樣,再用紫藤用細草用蒼苔打了底暈了色,不用說,這是造化的手筆。隱在屏障后的臉,是帶了蟬鳴的寧靜,是風來雨去只等閑的閑逸,一望,便能讓人心靜神寧。
南雁種了半坡野菊。藍瓣黃蕊,藍得清雅,黃得明艷。一眼望去,只覺得還沾著曉露的野菊,是眼眸清澈,笑聲清越的村姑,在輕風中搖擺著身姿。蹲下來,細嗅著菊香,微微清苦的香氣,一陣陣的,打壓住心上的無名火,上火多時的唇齒,便消了腫似的安適了。以寧靜鑲邊,明艷才不至浮躁,這是野菊的暗語吧,那心素如簡,人淡如菊,就是南雁寫了半坡的箴言了。半坡菊花,夠做一個菊花枕吧,枕一枕菊香入夢,時光蕩開漣漪,夜夜心心,都是清涼,都是修行。
仙姑洞是要去的,倒不是為沾幾許仙風道骨,只為洞西懸崖下的怡心院。其實,怡心院也沒什么特別,是院前那一片桂花林讓人魂牽夢縈。這時節的桂花,像深巷里的美酒,像腹有詩書的佳人,像胸懷韜略的大將,灼灼光華,藏是藏不住的了。索性,就不藏了,細細碎碎地開了,細細碎碎地碾開一條花香滿徑的路,把秋天逼得紅了臉,蕭瑟的日子都變得溫暖。按說,桂花是不適合道人修行的,因為它太濃烈,太灼灼逼人,太讓人心旌搖曳,一晃神,把持不住,多年修行匯聚的真氣,便一瀉千里。幸而山洞深幽,來自地底的幽冷,封存住濃濃的香氣,再慢慢釋放出來,就成了醍醐灌頂的冷香,難怪那道人能在這里一修百年。秋到南雁,是沒有愁煩和悲凄的,傷春悲秋,只是那些心窄眼小、神經脆弱的人的專利,大氣磅礴如南雁,千萬年的時光,早把那些小心思小情緒滌蕩得千回百轉,心胸開闊到亦無風雨亦無晴了。歲月的殺豬刀,從來都奈何不了活在年歲之外的人。
會文書院也是要走一趟的。華表峰下,石門開處,圓筒洞里,會文書院依洞而筑,清雅幽靜,泉水一滴一答,如鐘擺丈量歲月。古色古香的樓房,樹墩坐成一把風雅的凳子,這時候,最想持一卷詩書,朗聲誦上幾句,搖頭晃腦地,與化在故紙堆后的才思,把手言歡。一縷陽光斜射進來,明晃晃的,像一把穿越時空的利劍,猛插進來。瞇細了眼看,恍惚中,見北宋末年的陳經正、陳經邦兄弟也搖頭晃腦地踱著方步,見一干青衫席地而坐,聽朱熹狂曬思想,見孫衣言飽蘸濃墨,大筆一揮,刷刷寫下:“伊洛微言持敬始,永嘉前輩讀書多。”人生中的遇見,都在不經意間完成,在每一個細微的角落,總能遇見你想遇見的。
秋陽易逝,只一瞬,便鳴金收兵。攏回思緒,倚窗而坐,仿若坐在季節的渡口,落葉一枚,姍姍而降,是南雁書冊落下的書簽吧,穩穩接在手中,像握了一把蒼涼。紅塵的花影,芬芳的相會,都成前塵往事了,不變的,是時光的容顏、南雁的襟懷。也學著門前聽詩叟的姿勢,側耳聽南雁寫在風中的詩句,只覺得心間有一抹云淡風輕的覺知,在伸枝展葉。
坐一回纜車吧,如雁般,權當輕盈了一把,凌空了一回,把萬壑千山踩在腳下。南雁的纜車,其實是一把長椅,用一根鋼管輕輕一攔,無遮無擋地,雙腿一前一后地晃著,不必言語,清風自來,把身上的塵土,都抖一抖,把心上的煩憂,都滌蕩了去。
心里住了南雁,到哪里都是云水禪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