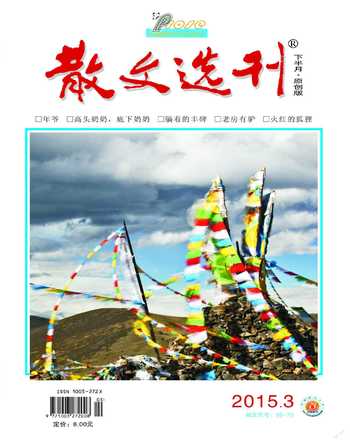土布就像母愛
周鋒榮
最近,母親送來一條珍藏了30年的土布,給我做被套。長長的土布,沒經過染料浸泡,柔軟而又樸實,幾條彩線像雨后的彩虹,閃爍著溫馨……
我接過土布,沉甸甸的,就像懷抱母親的艱辛和悲歡。撫摸著這每寸布,粗糙卻又溫厚,隱隱散發藍靛草的味道。一瞬間,仿佛看到母親端坐在織布機前,一心一意地編織著自己的夢,把時光織成了一匹匹美麗的錦緞。
在中國,紡線織布有著千百年的歷史。人們稱手工織的棉布為土布,商店里賣的機器織的布為“洋布”,而土布是人們的生活必備品。母親十幾歲就會織布了,18歲嫁給我父親時,已經輕車熟路,出嫁的被子都是母親用織的布來縫的。陪嫁的布越多,就意味著日子步步(布布)高。外祖母給母親的嫁妝,就是一輛紡車和木質織布機,目的是讓她在婆家勤快能干。
記得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母親白天要到針織廠上班,晚上則和我共用一盞昏黃的油燈,盤腿坐在紡車前,右手搖動紡車,左手有起有落地繞著紡的線,催動紡車“吱吱呀呀”地唱響一曲寂寞的夜歌。把紗紡成錠后,白白的一團,被堆在竹籃里,像一個個大鵝蛋。我看書寫字疲勞后,就趴在熱乎乎的被窩里,睡眼蒙嚨地看著母親忙碌著,額頭上細微的汗珠,在燈影里忽隱忽現地閃爍。我睡過一覺了,睜開眼睛一看,發現母親還在那里“嗡嗡嗡”地紡著。
經過紡線、染線、漿線后,母親就會坐在織布機上。織布機是用老槐木做的,結實耐用。母親織布的技術十分熟練,手里一邊穿梭子,腳下一邊踏織機,“咔——咔——咔——”織了起來。一點一滴的美好時光,都填進了這“唧唧復唧唧”的音樂中。有時凝望母親優雅的動作,我覺得母親不是在織布,而是在編織人生的藝術品。梭子在棉線里來回穿梭,引入緯線,機杼上下翻騰,這時,土布就像流水一般,從織機上涌流而出。織出來的布全都是白色的,心靈手巧的母親,有時會拿出舍不得花的錢,去供銷社買來各種染料,把布染成各種顏色。
母親忙完織布機上的活兒,用很會裁剪的手,去忙碌我們的衣裳了。在那個票證年代,穿衣服要靠發布票。母親發揮自己織布的一技之長,織出了全家人所穿衣服的布料,包括床上鋪的、蓋的。我時常穿著母親給我制作的家織布衣服,走在大街上,挺胸闊步,炫耀不已。我身上穿的都要比別的小伙伴們周正,就是一塊小小的補丁,母親也會用細密的針腳配著灰撲撲的土布頭,把它補成一朵花,或者一只小動物。穿了母親打過補丁的衣服,我總愛往人堆里鉆,聽著人們由衷的贊揚,感覺比穿了新衣還要自豪。土布還會用來做成被套,曾經作為最好的結婚禮物,送給我們兄弟姊妹。在我的孩子出生前,母親連夜趕制了土布做的小被子、小褥子。
對破得不能再穿的舊衣服、床單,母親會整理出來,裁成一片片,均勻地疊加起來,涂上面漿,一層層糊在木板上,用兩條長凳架住一塊門板,等晾干后揭下來,就成了做布鞋的原料。然后就用大針,一針針納成帶有圖案的鞋底,再把鞋底和鞋幫縫到一起。母親做成的鞋,穿著舒服,花型眾多,精致極了。到了上學的年齡,我便穿上嶄新的布鞋,風風光光地來到學校。同學們羨慕我穿的布鞋,特別是下課時圍著我的鞋子看,不斷發出嘖嘖的贊嘆聲。母愛同布鞋一起,托著我,穩健地走著歲月的每一步。
每逢晴天,母親總會搬出那只樟木箱,掏出一匹匹捆扎整齊的土布,挨個兒放在竹席上曬,并細心地扯平土布上的褶子。那藍底白花的老土布,在風中起舞,在暖陽的催促下,彌漫出藍靛特有的氣息。晾曬完畢,母親搬來一張小板凳坐在門前,手里做著針線活兒,偶爾抬起頭,瞇起眼,盯著土布好幾分鐘,然后心滿意足地繼續穿針引線。有一天,我和弟弟為一床在陽光下曬了一天的小被子,爭得不可開交,母親笑著說:“別爭,別爭,每個人都有。”于是,我們兄弟二人,都有了一床土布做的小被子。
現在,外祖母送給母親的紡車和織布機,完全成了一個爛木頭架子,上面的零部件全沒了,被閑置在閣樓上。前不久,母親一副依依不舍的表情,告訴我,已經把紡車和織布機一起賣了80元。
懷念土布,懷念它像母愛一樣貼身而又貼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