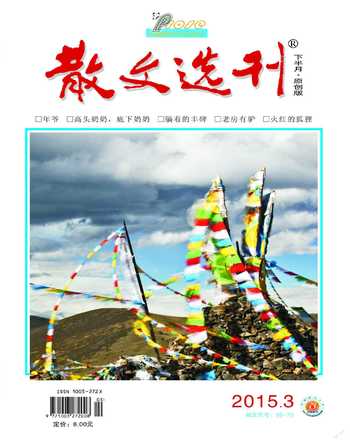老房有驢
王福利
已成街道的老宅上,那棵40年的老棗樹還在,樹身上那些啃疤一圈一圈的,重現著一頭小驢拴在院里閑得啃樹皮的畫面。
那些年,小驢的弱小讓我們家抬不起頭來——在那個人扛馬拉的非機械時代,每次趕著小驢下洼干活,總會成為路人打趣的對象:“大眼賊兒!”不管人們說什么,似乎也聽不懂人們說什么,它每天都是精神百倍地高昂著頭;現在再想起它的模樣氣質,雖然個頭矮小,但絕對是驢中的“美男子”,只是車上人那時還是孩子,只看到了它的缺點。
莊稼人常年與牲口打交道,也如人與人之間摸透了彼此的脾氣:偷奸耍滑的牲口,仿佛能比人看事看得更透徹——下地干活的路上,故意磨磨蹭蹭走得很慢,而且自己揀好道走,讓車轱轆在坑洼不平的路上顛簸;干活的時候,嘰嘰歪歪,就是不聽主人召喚,你把犁頭插得深了,怎么抽打它也不動彈,你剛把犁頭挨上地皮,它呼呼地一頓快行,反正就是剜著心眼地想著自己怎么省勁;只有在回家的路上,它才會顯示出生機活力,恨不得一步到家快些歇著。如果用這些反面牲口對比的話,小驢在所有方面,都超過了那些比它高壯很多的大牲口,盡管每次耠地耙地耩地都沒有大騾子、大馬干得快,盡管拉了沒有太多莊稼、坐車的人怕它拉不動都下來走,但每一次,快步急行的小驢都是渾身被汗水打濕,站在它旁邊就能感覺到汗水的熱氣,累得吃不下草料。看著它累成這個樣子,母親總會在槽里撒上厚厚一層玉米或高梁。
聰明的小驢也懂人的心思,只不過沒有用在偷奸耍滑上。每年“耠青”的時候,鄰居們又把它當成寶貝一樣搶,東家借,西家牽,對于人們口中的“大眼賊兒”來說,不亞于一年年的生死坎。天不亮,母親就提前給小驢加喂精料,沒等小驢吃飽,借牲口的人來了牽著就走,一直到后半晌,甚至黑天,才將渾身像洗了澡一樣邁不開步的小驢拽回來,不是累得沒有一絲力氣,要強的小驢何曾焉頭耷腦、走路拖沓!那一次送驢人來的時候,母親一眼就看到了它后腿上一尺多長的血道,走路也有些瘸了,可是牽驢人卻只是一句輕描淡寫,轉身就走了;心軟的母親,那次甚至疼得掉了淚。
應該就是在體力透支的那幾年里,本沒多大氣力的小驢,短短幾年變成了老驢,雖然還是小驢的體型,但也如人一樣在頭頂、唇邊有了斑斑點點的灰白。
小驢對于母親,用父親的話說,它就是母親的“腿”;它的腿傷了,母親能不掉淚嗎?就是在我已上初中的時候,有次騎自行車帶著母親去姥姥家,大冬天的正趕上頂風,十多里路歇了好幾次,母親看我累得大口喘氣的樣子,此后再沒有讓我用自行車帶過一次,又像以前一樣趕上了小驢車。那時已長大的我和姐姐,不會再像小時候那樣坐在她身后的車廂里,也聽不到她再跟我們念叨小驢是如何如何地認路通人性,不用人指揮,就一路小跑著跑到姥姥家,遇到對面來車,它還知道靠邊讓路。母親趕車的時候,不同于父親趕車時人們的調侃,而是變成了笑鬧里的夸贊:“喲!可真不賴,自己趕著車出門啊!”如果沒有小驢,不知母親要少回多少次姥姥家。
也是在人們半真半假的夸贊里,每逢過年、過節、趕廟會,母親趕著小驢車,拉著還是小孩子的我們,拉著房前屋后的嬸子大娘,踏著清脆的節奏,穿行在十里八村的土路上。雖然年紀小,卻也像母親一樣心疼著滿車人的分量給小驢帶來的負擔,卻也更深地印存著那份沉浸在無比興奮中的感受,至今那幅畫面還是如此清晰——河堤兩側的樹林里,被小驢的串串蹄聲時而驚起一只啄木鳥,從這棵樹飛跳到那棵樹;時而一群麻雀從林中飛起,在天空閃過一片烏云;我和小伙伴坐在顫顫悠悠的車里,用彈弓瞄準著前面的一樹喳喳嘈雜的灰白絨球,對笑談著家長里短、樂得嘎嘎的嬸子大娘們的鬧騰勁兒抱以厭煩表情。好不容易趕次大集,待嬸子大娘們湊齊在拴小驢的地方,已是下午一兩點鐘,小驢就那么老老實實地等在那里,一等就是多半天。
用母親的話說,小驢特別“仁義”,不只是別人家的婦女能夠放心大膽地趕著它下洼出門,就是一個小孩子,也能牽著它說走就走,不尥蹶,不咬人,不亂跑。每次母親趕著它回姥姥家的時候,剛剛十一二歲的小表哥都搶先從母親手里接過韁繩,非要騎著小驢滿洼里轉幾圈;每一次,小驢都是低眉順眼地聽從著表哥稚嫩尖嗓的吆喝,韁繩拉到哪里,它就咯嘚咯嘚地走到哪里,直到在光溜溜的驢背上磨得屁股生疼、兩條褲腿上沾滿了驢毛,小表哥才在大人們的哄笑里戀戀不舍地下來。臨走的時候,小表哥又搶過韁繩,幫著母親套上車,看著小驢在母親的一聲命令下歡快地踏上熟記于心的回家的路。
我后來出去上學上班,回家的次數越來越少,小驢留下的印象也越來越淡——姥姥姥爺去世后,母親已很少趕著它出門,更舍不得賣它,父親就買了一頭驢,同時養著兩頭驢,它終于可以歇一歇了。再到后來,不知什么原因,父親還是將它賣掉了。
父親說,買它的,是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兒,是為了趕集賣貨拉腳兒用。早已不是孩子的我,雖然失落,卻也心里好受了些——畢竟脫離了莊稼地里的重活,畢竟沒有因為它的老去無用而被賣到屠宰場。但愿它在那個老人的平靜余生里,安然度過一頭老驢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