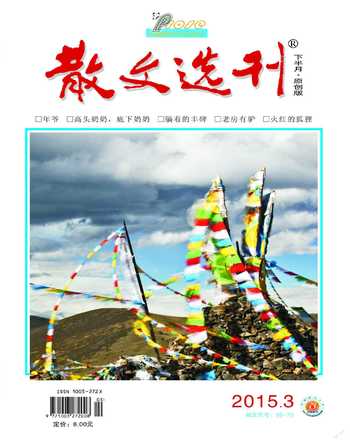南墻根
竇坤
老家在一條山溝里,整個村子南北長約二里多,東西不到一里;大多院落在靠東的山根,西邊山根也就十幾家,中間一條寬窄百米左右的沙河;自北向南分布著幾個泉眼,只有兩個大的泉眼蓄水修了澇壩。依據風水,靠東的院落主房也背靠東,大門向西;靠西的院落主房則背靠西,大門向東。地勢高的人家,出大門就能看見沙河對面人家院里的動靜。至于街巷,當然是南北為街,東西為巷。三個隊各有各的麥場,一隊、二隊的麥場基本在靠近沙河的院落中間,大小有足球場一般,三隊的麥場有兩個,都較小。三隊有公路東西向橫穿而過。老家冬天多西北風,即便有太陽,高原山地的風也凍人厲害。但有一處地兒可以享受陽關的溫暖,這就是南墻根。家家東西向南邊的院墻外,背風朝陽。在冬天里,哥三哥四抑或二姐五姐、張家老漢、李家奶奶的湊在一起,拉一些家長里短的閑話,甚至誰家最近有秘事也是從這個地方開始在村子里流傳。南墻根是整個村子里信息的集散之地,也是是非不一的流言發源地。
南墻根最理想的地方是麥場北面某家的南墻。一是眼界開闊,見誰路過,就近叫過來閑聊,不漏人;二是,帶了孩子來,孩子們正好在麥場滾鐵圈、跳房房、踢毽子,看得著、好照應;另外,孩子玩翻臉了打架也就近好拉架喝止,防止娃娃們手下無輕重,一個把一個防不著給打壞了就糟了。至于三隊,多是在公路北邊的人家南墻,正好閑聊,瞅著誰要出門了、誰從外邊回來了等等心上沒事卻要打聽的雜事兒。有時候也就是自家送人等班車來,大伙兒有事無事地抬會兒杠。那個時候人閑啊,冬天外出補貼生計的活兒也少,不是背煤,就是挖石膏去,而這活有危險,還是個苦力活。所以,大部分人閑散慣了,尤其一上五十歲,就以老自居了,樂于清貧地享受冬天無聊的閑適。每天早飯吃過,只要天氣好,就三三兩兩地聚在一起了。見面先問:“吃過了沒?”這一“國問”同樣在那個年代流行于我偏僻貧瘠的家鄉,這邊答道:“吃了,將兒吃了兩碗攪團。”這樣寒暄問候著靠墻而立,老一點的掏出煙袋鍋子,就著煤油火機抽上旱煙,滋兒滋兒地冒著嗆人的溫暖。年輕一些或是不講究的掏出報紙裁的紙條兒,順長折成一指寬窄,另掏出煙葉袋子,一溜兒倒上煙渣子,沾上唾沫,一頭包著細細的煙渣子攆緊了,一頭卷成細細的吸口,火柴“哧”地一下點著,一樣冒出青白的煙來,瞇上眼睛有一句沒一句地聊起張家長李家短的爛谷子事來。女人們則在不遠的另一處納著鞋底兒,高一句低一句地打探秘事、談論隱私。有時候常常是男人這邊聲高起來,原來是抬起杠來;而女人那邊早笑成了一團,一個天大的窗戶紙秘密又被揭發出來了。所以,女人們的笑聲不但放肆,還會夾雜放浪。男人們往往不屑地吐一口口水,繼續抬杠。男人們抬的杠不離乎誰的綽號怎么來的、哪個人的丑事是怎樣發生的、誰落了好事是什么原因、誰家倒霉是否是前世的報應等等。這邊說得活靈活現、如同親臨;那邊打斷了,說出又一個版本來。就為一個版本誰是真的可信的,經常爭得臉紅脖子粗,弄到高叫著對方的綽號,狠狠地損對方,目的只是迫使對方放棄個人的版本,承認自己的版本。這個時候,往往老成持重的人一句話就會敲定某一個版本的正宗,落了下風的人會說“不信了打聽啥”作為委婉的認輸,便不再爭論。女人們則擠眉弄眼地說一些大家都知道的秘密聊以解悶,誰也不會追究來源,只是添油加醋地議論,直到沒有心肺不負責任的言論發展成是非流言,又會在當事人面前指天發誓地辯解清白。最后是狗改不了吃屎,還是拿杜撰的流言蜚語繼續傳播損人不利己的這事那事。凡事總是離不開南墻根,尤其是沒來由的讓人興奮的大家都知道是杜撰的事,卻是說的人有天有理、唾沫飛濺、引經據實、滔滔不絕而無頭無尾、終歸流言的;聽的人卻也津津有味、故作萌態、假意奉承、順勢接話,成為流言自覺抑或不自覺的擴散者。事情有真有假、事件有小有大,大部分都借助南墻根這個小舞臺無意間生成、有意識地流傳。像風一樣,說來就來了,說走也就倏忽一下走了,連注意的心和操心的人都沒個準頭。
鄉里人的無聊時光和閑散生活,在每天南墻根的嘮叨和無聊里慢慢過去,孩子們也在南墻根的嘮叨和無聊里耳濡目染地慢慢長大。南墻根就像一個小型微縮的戲臺,演繹著老家那個時代貧瘠但幸福感滿滿的慢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