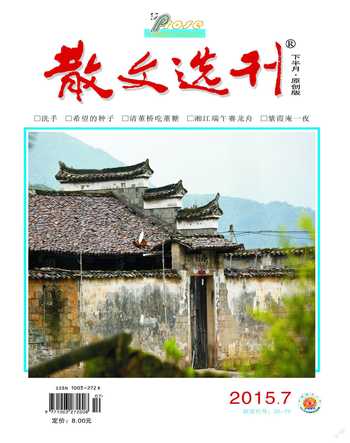嘆息,一種婚姻命運
楊志勇

吵了一輩子架,日子剛好過,咋就一起死了呢?
接到三舅和舅娘一同去世的電話,我不知怎地突然在開頭冒出了這么一句嘆語。在悲涼凄楚的事場,我發現親友對他們夫婦感嘆最多的話,亦是如我所說。
他們走了,我陡然感受生命里似乎少了一對兄弟夫婦,又才意識到原來我們之間的關系是兄弟般的友誼。三舅年齡比我大7歲,人莽實,又好斗,小時候孩子眼中的武俠,因為經常有他護著,我不會被同伴們欺負,又讓我童年每去他們家在鄰里左右玩耍,硬氣也神氣。很多時候,他帶著我一同上山坡放牛砍柴,下河溝捉鱉弄蝎,從早到晚有不盡的玩頭,因而讓我每每見到他,總是能夠找到那么一些快樂。經年后,我們如果在一起,除了禮貌上他是我的長輩,如交流、喝酒等則任性隨意,沒有禮儀規矩。五六年前的春節,我和媳婦去拜節,喝酒諞得高興,他嘴巴不把門,當著兩輩婦女的面,把我小時候××腫得大拇指粗的事抖落了出來。我沒有阻擋住,他說得繪聲繪色,還似有成就感。那時,我大概四五歲,和伙伴們在野地里玩,被慫恿用一種叫“貓眼草”的汁液涂到了××上,當天什么事都沒有,次日早一覺醒來,發現兩腿間礙得走不成路,低頭一看××腫得多粗,且皮膚發亮。聽大人說了土方子,他帶領大孩子把院場的石板一塊一塊揭起來,在底下尋了蚯蚓,搗爛,然后攪和鍋煤煙泥,還有幾樣我記不得的東西,給我涂抹了大概個把星期,便好了。
我不見怪又喜歡他這一點,實誠而又娃娃頭兒般的興致和快樂。正是親情之外多了這種不一般的友誼,他多少次請求我幫助處理麻煩事,我從未拒絕或者厭煩。只是因為他在多年里的不長進,每每見了面,我沒少批評他。他們生活了二十五年,不知他們彼此的自我感受如何,留給親友的印象是,兩口子年年過年都要吵架打架。在大家的感受里,他們家的大小事幫忙管不過來,有填不滿的“窟窿”事小,往往連個人情和面子話都落不下。慢慢地對他們的家事,大家心里便有些淡然,但因為他們的“小”,遇事大家還是向著他們,幫襯著他們。我母親對他,那不是對待兄弟,而是對待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他上學時母親操心,成人后找媳婦母親操心,結婚日子不好過了母親操心,夫妻經常吵架母親操心。媳婦每到我家里,不用問就知道多半是兩口子又吵鬧或者打架了,母親一邊勸說,一邊跟著數落自己的兄弟,兩個人嘮叨一天半晌地,回去了便會管上一段時間。
最近有三四年時間,我沒有接到過三舅的電話,聽說兩口子到我們家里也是很久沒有去過了。去年底和母親聊起這些事,聽說新房子蓋起來之后,兩口子奔好日子的勁頭分外大,非常勤勞。男的去年在煤礦打工,除了一次感冒和有事耽誤了兩天外,全年都是滿工,年底帶回去的凈錢八萬多。年前這一回去就著急著到處給人還賬,又是高興地到處走親戚。女的在家里把莊稼地種得到邊到沿,連地里的小石頭蛋蛋兒都撿拾得干干凈凈。之前,我聽說過幾次,調侃說太陽從西邊出來了,這日子不旺福他們都不行。
他們的新房子蓋得遲,但是樣式、規模和外表裝飾,在村里堪稱數一數二。外面欠的借款還得剩下不多,他們便打算在今年粉刷裝飾室內,修建灶房,美化院場,準備的磚頭、水泥、沙石等材料堆了幾個小山包。只待這房子收拾整齊了,給兩個兒子好找媳婦。如果有女子看條件,他們現在的家景當是不錯。在親友看來,他們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僅是從一間祖業的舊房子里搬出來,有了自己驕傲的新房子,且夫婦的關系恩愛有加。舅娘也想今年在外面打工,幫著掙錢一起盡快把賬還清,讓日子早點輕松。三舅心疼,不讓媳婦在外受苦,堅決阻止外出打工,說有他一個人在外辛苦就行。
兩口子感情好了,還有點膩。聽著,我都覺得點不習慣。但我能感受到他們生活的幸福和踏實,雖然來得遲,但總歸還是來了,就像他們的成熟和婚姻的和諧,在將要成為爺爺和奶奶的年齡里,不再如孩子過家家般的經常游戲,而且真正成了孩子和鄰里的榜樣。
今年過春節,兩口子把年節張羅得喜慶,又在年節里唯一的一次沒有吵架,然而卻在正月初五就一起走了。剛剛都在夸他們,而他們的死又讓人覺得他們還沒有長大。三舅在煤礦打工多年,曉得常識,死前幾天還在與別人說要小心煤氣中毒,村里人家的墻頭上也張貼著政府的提示,媳婦在大家眼里精靈跟兔子一樣,豈會犯小兒科的錯誤。可是他們一起偏偏在自己親手燃燒的焦炭里煤氣中毒亡命。謎就在這里,為什么?為什么是這樣?
看他們的遺像,一個像是有來頭的國家青年干部,不是愣頭的老實人;一個是漂亮精干的女人,看不出是生活受苦的農婦。照片是他們死前不久在城里隨意照的,沒有被美化。我想起,三舅的小名叫西娃子。母親說,娘生出來他就長相好,因人都稱長得稀而叫了稀娃這個名兒,戶口把“稀”寫成了“西”。三舅早年出了名的懶,母親曾教訓我,不勤快,就和你三舅一樣,將來連媳婦都找不到。而他在二十三四歲時,不但找到了媳婦,還找到了讓村里同齡人羨慕的好媳婦。舅娘身材高挑,五官秀麗,伶牙俐齒,待人處事大方,干活利落,且又做得一手好茶飯,出身可謂當地名門,其父曾任公社黨委書記、國家干部,對于三舅來說那是攀上了貴親、高枝。因此,他們日子過得爛包的時候,夫婦不管誰的對錯,親友批評的都是我三舅。三舅受話,不爭不辯,任何時候都是一副油抹布樣子,聽完了,就嘿嘿一笑。
兩班喪鼓打得咚咚響,一班在新房的東頭房間,一班在新房的西頭房間,中間隔著一間樓梯房,孝歌聲和鑼鼓聲此起彼伏。我聽得錐心,又無淚可流。他們的一輩子都不長,一個剛過四十八歲,一個才四十五歲。留下了一座兩家聯體的四間三層新房,還有兩個光葫蘆,一個24歲,一個20歲。都說,他們活著多好,好光景還在后頭哩。
他們一起走了,不用再麻煩我、打擾我,而我也沒有機會再向他們逞自己的能行,心里空落落地,只好一聲嘆息。
末了,他們的婚姻生活和命運歸宿卻擱在了我的心里,經常使我不自然地就琢磨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