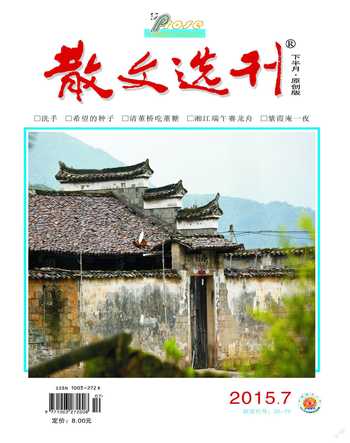請董橋吃董糖
葛坤宏

第一次吃到董糖的時候,剛隨父母從北方遷回如皋不久,塞慣面食的嘴巴初逢細膩精致的甜點,滿口清雅,覺得董小宛真像個蘭心惠秀的姐姐,從青瓦白墻的深深小院衣帶飄飄、款款走來。三十八年前的事了,還是個懵懂孩童,太小,看不透翻覆的歷史,更不懂委曲求全也是愛情。但董糖潤酥、暗香幽送,從此難忘。
那時的小城,城周以水,形近于園,四方設門,可惜抗戰時都給毀掉了,不過如皋人還是改不了老習慣,初次見面總會搭訕:“你丫旮(家)住哪個門?”這小城最可稱道的是外城之中還有內城,而且內外幾乎同形,從外到內的兩道環河,楊柳夾岸,石橋跨水,分外宜人。《惟有園林》里陳從周把小城如皋的造型喚作“雙環城”,以為“國內罕見”。1980年他初次游覽如皋,歲值深秋,雖然水邊人家,梅英橫斜,照影清淺,另有風姿,但到底沒有見到他嘆為“海內孤例”的水繪園的“水繪春色”,多少有些遺憾。的確,水繪園是小城的象征,也是如皋人的鐘愛。初春時分,煙雨空蒙,翠柳含煙,最宜信步,進門就能遇上冒辟疆的慈眉善目和幾縷胡須,小宛面容嬌柔,身形纖細,只是都古色古香、發暈發黃,就像平常如皋人家,堂屋里呈供的祖先圖像。一想起四百年前他倆在此演繹了顛沛流離卻又樸素真切的愛情,這小城和小園似有暗香。
一個溫婉的女子,攜了一份傾世的愛情,并蒂綻放而成一座古城的靈魂。每每想到上蒼把小宛賜給如皋,我的內心總是千百般柔腸掛肚,十分地感恩。小宛貌美若仙、靈秀賢惠,又嫁予東皋才俊,自然成為如皋人傾城、傾心鐘愛的女人。這段故事真是天生的情愛啟蒙教科書,古城男人打小沐雨熏風,個個憧憬才子佳人夢,誰不希望能遇到像小宛那樣的紅顏知己?
我那時也迷董小宛,讀遍她的故事,看遍她的字畫和詩歌。知道她名喚董白,字青蓮,是林黛玉的原型,曹雪芹比我還迷,甚至《紅樓夢》里也悄悄暗用她和辟疆的詩。這個溫婉的蘇州小女子,出生蘇繡世家,天生麗質,聰穎靈慧。詩詞書畫,刺繡昆曲,樣樣精絕。為償還家債,她被迫流落秦淮河畔,一笑傾城,二八豆蔻年華,名動金陵,競贏得“東南第一美女”之稱,這才是“漫贏得、青樓薄幸名”呀!我常常深恨自己生不逢時,沒有在昏黃的明末與她萍水相逢,看她刺繡、聽她撫琴。讀她的詩,想象她就是一枚顛沛青史、輾轉紅塵的嫻靜的蓮,歲月的流觴里,結緣與辟疆,從此在水繪園綻放。如何不叫天下人傾心呢?想想做藝妓,她是名動秦淮河畔的“金陵八艷”;為人妾,她位列凡間史冊“十大名廚”,當真“上得廳堂、下得廚房”,簡直斷了所有女人的退路,幸虧不和她一個時代。
小時候貪吃,小宛傳下來的諸多美食里最喜歡虎皮肉和董糖。后來,我以為天下兩道最著名的紅燒豬肉,莫過于東坡肉和虎皮肉,一個出白蘇東坡,一個出自董小宛,佳肴里不是詩詞,就是美女,都是傾慕的人呀!揚州人也愛董糖,傳說是小宛慰勞史可法將軍以及明朝將士的糕點,給明末清初慘烈的“揚州十日”屠城的血腥里,傳去了一縷酥香。無論是揚州城墻頭慰勞抗清將士的酥糖,還是水明樓上冒辟疆招待復明志士的糕點,董糖都可謂“天下第一點心”了。你若不信,可以就了碧螺春,淺試董糖,看看是否不膩不黏,潤酥怡人。
沒吃過董糖的人,看不懂紅塵里的擦肩和回眸,寫不出旖旎的董小宛。現代知識女性,少了史書里那些絕代佳人的柔婉和溫存,覺得愛情就是以“第一人稱”的姿勢為自己活著。這些覺醒的女人好像情感的盜墓人,大多看不得歷史的灰塵和滄桑,喜歡抹平時間、空間和人物的立體構造,單從感情的平面,審視前輩女人的愛情。其實,越是真摯的愛情才越是平凡生活的瑣碎流淌,個中沒有冷靜的思辨和理性的火光。明末清初國破家亡之際,如小宛這樣的江南才女,也只有辟疆這樣男人,才是她們認定可以托付一生的。再說辟疆年長小宛十三歲,救其于水火,使其從良妓到賢妾,在平凡的愛中,小宛表現了那份深深的依戀,再自然不過。更何況明代禮法森嚴,小妾的身份,本來比之侍人和丫鬟好去不多。小宛婚后,愛之苦,非一日;愛之娛,非一時。鞋腳和否,冒董自知,外人如何看透?
一個秋雨蒙蒙的夜里,就著清白的臺燈,我隨手翻看《影梅庵憶語》,看到暈暈的明鏡里,那個白發叢生的男人喃喃自語,遙念亡妻,真是“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一下讀懂了冒董的平白愛情,不烈焰,不肉麻,很平白,很樸素。
印象里的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逢了新年,如皋人還是遵循舊例,個個穿了新衣,扶老挈幼地趕著去水繪園游玩,隊伍浩蕩,有點像北方的趕集。每至佳節,親朋好友間一定會互贈董糖,朝拜和祭奠這段愛情傳奇。這對神仙佳侶就像是隔壁巷子里的鄰居,一直活在小城的杏花煙雨里,從未遠離。少年時代,我和同學穿過冒家巷去如師附小上學,總覺得冒辟疆就在黑色大宅門后、青瓦白墻的小院中踱來踱去,吟詩作詞。從柳絲輕舞的冒家橋遠眺,似乎看到董小宛就在水繪閣樓的軒窗邊,或梳妝打扮或扶針弄線。一旁站的是辟疆,癡癡地看。幾聲脆鳴是黃鸝,小宛詩中說它們“柳外時時弄好音”,只是不知道水繪園中那棵幾百年的老黃楊,是否依舊根深茂密、枝丫橫斜?
還是老男人懂得舊式女子。很多年以前董橋在東京,錯過了一幅扇頁,杏花半工半寫,意態娟麗,綠影微蒙,署名董白,好比四百年前秦淮河畔的擦肩,引以為深深遺憾。他的好友羅門更不幸,在巴黎畫店見到小小一幅董白畫像,殘破極了也娟秀極了,遲疑一宿怕假不敢買,結果被父親罵得狗血噴頭,訓了三個月!都是姓董的緣故,董橋很用心地寫冒董的傳奇愛情《如畫如史》,說“明末秦淮歌妓不同于一般青樓的庸粉俗黛,歌聲淚影里的凄艷故事譜完再譜,流傳千古”。他平生游歷,不是臺北,就是海外,一定沒到過如皋,一定沒吃過董糖,否則不會遺憾。
董橋不知道董小宛對于如皋人的意義,沖這一點,有機會一定請他吃董糖,請他嘗嘗那份浸潤了紅塵的暈黃的愛情酥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