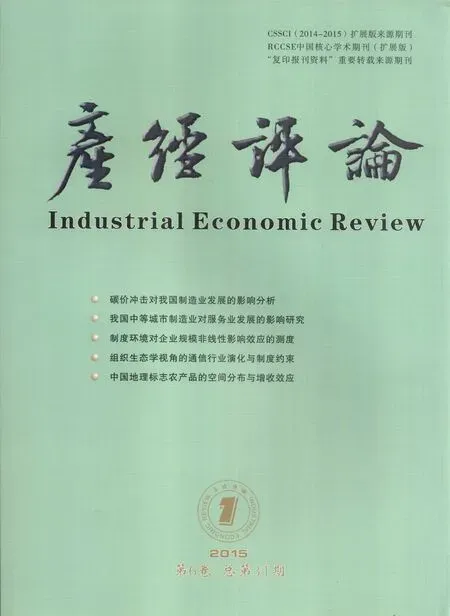最低工資標準的就業效應研究
——基于30個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
劉苓玲 黃 鋼
?
最低工資標準的就業效應研究
——基于30個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
劉苓玲 黃 鋼
通過構建一個由最低工資標準等因素共同決定的勞動力就業函數,從理論層面分析最低工資標準提升等因素對城鎮勞動力就業的影響。同時基于中國2004-2011年的省際面板數據,引入技術進步、城鎮化、老年撫養比等指標,運用面板分位數回歸方法進行實證分析。綜合比較來看:現階段最低工資標準提升與城鎮勞動力就業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而技術進步對城鎮勞動力就業的影響不能一概而論,具有不確定性。其他控制變量如城鎮化發展有利于提高城鎮勞動力就業,而老年撫養比、對外開放度的提高卻與城鎮勞動力就業呈負相關關系。其對策含義為:要充分考慮相關因素對勞動力就業的沖擊,理清不同地區、不同企業類型以及不同性別可能存在的有差異的勞動力就業效應,主張通過就業政策和勞動力市場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實現勞動力更加充分的就業。
最低工資標準; 勞動力就業; 分位數回歸; 面板數據
一 引 言
近20年來,隨著中國市場經濟制度的逐步完善,中國的最低工資制度在全國范圍內得到普遍落實和執行*1993年11月原勞動部制定了《企業最低工資規定》,1994年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的頒布最終以國家法律的形式明確確立了中國的最低工資保障制度,2004年3月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實施《最低工資規定》,2004年11月西藏頒布本自治區的最低工資標準,自此最低工資標準在全國范圍內確立。。近年來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呈現出勞動生產效率提高與勞動者工資補償性上漲相協調的跡象。但是伴隨著中國產業結構的升級(由依靠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依靠高附加值的技術密集型產業演進)、人口結構的轉變(人口老齡化加劇)以及城鎮化的快速推進,現實經濟中的最低工資標準提升會否是影響城鎮勞動力就業的重要因素?如果是,其影響方向和影響程度如何?這些問題匯集成本文的研究動機及研究重點。根據2011年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SS)的資料顯示:在所涉及到的內容中,城鄉居民對就業與失業問題的關注程度較高,且近幾年其關注度一直位居前列。與此同時,無論是國際社會還是國內政府也對就業問題給予了極大關注,如2011年的二十國集團(G20)戛納峰會通過了《增長與就業行動計劃》,2013年二十國集團(G20)圣彼得堡峰會的主題是“世界經濟增長和創造高質量工作崗位”,2012年十八大提出“要推動實現更高質量的就業”的目標要求,2013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又明確提出“把就業作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頭等大事,堅持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這些都表明了研究勞動力就業問題的重要性。

圖1 2011年城鄉居民的社會態度比較(單位:%)
資料來源:根據《2011年中國民生問題及城市化問題調查》的數據整理得到。
本文利用中國宏觀經濟數據對最低工資標準提升的城鎮勞動力就業效應進行分析。具體而言,主要從兩個層面展開研究:一是現階段最低工資標準提升與城鎮勞動力就業存在何種關系?二是考慮到地區間(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部門間(國有單位和私營企業)和性別間的差異,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對勞動力就業的影響是否也存在顯著差異?文章以下內容安排為:第二部分是文獻綜述;第三部分是模型的構建與數據說明;第四部分是模型的回歸分析及解釋;第五部分是穩健性檢驗;最后是結論與對策建議。
二 文獻綜述
近年來諸多學者從最低工資標準的視角對勞動力就業效應進行了考察。尤其是國外,由于相對完善的勞動力市場以及較早地推行了最低工資制度,使得其在最低工資就業效應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長足進展。Card和Krueger(1993)[1]以美國新澤西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的410家快餐店作為樣本(或參照),運用倍差分法(DID)對快餐店在最低工資調整之前和之后對就業的影響進行評估,發現最低工資標準的增加沒有對就業造成負效應。Leigh(2003)[2]針對1994-2001年澳大利亞6次提升最低工資標準的數據,運用自然實驗方法對其西部地區最低工資的就業效應進行比較研究,發現最低工資提升對勞動力就業具有擠出效應。Stewart(2004)[3]以英國1999年所設定的最低工資標準為參照,運用倍差分法(DID)評估其后兩年最低工資標準的上調對低工資工人就業所造成的影響,結果顯示最低工資標準的提升并沒有對勞動力就業造成顯著不利的影響。Marcus和Andreas(2010)[4]結合博弈論中的討價還價模型,分析了納什議價解和卡萊—斯莫羅廷斯基議價解,認為只有當行政性質的最低工資標準水平高于部分工人的市場平均工資水平時,最低工資標準才變得有實質意義,即只有較高的最低工資標準才會對勞動力就業產生影響,否則最低工資標準僅具有形式上的意義。Neumark和Wascher(1999)[5]考察了16個OECD國家最低工資(集體協商的制度性工資)對青年勞動力就業的影響,結果表明經過集體協商后確定的最低工資對年輕人就業有較大的負面影響。由于存在沒有加入工會的勞動者(工資不受保護),因此在現實中比最低工資更低的實際工資(subminimum wage)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緩解最低工資給年輕人就業帶來的負面影響。Bredemeier和Juessen(2012)[6]通過建立區分性別和婚姻狀況的勞動力供給結構模型,發現德國女性較男性擁有更高的勞動供給彈性和兼職率,同時最低工資能夠對已婚婦女帶來一個較強的和積極明確的勞動供給反應,而單身女性對此反應卻比較弱。Giuliano(2013)[7]借助微觀數據以美國一大型零售公司為例,發現平均工資的強制性提高對成年人的就業有負面影響,而對青少年就業有積極影響,特別是青少年相對工資的提高將導致更年輕、更富裕的青少年相對就業顯著增加。
近年來最低工資制度的就業效應也日益得到國內學者的關注,如韓兆洲和安寧寧(2007)[8]對深圳市的最低工資標準與就業相關性進行檢驗,認為最低工資標準的適當提高與勞動力失業并無顯著相關性,反而有助于促進勞動就業供給。賈朋和張世偉(2012)[9]以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CGSS)為樣本,指出最低工資水平的提升對低技能男性以及青年女性的收入上升有利,但也使得部分低技能中年女性失業。馬雙等(2012)[10]對最低工資上漲、企業平均工資和企業雇傭人數的關系進行檢驗,結果發現:最低工資上漲能夠從整體上提高員工的工資水平,但同時也會減少勞動力就業。其中最低工資每增加10%,企業平均工資將增加0.3%-0.6%,而企業雇傭人數將顯著減少0.6%左右。羅燕和韓冰(2013)[11]基于2004-2011年廣東省21個城市的面板數據,實證檢驗最低工資標準的就業效應,證實廣東省最低工資標準每上升10%,就業量會顯著增加1.86個百分點。孫中偉和舒玢玢(2011)[12]結合珠三角農民工的就業狀況與最低工資標準數據進行研究,發現最低工資標準對農民工工資增長具有顯著作用,同時農民工得通過大量的加班以補償最低工資所帶來的增長效應。戴小勇和成力為(2014)[13]研究了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對中國工業企業就業的影響,發現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對中國工業企業就業總量無明顯影響,但最低工資標準提升的結構性就業效應顯著,即最低工資標準提升顯著減少了平均工資水平較低企業的雇員數量,且對勞動密集型與中、低技術產業的就業產生不利沖擊。張璐和徐雷(2014)[14]指出,總體而言中國現階段最低工資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促進城鎮勞動力就業,但地區間也存在顯著差異,即東部地區最低工資提升與勞動力就業成正相關關系,中西部地區則相反。
從上述文獻可以看出,國內外學者均對最低工資標準與勞動力就業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研究。從數據來源來看,既包括傳統的宏觀經濟統計數據,也涵蓋了大樣本調研或搜集的微觀企業數據;而從研究對象的選擇來看,也將勞動者的性別、年齡、職業技能、地區、行業等特征指標囊括在內。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對相同的經濟現象進行研究也往往會得出相異的結論。從如上文獻綜述可見,目前中國最低工資標準的就業效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確定性。本文首先從理論層面探討最低工資標準等因素對勞動力就業的影響機制,然后結合2004-2011年的省際面板數據,實證檢驗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對中國城鎮勞動力就業的影響,以期通過數量化分析對中國最低工資標準的制定以及更好地促進勞動力就業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參考。
三 模型和數據
下面將采用2004-2011年中國30個省份(自治區、直轄市)的經驗數據,考察最低工資標準提升等因素對城鎮勞動力的就業效應。在此之前,我們將較為詳細地對計量模型加以分析,對所涉及到的變量和數據進行描述。
(一)計量模型

(1)
(2)
LnLit=φ1LnAit+φ2LnYit+φ3LnWit+φ4Lnrit
(3)

LnLit=α0+α1LnAit+α2LnMWit+γΠ+vi+εit
(4)
式(4)最終建立起一個由最低工資標準、技術進步等因素共同決定的勞動力就業函數式。其中變量νi表示不可觀測的地區效應,εit為隨機干擾項。在式(4)中LnL表示城鎮就業人員數量,LnA表示技術進步水平,LnMW表示勞動力最低工資標準*首先最低工資標準并非每年都進行調整,其中2008年與2009年各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未做調整,2010年與2011年海南、廣西、江西、四川、甘肅和黑龍江6省區的最低工資標準未做調整,但以2004年為基期,經過價格調整后數值均有變化。。由于α>0,β>0,所以φ1<0,即α1<0,表明:就業人員的數量(LnL)與技術進步(LnA)成負相關關系;而由于φ2>0和φ3<0,α2的符號將無法直接得出確定性答案,其系數符號取決于經濟發展水平(LnY)和工資水平(LnW)對最低工資標準(LnMW)影響的大小。同時為盡可能的避免回歸方程的遺漏變量偏誤問題,用符號Π表示對勞動力就業有影響的指標所組成的控制變量矩陣:
(1)對外開放度(Open)。對外開放程度的擴大促進了地區間勞動力流動、增加了勞動者就業機會,且加快了技術進步的傳播速度、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最低工資標準提升成為區域間的普遍現象。同樣對外開放也使得區域間競爭加劇,從而給勞動力市場帶來就業風險,對勞動力就業可能產生不利影響。本文用“所在地區進出口總額占其GDP的比重”來表示對外開放程度*官方統計資料提供的當期進出口貿易總額均以美元計價,我們參照當年平均匯率水平折算為人民幣,以實現計量單位的統一。。
(2)城鎮化率(Urban)。中國的城鎮化是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的最大期待,伴隨著城鎮化的發展,基礎設施得到改善,公共服務能力得到增強,而城鎮化過程中第二、三產業就業機會的增加將有助于促進城鎮勞動力就業。城鎮化在推動城鄉間、區域間勞動力流動的同時,有助于更好地優化人力資源配置。本文以“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表示城鎮化率。
(3)老年撫養比(Odr)。老年人口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勞動力的供給數量,提高了勞動力的稀缺性。受人口出生率長期下降等因素的影響,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從2012年開始出現絕對數量下降,根據人口發展規律,未來較長時期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還將繼續下降,這也意味著中國勞動力供給總量和就業需求規模將不斷減少。在此用“老年人口(65歲及以上)占勞動年齡人口數(15~64歲)的比重”來表示。
(二)數據說明


表1 相關指標的特征描述
四 計量方法選取與實證分析
(一)計量方法選取
本文采用分位數回歸方法,目的是區分在條件分布不同位置,最低工資標準提升、技術進步等因素究竟會對城鎮勞動力就業產生怎樣的影響。從理論上說,分位數回歸是一種基于被解釋變量y的條件分布來擬合自變量x的線性函數的回歸方法,是在均值回歸上的拓展。在考察最低工資標準提升、技術進步等因素對城鎮勞動力就業的作用時,運用分位數回歸方法,將使本文更好地發現在條件分布的不同位置上最低工資標準提升、技術進步等因素對勞動力就業的影響方向、大小及趨勢情況。
接下來本文將采用上述樣本數據實證分析最低工資標準提升等因素對城鎮勞動力的就業效應。考慮到地區間的經濟發展差異,在對回歸方程進行估計時,我們先進行整體回歸(見表2),同時考慮到地區間在對外開放程度、城鎮化水平和人口結構等方面的諸多差異,因而有必要通過分區域(見表3)、分企業類型(見表4)和分性別(見表5)進行比較研究,最后是穩健性檢驗(見表6),從而較為系統地完成了最低工資標準提升等因素對城鎮勞動力的就業效應檢驗。
(二)整體回歸分析
表2為面板數據在0.1、0.25、0.5、0.75和0.9分位點上分位數回歸的估計結果,同時展示了面板固定效應、隨機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為對固定效應、隨機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進行選擇,從Hausman檢驗結果來看,相比較而言,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更具有說服力。,從估計結果來看:最低工資(LnMW)的參數估計值顯著為正,最低工資(LnMW)每提高1%將帶動勞動力就業增加0.174%左右。綜合來看,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對城鎮勞動力就業具有正效應,其內在邏輯是最低工資增長在可能減少就業的同時,也會通過增加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從而促進就業增長。兩者相抵,很有可能實現就業的正增長*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綜合室副主任、研究員,王學力:“最低工資標準會引發失業負效應嗎?”解放日報:2007年12月24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GB/6689755.html。。從技術進步(LnA)來看,技術進步(LnA)對勞動力就業的影響不顯著。
從城鎮化(Urban)來看,城鎮化(Urban)對勞動力就業的影響十分顯著,且系數符號為正,這說明中國城鎮化的發展促進了城鎮勞動力就業。城鎮化的發展通過引導非農產業的發展,為勞動力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而老年撫養比(Odr)和對外開放度(Open)的系數均顯著為負,這從側面說明中國人口的日益老齡化,使得勞動力的供給數量減少,因此在一些地方出現了“用工荒”的困境,這將迫使企業通過提高用工成本以吸引勞動力就業,但長遠來看人口的老齡化將不利于勞動力就業(楊宜勇,2008)[19];從整體上講,貿易開放度的提高對就業有促進作用(許統生和涂遠芬,2009)[20],而文中對外開放度(Open)為什么與城鎮勞動力就業具有顯著負相關關系(盡管系數很小),通過數據觀察發現,近年來各地區的對外開放度(Open)普遍呈現出下降的趨勢(重慶、四川、黑龍江、江西和河南5省除外),因此也不難理解對外開放度的下降對勞動力就業具有負效應。我們進一步將對外開放度(Open)分解為出口依存度和進口依存度*其中出口依存度用“所在地區出口總額占其GDP的比重”來表示,進口依存度用“所在地區進口總額占其GDP的比重”來表示。,高文書(2009)[21]通過對中國1985-2008年29省市的數據分析得出,出口(進口)依存度每增長10%,就業增長0.35%(減少0.19%)。而中國出口依存度下降速度遠大于同期的進口依存度下降速度,所以更深入地說明了對外開放度(Open)下降對勞動力就業增長的抑制作用。

表2 整體回歸結果
注:***、**、*分別表示在1%、5%和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固定效應估計與隨機效應估計兩項的Hausman檢驗值為20.75(0.000)。表3、表4、表5、表6同。
(三)分區域回歸分析
整體回歸分析展示了各個變量較好的顯著性(技術進步除外),考慮到各變量的參數估計值均較小(對城鎮勞動力就業缺乏彈性),所以分區域回歸分析重點考察最低工資標準提升、技術進步等因素對城鎮勞動力就業是否存在差異性影響(見表3)。從估計結果的比較來看,地區間*一般意義上,東部地區指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11省市;中部地區指黑龍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省市;西部地區指四川、重慶、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廣西、內蒙古12省市、自治區。本文也使用這一劃分標準,因西藏部分年份數據缺失,故沒有包含在模型分析中。有著許多一致性的特征,但也存在著極為明顯的差異。
就最低工資(LnMW)而言,東部和中部地區最低工資(LnMW)的分位數估計值均為正,且具有較好的顯著性,而西部地區的最低工資(LnMW)的參數估計值顯著性相對較差一些,但是結合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最低工資(LnMW)的提升對各地區城鎮勞動力就業仍具有積極效應。其中按照最低工資(LnMW)標準提升的勞動力就業效應大小排序可以看出,最低工資(LnMW)水平每提高1%,將帶動東部地區城鎮勞動力就業增加0.307%,西部地區城鎮勞動力就業增加0.183%,中部地區城鎮勞動力就業增加0.106%。綜合來看,最低工資(LnMW)提升對增加城鎮勞動力就業依舊缺乏彈性。
就技術進步(LnA)而言,中部地區技術進步(LnA)的分位數估計值顯著為正,東部地區略差一些,而西部地區不顯著。結合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來看,中部地區技術進步(LnA)每提升1%,將促進其城鎮勞動力就業增加0.08%。東、中部地區的技術進步在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中,實施了有利于發揮勞動力比較優勢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戰略,促進其原有產業結構轉型,進而帶動城鎮勞動力就業。而地區間技術進步(LnA)指標估計參數出現較大差別可能的原因是:在計算技術進步時,采用的是全國各地區一致的生產函數,并沒有體現出地區間的差異性,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表3中對地區間技術進步(LnA)的參數估計值出現較大波動,因此技術進步(LnA)指標所顯示的較大差異性和較差顯著性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而從其他控制變量來看,各指標與表2中的整體回歸結果具有較高的一致性,說明估計結果較為穩健,因此上述所得結論是較為可靠的。

表3 分區域回歸結果
(續上表)

模型變量固定效應估計分位數q=0.1q=0.25q=0.5q=0.75q=0.9中部地區LnAit 0.077***0.109**0.094**0.071** 0.072***0.104*LnMWit0.106***0.095**0.103***0.104***0.102**0.097*Openit-0.008*-0.003***-0.004**-0.003***-0.005**0.012*Urbanit0.043***0.041***0.038***0.039**0.044***0.049***Odrit-0.011**-0.005***-0.006**-0.005***-0.013-0.015**常數項4.381***4.192***4.190***4.177***4.272***4.201***R20.7980.9480.9210.9060.9030.914西部地區LnAit0.361 0.032 0.195 0.319***0.495 0.406***LnMWit0.183**0.1790.1760.180***0.1850.184***Openit-0.004***-0.001***-0.005***-0.007***-0.004***-0.002***Urbanit0.014**0.024*0.012***0.014***0.013**0.014***Odrit-0.011***-0.007*-0.007***-0.006**-0.014-0.017***常數項4.935***6.065***6.012***5.790***5.784***5.905***R20.7760.9520.9210.9010.8870.892
(四)分部門回歸分析
2004-2011年,在城鎮就業人員中,國有單位與私營企業就業人員占其就業人員總數的比重一直維持在38%左右*城鎮就業人員中個體經濟就業人員占比從2004年的9.5%增加到2011年的14.6%,可見這3種單位類型的就業人員占據了城鎮就業人員總數的50%以上。個體經濟與私營經濟具有相似的發展特點,因此本文著重分析國有單位和私營企業,而對個體經濟不再贅述。,其中,國有單位的就業人數占城鎮就業人員總量從2004年的25.3%下降到2011年的18.7%,城鎮就業人員中私營企業就業人員占比從2004年的11.3%增加到2011年的19.3%。中國強勁的經濟增長一直伴隨著城市就業的快速增長(蔡昉,2007)[22],經濟成分的多元化和就業結構的巨大變化,使中國城鎮中單位外的從業人員數在增長,即中小企業、民營經濟以及非正規部門就業在增長,減少的只是城鎮的正規就業(蔡昉和王美艷,2004[23];蔡昉等,2004[24])。為考察最低工資標準提升等因素對城鎮國有單位和私營企業勞動力就業的影響,首先有必要就兩部門的勞動力就業數量(絕對數)及變化趨勢做一下分析(見圖2)。2004年以來,國有單位核密度的波峰略微呈現出右偏且上升的態勢(幅度不大),但就波及范圍來看變化不大,分散程度也基本保持一致,說明國有企業吸納的勞動力就業數量在整體上變化不大。并且國有單位勞動力就業數量分布主體為“單峰”分布,這也說明了地區間國有單位的勞動力就業數量沒有出現明顯的差異,就業數量處于相對穩定的態勢。而從2004年以來,私營企業核密度的波峰高度呈現出逐步右偏且下降的跡象,分布形狀呈現“扁平化”趨勢,波及范圍逐漸擴大,在整體上說明私營企業對勞動力就業數量的吸納能力不斷增長,并且地區間私營企業的勞動力就業數量也呈現出分化,地區間私營企業勞動力數量差距也日益擴大*從長遠看,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科學技術的進步,資本有機構成的逐步提高,企業必然要不斷進行產品、技術和組織結構調整,勞動力的相應調整與流動也會經常發生,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圖2 2004-2011年城鎮國有單位和私營企業勞動力就業數量的核密度估計

模型變量固定效應估計分位數q=0.1q=0.25q=0.5q=0.75q=0.9國有單位LnAit0.107** 0.120***0.099 0.051**0.070 0.081***LnMWit-0.0010.0060.003-0.0020.0040.021***Openit-0.00010.0002*-0.0001-0.0004**-0.0003-0.001***Urbanit0.0020.003***0.0020.0010.0010.004***Odrit-0.006**-0.001*-0.002-0.005***-0.011-0.015***常數項5.307***4.973***5.025***5.080***5.144***5.294***R20.6860.9730.9570.9430.9320.923私營企業LnAit0.155* 0.106 0.108 0.427***0.438 0.539***LnMWit0.404***0.516***0.523***0.421***0.395*0.294***Openit-0.004**-0.002**-0.002-0.003***-0.003-0.002***Urbanit0.023***0.016***0.015**0.021***0.0180.023***Odrit-0.003-0.008-0.010-0.015***-0.003-0.002常數項0.937***-0.285**-0.2930.026***0.4571.143***R20.6930.8470.8360.8360.8470.868
20世紀90年代以來所有制結構的私有化大大刺激了城鎮居民非正規就業的增長(胡鳳霞和姚先國,2011)[25]。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表明,非正規就業已占中國城鎮就業的58.85%(薛進軍和高文書,2012)[26]。而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數據(CHNS)顯示,從1997年至2006年,非正規就業人員占全部就業人員的比重從26.83%逐漸上升到42.46%(常進雄和王丹楓,2010)[27]。因此以私營(或個體)為主的非正規部門就業為城鎮勞動力就業做出了重要貢獻(蔡昉,2005)[28]。接下來將著重對影響城鎮就業人員中私營企業就業人員數量以及國有企業就業的相關因素進行分析。從表4可以看出,私營企業主要變量(LnA、LnMW)的符號(或顯著性水平)與表2中的結果基本保持一致,并且相應的變量系數也沒有發生較大的變化,從而說明相關的計量結果是較為穩健的。從其他變量來看,城鎮化(Urban)、老年撫養比(Odr)和對外開放度(Open)系數的顯著性均較表2有所差異。而總體來看,國有企業的相關計量結果顯著性較差,其原因是國有企業的勞動力就業人數相對穩定,使得各指標之間的相關關系無法充分表現。
(五)分性別回歸分析
根據2001-2012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的相關數據,觀察城鎮單位男性、女性就業人員占比的演變軌跡,從圖3中可以看出:山東、浙江和湖北等省市的男性、女性就業人員占比呈現出“喇叭形”趨勢,即男性占城鎮單位就業人員的比重不斷提高,而女性占城鎮單位就業人員的比重不斷下降。而男性、女性城鎮單位(正規部門)就業占比的變化趨勢,勢必與非正規部門就業占比呈現出相反的趨勢。譚琳和李軍鋒(2003)[29]證實中國的非正規就業存在明顯的性別特征,女性比男性更多地參與非正規就業,也更容易成為非正規就業者。劉玉成和童光榮(2012)[30]采用“城鎮單位中女性就業人數的占比”這一指標,得出了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對城鎮女性帶來了就業擠出效應的論斷。從圖3可以看出,城鎮單位女性就業人員占比是趨于下降的,這與近年來最低工資標準的上漲顯然是負相關關系。但由此得出“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對城鎮女性就業具有擠出效應”這一結論還有待商榷。為便于與表2進行對比,接下來我們將考察最低工資標準提升等因素對男性、女性就業是否存在差異性影響。




圖3 2000-2011年各地區城鎮單位女性、男性就業人員比例變動趨勢
從估計結果來看,城鎮單位男性、女性就業有許多一致性的特征,但也存在著極為明顯的差異。整體而言,最低工資標準提升等因素對城鎮單位男性和女性就業的影響是一致的,并且與全國的整體水平相一致。而從性別間的差異性來看,技術進步因素對城鎮單位女性就業較男性就業具有更好的顯著性,且系數更大;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因素對城鎮單位男性就業較女性就業具有更好的顯著性,且系數更大。但綜合來看,城鎮單位男性的回歸結果展示出更好的顯著性,其原因是城鎮男性勞動力在就業市場上占據更高的份額,因而其受宏觀經濟指標的影響更大,進而表現出更高的相關性。

表5 城鎮單位女性、男性回歸結果
(六)穩健性檢驗
由于本文是運用宏觀數據考察微觀勞動力市場上的就業變化,為了更好地克服內生性對于估計結果偏誤的影響和考察本文的結論是否穩健,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穩健性分析:
首先在方法穩健性檢驗方面,采用GMM方法建立動態模型是基于以下兩個考慮:第一,中國勞動力就業在經濟變革的環境中有極大的慣性,勞動力就業的滯后項會影響到當期勞動力就業的變化,運用GMM方法便于捕捉因變量的滯后項效應;第二,某些解釋變量(如最低工資標準、技術進步水平等因素)也受到城鎮化發展的影響,這樣就帶來解釋變量的部分內生性,而這些內生性問題可能使估計的結果發生偏差,進而造成統計推斷失誤。為克服可能的遺漏變量以及變量內生性對模型結果的影響,有必要對相關因素加以控制。表6結果顯示,基于城鎮勞動力就業滯后一期(L.LnLit)的系數均顯著為正,并通過1%(5%)的顯著性檢驗,這表明勞動力就業存在強慣性。由于本文的樣本量相對較少,動態面板GMM估計量較容易產生偏倚,而將模型的GMM估計量與OLS估計量、固定效應模型(FEM)估計量進行對比,比較因變量滯后項的GMM估計量是否介于滯后項的其他兩個估計量之間是判斷發生較大程度偏倚的一種方法(Bond,2002)[31]。在此以全國總體樣本為例,對動態面板模型進行OLS和固定效應模型估計,得到滯后項(L.LnLit)的OLS估計值為1.153,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值為0.960*受篇幅的限制,含有滯后項(L.LnLit)的OLS估計值、固定效應模型(FEM)估計值在此未加以展示。而之所以僅以全國樣本為例來比較城鎮勞動力就業滯后一期(L.LnLit)的系數,其原因是考慮到樣本數據的時期數和截面數,全國數據相對而言代表性更強,相應的結果也更為平穩。。而表6中滯后項(L.LnLit)的GMM估計值為1.017,該數值確實位于其他兩個估計值之間,表明本文的估計結果是穩健的。
其次在變量穩健性檢驗方面。一般而言對外開放度高的地區相應的城鎮化水平也較高,考慮到地區間對外開放度(Open)與城鎮化率(Urban)可能存在一個交叉的影響,因此我們引入市場化指數(Market)。這一指標是由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產品(要素)市場的發育等方面內容組成的觀測體系(樊綱等,2011)[32]。市場化指數(Market)能夠對對外開放度(Open)與城鎮化率(Urban)進行較好的替代*由于各地區市場化指數公布數據相對滯后,在此我們采用2002-2009年的數據加以代替。,同時用人口老齡化*其計算公式為“老年人口(65歲及以上)占總人口數的比重”。代替之前的老年撫養比(Odr)指標。從表6模型的回歸結果來看,各因素對勞動力就業的影響與基準整體回歸的結果在方向上基本一致。然后剔除技術進步因素(LnAit)。雖然我們對技術進步的數值進行了測算,但是由于樣本的時間較短,同時使用的α、β和δ的相關數值也不十分精確(熨平了地區間的差異性),考慮到技術進步對城鎮勞動力就業的影響顯著性不高,剔除掉這一變量后觀測模型5和6的回歸結果,發現各個變量仍具有較好的顯著性和穩定性。綜合來看動態面板估計下的變量顯著性與前文中的靜態面板估計結果差別不大,控制變量的系數符號也具有較高的一致性,且顯著性變化不大,僅是相關變量的系數數值出現了較大差異。其原因是GMM估計方法也有其局限性——適合具有較短時期(T)和較寬截面(N)的面板數據。但綜合來看,相關估計結果較為穩健。

表6 基于全國數據的穩健性檢驗
注:粗體表示采用指標“人口老齡化(Old)”的回歸結果。
通過上述兩方面的穩健性檢驗,可以判定文中結論是較為可靠的。而通過與前文的比較可以看出:理論模型分析與實證結果間存在著些許出入,其中最為明顯的差異表現在城鎮勞動力就業與最低工資標準方面。Neumark和Wascher(2006)[33]認為可能是由于跨越不同階層人群、受不同經濟環境和背景的制約,使得最低工資的就業效應有所不同,以至于一般經濟理論往往無法給出一個明確的預測。為進一步分析變量間的關系,我們引入了最低工資標準的二次項,以觀測最低工資標準提升與城鎮勞動力就業是否存在“∩”型或“∪”型關系,從圖4的擬合結果來看,最低工資標準提升與城鎮勞動力就業存在“∪”型關系,即現階段最低工資標準的提升有助于促進城鎮勞動力就業,或者是最低工資標準的提升有助于吸納非城鎮勞動力進入城鎮就業。很多研究和實踐表明“最低工資與失業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這一觀點在中國是荒謬的。因為最低工資制度更多的是一種保障制度,而非經濟杠桿,有利于提高就業質量,但基本不會導致就業數量減少(張麗賓、楊濤和常凱,2006)[34]。

圖4 2004-2011年各地區最低工資標準對勞動力就業的庫茲涅茨曲線檢驗
注:圖中其余三條直線的回歸分析(趨勢預測)類型是線性、指數和對數形式,由于較為密集且趨勢基本一致,因此未標記其擬合公式。
為什么現階段最低工資標準的提升與城鎮勞動力就業呈現正相關關系?接下來我們對最低工資標準(最高檔)占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比重這一指標進行考察。從圖5可以看出,中國各地區最低工資標準(最高檔)占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比重在經歷了一個大幅度下降之后,近年來才有所緩解,部分地區呈現出“L”型或“V”型的變化趨勢。總體來看最低工資占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比重僅為30%左右,遠未達到《促進就業規劃(2011-2015年)》預期的水平。因此筆者猜想:現階段相對較低的最低工資標準仍不具備對勞動力就業的擠出效應,城鎮化的發展以及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較快上漲有利于吸引勞動力就業,吸納農村勞動力進入到城鎮就業。這兩種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目前的最低工資標準提升與城鎮勞動力就業呈顯著正相關關系。相信今后隨著最低工資標準的提升,在其達到某一門檻值后,最低工資標準的就業擠出效應也將逐步體現,因此有必要對最低工資的就業效應進行持續觀測和評估。


圖5 1994-2012年最低工資標準(最高檔)占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比重(單位:%)
資源來源:1994-2003年數據根據王梅(2010)[35]一文中相關數據整理而成。重慶市1994年和1995年的數據缺失。
五 結論與對策含義
本文采用中國2004-2011年30個省(市、自治區)的數據較為全面地探討了最低工資標準提升等因素對城鎮勞動力就業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最低工資標準的提升與城鎮勞動力就業更多地表現為顯著正相關關系。從城鎮登記失業率的變動來看,2004年以來最低工資標準的歷次調整,可以說在提高低收入者工資水平的同時,未對就業造成明顯的負面影響*《漲薪呼聲高,勞動力價格上漲會影響就業嗎》,源自:人民網《人民日報》。2010年8月9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2378438.html。長期以來,中國最低工資標準一直偏低,且監管力度較弱,比如以東南沿海經濟發達的廣州市為例,2009年廣州的最低工資為860元/月,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國的最低工資標準并沒有起到應有的社會保障作用。因此有必要就中國最低工資標準的成效做進一步討論。眾所周知,若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資標準較市場提供的最低工資還要低,那么這一法定最低工資制度使得政府未對市場形成有效干預,而僅僅具有經濟層面的象征性意義。目前中國每個城市出臺的最低工資標準,幾乎都大大低于當地低收入者的工資收入。這一典型的“中國式”最低工資制度是由何種原因造成,需要結合中國二元經濟結構以及城鄉勞動力就業結構進行分析。由于中國最低工資制度的完善是伴隨著中國城鎮化的快速發展,而城鎮化發展的最顯著特征是農村相對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的大規模轉移。從這一視角來看,最低工資標準提升與城鎮勞動力就業之間的統計關系,實質上不是二者之間的相互因果效應,而是中國城鎮化發展的副作用。由于選擇的樣本期(2004-2011年)正好處于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上升時期*期間盡管經歷了金融危機,但中國政府采取了積極應對措施,使得勞動力就業壓力在經濟不景氣的時期也得以較好的緩解。,這使得我們的結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可以進一步對行業門類進行劃分,對建筑業、制造業等門類進行研究,相信會得到更具普遍意義的結論。從文獻資料整理來看,相關學者對相關行業的研究也基本都證實了目前中國最低工資標準提升的就業擠出效應是不顯著的。。但從最低工資標準提升的視角研究城鎮勞動力就業問題,有助于我們深化對此問題的認識,提出相應的對策和建議*2012年11月12日,人社部副部長楊志明表示將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解決就業問題:要推動經濟增長和擴大就業互促共進,鼓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大力發展中小企業。多年的實踐證明,中小企業是解決中國就業的主渠道。http://www.chinadaily. com.cn/chinesevideo/2012-11/13/content_15928127.htm。
首先,本文實證結果表明最低工資標準提升與城鎮勞動力就業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但這一結論的背后仍有許多政策層面的因素發揮作用,這是我們不能忽視的。比如近年來,國家在促進勞動力就業方面所作出的努力,通過制定《就業促進法》與《勞動合同法》借助法律法規加大對勞動者就業的保障,同時通過稅收減免、優惠等措施鼓勵企業積極生產,擴大用工,這些政策措施均促使在城鎮化進程中,最低工資的提升與勞動力就業呈現顯著正相關關系。
其次,中國的具體國情、特定的發展階段以及相關政策措施的激勵,尤其是伴隨著中國城鎮化的大力發展,傳統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正在向現代經濟結構轉換,使得現階段各因素對勞動力就業的影響有其自身的特點,從而造成不同地區、不同企業類型以及不同性別可能存在著有差異的勞動力就業效應,因此有必要理順各因素對就業的傳導機制,實現社會發展與促進就業的良性互動。
[1] David Card, Alan B. Krueger. 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A Case Study of the Fast Food Industry in New Jersey and Pennsylvania[J].NBERWorkingPaper, No.4509, 1993:1-57.
[2] Andrew Keith Leigh. Employment Effects of Minimum Wages:Evidence from a Quasi—Experiment[J].AustralianEconomicReview, 2003, 36(4):361-373.
[3] Mark B. Stewart. The Employment Effects of the National Minimum Wage[J].TheEconomicJournal, 2004, 114(494):110-116.
[4] Dittrich Marcus, Knabe Andreas. Wage and Employment Effects of Non-binding Minimum Wages[J].SchoolofBusiness&EconomicsDiscussionPaper, 2010: 3-22.
[5] David Neumark, William Wascher.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Minimum Wages on Youth Employment[J].NBERWorkingPaper, No.7299, 1999:1-50.
[6] Christian Bredemeier, Falko Juessen. Minimum Wages and Female Labor Supply in Germany[J].DiscussionPaper, No.6892, 2012:1-32.
[7] Laura Giuliano. Minimum Wage Effects on Employment, Substitution, and the Teenage Labor Supply: Evidence from Personnel Data[J].JournalofLaborEconomics, 2013, 31(1):155-194.
[8] 韓兆洲, 安寧寧. 最低工資、勞動力供給和失業——基于VAR模型的實證研究[J]. 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7, (1):38-45.
[9] 賈朋, 張世偉. 最低工資標準提升的就業效應——一個基于自然實驗的經驗研究[J]. 財經科學, 2012, (5):89-98.
[10] 馬雙, 張劼, 朱喜. 最低工資對中國就業和工資水平的影響[J]. 經濟研究, 2012, (5):132-146.
[11] 羅燕, 韓冰. 廣東省最低工資標準的就業效應研究——基于21個城市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 產經評論, 2013, 4(4):142-151.
[12] 孫中偉, 舒玢玢.最低工資標準與農民工工資——基于珠三角的實證研究[J]. 管理世界, 2011, (8):45-56.
[13] 戴小勇, 成力為.最低工資標準提升的結構性就業效應——來自我國工業企業的自然實驗[J]. 現代財經, 2014, (5):105-113.
[14] 張璐, 徐雷.最低工資水平對城鎮正規部門勞動力就業的效應分析[J].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學報, 2014, (1):70-76.
[15] 張軍. 資本形成、工業化與經濟增長:中國的轉軌特征[J]. 經濟研究, 2002, (6):3-13.
[16] 張軍, 吳桂英, 張吉鵬.中國省際物質資本存量估算:1952-2000[J]. 經濟研究, 2004, (10) :35-44.
[17] 王小魯, 樊綱. 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跨世紀的回顧與展望[M]. 經濟科學出版社.北京, 2000:217-235.
[18] 肖林興. 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估計與分解——DEA—Malmquist方法適用性研究及應用[J]. 貴州財經學院學報, 2013, (1):32-39.
[19] 楊宜勇.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就業政策與人口政策的完善[J]. 中國金融, 2008, (7):45-48.
[20] 許統生, 涂遠芬. 貿易開放度的就業貢獻率比較——基于1995-2006年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 當代財經, 2009, (5):87-92.
[21] 高文書. 中國對外貿易就業效應的系統廣義矩估計——基于省級動態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 云南財經大學學報, 2009, (6):25-31.
[22] 蔡昉. 中國勞動力市場發育與就業變化[J]. 經濟研究, 2007, (7):10-18.
[23] 蔡昉, 王美艷. 非正規就業與勞動力市場發育——解讀中國城鎮就業增長[J]. 經濟學動態, 2004, (2):26-30.
[24] 蔡昉, 都陽, 高文書. 就業彈性、自然失業和宏觀經濟政策——為什么經濟增長沒有帶來顯性就業?[J]. 經濟研究, 2004, (9):18-25,47.
[25] 胡鳳霞, 姚先國.城鎮居民非正規就業選擇與勞動力市場分割——一個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 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1, 41(2):191-199.
[26] 薛進軍, 高文書.中國城鎮非正規就業:規模特征和收入差距[J]. 經濟社會體制比較, 2012, (6):59-69.
[27] 常進雄, 王丹楓.我國城鎮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的工資差異[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 2010, (9);94-106.
[28] 蔡昉.非正規就業:發揮勞動力市場配置資源作用[J]. 前線, 2005, (5):17-19.
[29] 譚琳, 李軍鋒.我國非正規就業的性別特征分析[J]. 人口研究, 2003, (5):11-38.
[30] 劉玉成, 童光榮.最低工資標準上漲與城鎮正規部門女性就業擠出——基于中國城鎮單位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 經濟與管理研究, 2012, (12):66-76.
[31] Bond, S..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 A Guide to Micro Data Methods and Practice[J].PortugueseEconomicJournal, 2002, 1(2):141-162.
[32] 樊綱, 王小魯, 朱恒鵬. 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2011年報告[M]. 經濟科學出版社, 北京, 2011:400-425.
[33] David Neumark, William Wascher. 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A Review of Evidence from the New Minimum Wage Research[J].NBERWorkingPaperSeries, 2006, November:1-155.
[34] 張麗賓, 楊濤, 常凱. 設最低工資不會造成就業減少[N].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6-10-09(5)[2014-09-28].
[35] 王梅. 二元經濟結構下最低工資效應研究——對中國的實證分析[D]. 天津:南開大學, 2010:74-81.
[引用方式]劉苓玲,黃鋼.最低工資標準的就業效應研究——基于30個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產經評論,2015,6(1):143-160.
A Study on the Employment Effects of Minimum Wage Standards in China——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30 Cities
LIU Ling-ling HUANG Gang
Through constructing a labor employment function, containing of minimum wage and other factors, analysis of improving the minimum wage the impact on urban labor employment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Simultaneously introducti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urbanization, the elderly dependency ratio and other indicators, Based on 2004-2011 panel data, using panel 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 methods to empirical analysis. Compared comprehensively, At this stage minimum wage increase and urban labor employment has the remarkable positive correlation.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employment, we can’t get the conclusion in a word. From other study parameters, urbanization will help improve the urban labor employment, elderly dependency ratio and open-up are negatively related with urban labor employment. The policy implication is that,Fully take into account relevant factors on the impact of labor employment,clarify the different regions, different type of business, as well as gender differences that may exist between labor employment effects,Advocated the adoption of employment policies and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to further improve, realizing full employment of labor.
minimum wages; labor force; quantile regression; panel data
2014-09-28
西南政法大學研究生科研創新計劃項目“中國勞動力就業質量支撐體系研究”(項目編號:2012XZYJS114,主持人:張璐)。
劉苓玲,西南政法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研究方向:勞動經濟學與社會保障;黃鋼,西南政法大學經濟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勞動經濟學與社會保障。
F244
A
1674-8298(2015)01-0143 -18
[責任編輯:陳 林]
10.14007/j.cnki.cjpl.2015.0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