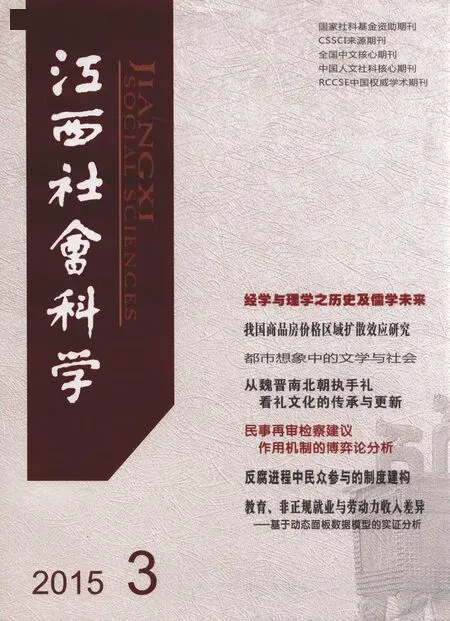廬山文化景觀與廬山文獻
杜玉玲
廬山文化景觀與廬山文獻
杜玉玲
世界文化景觀遺產誕生后,廬山成為中國第一個入選的遺產。在申遺專家與研究者的被動接受與主動面對過程中,廬山文化景觀逐漸被揭示,并與世界遺產標準產生某些契合。然而,目前對廬山文化景觀的認識還比較膚淺,尤其是未能充分利用廬山豐富而系統的歷史文獻資料,深入揭示其固有的“突出普遍價值”。因此,從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學術視野,對廬山文獻進行系統研究和深度解讀,對于發展廬山旅游文化、推進申報世界遺產工作和擴充世界文化景觀遺產的包容性,都具有認識論意義與實踐價值。
世界文化景觀遺產;廬山文化景觀;廬山文獻;社會文化史
杜玉玲,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生,江西師范大學圖書館館員。(江西南昌 330022)
兩次世界大戰后,在“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統一”理念的不斷追求下,世界文化景觀遺產誕生。廬山因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與秀麗的自然風光,以及依然不斷有機演進的多元文化元素,于1996年列入世界文化景觀遺產名錄。然而,很長時間以來,面對建立于歐美文化地理學基礎之上的文化景觀遺產理論,中國申遺專家和研究者都處在一知半解與被動接受狀態。受此影響,我們對廬山文化景觀遺產的認識還比較膚淺,未能深入揭示廬山所具有的“突出普遍價值”和“中國文化特色”。為此,我們必須充分利用廬山豐富而系統的歷史文獻資料,重新還原廬山文化建構的歷史過程,進而達到對廬山文化景觀作“整體的、本質的描述”。近年來文獻學研究領域的社會文化史轉向,為這一研究思路提供了必要的理論與方法。
一、廬山文化景觀從概念到觀念的接受
1992年,在世界遺產組織保護名單中,出現除自然遺產、文化遺產和自然與文化混合遺產之外的第四類遺產——世界文化景觀遺產。其遺產理念建基于新文化地理學的文化景觀概念之上,經歷從精英的、偉大的、靜止的向平民的、普通的、動態的發展過程,集中體現該學科概念的內涵與特點。[1]世界文化景觀遺產作為文化遺產的一個特殊類別,成為架構自然和人文的一座橋梁,展示人類社會與聚落在自然環境的物質性制約或機會下,以及在社會、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內在和外在持續作用下的演進,突出強調人和自然之間長期而深刻的相互作用關系。[2]在此視野下,先前困擾世界遺產組織和申遺國家間的自然與文化兩極對立的問題得以解決。
1996年,廬山入選世界文化景觀遺產名錄。然而,由于中西方文化景觀概念的差異,在申遺前后近二十年時間里,中國學界對文化景觀遺產的理解并不到位,經歷了一個從概念到觀念逐步轉型的過程。
1996年前后,為準備廬山申報世界遺產,一批申遺專家及研究者致力于對廬山文化的研究,從而成就廬山研究史的高峰期。據江西財經大學胡海勝教授統計,1980—2006年期間,總計796篇廬山研究文獻,其中文化景觀類占211篇,位居研究成果之首。[3](P68)這兩百多篇文獻主要研究的是廬山文化及其物質載體,如別墅、寺廟、書院、橋梁等。[3](P69)在作者看來,廬山文化景觀即是廬山文化與別墅等景觀的融合體。然而,真實的情況是,在胡海勝之前,“廬山文化景觀”一詞并沒有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大部分研究成果依然是以“廬山風景名勝”、“廬山文化遺產”、“廬山自然遺產”等為論題,所謂的“文化景觀”研究,只是胡海勝基于自身的認識而使用的概念。[3](P77)作者在文中所列的“廬山文化景觀一覽表”,就是直接承襲了鄭艷萍編制的“廬山文化遺產一覽表”。
2006年,鄭艷萍圍繞“廬山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利用”這一主題,從廬山文化發展史、廬山文化遺產分類評價及廬山文化遺產如何保護與利用三方面進行分述。作者根據國內外文化遺產的分類標準和體系[4],將廬山文化遺產分為2大主類、9個亞類、42個基本類型,共445個文化遺產資源單體,即文中所列“廬山文化遺產一覽表”。其中2大主類分別為有形物質文化遺產與無形物質文化遺產,9個亞類分屬在2大主類之下,有形物質文化遺產分屬遺址遺跡、建筑物、紀念性景觀、地方土特產品、文獻與遺物5個亞類,無形物質文化遺產分屬口頭表述、民間科技、社會習俗、人事記錄4個亞類,古人類生活遺址等42個基本類型又分屬在9個亞類之下,最后亭子墩新石器晚期村落遺址等445個文化遺產資源單體又分布在42個基本類型之下。[4]由此看來,作者對世界遺產實踐的理解,依然停留在20世紀70年代世界遺產組織成立初期的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分開保護理念。在此觀念下,文化遺產僅局限于單個或組團的建筑或構筑物,去除與之相關的整體的自然或人文環境;而其中所列無形物質文化遺產是從有形物質文化遺產中分離出來的,它人為地剝離各文化遺產單體的整體性;同時,各遺產單體雖然非常有序地被分到各類,但它們之間的時空關聯性卻被無形打破。因此,鄭艷萍所揭示的“廬山文化遺產”,只能是眼見的、單體的、凝固的、斷裂的物質實體。這一研究視角集中代表自1996年廬山申遺以來的研究現狀:對研究者來說,“廬山文化景觀”依然是一個陌生的概念,大部分研究成果依然停留在文化遺產與自然遺產截然分開的狀況。
2004年,以費勒教授為代表的國際社會質疑中國規避申報世界文化景觀遺產[2],引起中國申遺專家與研究者的重視,開始從理論與實踐上尋求與世界對接的途徑。在理論上,一批研究者開始梳理建基于地理學科理論之上的“文化景觀”一詞的定義、分類、標準、特征及文化景觀遺產保護的方法與途徑[5](P5-37)。自2005年以來,研究者開始陸續使用“廬山文化景觀”一詞進行研究。不過,從其研究內容可以發現,固有的觀念依然左右著研究者的思路與行文。如前引胡海勝的博士論文《廬山文化景觀變遷研究》,雖然接受了“廬山文化景觀”概念,但作者所揭示的“廬山文化景觀”,依然是眼見的、單體的、凝固的、斷裂的物質實體,與前述鄭艷萍所揭示的“廬山文化遺產”并無二致。[3](P148-151)至于景觀與景觀之間的聯系,現有景觀與已經消失的景觀之間的聯系,有形的物質景觀與禮儀、制度、山規等具有強烈社會象征意義的景觀之間的聯系,尚未進入他的研究視野。
2009年6月,五臺山成為中國第二個以混合遺產提名卻被世界遺產組織以“文化景觀”名類納入的世界遺產。中國的申遺專家與相關研究者開始認識到,“文化景觀遺產”不僅僅是一個必須接受的新概念,而且必須從觀念與理論上去理解與接受。2011年,四川師范大學盧娜的碩士學位論文《世界遺產視野下的廬山文化景觀解讀及旅游意義》,試圖通過梳理世界文化景觀遺產出臺的學科背景與理論基礎,探尋廬山被列為世界文化景觀遺產的真正原因,進一步揭示廬山有別于其他山岳文化而具有的“突出普遍價值”。作者明確指出:“人與自然相互融合”是中國傳統名山都具備的特性,而廬山相較于其他名山的顯著特點,在于文化景觀的相互演替及其關聯性,這才是廬山文化景觀遺產所具有的“突出普遍價值”。[6]基于這一認識,作者梳理了廬山文化景觀從秦至現代兩千多年的簡史,對廬山文化景觀之間在時空上的相互演替做了總結,編制了“廬山文化景觀演替表”。該表不同于前述鄭艷萍和胡海勝的“廬山文化遺產(景觀)一覽表”,旨在揭示動態的、演進的文化景觀。從東林寺、簡寂觀、白鹿洞書院、御碑亭、牯嶺直至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隨著歷史的發展、文化因子之間的競爭,廬山南北各景觀相繼以不同的情景呈現。[6]在盧娜看來,廬山文化景觀是一個動態過程,是人類活動相繼疊加的結果。在這個疊加過程中,什么文化都能看到,可每種文化又不是同時的,它反映了不同時代。這就使廬山有別于“封禪之地——泰山、佛教圣地——峨眉山、道教圣山——武當山”等歷史名山,因而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符合世界文化景觀遺產的入選要求。
然而,從時空的角度,我們看到的只能是廬山文化景觀從東林寺至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一個線性的、前后承繼的、動態演進的結果,但對于現有景觀與那些已經消失在廢墟中、目前卻只能從文獻中找回的景觀之間的聯系,以及有形的物質景觀與那些無形的、曾經存在過、目前也只能在文獻中見到的禮儀、制度、山規等具有強烈社會象征意義的景觀之間的聯系,我們依然無法揭示。而在實際上,正是這些無形遺產與有形遺產之間的內在歷史聯系,更多地體現世界文化景觀遺產的內核。
二、廬山文獻之于廬山文化景觀的意義
“文獻”一詞,最早出現于《論語·八佾》,原文如下: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孔子的這段話,學者一般用來說明“文獻”一詞如何從“典籍和賢人”演變為專指“典籍”的過程。而引起筆者興趣的,卻是“文獻”之于夏朝和殷朝已逝去的禮儀制度之間的關聯,前者可以用來證明后者的存在或是存在的全景。這樣一種引證關系,讓筆者聯系到廬山文獻與廬山文化景觀之間的關系。
如前所述,從445個文化遺產單體,到493個文化景觀資源單體,再到四百多個景觀單體之間的時空演替性,這些讓我們得以窺見廬山文化景觀豐富內涵的一角,但顯然不能代表廬山文化景觀的全部。我們應該明白,在四百多個文化景觀單體中,每一個景觀單體背后都可能蘊含著其生存時代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都可能和其他一個或幾個單體產生某種聯系,都可能有曾經與之相關、現在遺失在廢墟中的另外一個或幾個單體。那么,我們究竟應該如何揭示廬山文化景觀的時代意義?如何揭示景觀與景觀之間的關聯性?如何揭示現存景觀與那些遺失的景觀之間的聯系?在這方面,胡適的《廬山游記》給了筆者進一步的啟示。
1928年4月7-9日,胡適受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商王云五的邀請,在沈昆山、高夢旦、蔣竹莊等友人和英國傳教士甘約翰的陪同下,游覽了廬山的17處景點。胡適在此行中寫下《廬山游記》,因而永載廬山史冊。胡適指出:
廬山有三處史跡代表三大趨勢:(一)慧遠的東林,代表中國“佛教化”和佛教中國化的大趨勢;(二)白鹿洞,代表中國近世七百年的宋學大趨勢;(三)牯嶺,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國的大趨勢。[7](P26)
胡適的“三大趨勢論”,對廬山文化特征的概括極為精辟,在此后上廬山的文人、學者、游客及廬山當地人中傳唱不絕。那么,胡適的立論依據又是什么呢?通讀游記可以發現,胡適在整個游程中,查閱大量的廬山歷史文獻,如康熙七年(1668)吳煒編訂的《廬山志》、康熙五十七年(1719)毛德琦的《廬山新志》、嘉靖四十年(1561)桑喬的《廬山紀事》(以上山志分別簡稱《吳煒志》、《毛志》、《桑紀》)、民國十四年(1925)陳云章編著的《廬山指南》及梁朝慧皎的《高僧傳》、明代釋德清編纂的《廬山歸宗寺志》,等等。[7](P5-28)通過游覽古跡與閱讀山志,胡適總結出了“三大趨勢論”。
1928年時,東林寺、白鹿洞書院已然凋落不堪,牯嶺正處在它的繁盛時期,胡適的“三大趨勢論”建立于文獻閱讀、古跡游覽與現實感受基礎上,它讓我們明白昔日曾經輝煌的文化景觀是可以在《桑紀》、《毛志》、《廬山歸宗寺志》等文獻中找回。此后,在胡適游記等文獻基礎上創作的后續文獻,又見證了“牯嶺文化”的繁盛。文獻與文化景觀就是在這種互相建構過程中層層累積下來。這與兩千多年前孔夫子關于文獻之于禮儀制度的意義有不謀而合之處。《廬山游記》出版兩年后(1930),吳宗慈開始著手編纂另一部《廬山志》(以下簡稱《吳志》),在承襲《桑紀》、《吳煒志》、《毛志》的基礎上,特別開創了“山政”一綱,專門記錄“牯嶺”特區的形成,同時也收錄了胡適的這篇游記。我們現在看到的歷代廬山文獻,就是在這樣層層疊加的情況下傳承下來的。由此我們就回到前述的幾個問題。舉例來說,作為個體存在著的東林寺,若要解讀出蘊含其中的反映魏晉至唐宋時期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的整體意義,我們最可靠的依據是產生于那個時代的文獻,諸如《廬山遠公話》之類的民間話本、《復東林寺碑》之類的碑刻、《廬山記》之類的山志、《高僧傳》之類的佛教典籍及唐宋時期士人的廬山游記等等。從這些文獻中,我們可以把前述研究者列入不同類別的、孤立的文化景觀單體——諸如東林寺、西林寺、遠公塔、慧永塔、東林寺碑刻、三笑亭、遠公講經臺、虎溪橋、聰明泉、卓錫泉、虎跑泉、出木池、白蓮池、杏林、文殊金像、蓮花漏、虎溪三笑、佛教、慧遠、陶淵明、謝靈運、陸修靜等[3](P148-151)——建立起某種聯系。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進而探討那些曾經存在、如今消逝且只有在文獻中能見到的景觀及所有與東林寺相關的景觀背后蘊藏的社會象征意義。東林寺作為單體的文化景觀,它與其他景觀之間的關聯,與那些遺失了的景觀之間的關系,與它所生存時代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之間的意義,就是在這種文獻解讀的過程中得以揭示。依此類推,若要揭示東林寺與太平興國宮、白鹿洞書院等其他文化景觀之間的關聯性,我們同樣需要依據唐宋之前及此后產生的一系列廬山文獻。
福柯在《知識考古學》序言中,對“歷史遺跡與文獻”的關系作了深刻的分析,對我們頗有啟迪意義。他認為:
就傳統形式而言,歷史從事于“記錄”過去的重大遺跡,把它們轉變為文獻,并使這些印跡說話,而這些印跡本身常常是吐露不出任何東西的……在今天,歷史則將文獻轉變成重大的遺跡,并且在那些人們曾辨別前人遺留印跡的地方,在人們試圖辨認這些印跡曾經是什么樣的地方,歷史便展示出大量的素材以供人們區分、組合、尋找合理性、建立聯系,構成整體。……歷史只有重建某一歷史話語——對歷史重大遺跡作本質的描述——才具有意義。[8](P5-7)
廬山文獻是廬山歷史的素材,我們可以通過對文獻的區分、組合,尋找其合理性,建立其關聯性,從而對廬山文化景觀作出整體的、本質的描述,揭示其真正的“突出普遍價值”。
三、廬山文獻系統與社會文化史研究
廬山北枕長江,東、南面臨鄱陽湖,交通便利,風景秀麗,氣候宜人。自東晉以來,廬山吸引眾多的宗教信徒和文人墨客、諸侯帝王來往其中,創作大量的寺院道觀志、山志、府縣志、書院志、游記、摩崖石刻、旅游指南等文獻,形成極為龐雜的廬山文獻系統。這些歷史文獻建構并承載廬山豐富、多元的文化,為研究廬山文化景觀遺產提供豐富而系統的素材。
廬山圖書館前館長徐效鋼先生,曾經積二十年之力,編纂了《廬山典籍史》(以下簡稱《徐書》),揭示了歷代廬山文獻的大致面貌。該書是一部地方文獻史,共揭示《廬山記》《桑紀》《毛志》《吳志》等廬山地方史志三十二種,《太平興國宮采訪真君事實》《御制周顛仙人傳》《廬山秀峰寺志》《廬山歸宗寺志》等宗教典籍三十三種,《廬山遠公話》《陶淵明集》等文學著作八十種,《白鹿洞書院新志》《白鹿書院教規》等書院典籍二十三種,《廬山指南》《廬山導游》等旅游著作七種,《冰期之廬山》《廬山地志略》等科學研究著作八種。[9](P1-3)該書是目前所見最全面、最系統研究廬山地方文獻的著作,可以作為研究廬山歷史的最佳指南。
已有研究成果表明,文獻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編出來的,它是歷史的記錄,同時也是文化的建構。[10](P159)面對前述如此豐富的廬山文獻,歷史研究者不僅需要對各種文本做諸如版本、校勘、目錄、注釋、考證、辨偽、輯佚等傳統文獻學范疇的研究工作,而且應該思考如何對它們進行區分、重組、劃分層次、建立序列、從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煉出合理的因素、測定各種成分、確定各種單位、描述各種關系,通過還原文獻的歷史,重建廬山多元文化景觀形成的過程。基于這樣的認識,當我們面對每一種廬山文獻時,都必須思考如下問題:文獻是如何被創作的?是在怎樣的背景下創作的?包含什么內容?這些內容在后世又是如何流傳的?對后世有哪些影響?后人如何解讀這些文獻?后人的解讀如何反映時代的變遷?
傳統歷史文獻學旨在解讀文本的審音、識字及在此基礎上的一切考索校定的“文獻分析技術”難以全面解答上述問題。[11](P35-37)近幾十年來,致力于書籍史、文獻學研究的學者,逐漸突破版本、校勘、目錄、注釋、考證、辨偽、輯佚等領域的研究,越來越多地涉及社會和文化領域的問題,從而掀起一股向社會文化史轉向的學術潮流,研究成果非常豐富。[12]這種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取向,提醒研究者更多地從文獻的生產過程、流傳過程、使用過程去看蘊藏于文本背后更為宏觀的思想、社會、政治及文化走向。[13]這一研究取向提醒我們,解讀歷史文獻必須了解已逝作者特殊的精神結構——他們的思維、情感與價值觀,了解作者寄身于這一結構的時代背景與特征。即對文本的作者及文本所處時代的精神結構進行解釋,我們暫且給其定義為“精神分析技術”。[11](P35-37)
由此可見,在歷代廬山文獻研究中,不僅需要全部的“文獻分析技術”,更應該注意到每種文本獨特的精神結構——即借助于各種歷史的、文化的知識,盡研究者所能,考證每種文本的作者生平、所處時代及文本的資料來源等等,考察它們被創作的歷史語境,分析每種文本的內容特征。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考察后世對文獻內容的解讀和利用:文本的重抄、重印、重編,或是被收入其他文本,或是被轉化成宏亭廟宇,或被轉化成儀式規范。正是這些文本的創作、流傳與使用過程中所體現的思想、社會、正文論及文化走向,反映廬山文化景觀之間的整體性、連續性與融合性,體現它所具有的“突出普遍價值”。
在具體的廬山文獻研究中,同樣如此。如陳舜俞的《廬山記》,這是現存下來的最早的一部廬山志書。我們可以吸收已有的以“文獻分析技術”為基本研究方法的研究成果,考證它的作者、卷目與版本,也要借助于這些技術考索《廬山記》版本的種類、文字的差異、卷目的多少、版本的精良等等,但這還只是研究工作的起步。在進一步的研究工作中,我們還要考證陳舜俞的生平和知識結構、《廬山記》的資料來源和創作背景。這就需要借助于我們對宋史、佛教史、道教史、儒學史的宏觀認識,才能夠清晰地判斷出《廬山記》為什么會編成這個樣子?它為什么會花大量篇幅去記錄東林寺與慧遠?為什么熱衷于去講與慧遠有關的“神運殿”、“虎溪三笑”之類的傳說與故事?在明白這些問題后,我們就找出了《廬山記》的內容特征,也即是它的時代性。接著,我們要考察《廬山記》講述的慧遠傳說與故事在后世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它們是如何被解讀的?不同的解讀背后隱含著什么樣的時代特征、反映著不同文化元素之間的變化?要解答這些問題,需要我們對宋、元、明、清、民國等不同時期的大歷史背景與文化元素的變化有宏觀把握,才能明白為什么兩宋時期的士大夫與僧人熱衷于對慧遠傳說進行重述與擴充,明代為什么開始對其進行質疑,明末清初為什么開始進行全面解構。伴隨這種內容解讀的變化,由傳說轉化而來的各種建筑景觀由繁盛到備受冷落,再到全面敗落。通過如上三個研究步驟,我們不僅看到“慧遠的東林,代表中國‘佛教化’和佛教中國化的大趨勢”,而且看到廬山佛教文化與儒、道、國家意識、西方文化的相互競爭及變化過程。在這一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各種文化景觀,有的留存至今,有的歷經重建,有的僅存廢墟,有的已蕩然無存。對于這些歷史命運不同、生存狀態各異的文化景觀,我們只有通過對《廬山記》及其相關文獻的生產、流傳與使用過程的解讀,才有可能重新建立起它們之間的聯系。
如上所述,通過對歷代的廬山文獻的深度解讀和系統研究。我們有可能逐步揭示現存四百多個文化景觀單體之間的聯系、景觀背后蘊藏的社會象征意義以及現存景觀與那些遺失了的景觀之間的聯系。換言之,廬山文化景觀的相互演替及關聯性,可以在歷代廬山文獻的還原與研究過程中得以全面揭示。
四、結語
自從廬山被列入世界文化景觀遺產以來,學術界及相關部門就一直在醞釀著如何打造廬山這塊“世界文化遺產”招牌,江西旅游局一度提出“江西旅游打廬山牌,廬山旅游打文化牌”的口號。然而,究竟應該如何打造廬山“文化牌”?至今尚未形成明確的思路。或許是由于時代較近、文獻易得、文字易懂及文化易理解等因素,晚清民國以來外國傳教士在廬山開發的以牯嶺為中心的歷史及景觀,成為大部分研究者及國內外游客關注的主要對象,而廬山西北麓和東南麓的東林寺、太平興國宮、白鹿洞書院、秀峰等匯集自唐宋至明清以來文化積淀的諸多文化景觀,因時代的阻隔及文獻、文字與文化的隔膜,成為研究與旅游的“冷點”,往往被研究者與游客繞過和忽視掉。[6]我們現在看到的廬山“文化牌”,似乎始終是一張殘缺的、本末倒置的品牌。
“品牌定位不是去塑造新奇的東西,而是去操縱已存在心中的東西,去重新結合已存在的聯結關系。”[14](P26)原來沒有而無中生有,有一種言而無據的尷尬;原來有而無法言說,卻是另一種欲說不能的無奈。面對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廬山,研究者的當務之急是如何操縱那些延續千年的文化積淀,使之重新聯結起來,打造出完整而靚麗的廬山“文化牌”。在這方面,廬山文獻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學術資源和文化建構策略。
廬山與五臺山都是先申報世界自然與文化混合遺產,而后被列入世界文化景觀遺產。由于對文化景觀的概念和價值沒有清晰的認識,這些文化景觀遺產在申遺過程中未能進入國家的提名議程,因而進入預備名單。在對文化景觀理論、概念與價值梳理清晰之后,申遺專家及研究者發現,中國不但不乏此類遺產,而且非常豐富。甚至先前列入文化遺產或混合遺產之列的其他遺產,都可歸入此類。面對如此豐富的文化景觀遺產,擺在申遺專家與研究者面前現實而又具體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撰寫申遺文本?如何展示各文化景觀遺產的不同面向?通過對廬山歷史文獻與廬山文化景觀的深入探討,或可為今后的此類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鑒。
世界遺產組織的保護對象,從自然遺產、文化遺產到自然與文化混合遺產,再到文化景觀遺產的過程,有力地證明其保護理念與實踐是不斷發展、與時俱進的。1986年和1989年,英國湖區兩次申遺都遭受失敗,原因在于其擁有的難以分割的歷史文化淵源與自然鄉村風光,致使其在世界遺產組織中無類可從。[1]這一事件,直接催生世界文化景觀遺產的誕生。文化景觀是一個西方詞匯,它的理論基石是歐美的文化地理學。[2]自其誕生之日至2009年的近十七年的時間里,中國一直處于一種被動接受狀態。然而,文化景觀遺產所突出強調的“人和自然之間長期而深刻的相互作用關系”,卻與中國哲學和文化中對于人和自然關系的整體把握、對天人和諧關系的思考有不謀而合之處。由于“文化景觀”本身是一個不斷發展而難以界定的概念,對其定義、分類及標準的研究因地區或國家的差異而有不同。借助對廬山及五臺山等文化景觀遺產的全面研究,有助于促成我國申遺工作的觀念轉變。在對文化景觀遺產面向深度認識的基礎上,主動影響世界遺產保護,使其成為中西融合的遺產標準。這種不斷發展、與時俱進及包容性,也正是世界遺產組織自誕生至今的魅力所在。
[1]韓鋒.世界遺產文化景觀及其國際新動向[J].中國園林,2007,(11).
[2]韓鋒.文化景觀——填補自然和文化之間的空白[J].中國園林,2010,(9).
[3]胡海勝.文化景觀變遷理念與實證研究[M].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11.
[4]鄭艷萍.廬山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利用研究[D].桂林:廣西師范大學,2006.
[5]單霽翔.走進文化景觀遺產的世界[M].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2010.
[6]盧娜.世界遺產視野下的廬山文化景觀解讀及旅游意義[D].成都:四川師范大學,2011.
[7]胡適.廬山游記[M].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
[8](法)米歇爾·福柯.知識考古學[M].謝強,馬月,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
[9]徐效鋼.廬山典籍史[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1.
[10]鄭振滿.新史料與新史學——鄭振滿教授訪談[J].學術月刊,2012,(4).
[11]劉士林.先驗批判:20世紀中國學術批評導論[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
[12]洪慶明.從社會史到文化史:十八世紀法國書籍史與社會研究[J].歷史研究,2011,(1).
[13](美)梅爾清.印刷的世界:書籍、出版文化和中華帝國晚期的社會[J].史林,2008,(4).
[14]李蕾蕾.旅游地形象策劃:理論與實務[M].廣州:廣東旅游出版社,2004.
【責任編輯:彭民權】
G127
A
1004-518X(2015)03-0235-07
江西師范大學規劃項目(人文社科)“世界文化景觀遺產視野下的廬山文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