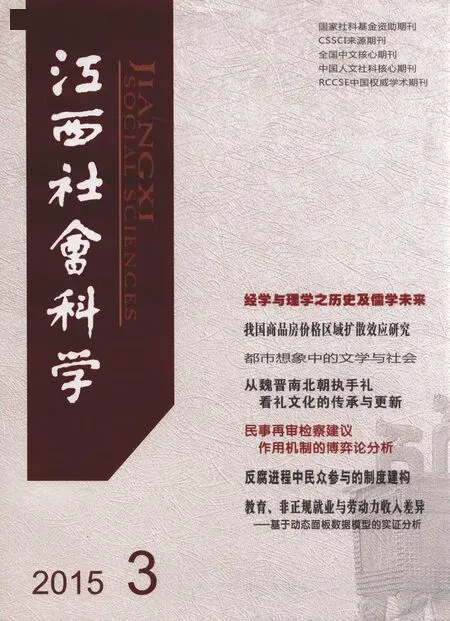王陽明的身體哲學思想
方英敏
王陽明的身體哲學思想
方英敏
所謂王陽明的身體哲學思想,不是指在陽明哲學作為“心學”的整體性質外又另存一個與之性格完全相異的“身學”,而是指陽明哲學在思維方式和質地上的根身性,它是對中國古代哲學“體知”傳統的一種回響。身體隱喻、身心一體、身物不二的身體哲學觀念與思維,在王陽明論證萬物一體、知行合一以及致良知的功夫選擇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王陽明;身體哲學;“體知”傳統
方英敏,《貴州大學學報》編輯部/貴州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博士。(貴州貴陽 550025)
一般而論,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上,陽明哲學以“心學”著稱,學界也習慣把陽明哲學等同于“心學”。顧名思義,作為“心學”的陽明哲學,核心或最高概念是“心”。從這個角度講,陽明哲學只有唯“心”而論之,把“身”的問題隱藏起來,才能最為理想地彰顯自身思想的識別性。不過,新近以來學界興起的關于陽明身體哲學研究的現象表明①,陽明哲學的內涵又還不為 “心學”窮盡,“身”的問題亦是它的題中之義。那么,陽明的身體哲學思想所指什么?下面我們選取陽明哲學中幾個公認的基本觀點來檢視蘊藏其中的身體之思。
一、身體隱喻與萬物一體
“萬物一體”是陽明哲學的基本精神,它不僅意味著萬物一體論在陽明哲學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同時還彰顯陽明作為一個哲學家的普遍卓識,因為從西方哲學史看,萬物一體是如何可能的,亦堪稱一個影響哲學史的大命題。笛卡爾為此努力論證,仍不得其解,而產生了著名的所謂“笛卡爾難題”:人(精神)與物(物質)作為兩種絕然異質的實體存在,二者之間何以統一?“笛卡爾難題”的中國式表述之一就是萬物一體如何可能。對此,陽明從不同的角度論證,其中最為顯在的思路有二:一是從“心”上說,把人與萬物一體歸結為人心容納萬有、賦予萬物以意義的心靈體驗與境界;二是從“氣”上立論,忠實地繼承中國哲學自先秦以來用 “氣一元論”解釋世界的慣習思路:既然人與萬物皆由 “氣”所生所化,那么人與萬物的本質就是相同的,即都是“氣”,故能相通。從“心”和“氣”兩種角度論證萬物一體的思路,既是浮現于陽明哲學之中的顯在邏輯,也業已積淀為學界關于陽明哲學認知的基本常識。
不過在論證萬物一體上,陽明除了上述兩種顯在的思路外,還有一種較為隱在的基于“身體性隱喻”[1](P200)的思考。所謂隱喻,是一種以“此”說“彼”的修辭與思維方式,具體地說,就是用簡單或熟悉的存在對象或經驗來言說相對抽象、不容易理解的對象。邏輯上講,隱喻的修辭、思維方式必須建立在“此”與“彼”兩種對象之間的相似性之上,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物是無法并置在一起予以言說的。陽明善于隱喻的論說方式,如他所說“凡言意所不能達,多假于譬喻”[2](P882)。身體隱喻正是陽明論說萬物一體之理所假道的路徑之一:“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2](P798)這是陽明表達萬物一體觀念的典型表述,它正是以身體譬喻的方式,即所謂“中國猶一人”來形象曉喻萬物一體之理。顯然,若從分別計較之心的角度看,萬物之博雜,物與物以及人與人之間怎么可能一體呢?但若從人形軀上起念,似乎又不難理解。人的五官、四肢、五臟、六腑等組織器官雖然都各有所屬,性質、功能各各不同,但又經脈相連,同屬“一體”。在日常經驗中,個體形軀上的某一器官組織的病變往往會牽引人的身體的整體不適感,最能說明人體的整一性。也就是說,在人體之中蘊藏著多樣性與同一性相統一的秘密。從辯證法角度看,這種“多”與“一”的統一關系也正是萬物一體之理的哲學意涵之一。從這個角度說,學者只要返身體會切于己身的身體經驗,便能夠從中獲具足夠的啟發,進而有對“萬物一體”的“本質直觀”。
從陽明的有關論述看,身體隱喻之所以能夠幫助學者通達對事物的理性認知和本質洞觀,并不僅僅在于修辭學意義上的形象譬喻那么簡單,還在于身體的體驗被視為學者認知、理解和認同世界的先決條件和共同基礎。陽明舉例說:“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2](P4)即基于自家切身體驗的自痛、自寒、自饑是學者獲得普遍意義上的關于痛、寒、饑之認知的感性且真切的基礎。“吾一人之視,其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目者,同是明也;一人之聽,其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耳者,同是聰也;一人之嘗,其味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口者,同是嗜也。”[2](P1103)這段話隱含的意思則是,人與人之間的身體感覺、體驗具有不附帶條件的相通性。一個人只要視覺、聽覺、味覺感官沒有生理缺陷,那么不同的個體面對同一色、聲、味對象的感覺應是大致相似的。面對同一對象,如果說人的心靈之知因受制于不同接受者的前在成見影響而有差異的話,那么人的身體之知則是真實無欺且相通的。譬如人的饑餓感,對任何個體而言,此種感覺一旦發生,大都有相似的生理和行為表征,如渾身乏力、頭暈、心慌等,并饑不擇食,而此時有誰還會去疑慮一下這饑餓感覺的真實性呢?人的饑餓感是如此,其他的身體感覺、體驗亦如是。
正是基于人的身體體驗的真實性與相通性,陽明認為,人與我、人與物之間可具一體性:
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為是而以蘄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2](P69)
從這段話看,無論“古之人”還是“世之君子”,他們之所以能做到“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盡管在于他們 “惟務致其良知”,在于人心的明辨與博大,但它的前置基礎卻是“知吾身之疾痛”。在陽明看來,“知吾身之疾痛”是“是非之心”以至“良知”的發生學基礎,換言之,身覺是心覺的基礎,這正是陽明的深刻之處。從經驗看,若沒有“知吾身之疾痛”的切己身體體驗為基礎,即便一個人主觀上想著“惟務致其良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但在客觀效果上難以做到真切、實在。這里極端的例子是晉惠帝“何不食肉糜”的笑話。錦衣玉食的晉惠帝面對哀號忍死的饑民也不免心生惻隱同情之心,但處于深宮之中、沒有棲身體驗過人間疾苦的他在冥思苦想之后卻悟出一個 “百姓無粟米充饑,何不食肉糜”的“解決方案”來,而為歷史所笑。所以在一定意義上講,人與人之間的是非好惡、喜怒哀樂在心靈上是不相通的,“朱門酒肉臭”與“路有凍死骨”之所以會形成如此對立的格局而難以冰釋,并在歷史的輪回中反復上演,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前者與后者沒有相同的身體體驗原型作為對話基礎。以此觀之,陽明以“知吾身之疾痛”為通向萬物一體的倫理道德之境的基礎,確乎是深刻的。在他看來,所謂萬物一體可以且應該在身體的體驗中得到體現、體會和體認。
陽明從身體隱喻角度論證萬物一體,從思想的源流上說是對發端于先秦的身體隱喻思維的復歸。《易傳·系辭下》云:“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3](P265)顯然,對萬物是如何化生的這一至今仍需自然科學家深度探秘的宇宙生成論問題,《易傳》作者是從男女構精的身體生命孕育現象入手予以類推解釋的,這便是一種“依形軀起念”的身體隱喻思維。男女結合而構精,一為二,二生三,子子孫孫,無窮匱也,這與宇宙萬物由簡而繁的化生過程至少在形式上是類似的。這種“依形軀起念”的身體隱喻思維的科學性當然是值得商榷的,但在科學蒙昧的年代它又不失為一種直觀的世界認知方式。陽明的萬物一體論繼承了先秦哲學的身體隱喻思維。如果說《易傳》作者借此主要描述宇宙生成模式的話,那么陽明則是借之論證世界的統一性,即萬物一體。
二、身心一體與知行合一
陽明在龍場悟道后,漸倡知行合一之教。知行觀本是中國古代哲學中的一個普遍命題,在知行關系上,前賢有知先行后、知易行難之論,而陽明卻以知行合一論標榜于哲學史。他說:“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學只一個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2](P12)這句話較為扼要地表達了陽明的知行觀,即知行合一,用陽明的慣用表述是,知行是“一個功夫”、“不可分作兩事”。
知行合一作為陽明哲學的精彩節目之一,其內涵意義當是一本大書的題目,本文感興趣的問題是知行合一成立的依據是什么。從史料看,對于陽明倡立的知行合一論,學者對它的理解與接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便是陽明最為得意的弟子徐愛也對乃師的立言邏輯心存接受障礙。徐愛曾因未能完全吃透知行合一之旨,在與學友的論辯中非但未能說服對方,而且在恍惚糾結中仍覺知與行是兩件事。但是,陽明一再強調,他倡立知行合一論 “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2](P4),“圣賢教人知行,正是安復那本體,不是著你只恁的便罷”[2](P3)。也就是說,陽明認為,他的知行合一論,既不是他本人的鑿空杜撰,也由不得他人的主觀詭辯,而是“知行本體”原本如此,知行合一論不過是“安復那本體”而已。那么,到底是什么推動著陽明如此言之鑿鑿地倡立知行合一之教呢?這里的關鍵是要理清陽明所謂“知行本體”指的是什么。哲學上的“本體”概念是指事物存在的最后依據,因而弄清了“知行本體”是什么,則知行合一的終極根由也就迎刃而解。
細繹陽明思致,我們發現他所謂 “知行本體”是指身心一體。在為徐愛釋疑解惑的過程中,陽明特意舉譬《大學》所引“好好色,惡惡臭”的生活現象學予以形象曉喻知行合一之理:
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后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后別立個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2](P3)
應該說,陽明用“好好色,惡惡臭”的生活現象學闡釋知行合一,確乎是一個極有說服力的例子。如果說“見好色”、“聞惡臭”屬知,“好好色”、“惡惡臭”屬行,那么見好色與好好色、聞惡臭與惡惡臭,二者之間確實是同時發生的。日常生活中,人見好色,大都會直接牽連著“好”的身體反應,如身體趨前、回眸一看等;同樣人聞惡臭,也會立即表現出“惡”的身體動作,如掩鼻、扭身、掉頭而去等。進而言之,如果說“知”是“心”在“知”,“行”是“身”在“行”,那么知行合一成立的深層依據便是身心一體。因為從邏輯上講,如果人的身心分裂或存有障礙,那么要實現從“見好色”到“好好色”、從“聞惡臭”到“惡惡臭”的即知即行便無可能。
從概念辨析的角度看,知行關系與身心關系不是對等的命題。在陽明哲學中,知行合一的立言宗旨歸根結底是個揚善懲惡的道德認知與踐履問題,如陽明自謂“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2](P84-85),而身心關系則是一般意義上的人學問題。但陽明論知行合一,確是從身心關系入手予以深度立論的。陽明早年曾效仿朱熹格物致知之法,但在經歷“格竹”多日而勞思致疾的失敗后,“乃知天下之物本無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2](P105)。這一自省是陽明與朱熹分道揚鑣的端倪,它表明,陽明已經意識到對終極之道的占有必須由外求而內索,在身心關系的基點上重究天人之際。
再看一段陽明與弟子的對話:
希顏曰:“先生謂格物致知是誠意功夫,極好。”九川曰:“如何是誠意功夫?希顏令再思體看,九川終不悟,請問。”先生曰:“惜哉!此可一言而悟!惟浚所舉顏子事便是了,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與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視、聽、言、動?心欲視、聽、言、動,無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無心則無身,無身則無心。”[2](P79)
在這段對話中,陽明關于 “格物致知是誠意功夫”的觀點與其知行合一的論旨是相通的。由于陽明認為“心外無物”,把外物還原成人心,因而他所謂“格物致知”就是指學者通過誠意功夫實現知行合一,使良知(知)朗顯、播撒為現實的為善去惡的道德實踐 (行),如陽明在另處所說:“若以誠意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為善去惡無非是誠意的事。”[2](P34)這與朱熹的“格物致知”含義——探尋事事物物之中的普遍規律或客觀知識是不一樣的。在這個意義上,檢驗學者“格物致知”的成效就是看他能否做到知行合一。陽明也因此認為格物致知是誠意功夫,實際上也就是認為知行合一是誠意功夫。弟子希顏領悟到這一點,所以他說“極好”;但九川“終不悟”,并繼續追問“如何是誠意功夫”,也就是為什么通過誠意功夫能使知行合一呢?而對于九川的請問,陽明循循善誘、次第啟發,最終在身心關系上使九川 “一言而悟”,而這“一言”就是“無心則無身,無身則無心”的身心一體觀。為什么是身心一體是知行合一的本體依據?在此陽明也是點到為止,沒有細說,但隱含其中的邏輯還是明白的:因為如果人的身、心分裂,則怎么使用誠意功夫也不可能使得心之知與身之行到達合一。而顯然,九川對知行合一的不悟當并不在于知行合一論的淺表邏輯,而是一時“健忘”于其隱在的立論前提,即身心一體。
應該說,陽明以身心一體作為其知行合一論的本體理據是有力的。從邏輯上講,人的身心關系有三種情形:第一種是身心完全統一;第二種是身心完全對立;第三種是身心既統一又對立。一般而論,第一種是身心關系的理想狀態,第二種意味著人的病態,第三種是人的身心關系的日常情形。在日常狀態中,人的身心之間一般是統一的,否則人日常的視聽言動便難以為繼,但同時人的身心又偶存緊張狀態。陽明的知行合一觀以身心統一論為理據,但又注意到身心對立的情形。從前者說,人的身心在普遍情形下是統一的,所以知行合一實屬常態;從后者說,陽明認為人的身心之間雖然由于私欲、習心的摻入、阻隔而偶呈對立狀態,但通過誠意功夫剔除私欲、習心的影響,則可以內調身心緊張關系、達致統一而外顯為知行合一。質言之,無論從身心一體的實然狀態還是應然要求說,知行合一原本都不成問題。
在身心一體論上,陽明哲學可謂又一次伸向了中國哲學的源頭處。身心一體是中國哲學自先秦以來一直綿延的信念。日本學者湯淺泰雄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指出:“東方肉身觀中存在著一種強烈的傾向,即把身與心看作是不可分割的一體,但這并非指身與心是簡單的不可分割。它暗示作為一種觀念,身與心應該是不可分割的。”[4](P12)正是基于身心一體論,中國哲人自先秦始無論儒家言修身還是道家講養生,都主張身心同修同養。中國先哲并非意識不到身與心的概念內涵有別,以及現實中身心之間的分裂狀況,但身心一體(如是或應當一體)乃是中哲的信念,這如同身心二元論為西哲的思維定式一樣。因而,盡管縱觀陽明的整個哲學思想體系,它對身心一體觀所論不多,以至于學界以往也容易忽略這一問題。但是,所論不多并不意味著這個問題在陽明哲學中不重要,恰恰相反,它說明在陽明看來身心一體與其說是一個尚待證明的命題,還不如說是思想立論的前提、基礎。這從如前所述陽明以“無心則無身,無身則無心”的簡單“一言”而使九川悟得知行合一之理的輕描淡寫便可見出。陽明論知行合一,費了很多工夫重釋經典,在重釋經典中使學者接受知行合一之新論,而對身心一體論所述不多,但這只能理解為陽明對發韌先秦哲學的身心一體論予以默認與繼承。
三、身物不二與“事上磨煉”
在陽明哲學中,承續“萬物一體”、“知行合一”的理路發展而來的是致良知學說。陽明說過:“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2](P818)這足見致良知在陽明心目中的分量。陽明的致良知是良知(本體)和致(工夫)的統一。關于這一點,學界已有深度闡釋并成共識,此不贅言。而一個為學界都注意到的事實是,在致良知的兩種功夫即“事上磨煉”和“靜坐”中,陽明尤重前者。他說:“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2](P11)“人須在事上磨煉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2](P81)靜坐本是傳統的修身體道方式,從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到莊子的“心齋”、“坐忘”以及禪宗的“坐禪”、宋明儒的“主靜”都是靜坐理論及實踐的不同形式,這是一種收視反聽的冥契狀態,對平息人欲的躁動、思慮的不安能收到非常積極的效果。但陽明認為,靜坐只是初學功夫,若走向懸空靜守、槁木死灰的狀態,則無用甚至有害。他本人曾在佛、老的“虛”、“無”之境中尋求長生久視之道,但最終從中出走,就是對靜坐的消極意義的深切省思。而“事上磨煉”則要求學者在身體力行中將良知推致到事事物物之中。
陽明為何偏舉 “事上磨煉”對致良知的意義,學界首先看到它與儒學實踐精神的關聯。因為在儒家的一貫理解中,學者的問道、體道并非一項坐而論之的務虛工作,而是要落實為修齊治平的現實實踐。因此,陽明強調“事上磨煉”當然是對儒學實踐品格的復歸或曰傳承。不過,從身體哲學的角度看,陽明對“事”的哲學內涵的著意理解與他偏舉“事上磨煉”的踐履工夫卻有著內在的邏輯一致性。在陽明看來,“事”與“物”是有區別的,所謂 “事上磨煉”不是 “物上磨煉”。陽明刻意對“事”與“物”做了區分,在他看來,“物”是指朱熹版的“格物”之“物”,乃是外在于人的客觀對象,是思維認知的對象,如格竹之竹;而“事”則不然:
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2](P5)
顯然,這里的“物”已非朱熹主客分離意義上的客觀對象之物,而是為人的身、心、知、意所指涉和糾纏,諸如事親、事君、仁民愛物、視聽言動等均不脫離人的身心狀態的規定,實質上是一種與主體之人的當下存在不可或分的生存情境,即“事”。質言之,“事”是身、物不二的。在“事”中,“人-物”關系、“人-我”關系和“人-世界”關系相互纏結并交織其中。“事”作為一種向人、我、世界敞開的生存情境,它是具體鮮活乃至變動不居的關系之域,而非靜止孤立的原子之物。所以,致良知“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這是因為“事”作為一種切于個體己身的生存情境,學者若想脫“身”“事”境而致良知,在邏輯和現實性上的可能性均很小;不但如此,面對復雜紛擾的生存事境,原本寂靜的心靈狀態還會被撩撥得六神無主、無所適從,此之謂“遇事便亂”。
既然“事”是身物不二的存在,如果借助意識、思維的“思知”可以把握“物”,那么,基于身體的“體知”則更勝任把握“事”。“物”是可以邏輯地予以把握的,這也是西方的認識論哲學、科學之勝處,它嚴格地劃分人與物的界限,進而借助歸納、演繹、推理等方式,以內涵、外延都非常明晰的概念、范疇和命題間接地把握對象,獲得對對象的明確知識。而“事”則不盡如然,它“身物不二”的存在特征規定了,對“事”而言,學者若純然置“身”于“事”外,則他對“事”的把握難免隔靴搔癢;相反,只有“身”臨其“事”中,以全息之身來“體知”事境,才能獲得對“事”的全景感受。當學者把身體的全部感官、感覺都向“事”敞開,則他在“事上磨煉”獲具的結果就不止是知識學意義的客觀知識,還有與主體的身體體驗、生命需要須臾相關的是非、善惡之辨乃至安身立命的意義追問。陽明不止一次說過:“‘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2](P5)他訓“物”為“事”的良苦用心正在于強調,“事上磨煉”不是純粹朱熹意義上的“格物”的求知活動,而是包含于此又不止于此的價值意義建構活動——對是非善惡的明辨及為善去惡之踐履。如果說“格物”是“思知”活動的話,那么“事上磨煉”則是“體知”即“體之于身”的活動,它對致良知的效果生成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而這也就是陽明在論述致良知的功夫時如此偏舉“事上磨煉”一端之所以然了。
四、余論
綜上所論,身體隱喻、身心一體、身物不二的身體哲學觀念和思維在陽明論證萬物一體、知行合一以及致良知的功夫選擇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它表明,陽明哲學中確實內蘊著身體之思。不止如此,陳立勝、張再林等學者的研究成果表明,陽明哲學中的其他許多命題也都可以從身體視角予以新的闡釋。不過如此一來,陽明哲學中既然存有如此豐富的身體哲思,這是否意味著它可以改寫陽明哲學作為“心學”的整體性質?學界是否又要重立另一名號“身學”而非“心學”來指稱陽明哲學的整體特征呢?
我們認為,這實未必如此。首先,在陽明哲學中無論“萬物一體”、“知行合一”還是“致良知”都是可以單獨成書的大題目,而陽明證成“萬物一體”、“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三命題,其中身體視角只是諸多思想路徑之一。其次,從中國古代哲學大勢來看,在身與心二端,揚心抑身是主旋律,而身逐漸擺脫心的抑制并出奴入主,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了。在這個意義上,整個中國古代哲學實皆為一“心學”而非“身學”,不但學界以“心學”來概括陽明哲學的整體性質是貼切的,而且陽明哲學濃郁的唯心主義特色還真切地反映了中國古代哲學的普遍性特征。因此,即便學界繼續深度掘進、展示陽明哲學中身體哲思的富藏,在邏輯上它也并不足以撼動陽明哲學作為“心學”的整體性質。
但如我們討論的那樣,考諸陽明哲學思致的深處,其中確乎閃爍著身體哲思,這何以可能呢?原因大概有兩方面:一是在經驗和事實上講,人是身心合一的生命整體,身心之間本就糾纏難分;二,也是更重要的,中國哲學自先秦以來就秉持身心一如之論,沒有形成西方傳統哲學身心二元對立論的傳統,而是論身而及心,論心而又耦合著身。不但如此,如張再林揭示的那樣,中國古代哲學在“尊心”主潮的大傳統外,還另存一個“體知”的小傳統,即“體之于身”的身體之知也是中國古人特有的認識和把握世界的重要方式。[5](P92-96)《易傳·系辭下》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3](P256)這句話扼要地概括了古人認識世界的兩種基本方式,即“近取諸身”和“遠取諸物”,其中所謂“近取諸身”就是指從身體出發來認知和把握世界的思維范式,它發端于先秦,且這一近取諸身的生命智慧一直為后世哲學繼承,因而形成了中國古代哲學有別于西方傳統哲學的 “體知”傳統。黃宗羲曾云:
有明學術,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所謂“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自姚江指點出良知,人人現在,一返觀而自得,便人人有個作圣之路。故無姚江,則古來之學脈絕矣。[6](P178)
在一定意義上,陽明背離朱熹正在于陽明哲學的“反身”性質,接續了黃宗羲所謂“古來之學”,其中重要一端就是發端先秦的中國哲學的 “體知”傳統,無論是蘊藏于陽明哲學中的身體隱喻、身心一體觀還是身物不二論,都是這個“體知”傳統的重要內容。綜上所述,所謂王陽明的身體哲學思想不是指陽明哲學除了作為 “心學”的整體性質外,又另存一個與之性格完全相異的 “身學”,而是指陽明哲學在思維方式和質地上的根身性。
徐復觀曾敏銳地指出,中國文化作為“心”的文化不是“形而上學”,而是“形而中學”。[7](P113-114)這是一個很準確的判斷,它深刻地揭示了包括陽明哲學在內的中國古代文化和哲學的整體特征。從身心關系的角度講,中國文化、哲學之所以是“形而中學”而不是“形而上學”,原因就在于它的身心一如論傳統,沒有形成西方傳統哲學那樣的身心二元論。徹底的“形而上學”的建立必須奠基在身心二元對立論的基礎之上,論心則不及身,論身則不及心,才能建立起徹底的心本論或身本論哲學。從西方哲學史來看,笛卡爾哲學與尼采哲學分別是心本論哲學與身本論哲學的典型,它們各自把唯心論與唯身論推向了極致,顯示出人類抽象思維與分析思維能力所能伸展的極致高度,令哲學史印象深刻。而中國哲學卻始終秉持身心一如的中道觀,當西方哲學發展到梅洛·龐蒂那里才發現身心一體關系時,中國哲學卻在人類的前現代時期較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但與此同時,它也制約了中國文化、哲學的某些成就,一如徐復觀所說,未能建立起徹底的“形而上學”,從而使中國文化、哲學對“心”或“身”的哲學討論所能達到的高度均有限。因為從邏輯上看,在身心一如或一體論中,當學者欲對“心”或“身”做專心致志的哲學討論時,他會不自覺地受到另一種潛在思維定式的影響和掣肘,即人難道不是一個身心統一體,“心”可以脫離“身”而存在嗎(反之亦然)?如此一來,任何對“心”或“身”稍作深入、系統的哲學討論就會化為泡影,其結果只能奔向身心一體的中道觀。理解于斯,我們才能明白為什么中國文化、哲學是“形而中學”,進而才有對陽明哲學的準確定位:一是雖然學界慣于把陽明哲學奉為 “心學”,但與西方哲學的唯心主義成就相比,其“唯心”論到達的深度是有限的;二是雖然陽明哲學中蘊藏豐富的身體之思,但它并不足以形成一種身本論哲學。這樣理解,才能對學界有關陽明身體哲學的研究作出恰如其分的闡釋和定位。
注釋:
新近以來,隨著大陸學界身體哲學研究的悄然整體升溫,從身體視角入手研究陽明哲學亦形成了一個小小的熱點,代表性的成果有:陳立勝《王陽明“萬物一體”論——從“身—體”的立場看》(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李洪衛《論王陽明的身心觀》(華東師范大學2007年博士論文)、張再林《本心與習心——基于“身體哲學”的陽明心學闡釋》(人文雜志2010年第2期),等等。
[1]陳立勝.王陽明“萬物一體”論——從“身—體”的立場看[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2](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周振甫.周易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6.
[4](日)湯淺泰雄.靈肉探微——神秘的東方身心觀[M].馬超,譯.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0.
[5]張再林,張云龍.試論中國古代“體知”的三個維度[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8,(9).
[6](清)黃宗羲.明儒學案[M].北京:中華書局,2008.
[7]徐復觀.心的文化[A].李維武.中國人文精神之闡揚——徐復觀新儒學論著輯要[C].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96.
【責任編輯:趙 偉】
B248.2
A
1004-518X(2015)03-0017-08
貴州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項目“王陽明的身體哲學思想研究”(JD2013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