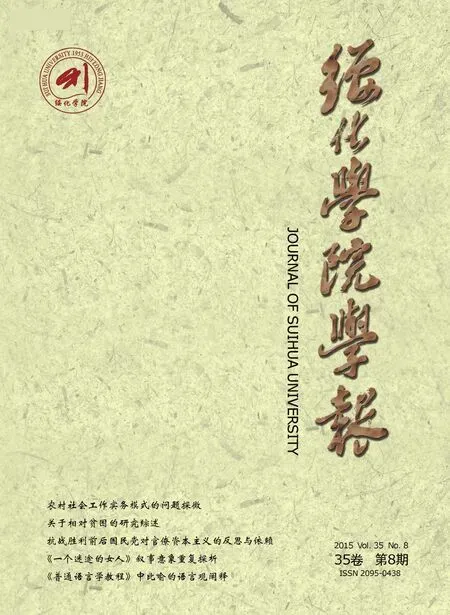帕爾默“文化語言學”及其發展評述
馮軍
(四川外國語大學研究生院 重慶 400031)
帕爾默“文化語言學”及其發展評述
馮軍
(四川外國語大學研究生院 重慶 400031)
美國語言人類學家帕爾默1996年首次將語言人類學的三大傳統與認知語言學結合起來,提出了“文化語言學”概念。雖然在理論上具有開創性歷史意義,但受當時學術發展的影響,帕氏文化語言學在學科定位上略顯保守、理論上缺乏堅實的認知基礎,不利于其長遠發展。隨著研究的進展,當今國外學者對“語言、文化與認知”的研究的愈發重視,一批批著作也相繼問世,這啟示我們有必要對帕氏文化語言學作出新的評價,并順應學術潮流進一步推動文化語言學的完善與發展。
文化;認知;認知語言學;語言人類學;文化語言學
眾所周知,語言是文化的重要載體。人們對于語言與文化的研究已有悠久的歷史,其中最為著名的是“薩皮爾-沃爾夫假說”即語言相對論。但首次將語言與文化的研究概括為“文化語言學”是美國著名人類語言學家帕爾默(GaryB· Palmer)1996年所著的《文化語言學理論構建》(“Towarda TheoryofCulturalLinguistics”)一書。該書一經問世,就成為西方語言人類學和語言文化研究論著中第一部集中論述文化語言學的理論專著,同時也成為語言學、人類學研究者等專家學者研究的理論之一。
一、帕爾默文化語言學
(一)《文化語言學理論構建》內容回顧。“文化語言學(culturallinguistics)”源于1996年美國語言人類學家帕爾默的專著《文化語言學理論構建》(Toward a TheoryofCultural Linguistics)。該書一書共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關于文化語言學的目標及概念;第二部分是關于文化語言學的解釋與運用。
第一部分分為五章:第一章是引言及學科背景介紹。在這一章中,帕爾默以新幾內亞南部的Kaluli部落的一種信仰隱喻說明語言、現實與意象的關系:特定的經驗必然產生特定的意象,而特定的意象必定產生特定的語言表達法。第二章詳細介紹了語言人類學的三大傳統:博厄斯語言學(Boasian linguistics)、民族語義學(ethnosemantics)和會話民俗學(theethnographyofspeaking),并指出了各自的弊端。第三章則主要介紹了認知科學及認知語言學的崛起及理論發展。第四章介紹了“文化語言學綜合體(thesynthesisofcultural linguistics)”。他認為雖然三大傳統中,這樣一個綜合體已經存在,會話民俗學就是一個最好的代表。但是人類語言學還是有必要采用一個更加系統的認知方式,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本族語者的觀點、更好地研究語言在社會和文化環境下的使用。第五章介紹了文化語言學所涉及的核心意象概念,包括認知模式(cognitivemodel)、象征性符號(symbol)、意象圖式(image-schema)、原型(prototype)、基本范疇(basic category)、復合范疇(complex category)、隱喻(metaphor)、轉喻(metonymy)和社會情態(socialscenario)等等。
第二部分是關于文化語言學的解釋與運用,分為六章(第6章至第11章)。第六章探討語言與世界觀的關系;第七章介紹了話語分析與敘事;第八章介紹了隱喻與轉喻;第九章介紹了單詞與句子語法的建構與解構;第十章介紹了文化音位學;第十一章總結出文化語言的八條原則以及文化語言學對民族志學研究的啟示。
(二)理論介紹。帕爾默在《文化語言學理論構建》中系統地闡述了文化語言學的學科基礎、核心概念和發展框架。文化語言學主要基于語言人類學的三大傳統:博厄斯語言學(Boasian linguistics)、民族語義學(ethnosemantics)、會話民俗學(theethnographyofspeaking)和認知語言學。博厄斯派語言學是由美國民族學之父博厄斯開創的,盛行于上世紀上半葉。該學派強調運用實證和經驗方法對語言進行客觀描述記錄,反對抽象推理。博厄斯對語言和民族文化的心理基礎感興趣。他認為語言與心象息息相關,語言是心象最重要的工具,語言研究應該屬于人類學研究范疇。根據帕爾默的定義,民族語義學是通過認知對不同文化的知識領域如植物、動物、親屬等進行范疇域的研究[1](P19)。民族語義學從各民族特定的文化和社會語境入手分析各民族語言意義上細微差別。會話民俗學研究不同社會文化環境中人們之間的會話行為,以及其背后的結構特征。
帕爾默認為人類語言學三大傳統之間相互聯系,相互補充,同時也有各自的弊端:博厄斯派的觀點有點極端;民族語義學的觀點實證性太強;會話民俗學不夠精確。一直以來人類語言學關注語言文化現象的描寫和解釋,由于缺少認知維度,人類語言學不但發展緩慢,對某些語言現象也無法做出合理解釋。他認為雖然三大傳統中,文化和語言綜合體已經存在,會話民俗學就是一個最好的代表。但是人類語言學還是有必要采用一個更加系統的認知方式,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本族語者的觀點、更好地研究語言在社會和文化環境下的使用。當時新興的認知語言學從認知入手,認為語言是人類認知活動的產物和工具,語言能力是人普遍認知能力的一部分,語言與人的認知能力密切相關。語言結構與人的概念知識、身體經驗以及話語功能有關,并以此為依據。帕爾默接受了認知語言的認知觀,但發現認知語言學對文化維度有所忽視。所以人類語言學和認知語言學的結合不但可以彌補“語言、文化、認知”三者之間的空白,同時能挽救人類語言學的沒落頹勢,帕爾默將二者的結合命名為“文化語言學綜合體(thesynthesisofculturallinguistics)”[1](P35)。
帕氏文化語言學的核心概念是來自認知語言學的“意象(imagery)”(后來認知語言學用“圖式”替代了“意象”)。傳統語言研究注重形式而忽略了意義,語言被視為抽象的符號,意象概念的重要性多年來一直被語言學家們所忽視。帕爾默認為語言能夠激活意象,語言理解離不開意象。帕爾默決心要重新喚起人們對文化意象的興趣。他認為文化語言學和認知語言學本質上都是關于“心象(mentalimagery)”的理論。二者都試圖利用各種相關的意象概念去探尋說話者是如何使用言語的,而聽者又是如何理解言語的。他還將認知語言學中的認知模式(cognitivemodel)、象征性符號(symbol)、意象圖式(image-schema)、原型(prototype)、基本范疇(basic category)、復雜范疇(complexcategory)、隱喻(metaphor)、轉喻(metonymy)和社會情態(socialscenario)等概念引入文化語言學,而且將這些概念與意象聯系起來。意象的建構是受文化影響的,這種受文化影響的意象掌控著敘述、修辭、語義、語法、話語甚至音位。所以帕爾默文化語言學還認為語言、意象、世界觀具有同構關系。
二、帕爾默文化語言學評論
在《文化語言學理論構建》一書中,帕爾默稱文化語言學是一個“綜合體(synthesis)”,揭示了文化語言學的跨學科性。帕爾默認為語言人類學(linguisticanthropology)的三大傳統需要一種系統的認知方法作為補充,而認知語言學(cognitive linguistics)則缺少極為重要的文化維度,所以他力圖將它們四者結合起來,構建一種對語言現象解釋力更強的理論——文化語言學(culturallinguistics)。帕爾默提出“文化語言學”這一概念,將新興學科與傳統學科結合起來,首次將語言、認知、文化三者結合起來,在語言學和文化研究中都具有開創性歷史意義,為語言和文化研究提供了新視角,注人了新活力。該理論充分繼承了語言人類學三大傳統的優點,同時舍棄了其不足。更重要的是,將語言與世界觀聯系起來,而且將文化拓展到音位層面提出了“文化音位學(culturalphonology)”[1](P272),同時吸收了當時認知語言學的主要概念和理論,彌補了認知語言學研究在文化層面的不足。
但是,帕氏文化語言學也有不足之處。主要體現在兩點:第一,帕氏文化語言學缺乏堅實的認知基礎。帕爾默提出建立文化語言學的目的是為發展和豐富美國語言和文化研究中的三大傳統,這就注定了他不會將“語言、文化、認知”三者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所以該理論的名稱“文化語言學”也沒有體現出“認知”維度。帕氏文化語言學一直受到許多學者的批評,他們(如Peeters①)認為帕爾默的文化語言學缺乏堅實的認知基礎。謝里夫(Sharifian)認為這種批評可能是因為各自對“認知”的理解不同。帕氏文化語言學從認知語言學中引入的概念包括認知模式(cognitivemodel)、象征性符號(symbol)、意象圖式(image-schema)、原型(prototype)、基本范疇(basic category)、復合范疇(complexcategory)、隱喻(metaphor)、轉喻(metonymy)等。我們認為帕氏文化語言學缺少堅實的認知基礎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沒有將龐大的認知科學體系作為認知理論的來源,單從認知語言學借鑒一些概念和理論不足于支撐文化語言學的研究。
第二,學科定位過于保守。帕爾默將“文化語言學”描述為“文化心象理論(a theoryofculturallydefinedmentalimagery)——文化語義理論(aculturaltheoryoflinguisticmeaning)”[1](P4),這說明他對文化語言學的定位還只是一種基于“意象(imagery)”的語義理論,并不是想建立一個語言學分支學科。這就導致了文化語言學在理論基礎的方面顯得過于狹隘。基于最新的文化語言學著作來看,如今的文化語言學現已超出了“文化心象理論”的定義。文化語言學不再被定位為一種語義理論,而是語言學分支下的一個綜合性、跨領域學科。其理論基礎不僅限于語言人類學和認知語言學,還包括認知文化學、社會語言學、認知社會語言學、心理語言學、認知心理學、認知人類學、文化人類學、語言哲學以及母體認知科學等。綜上所述,我們權且對“文化語言學”作出如下定義:文化語言學是在第二代認知科學革命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一個新興的跨界學科,其主要學科基礎是語言人類學、文化人類學、認知科學(包括其下屬分支學科如認知語言學、認知社會語言學、認知心理學、認知文化學等等),該學科以文化為切入點圍繞“語言、文化、認知”三者的關系對語言和語言現象及其背后的文化和認知機制進行綜合研究。
三、文化語言學的最新發展
近幾年來,文化語言學開始從其他學科中汲取養分逐漸建立自己的理論如“文化認知(culturalcognition)、文化概念化(culturalconceptualization)”[2]等。此外,認知科學中的“分布式認知”“社會認知”“集體認知”等認知理論也可以被作為文化語言學的認知基礎。在TheRoutledgeHandbookofLanguageand Culture一書中,“語言、文化、認知”被單獨作為一個部分,分別從具體方面著手研究語言、文化與認知,如語言、文化與涉身,文化與語言加工,顏色詞、思維與文化,文化與情感語言等。這些研究都跟認知相關,這表明當前的文化語言學家已經充分認識到“認知”在文化語言學中的重要地位。
此外,隨著文化語言學理論的豐富和完善,其研究范圍也越來越廣,我們認為主要包括三大類:理論本身研究、理論拓展研究和理論應用研究。第一,在理論本身方面就是語言與文化及認知之間的關系研究以及完善和豐富文化語言學的理論體系研究,具體包括“文化語義學”“文化語用學”及文化句法學(目前還沒有這種提法)等。還包括在“Handbook”一書中包括:語言文化與具身研究、語言文化與原型研究、語言文化與空間認知研究、語言文化與時空研究、語言與文化腳本研究、語言與世界觀研究等等。第二,在理論拓展方面,主要將文化和語言與第三方結合進行綜合研究。TheRoutledge HandbookofLanguageandCulture一書為讀者展示了豐富的研究范圍,包括語言文化與性別研究,語言文化與禮貌研究,文化與親屬語言研究,語言文化與身份研究,語言與文化歷史研究等等。第三類是應用領域研究,直接將文化語言學的理論應用于其他研究對象,包括二語習得與語言教學中的語言與文化研究、跨文化交際中的語言與文化研究、翻譯中的語言文化研究、世界英語研究、話語分析與敘事研究等等。
總之,圍繞“語言、文化、認知”的研究將越來越受到學者們的重視,這在國外已呈明顯的趨勢。認知語言學家早期就認識到文化知識的重要性,認為文化不僅是語義詞匯的基礎還是語法的一個重要方面。Langacker進一步提道“雖然語義被視為概念化,但認知在各個層面既是具身的又是文化嵌入的。”[3](P31)如今,認知語言學和語言人類學在國外也開始了第二次融合(第一次是帕爾默提出“文化語言學”概念),例如約翰·本杰明斯(JohnBenjamins)出版社從2011年開始陸續出版的“文化語境中的認知語言學研究”(CognitiveLinguisticStudiesin CulturalContext)系列叢書和PalgraveMacmillan出版社2014年的新書ApproachestoLanguage,CultureandCognition——The Intersection ofCognitive Linguisticsand Linguistic Anthropology,以及上文提到的Routledge出版社于2015年年初出版的The RoutledgeHandbookofLanguageandCulture一書。我們認為不同出版社在相對短的時期內先后推出融合“語言、文化與認知”研究的著作絕非偶然,這或許預示著該領域的研究將是未來語言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發展方向。
綜上,本文主要對帕爾默文化語言學加以介紹和評論,希望能夠引起國內對該領域感興趣的學者對“語言、文化與認知”三者融合研究的注意,對文化語言學的重視,從而推動文化語言學的完善與發展,最終揭示語言、文化與認知三者之間的奧秘。
注釋:
①Peeters,B.“DoesCognitiveLinguisticsliveup toitsname?”, in R.Dirven,B.W.Hawkinsand E.Sandikcioglu(eds)Languageand Ideology,Vol.1:CognitiveTheoreticalApproaches[M].Amsterdam/ Philadelphia:JohnBenjamins,2001.
[1]Palmer,G.B..Toward a Theory ofCultural Linguistics[M]. Austin:UniversityofTexasPress,1996.
[2]Sharifian,F..Cultural Conceptualizations and Language: TheoreticalFrameworkand Applications[M].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Benjamins,2011.
[3]Langacker,R.W..“Culture,cognition and grammar”in M. Pütz (ed.)Language Contact and Language Conflict[M]. 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Benjamins,1994.
[責任編輯 靳開宇]
H0-06
A
2095-0438(2015)08-0072-03
2014-05-05
馮軍(1989-),男,陜西漢中人,四川外國語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認知語言學、認知詩學、文化語言學。
2014年重慶市研究生科研創新項目(CYS14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