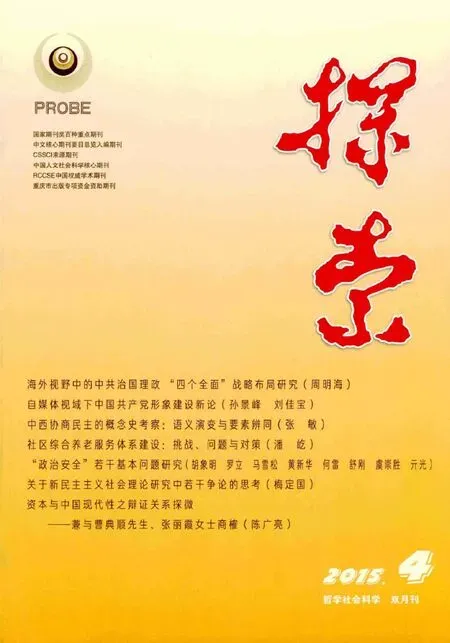現代西方協商民主的社會實踐和理論探索
(四川大學政治學院,四川成都 610207)
在對人類民主歷程進行梳理時,有學者對西方近代以來的民主政治做出了如下評價:“1776年以來,在任何時候,在任何條件下,民主作為一種國家形式,一直保持著勝利者的姿態,但很顯然,這種民主是代議制民主而不是參與式民主。”[1]257這樣,作為代議制民主運作形式的選舉競爭成為現代民主政治實踐的主流;而通過對選舉競爭民主實踐的理性觀察和分析,近現代多位知名政治學家漸次發展和完善起來的精英民主理論也成為現代居于主導地位的民主政治思想。不僅如此,由于精英民主理論的完善和以選舉競爭為特點的代議民主的廣泛實踐,人們幾乎喪失了對主流民主政治思想和實踐的批判意愿和能力。這正如有的學者所言:“最近一段時間以來,由于熊彼特對‘古典民主學說’神話的如此成功地傳播,關于民主理論的討論熱情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這意味著關于這一主題的流行的學術正統,即當代民主理論,沒有受到實質性的、有力的批評。”[2]97所以,現代民主政治實踐和民主政治理論中,在古希臘獲得萌生、近代獲得多元探索的協商民主日益被人忘卻,即使進行探索,也面臨著社會理性的冷遇。協商民主的實踐也日趨式微。但是即使面臨諸多的理性難題和實際冷遇,協商民主的實踐和理論仍在艱難摸索和頑強生長。
1 協商民主的現代社會實踐探索:合作主義的推進與困境
20世紀上半葉,合作主義在西方社會領域中逐漸滋生并獲得了多元政治實踐。它的萌生和發展根源于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上半葉,壟斷資本主義發展導致西方工業社會內部勞資矛盾不斷激化,向國家提出了嚴峻的社會管理問題。該時期壟斷導致的經濟權力集中,使資方在勞資矛盾沖突中占據著優勢地位。他們通過資本投資的轉移,掌握著工作機會的供給,不斷削弱個體勞工實現訴求的能力。與此相對應的是,19世紀末期以來社會日益組織化,勞工結成了強大的工會組織或政黨。結果是在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上半葉“無論資本還是勞工,都產生了強大的組織,這些組織在市場上進行對抗,彼此都可以而且力圖破壞對方的打算”[3]286。在這種背景下,資本家通過拒絕投資或資本向外國的轉移與勞工對抗,而勞工則通過罷工運動和資方相抗衡。他們的行為不斷損壞社會經濟增長能力和國家政治調控能力。其二,凱恩斯國家干預理論的提出,一定程度上為國家對勞資雙方的對抗管理提供了新的思維。1936年凱恩斯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針對西方經濟大危機批判了資本主義市場的自我管制思想,提出了國家干預理論。自此,國家干預經濟和社會事務的角色日益受到各方承認和重視;部分西方國家開始在國家、資方和勞工之間建立起一定的協商溝通渠道,以消融它們所面臨的尖銳社會矛盾,促進各方合作。協商合作實踐的核心,就是通過三方協商以緩和勞方和資方在爭議方面的沖突,既有效實現勞方和資方對基本工資、福利等社會政策制定的參與訴求,又使國家能夠保持基本的社會穩定和維持必要的社會秩序。
20世紀上半葉,合作主義實踐探索呈現出二維分野的政治態勢。一方面是德國和意大利法西斯政權、西班牙佛朗哥政權、葡萄牙薩拉查政權等的“國家合作主義實踐”。在這些國家合作主義實踐中,它們強行將社會分工中履行不同職能的社會階層劃分成各種社團,將所有人納入國家的控制之下;同時,它們賦予這些強行成立的社團以壟斷代表特定社會利益的政治權利。在國家建構的官方或半官方的合作渠道中,這些社團和國家代表共同對相關公共政策進行磋商,緩和社會矛盾,維持了社會的高度穩定。如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按照合作主義原則建立了各式各樣具有半官方性質的“協會”,以“消滅資本主義、推動勞資合作實行利益分配制”[4]95。正因如此,人們認為20世紀二三十年代德國和意大利法西斯政權是“國家合作主義”的典型,而且“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期間,合作主義在理論上被設想為法西斯政權的一個基本意識形態部分”[5]181。國家合作主義理論及其實踐,由此被法西斯污名化,成為法西斯國家控制社會的遮羞布和專制工具。二戰結束后,被污名化的國家合作主義理論和實踐逐漸脫敏,在新加坡等國家的實踐中獲得了新的評價和政治認可。另一方面是奧地利、北歐諸國和美國新政時期的“社會合作主義實踐”。這些國家將行業代表壟斷權授予具有自治特征的行業勞工組織和雇主組織,換取相關組織領袖(即社會精英)及其所代表的社會成員對國家社會政策的認同。實踐中,它們通常成立由國家、資方和勞方組成的三方委員會,就收入政策和社會福利等有限的宏觀政策進行協商討論。在此過程中,國家扮演調停者的角色,勞資雙方按照嚴格程序進行有序協商,追求政策共識。強大的勞工組織就成為“與最高雇主聯盟和國家談判經濟和社會政策的‘社會伙伴’”[6]186。“社會合作主義”的實踐,既實現了社會力量對相關國家政策制定的有序政治參與和國家對社會力量的有效政治吸納,又使得國家政策能夠得到社會認可和高效執行。它保障了社會的自主自治和國家公權力的政治權威。

表1 20世紀上半葉部分合作主義國家情況一覽表①根據翟玉忠的論文《合作主義基礎》(http:∥corporatism.bokee.com/50516.html)、李路曲的論文《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國家合作主義》(參見《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2期)和《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社團主義·社會合作主義”與“人民黨主義·民粹主義·民眾主義”詞條)提供的材料整理而成。
雖然合作主義在20世紀上半葉獲得了兩個方向維度的實踐。但是,以德意法西斯政權為代表的國家合作主義的政治實踐,使得合作主義一度成為法西斯的代名詞,受到世人的詬病。而在美國新政時期與奧地利、北歐等國家中的社會合作主義實踐,卻被限制在狹隘的社會政策領域范圍內。所以赫爾德認為:“廣泛的合作主義安排,僅僅在少數的幾個國家得到了實行,其中突出的有奧地利、荷蘭和瑞典。”[3]291在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初的經濟發展時期,合作主義的發展呈現出極為光明的前景。然而,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的嚴重經濟困難十分尖銳地表明,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共同基礎是有限的,以談判和妥協意愿的存在為前提的制度,其實施前景是暗淡的”[3]291。所以,合作主義在現代的實踐“標志著資本主義社會民主理論和實踐的一種令人感興趣的但也是有限的發展”[3]292。協商民主雖在社會管控方面發揮了突出的政治作用,但很難進入主流的民主政治視野之中。這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協商民主在現代西方面臨的實踐困境。
2 協商民主的現代思想探索:杜威和佩特曼的相關思想分析
萌生于20世紀初期并獲得多方探索的合作主義社會實踐、精英民主理論支撐下的選舉競爭式民主的弊端和社會分化激發的大眾政治參與,再次激起了部分西方政治學者的民主反思精神。他們展開了對協商民主的多元思想探索。
2.1 杜威對民主的反思:協商的政治哲學探索
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西方以選舉競爭為主要特點的民主政治和以自由資本主義為指導的經濟,都相繼陷入了危機狀態。民主政治實踐中,階級利益逐漸侵蝕甚至遮蔽了公共利益;勞資矛盾沖突日益加劇,并成為國家管理的重要難題。面對這種情況,西方民主政治或陷入社會動蕩,民眾政治認同度日趨下降;或誤入法西斯歧途,危害人類。針對民主政治的衰落和蛻變,杜威一再強調民主的目的,“專為人民的幸福,不是為了私人的一部分的幸福”[7]103。在民主政治中,個人權力固然不能拋棄,但是當公民進入政治公共領域,就應該替公眾謀利益。在利益抉擇時,公眾利益重于個人利益,個人應該犧牲自我利益維護或增益公眾利益。所以,民主的意思是“處處要有共同協作的心思、服務社會的精神,并非我所好的好之,我所要的要之的意義;總要別人所希望的,我也好之,別人所愿意的,我也愿意,處處洽著大眾的同情才好”[7]104。所以,杜威通過對現代民主政治運作的反思,開始逐漸形成以公民偏好開放和偏好交融為特征的民主運行觀點,即協商合作式的民主觀念。
在經濟社會領域,1929—1933年席卷西方的經濟大危機更是彰顯了西方在社會哲學方面的諸多重大缺陷。經濟大危機之前的西方社會,奉行根源于市場經濟的個人主義理念,認為每一個個體都有權利去謀求自我的利益,追逐自我的幸福。但是杜威認為這種理念的凝結——即傳統的自由主義哲學,“它支持有著先定特權的個體解放,卻對所有人的普遍解放漠然視之”[8]280-281。這進而導致社會各個個體或其組織在謀求自我利益時相互傾軋,社會整體混亂失序;社會個體在內心感受上孤獨無依,日益“原子化”。不僅如此,謀求經濟資源的無窮占有成為個體發展、社會地位提升和政治權力斗爭的根本支撐力量,整個社會日益形成“金錢文化”。在這種文化中,“個人主義所代表的機會平等、自由的聯合與相互交流正在變得模糊,逐漸暗淡下去”[8]18。針對這些現象,杜威提出“個性回歸”的新個人主義。個人本是環境的產物,沒有超越環境的絕對自由的個人。“個人主義者只有當他們的觀念和理想同他們所處的時代現實相協調時才會重新找回自我”[8]70。而在這種“個性回歸”的過程中,個體之間的社會交往性——即個體與個體之間的社會合作性——將逐漸為社會個體所體認。他們將在社會合作中擺脫個人孤獨,融入社會合作,最終是傳統的個人主義所主張的個人解放演變為新個人主義下群體的普遍解放。社會個體的“個性回歸”引導他們去認知、追求共同利益。所以,杜威依據他的新個人主義認為,應該“創造一種新型個人——其思想與欲望的模式與他人具有持久的一致性,其社交性表現在所有常規的人類聯系中的合作性”[9]91。當然,在此轉變過程中,以前在公共事務上處于消極狀態的公民,將成為積極公民。他們將在不妨礙他人同等權利的前提下,發揮自己的能力,追求自我的幸福并造福于社會。這就為杜威對協商民主進行探討奠定了哲學上的主體基礎。
在對民主政治運行進行哲學反思的基礎上,杜威從三個方面對民主政治中的協商做了抽象理性分析和認知總結。
2.1.1 公共決策需要爭辯、討論和說服的民主方法
在20世紀上半葉,人們面對社會資源的配置,形成了互相沖突的多元觀點,而社會資源的有限性又削弱了國家對沖突性觀點和對抗行動的調解能力。所以杜威在《公眾及其問題》一書中認為現有的資源所要面對的公眾和公共話題太多了。在公共話題所聚焦的公共事務的解決過程中,為了避免強勢力量對話語的控制和利益的獨占,杜威進而強調在公共事務的全面認知和權威決策中最迫切需要的“是使我們用以進行爭辯、討論和說服的各種方法和條件得到改善,這就是公眾所面臨的問題”[10]281。
2.1.2 個體“自由的知性”假設,要求民主政治中的個體在探索公共問題的政策調適過程中進行理智的協作
臺灣有學者認為,杜威的自由主義“就是一切探討、討論和表達都依自由的知性而進行”[11]215。這里的“自由的知性”,就是指每個人都能依據個人理性做出事實判斷和價值選擇,即依據科學和理智處理自己的私人事務及個人面臨的社會事務。所以,針對20世紀上半葉的社會現實,杜威在《公眾及其問題》一書的緒論中強調:當前生活不可救藥的弊端在于科學方法運用方面的不平衡,即過多地運用于自然領域,而過少地用于人類事物的領域,“消除這些弊端的最直接和有效的途徑,是穩妥而系統地致力于在人類事物中發揮名為科學方法的有效理智”[12]983。據此邏輯,人類在管控社會分歧時應運用理智的方法進行分析和處理,尤其是“理智協作方法”。在理智方法的運用過程中,人們只服從真理和事實真相或邏輯力量。面對社會事務,參與各方真實地表達內含著特定洞見的個人意見并相互辯論。理智方法的運用最終“有可能以一種超越自私利益或分歧雙方的狹隘觀點的標準結果來評價”[12]985,即形成理性共識。在此過程中,個體之間的理性交融也使個體的知性獲得發展,擴展了個體的自由,使個體的獨特性建構在豐富性的基礎之上。所以,生活中“只有通過個人在他們自愿協作中得到發展,個性的發展才是安全的和持久的”[13]407。當然,個體知性的運用和自由發展不可能脫離社會大環境的制約和其提供的可能,尤其是政治生活。個體知性的運用和自由發展,依賴于民主政治為其提供的多方保障。杜威在《哲學的改造》一書中就認為在民主的眾多意義中,其“道德意義就在于解決這樣一個問題,即一切政治制度和工業制度的最高檢驗標準就是他們有助于每個社會成員的全面發展”[12]987。換句話說,民主政治不僅為個體知性在私人事務和社會事務的運用上提供權利保障,而且追求讓物質發展服務于個體知性在民主政治生活中的自由運用和全面發展。
2.1.3 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是在差異的基礎上通過理智協作尋求認知拓展和決策的過程
在通常的意義上,民主一般被理解為一種政治體制、一種國家政治結構甚或一架政治機器。但杜威認為:“這種理解是不夠的,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13]415這種判斷內含著三個信念:
其一就是關于人性的信念。在杜威看來,一個民主政治共同體中,無論種族、膚色、性別、家庭背景、物質財富或文化水平存在多大的差異,普通人之間應該擁有相互的信任。這種信任不僅應存在于人們潛在的道德認知之中,在可能的情況下還應通過法令來規定這種信念。不僅如此,人性的信念里還包括公民之間是平等的。這里的“平等”,強調的是無論一個人所擁有的外在財富多寡或內在能力大小,他們在處理社會事務時都擁有與他人平等的機會或權利去發揮自己的才能。換句話說,民主生活方式中的人性信念相信每一個人都有能力使自己的生活不受他人的強制,而且人們還有能力相互協作處理好公共事務。
其二就是“人類能夠在具備適當條件下理智地進行判斷和行動這樣一種信念”[13]416。杜威關于人性的信念使人們對普通人的“自由的知性”和理智判斷能力充滿著社會信任;而民主權利又保障著人們的自由研究、自由集合、自由交往以及在前三者中個體能力的自由發揮和觀念的自由表達。在個體對社會的認知中,如果人們由于宗教、政治、事業方面的意見分歧或種族、膚色、財富、文化水平方面的差異而互相歧視、互不寬容時,杜威認為“這是對民主生活方式的背叛。因為任何一種妨礙自由地和充分地交換意見的行為,都會建立起種種壁壘,使人們分裂為不同的派別和宗派,形成敵對的黨派,從而破壞民主的生活方式”[13]416。換言之,他主張人們在面對差異時能夠相互寬容、彼此交流。這樣,人們在共同處理社會事務時進行理性的認知和決策,才具有可能性。杜威有關人的社會信念、權利保障和認知開放等思想,為公民理性認知和決策判斷提供了主體條件保障。此時的“民主信念就其在輿論的形式中進行協商、交流、說服、討論這種作用而言(這種作用歸根到底是能自我校正的),還能是什么呢?”[13]416
其三就是個人“在日常生活中能與別人協力合作這種信念”[13]417。合作源于差異。現實生活中,每個人都是獨特和充滿個性的。因為每個人生活的環境總有其獨特性,而這種獨特性既賦予個體獨特的生活經驗和理性認知,又使它們擁有獨特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獨特的認知和人生追求,必然引發個體之間乃至個體與社會之間的沖突。但在杜威的民主生活方式中,每一次沖突都應該被當作一次進行理智協商和互相學習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權利和機會參與對沖突事務的認知和決策。因為在杜威的視野里,“凡為社會制度所影響的一切人們都必須共同參與在創造和管理這些制度之中”[14]44。而在這種參與過程中,每一個體都要保持認知結構的開放性,將各自對環境的體認即個人經驗,作為相互交流和理性共享的堅實基礎,不僅貢獻出自己的經驗和認知,而且傾聽別人的意見和經驗。杜威將此視為“民主觀念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9]24。經驗和意見的交流,個體“自由的知性”在相互碰撞中進行融合,不僅使個體的生活經驗得以豐富,形成處理該社會事務的共識和對該社會事務全貌性的認識,從而開辟認知新事務和獲得新知識的途徑。在此過程中,杜威反對以強制方式扭曲他人在協作中的意見表達和理性交融,不管這種強制是以武力、投入監獄或送入集中營還是以辱罵、嘲笑、恐嚇的方式出現。
整體而言,當杜威把民主理解為一種生活方式后,民主的基礎就演化為“對人性之能量的信賴,對人的理智,對集中的合作性的經驗之力量的信賴”[9]7。由于人們每天都在感知環境和做理性的思考,因而在杜威的民主視野下針對日常生活和社會事務的協商討論每天都在發生。人們相互交換意見、豐富自我。這幾乎是每個個體每天都要完成的任務。所以,當把民主理解為一種生活方式后,“民主的任務就永遠是要創造一種更加自由、更加合乎人性的經驗,所有的人都分享這種經驗,都對這種經驗做出自己的貢獻”[13]418。社會環境的變遷、公共事務的迭現呼喚著日常民主生活中這種協商討論的連續開展。這樣,民主就成為人們的一種生活常識,更加具有實在性。針對杜威對協商民主的理論貢獻,埃米·古特曼和丹尼斯·湯普森都認為:直到20世紀初,協商才明確地和民主勾連起來,杜威在他的“著作中毫不含糊地聲稱,民主政體需要現代意義上的政治討論”[15]8。
2.2 精英民主理論的反思:參與民主理論的產生奠定了協商民主復興的思想前奏
精英民主理論在現代的廣泛實踐,也逐漸暴露了它的理論缺陷和實踐弊端。20世紀70年代,以卡羅爾·佩特曼為代表的一些學者結合現代民主政治運作的實際狀況對精英民主理論進行了反思。佩特曼認為以選舉競爭為主要特點的精英民主理論及其實踐,引發了兩個方面的問題。其一就是各個政黨及其代表在政治市場上以各種競爭手段爭相謀取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結果造成了部分利益對整體利益的遮蔽和因利益或意見的僵持而引發政治運作的低效率。其二就是“民主理論不再集中關注‘人民’的參與”[2]98。與此相對應,政治精英成為政治活動的主體,選舉動機受著社會精英或政黨的塑造,民眾只能在有限的候選人中間選舉政治領導人。有限政治參與活動及其參與活動的政治低效能,共同滋生了大眾的政治冷漠心理。但是精英民主理論認為少數精英的政治參與才是政治運作的關鍵,而缺乏政治效能的、冷漠的普通民眾卻正好是社會穩定和精英高效工作的主要屏障。這更是加劇了民眾政治冷漠心理的蔓延。政治參與機會的減少和政治冷漠心理的蔓延,最終削弱了公民政治參與的能力,腐蝕了公民政治品質。公民淪為政治生活中的消極者,對公共政治漠不關心,冷眼旁觀。
基于對精英民主理論及其運行弊端進行的理性反思,佩特曼等人提出了參與民主理論。他認為:“全國層次上代議制度的存在不是民主的充分條件,因為要實現所有人最大程度的參與,民主的社會化或‘社會訓練’必須在其他領域中進行。”[2]39換言之,佩特曼主張民眾應以包括選舉競爭在內的多種民主活動方式在各個社會領域中實現廣泛的政治參與。在20世紀70年代出版的《參與和民主理論》一書中,他就詳述了前南斯拉夫在工作領域中所開展的廣泛民主參與。這種廣泛多樣的政治參與對于公民個體和民主社會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對于公民個體而言,廣泛多樣的政治參與會產生兩個方面的效能。其一就是政治教育功能的發揮。它可以全面提高公民的政治技能和改善公民的政治心理。其二則是廣泛多樣的民主參與可以提高公民對周邊環境的理解和掌控能力,進而提升公民的政治效能感。二者相結合,可以消除精英民主理論指導下現代民主政治所形成的消極公民以及他們身上逐漸滋生的非民主態度,可以培育對身邊事務乃至國家事務充滿興趣和信心的具有適當技能的積極公民。積極公民將通過對社會事務的廣泛多樣參與,實現民主自治。
對社會而言,廣泛多樣的民主參與則會產生三個方面的作用。第一,這有助于整合閑散的社會力量。參與本身具有政治整合的功能,因為參與有助于人們接受決策結果。并且,參與的長期開展和自我完善將催生相關制度和機制的產生,最終形成相關社會力量的程序化政治參與機制,不斷地完善社會制度。第二,它將促成一個參與性社會的形成。社會中所有領域的政治體系將通過參與活動得到民主化和社會化,精英的神秘性將逐漸消融,民眾對政治的掌控能力將得到增強。第三,它將改善政治過程中信息輸入與輸出的質量。在參與民主理論中,參與指“在決策過程中的(平等)參加,‘政治平等’指在決定決策結果方面的權力平等,一個完全不同于當代理論對此的界定”[2]39-40。這種平等的政治參與,一方面能為需要決策的公共事務提供理性共識支撐,使政治決策質量更高,輸出具有更高科學性、更具適應性和受到民眾廣泛認同的公共政策;另一方面,參與各方特殊經驗的共享和相互之間的理性辯駁,也將使參與主體的認識結構得以完善、社會能力和民主技能獲得提升。兩方面良性循環,將不斷地改善政治系統輸出的政策質量、豐富參與主體的政治知識和提升它們的政治技能。
在佩特曼等人的理論視野中,參與民主理論不是一個僵化或終極的民主理論。它“能夠被吸收進入當代民主理論的一般框架內,如果有一種穩定民主理論存在著比目前的民主理論具有更為堅實的基礎的話”[2]99。換言之,雖然佩特曼發現了精英民主理論和實踐的諸多缺陷,提出以廣泛多元的民主參與來對此進行彌補,但是他還沒有發掘出與選舉競爭民主相對應而又能適應當代民主政治發展要求的民主形式,所以他認為參與民主理論只是提出了一個理論命題,還需要其他人來破題,完善這一理論。國內學者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在評價參與民主和當代復興的協商民主理論時,有學者認為:“參與民主理論在20世紀后期的重要發展,是‘協商民主’理論的興起。”[2]11這樣,參與民主理論構成了協商民主當代復興的理論前奏。
3 結語
進入20世紀,西方在近代選舉代議民主多元實踐和理性探索的基礎上,進一步形成了內容日趨完善的精英民主理論和運作日益程序化的選舉競爭式民主。但是,精英民主理論的弊端和選舉競爭民主的負面政治效應,也不斷激起人們對于民主的理性反思和實踐開拓。杜威在反思西方民主的基礎上,從政治哲學的角度為協商民主的現代發展作了主體建構,提出作為“自由的知性”主體應該以理智協作的方式、爭辯討論說服的民主方法開展民主生活。佩特曼在反思代議民主的基礎上,認為民主應該在更為廣泛的社會空間以更為多樣的民主形式獲得展開,建設一個參與式的民主社會。合作主義的現代理論和社會實踐,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從思想方面消融了選舉競爭式民主可能帶來的社會對抗思維,而且以協商的方式促成了多元社會力量的民主妥協和內部自治。正是在反思精英民主理論和選舉競爭民主基礎上的這些不懈探索,為協商民主在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復興和政治探索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對于協商民主在后發國家中的探索,這種分析具有一定的歷史定位和建構發展方面的參考價值。
參考文獻:
[1]約翰·鄧恩.民主的歷程[M].林猛,等,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2]卡羅爾·佩特曼.參與和民主理論[M].陳堯,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
[3]赫爾德.民主的模式[M].燕繼榮,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4]朱庭光.法西斯新論[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1.
[5]張靜.法團主義[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6]戴維·米勒,韋農·波格丹諾.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M].鄧正來,等,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7]袁剛,等.民治主義與現代社會:杜威在華講演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8]John Dewey.Philosophy and Civilization[M].Minton:Black&Company,1931.
[9]杜威.新舊個人主義——杜威文選[M].孫有中,等,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
[10]豬口孝,愛德華·紐曼,約翰·基恩.變動中的民主[M].林猛,等,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11]李日晨.杜威小傳[M].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
[12]列奧·施特勞斯,約瑟夫·克羅波西.政治哲學史(下)[M].李天然,等,譯.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13]涂紀亮.杜威文選[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14]杜威.人的問題[M].傅統先,邱椿,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15]談火生,等.審議民主[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