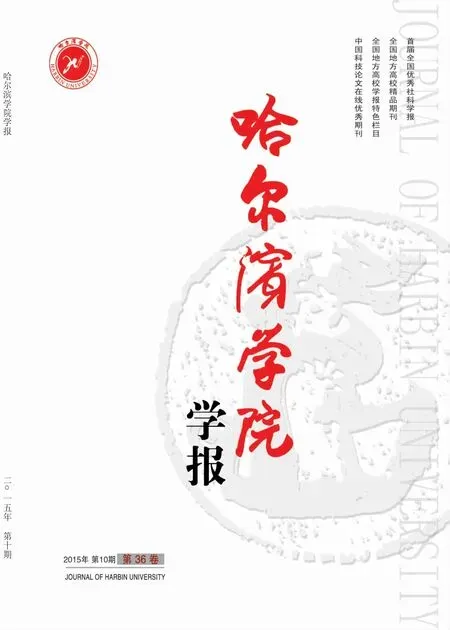《耶穌之子》中的信仰重塑——美國戰后頹靡青年的罪惡之源與救贖之路
《耶穌之子》中的信仰重塑——美國戰后頹靡青年的罪惡之源與救贖之路
豐俊超
(哈爾濱理工大學 外國語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150080)
[摘要]丹尼斯·約翰遜在其《耶穌之子》里埋藏下一條內在的基督教主線和與之相對應的節點,即“知罪、渴望重生和自律”。小說集探討了美國戰后青年人的罪惡之源和救贖之路,揭示出作者對戰后缺失精神信仰青年一代的人文關懷,以及對人生價值深層含義的倫理道德判斷。作品表現了現實的殘酷和怪誕,存在的虛無和痛苦,反映了作者對人類生存狀況的深刻憂患意識,諷喻了美國社會陷入“道德危機”背后的根源。
[關鍵詞]丹尼斯·約翰遜;救贖觀;精神探索;倫理價值
[中圖分類號]I072.074
[收稿日期]2014-11-19
[作者簡介]孫梓偎(1992-),女,黑龍江牡丹江人,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戲劇戲曲文學創作理論研究。
[文章編號]1004—5856(2015)10—0096—04
《耶穌之子》是被哈羅德·布魯姆選入西方正典的經典短篇小說集,但其作者丹尼斯·約翰遜,因其一向深居簡出、低調寡言,并不廣為中國讀者而熟知。約翰遜的作品中糅合類型小說的元素,具有深厚的精神價值以及犀利的思想鋒芒,頗受美國諸多名家的欣賞。在二十多年的創作生涯里,真正令他聲名鵲起的作品是1992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耶穌之子》。約翰遜以獨特的表現手法和藝術特色描繪了一個荒誕的世界。這個荒謬是對存在的解釋:社會中存在著使人“非人”的因素,“荒謬”是人類對這些因素的極端厭惡和不適應,從而證明了人的存在。[1]小說中人物的異化在嚴峻的社會動蕩和心理危機面前作出強烈的反應。小說集標題取自地下絲絨樂隊《海洛因》里的一句歌詞:
當我將針頭插入血管里
我會告訴你,一切都變得不一般
當我在興奮的奔跑時
我覺得自己就像是耶穌之子
借此,丹尼斯·約翰遜表達出他眼中作家的“道德觀”與現實的關系:作為一名作家,最重要的道德觀是盡量要寫得確切,要講述作家所知道的真實。在這漫長的歲月里,約翰遜也如敘事者“我”一樣在現實世界中進行人生價值的道德訴求,尋找自我救贖的出口。
然而,這部構思奇特、語言優美的小說集,并未引起足夠關注。至今中國國內除了散見的書評,尚未見到針對這部小說集的學術性研究論文。國外研究中,目前僅見兩篇針對作品進行主題解讀的文章:一篇題為《耶穌之子之天國降臨》;另一篇名為《耶穌之子中的豬巷和路加福音》。約翰遜的作品未能在國內引起廣泛關注的原因可能主要有兩點:其一,被譽為“骯臟現實主義”的《耶穌之子》,處于邊緣的文學作品難入國內研究的主流,其極簡的文字蘊含深層的道德倫理及宗教寓意,令國內的研究者望而生畏;其二,較為混亂的后現代敘述風格,映射出美國“垮掉一代”青年的精神狀態,讓讀者擁有恰當的難解之狀。《耶穌之子》之所以讓讀者感到艱澀虛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埋伏在小說里的故事本體和表達層面的“罪惡和救贖”所引起的。約翰遜在小說集的大部分故事中,都提及到上帝和圣經的典故,實則是影射當時美國社會的混亂與荒誕。由此可以看出約翰遜要尋找的真理是生命悲劇的原因和生命的意義所在。
因此,本文從基督教“救贖觀”的研究視角入手,找出約翰遜埋藏在小說集中的一條內在的宗教信仰主線,即“知罪、渴望重生和自律”,小說集各個片段在這條基督教主線上均有與之相對應的節點。約翰遜從極簡的文字方式刻畫戰后缺失精神信仰青年一代的生活狀態,揭示對這些邊緣人物的人文關懷,以及對人生價值深層含義的倫理道德判斷,進而諷喻了美國社會陷入“道德危機”背后的根源。同時,作者對《耶穌之子》做出道德倫理判斷,表現出現實的殘酷和怪誕,存在的虛無和痛苦,反映了作者對戰爭后人類生存狀況的深刻憂患意識,也諷喻了作者置身其中的“道德危機”的當代社會。
一、《耶穌之子》的罪惡之源
約翰遜寫作的終極目的是將人類精神救贖的希望放在了自己對宗教理解的視野當中。他以基督教的救贖觀和自我的道德訴求對世界進行觀察和研究,并以自傳的敘述方式進行指涉,表現出對美國社會非同尋常的透視力。傳統基督教認為,人類出生即有罪,又無法自救,于是上帝派遣其獨生子耶穌降世人間,為人類的罪代受死亡,流出鮮血,以贖人類的原罪。自中世紀以來,宗教一方面是為頌揚對上帝的信仰;另一方面是以規范人的行為為目的的。[2]遵照“救贖觀”這一教義,人須救己于道德的過錯。基督教思想家托馬斯·阿奎那曾將救贖闡釋為對人類罪惡的克服。約翰遜力圖透過當時社會這面鏡子,借助宗教思想探索來揭示人類生活的罪惡之源。
在《耶穌之子》中,“我”以及無名的美國青年在“毒癮之惡”的誘惑下,尋求抗拒“惡”的救贖之路。根據11個短故事,我們發現約翰遜筆下的“惡源”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源自于美國青年士兵戰后生活的空虛和失落,人們能否克服未來道德罪惡的問題所涉及的是個人的意志問題,是人明知故犯的問題;其二,源自于美國進入了工業化時代,環境遭到極度破壞而導致“美國夢”的破滅。這兩種惡源與美國當時的社會環境有極大的關系。其實,約翰遜是借助上帝的力量,闡釋人類自由意志的可塑性。按照基督教教義,人有自由意志,也就是說人可以控制他的意志;同樣,按照基督教教義,上帝是全能的,既然人的意志出了問題,上帝應該能做出全能的修整,能以其無限的能力使人意愿其所應意愿者。[3]
一方面,小說集中的“我”與那些無名的美國青年如“旅館”杰克、斯坦、“咚咚”等,生活漫無目的,深刻地感受著生活的空虛與失落。他們與上帝的關系有兩類障礙:其一,曾做過見不得人的、恥于讓朋友和父母知道的事——吸毒、亂性、勸女友墮胎、追殺和偷竊等;其二,傾向于作惡且一再作惡。這就是世界上為什么沒有一種文化,沒有一個時代,沒有一個政府曾成功地根除過人類自己造成的苦難。按照救贖的教義,基督的受難和死亡能同時從兩方面解決人類惡的問題。因此,《耶穌之子》中的“我”在“戒毒”過程中相當于耶穌的受難解決了自我之“惡”,作品中的人物“旅館”杰克、斯坦、“咚咚”等在死亡中解決了他們的“惡”。
另一方面,小說集著重描述了美國進入工業化社會后的荒蕪景象,體現出人們遭受著自然荒蕪和精神荒蕪的美國社會環境。在《咚咚》的結尾處,“感覺就像救世主降世前那一刻。可惜救世主雖說要來,但我們還得等很長時間。”[4](P36)他們像基督教徒一樣,渴望在自然荒蕪和精神荒蕪的世界中等待重生。約翰遜對“為何救世主到來的時間會如此長”進行剖析,其原因是,“近些年旱得厲害,平原上空掛著青銅色的塵霧”,[4](P36)呈現一片荒原景象,“種植的大豆又死了,沒有長成的枯萎豆桿倒在地上,活像成排的女人內褲。大部分農民根本不在這一帶種莊稼了。虛假的夢幻都已破滅”。[4](P36)誠然,造成這種荒蕪景象的“惡根”是:20世紀中后葉,尤其是戰后的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起從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過渡到壟斷資本主義。由于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根本矛盾,美國社會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面對經濟危機及其引發的各種社會問題。此外,壟斷資本主義還導致了“物欲橫流”的社會風氣。許多人在紙醉金迷中陶醉,在陶醉中踐踏社會生活應有的精神價值。社會價值觀念體系的“失效”必然導致道德這一社會調控手段的“無能”,因此,美國在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之后陷入了“道德危機”,表現為社會道德風尚的淪落。在道德危機的條件下,美國人對道德普遍存在一種“恐懼感”。他們厭惡道德,憎惡道德,逃避道德。對于他們來說,沒有道德約束的生活顯得更加現實,更加可靠。
二、《耶穌之子》的救贖之路
《耶穌之子》埋伏了一條知罪、渴望重生和自律的救贖主線,以體現現代社會當人們面臨“道德危機”而無法擺脫困境時,尋求“自我救贖”之路,揭露世界的荒謬和無序對人心造成的影響。首先,在《保釋出獄》中,“我”相信上帝通過救贖做成了“我”不能直接去做的事。“大體而言,我離琢磨生命意義最近的時候,也不過是在想我肯定是某個惡作劇的受害者。我們沒有摸過神秘人的衣裳穗繸子①……我確信我之所以還活在世上,是因為我忍受不了其他的地方。”[4](P29)約翰遜在此消解了西方傳統的悲劇描寫模式,“我”在吸毒過量后瀕臨死亡時探尋救贖的方式,沒有能摸到耶穌衣裳繸子,暗示“我”沒能找到戒毒成功的方式。約翰遜這種轉而沖向后現代的軌道描寫,超越常人的思維,將宗教的救贖進行荒誕的處理,將苦難與玩笑并置,讓“我”像小丑一樣,表現出滑稽可笑的一面,以病態的幽默現實呈現出“我”和“旅館”杰克對生活的茫然,對自我意志的放縱,以及對現代生存的絕望情緒,突出“我”在基督教主線上“知罪”的這一節點。
其次,《搭車遇禍》《咚咚》《歡快時刻》《工作》和《急救》這些片斷讓我們看到基督教主線上“渴望重生”這一節點。約翰遜描述的每一個人無一不是面臨“道德危機”的典型例子——生活在戰后的美國,他們懷疑一切價值,認為人進入這個世界就是被拋入一種無意義、荒謬的存在狀態,因此正如都是孤獨的、絕望的被遺棄者,他們生活在一個充滿毒癮、迷失、沒有信仰和不確定支配的世界里,意識到“惡”帶給他們的重創,渴望重生。約翰遜巧妙地在《歡樂時刻》里的描述形如復活節彩蛋②的“迷幻蘑菇”帶給“我”的歡快時刻就是重生之時。同時,“我”在渴望重生這一節點上進行了自我深刻的倫理道德反思。這一針見血地道出現代道德觀念體系中信念倫理的極度缺乏。
此外,人類世俗社會的倫理道德、精神創造、公正秩序、理想追求,無不具有宗教般的神圣性,引導個人生活和社會秩序朝著健康向上的方向發展。就像《工作》中他們有了錢,有了男人勞作過的感覺,和前面提到的“平日我們總有負罪感,提心吊膽的,因為我們有地方不對勁”[4](P46)形成了“工作重生”與“吸毒之惡”的鮮明對比,體會到道德秩序健康向上帶給人們內心的平靜與踏實。因此,重建生活信念和價值理想已經是現代道德擺脫困境,能夠真正承諾自身文化使命的出路之一。《急救》中,約翰遜借用基督教中的復活節兔的典故,描繪那幾只粘糊糊的微型兔寶寶,象征了春天的復蘇和新生命的誕生,因為兔子是愛神阿佛洛狄忒的寵物,也是日耳曼土地女神霍爾塔的執燭引路者。約翰遜給讀者的靈魂敲響警鐘,人們向上的精神追求在整個社會都崇拜金錢萬能、物質享受中失效,因為世俗的單調和乏味將他們驅趕出健康的精神家園。由此可見,宗教所特有的信念體系和由此出發所提出的現代社會批判,正是現代道德所缺少和亟需的。
最后,《西雅圖綜合醫院一雙平穩的手》和《貝弗利修養所》的“我”完成了基督教主線上自律這一節點——踏上自我救贖之路。《西雅圖綜合醫院一雙平穩的手》中的“我”在配合醫生給予的戒毒治療,“我每個月都愿意來這住兩周”。[4](P94)就像《快樂時刻》那段描述一樣:“陽光貓著腰鉆出云脊,引燃海洋,熔金般的光線填滿了大觀景窗,我們于是在燦爛光霧中進食做夢……但沒有什么會得到治愈,鏡子是把刀,分開萬物及其本體,虛假的伙伴情誼惹出眼淚,濺到吧臺上。”[4](P86)鏡子在這里是個隱喻的象征,實則將“我”的“過去”和“現在”分割開來。“我”曾在荒蕪的世界里震顫迷失,用鏡子斬斷過去的“我”如今可以擁有一雙平穩的手為自己剃須,實則暗示“我”在“自律”的自我救贖之旅上,洗心革面,掙脫虛無的精神世界,找尋意義的存在,并且,這雙平穩的手還可以幫助其他人剃須,意味著“我”像耶穌一樣,幫助他人一起尋找重生后的生活意義。
《貝弗利休養院》的“我”星期四晚上通常去圣公會教堂地下室參加匿名戒酒會活動,這種積極的“自律”使我成為耶穌之子,成為耶穌精神的繼承者,[5]像耶穌一樣將愛播撒給世人,幫助休養所那些喪失行動能力的人們。“我”以邊緣人的視角偷窺一個普通幸福之家,這個普通家庭的簡單、純凈、節制——純潔地像祭臺上的犧牲品——使“我”百感交集,讀者通過“我”的視角體驗到日常生活中令人震撼的美。所以,似乎可以這樣診斷,在這部關于道德熵壓縮的經典里,作者宣判耶穌之子只經受“苦路”十一處,[6]最終完成自我“救贖”。約翰遜認為在荒誕不經的世界里,“自律”是人們唯一能最終找到救贖的方式和手段,要求人們超越自己,超越現實,以便更清醒地認識世界,揭示荒謬。
三、《耶穌之子》的道德倫理判斷
約翰遜通過每一個故事發掘深層人生價值的道德訴求。這個集子里的故事充滿了極致的悖論,“罪惡”和“救贖”二者本身就充斥著矛盾,然而,約翰遜通過“縱欲”“自甘沉淪的罪過”“現實的地獄”“地獄似的荒原”“末日審判”“耶穌的繸子”“基督的胸膛”“復活節彩蛋”和“救世主降世”等的描述,體現出人類“知罪”“渴望重生”和“救贖”的宗教內涵。約翰遜將各宗教內涵聯結成一條基督教的救贖主線,他認為這是面臨“道德信仰危機”的人得到救贖的必經之路。
在世界社會文化中,宗教是一種與人們的價值密切相關的意識形態,更是扮演著維護道德秩序的重要角色。在物欲橫流的世界,人們面對各種誘惑和挑戰,對于宗教的崇拜和敬畏不斷喪失,這直接導致在宗教信仰下人們應有的行為模式或道德情操難以維系。因此,《耶穌之子》中的人物在逆境或者不滿中將迸發出相對以往更大的邪惡力量。“我”在靈魂救贖之旅中,沒有能力構建“結構勻稱”的故事,甚至沒有辦法直截了當地講述他生活中的真實事件,總要活靈活現地附帶上他的那些機能失調行為。[5]雖然,約翰遜采用一種錯亂無序,近似囈語般的敘事語言,讓那個不清醒的世界圖景躍然紙上,但是它的真切不在于讓讀者感到確實可信,而是有一股魔力裹挾著讀者,將其吸入那意識混沌的黑洞,即喪失道德信仰的黑洞。[7]
丹尼斯·約翰遜是個負責任的創作者,他既不愿意為某種特殊道德原則提供辯護,也不愿告訴人們什么是善、什么是惡、什么是對、什么是錯。這與元倫理學家斯蒂文森的情感主義倫理學主旨有不謀而合之處:情感意義在產生道德命令力量方面不僅發揮著描述的功能,而且具有能動和命令的功能。[8](P222)《耶穌之子》中像荷馬史詩里那些半人半神的反英雄人物,激起讀者對道德判斷情感意義的思考;讀者通過閱讀體驗那些無名青年在義無反顧地追求“墮落”的道路上所遭遇放逐、囚禁、刺瞎、毀滅的命運,對事實的道德做判斷,以此來面對自我道德態度的問題。由于戰后的美國道德價值被模糊化、邊緣化,人們的道德生活也因此而變成了一種沒有價值導向的生活,整個社會仿佛陷入了一種無道德的狀態。因此,作品的敘述去除一切不必要的裝飾和技巧,以呈現出內容最接近本質的純粹和精華,背后卻包含著深層復雜的思考及精準的描述。
《搭車遇禍》中“我”經歷了生死考驗,“灰色大腦”的云朵盤旋在“我”的上空,吃了安非他命的“我”實則隱喻人類陷入一個無價值的“深淵”——嚴重缺乏秩序和道德信仰的世界。然而,當“我”注意到“醫生領她進了走廊盡頭有辦公桌的房間”,[4](P7)“門底下的縫隙射出一橫條燦爛的強光,好似鉆石正被億度高溫焚成灰燼。多么驚人的兩個肺啊!”[4](P7)當“我”聽到她尖叫起來像我想象中的鷹隼。那一刻讓“我”感受到“能活著聽見這聲音可真是謝天謝地!我曾為了尋找這種感覺而東奔西走”。[4](P7)讀者在這種混亂無序和不確定中,必須與文本的敘述者一起思考,一起游戲。這種“非結構勻稱”的敘述也在揭示著世界的本質——無序性,著意揭露世界的荒謬,突出荒誕世界中人類生存的艱難。
此外,《耶穌之子》里的人物則多來自于底層社會,在對抗精神焦慮方面,他們更務實,他們更樂于采用難以解釋的冒險行動。在約翰遜的故事里既呈現年輕人的勇氣、欲望和荒唐,也漫布著中年人的世故和滄桑。就像約翰遜自己說的,寫出了一個雙重的幻境的救贖里程。這與中國古代的圣賢荀子的思想不謀而合:“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不善在身,緇然必以自惡也”。對不好的品行,一定要憂懼地加以自我反省;如果不好的品行在身,一定要像被玷污一樣厭惡它。為了達到真正關懷“生命”的目的,約翰遜擅長于故事以熱血開頭,結局卻冷如高懸于冥河之上的月亮。讓讀者看到道德原則將變成人們生活中的“德行”,并引導人們追求健康意識、整體觀念和安全思想。約翰遜從宗教倫理的視角探究人生存的道德價值和道德意義,認為人類目前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解決以物質主義、工業主義、壟斷資本主義為根本特征的精神危機。
四、結論
通過對《耶穌之子》的研讀,可以發現盡管約翰遜的思想呈現出明顯的反體系性和碎片化特征,發現罪惡和救贖不僅讓敘述者“我”對人生價值的道德把握若即若離,同時也讓讀者在閱讀文本時永遠居于多義性帶來的不確定之中。約翰遜追求的終極目標是人的救贖,即如何在一個工具理性肆虐的發達資本主義時代昭示出人得以獲救的路徑,這是潛藏在《耶穌之子》著述下的隱秘線索。《耶穌之子》將宗教的超驗之維引入哲學思考,約翰遜所描寫的“罪惡和救贖”能夠超越學科和意識形態的分歧,并持久激發人們的興趣。
注釋:
①典出《圣經·新約》馬太、馬可和路加福音,有人摸到耶穌的衣裳繸子,病立刻就好了。
②復活節是紀念耶穌死后三天復活的基督教傳統節日,蛋的原始象征意義是為“春天—新生命的開始”,基督徒則用復活節彩蛋來象征“耶穌復活,走出石墓”。
[參考文獻]
[1]汪小玲.美國黑色幽默小說研究[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
[2]杜雋.論《羅摩拉》中道德問題的現實意義[J].外國文學研究,2011,(5).
[3]洪增流.美國文學中上帝形象的演變[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4]丹尼斯·約翰遜.姚向輝.耶穌之子[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
[5]Timothy L.Parrish.Denis Johnson’s Jesus’ Son:To Kingdom Come[J].Critique: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2001,(1).
[6]〔美〕詹姆斯·麥克馬納斯,仲召明.通向戒癮診所之路[J].書城,2012,(11).
[7]晏玉榮,李文婷.弗洛姆的道德選擇心理理論[J].哈爾濱學院學報,2010,(10).
[8]向玉喬.人生價值的道德訴求——美國倫理思潮的流變[M].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責任編輯:張慶
Reshaping Belief in “Jesus’ Son”
——The Original Sin and Salvation for American Post-war Youths
FENG Jun-chao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arbin 150080,China)
Abstract:Dennis Johnson made a node for the main plot of Christianity and its correspondence,that is,“confession,eagerness to rebirth and self-discipline”. The novel is mainly about the origin sin and way of salvation of American post-war youths,which reveals the author’s humanistic concern for the generation who are lack of belief,ethical-moral judgment on the deep value of life. The cruelty and absurdity of reality is expressed in the story. Nihility and pain of the existence reflects the author’s anxiety for people’s living condition,which reveals the root of “moral crisis” in the American society with a satirical metaphor.
Key words:Denis Johnson;salvation;spiritual exploration;ethical 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