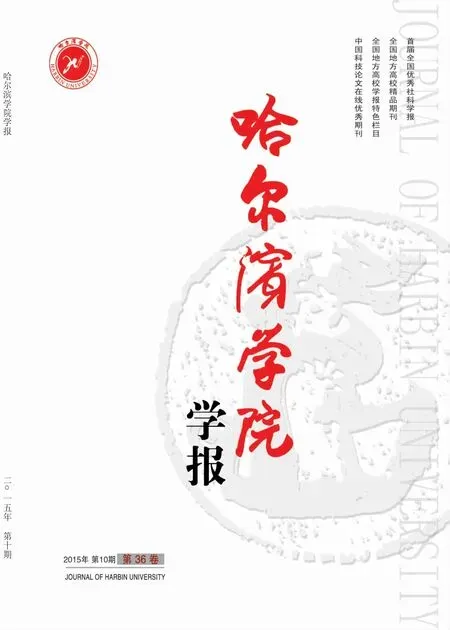“可然”與“必然”——從《詩學》視角讀《源泉》
“可然”與“必然”——從《詩學》視角讀《源泉》
楊伶俐
(揚州大學 外國語學院,江蘇 揚州225009)
[摘要]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探討了一系列的理論問題,如藝術摹仿、情節組合、詩和歷史異同等;安·蘭德思想中關于理想和客觀的部分來自于亞里士多德詩學中的理念。基于這點,文章試從“可然”與“必然”之原則、情節的可然與必然、沖突的可然與必然、普遍與特殊的可然與必然以及人物性格的可然與必然等幾方面分析《詩學》如何影響《源泉》的創作。
[關鍵詞]《詩學》;《源泉》;“可然”與“必然”
[中圖分類號]I106.4
[收稿日期]2014-11-23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資助項目,項目編號:14YJC752035。
[作者簡介]豐俊超(1982-),女,哈爾濱人,講師,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美國文學、文藝評論研究。
[文章編號]1004—5856(2015)10—0091—05
亞里士多德的《詩學》被視為西方第一部系統的文藝理論作品,“可然”與“必然”是亞里士多德美學思想中一個重要的理論命題。這一命題體現在其《政治學》中的觀點之一為“主治的人們永不更替”。[1]安·蘭德(Ayn Rand,1905-1982)是20世紀美國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其“客觀主義”哲學在世界范圍都有廣泛影響。她于20世紀90年代進入中國讀者的視野,其主要貢獻是提出自我主義人生觀,提倡一種理性的利己主義,即創造是自我的事情,不需要得到也無須期待他人的認同,她提倡的自私自利概念往往被人誤解而引起爭議。《源泉》出版于1943年,其主題為“個人主義對抗集體主義,并非在政治意義上,而是在人的靈魂深處”。[2](P80)在1945年寫給《源泉》讀者的信中,安·蘭德如是說:
“我九歲時立志成為作家,那是經過思考后的決定,我依舊記得那一天的那個時刻。我并非從嘗試寫鄰人開始,我想寫的是鄰人永遠不會做的事。我對‘人之為人’興致不高,但我腦海中印有一副‘人能為人’的醒目畫面。這一志向從未改變,但我花數年時間思考一個問題,即小說創作完全屬于個人意愿,不必在意他人看法,后來,我發現自己的思想受惠于亞里士多德,他說過小說比歷史更富哲學意義,因為歷史記錄已經發生的事,而小說描述可能發生的事。《源泉》便是一例。”[3](P669-670)
那么,安·蘭德創作《源泉》時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亞里士多德的啟發呢?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寫道:“詩人的職責不在于描述已經發生的事情,而在于描述可能發生的事,然后根據可然或必然的原則發生的事情……”[4](P81)從“可然”到“必然”,安·蘭德誤引了亞里士多德嗎?字面上看或許如此,但她充分理解了亞里士多德《詩學》中“可然”的含義。本文試從“可然”與“必然”之原則、情節的可然與必然、沖突的可然與必然、普遍與特殊的可然與必然以及人物性格的可然與必然等幾方面分析《詩學》如何啟發了《源泉》的創作。
一、“可然”與“必然”之原則
亞里士多德認為詩人描述“可能”的事件不僅僅意味著作品中虛構的事件,同時也包含歷史事件,“可能發生之事是可信的;我們不相信從未發生過的事是可能的,但已經發生之事則顯然是可能的,否則他們就不會發生”。[4](P81)這里就引出了“可然”與“必然”的討論。亞里士多德“可然”與“必然”的原則也體現在人物性格和故事情節中,“刻畫性格,就像組合事件一樣,必須始終求其符合必然或可然的原則。這樣,才能使某一類人按必然或可然的原則說某一類話或做某一類事,才能使事件的承繼符合必然或可然的原則”。[4](P112)同時,事件“應出自情節本身的結構,方能表明它們是前事的必然或可然的結果”。[4](P88)
性格與情節是文學作品事件中不可缺少、密不可分的兩部分。首先,亞里士多德的性格概念以道德為核心,關于性格刻畫,應做到“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性格應該好,言論或行動若能顯示人的抉擇,即能表現性格。所以,如果抉擇是好的,也就表明性格亦是好的”。[4](P112)其次,離開某種情景并不能說明人物的道德品格會導致其具體行為,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并未詳細解釋這一點。舉個例子,安·蘭德的道德哲學里,效率是種美德,如種植馬鈴薯是件有成效的事,但這并不意味著有美德的人都會種馬鈴薯,這里的效率是對無數具體事物進行抽象后的概念,有美德的人會選擇某種帶來成效的行為,但具體行為取決于情境,如其價值觀、知識構成以及所處環境等。
安·蘭德將道德理想的描寫作為其最終文學目標,她的創作目的是表現一個理想人物,因此,她界定了造就理想人物存在所需要的條件,“既然人的性格就是環境的產物,我必須界定和表現造就理想人物并驅動他行為的環境和價值觀”。[5](P6)
為了證明一個人的某個特定行為遵循著其道德性格,首先必須了解其道德源起的情境,而這一情境則貫穿著小說的整個事件。這樣,小說作者在敘述事件的過程中便可自然地將道德元素滲透其中。如果人物道德性格是正面的,事件的結果便體現了“可然”與“必然”的原則。《源泉》中的中心事件便是主人公霍華德·洛克炸毀科特蘭德大廈,洛克最顯著的性格便是獨立與正直,他不遵循陳規,認為世上沒有權威,能依賴的唯有自身的獨立判斷,并為其創造性工作的完整性同各種社會反對力量抗爭。用他自己的話說“唯一重要的是,我的目的,我的獎賞,我的開端,我的結局都是工作本身。我的工作按照我的方式來做。”[5](P747)
但一個獨立正直的人未必會炸毀政府的居家工程,而洛克的行為是在小說的一系列事件中遵循了人物性格。首先,洛克設計了科特蘭德大廈,政府答應原原本本按其設計方案施工,但兩名二手貨①建筑師高登·L·普利斯特和古斯·韋伯將設計方案改得面目全非。如果洛克不采取措施,改動方案后建成的大廈便永遠矗立在那兒,但洛克的成果遭到褻瀆,對于一個獨立正直的人來說情何以堪,他不能控訴政府,唯一能做出的反擊便是摧毀那個龐然大物。如果事先情況完全相反,如果沒有違反合同,洛克或許采取不同方法,先前他不是沒有摧毀斯考德神廟嗎?如果洛克不具有那種特立獨行的性格,如果他是彼得·吉丁,他的行為也會完全不一樣。
沒有離開情境的人物性格,也沒有脫離人物性格的情境。洛克的行為是一種符合邏輯而非確定性的必然之可然,亞里士多德“必然”一詞無宿命論色彩,安·蘭德刻畫的霍華德·洛克也不是相信宿命論的人物,他顯示的是一種更純粹的存在,不是一種“必然”,而是“可然”,他并非必須炸毀科特蘭德大廈,但他堅守自己的建筑信仰,現實與信仰的沖突促使其為之。
二、沖突的必然與可然
小說人物性格受先前事件情境影響,但并非所有的先前事件都能構成必然的情境。對洛克來說,設計科特蘭德大廈是一項艱巨且讓人筋疲力盡的工程。工程竣工后,他度了長達數月的假期,這一行為合情合理,因為在科特蘭德大廈工程之前,洛克已忘我工作若干年,需要靜養一番。但休假并非出于人物性格或先前事件之必然,如果小說中未提及休假事宜,讀者也不會意識到其中的缺失。這一小插曲并非不具有典型意義,它代表了人類行為的普遍模式,即人類行為并非由孤立的事件,而是由人的價值觀、知識構成以及環境組成的大情境推動的,而大情境又離不開小細節。安·蘭德如此描述洛克的休假事宜,“接下來的幾個月,事務所里也沒有多少活要求洛克在場。他目前的工作已經完成了,兩個新的項目要等春天才開工。”[5](P778)這是大情境中相關的部分情境,邏輯上也不足以使休假成為必然,而我們所獲得的信息是洛克終于得以休閑。
這讓我們想到另一原則,作者為了讓人物行為遵循其性格發展必須將先前事件部分融入后發事件的相關情境,典型手法體現為對人物的基本價值觀發起挑戰。設想有人試圖爬向一座休眠火山,離開情境,我們難以猜測他此舉的原因;但如果火山爆發,熔巖向他襲來,他一定轉身逃離,原因所在是因為他的生命受到威脅。同樣,我們可以解釋洛克炸毀科特蘭德大廈一舉。別人擅自改動他的設計方案是對洛克自我價值觀的最殘酷挑戰,唯有將其摧毀才能符合這一人物性格。洛克對政府的安居工程雖然不屑,但他喜歡這一項目,因為他想讓它真實、鮮活并發揮作用。他捍衛自己的設計,因為在他看來那是一種純粹的思想,沒有人能夠改變或觸及,他想看見大廈嚴格按他設計的樣子修建。
女主人公多米尼克同樣面臨著個人價值觀受到挑戰的情形。她是一個熱情洋溢的理想主義者,她相信絕大多數男人道德敗壞,有真實價值的人容易受到敵意攻擊。在生活中,多米尼克并不遵循嚴肅價值觀,這使她能夠自我防護并保持內心平靜、傲慢不恭。但她愛上了洛克,當她認識到洛克是個建筑天才時,她認為洛克難逃一劫,同時她的價值觀念受到威脅,來自洛克的威脅。她對此威脅作出反擊的唯一方式是隨時尋找機會阻礙洛克的事業,從而減輕外界對他的攻擊。多米尼克所做的一切看似對洛克的千般阻撓,實質是出于愛情而予以洛克的保護傘。
可以看出,故事情節發展過程中充滿各種沖突,最終導致某種“必然”,多米尼克與社會以及洛克間的沖突,洛克與高登·L·普利斯特和古斯·韋伯以及政府間的沖突等,在上述隱喻中,爬山者與熔巖的沖突,都體現了沖突在小說中推動事件發展的角色。但現實生活中沖突卻不受歡迎,人們可以從小說中審視現實生活可避免的沖突環節,從而領悟“可然”與“必然”間的普遍又特殊的微妙關系。
三、普遍與特殊的可然與必然
亞里士多德在《詩學》第九章中寫到,“詩是一種比歷史更富哲學性、更嚴肅的藝術,因為詩傾向于表現帶有普遍性的事,而歷史傾向于記載具體事情。所謂‘帶普遍的事’,指根據可然或必然的原則,某一類人可能會說的話或會做的事。”[4](P81)
詩歌或小說如何比歷史更能表達普遍性?《源泉》中,洛克炸毀大廈一事使抽象事物具體化,即其獨立耿直的性格驅使。一位優秀的歷史學家并非簡單羅列歷史事實,而會進行客觀評價,如有歷史學家評論說,喬治·華盛頓的勇氣以及其對共和國的忠誠使得他成為優秀的政治家。小說事件同時又不僅僅將抽象事件具體化,如前文提及種植馬鈴薯一例,這是美德的一種具體體現,但并不意味著有美德的人都去種馬鈴薯。人們追求效率的方案及其多元,而具體的選擇很大程度取決于情境。反之,種植馬鈴薯的人并非都是有德行的,或許他只是繼承了家業的因循守舊者,不得已而為之。但設想一個人被困在人跡罕至的沙漠里,唯一可食的僅有馬鈴薯,這種境況下,種植馬鈴薯便成為眾多普遍選擇中的特殊選擇。荒島上魯濱遜的行為似乎和其價值觀格格不入,因為他面臨的是惡劣的生存環境,為了生存而野人般求生。同樣道理,面對熔巖的襲來,攀爬火山的人若想活命只能選擇轉身逃離,洛克想維護自己作品的完整性只能選擇破壞。所有這些特殊事件都體現了具體情境下的必然與可然。
我們可以看出為什么小說傾向于表現帶有普遍性的事,而歷史傾向于記載具體事情,因為小說的具體事件在特性情境下體現了普遍與特殊的統一。以道德為核心的人物刻畫將“可然”置于各種抽象的具體化中,小說作品并非純粹關于道德的說教,讀者期待的是具體情境下的可然。可以存活下來的小說所論述的不是日常的平凡瑣事,而是闡釋永恒的、普遍的問題以及人類存在的價值,不是忠實的記載或逼真的描繪,而是進行創作或將思想情感加以形象化和具體化。用亞里士多德的話概括,它所涉及的不是事物實際的狀態,而是事物可能的或應該所具有的狀態。當人物說話或做事符合他們所屬的性格類型時,也就合乎必然與可然之定律,具有了典型的普遍性。
四、人物性格的可然與必然
小說中被具體化的人物性格及價值觀往往有其現實性與社會性,那些認為《源泉》沒能體現“何為應該”的讀者往往忽視這一點,即主人公生活在一個充滿敵意的社會里。主人公價值觀奠定了小說的基調,洛克的獨立與正直是被升華了的道德抽象,同時人物性格刻畫似乎有含糊的一面。如,小說結尾,多米尼克意識到自己世界觀發生改變,她開始相信善有善報,她仿佛聽見一個聲音,“堅持到最后,那就是勝利,對于那些應該取勝,那種推動著世界前進,卻從來得不到承認的力量來說,也是一種勝利”。[5](P900)
多米尼克百般阻撓洛克的行為基于她對周圍世界的錯誤判斷,并非應該的行為。但換個角度來看,由于多米尼克捍衛完美主義的欲望,其行為可視為“應該為之”,人物性格并非由單個孤立的而是一系列有聯系的前提決定的。如果這些前提不具備連貫性,只能通過基本道義判斷人物性格的善惡,以及其行為多大程度上受到推崇。再如《悲慘世界》里主教與小偷一例,男主角Jean Valjean出獄后成為社會唾棄的人,在走投無路之際,被和藹的主教Digne收留。主教使用銀器盛裝食物,待之如賓客,不料,Jean Valjean半夜卻偷了主教家柜子中的銀器而逃。被抓后竟謊稱是主教送他的禮物。沒想到他被帶至主教面前對質時,主教不僅承認那些是送他的禮物,還拿起桌上最后的兩只銀燭臺贈予他,后來Jean Valjean逐漸成為一個光明正直的人,讀者也順理成章地接受了Jean Valjean的變化。
當多米尼克的行為未能阻礙洛克前進的步伐時,她意識到作為他的情人會永遠撕扯著對他的感情,同時讓她承擔著對他被摧毀的恐懼,由于忍受不了這樣的內心折磨,她選擇了離開,向她所鄙視的周遭作出妥協。看似可能的幸福事實上對她的靈魂構成威脅,她用自己能做到的方式進行還擊,即嫁給彼得·吉丁。如果“應該”體現了多米尼克理想主義的核心,這場婚姻意味著為了保護洛克而“應該為之”,同時也流露出一種令人心碎的失敗感。從吉丁的角度來看,這樁婚姻意味著某種虛無而又不道德行為,因為此時他已經同凱瑟琳·海爾西訂下婚約。誠然,彼得·吉丁第一次見多米尼克就被其深深吸引,但突如其來的婚姻讓其措手不及,不得不讓人懷疑其中的愛情成分。某種程度上,吉丁是受埃斯沃斯·托黑的慫恿而做出選擇:
“看著今晚的你,我忍不住想起一個原本可以在你身邊組成完美圖畫的女人。”
“誰?”
“哦。不要在意我說的話。只是美學上的奇思異想。生活從來沒有如此完美過。人們嫉妒你的東西太多了。你不能把那個人也加到你的成就里。”
“誰?”
“不要再問了,彼得。你得不到她的。沒有人能得到她。你很優秀,但是你還沒優秀到能夠得到她。”
“當然是多米尼克·弗蘭肯。”[5](P407)
托黑告訴吉丁這場婚姻會為他帶去更多關注,而凱瑟琳缺乏泰然自若和超然出眾的社交魅力。這正迎合了吉丁的意愿,作為一名二手貨,他依賴于別人予以的贊譽生存。他對洛克說,“我很樂意免費與你分享(我的原則):永遠要成為人們希望你成為的樣子。這樣一來,在你需要的時候,人們就會幫助你。”[5](P332)某種意義上,這體現了吉丁的處世哲學,基于這一前提,面對多米尼克的求婚,他必然接受。一方面,吉丁不關心事實和工作,只關心大家怎么想,不會創作只會作秀,沒有能力但有朋友,沒有美德但有影響力。另一方面,多米尼克不僅僅是名符其實的白富美,她有自己的社交圈,唯有娶她才能為吉丁提供吸引別人關注的機會。
出于小說情境需要,吉丁娶多米尼克的決定體現了典型的以道德為核心的人物刻畫以及敘事方式,然而其前提是違背道德的“不該”行為,也體現了“可然”“不該”“應該”的邏輯。文學作品中更重要的是描述美好,邪惡屬于枝節問題,《源泉》中的代表人物分別為創造者洛克與二手貨吉丁。
洛克對多米尼克的第一次婚姻作出如下反應:
“多米尼克,如果現在我告訴你馬上讓那樁婚姻去見鬼——忘記這個世界和我的奮斗——不去感受憤怒、憂慮、希望——僅僅為我而存在,為我對你的需要而存在——做我的妻子——做我的財產……”[5](P476)
多米尼克回答,“我會聽命于你。”
但洛克說,“如果你現在和我結婚,我會變成你的全部。那時我將不會想要你,你也不會想要你自己——所以你將不會長久地愛我了。為了說‘我愛你’,一個人必須先知道如何說‘我’,現在我本可以從你那兒得到的那種屈從只會讓我變成一個徒有外表的軀殼。如果我要求這個,我會毀了你。這就是我不想阻止你的原因。我將讓你回到你丈夫那兒。”[5](P477)
鬼子都打到龍游了,那蘭溪是不是早已失手?老三還能不能把報喪信送到志浩手上?甚至,志浩是不是早已為國捐軀都是件難說的事。雖說蘭溪離衢州不過六七十里地,趕船也就半天的腳程,但這兵荒馬亂的,即便志浩回來奔喪,沒個一天半截估計是到不了的。
無疑,多米尼克與吉丁的婚姻同樣對洛克的價值觀構成威脅,但如果勸其放棄則更加挑戰了洛克的人物性格,他不愿將多米尼克變成缺乏思考能力的附屬品,因此,他必須放棄這一行為。亞里士多德在《詩學》第25章中提到,“衡量一個人言行的好壞,不僅應該考慮言行本身,而且還應考慮其他因素:言者和行動者的情況,對方是誰,在什么時候,用什么方式,目的是什么,是為了更美好的善,還是為了避免更大的惡。”[4](P178)《源泉》中,安·蘭德通過刻畫吉丁的不道德,充分利用一系列必要的情境塑造洛克這一理想的創造者形象,盡管一再被否定、被迫害,但總會繼續前進,以自己的精神帶動整個人類在逆境中繼續進步。
五、情節的可然與必然
亞里士多德認為一個作品應該具備完整性,即一個完整的事物是由起始、中段和結尾組成。起始指不必繼承他者,但要接受其他存在或后來者出于自然之承繼的部分,這一承繼或是因為出于必須,或是因為符合多數情況。中段指自然地承上啟下部分。因此,組合精良的情節不應隨便地起始和結尾,其構成應該符合上述要求。[4](P74)
情節是推動故事發展不可或缺的環節,同時又由可然與必然原則推動,這一結構構成逆境統一的整體,并隨著故事發展對價值觀構成一系列的威脅。《源泉》中的一例便是多米尼克與洛克的偶遇,被對方吸引,接著對洛克事業的阻撓,隨后選擇離開嫁給吉丁直到小說高潮部分,多米尼克意識到洛克永遠不會向外界屈服,不會被擊潰,最終其價值觀發生轉變。小說到此,兩人終成眷屬,沖突不再。
亞里士多德強調了文學作品中逆境的重要性,“作品要以能容納可表現人物從逆境轉入順境,或從順境轉入逆境的一系列事件,并按可然或必然的原則依次組織起來為宜。”[4](P75)但同時又說,一個構思精良的情節“應該表現人物從順境轉入逆境,而不是相反,人物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為本身邪惡,而是因為犯了某種后果嚴重的錯誤”。[4](P98)無論如何表述,都說明逆境更能造就一個悲劇人物,洛克經歷了各種感情以及事業上的逆境沖突并與之抗爭。
某種意義上,安·蘭德對情節沖突的依賴又體現了其浪漫主義情懷。文學上的“浪漫主義”興起于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期,主要特征在于注重個人感情的表達以及價值觀的差異,體現了對傳統的顛覆。浪漫派作家尋求強烈的藝術效果,描寫不同尋常的情節、事件以及人物性格,基于價值觀的沖突刻畫便體現了浪漫主義文學的一種創新。安·蘭德對文學作品中的逆境與沖突做了形而上學的解釋,“情節體現了目的行為的戲劇化,不得不基于沖突。可能是人物自身的內心沖突,可能是人物之間目標與價值觀的沖突。由于目標不能輕易觸及,戲劇化過程中必須設置某些障礙,包括人物的抗爭”,[6](P77)而作為推動“價值—威脅”前進的逆境與沖突構成了小說的情節結構。
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用例最多的是希臘神話,他認為情節的解開也應是情節本身發展的結果,而不該借助于突然出現的事物,完美的結構應是復雜型的,悲劇不應表現好人由順境轉入逆境,因為這不能引發恐懼和憐憫,反而會使人反感;同時不該表現壞人由逆境轉入順境,因為這與悲劇精神背道而馳。[4](P97)在這一點上,亞里士多德顯得自我矛盾,安·蘭德也解釋了其中的模糊性。逆境代表著某種惡意的形而上觀點,向人們傳達了一個信息,即人的成功和失敗與道德無關,在以倡導道德為核心的作品中,逆境與整個故事格格不入,而在類似于《永別了,武器》這樣以感情為核心的作品中則體現出和諧。
六、結語
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寫道,“既然詩人和畫家或其他形象的制作者一樣,是個摹仿者,那么,在任何時候,他都必須從如下三者中選取摹仿對象:過去或當今的事,傳說或設想中的事以及應該這樣或那樣的事。”[3](P177)作品往往高于原型,就創作而言,一件不可能發生但卻可信的事比一件可能發生但卻不可信的事更為可取。如描寫馬的兩條右腿同時舉步不合情理,因為它是在違反可然性的情況下發生的。由此可見,亞里士多德要求創作必須符合可然與必然的原則,實際上也就是要求創作必須符合有機整體。亞里士多德關于“可然”與“必然”定律的論斷顯明,文學沒有必要自慚形穢。
安·蘭德在《源泉》中遵循了“可然”與“必然”的原則,從角色沖突、普遍性與特殊性、情節結構安排等方面賦予了小說創作的形式。在1944年一封寫給《源泉》粉絲的信中,安·蘭德講了一個關于米開朗基羅的故事,“他的一件雕塑(我想應該是‘大衛’)里有一塊真實人體不可能擁有的肌肉,當有人告訴他這不符合自然規律時,他說大自然應該允許他這么做。這就是真正的藝術家”。[2](P669-670)
有人說《源泉》中的許多事情不可能發生,但它們的確在《源泉》里發生了。安·蘭德是一名來自蘇聯的流亡者,在美國生活過程中對美國的社會價值觀顯示出高度認同。她認為美國是一個建立在其道德基礎上的國家,也是唯一能讓她自由寫作的國家。安·蘭德借主人公霍華德·洛克之口宣稱,世界上沒有任何靠得住的權威,只有自己的獨立判斷。安·蘭德在《源泉》二十五周年再版序言里引用雨果的一句話表達了其創作態度,“如果一個作家只是為了他自己的時代而寫作,那我就得折斷我的筆,放棄寫作了。”[5](P3)有許多小說從寫出至出版仿佛雜志一樣曇花一現,很快消失于讀者視野,《源泉》雖曾因為太過理性化而連遭十二家出版社拒絕,但出版后卻一版再版,擁有廣大的受眾。對《源泉》中的“可然”與“必然”原則進行一番梳理,讀者會找到其中所傳達的理念。
安·蘭德的創作目的在于表現一個理想人物,所以她界定了可能造就這一理想人物存在的必要條件;人物的性格受環境影響,所以她表現了驅動理想人物行為的環境、價值觀以及道德準則;由于人是社會的人,所以她表現了可能使理想人物存在并發揮作用的社會體系,在《源泉》中,這一社會體系便是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無論在文學作品中還是在現實生活里,“人能為人”才是目的,這也是《源泉》魅力所在。
注釋:①小說原文為“the second-hander”,指那些沒有“自我”,依賴他人生存的人,同“創造者”相對。
[參考文獻]
[1]張超.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中的社會管理思想及啟示[J].哈爾濱學院學報,2015,(2).
[2]〔美〕蘭德.馮濤.至新知識分子[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3]Michael S. Berliner, ed.Letters of Ayn Rand[M].New York:Dutton,1995.
[4]亞里士多德.陳中梅.詩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5]〔美〕蘭德.高曉晴,趙雅薔,楊玉.源泉[M].重慶:重慶出版社,2013.
[6]Ayn Rand,“Basic Principles of Literature,”The Romantic Manifesto:A Philosophy of Literature;Revised Edition[M].Signet,1971.
責任編輯:魏樂嬌
“Might Be” and “Ought to Be”
——Interpreting “Fountainhead” With “Poetics”
YANG Ling-li
(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009,China)
Abstract:In Poetics,Aristotle touched upon a series of theories of writing,such as imitation,plot,character and so on. Some of Ayn Rand’s ideas of writing,to certain degree,derive from those of Aristotle’s. This paper aims to focus on the following elements,such as the principle of necessity and probability,the role of conflicts in literature,and the union of the universal and the particular,to analyze how and to what extent the writing of the Fountainhead is influenced by Poetics.
Key words:Poetics;Fountainhead;“Might Be” and “Ought to 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