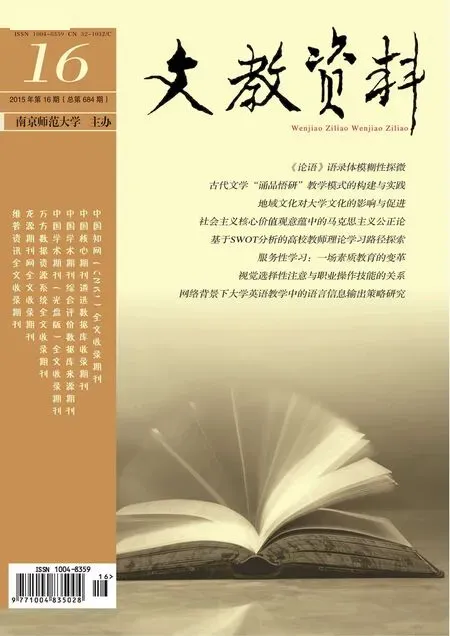漢代兩次圖書整理運動的政治動因
申紅義
(四川外國語大學 中文系,重慶 400031)
漢代兩次圖書整理運動的政治動因
申紅義
(四川外國語大學 中文系,重慶 400031)
漢代有過兩次大規模的圖書編修工作,第一次在漢武帝時期,第二次在成、哀之際。前者是在漢武帝尊儒抑老的背景下發生的,后者則貫穿古、今文經學之爭,這兩次圖書整理活動的背后都有政治力量的推動。
漢代 兩次圖書整理 政治動因
秦始皇三十四(前213年)發布挾書令,除數學、醫藥和農學方面的著作,其他書籍尤其是經史諸子一律禁止私人擁有。又經過秦末的戰火,圖文書籍毀壞殆盡。漢初國家趨于安定,漢惠帝四年(前191年)廢除挾書令,之前被銷毀的書籍經過學者們的編修而重新出現,被藏匿起來的則重新示于世人。之后這些宮廷藏書由于缺乏維護而大量損壞,“書缺簡脫”[1]。到漢武帝時,“建臧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2],設立了專門的藏書機構,安排了專門負責書籍編修謄寫的官員,將各種書籍收藏到“秘府”,也就是宮廷圖書館,這是漢代第一次由官方組織的大規模圖書編修活動。至漢成帝時,“秘府”內的書籍再次大量散亡,皇帝委派官員陳農搜求民間的書籍,以補充宮廷藏書。同時詔令光祿大夫劉向整理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整理兵書,太史令尹咸整理數術類書籍,侍醫李柱國整理方技類書籍。這是漢代歷史上第二次大規模的古籍編修和整理工作,同樣由官方發起。整理出來的每一部書由劉向進行總校理,寫出內容提要,定為《別錄》并呈于皇帝。具體方法為:廣羅遺本,較之異同,除去重復,條別篇章,定著目次,寫定正本,并敘撰人之生平,辨書籍之真偽,剖學術之源流。這項編修工作沒有完成劉向就去世,由其子劉歆接替。劉歆在其父工作的基礎上寫成《七略》,即《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其中《輯略》為諸書的總目提要,其他六略是按書籍內容進行的分類編目。《七略》是中國第一部官修目錄,是當時政府擁有的全部善本圖書總目錄。
《別錄》和《七略》先后亡佚。《別錄》經劉歆的分門別類形成《七略》,《七略》又經過班固的刪訂,保留于《漢書·藝文志》。《漢書·藝文志》對當時所見書籍的分類和對每一學派的探源述評都出于劉歆《七略》,是了解先秦和漢代學術史的門徑。
漢代這兩次大規模的圖書編修工作不僅保存了大量的典籍,而且形成了由國家統一組織文獻編修和著錄工作的傳統。從此以后,除元朝以外的每一朝代都有自己的官修目錄。
漢代圖書編修整理工作的內容主要有兩項:一是廣泛收羅散落于民間的各種書籍,二是組織學者對匯集來的書籍進行整理。前者是對秦代焚書及秦末戰亂造成的文化災難的補救,后者是對圖書進行重新編修校訂的過程。
漢武帝即位之初的建元元年(前140年),即開始罷黜百家。《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冬十月……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3]這是漢代意識形態的一次重大轉變。西漢初期統治者尊崇“黃老”,《漢書·外戚傳》:“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史記·太史公自序》記司馬談論六家要旨:“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4]司馬談此處所謂“道家”,是西漢初期盛行的假托為“黃帝、老子言”的“黃老道家”。1973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早期墓出土的帛書中,就有大量可以確定為“黃老道家”學派的著作,證明了“黃老”在西漢初期的顯學地位。“黃老道家”不是后人熟知的《老子》、《莊子》一系的思想,而是一種以道、法為主,兼采儒、墨、陰陽、刑名思想的龐雜體系,在政治、軍事方面完全是積極進取的,和后來老、莊的消極避世迥然不同[5]。尊崇黃老之學的竇太后于漢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六月駕崩,兩年后的元朔五年(前124年)六月,武帝即下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6]明確提出以禮、樂教化人民,并感嘆“禮崩樂壞”,同時開始大量任用精通“禮”的儒生,正式將“儒術”運用于政治并以之一統天下。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有了第一次大規模的圖書整理工作。從漢惠帝四年(公元前191)“開禁”,直到68年后即漢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才有了第一次實質性的圖書編修工作,最直接的推動力來自統治者治國理念的轉化——從尊崇黃老轉向獨尊儒術。這一點還反映在《漢書·藝文志》中。《漢書·藝文志》總序說:“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認為孔子即其弟子的沒世造成了微言大義的滅絕和天下學術的混亂,這顯然是儒術獨尊后論調。從《漢書·藝文志》可知《七略》排定的目次為《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其中《輯略》相當于諸書總要,其他六略都是按書籍內容進行的分類編目。從后六略的排序可以看出諸家在編纂者心目中的地位。“《六藝略》”中的“六藝”指易、書、詩、禮、樂、春秋六方面的知識,其中所列就是這六大類圖書。前三類易、書、詩在孔子時代就已經有經典傳世,禮、樂則是孔門弟子的必修課,孔子被認為曾撰《春秋》,所以“六藝”原本都是孔門之學。《六藝略》中還收有《論語》、《孝敬》兩大類書籍。《諸子略》列于《六藝略》之后,其中收有十家,最前面的儒家,不收孔子的書(《論語》等已列入《六藝略》),主要收的是孔子后人子思、七十弟子及再傳弟子們的著作。儒家之后才是道家,能直接體現漢初黃老之學的《黃帝四經》等列入此類。這些類目的編排都體現了作者編輯圖書時遵循的一個指導思想——“獨尊儒術”。
班固《漢書·藝文志》源自劉歆《七略》,包括其中的總論部分。而在漢代經學歷史上,劉歆為古文經學家,所以《藝文志》體現的是古文經學家的視野。漢代今文經和古文經的爭斗,并非單純的學術爭鳴,而是權力、名分和利益之爭,本質上是政治斗爭。劉歆《七略》系奉皇帝之命以古文經學家的背景和視野對當時所能見到的圖書進行編輯、校讎并綜論題旨,可以看做古文經學的一次學術和政治上的勝利。
關于漢代今、古文之爭的源起,還要從秦末說起。戰國至秦代設有“博士”,即列為官學的學派代表人物,相當于“學術帶頭人”。即使經過秦始皇焚書和秦末戰火,“博士”一直存在,如漢初傳授《尚書》的伏生就以治《尚書》而為秦博士,為劉邦設立朝廷儀禮的叔孫通在秦代以文學征為博士,后來又被尚未稱帝的劉邦拜為博士,孔子后裔孔鮒被漢惠帝拜為博士。但漢朝建立之初,官藏和民間的書籍毀壞殆盡。統治階級內部權力斗爭激烈,不遑顧及文化事業,直至漢惠帝四年才撤銷禁書令。漢文帝時,開始廣立學官,增設博士,如申培、韓嬰以精通《詩》立為博士,伏生的弟子張生以《尚書》立為博士,《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有博士。據記載,僅文帝時有博士七十余人。立為博士意味著學者所傳習的學問成了官學,本人也有了祿位,這些都極大地促進了學術復興。漢武帝開始大力尊孔,設立五經博士,所立博士僅限于精通易、書、詩、禮、春秋五類典籍者,自此儒學大盛,儒生日眾。
秦始皇焚書和秦末戰火使書籍遭受了巨大的破壞。漢代隨著學術的復興,書籍的獲得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前朝學者們的傳承和整理,二是前朝隱藏于民間的書籍不斷被發現。前者如秦代焚書后禁止民間私藏的《詩》,在漢文帝時即有申培、韓嬰因精于《詩》而立為博士,可能就是因其口誦的特點而得以保全。又如秦《尚書》博士伏生在戰亂中攜一部《尚書》逃回老家濟南,將之藏于壁中后再次逃亡,戰亂結束后又重新找回,但已殘缺不全,僅剩二十八篇。因其年老,無法記起殘損的內容,這就是后來的今文《尚書》。后者如漢武帝末年魯共王拆孔子故宅時于壁中發現 《尚書》、《禮記》、《論語》、《孝敬》凡數十篇古文典籍,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和《老子》等。
秦漢之際是漢字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秦國的小篆發展成漢代通行的隸書,隸書之后的文字為今文字,隸書之前的文字為古文字,兩者形體差別較大。小篆在秦代已經演變出了早期隸書——古隸,到漢代又演變成漢隸,成為通行文字,經歷過秦漢兩朝的學者都親歷了這一文字演變的過程,圖書編輯過程中應不存在文字識別困難。伏生所持《尚書》在秦朝即使以小篆或古隸書寫,到漢代轉換成漢隸當無太大困難,其他如《詩經》等靠口耳相傳的學問更無此類問題。
但是自戰國以來,秦國和東方六國的文字在形體上已漸行漸遠。戰國時期的秦國文字和東方六國文字差別很大,在近年來出土的簡帛文獻中十分明顯。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統一中國后開始“書同文”,三十四年(前213年)又頒布“挾書令”,很多東方六國的書籍來不及轉寫為秦文字就被匆匆藏匿起來。到了漢代再次被發現時,已經習慣于漢隸的人們無法辨識這些曾通行于秦國之外的字體,因其難辨,稱之為“古文”。六國文字和秦文字本為同一時期不同地域的兩種字體。前者在秦朝被禁絕,造成其演變的中斷,后者演變成漢代的隸書,所以漢代人對六國文字感到很陌生,視之為遠古時代的文字。
自漢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設立五經博士至漢平帝即位(公元1年)的一百三十多年間,經學博士都是靠研習用隸書寫就的經文而立于學官。不過在此期間,用六國文字書寫的書籍不斷被發現。最著名的是漢武帝末年魯共王為擴建自家宮室而壞孔子舊宅時于壁中發現的古文《尚書》、《禮記》、《論語》、《孝敬》凡數十篇古文典籍,都用古字寫成。今天看來,這些書籍應該是用六國文字寫成的戰國寫本,因秦始皇禁書或秦末戰亂而被藏匿起來,被漢代人稱為“古文”、“古字”。這些書籍經過歷代學者的研習,逐漸得到解讀。孔子的后人孔安國在武帝時就曾想奏請將壁中書列于學官,不巧遇到朝廷巫蠱事件而擱置下來。劉向、劉歆父子一起奉漢成帝之命編輯校訂“秘府”藏書,有機會接觸到這些深藏宮中秘不示人的古文書籍,并為之疏解,漸成系統,于是提議將《左氏春秋》、逸《禮》、《尚書》等用古文寫成的典籍都立于學官。漢哀帝讓劉歆與當時的五經博士協商,但靠今文經書得勢的官學博士們卻保持集體沉默,劉歆便寫了著名的《移讓太常博士書》,對今文經學家們的抱殘守缺、器量狹小進行揭露和批評。《漢書·藝文志》不僅詳述古文書籍的發現和整理過程,而且在所列同類文獻中“古”字打頭,古文文本一律列為“排頭書”。這種編排出自《七略》,體現了西漢古文經學家兼容并包、匯通古今的優點[7]。
漢代兩次大規模的圖書編修整理工作使大量秦漢著作保存下來,給后人留下了豐富的遺產。第一次是在漢武帝決定尊儒后有感于“禮崩樂壞”而發起的。設立五經博士,極大地刺激民間學者整理書籍的熱情。第二次由劉向、劉歆父子擔任,編輯和整理了一批古文經,向今文經學壟斷儒學的局面發起挑戰,并最終借助政治力量將古文經學推上舞臺。和漢代之后的各個朝代一樣,這兩次圖書編修活動的背后都有政治力量的推動,其過程都擺脫不了政治因素的影響。
[1][2][漢]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2005:1351.
[3][4][漢]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2005:111,2051.
[5]魏啟鵬.馬王堆漢墓帛書《黃帝書》箋證[M].北京:中華書局,2004:2.
[6][漢]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2005:122.
[7]李零.蘭臺萬卷[M].上海:三聯書店,2011:7.
教育部人文科學研究一般項目“簡帛異文匯考疏證”(14YJA740027)、重慶市社科規劃一般項目“簡帛儒家文獻異文綜合整理與研究”(2014YBYY084)系列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