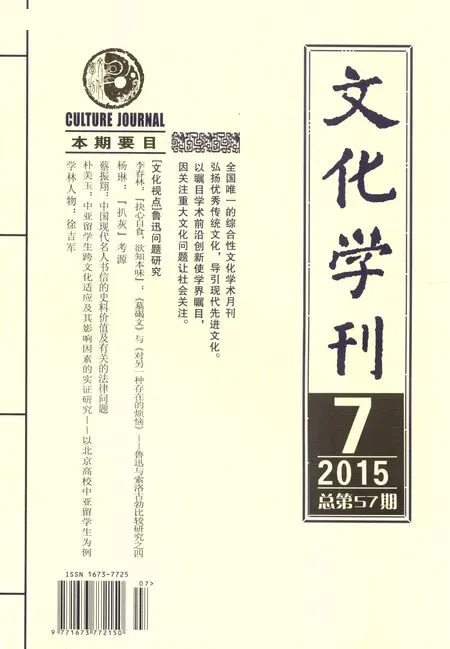唐代邊塞詩離怨色彩的形式意義分析
杜潤青
(甘肅省文縣第一中學,甘肅 隴南 746400)
唐代邊塞詩離怨色彩的形式意義分析
杜潤青
(甘肅省文縣第一中學,甘肅 隴南 746400)
從唐代邊塞詩創作實際出發,透視并分析了這一色彩在不同體式邊塞詩中的體現,以及由它造成的邊塞詩的多層次立體化、悲劇性的審美價值和過渡性的詩史意義。
唐代邊塞詩;離怨色彩;審美價值
離怨色彩的體現
基于造成離怨情結因素的復雜,其體現形式也較為復雜,它運用多種詩歌體式,表現詩人自我或非我強烈的內心波瀾、表現他們的生存困境和情感傷痛。
在唐代邊塞詩中,詩人把征夫思婦的離別之痛主要通過贈別體、代言體等形式表述出來。
首先,在贈別詩中,往往是對贈別對象的一種安慰與勸勉,如嚴羽所說:“古人贈答,多勸勉之詞。”[1]而這種安慰與勸勉的根由大多來自于征人思婦的“離情閨怨”,同時在這種安慰與勸勉之中又往往體現出對自我或非我悲苦生活的無奈與怨恨之情,如:
飄蓬多塞下,君見亦潸然。
迥磧沙銜日,長河水接天。
夜泉行客火,曉戍回京煙。
少結相思恨,佳期芳草前。
(賈島《送友人游塞》)
在此盡管說著“少結相思恨,佳期芳草前”的安慰之詞,然而在詩人的筆墨背后深潛著的又是面對“迥磧沙銜日,長河水接天”的荒涼環境所引發的無奈與怨憤。另如:
渭城朝雨邑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王維《渭城曲》)
臨行勸老友多喝一杯酒,殷殷惜別,亦所以借酒澆愁,“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比喻了流落遠方的寂寞和舉目無親的哀愁。
看得出,在這類贈別詩中,“離怨”色彩不僅體現的是贈別對象的離別之苦,也包融了詩人對自身身世際遇的哀怨之情。
其次,離怨在代言詩中顯得較為復雜,有代征夫言的,有代思婦言的,也有代征雁言的等,這類詩往往描述他們的生存現狀和情感傷痛,同時又在一定意義上寄托自身的某種怨恨情感。正如楊義先生所說:“為詩而采用代言體,乃是一種化裝的抒情。因為詩人和詩中的抒情主體‘有緣’而‘非一’,他要在詩中直接呈現他人的心聲,把詩歌言志緣情的功能轉化為‘言他志’‘緣他情’。”[2]他又指出:“代言體的秘密在于那個‘代’字,代言對象的內心隱秘是通過詩人的體驗折射出來的,在體驗的過程中也難免有詩人的知識、才華和趣味的投影。”[3]當詩人之情志與抒情主體之情志有了一個相似點和溝通點時,詩人之情志便能夠通過抒情主體之情志表達出來。在唐代邊塞詩中,這一相似點與溝通點是“離怨”情結,征夫思婦的“離情閨怨”與詩人對征夫思婦的同情,以及由此引發的詩人對自身生存境遇的強烈不滿,在這里便進行了對話與互感。從而在詩人代言體邊塞詩中大多滲透著“離怨”色彩。代征人言的如:
西風屢鳴雁,東郊未升日。
繁煙幕幕昏,暗騎蕭蕭出。
望云愁玉塞,眠月想蕙質。
借問露沾衣,如何香滿室。
(楊衡《征人》)
在這首詩里,詩題就明確了代言對象——征人,其每字每句都流露出“離怨”的情感,同時,在一種朦朧的思戀中襯托了離別之悲。代思婦言的如:
寸心杳與馬蹄隨,如蛻形容在錦帷。
江上月明船發后,花聞日暮信回時。
五陵夜中酬恩什,四塞秋為破虜期。
待到乘軺入門處,淚珠流盡玉顏衰。
(黃滔《閨怨》)
由此可見,唐代離怨色彩的代言體邊塞詩所表達的情感是詩人的情感與他所“化裝抒情”的主體——征人思婦的情感因有了“怨”這一共同的情感支撐點,從而表達出的更為復雜的情感內容,同時這也使得這類詩歌的“離怨”色彩更為濃厚,“離怨”情結更為感人。
另外,征夫之怨與思婦之怨并不是完全獨立地表現在不同詩中,有的在同一首詩中同時表達征夫思婦的“離怨”情結,最典型的例子當數高適的《燕歌行》:
漢家煙塵在東北……
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
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
大漠窮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當恩遇常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
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箸應啼別離后。
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
其中由環境(自然的、社會的)描寫襯托了征人思婦“離怨”情結下所暗含的悲劇結局:“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征夫與思婦在這首詩中似乎進行著無言的“對話”,在這種無法相會的“對話”中,更強化了他們的悲劇命運在詩中的表現力,這比血還濃的悲涼之氣與哀怨之情在這首詩中得到了同步的升華,而“離怨”色彩的最高藝術境界也許就在這里完成。
離怨色彩的價值意義
唐代邊塞詩中濃厚的“離怨”色彩為唐代邊塞詩的藝術審美性增添了無窮的魅力,同時也深刻地影響了后代文學的發展,因此具有極高的審美價值和過度性的詩史意義。
第一,雄渾開闊的意境表現出的陽剛美與這種悲苦離怨情調的陰柔美高度融合,使唐代邊塞詩呈現出多層次、立體化的審美效果。前人評及唐代邊塞詩都以“風骨”“陽剛”“悲壯”為標準定性,往往縮小甚至忽略了“離怨”色彩及其所具有的美感。其實這些觀點是有些片面的。美體往往是陰陽相濟才顯出其美的,正如姚鼐在《復魯絜非書》所言:
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
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
以至于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
陽之為道。[4]
唐代邊塞詩之所以成為唐代詩壇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成為歷代邊塞題材詩歌的最高音,不只是因為它具有陽剛美或“風骨美”,也許更為重要的原因是在這種陽剛美的意境中加入了濃濃的“離怨”情結及其所具有的哀婉悲涼的陰柔之氣,從而構成了唐代邊塞詩所特有的多層次、立體化的美感。從小處看,這種美感充分地在一首邊塞詩中的不同層面表現出來,如高適的《燕歌行》,把這種立體化的審美效果表現得極為突出,前半部分極力表現征戰中征人的豪邁陽剛之氣:“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摐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而到了后半部分,便把征人思婦凄婉、哀怨的生命之苦用血淚融注于其中:“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箸應啼別離后。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前后結合,陰陽相濟,儼然是現實生活的悲壯與悲慘之態,極為豐滿,極富三維效果。從大處看,整個唐代邊塞詩中,在陽剛美的另一面,處處可見陰柔之氣,使唐代邊塞詩的整體具有多層次、立體化的審美效果。如高適、岑參等的邊塞詩更多地體現出陽剛美,“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5]同時,在唐代邊塞詩中,以哀怨、凄婉之詩見長的詩人有很大的群體,如王勃、駱賓王、李頎、王昌齡及晚唐大部分詩人,這就使得唐代邊塞詩這一整體具有了多層次、立體化的美感。
正是這種邊塞詩“離怨”色彩的陰柔美為整個唐代邊塞詩補充了血液和營養,從而使其更為豐滿鮮活,具有了立體化的審美效果,同時這也是唐詩影響深遠的因素之一。
第二,通過表現普通人的內心情感,豐富了邊塞詩的藝術審美內涵。唐代離怨色彩的邊塞詩廣泛地反映了征人思婦悲涼的生存狀態及悲慘命運,這種生存狀態與悲慘命運在一定意義上構成了這類詩歌的悲劇性藝術審美內涵。
當征夫(包括詩人)懷著一腔熱血奔赴疆場實現自我理想時,面對現實的沖擊,一個個或多或少地受到打擊,從而表現出對自我生存際遇或對社會的失望感,悲劇性從此產生,而“悲劇的解決就是使代表片面理想的人物遭受痛苦或毀滅。”[6]如郭震,他“少有大志”,“任俠使氣,拔去小節”,然而經過現實的磨合,最后“以軍容不整,流新州”,[7]完成了他的悲劇性的命運歷程。另如杜甫,他早期懷著“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的高昂人生理想,但最終只能在“我終為奴仆,幾時樹功勛”(杜甫《前出塞九首》之五)的失落中完成他悲劇性命運的一生,而“藝術中的悲劇,是藝術家對生活中悲劇現實進行了藝術認識和藝術凈化后的結果,因而它可能而且應該直接顯現出巨大的審美意義。”[8]所以這種普通人的悲劇性命運進入邊塞詩中,便是“離怨”色彩下的悲劇性藝術審美效果,唯其如此,唐代邊塞詩的離怨色彩才真正具有了永恒的藝術審美價值。如:
明月出天山,蒼茫云海間。
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
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
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
戍客望邊邑,思婦多苦顏。
高樓當此夜,嘆息未應閑。
(李白《關山月》)
詩中,“胡窺青海灣”的悲劇性社會現實造成征人思婦別離的悲劇性命運:“在‘不見有人還’的通向死亡的道路中,他們的青春將喪失,軀體將毀滅。”[9]而這雙重悲劇造成了詩歌悲劇性的藝術審美感覺:意境的蒼涼感和凄婉哀怨的詩歌情感基調等悲劇性藝術效果。
“神的寵兒往往早亡,一切事物莫不如此,然而他們卻和神一起永生。”[10]正是唐代邊塞詩離怨色彩的這種悲劇性藝術審美效果,使唐代邊塞詩“風骨美”的另一面包含了更多的人性內容,從而擴大了邊塞詩的藝術審美內涵。
第三,唐代邊塞詩的離怨色彩,傳承了中國傳統的“詩可以怨”的詩學理論,并為宋詞、特別是婉約一派的抒情模式的形成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怨”這一中國古典詩歌的重要抒情基調,到了唐代離怨色彩的邊塞詩這里,無論從抒情的層面還是藝術層面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發展。從抒情功能上看,唐代邊塞詩的“離怨”不僅表達了寫作客體征人思婦的“離情閨怨”,同時也表達了寫作主體詩人的各種復雜情態,如對征人思婦的同情、對自我生存狀態的不滿、對殘酷社會現實的強烈怨恨大都借助“離怨”色彩表達于邊塞詩中。從藝術層面看,唐代邊塞詩無論從詩歌意象、意境描寫,還是語言運用都承傳了前代“離怨”之詩的傳統,如“月”“雁”意象,在唐以前“離怨”之詩中就是常用意象,楊義指出:“明月是中國古典詩詞中用得最多的意象之一。”[11]到了唐代,“月”“雁”意象在表達離怨情結的邊塞詩中幾乎都曾出現過。另如表現惡劣環境的自然物象“雨”“雪”“霜”“沙”等和胡樂意象,這些意象在唐代之前的邊塞詩中都是常用意象,而唐代仍沿用了這些意象,因為這些陰冷、灰暗、深沉的意象是引起抒情主人公產生“離怨”情結的誘因。在語言上唐代邊塞詩大量沿用唐以前詩歌的語言類型,表現最為突出的是對詩題的沿用,如《關山月》《鳴雁行》《隴頭水》《閨怨》等,在唐代邊塞詩中常常用來表達離怨情結。
唐代邊塞詩富于離怨色彩的抒情審美傾向影響了宋代詞壇,特別是婉約派的抒情審美模式的形成與發展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唐代邊塞詩離怨色彩的影響。如: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
邊聲連角起。千嶂里,長煙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
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
(范仲淹《漁家傲》)
此詞不僅以邊塞為題材內容表達“將軍白發征夫淚”的離愁別怨,還在用詞、意象用典等方面都緊承了唐代離怨色彩的邊塞詩,如“雁”“落日”“孤城”“羌管”“霜”等意象的使用,“燕然未勒”典故的引用,征夫思婦的離愁別怨都與唐代離怨色彩的邊塞詩一脈相承。另如周邦彥的詞“艷情與羈愁幾乎占了他的《清真詞》的全部內容。”[12]因此,唐代邊塞詩的“離怨”色彩在詩歌發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啟后的重大作用,為宋詞、特別是婉約派抒情審美傾向的形成與發展繁榮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綜上,唐代邊塞詩的“離怨”色彩不僅造成了唐代邊塞詩立體化、悲劇性的審美價值,同時也在詩歌發展史上起到了過渡性的詩史意義。
[1][5]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205.181.
[2][3][11]楊義.李杜詩學[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224.206.337.
[4]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第三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510.
[6]朱光潛.西方美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493.
[7]彭定求.全唐詩[M].北京:中華書局,1960.756.
[8]劉叔成等.美學基本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99.
[9]馬美信,賀圣遂.中國古代詩歌欣賞辭典[M].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0.185.
[10]尼采.悲劇的誕生[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122.
[12]游國恩等.中國文學史(第三冊)[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80.
【責任編輯:周 丹】
I207.22
A
1673-7725(2015)07-0214-04
2015-04-28
杜潤青(1979-)男,甘肅通渭人,一級教師,主要從事中學語文教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