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姆的《翻譯史研究方法》和譯者主體性
陳嘉昱
陳嘉昱/湖南師范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在讀碩士(湖南長沙410006)。
中西方的翻譯活動(dòng)都有著悠久的歷史,人們對(duì)于翻譯活動(dòng)的關(guān)注自然也由來已久。據(jù)記載,西塞羅在公元前一世紀(jì)已經(jīng)提出為后人所熟悉的譯詞和譯意兩種翻譯方法。自20世紀(jì)中葉,翻譯的地位不斷提升,翻譯研究開始成為獨(dú)立學(xué)科門類,翻譯史相關(guān)的著作也越來越多。
一、《翻譯史研究方法》作者皮姆簡介
皮姆是澳大利亞人。傳播學(xué)、比較文學(xué)學(xué)士,社會(huì)學(xué)碩士及文學(xué)社會(huì)學(xué)博士。曾在包括哈佛大學(xué)在內(nèi)的多個(gè)大學(xué)任職,現(xiàn)為西班牙洛維拉維吉利大學(xué)教授。曾在多國多個(gè)學(xué)校任職的經(jīng)歷使皮姆對(duì)于翻譯的特性、譯者的身份特征等有著獨(dú)特的觀點(diǎn)。皮姆共出版了六部專著、七本論文集,發(fā)表了140多篇論文。他注重社會(huì)學(xué)翻譯研究,關(guān)注翻譯和社會(huì)各因素之間的關(guān)系。
二、《翻譯史研究方法》主要觀點(diǎn)
《翻譯史研究方法》全書共12章。由于皮姆重視實(shí)證研究,書中有大量事例和數(shù)據(jù)。前6章圍繞如何具體書寫翻譯史這個(gè)主題,詳細(xì)地說明了種種編寫翻譯史的方法。后半部分(7-12章)則側(cè)重理論上的探索,探討如何解釋翻譯活動(dòng)形成的原因及怎樣揭示其內(nèi)在規(guī)律等等。翻譯史的選題有何技巧?翻譯史研究的意義是什么?翻譯史研究有無理論?這些問題都是對(duì)翻譯史感興趣的人們十分關(guān)注的話題。因此,對(duì)于譯史研究,這本書有很大的理論和實(shí)踐意義。任何研究的目的都是為了回歸實(shí)際、解決問題,譯史研究也不例外。因而,皮姆制定了4條原則:1)譯史研究要解釋翻譯的社會(huì)起因;2)翻譯史的主要對(duì)象應(yīng)該是作為人的譯者;3)翻譯史的重點(diǎn)在于譯者,因而翻譯史的寫作必須圍繞譯者生活及其經(jīng)歷過的社會(huì)環(huán)境展開;4)翻譯史研究應(yīng)表達(dá)、討論或解決影響我們當(dāng)前的實(shí)際問題,在這個(gè)過程中,研究者個(gè)人的主觀介入不可也不應(yīng)避免。[1]這幾條原則強(qiáng)調(diào)了社會(huì)環(huán)境和譯者主體性對(duì)翻譯的影響。
三、譯者主體性與翻譯
《翻譯史研究方法》的第十和十一章,皮姆著重討論了譯者和文化方面的問題。皮姆指出,翻譯史的研究存在一些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問題,其一,翻譯史的研究常常集中于翻譯而非譯者,在研究的過程中經(jīng)常會(huì)忽略譯者可能發(fā)生的一些情況對(duì)于翻譯的影響。其二,翻譯史的研究常常集中于很少的幾個(gè)專業(yè)的譯者,而很少關(guān)注其他大多數(shù)譯者的翻譯行為。因此,針對(duì)這些問題,在第十章中,皮姆談到譯者時(shí),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區(qū)分單數(shù)的譯者(the translator)和復(fù)數(shù)的譯者,即譯者們(translators)”[2]。在他看來,翻譯史所研究的不應(yīng)該是抽象意義上的譯者,而應(yīng)該是實(shí)實(shí)在在的譯者群體;不應(yīng)該是很少的幾個(gè)專業(yè)的譯者,而應(yīng)該是其他大多數(shù)譯者的翻譯行為。譯者是在翻譯的過程中占據(jù)主動(dòng)地位的因素,是有各自職業(yè)背景、興趣愛好、活動(dòng)范圍的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抽象的譯本的制造者。
“譯者具有主體性,每一名譯者在進(jìn)行翻譯活動(dòng)時(shí)都受到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甚至是法律等各個(gè)方面的影響。每一名譯者都是有著實(shí)實(shí)在在的物質(zhì)軀殼,是活生生的生物體,這也就意味著他們有著生活的需求,他們需要謀生、養(yǎng)育后代或者為了生計(jì)而奔走于不同的文化之間。”[3]也正是因?yàn)檫@些原因,他們不得不關(guān)心報(bào)酬,而且常常除了翻譯之外,他們還得為了生計(jì)從事其他的一些工作。很多譯者除了從事翻譯,也可能是教師,也可能是商人,又或者是政客,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在文中,皮姆也給出了幾個(gè)例子。“17世紀(jì)以來,在434名巴西的譯者中,僅有9名從未從事過除翻譯以外的其他職業(yè)。20世紀(jì)從事文學(xué)翻譯(阿拉伯語到希伯來語)的150名譯者中,只有一名為全職翻譯。”[4]某種程度上說來,正是由于譯者有著不同的社會(huì)地位以及在其他職業(yè)中的優(yōu)勢(shì),和作為單純的譯者相比,他們擁有了更多的社會(huì)力量和資源來幫助他們成為更出色的譯者。其實(shí),從真正意義上說,每一名譯者都不僅僅只是譯者,而且有著多重的社會(huì)身份。此外,很多翻譯都必須考慮到經(jīng)濟(jì)方面的因素。“比如,翻譯和出版市場、讀者等因素就息息相關(guān)。”[5]翻譯一部作品,有時(shí)不僅僅要求譯者要做到忠實(shí)原文,還需要考慮到出版市場的接受度,讀者的喜愛度等許許多多的因素。或許也正是因?yàn)檫@些因素的刺激,他們才會(huì)耗費(fèi)更多的精力以做出更好的翻譯,成為更出色的譯者。
每一個(gè)譯者都是一個(gè)活生生的人,也無疑會(huì)有自己的興趣愛好。他們或許成為譯者又或許下一刻想脫離譯者這個(gè)身份。有些譯者或許會(huì)在翻譯的過程中感覺失去了自我。翻譯是一種傳達(dá)別人的話語的過程,很多時(shí)候,他們必須盡自己所能不要摻雜進(jìn)自己的感情因素,盡管這很難做到。我們都知道,同一部作品,由不同的譯者翻譯,往往會(huì)有不同的譯作。許多翻譯研究者們也就這個(gè)問題討論過,結(jié)論無疑是譯者本身的原因。每一個(gè)譯者都有不同的生存環(huán)境,不同的教育背景、文學(xué)素養(yǎng),而這些無疑都會(huì)對(duì)翻譯造成舉足輕重的影響。“有些譯者覺得自己終日傳遞他人的思想,還要抑制自己不要摻雜自己的感情因素,以至于到最后,已經(jīng)到了沒有機(jī)會(huì)以自己的名義說話、表達(dá)想法的程度。”[6]因而,他們可能因此對(duì)翻譯本身產(chǎn)生抗拒感,希望找回自己的聲音。有些譯者本身對(duì)于翻譯有著極其濃厚的興趣,這興趣會(huì)支持他一直從事翻譯,亨利艾伯特就是這樣的一個(gè)譯者。亨利艾伯特是一名文字記者、作家。但是,亨利把讓尼采聞名全法視為自己一生的使命,他終其一生翻譯尼采的作品。他從事這一職業(yè)已經(jīng)不再只是為了追逐經(jīng)濟(jì)利益,而是對(duì)于尼采的深深熱愛。在皮姆看來,要理解作為人的譯者們,必須了解他們?yōu)楹螐氖路g,又為何不再從事翻譯,并且要了解他們翻譯的背景。此外,由于譯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是活動(dòng)的個(gè)體,他們可能因?yàn)楦鞣N原因,不僅僅只是處在單一的文化或社會(huì)中。他們可能從中心城市搬到偏遠(yuǎn)鄉(xiāng)村,也有可能從這個(gè)國家去到另外的國家。無論如何,和那些必須依靠翻譯才能理解其他文化的人相比,譯者們往往有著更多的外國語言、文化方面的知識(shí),也就意味著他們能走到更遠(yuǎn)的地方,了解更多的文化。據(jù)皮姆統(tǒng)計(jì),不同的歷史時(shí)期,處于不同地域的譯者,往往會(huì)呈現(xiàn)出不同的移動(dòng)傾向,而影響這種傾向的原因也多種多樣。
總之,皮姆的《翻譯史研究方法》深入淺出地討論了翻譯史研究中的各種現(xiàn)象和問題,為翻譯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該著作不僅僅是對(duì)于翻譯史,乃至于對(duì)整個(gè)翻譯活動(dòng)的研究都具有很重要的意義。書中強(qiáng)調(diào)了譯者主體性在翻譯過程中的重要作用。譯者主體性體現(xiàn)在翻譯活動(dòng)的各個(gè)方面,從譯本選取到翻譯過程,再到策略選擇,都有著譯者主體性的影子。翻譯活動(dòng)中,譯者只有不斷地提升自身素養(yǎng),充分發(fā)揮譯者主體性,才能不斷提高譯文質(zhì)量,進(jìn)一步為翻譯研究做出貢獻(xiàn)。
[1]Anthony P.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7.
[2]柯飛.譯史研究,以人為本—談皮姆翻譯史研究方法[J].中國翻譯,20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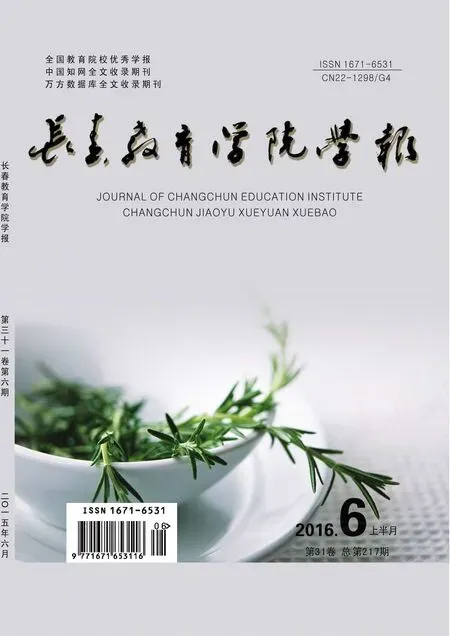 長春教育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5年12期
長春教育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5年12期
- 長春教育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的其它文章
- 基于“研學(xué)后教”理念的初中英語課堂母語使用情況調(diào)查分析
- 詞塊教學(xué)法在初中英語寫作教學(xué)中應(yīng)用的實(shí)證研究
- 數(shù)學(xué)建模隊(duì)員選拔問題解析
- 青年學(xué)生自信心、社會(huì)支持、狀態(tài)-特質(zhì)焦慮關(guān)系的研究
- 高等中醫(yī)藥院校大學(xué)生宗教經(jīng)驗(yàn)觸發(fā)因素研究
- 90后大學(xué)生心理健康教育課程實(shí)效性探究
——以嶺南師范學(xué)院生命科學(xué)與技術(shù)學(xué)院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