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呼蘭河傳》看蕭紅悲劇人生的性格
莫瑞芬
從《呼蘭河傳》看蕭紅悲劇人生的性格
莫瑞芬
《呼蘭河傳》是蕭紅的自傳體長(zhǎng)篇小說(shuō)。在《呼蘭河傳》中所隱藏的對(duì)生命的追逐,正是蕭紅人生悲劇命運(yùn)的真實(shí)寫照。蕭紅在以個(gè)體意識(shí)為中心的美學(xué)悲劇創(chuàng)作中,將自我與社會(huì)、自然環(huán)境之間的對(duì)立與沖突以及因自主意識(shí)受到阻礙而迸發(fā)的情感抗?fàn)幐吨T筆端,寄托在凄婉悠長(zhǎng)的文學(xué)里。本文從對(duì)《呼蘭河傳》文字片段的解析中,挖掘潛藏在蕭紅悲劇人生中的“達(dá)芬奇密碼”,琢磨“性格即命運(yùn)”的文學(xué)意蘊(yùn)。
《呼蘭河傳》;蕭紅;自主意識(shí);人生悲劇;性格迷失
在《呼蘭河傳》的開篇,我們可從對(duì)“卑瑣平凡的實(shí)際生活”描述中,觀照蕭紅的人生及真實(shí)的社會(huì)生活。這種生活沒(méi)有鮮花、沒(méi)有詩(shī)篇、沒(méi)有光和熱,也沒(méi)有音樂(lè)、藝術(shù),更沒(méi)有趣味。在所有該過(guò)去的,都算是忘記了。人們生活在這個(gè)世界里,“天黑了就睡覺(jué)”,“天亮了就起來(lái)工作”,[1]似乎人生就是自然地長(zhǎng)大,長(zhǎng)大了就算長(zhǎng)大了,長(zhǎng)不大也就算了。在這種與眾不同的“稚拙”的人生感悟中,童年的孤寂及對(duì)自我、自尊的過(guò)于敏感,培育了蕭紅悲劇人生的萌芽。
一、失落的童年鑄就任性的性格
在《呼蘭河傳》中,有一段關(guān)于《祖父的園子》的描述。一個(gè)四五歲的小女孩,是蕭紅童年在祖父身邊那個(gè)天真、無(wú)憂的生活情景的寫照。祖父每天都要到后園去勞作,小女孩也跟著去,“祖父戴著一個(gè)大草帽,我也戴一個(gè)小草帽;祖父栽花,我也栽花;祖父拔草,我也拔草”。[2]對(duì)后園子燦爛生命圖景的描寫,詮釋了蕭紅兒時(shí)的純真與對(duì)自然的熱愛(ài),并由此形成了蕭紅成年后情感寄托的閘口,清新的童年回憶,美麗的影像描述,是充滿孩子氣的心靈釋語(yǔ)。然而,童年并非都是絢爛的,在缺失父母之愛(ài)的童年孤寂里,蕭紅有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抗?fàn)帥_動(dòng),她因?yàn)橐疗瓢變舻拇皯艏埗艿阶婺傅尼槾蹋诒姸嗳说募彝ダ铮枃L了冰冷的人生際遇。20歲的蕭紅離開了家鄉(xiāng),開始了漂泊的人生,之后情感的波瀾、疾病的困擾,將近中年的她更加懷念童年的故鄉(xiāng),渴望回到她曾經(jīng)留下快樂(lè)時(shí)光的祖父的園子。在那里,她能夠與慈祥的祖父一起種菜;在那里,她能夠獲得老祖父的疼愛(ài);在那里,她能夠從深深的孤寂與落寞中找到無(wú)比的溫暖和安慰。
在《祖父的園子》里,有蕭紅對(duì)童年的回憶,有情感的自然流露,讀者從中可以解讀出她的獨(dú)特情感與自我愿望。“花開了,就像是花睡醒了似的;鳥飛了,就像是鳥飛上了天似的;蟲子叫了,就像是蟲子在說(shuō)話似的”。在無(wú)拘無(wú)束的文字間,蕭紅表達(dá)了對(duì)自然生活的向往,也為我們剖析蕭紅的性格特點(diǎn)創(chuàng)造了條件。在園子里澆水、種菜的情景是生動(dòng)的,蕭紅的胡亂折騰并未受到祖父的責(zé)怪和限制,在這種為所欲為的情感流淌中,形成了蕭紅的自我意識(shí)與對(duì)生活的真實(shí)追求的對(duì)照。表達(dá)了她“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樣,就怎么樣”的心靈自由。[3]在這份渴望里,她的心愿及理想就是在玩耍的時(shí)候能夠恣意而行,假借自我表達(dá)對(duì)成人意識(shí)的厭倦。在人生的終點(diǎn),強(qiáng)撐病體的蕭紅傾盡心力來(lái)描述祖父的園子,是在人生的落寞回憶中對(duì)童年夢(mèng)幻的深切依戀,這也是生命委頓經(jīng)歷的率性使然。
二、蕭紅的悲劇體驗(yàn)是其悲情性格的最大誘因
呼蘭河邊的生活是單調(diào)的,日復(fù)一日的。因年深月久而形成的“日常化”生活,與其說(shuō)是痛苦的,不如說(shuō)是應(yīng)對(duì)災(zāi)難生活的生命戰(zhàn)栗。蕭紅在《呼蘭河傳》中,有對(duì)如跳大神、放河燈、唱秧歌、娘娘會(huì)……等節(jié)日活動(dòng)的記述。跳大神是為了祭鬼,唱大戲是為了看龍王爺,為鬼而作的盛舉,多是呼蘭河人麻木的精神寫照。虔誠(chéng)的呼蘭河人在生命的流逝里,對(duì)死亡莊嚴(yán)、神秘的恐怖感,完全變成了精神上的盛舉,死了的人沒(méi)有什么,活著的人似乎無(wú)所牽掛,在無(wú)價(jià)值的生與死上,面對(duì)生命的漠然,兩個(gè)年輕的學(xué)徒為了爭(zhēng)一個(gè)婦人而大打出手。與小團(tuán)圓媳婦的死相比,在人們的視野里,小團(tuán)圓媳婦就不應(yīng)該長(zhǎng)那么大,走路也不應(yīng)該生風(fēng),而這些無(wú)中生有的所謂“病”,是其走向死亡的罪魁禍?zhǔn)祝渲袚诫s的真誠(chéng)的愚昧與善良的殘忍,令人心魂顫抖。蕭紅在《呼蘭河傳》里,用異乎尋常的語(yǔ)調(diào)來(lái)記述死亡,在荒涼的生命軌跡里籠罩著精神暗影,引導(dǎo)我們窺探生命悲劇的人性觀,儼然是她個(gè)人生命孤寂的流露。在對(duì)“死”的敘述中,將內(nèi)心的繁復(fù)性委婉而深切地表露出來(lái),奠定了其生命悲劇的灰色。
生命的悲劇性不僅是對(duì)生命的持續(xù)掙扎,也是對(duì)生命渴望的永恒追逐。在《呼蘭河傳》中,缺乏靈性的塵世生活,使蕭紅失去了真切的情感體驗(yàn),而生命中的矛盾與沖突,是蕭紅悲劇人生的根源。蕭紅的個(gè)人身世貫穿于社會(huì)、民族命運(yùn)的漩渦中,尤其是在悲劇人生的精神體悟中,將小團(tuán)圓媳婦、馮歪嘴子的生死理解融入自我的情感寄托中,也從切膚之痛中理解了在死亡邊緣掙扎的困苦。蕭紅的苦難生命源自早熟的童年,背負(fù)著父母之愛(ài)的缺失,其主觀情感充滿了沉重與寂寞。“我家的園子是很荒涼的,我家是荒涼的……”[4]這種苦難的人生悲劇情感打破了內(nèi)心的安靜,成為蕭紅悲劇人生性格的最大誘因。人性的建樹與情感的融合是構(gòu)建堅(jiān)固生命的根本,而蕭紅的悲劇性人格,在面對(duì)死亡的恐怖與對(duì)生命執(zhí)著的追求中,期許與荒寂終其一生的相伴。蕭紅不是哲學(xué)家,在理解生命及超越自我中難以從哲學(xué)視閾來(lái)梳理情感,不可能從童年的精神危機(jī)中感知生命的質(zhì)樸。馮歪嘴子面對(duì)生命的挫折,看到一天比一天長(zhǎng)大的孩子,能夠從中獲得生命的理解,從感情上拾起愛(ài)的希望與慰藉。然而,對(duì)于蕭紅的激蕩人生來(lái)說(shuō),這種冷靜而樂(lè)觀的生活態(tài)度,無(wú)法從人性憧憬中獲得滿足,更難成為她筆下的堅(jiān)強(qiáng)與執(zhí)著。盡管蕭紅能夠從自信中延續(xù)著對(duì)活著的執(zhí)著,但卻是悲涼的,無(wú)可奈何的。
三、情感糾葛與率性是蕭紅人生夢(mèng)幻之殤的性格悲劇
現(xiàn)實(shí)中的蕭紅在對(duì)理想的追求中,跌入了夢(mèng)幻的悲情世界。在人生的每一個(gè)階段,現(xiàn)實(shí)與夢(mèng)幻的糾葛繁復(fù),一方面強(qiáng)化了蕭紅對(duì)童年生活的懷念,一方面游走于現(xiàn)實(shí)與夢(mèng)幻之間。蕭紅與汪恩甲的婚姻是包辦的,而在蕭紅離家出走被抓回后,與未婚夫家解除婚約。其后的蕭紅再次離家與汪恩甲同居,最終兩人因矛盾糾葛而未能走到一起。蕭紅的情感因其任性而得不到“童年夢(mèng)幻”,以至于率性而為的性格成為破壞愛(ài)情誓言的尖刀。蕭紅的第二次婚姻是在真愛(ài)中度過(guò)的,蕭軍不僅不嫌棄蕭紅懷著別人的孩子,還鼓勵(lì)蕭紅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但后來(lái)又因情感不合而心生嫌隙,最終分手。蕭紅對(duì)蕭軍的大男子主義不解,而蕭軍對(duì)蕭紅的忍屈受辱最終成為兩人情感破裂的導(dǎo)火線。得不到情感慰藉的蕭紅在抱怨中近乎苛求,而蕭軍的性格也難以像蕭紅的祖父那樣滿足蕭紅的“童年夢(mèng)幻”。端木蕻良是蕭紅的第三段婚姻,也是蕭紅人生的最后一次離殤的愛(ài)情。蕭紅的率性未獲得端木的理解,在蕭紅身患重病期間不辭而別。一路跌跌撞撞的蕭紅,難以從兒時(shí)的童年夢(mèng)幻中獲得釋懷,而在其“半生盡遭白眼冷遇”的悲情呼聲中,更多的是自我感傷。短暫的生命與糾葛的情感經(jīng)歷,使人生理想幻滅,在造就蕭紅悲劇生命的情感寄托中,也加劇了其作品的困頓與坎坷。祖父的寬容與寵愛(ài)不過(guò)是童年的自由生活,是不可復(fù)制和再現(xiàn)的,其偏執(zhí)的性格,是悲情生命至死不醒悟的緣由。
蕭紅對(duì)悲劇人生的“冷處理”與樸實(shí)真摯的文字,向我們?cè)V說(shuō)了“忘卻了難以忘卻”的情感回憶,也增添了《呼蘭河傳》原始的、悲涼的審美意蘊(yùn)。對(duì)于普通的生命與生命意識(shí),在驚心動(dòng)魄的消亡中恰恰體現(xiàn)了悲劇人生的審美深度,正是這種崇高而悲壯的情感體驗(yàn),在淋漓痛快地宣泄后,為讀者呈現(xiàn)了特殊的情感。正因?yàn)槿绱耍凇逗籼m河傳》中,從蕭紅的悲劇人生的悲情意識(shí)閱讀與理解中,她所選擇的悲劇形式及悲劇內(nèi)容,從根本上抓住了莊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美學(xué)實(shí)質(zhì),從而增強(qiáng)了作品的藝術(shù)感染力。
[1]錢理群.改革民族靈魂的文學(xué)[J].十月,1982,1.
[2]蕭紅.呼蘭河傳[M].時(shí)代文藝出版社,2003:278.
[3]蕭紅.呼蘭河傳[M].時(shí)代文藝出版社,2003:296.
[4]曉川,彭放主編.蕭紅研究七十年(下卷)[M].北方文藝出版社,2011:319.
責(zé)任編輯:丁金榮
I106
A
167-6531(2015)12-0033-02
莫瑞芬/廣東科技學(xué)院教師,碩士(廣東東莞5230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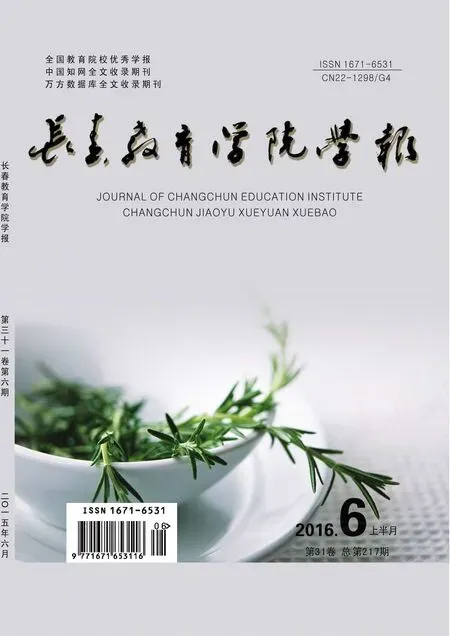 長(zhǎng)春教育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5年12期
長(zhǎng)春教育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5年12期
- 長(zhǎng)春教育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的其它文章
- 基于“研學(xué)后教”理念的初中英語(yǔ)課堂母語(yǔ)使用情況調(diào)查分析
- 詞塊教學(xué)法在初中英語(yǔ)寫作教學(xué)中應(yīng)用的實(shí)證研究
- 數(shù)學(xué)建模隊(duì)員選拔問(wèn)題解析
- 青年學(xué)生自信心、社會(huì)支持、狀態(tài)-特質(zhì)焦慮關(guān)系的研究
- 高等中醫(yī)藥院校大學(xué)生宗教經(jīng)驗(yàn)觸發(fā)因素研究
- 90后大學(xué)生心理健康教育課程實(shí)效性探究
——以嶺南師范學(xué)院生命科學(xué)與技術(shù)學(xué)院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