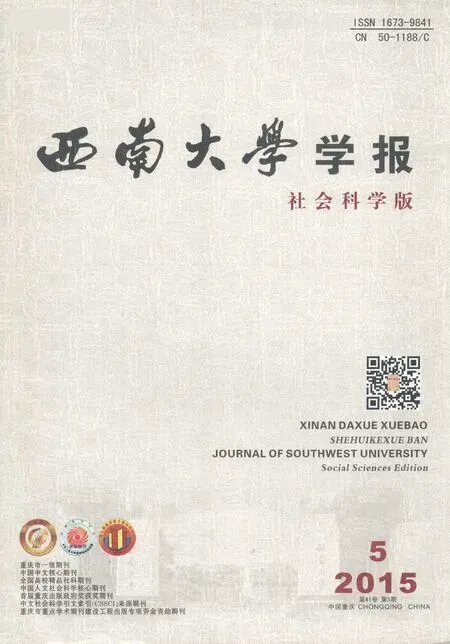新漢學時代與中國新詩
呂 進
(西南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重慶市400715)
新漢學時代與中國新詩
呂 進
(西南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重慶市400715)
目前正處于從傳統漢學到新漢學轉型的階段,這一轉型有其必要性,具體體現于中國新詩在國外的新漢學情況,尤其是在韓國和日本的研究情況以及中國現代詩學當下的前沿領域,突顯出在新漢學時代加強中國新詩研究的一些值得關注的學術問題,比如中國新詩的建設時代所面臨的“三大重建”等.
國學;西學;漢學;新漢學;中國新詩;三大重建
一、從漢學到新漢學
中國的歷史文化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有三種學科,其中,中國學者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叫“國學”.自西學東漸的清末民初以降,中國固有的或傳統的學術文化,包括哲學、歷史學、考古學、文學、語言學等,均為國學的范疇.在歷史上,章太炎、鄧實等是國學的先行者.章太炎創辦了“國學講習所”,1925年成立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在四大導師的領軍下,培養了一大批國學的著名學者.中國學者研究外國歷史文化的叫“西學”.所謂“西學”,最早是指在西方產生并傳播到中國的西方學術,印度的佛學就是中國人最早知道的西學.后來,西學不再具有“西方人的學問”的概念,而是“中國人研究西方學術的學科”,這是用中文思考、研究和寫作的學問.“學到”的經驗,“學錯”的緣由,“學失”的教訓,是西學的主要組成板塊.除開上述兩種學科外,還有一種本文考察的學科——外國學者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漢學”,即sinology,包括外國學者對中國歷史、現狀、哲學、語言、文學、藝術的研究.
俄羅斯漢學、法國漢學、英國漢學、德國漢學、美國漢學都各有成就.在歐洲的早期漢學著作中,意大利的利瑪竇所著《中國札記》、外國傳教士的書信報告集《耶穌會士通信集》(又稱《通信集》)、法國傳教士主編的《中華帝國全志》、意大利的馬可·波羅的《馬可·波羅游記》都是漢學名著.德國研究《老子》的著作達700余種,《老子》的德文譯本迄今多達82種.歐美有一批優秀的漢學家,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荷蘭萊頓大學中國研究系、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和歐美其他一些研究機構,可謂人才濟濟,碩果累累.蘇聯的費德林是可圈可點的學者,曾任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費德林和許多中國當代作家有直接交往,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都和他相識,詩人艾青更是他的摯友,他到艾青家里訪問就有多次.他當年的博士論文是關于中國詩歌的:《屈原的生平與創作》.費德林的漢學著述和中國文學作品翻譯很多,還主持編寫了15卷本的《中國文學百科全書》.瑞典的馬悅然是另一位杰出的漢學家,馬悅然師從著名漢學家高本漢,是18位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委之一,他年輕時在四川進行田野考察的成果《中國西部語音研究》為他贏得了最初的聲名.馬悅然翻譯出版了許多中國文學名著,包括郭沫若、聞一多、卞之琳、艾青等的新詩,還翻譯出版了北島和顧城的詩選《海岸和被寵壞的孩子》(1983)、《中國八十年代詩選》(1986).
作為人文學科的漢學,歷經游記漢學、傳教士漢學、學院漢學三個階段,今天已發展成為新漢學.新漢學的“新”不止于時任澳大利亞總理的陸克文(Kevin Lu)2010年4月28日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新漢學》一文的闡述.中國教育部的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國家漢辦)近年提倡面對中國的崛起和世界格局的變化,要加大拓寬傳統漢學的研究面,特別要關注當下的中國,這是新漢學的“新”的主要內容.因此,在中國文學研究領域,新漢學就不止于經史子集的研究,除了重新發現古代中國的經典,還在努力加大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份量.
中國現代文學在新舊之爭、人我之分、中西之辨中逐步站穩腳跟.在現代文學中,敘事文學逐漸走向中心,但是,詩美仍然是普遍存在,詩魂仍然是作家最高的審美理想和語言理想,詩的建設仍然牽動著整個文學的建設.詩仍是中國文學的皇冠,抒情詩仍然是這頂皇冠上的一顆珍珠.
在中國,詩從來就是文學中的文學,中國的古代文論基本就是詩論,中國文學是具有詩美特征的文學.所以對于新漢學而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中心之一是新詩,新詩是中國文學登上現代歷史舞臺的排頭兵.新詩在“現代轉型”上的文學史價值已是不爭之論.然而,文學史價值并不能簡單地等同于文學價值,它絕對不能取消這樣一個藝術事實:排頭兵只是排頭兵,只有百年歷史的新詩只是有待成熟與有待完美的中國詩歌的現代形態和現代詩歌的中國形態而已.和后起的小說等文學的散文品種相比,新詩在中國讀者那里獲得的認同度很不理想,新詩的一些似曾相識的爭論(比如詩的“變”與“常”、詩的大眾與小眾、詩的生命價值與使命價值、詩的明朗與晦澀、詩的藝術純粹與社會參與、詩的自由體與格律體等等)在近百年間不斷地去而復來,周而復始.
究其原因,可能源自新詩與幾千年的傳統詩歌美學的斷裂,成為一種無章可尋、無源可清的文體:中國新詩并不起于中國,所謂的第一首新詩——胡適《關不住了》其實是翻譯詩;新詩采用的標點和分行都來自異域.新詩的開創人胡適與郭沫若在新詩初期的一些說法做出了錯誤的導向.比如胡適在《嘗試集自序》中說:“詩體的大解放就是把從前一切束縛自由的枷鎖鐐銬,一起打破: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話怎么說,就怎么說.”郭沫若在《三葉集》中也主張詩應該“打破一切形式”,“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詩形,也不失其詩”,并且稱新詩是“裸體美人”.
這些詩文不分的言論給新詩的美學建設造成了負面作用,新詩的先天不足由此而生.一直到了20世紀30年代,提倡新詩由破格轉向創格的聞一多出現了,他在中外古今的聯結點上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主要參照系提出“戴著鐐銬跳舞”的現代格律論,新詩由此進入建設時期.這個建設時期進展非常緩慢,以致新詩是不是需要有共同的作為詩歌藝術的審美標準也成了爭論不休的話題.所以,新詩研究是新漢學的一個難題,對從事這一研究的漢學家值得鞠躬.
二、韓國和日本的新詩研究
對中國新詩進行翻譯和研究的,既有俄羅斯和歐美的漢學家①德國波恩大學的顧彬、曾任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院長的施舟人和在德國慕尼黑大學、漢堡大學等高校任教的施寒微,號稱當今歐洲的三大漢學家,他們對新詩均有所涉及.前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契爾卡斯基的俄語著作《戰爭年代的中國詩歌(1937-1949)》(前蘇聯解體后契爾卡斯基已移民以色列)、荷蘭漢學家柯頓的《粉碎的語言:中國當代詩歌與多多》和《精神、混亂和金錢時代的中國詩歌》等著作,都是研究中國新詩有影響的專著.,更有東亞的漢學家.在東亞,韓國和日本漢學家的中國新詩研究大大超過其他地區的漢學家.就是從漢語新詩的創作來看,不說僑居在東亞的華人詩人(數量很多,而且越來越多),單說外國人中的漢語詩人,目下就已經有了一個可觀的隊列.隨意地舉出一些姓名吧:馬來西亞有吳岸、蘇清強、杰倫、王濤、晨露、孟沙、彼岸和方昂,新加坡有賀蘭寧、秦林、方然、周粲、陳劍、長瑤、簡笛、希尼爾、南子、適民、史英、沈壁浩和曦林,這兩個以華族為主的國家被稱作今日地球村的漢語新詩重鎮.菲律賓的云鶴、月曲了、明澈,印度尼西亞的顧長福、旭陽,越南的林小東,文萊的海庭,泰國的曾心,他們都是土生土長的“老外”.
先說說韓國漢學的中國新詩研究.
近年從事漢學研究的韓國學者逐日增多,一百多所高校紛紛設立漢學專業,有關中國新詩研究的碩博士論文也有相當數量.韓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會長樸宰雨先生曾說,韓國光復后的中國新詩研究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開拓期(1990年前);第二時期(1991-2000);第三時期(新世紀).從1947年尹永春翻譯出版《現代中國詩選》(青年社)開始,韓國翻譯中國現代詩人作品的活動一直持續不斷,詩人艾青、郭沫若、北島、舒婷尤為韓國漢學界所矚目.1930年《朝鮮日報》連載的丁永東的《中國新詩概觀》是最早的研究中國新詩的文獻.中國新詩研究的開山之作是許世旭先生的《中國現代詩研究》(明文堂出版社,1992),此書論述的時間囊括20世紀20年代至70年代,論述視野除了中國內地,還包括了中國臺灣.1994年,韓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編輯出版《中國現代詩和詩論》.樸宰雨先生近年和中國詩人合作,多次主辦了韓中詩歌朗誦會,并出席西南大學和北京《文藝研究》雜志社主辦的第四屆華文詩學名家國際論壇,發表主題講演.釜山的東亞大學近些年主辦過多次中國新詩國際學術研討會.
談到韓國的中國新詩研究,本文想重點談談韓國漢學家許世旭先生.
許世旭畢業于韓國外國語大學中文系,然后到臺灣師范大學留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回國后,先后在韓國外國語大學和高麗大學執教.他說:“我究竟發現了一條路,中國詩歌,無論新舊,是一座甘泉.”[1]到臺灣的第二年,許世旭就開始了中國新詩的創作與研究,他是用韓語和漢語同時寫作的雙語作家和學者.他與臺灣當代許多著名新詩人都有交往,《創世紀》的洛夫、痖弦、張默這三劍客都是他的好友.
許世旭生前是韓國中語中文學會會長和韓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會長,出過幾本用中文寫作的現代派詩集:《雪花賦》(臺北聯經出版社,1985)、《東方之戀》(三聯書店,1994)和《一盞燈》(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他是美國伯克利大學、中國復旦大學和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的客座教授,多次到所里講學.在慶祝中國新詩研究所建所20周年的時候,他寫過一篇文章《在有山有水的校園里,我曾做過島民》[2]522,深情而又細致地回顧了在中國新詩研究所講學的日子.
《一盞燈》里有一首《懷北碚》[3]119,詩里有這么幾行:
吠日的地方做客好
坡下有清瘦的高個子站著
供我一個夜也吃不飽的火鍋。
這是寫的在我家吃火鍋的趣事,我就是他筆下的“清瘦的高個子”.當晚我準備了火鍋,在家里招待許世旭吃飯.突然停電,于是,在黑暗里,他只好就近吃著擺在面前的一碗紅苕粉,當然就“一個夜也吃不飽”了.
1998年,臺灣三民書局出版許世旭用中文寫的《新詩論》.著者梳理了中國新詩與傳統詩歌的關系,勾勒了臺灣新詩的發展軌跡,比較研究了兩岸新詩,這是韓國學者研究中國新詩的力作.書中有一篇論文是《兩岸新詩的發展比較(1949-1989)》,他在中國新詩研究所講這篇文章時,以對人嚴格著稱的中國老詩人方敬(時任西南師范大學副校長)也帶頭鼓掌,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我經常想起在《一盞燈》的《自序》里許世旭寫的話:“希望我的一盞燈能夠照亮中國的一塊角落,還希望中國的讀者能記住黃河的河口,在度過黃海的那一邊有一個韓國的詩人從小喜歡中國,又愛上過中國人這種跨海的戀情.”[3]2
再說說日本漢學的中國新詩研究.
日本大規模翻譯介紹中國新詩,是從1949年新中國建立開始的.日本對中國新詩的研究開始得很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1920年,京都帝國大學教授青木正兒在該大學的校刊《支那學》雜志上,介紹了胡適倡導的白話詩運動.緊接著,1922年出版了大西齊、共田浩編譯的《文學革命與白話新詩》一書.該書首次用日語將中國的白話詩系統地加以譯介.之后,又陸陸續續地出版了一些相關書籍①這里采用了我與巖佐昌暲先生用對話體合寫的《中國與日本:中國現代詩學的昨天和今天》中巖佐先生的論述,見《文藝研究》2007年第6期..在研究中國新詩的日本漢學家中,本文想重點介紹兩位學者.
秋吉紀夫先生(1930年生,九州大學榮譽教授)在研究中國現代詩方面是老一輩的首屈一指的專家.
秋吉先生是詩人和學者,詩集和著述頗多.他曾到重慶采訪詩人梁上泉、方敬,也到過中國新詩研究所.最令人感佩的是從1989年到1998年十年間陸續出版的《精選現代中國詩集》,這套詩集由日本土曜美術社出版,計有《馮至詩集》(1989)、《何其芳詩集》(1991)、《卞之琳詩集》(1992)、《穆旦詩集》(1994)、《艾青詩集》(1995)、《戴望舒詩集》(1996)、《陳千武詩集》(1996)、《阿垅詩集》(1997)、《鄭敏詩集》(1997)、《牛漢詩集》(1998),共10部.每部詩集的前面,都有秋吉先生的研究論文,在翻譯的代表作后面,還附上年譜、著作目錄和研究資料.秋吉先生出版的《陳千武論》(土曜美術社,1997)也頗具功力.他的公子秋吉收,子承父業,也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兩次到過中國新詩研究所.
漢學是外國研究中國的學問,由于各國各自知識系統的不同,便產生了解釋中國的不同角度.這樣,漢學就為中國人多了一個思考自身的角度.秋吉久紀夫在《何其芳詩集》里翻譯介紹了何其芳的詩《我看見了一匹小小的驢子》.看著小驢子輕快地歡跳,詩人嘆息:
它不知道它長大了的時候
它的背上將壓上什么東西
作為中國的詩評人,我原來不很注意這首詩.待得讀到秋吉先生的翻譯和評說,我才悟出了這首詩的人性含量和愛的溫馨,確認了這首短詩的價值.
另一位日本漢學家是巖佐昌暲先生.
巖佐1942年生,畢業于大阪市立大學,長期擔任日本九州大學教授,2005年任九州大學榮譽教授、熊本學園大學教授.他是日本郭沫若研究會會長,也曾長期擔任九州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巖佐是極少數在北京親身經歷過“文革”的外國專家,當時他是廖承志領導下的外國專家組成員.文革詩歌和郭沫若研究是巖佐付出了許多精力的領域,他還研究朦朧詩并撰寫了一系列論文.在中國新詩研究方面,編著有《詩刊(1957-1964)總目錄·作者名索引》、《紅衛兵詩歌選》(與劉福春合編)、《郭沫若的世界》.2014年汲古書院出版的《中國現代詩史研究》是一本有份量的漢學著作.這本書分曙光的時代、建國后十七年的詩壇、文革時期的現代詩和新時期的現代詩四章(日文稱作“四部”)展開論述,學術含量比較高.比如在第四章里,作者分節敘述了朦朧詩、朦朧后、“歸來者”詩人、“新生代”詩人、老詩人和香港現代詩,是外國人的中國新詩研究著作的佼佼者.在日本漢學家中,巖佐昌暲有自己的治學方法.日本漢學家研究中國現代詩歌,最大特點就是以非常精密準確的論證為基礎來解釋詩歌,因此,一般都會以“關于某某詩人的某首詩”的形式來寫論文,通過精密的解讀,把詩人的詩的世界清晰地展現在人們的眼前.應該說,這是日本學者的基本研究模式.中國學者常常做的一些宏觀的理論研究,在日本不被看好.巖佐昌暲肯定日本學者的治學方式,但是同時提醒,過于拘泥于細節,就會有迷失大方向的危險,在研究過程中始終要保持一種意識,就是在現代詩歌的研究中,自己處于什么樣的位置,自己到底能為整個研究做出什么樣的貢獻.這是很有見地的,對研究方法論有這樣的洞見的日本學者并不多見.
巖佐昌暲是中國新詩研究所的客座教授,和中國新詩研究所關系密切,和我的友誼非常深厚.他用中文寫過一篇文章《呂進兄,辛苦了》,文章回憶了他和我的十幾年的交往,他說:“我比較了解呂進這位詩人、詩歌評論家.我喜歡他的坦率、熱情和幽默.他的這些性格特點是通過跟他的極平凡的交往中體會到的.”[2]528
在新漢學時代,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中國新詩研究這個領域,正在等待有心人的開拓.
三、中國新詩的建設時代
正處在建設時期的新詩,面臨三大前沿問題:實現“精神大解放”以后的詩歌精神重建;實現“詩體大解放”以后的詩體重建;運用現代科技條件的詩歌傳播方式重建.這三大重建,關涉到中國新詩的發展甚至興衰,新漢學應該予以更大關注.
關于精神重建.從誕生以來,現代詩學就在重建屬于自己時代的詩歌精神.在比較長的時期里,新詩比古詩更加強調詩的政治屬性,更加看重“大我”,更加張揚“炸彈”和“旗幟”的社會功能.這是現當代中國歷史環境使然,有其歷史的合理性.應當說,在多災多難的中國,除了加強自身的社會關懷,詩別無出路.在生存的苦難下,在戰爭的硝煙中,在革命的大潮里,詩不可能脫離民族的憂患去一味地抒發生命關懷.但是,庸俗社會學困擾著、折騰著、毀滅著詩歌.許多詩歌偏離了藝術本質和藝術軌道,成了單純的政治工具和傳聲筒.在20世紀的新時期,現代詩學在思想解放運動中獲得精神大解放.詩學界批判“左”的桎梏,革除思維惰性,打破習慣定勢,圍繞詩歌本體解決了一系列詩學理論問題,推動詩歌擺脫長期以來的詩外承載,使詩得以回歸自身.從80年代后期開始,新詩漸入困境.于是,精神重建中的某些偏頗也暴露在人們面前.新詩出現的精神危機主要表現為新詩的社會身份和承擔品格的危機.在藝術上有了長足進步的同時,新詩又在相當程度上脫離了社會與時代.多元掩蓋了偽詩.詩回歸本位,當然是回歸詩之為詩的美學本質,但絕不是回歸詩人狹小的自我天地.當前詩歌精神重建的中心正在于此.
詩體重建是當前現代詩學界的又一熱門話題,不僅中國,全世界的華文詩歌界都在熱烈討論.新詩是從詩體的突破中誕生的,它是“詩體大解放”的產物.從“詩體解放”到“詩體重建”本是合乎邏輯的發展.然而,由于長期戰爭、動亂的外部環境的局限,更由于在理念上對“新詩”的“新”的誤讀(就像梁實秋在《新詩的格調及其他》一文中所說:“新詩運動的最早的幾年,大家注重的是‘白話’,不是‘詩’,大家努力的是擺脫舊詩的藩籬,不是如何建設新詩的根基.”其實,豈止是“最初幾年”,可以說,對新詩的這個“根基”的忽略是長期的).總體而言,新詩的詩體重建在20世紀的進展比較緩慢.極端地說,不少舊體詩有形式而無內容,而不少新詩則是有內容而無形式.詩體重建的缺失使詩人感到新詩詩體缺乏審美表現力(所以包括郭沫若、臧克家在內的不少詩人在晚年出現了聞一多說的“勒馬回韁寫舊詩”的現象),使讀者感到新詩詩體缺乏審美感染力(所以不少讀者在走出青年時代后就不再親近新詩,而是去讀唐詩宋詞了).提升自由詩,成形現代格律詩,增多詩體,是詩體重建的三個美學使命.
詩歌傳播方式的重建在近年進展最快.在“互聯網+”的時代,詩歌傳播面臨最好境遇.近年中國詩壇上“烏青體”的出現,農民詩人余秀華的崛起,都和網絡的造勢密不可分.互聯網為詩開辟了新的空間.日益發展的網絡傳播對詩歌創作、詩歌研究、詩歌傳播都提出了許多此前從來沒有的理論問題.信息媒介的變化能夠導致人的思維方式和審美方式的變化.作為公開、公平、公正的大眾傳媒,網絡給詩歌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網絡詩以它向社會大眾的進軍,向時間和空間的進軍,證明了自己的實力和發展前景.現代人在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休閑方式等方面的大變化,都為增多詩體提供了條件和可能.比如,運用憑借聲光音像,豐富自己的體式,就是增多詩體的一條坦途.當下的歌詞和PTV等等,都不僅具有操作意義,也很有詩學的理論價值.
[1]許世旭.新詩論[M].臺北:三民書局,1998:2.
[2]呂進.呂進文存:第4卷[M].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3]許世旭.一盞燈[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
責任編輯 韓云波
I207.25
A
1673-9841(2015)05-0108-05
10.13718/j.cnki.xdsk.2015.05.015
2015-06-03
呂進,西南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