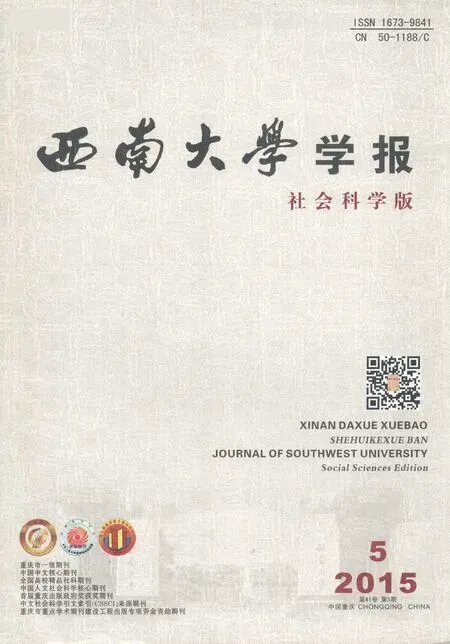如何更好地對待弱勢群體?
秦子忠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北京市100872)
如何更好地對待弱勢群體?
秦子忠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北京市100872)
如何更好地對待弱勢群體?對這個問題的回答至少有三種路徑:一是主張無差別對待的路徑,二是主張高于門檻水平對待的路徑,三是主張恰當對待的路徑.與前兩種路徑相比,后一路徑的主要優勢在于它既能夠充分尊重弱勢群體中那些理性健全者的自主選擇,又能夠合理地解決該群體中那些理性不健全者的救助性問題.
弱勢群體;平等主義;充分主義;恰當主義;分配正義;“項目-互惠”體系
“如何更好地對待弱勢群體?”這一問題,是完善我國福利體系的核心議題之一.但是就國內研究現狀來看,研究該問題的實證性文獻雖然很豐富但規范性文獻卻明顯不足.在本文中,筆者側重從規范性視角來看待這個問題,并期待這種分析與探索能夠深化人們對該問題的認識以及助力于我國當前的社會保障體系改革.在筆者看來,這個問題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內容:一是“弱勢群體”的識別,即目標群體如何確定;二是解讀“更好”的理念,即怎樣才能算是更好地對待;三是“對待”的方式,即誰實施補償以及如何實施.本文將依次考察它們.
一、尺度與“弱勢群體”的構成
如何識別社會中需要救助的人群,有兩種基本的致思路徑:一是基于直覺主義的判斷,二是基于深思熟慮而制定的尺度.直覺主義路徑的優越性是它可以高效地排除那些明顯不需要救助的人群,比如,與居住于棚戶區的殘疾者相比,憑直覺,就能將居住于高檔小區中的健康者排除在目標群體之外.[1]但是,直覺主義路徑的局限性是它難以察覺隱蔽的或細微的差別,比如,當救助物資非常有限時,它自身難以合理地在由痛苦者、貧者、殘疾者等人構成的群體中將某些人排除在目標群體之外.[2]33就此而言,與直覺路徑相比,基于深思熟慮而制定的尺度(比如羅爾斯的基本善),就是一種相對合理的路徑.但問題是,如阿瑪蒂亞·森所言,尺度的選取本身具有巨大的切割力,“這既是因為它將一些有潛在價值的對象包括進來,也是因為它將把另外一些給排除出去”[3]33.相應地,依據的尺度不同,目標群體的構成也不相同.以下的討論將展示:尺度的選取深刻地影響目標群體的構成.
當效用作為尺度時,個人的快樂及其強度、偏好滿足及其程度才是相關的信息,其他方面則被忽略掉.因此,以效用為尺度,快樂強度或偏好滿足程度最低的那些人員才被識別為要加以補償的目標群體.但是,效用尺度的主要缺陷是它的信息束太窄,以至當福利政策以它為標準時會產生一些違背道德直覺的現象.比如,它會把痛苦的富人納入目標群體中,而將具有開朗性格的殘疾人排除在外.[4]217
與效用不同,羅爾斯提倡的基本善排除了個人的主觀感受,它是一系列益品的集合,該集合包括如下元素,自由、機會、收入、財富、自尊的社會基礎.這些元素,都是個人在社會中實現其人生價值所必需的東西,因此,這些元素的有無以及量上的多寡,都會直接地影響一個人的生活質量.[2]93因此,以基本善為尺度,自由和機會不足、收入和財富較少的那些人員才會被識別為要加以補償的目標群體.與效用尺度相對照,依據基本善尺度,被列入目標群體中的那些人,可以是快樂的窮人,但不可以是痛苦的富人.不過,以基本善為尺度會在兩個方面違背道德直覺:一是它忽視對生理缺陷的補償問題,因為它使得一部分殘疾人被排除在目標群體之外;二是它沒有恰當地處理個人責任問題,因為它使得一些有就業能力卻選擇游手好閑的人會被不合理地納入目標群體當中.[5]2
當尺度從效用和基本善轉移到阿瑪蒂亞·森提倡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時,相關的信息束既不是個人的主觀感受也不是外在于個人的資源束,而是介于兩者之間的東西,比如個人的各種活動和狀態,以及獲取這些活動和狀態的自由.依據可行能力尺度,營養不良者、體弱多病者、能力缺失者(比如癱瘓者、不能參與共同體生活者等)都會被識別出來并被列入目標群體之中.[4]218因為基本善的不足,效用的不足,都會給個人活動和狀態帶來負面影響(比如無財富、無收入致使某些人挨餓和營養不良,無受教育機會致使某些人喪失參與共同體生活的部分能力,長期精神抑郁致使某些人身體素質較差,等).因此,依據可行能力尺度,被識別出來的目標群體,其范圍要大于由效用尺度(或由基本善尺度)識別出來的目標群體的范圍.顯然,可行能力尺度能很好地處理針對生理缺陷的補償問題,但是它依然沒有恰當地處理個人的責任問題.假定A和B具有等價的可行能力,但是A選擇過冒險性生活而B則選擇安穩生活,結果A在一次登山時摔斷雙腳.此時,有兩種可能情形:一是將A列入目標群體當中,但是這種做法沒有考慮A的個人責任問題;二是將A排除在目標群體之外,這種做法顯然要求A要為他自己的選擇行為承擔相應責任.按照可行能力尺度,它會偏向第一種情形.問題是,這種不考慮個人責任的補償舉措可能一方面會鼓勵一些沒必要的冒險和犧牲,另一方面也會加重其他社會成員的負擔(以稅收的形式),并且對那些因非選擇性原因而失去雙腳的人也是不公平的.進而言之,如果識別目標群體的尺度的設計沒能妥當地處理個人責任問題,那么它將成為誘發福利依賴問題的根源之一.
充分考慮個人責任在福利體系中的分量,要求相關方在制定福利體系時,要區分不可責備的弱者和可責備的弱者,然后優先地對前者進行補償,或者給予前者的補償份額要高于后者的份額,如果不是將可責備的弱者全部排除在目標群體之外的話.[6]340就此而言,科恩的相關工作是值得重視的.
科恩提倡的優勢可及(access to advantage),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被看成是前三種尺度的并集.科恩賦予“優勢”(advantage)術語以豐富的內涵,它包括個人的效用方面、可行能力方面,也包括個人的益品方面.相應地,“可及”(access)術語也被賦予豐富的內涵,它除了其通常含義(比如可及的這一通常用法:對于空氣人人都可及它)外,還具有這樣的擴展義,即將那些不是由個人直接導致的可及物(比如空氣)也看成是個人實際擁有的東西.[7]380“可及”是自由家族中的一位成員,它與外在性條件和主體性條件相關.因此當某個人對優勢缺乏可及性時,如果缺乏的原因純粹是外在性條件使然,那么個人對其劣勢是完全不負責任的;如果缺乏的原因純粹是個人選擇使然,那么個人對其劣勢是完全負責任的;如果缺乏的原因是由兩者共同使然,那么個人對其劣勢只能負部分責任.[8]922-925不過需要指出,科恩實際上認為完全選擇(或者完全負責)的情形幾乎是不存在的,他這樣指出:“我們并不是要在真正選擇的存在與缺失之間作出絕對的區分.選擇中的真正性數量是個程度的問題……這個程度是幾個東西的函數,而個人處境中的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完全歸于真正的選擇.”[8]923追隨科恩,福利體系的補償份額應當如此設計,以至于它能體現這樣的觀念:如果個人的處境變壞與其選擇這樣行為相關,那么當他的選擇行為對其不幸處境的貢獻越多時,他應得的補償份額就應當越少.這樣,依據優勢可及尺度被識別出來的目標群體,它的范圍至少不會小于前三種尺度中任何一個尺度所產生的目標群體的范圍.
二、解讀“更好”的理念
以上的論述表明,目標群體的構成及其范圍,會隨著尺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別.哪個尺度更好,實質上可以轉換成這樣的問題,哪個尺度識別出的目標群體的構成及其范圍更具合理性或者更吻合人們的道德直覺.由此看來,“更好地對待弱勢群體”中的“更好”可以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如何確定目標群體的構成及其范圍或者說如何選取識別目標群體的尺度,二是如何選取對待目標群體的方式.第一方面在第一節的討論中已經得到詳細的說明.第二方面將在第三節中得到討論.本節的討論只涉及我們應當如何界定“更好”的問題,或者說,在關于“更好”的多種解讀路徑中如何挑選出最不差的那個路徑.
就當前文獻而言,“更好”至少存在三個解讀路徑,其核心理念分別是:平等理念,充分理念,恰當理念.實際上景天魁先生早在2003年就注意到,“中國社會保障研究最缺乏的是理念”.[9]但是時隔12年,中國社會保障研究最缺乏的可能不是理念而是在學理層面上對諸多理念進行辨析與評估.因此,以下討論某種意義可算是景先生議題的延展性探討.
首先是平等理念.一般而言,平等是指無差別(相近術語有同一、同樣等).因為人與人之間既存在外部性的差別,也存在內部性差別,因此無差別對待每個人,意味著不平等本身就是壞的,或不平等的效果就是壞的,因而不平等應當被消除.[10]3-6設想這樣的社會,其中A群體處境好,B群體處境壞.這樣,在資源的分配中,無差別對待可以采取以下三種方式之一:一是某方面向上同一,即將B群體處境提高到和A群體處境一樣好的水平上;但是這種方式會遭遇自然資源承載力不足的瓶頸.北歐國家當前面臨的福利病,就其深層根源而言,就是它以這種平等形式作為其指導理念.不過,也有學者如此主張: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北歐諸國所進行的一系列社會政策改革已經使得它們的福利制度在深層次上偏離了平等理念.[11][12]二是某方面向下同一,即將A群體處境拉低到和B群體處境一樣差的水平上;這種方式可以避免資源瓶頸問題,但是它卻難以回應由帕菲特(Derek Parfit)所展示的“拉平反駁”(leveling down)[10]16-17.拉平反駁揭示了這樣的荒謬性,即如果某類事情發生,A群體的財物將全部消失以至于他們與B群體一樣貧困,那么這類事件將不僅不被防止反而被促成,即便在這個事件中沒有人受益.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的具有平均主義特征的福利制度,可以近似地看作拉平反駁的一個例證.[13]三是某方面局部同一,即同一地對待某一群體而與另一群體無關.我國現存的城鄉二元分離的福利制度可以近似視為這種方式的一個事例.這種方式既可以避免資源瓶頸問題也可以避免拉平反駁,但是它依然會遭遇困難,比如沒有很好地處理個人責任問題.假定張三和李四同是城市中(或者鄉村中)的具有同等劣勢的人員.如果張三的劣勢是由于好吃懶做,而李四的劣勢則是由于先天性殘疾,那么這種方式(即不加以區分地給予他倆同樣的補償份額),顯然沒有很好地處理張三的個人責任問題.
為了回應批評或避免困境,當無差別對待從第一種方式退回到第三種方式時,平等理念實際上已經從其絕對的價值立場(即平等具有內在的價值)退回到相對的價值立場(即平等的價值在于它促進其他價值的實現).[14]33-40如果平等的價值僅是作為工具價值而非內在價值,那么,在資源的分配中,它的道德重要性就是非常可疑的.法蘭克福特(Harry Frankfurt)就指出:“經濟平等本身并不具有特別的道德重要性.從道德觀點來看,就經濟財物的分配而言,重要的不是每個人都應當具有相同的(the same),而是每個人應當具有足夠的(enough)……我把這種對平等主義的替代物……稱為‘充分性(sufficiency)學說’.”[15]21-22
其次是充分理念.充分是一個比較性概念,因為它總是相對于某個基準線或門檻而言的.據此,我們可以從兩個視角來闡述充分理念:一是如果既定的門檻水平被滿足,那么這個滿足本身就是充分的;另一是如果既定的門檻水平被超過而非僅僅被滿足,那么這個超過本身就是充分的.這兩個視角通過門檻水平的確定而關聯在一起,但是它們的關注點并不完全一致——前者只關注事態中的資源信息而后者同時兼顧事態中的個人責任信息.法蘭克福特著重從第一個視角闡述他的充分理念,即“在充分性學說中,‘足夠’概念的使用是指滿足某個標準而不是達到某個極限”[15]37,低于這個標準(即門檻水平)意味著相關資源的不足或缺乏.法蘭克福特舉了這樣一個證明充分理念優越于平等理念的例子:有10個人,每個人維持生命至少需要5個單位資源,總資源40個單位.按照平等理念,10個人都將會餓死(因為每個人都具有同樣單位的資源,但是4個單位資源不能維持生命).按照充分理念,至少8個人能夠活下來(通過把標準或門檻設定為5個單位資源).為了避免整體性毀滅,充分理念看來是更有說服力的.但問題是,誰應當是那幸運活下來的8個人之一,或者說誰應當是那不幸餓死的2個人之一.這一涉及道德因素的問題在法蘭克福特那里遠非清楚,這或許是因為他用以說明充分理念的這類事例過于依賴這一做法,即將門檻水平作為區分生與死的分界線.假定門檻水平不再是作為生與死而是作為多與少的分界線,那么道德因素的問題便有了更多討論的余地.這個余地是從第二視角解讀充分理念的吸引力所在.從第二個視角來看,充分理念體現為它所蘊含的補償方式在滿足既定的門檻水平之后還存在一個浮動區間.但是,如何確定門檻的水平?這并不是一個毫無爭議的問題.[14]28-29這個問題的復雜性不僅與社會(而非僅僅福利體系)的總物資水平有關,而且與當時社會文化對體面生活的理解或界定有關.
不過,暫且將確定門檻水平的問題放在一邊.我們來看充分理念涉及的第二個問題,即門檻是一種還是多種?如果門檻只有一種,那么充分理念不僅依然殘留平等理念的痕跡,而且依然沒有解決個人責任問題.因為當門檻只有一種時,在門檻水平既定的前提下,充分理念類似于以第三種方式出現的平等理念(即無差別地對待某一群體而與另一群體無關);兩者的區別在于,無差別補償是給予相關者以同樣的補償份額,因而無視個人責任問題;充分補償則可以如此處理個人責任問題,即在浮動區間范圍內,有差別地對待目標群體中可責備的成員和不可責備的成員,比如給予前者較低些的補償而給予后者較高些的補償.顯然,充分理念處理個人責任的方式比平等理念更為靈活些,但是這種方式不是解決而只是緩解個人責任及其導致的相關問題.如果門檻有多種,那么它可以擺脫平等理念的束縛,但它是否解決了個人責任問題則需具體討論.當門檻不止一種時,充分理念已經將多樣性吸納其中.假定充分理念如此區分若干種門檻,比如說,將門檻按照個人對事態負責的程度而區分為三種梯度逐漸上升的門檻,第一種針對的是目標群體中完全可責備的成員,第二種針對其中部分可責備的成員,第三種針對其中完全不可責備的成員.顯然,按照這個假定,充分理念將很好地處理(我不是說完全解決)個人責任問題.但是當充分理念如此處理門檻時,它已經滑向以下將討論的恰當理念.恰當理念類似于吸納多樣性的充分理念,但兩者的區分是明顯的.
最后是恰當理念.與前兩個理念有所不同,恰當理念既不要求無差別的對待,也不要求高于門檻水平的對待,而是要求恰當的對待,或者用戴維·米勒的話來說,要求“以適合于每個個體自己的方式對待每個人”[16]35.設想這樣的場景,A和B的腳分別是20碼和30碼,他們都欲求與其腳適合的鞋子.如果現在有兩雙鞋子且尺碼分別為20碼、30碼(暫且不考慮鞋子其他方面),那么當A和B分別得到20碼、30碼的鞋子時,我們就可以說,A和B得到了恰當的對待.在這個場景中,恰當理念關注了兩方面的信息:一是目標群體的成員的具體信息(比如腳的大小),另一是待分配物的具體信息(比如鞋子的尺碼).轉換到福利體系場景,恰當理念在處理個人責任問題上,它可以區別地對待目標群體中的完全可責備成員、部分可責備成員和完全不可責備成員;在處理同組成員(比如先天性殘疾者組成的集合)的需求問題上,它可以因人而異地滿足他們的需求,即給他們提供多樣化的補償選項,比如一定數量的金錢,等價的培訓,等價的就業崗位,甚至等價的實物等.顯然,除了對待方式不同外,恰當理念所關注的信息束也不同于前兩個理念所關注的信息束,進一步說,恰當理念的信息束較其他兩個信息束更加寬闊.問題是,與前兩個理念相比,恰當理念所蘊含的補償方式會不會因為成本過高而缺乏可行性?這依然是一個開放性的問題,對此本節不再討論.下一節,我將集中探討恰當理念所蘊含的補償方式,以深化我們對恰當理念的理解.
在進入下節討論之前,我將概述中國當前福利研究現狀的三個隱患.國內學者如景天魁[17]、鄭功成[18]、王陽[19]等人的研究從多個維度證實了我國當前福利體系建構有著朝向普遍型福利的發展趨勢.這種普遍型福利,具有全覆蓋和無差別的特征.由于我國人口數量龐大并且地區發展不平衡,因此緊隨全覆蓋與無差別特征的是中國福利體系在一段時期內將具有低水平特征.然而,如上文提及的法蘭克福特的那個例子所示,當“低水平”低于某個數值時,整體福利效果有可能是微乎其微的.此其一.其二,全覆蓋與無差別傾向是北歐國家患上福利病的深層原因.然而從國內權威性研究報告來看,這些深層原因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考量.因而這類報告不但沒有警惕反而通常會預設一個主導型政府并且對中國經濟發展也寄予過高的預期.如果以上所論述的三個理念的演進能夠合理地反映發達國家福利制度的歷史演進,那么我國在構建自己的福利體系時就應該警惕而非崇尚平等理念.因為平等理念極易忽視個人責任、挫傷主體性,因而也極易抑制經濟效率、促生福利依賴.實際上,國內早有學者對我國福利依賴的現狀與影響、原因以及預防對策進行了有益的研究.[20][21][22]但這類研究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其三,我國建構的福利體系有可能過分強化政府的責任而沒有充分培育其他主體的責任.
三、實施“對待”的主體與方式
上面論述的三種理念,每一個都有支持它的合理理由.但是以不同的理念作為構建福利體系的指導思想,會產生非常不同的后果.不過,在“如何更好地對待弱勢群體?”這一問題中,以它們任何一個作為解讀“更好”的理念,都會涉及誰(即主體僅僅是國家,還是還有組織、個人,甚至目標群體中的成員自身?)來實施補償以及如何(即補償方式僅僅是基于稅收的再分配,還是還有慈善,合作互惠?)實施補償的問題.在福利體系中,國家是唯一主體(或絕對主導性主體)的情形,顯然區別于國家是重要主體(或輔助性主體)的情形;并且,國家采取直接的補償方式的情形,顯然也區別于采取間接的補償方式的情形.這兩種區分結合在一起就產生四種不同的與國家相關的補償方式: (1)國家主導直接方式;(2)國家主導間接方式;(3)國家輔助直接方式;(4)國家輔助間接方式.這些方式當然不是涇渭分明的,但是將它們等同的做法無助于清晰地闡釋問題.為了避免誤解也為了便于討論,針對這四種方式,本文支持這種做法,即除了質上的限制外,同時引入量上的限制作為區分它們的必要條件:一是國家投入到任意一種方式中的稅收資源總量是相同的①福利支出的具體數額應確定為多少,這是一個值得高度重視的問題.希臘當前的主權債務危機某種意義上就是沒有處理好福利支出與經濟發展承載力之間的平衡關系.我國在構建自己的福利體系藍圖時,應當以希臘當前的高福利困境為前車之鑒.;二是福利體系中國家稅收資源總量與福利體系中所有資源總量的比例不大于某個值時,它的主導性身份便滑向輔助性身份;三是當國家用以救助弱勢群體的直接性稅收資源總量(比如金錢、食物、住所等)與其間接性稅收資源總量(比如購買第三方組織服務目標群體的產品、項目等)的比例不大于某個值,它的補償方式便由直接方式滑向間接方式.
在這里,對每個補償方式進行面面俱到的論述是不合適的.基于主題和篇幅的考慮,我將探討支持或者相容于恰當理念的三種福利體系,即“底線-迎合體系”、“保險-慈善體系”與“項目-互惠體系”.每種福利體系都涉及上面四種補償方式中的一種或多種.因為每個福利體系都比上述四種補償方式中任何一個具有更高的抽象性.
首先是“底線-迎合體系”.在這個福利體系中,國家是唯一主體,維持福利體系的資源單純地來源于強制性稅收,其補償方式近似于作為多樣性的充分理念所允許的方式——根據現實情況而確定各種門檻并且允許一定浮動.這些門檻的確定即所謂的“底線”.一定浮動所顯示的靈活性即所謂的“迎合”.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在這個體系中,恰當理念在操作層面上完全等同于作為多樣性的充分理念.這里至少有兩方面的原因可以說明這點.一是它們所依據的信息基礎不同,二是它們接受“底線”(即門檻)和“迎合”(即浮動)的理由不同.第一方面原因見上一節的討論,以下著重探討第二方面原因.恰當理念接受“底線-迎合體系”的理由是出于現實復雜性的考察,比如因為現實社會并不存在純粹的個人選擇,因而在實際操作中,只能做到相對精確(而非絕對精確)地處理事態中的個人責任問題,這意味著它要確定各種類型的補償的基準線或“底線”;“迎合”則是就基準線內容而言,它要求在基準線允許的范圍內,要適當考慮目標群體的需求,進而提供等價的多樣化的補償選項.與此不同,充分理念是一個比較性理念,它自身預設與之相對比的基準線或門檻,它的充分性體現在給予高于基準線的補償份額;而“浮動”只是就基準線水平而言,它只要求高于基準線水平,既不要求考慮目標群體的需要,也不要求提供多樣性的補償選項.不過,“底線-迎合體系”存在兩點不足:一是過于依賴國家作用而沒有吸納社會上的其他可利用性資源,二是沒有充分地考慮到目標群體的多樣性及其生活方式的流變性.
其次是“保險-慈善體系”.與“底線-迎合體系”不同,在這個體系中,國家、慈善企業、公益性組織、慈善人士等都是主體;相應地,維持福利體系的資源不再單純依靠國家稅收的支持.在這個體系中,國家的作用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為目標群體提供可自由選擇的保險選項,二是為其他主體幫助目標群體提供相應的慈善網絡,即各種渠道.因此在“保險-慈善體系”中,國家投入的資源需要按照某個比例把一部分用以維持提供給目標群體使用的保險選項系統,另一部分用以建立和完善提供給其他慈善主體使用的慈善網絡.初看起來,與“底線-迎合體系”相比,在“保險-慈善體系”中的目標群體直接獲取國家資源的平均份額相對較少,因為國家投入到福利體系的稅收資源總額是固定的.但是實際上他們卻可以獲取慈善網絡作為工具所增加的價值或資源,即來自其他主體提供的捐贈、資助和幫助(義工)等.國家提供的保險選項系統,其功能類似于“底線-迎合體系”所發揮的功能,即給目標群體提供各種保障;兩者的區別在于,與后者相比,前者更合理地對待這類事實,即目標群體中的(至少部分)成員依然具有自主性,渴望有更多的選擇自由,并能夠行使這些自由.
設想這樣的場景,A是目標群體中部分可責備的成員,現在他可以有兩種可能的生活圖景:一種是由“底線-迎合體系”提供,另一種是由保險選項系統提供(暫且不考慮慈善網絡).按照第一種圖景,國家提供針對他這類成員的若干個等價的選項組合,他可以從中選出一個組合作為國家對他的補償.按照第二種圖景,國家提供一個選項豐富的保險菜單(包括防護性選項、預防性選項等),這樣,在他手里的購買券(即國家按照相關程序發放給他的補償金的等價票據)允許范圍內,他可以自由購買令他滿意的若干個選項作為國家對他的補償.在第二種生活圖景中,A不僅可以有保障地過他當下的生活,也可以有保障地(以購買相關保險的形式而獲得的保障))選擇去過他渴望的但有風險的那種生活,比如有登山活動的生活(因為如果他在登山時不小心摔斷雙腿,那么他此后的生活質量依然會得到其先前購買的保險選項的保障).與此不同,如果在第一種生活圖景中發生同樣的事情,那么A此后的生活質量只能由更低的補償水平來保障.因為他的不幸是由他個人的選擇造成的,因而他新增加的不幸(雙腿殘疾)不是按照原來的補償水平,而是按照新的因而是更低的補償水平(即針對完全可責備成員的補償水平)來保障.在這兩種圖景中,當不幸發生時,保險性保障與針對完全可責備成員的保障,在物資層面上,何者更具豐裕,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但是這一判斷看來是合理的,即如果A擔心不幸發生時生活質量會由更低的補償水平來保障是他不敢過有登山活動的生活的唯一原因,那么在第二種生活圖景中,A將有過這種生活的自由(假定當不幸發生時,保險性保障在物資層面上不低于針對完全可責備成員的保障).
當我們同時考慮國家建立和完善的慈善網絡的效果時,與“底線-迎合體系”相比,“保險-慈善體系”的優越性表現為后者給目標群體提供更多的自由,更好地促進社會團結等.因為慈善網絡不僅會擴寬其他主體幫助目標群體的渠道,也會促進而非阻礙社會各階層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顯然,“保險-慈善體系”很好地克服了“底線-迎合體系”過于依賴國家的不足,并且也合理地處理了目標群體中成員的多樣性及其生活方式的流變性.因為通過保險的形式,他們可以選擇過各自想過的那種生活,因而不必因為擔心背負過重的生活壓力而過分壓制做出改變生活方式的意愿.但是,對于目標群體中那些理性不健全的成員(比如精神病患者、癡呆者等),“保險-慈善體系”可能給予的自由過多,以至于這些理性不健全者反而沒有得到恰當的補償,比如他們自己不能選購對自己有利的保險,也不能很好地照顧自己.
最后是“項目-互惠體系”.“項目-互惠體系”與“保險-慈善體系”在整體上相類似,即在這兩個體系中國家都不是唯一主體,并且國家投入體系中的資源都不是全部而僅僅是部分直接被用來救助目標群體.這兩個體系的區別體現在微觀層面上.在“項目-互惠體系”中,“項目”按照支撐它的資源來源,可以區分為三類項目:(1)單純由國家稅收資源支撐的項目;(2)單純由其他主體捐贈資源支撐的項目;(3)由國家稅收資源和其他主體捐贈資源共同支撐的項目.“底線-迎合體系”整個體系,或者“保險-慈善體系”中的保險選項和慈善網絡自身,都可以作為具體項目,屬于第一類項目;通過各種渠道而出現的慈善項目,比如企業或慈善人士的扶貧項目,救災項目等,屬于第二類項目.鑒于第一、二類項目,前文已經加以討論,以下我將著重討論第三類項目.第三類項目,是指經過一套既定程序而產生的項目,包括按照程序向第三方購買的有償性項目,與按照程序審批通過的資助性項目.有償性項目,一般由盈利性組織生產和提供.這些組織生產和銷售針對目標群體的專業性產品或服務,比如針對聾啞人的培訓項目,并向政府(或國家)出售這些產品或服務.如果這些項目產生的效果不小于由國家自身提供的類似項目的效果,那么國家選擇購買這些項目而非獨自生產它們就不是不可接受的.資助性項目,一般由非盈利性組織生產和提供.這些組織自愿地為目標群體提供這樣或那樣的幫助和服務,但是它們實施這些幫助和服務所需的資源不足(甚至沒有資源),因而它們以項目的形式向福利體系的代理人(即國家或相關機構)申請資助.如果這些項目是必需的,比如它們旨在幫助和服務目標群體中的理性不健全者,而這類成員恰好長期需要看護人,那么這類項目(如果這類項目充足,那么可以同時考慮時間性,使得它們具有連續性)就應當得到資助.這里,我希望擴展資助性項目的主體范圍,即我認為目標群體的成員也應當被看成是有資格申請資助性項目的主體之一.這一擴展受這樣的觀念驅動:目標群體中的(至少部分)成員也渴望實現自身的價值,比如幫助他人,并且他們之間的相互幫助是好的.事實上,在現實中也不缺乏殘疾人之間互助的場景,比如聾啞人推著輪椅上的癱瘓者在公園中散步,殘疾人之間的聯誼活動,能自理的老人照顧喪失自理的老人,等.因此,我的意思不是說,殘疾人之間的互幫互助需要資源的資助才得以進行,而是說如果他們之間的互幫互助活動本來可以很充分但因為資源缺乏而被沒必要地削減,那么選擇性地給予其中一些活動以資助就是合理的.
在“項目-互惠體系”中,“互惠”只是就這三類項目的某方面價值而言,即在項目的實施過程中,互惠是指,在強意義上,實施的主、客體的福利(包括效用、能力、收入等)同時都得到增加;在弱意義上,一方的福利增加而另一方的福利不減少.考慮到現實社會的多元性和復雜性,強意義的互惠條件是難以滿足的.以下,我將結合這三類項目來討論弱意義的互惠被滿足的條件.
就第一類項目而言,實施主體是全體公民的代表者即國家,客體是目標群體.如果在這類項目的有效實施過程中,目標群體的福利得到增加而其他群體的福利沒有減少,那么互惠條件就能得到滿足.這個條件實際還可以這樣加以表述,即如果與實施這類項目的情境相比,在不實施這類項目的情境中不僅其他群體的福利而且目標群體的福利都會變得更少,那么這類項目的實施本身就是互惠條件的滿足.
就第二類項目而言,實施主體是慈善主體(自然人,或者組織;暫且不考慮組織情況),客體是目標群體的這些或那些成員.因為慈善主體一般是社會上處境好的個人或群體,并且他或他們提供的慈善項目是自愿性的,因而只要這類項目能夠得到有效實施,那么他或他們的福利就會增加(至少不會減少),目標群體中的這些或那些成員的福利因為得到資助而增加.在這種情況下,不僅弱意義的互惠條件得到滿足,甚至連強意義的互惠條件也有可能得到滿足.如果實施主體是組織,那么它提供的慈善項目有兩種情況:一是把慈善作為目的善,即為了慈善而慈善,二是把慈善作為工具善,即為了其他善(比如利潤最大化)而慈善.但不管是哪種情況,目標群體的福利都會因得到資助而增加.當它是第一種情況時,它類似自然人的情況,即互惠條件得到滿足.當它是第二種情況時,它的福利(比如利潤、影響力等)能否增加,取決于在其項目的實施過程中所產生的效果是否得到它的預期.如果達到,那么互惠條件得到滿足.反之亦然.
就第三類項目而言,有償性項目的情形類似于第二類項目中把慈善項目作為工具善的情形.區別在于前一情形的實施主體的福利增加與否,直接取決于其提供的項目是否被購買,而后一情形的事實主體的福利增加與否,則直接取決于其提供的項目所產生的效果是否達到其預期.資助性項目的實施主體是目標群體的某些成員,其客體是目標群體的另一些成員,在這些項目的實施過程中,如果實施主體和客體的福利(比如效用、能力等)都得到增加或至少都沒有減少,那么互惠條件得到滿足.
綜上所述,與前兩個福利體系相比,“項目-互惠體系”除了具有前兩者的優點外,還能夠更合理地處理那些理性不健全者的保障性問題,即以項目的形式,尤其是以第三類項目的形式來彌補第一類項目的不足.結合前兩節的內容,在目標群體的構成及其范圍既定的前提下,與平等主義路徑、充分主義路徑相比,恰當主義路徑更能合理地體現對處境差者的真誠關懷與個性化救助.
[1]金里卡.當代政治哲學[M].劉莘,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4.
[2]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3]Amartya Sen.Capability and Well-being[J].In Amartya Sen and Martha Nussbaum(ed.),The Quality of Live.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
[4]Amartya Sen.Equality of What?[J].In S.Mc Murrin(ed.),Tanner Lectures on Hunan Values.Vol.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5]Ronald Dworkin.Sovereign virtue: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6]Richard J.Arneson.Luck Egalitarianism and Prioritarianism[J].Ethics,2000,110(2).
[7]Cohen.Equality of What?On Welfare,Goods and Capabilities[J].Recherches?conomiques de Louvain,1990,56.
[8]G.A.Cohen.On the Currency of Egalitarian Justice[J].Ethics,1989,99(4).
[9]景天魁.中國社會保障的理念基礎[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3(3):60-64.
[10]Derek Parfit.Equality or Priority[J].The Lindley Lecture,University of Kansas,1991.
[11]亞伯拉罕.斯堪的納維亞模式終結了嗎?——論北歐國家的福利改革[J].殷曉清,譯.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5):16-22.
[12]林卡.北歐國家福利改革:政策實施成效及其制度背景的制約[J].歐洲研究,2008(3):99-110.
[13]成海軍.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社會福利制度的歷史考察[J].當代中國史研究,2008(5):48-55
[14]Jeremy Moss.Reassessing Egalitarianism[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4.
[15]Harry Frankfurt.Equality as a Moral Ideal[J].Ethics,1987,98(1).
[16]米勒.社會正義原則[M].應奇,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17]景天魁,畢天云.從小福利邁向大福利:中國特色福利制度的新階段[J].理論前沿,2009(11):5-9.
[18]鄭功成.中國社會福利改革與發展戰略:從照顧弱者到普惠全民[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1(2):47-60.
[19]王陽.我國普遍型社會福利體系的公共財政支持研究[J].經濟研究參考,2011(65):3-8.
[20]藍云曦,周昌祥.社會結構變遷中的福利依賴與反福利依賴分析[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4(8):467-472.
[21]鄧蓉,周昌祥.當前中國社會福利依賴現象與反福利依賴社會政策的介入[J].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6):82-86.
[22]周昌祥.防范“福利依賴”的思考[J].經濟體制改革,2006(6):151-154.
責任編輯 劉榮軍
B82-05/C912
A
1673-9841(2015)05-0032-08
10.13718/j.cnki.xdsk.2015.05.005
2015-03-25
秦子忠,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博士研究生.
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可行能力與責任——阿馬蒂亞·森的正義理論研究”(15XNH12),項目負責人:秦子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