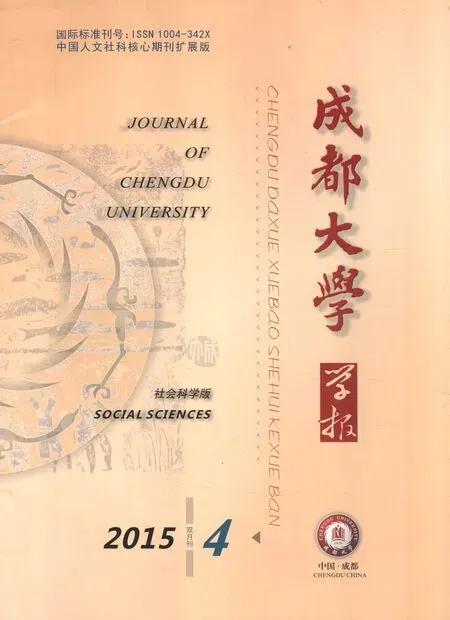地域文化產品英譯的譯者跨文化傳播力解析*
李 萍
(成都大學外國語學院,四川 成都 610106)
一、引言
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出現了翻譯學與文化學的融合發展態勢。西方翻譯研究進入了“文化轉向”研究階段,這一時期的文化學派翻譯思想與翻譯理論構建引領了國際范圍內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翻譯界在此方向所進行的以微觀研究為主的研究成果也逐步積累,為后來中外研究者以中國文化對外翻譯為對象的中觀策略研究與宏觀理論研究提供了基礎。
文化學派“將翻譯視為一種通過譯者獨特的創造性實現的一種藝術再造、審美交際、文化交流的文化信息傳播過程,是譯者對文本的主動操縱過程。”[1]在已有的文化學派研究成果中,譯者從以往次要的隱性的地位逐漸上升到更為重要的顯性的地位。譯者從“作者背后的跟從者”逐漸被描述為“跨文化傳播者”、“第三種文化創造者”和“語言服務責任者”。譯者在文化翻譯傳播中的主體性與創造性受到研究者前所未有的重視。畢文成[2]從對外宣傳翻譯視角、劉弘瑋[3]從翻譯忠實標準視角、王正良[4]從譯者主體性的多維度構建與博弈視角、雷芳[5]從翻譯過程中譯者主體性的介入視角、季宇[6]從譯者身份的變遷視角、柳曉輝[7]從語言哲學反思視角、宮軍[8]從翻譯的不確定性視角、束慧娟[9]從動態投射視角,多維度地分析了譯者主體性在翻譯實踐中的重要地位。龐學峰[10]、王曉農,王宏印[11],趙志華[12],徐艷利[13]、廖文麗,譚云飛[14],孫愛娜[15]等研究者分別依托解構主義理論、闡釋學理論、翻譯目的論、概念整合理論觀、文化社會學理論、翻譯不確定性理論和生態翻譯學理論對譯者主體性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分析。而孫曉暉[16],李廣榮[17],劉迎姣[18],屠國元,朱獻瓏[19],王慶華[20],張艷豐[21],朱耕[22]分別以中國譯者與漢學家譯者的翻譯作品為案例,通過翻譯案例分析與對比,論述了譯者主體性在翻譯實踐中的具體體現方式,總結出譯者主體性發揮的應用策略與原則。從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從翻譯語言服務的視角來關注地域文化中譯外中的譯者主體性研究是譯者主體性研究領域中可以進一步深化的對象。因此,我們選擇了以西南彝族地域文化產品的英譯為研究切入點,從語言服務的視角來解析譯者文化傳播力內涵及其在翻譯中的實踐意義。
二、彝族地域文化產品英譯的目的
(一)地域文化翻譯的目的
當前,翻譯的對象從以往的以宗教文獻、文學名著、社科作品翻譯為主體動態轉變到當代的以經濟產業、科技技術、文化旅游等領域的非文學實用產品為主要翻譯對象。隨著翻譯對象的多元化、實用化的變化,翻譯傳播的目的與功能也隨之動態轉變。
漢斯·弗米爾(Hans Vermeer)提出的目的論(skopos theory)認為:翻譯是有目的的行為,并將翻譯定義為“在目標環境中為目標目的和目標讀者而生產的目標情境中的文本”[23]。他從語言行為論、接受美學的理論基礎上提出翻譯的文本應當面向目的語文化。他認為翻譯的目的可以劃分成三個層次:翻譯過程的目標、翻譯結果的功能、翻譯形式的意圖。弗米爾認為:“翻譯原文,讓預期的讀者理解就是譯者的目標;特定的目的自然會排除某些詮釋,但保留詮釋的廣度也可能是翻譯的目標之一;譯者只要相信自己用讓人可理解的方式進行表達,就一定存在潛在的讀者對象,只是這個對象不明確而已。”[24]中國學者關熔珍在翻譯實踐方面也提出:“翻譯是為了引導西方的讀者去深入了解原文的語言文化,了解另一種不同于英語的語言。”[25]
弗米爾的理論對于面向市場傳播受眾的當代非文學實用作品的翻譯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非文學實用產品占據了地域文化外譯產品的較大份額,它們主要承載著兩類傳播功能:地域文化信息的跨國界跨文化傳遞功能、目的語國家傳播受眾的跨文化參與行動的喚起功能。
(二)彝族地域文化產品英譯的目的
地域文化傳播的翻譯產品具有獨特的文化內涵和表達形態。西南彝族文化翻譯傳播產品類型有兩個典型類型:西南彝族地區特色文化信息類翻譯傳播產品;彝族地域文化產業開發與拓展跨文化國際合作參與的呼喚類翻譯傳播產品。第一類產品的表現形態以旅游宣傳冊與文化書刊為代表,產品中蘊含著較多的彝族地域特色文化,例如:彝族民族心理文化、服飾文化、景觀文化與物品文化等。從語用表達方式來看,產品以文字語言符號為主體,輔以插圖、圖表、照片等,語言表達以描述性的、表情類的句子居多。這類產品的翻譯要求譯者重點關注如何保留彝族特色文化的信息。因此,譯者在翻譯中宜多采用異化翻譯策略,采用靈活的直譯與意譯方法盡可能地保留西南彝族地域文化詞內涵。并在此基礎上,充分考慮海外受眾對于彝族文化背景缺乏甚至缺失的認知現實,使用簡潔明了、修辭類比的語言表達方式進行翻譯。而第二類產品的表現形態更為多元,以各類廣告、媒體新聞報道、文化會展資料為代表。由于翻譯產品的主要傳播目的——吸引目的語的傳播受眾對于西南彝族文化產業開發與拓展的參與、促進目的語的傳播受眾的彝族文化旅游產品購買行為,因此這類產品中存在更多的呼喚性的、煽情類的語言表達。要達到傳播的目的,譯者在翻譯中需要以歸化翻譯策略為主導,通過增譯、減譯、變譯等翻譯方法來完成翻譯,以順應目的語的傳播受眾的認知習慣與接受水平為首要,以便有利于傳播受眾對于翻譯產品的二次傳播。
三、彝族地域文化翻譯產品的受眾定位
西南彝族地域文化翻譯產品傳播受眾可分為兩個大類,即:一類是以英語為母語的來華工作或者學習的人員;一類是居住在目的語國家,但有可能來中國西南地區旅游的人員、彝族文化研究專家、彝族文化產業開發投資商。
對于以英語為母語的來華工作學習的人員來說,他們比另外一類傳播受眾更容易理解翻譯產品中的彝族文化內涵,這是因為他們周圍的中國文化環境與人群有助于他們更快更好地認知彝族地域文化的內涵,而且這一部分人群中還有具有一定漢語交流能力的人員。因此,譯者在翻譯指向這一類傳播受眾的彝族文化產品時,可以考慮更多地采用“異化”翻譯策略,例如可以采取直接音譯保留彝族文化詞,再通過注釋或者語用闡釋翻譯策略來補充說明源語產品中的文化詞內涵。例如:有的譯者將“彝族花鼓舞”一詞直譯成Flower drum dance。然而,彝族花鼓舞是一種彝族民間喪禮儀式舞蹈,與花鼓其實并沒有關聯。所以譯者應根據彝語“彝族花鼓舞”一詞的當地發音將其音譯為Zhebobi(“者波比”)后再進行信息補充:a kind of local ritual dance at funeral among Yi People。
然而,對于居住在目的語國家的傳播受眾,由于他們所處的文化語境與彝族文化翻譯產品中所呈現出的彝族文化語境可能存在較大差異,他們在理解翻譯產品的傳播信息與意圖時容易出現誤讀或者誤解。因此,譯者在翻譯中可以考慮更多地采用“歸化”翻譯策略進行翻譯。例如采用類比翻譯方法,以傳播受眾所熟悉的語用表達方式來完成翻譯,實現彝族地域文化內涵意義的順應式跨文化傳播。例如:“獨筷調不勻糌粑,獨狗攆不出野豬。”可以翻譯為 One flower makes no garland,one swallow doesn’t make a summer.
綜上所述,譯者在西南彝族地域文化產品的英譯實踐中需要依據傳播目的、傳播功能、傳播受眾、傳播語境等要素來通盤考慮后再做出決策,這就需要譯者具有較強的譯者跨文化傳播力。
四、譯者跨文化傳播力解析
(一)譯者的主體性
譯者跨文化傳播力是譯者主體性的行動基礎。譯者主體性是指譯者在翻譯實踐過程中所表現出的主體思想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王曉農在《概念整合理論觀照下譯者主體性的客觀性》中指出:譯者主體性是能動性、受動性和為我性的統一,譯者主體性和創造性是翻譯的本質屬性,翻譯主體具有文化創造者的身份。[26]劉宓慶也指出,所謂主體應當具有三個主要特征:一是主導性,即主體具有內在的規定性;二是主觀性,即主體以自己的意志、意向、目的為軸心的心理傾向;三是主觀能動性,即主體在一種精神或者觀念支配下的創造性行為。[27]譯者不僅要依托原著能忠實地轉達原著作者的語用意思,還應當使翻譯作品在原著的基礎上增加美學形式而創造美。譯者一旦接受翻譯委托就應當承擔翻譯的責任,成為翻譯行動的控制者、多種文化融合空間的構建者。具體表現在:譯者對于翻譯產品的選擇權、翻譯策略的選擇權、翻譯技巧的調配權。但要成功實施這些權利,譯者需要具有跨文化的傳播力,即具有對不同文化邏輯的分析能力、對不同文化美學價值的判斷能力、對于多元文化的融通能力和雙語語用的轉換能力等。而這些能力則具體落點到譯者在翻譯中的遣詞造句、文體修辭、倫理美學上的翻譯風格。正如王正良、馬琰所言:“譯者主體性不是雙向維度中的一極,而是時代背景、原作文本、意識形態、主流詩學、文化差異等眾多因素的復雜互動與博弈的結果,并表現為不同的譯者風格。”[28]
(二)譯者跨文化傳播力闡釋
譯者跨文化傳播力是譯者的主體性的外顯。這種能力受多重翻譯關聯因素的影響,如:譯者成長環境、翻譯意識、翻譯態度、文化視野、百科知識、興趣性格、翻譯技能、譯入語文化主流詩學熟悉程度等等。正如大衛·卡坦(David Katan)[29]所闡釋的:譯者作為文化中介者在構建、理解、重構、傳遞源語文化現實的過程中應當具備文化的自覺性與相應的文化能力。譯者跨文化傳播力是譯者作為翻譯主體在翻譯實踐中與多元文化交互融通的對話能力與重構表達能力。以西南彝族地域文化英譯為例,從翻譯語言服務的視角闡釋了譯者跨文化傳播力的內涵:譯者對于彝族地域文化產品與英譯產品中所內嵌的文化邏輯與文化關系差異的分析力、對于翻譯產品實踐過程中所涉及的多元文化沖突的協調力、以及在翻譯產品中所體現出的目的語文化框架里的跨文化語用順應力。
分析力。分析力是指譯者對于翻譯所涉及的不同文化思維邏輯、文化關系的分析能力。以彝族地域文化產品英譯為例,為了達到翻譯產品委托主體所預期的翻譯傳播目的與傳播效力,譯者需要在充分了解委托客戶對于翻譯產品的功能定位、受眾定位、時間限制、媒介限制、翻譯技術、數據庫資源等,對彝族地域文化源語產品中的所牽扯的文化關系進行分析,這就要求譯者熟悉產品中所包含的彝族文化符號及其背后的文化象征與語用意圖。此外,譯者還需要分析翻譯產品委托主體的傳播目標在彝族地域文化產品上的如何落地問題,并分析預測海外傳播受眾對于這些文化邏輯與文化關系的接受能力。在這些分析的基礎上,譯者才能預測自己的翻譯重點與難點,選取合適的翻譯策略與翻譯技巧,做到翻譯中的目標明確、刪減得當,闡釋合理,輕重有序,文化凸顯。
協調力。協調力是指譯者對于翻譯過程中所涉及的多元文化沖突的協調能力。這種協調能力保障譯者成功游走在源語文化和目的語文化的語用框架中,謹慎并巧妙地構建出具有譯者風格的、能被特定領域的源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群體雙重接受的、具有兩種文化根基的彝族地域文化英譯產品文化交界。這種能力貫穿譯前準備、翻譯過程、譯后反思整個翻譯過程。它涉及到翻譯信息轉換過程中譯者對于目的語傳播受眾對于異域文化的情感容忍度的判斷能力,語用文化沖突的平衡能力以及跨文化的翻譯遷移能力。具有較強的文化協調力的譯者始終會從文化的自覺意識和跨文化傳播的譯者主體性來關照著翻譯中文化關系如何在他者文化中的順利傳播,尋找目的語相同文體參照范式,盡量促使源語產品中的語言與文化現實的距離與翻譯產品中語言與文化現實的距離相近。
20世紀60年代,卡特福德(J.C.Catford)提出了翻譯“語境”、“語境意義”理論思想,這兩個概念對后來的翻譯研究有深遠的影響。[30]到了90年代,語用學的發展更加加速了“語境”學說在翻譯領域中的應用。語篇成為翻譯和理解的認知單位。西南彝族地域文化產品內容涉及彝文經典、彝文古書、人文景觀、民居服飾、習俗文化、民間傳奇方面的文本內外關聯語境,要較好地完成彝族地域文化產品的英譯,譯者需要熟悉彝族文化語境、中華文化海外傳播語境、目的語傳播受眾群體文化語境以及目的語傳播受眾主流文化語境。特別是對于彝族文化詞的處理,譯者要充分協調語境變化造成的翻譯難點,創造屬于翻譯產品的第三文化空間。
順應力。是指譯者在翻譯中能使用傳播受眾所喜愛的語言與語用表達方式,在目的語文化框架里實現源語文化產品信息的跨文化傳播的語用能力。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需要盡量以目的語類似文化產品的表達范式為翻譯的參照表達范式。譯者的這種順應能力直接影響地域文化英譯產品是否能得到傳播受眾的認可與接受。作為語言服務產品,地域文化對外傳播翻譯產品質量高低的評價直接或者間接地取決于傳播受眾反饋。產品的翻譯呈現方式與語言表達習慣只有符合傳播受眾的思維模式、文化認同、審美觀才能達到產品的傳播目的。
簡言之,在西南彝族地域文化產品翻譯中,譯者要以主體創造性與決策性來進行調整翻譯產品中的語言表達形式與傳播呈現方式,把控異化與歸化翻譯策略使用選擇與傳播受眾接受度的關聯。在最大限度內促使翻譯產品在文體呈現、敘事方式、語言表達、修辭表現等方面采用符合傳播受眾的認知習慣。對于容易引起民族負面情感或者誤解的非核心信息給予刪減;對于容易引起民族負面情感或者誤解的核心文化信息則可以采用文化類比的方式進行翻譯,在目的語傳播受眾的文化框架中詮釋彝族地域文化具象和文化意境,讓西南彝族地域文化產品的文化意境與意象在翻譯產品中順利遷移。例如,彝族中流傳的“萬丈青松不怕寒,勇敢的阿黑吃過虎膽”可以采用類比的翻譯方法來譯為:He fears not winter‘s coldness;as if he’d supped on tiger’s blood.譯者通過采用目的語修辭手段進行翻譯,增加翻譯產品在傳播受眾中的吸引力,促進傳播受眾對于彝族文化的關注與參與行為,確保彝族地域文化產品預期傳播功能的實現。
五、結語
譯者跨文化傳播力是譯者對于彝族地域文化產品與英譯產品中所內嵌的文化邏輯與文化關系差異的分析力、對于翻譯產品實踐過程中所涉及的多元文化沖突的協調力、以及在翻譯產品中所體現出的目的語文化框架里的跨文化語用順應力。它貫穿翻譯的前期準備、翻譯過程與后期反思。譯者跨文化傳播力的充分具備基于譯者的扎實的語言解構與重構能力,基于譯者的的大量雙語閱讀與寫作實踐,基于譯者的國際視野與文化經歷。譯者跨文化傳播力的深度探討需要在闡釋的基礎上進一步進行實證調查與量化分析。
[1] 呂俊,侯向群.翻譯學——一個建構主義的視角[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
[2] 畢文成.淺析對外宣傳翻譯中譯者主體性的凸顯[J].出版廣角,2012(2).
[3] 劉弘瑋.從譯者主體性看翻譯忠實標準[J].江西社會科學,2010(11).
[4] 王正良.譯者主體性的多維度構建與博弈[J].外語教學,2010(12).
[5] 雷芳.論翻譯過程中譯者主體性的介入[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2(5).
[6] 季宇.論譯者主體性——從譯者身份的變遷談起[J].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1).
[7] 柳曉輝.譯者主體性的語言哲學反思[J].外語學刊,2010(11).
[8] 宮軍.從翻譯的不確定性看譯者主體性[J].外語學刊,2010(11).
[9] 束慧娟.動態投射與譯者主體性[J].上海翻譯,2012(11).
[10] 龐學峰.發揮與控制的統一——德里達解構主義視角下的譯者主體性研究[J].外語與外語教學,2010(3).
[11] 王曉農,王宏印.概念整合理論觀照下譯者主體性的客觀性[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2(12).
[12] 趙志華.“生存心態”:譯者主體性研究的理據[J].外語與外語教學,2011(2).
[13] 徐艷利.論“翻譯的不確定性”論題中的譯者主體性問題[J].外語研究,2013(1).
[14] 廖文麗,譚云飛.論闡釋學理論和現象學意向性原則對譯者主體性發揮的啟示[J].外國語文(雙月刊),2011(6).
[15] 孫愛娜.試論生態翻譯學對譯者主體性的消解[J].教育探索,2012(11).
[16] 孫曉暉.發揮譯者主體性作用在翻譯中表達散文的韻味——以歸有光《項脊軒志》英譯為例[J].文苑經緯,2012(20).
[17] 李廣榮.視域融合:文本意義的譯者主體性——以嚴復譯著為例[J].山東外語教學,2012(4).
[18] 劉迎姣.《紅樓夢》英全譯本譯者主體性對比研究[J].外國語文,2012(1).
[19] 屠國元,朱獻瓏.選擇性順應與順應性選擇——佛教中國化進程中的譯者主體性構建透析[J].中國翻譯,2010(11).
[20] 王慶華.譯者主體性——張培基散文翻譯藝術賞析[J].文苑經緯,2011(35).
[21] 張艷豐.譯者主體性與散文翻譯——《英國鄉村》兩種譯本的個案研究[J].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3).
[22] 朱耕.譯者主體性在霍克斯英譯《紅樓夢》中的體現——以《紅樓夢》中“飛白”修辭格的翻譯為例[J].名作欣賞,2012(11).
[23] Nord,Christiane.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anchester,UK:St.Jerome.1997:12.
[24] 謝天振.當代國外翻譯理論[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
[25] 關熔珍.中國文化元素的保持與對外翻譯[J].現代傳播,2010(5):140.
[26] 王曉農,王宏印.概念整合理論觀照下譯者主體性的客觀性[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2(12).
[27] 劉宓慶.翻譯與語言哲學[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1.
[28] 王正良,馬琰.譯者主體性的多維度構建與博弈[J].2010,31(5):107.
[29] 大衛·卡坦.文化翻譯——筆譯、口譯及中介入門[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
[30] 黃國文.導讀:關于語篇與翻譯[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