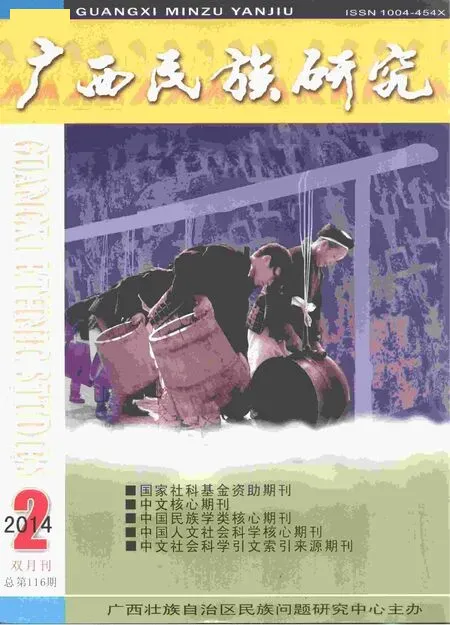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對外傳播與翻譯的多維思考*
劉汝榮
一、引言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外學術界出現了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翻譯學界的一批翻譯理論家如埃文·佐哈爾、安德魯·勒弗爾、蘇珊·巴斯奈特、西奧·赫曼斯等,不斷從文化層次闡述翻譯問題。例如,Bassnett&Lefevere在合著的《翻譯、歷史與文化》中探討了翻譯與權力、意識形態的關系。在中國,王克非、王秉欽、許鈞、楊仕章、徐珺、崔永祿探討了民族文化的發展與翻譯的互動關系、文化多樣性與翻譯的使命、典籍外譯中的文化觀等問題。隨著翻譯研究的文化學轉向以及全球一體化的高速發展,翻譯不再被當作一種純語言的行為,而是越來越多地被當作一種文化實踐活動。這種活動與目的語國家的文化語境、意識形態、社會制度、文學觀念密切相關,與譯者的文化態度、立場等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文化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力量,文化力日益成為現代社會發展的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證,是國家軟實力的根本體現。從某種意義上說,翻譯已經成為文化競爭中的一種工具。因此,在培育文化競爭力、利用文化手段展現中國形象、宣傳中華民族價值觀、擴大國家影響力的關鍵時刻,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的外譯和傳播是一項非常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
二、中華文化外譯的歷史與現狀、民族文化外譯的難題
中華文化外譯的實踐及理論研究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譯著主要有《四書》《五經》等典籍、《紅樓夢》《水滸傳》等文學名著以及《大中華文庫》《學術中國》等中國學術思想和學術著作。但是相對于外譯中而言,中譯外的作品太少,且較有影響和受歡迎的多為外籍漢學家的譯著;中譯外的理論研究起步較晚,且存在深度不夠、角度欠缺等問題;中譯外在很多時候被人僅僅當成是“漢譯外”,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的外譯幾乎被人遺忘。
(一)中國翻譯界的幾次翻譯高潮皆以外譯中為主,中華文化“逆差”現象嚴重。
在“五四”運動前,中國翻譯史上出現過3次翻譯高潮,即東漢至唐宋的佛經翻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和鴉片戰爭后至“五四”前的西方政治思想與文學翻譯。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們迎來了第四次翻譯高潮。無論從其作品的數量抑或從翻譯的研究來看,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以外譯中為主。這可能緣于西方的影響,歐美學者歷來只把外語譯成母語,他們認為,將母語翻譯成外語是一種“錯誤的選擇”。在國際組織中,一般的慣例也的確是從外語譯入母語。受其影響,中國學者多進行的亦是外譯中的翻譯工作。下面的數據很能說明該問題:“據了解,近幾年我國每年從國外買版權大約七八千種,外國買我們的最高年份只有六百多種,這就是文化逆差。”[1]“從公元1900年到公元2000年100年間,中國全盤翻譯的西方文史哲政經法數理化等書將近10萬冊,但是西方完整翻譯中國的書不到500冊。”[2]在2011年世界文化市場的格局中,美國、歐盟、日本、韓國所占比重依次為43%、34%、10%和5%,而我國僅為4%,從這個層面來看,我國文化赤字狀況盡管有所緩和,但仍舊逆差明顯。
(二)中譯外作品中真正有影響力的不多,且大多受歡迎的作品多為外國人主譯或者參與翻譯的作品。
中譯外的翻譯活動或研究一直都有,最早被外譯的漢著可追溯到一千多年前北魏 (公元508-534)時期被印度僧人翻譯成梵文的《大乘章義》。16世紀末,中國的儒學經典和文學作品開始被譯介到西方。在外譯的漢著中,最富影響力和代表性的首推《四書》《五經》等儒學名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譯外的發展與中國走向世界的努力同步并行:創辦了《對外大傳播》《中國翻譯》《上海科技翻譯》等專門的翻譯研究雜志;翻譯界于2007年、2011年先后兩次舉辦了中譯外高層論壇,中聯部、外交部、文化部等國家部委均派代表參加;中國外文局、外文出版社近年出版了英文版的《中國文化與文明》《本草綱目》《學術中國》,《大中華文庫》百部中國文史哲經典作品英譯即將完成。盡管如此,這一數量與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遠不相稱。其中一個重要的現象也不容忽視,那就是眾多的外譯作品中真正受到西方人歡迎和喜愛的是外國人譯的作品,《四書》《五經》能讓中國儒家思想在西方產生巨大影響,是因為世界知名漢學家、英國倫敦會傳教士理雅各 (James Legge)的譯本The Chinese Classics(《中國經典》),《水滸傳》能引起西方世界讀者的巨大興趣是因為美國女作家賽珍珠和中國籍美國人沙博理的的翻譯,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共同翻譯的《紅樓夢》英譯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之所以能夠轟動中外出版界,母語為英語的妻子戴乃迭的修改和加工整理功不可沒。在中國,包括香港、臺灣,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從事中譯外工作的譯者普遍缺乏在外國實際體驗所學外語在社會生活中的應用;再者,由于中文的特殊性和中國文化的復雜性,中譯外工作需要面對難以逾越的因中華民族與他民族思維模式之間的巨大差異而形成的語言鴻溝,使得國內許多從事翻譯工作的人員知難而退、望而卻步,出現了許多的中國經典由外國人譯成他國文字的現狀。但是,我們認為,任何時候、即使是全球一體化的今天,通曉中國語言文化的外國人極為有限,西方翻譯中國的作品歷史雖然悠久,數量畢竟有限。由于翻譯目的、思維方式、文化態度等因素的限制,外籍人士對中國作品的翻譯未必準確、真實,中華民族燦爛的文化最終還要靠中國人自己來自主而全面地對外傳播的,因而,我們需要培養自己的中譯外人才、建立自己的中譯外隊伍。
(三)中譯外理論研究較為薄弱,國內已有研究課題角度缺失。
豐富的翻譯活動,一直被實踐者認為是充滿障礙的工作。翻譯家楊絳先生說過,翻譯家是“一仆二主”。一個“主”是原作者,另一個“主”是讀者,兩邊都要伺候好,這很不容易。因而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對于中譯外的理論少有學者對其進行深入而系統的研究。筆者在中國知網數據庫里分別以“中譯外”、“外譯”為主題進行搜索 (截止2012年8月),1979-2012年間的論文數分別僅為138、287篇。同樣數據庫,相同年代的“漢譯”為主題的文章有10683篇。有限的中譯外研究文章從性質上看,多為規約性論述,即評價中外譯者的中譯外實踐,缺少描述性分析;從主題上看,多以某一翻譯作品研究為主,尤其集中于討論微觀的語言轉換策略,缺乏過程性研究。在對近10年的國家社科課題統計中我們發現,對外傳播的研究課題有10余項,大多是外宣個案研究。無論是文章還是課題,少有從中譯外的翻譯技巧上予以探討、從人才培養的高度著眼,所以不能真正解決文化外譯中最根本最亟待解決的問題。
(四)數量不多的中譯外作品主要是漢語譯成外語,少數民族的作品翻譯甚少,理論研究幾乎無人涉足。
這對于由56個民族文化構成的大中華文化來說,既不符合實際也不利于向國外介紹我國各民族平等繁榮的民族政策。這與少數民族翻譯人才匱乏不無關系,因此需要加強少數民族翻譯人才的培養,更好地向外傳播中國少數民族的經典文化。新疆維吾爾族古典長詩《福樂智慧》(Wisdom of Royal Glory:A Turko-Islamic Mirror for Princes)和藏蒙史詩《格薩爾》(The Superhuman Life of Gesar of Ling)的成功外譯,給予了我們一定的啟示。
筆者在此花費如此多的筆墨來梳理中華文化外譯的歷史與現狀,是因為中國少數民族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外譯所面臨的問題與整個中華文化外譯面臨的問題既有相同之處,又存在一定的特殊性。由于歷史和地域的原因,中國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文化處于相對落后狀態,文化外譯更是少有人涉足。像《福樂智慧》《格薩爾》那樣能被譯成多國文字并被關注的少數民族典籍少之又少。《福樂智慧》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它是世界四大文化體系 (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交匯的產物,吸引了眾多國內外學者投入到它的翻譯與研究中;活態史詩《格薩爾》在世界上流傳廣泛,先后被譯成德、俄、英、法、日文,與它活態流傳于我國的藏、蒙地區以及印度、不丹、尼泊爾、錫金以及前蘇聯的卡爾梅克、布里亞特等國家和地區,產生了越來越多的異文本不無關系。因而,我們要讓中華文化中燦爛的少數民族文化走向世界,首先需要挖掘出更多的像《福樂智慧》《格薩爾》這樣的民族典籍;同時需要像《格薩爾》那樣不斷創新,保持民族文化的新鮮感、時代性,發掘民族文化中的世界元素;再者就是怎樣保持民族文化的完整性及真實性,讓世界讀者接受真實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其次,由于少數民族語言、文化的特殊性,世界上能真正通曉少數民族語言、文化的外籍人士十分有限,大量的少數民族文化的外譯只能是本族語者自己去完成,因而如何培養專門的翻譯人才將是民族地區高校面臨的重要課題;最后,在思考民族文化外譯的整個過程中,我們不能忘記民族文化外譯的目的之一是幫助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產品外銷,促進民族地區文化產業的發展和現代化的進程,只有富有了,才會增強其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三、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外譯需要解決的迫切問題及對策
“文化是一個復雜的整體,它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所習得的其他任何能力和習慣。”英國文化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 (Edward Tyler)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書中對文化第一次進行了系統的表述。文化一般具有民族性、多樣性、相對性、延續性和積淀性等特點。民族文化的對外翻譯問題的研究應該擺在歷史與現實、中國與世界、現在與未來的總體坐標上進行全方位的考量。以分析現狀、闡發理論、研究措施、服務現實為研究思路,以比較與分析、歸納與演繹相結合為研究方法,廣泛運用文化學、翻譯學、語言學、傳播學、社會學的最新研究成果來研究民族文化外譯的原則與策略等系列問題,以期為少數民族文化與在世界的平等溝通與交流,維護世界文化生態平衡以及推動民族地區現代化進程提供一個理論框架、方法論原則和實際操作的體系。具體來說,就是解決譯什么、如何譯、誰來譯的問題。
(一)譯什么?
站在世界的坐標上看,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的外譯和傳播是保持世界文化多樣性,維護世界文化生態平衡,消解文化霸權的有效手段,因為“各種文化只有準確、自然地表現出自己的精神氣質、特色個性,才能真正構成一個多彩多姿、差異性與共性并存的文化生態平衡系統。”[3];站在中國的角度看,中國與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相比,差距最大的不是國內生產總值和軍事實力,而是各種軟力量。“軟權力的力量來自擴散性,只有當一種文化廣泛傳播時,軟權力才會產生強大的力量。”[4]“我們必須加快推進文化改革發展,廣泛開展人文交流,堅持政府與民間并舉、文化交流與文化貿易并重,推動優秀文化產品走向世界、造福人類,增強我國國際話語權……。”[5]民族文化外譯是增強我國國際話語權的一個必不可少的媒介,是對外介紹中國的最為有效的手段。從民族地區文化、經濟發展的角度看,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與發展,與世界各國和地區在經濟、文化、教育以及其他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日趨密切和頻繁,民族地區迎來了各種形式的對外交流活動,只有準確地將我們的方針政策、經濟制度進行對外宣傳,將我們的歷史文化、傳統習俗以及風景名勝介紹給外國朋友,才能吸引外商、外資,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推動民族地區經濟建設更好更快地發展。
“軟實力”理論提出者、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 (Joseph S.Nye)認為,中國文化在全球傳播有很好的前景,理由有兩條:一是中國文化底蘊深厚,對西方一直有很強的吸引力;二是伴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中國文化的影響力也會逐步擴大。其實,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是有吸引力的,吸引力并不是文化的本質特色。因此,外譯文化內容的選擇十分關鍵。譬如說我們的“國寶”——中醫中藥,在向西方推廣時遇到巨大的困難,西方人認為“頭痛治腳,腳痛治頭”的中醫是“偽科學”,遭遇的阻力很大程度上是來自西方與我們迥異的思維方式。實際上,中醫最核心的思想是“天人合一”、“以人為中心,調理人體陰陽平衡,疾病自愈”,“養生”是中醫的根本目的。養生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是極具向世界傳播的價值的。天人合一、倡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這是可持續發展追求的最高境界。
再如湘西苗族融宗教與藝術于其中的巫儺文化,啟迪人們“不信天命”,“追求真理”,“崇尚平等”,信仰“萬物有靈”,把一切的自然物都想象成有感覺、有意志、有思維的生命體,能像人那樣進行有意識、有感情的活動,具有人一樣的社會關系,使自然人格化,與人平等相處。這與當今世界各民族倡導保護地球、保護自然、與環境和諧相處的理念是具有“共鳴點”的。
因此,我們在進行少數民族文化外譯的時候首先要挑選那些真正經典的、有利于樹立中華民族正面形象的文化;其次,由于文化具有民族性、地域性、時代性等特征,并不是所有的中國文化對于他國受眾都有吸引力,因此我們要善于挖掘民族文化中的世界元素。在了解世界與我們不同的前提下,找到我們與世界讀者的“共鳴點”,對這樣的“共鳴點”進行外譯才能達到有效的溝通。這是民族文化外譯亟待解決的問題,也是最具挑戰性的研究。賽珍珠將《水滸傳》譯成在美國暢銷的英文版的All men are brothers讓“從中國殺將過去的這批‘梁山好漢’,一下子就‘躥’上了美國權威的‘每月圖書俱樂部’的排行榜。”[6]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譯作中的“人物頗與英國的羅賓漢等綠林豪杰相似,所以這樣有興趣的,合西洋人口味的,而有永遠性的人皆兄弟,更引起歐美讀者的歡迎。”[7]這類的成功例子是值得借鑒的。由于民族文化外譯的目的之一是推動地方經濟更快更好發展,所以,除了挖掘民族經典文化作品外,還要發展和創新經典,比如湘西苗族的巫儺文化的宣傳和創新可以跟現今的旅游熱點南長城相結合,將湘西苗族的氏族部落生活、遷徙歷史以及巫儺文化、平等觀念等融入其中,賦予南方長城真正的歷史性、文化性、生動性的畫面感,這樣南長城的旅游賣點凸顯出來了,巫儺文化及其精髓得以傳播和發揚。
(二)如何譯?
德國目的翻譯理論 (Skopos Theory)認為,翻譯行為所包含的交際意圖/目的 (purpose/skopos)或功能 (functions)是譯者決策的根源所在。目的決定了譯者選用什么樣的譯本、翻譯方法及翻譯策略,即目的決定手段。
塑造民族文化形象,促進民族文化自信和自尊,加強與世界文化的對話與交流,推動民族地區經濟建設更好更快地發展,這是民族文化外譯的目的所在。后殖民批評家佳亞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說:“梳理翻譯的政治時,我們必須考慮語言在國際上的地位。”[8]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考慮語言的地位即是考慮文化的地位。因而,在民族文化外譯的過程中,我們要保留完整的民族身份,保持我們民族歷史和文化的完整性、獨一性和異質性。用魯迅先生的話說,就是對原文“不主張削鼻刻眼”。用現代的話說,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格局中保存自己。著手進行翻譯時,首先要充分了解源語的文化內涵,其次考慮在譯文中如何體現這一文化信息,幫助目的讀者理解或接受,不能一味地從目的語文化出發,過分考量目的語讀者對異文化的辨別能力和接受能力,用目的語文化的價值觀強行歸化源語文化,掩蓋或扭曲原文的文化事實。也就是要運用“異化”翻譯法,“突出翻譯作品中外國文本的外來身份并保護原文本不受譯入語文化意識形態的控制”,創造出一種富有變化的、“含有異質成分的話語”,實現“把外國文本中的語言文化差異注入目的語之中,把讀者送到國外去”的目的[9]。
如1.“嫁雞隨雞嫁狗隨狗”——Marry a cock and follow the cock;marry a dog and follow the dog.(摘自楊憲益譯《紅樓夢》)2.“成則王侯敗則賊”——Such people may become princes or thieves,depending on whether they’re successful or not.(摘自楊憲益譯《紅樓夢》)均是完整地保留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內涵和神韻的異化翻譯。在此我們不得不再次提到賽珍珠,為了將中國名著《水滸傳》原原本本地介紹到西方,正如她自己所說“就是盡己所能使譯本逼似原著,因為我希望不懂中文的讀者至少能產生一種幻覺,即他們感到自己是在讀原本。”她保留了中國古代語言特有的表達方式和行文習慣,她將“吃酒”譯為“eat wine”; “江湖好漢”譯作“a good fellow of the rivers and lakes”;甚至不惜冒著被指責為“誤譯” “死譯” “胡譯”的風險,在明確知道“放屁”即表示“胡說”的情況下,將書中出現的類似于“武行者心中要吃,哪里聽他分說,一片聲喝道:‘放屁!放屁!’”中的“放屁”直譯為“pass your wind”。她的譯作不僅當時深受英美讀者歡迎,而且All Men Are Brothers在今天互聯網西方網上售書公司的推介書目中任然頻頻出現。賽珍珠的翻譯對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外譯是非常具有借鑒意義的。
譯文效果是檢驗翻譯是否有效的、交流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譯文效果如何,讀者最有發言權。正如Nord Christian所說,“目標讀者是譯文的接收者,因此在翻譯過程中起著決定性作用。”[10]因此,譯者在進行民族文化外譯時,一定要有“讀者意識”。在從事翻譯活動時要充分考慮譯作的目標讀者因素,對目標讀者的“期待視野”有足夠的了解,只有這樣,譯文才可能順利地被譯文讀者接受。“期待視野”是西方學者Hans Robert Jauss在接受理論的基礎上提出的概念,用來指目標讀者的思維方式、審美取向、閱讀期待、原有知識等因素。外譯作品要在目的語國家產生預期效果、被目的語讀者接受,譯者的讀者意識至關重要。
因此,為了實現我們認為民族文化外譯的預期目的,譯者宜采用異化為主、歸化為輔的翻譯策略,在作品的選擇和翻譯過程中充分考慮目標讀者的期待視野。采用圖像、模仿、替代、闡釋、淡化等表現手段,將中華民族文化精髓傳播到世界各地。
(三)誰來譯?
通過歷史上外譯作品的分析,我們發現一個不容樂觀的問題:那些受外國讀者歡迎和喜愛的中譯外作品大多出自外國人之手,或者是由中外人士合譯。楊憲益所譯的《紅樓夢》(A Dream of Red Mansions)如果沒有夫人戴乃迭的參與也不會獲得如此成功。但是,漢語目前在國際上還屬于非國際通用語言。近些年,掌握漢語的外國人雖然與日俱增,但短時間內還不能滿足中外各領域交往的需要,掌握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的外國人更少,根本不能滿足向世界推廣中國文明和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的需要。因此,將多彩的少數民族文化翻譯成不同國家語言的重任自然要落在以漢語為母語的或者是以某一少數民族語言為母語的中國人身上。一方面,國家要努力提高翻譯人員的整體素質和培養力度,另一方面,各高校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高校的外語學院要將培養高素質的外譯人才作為翻譯教學的改革方向。
中譯外人才的培養首先要確定的是培養目標,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外譯人才。我們認為民族文化對外傳播需要的人才應該具備如下素質:第一,要有良好的譯德,熱愛中譯外事業。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指出:“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德”,是“才”的方向和靈魂,是“才”發展的內部動力;“才”,是人得以發展和成功的基本條件和基礎。二者之間,“德”是首要的、第一位的,培養中譯外人才必須“以德為先”。具備良好譯德的譯者才能運用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去分析、研究和深入理解原文的內容,解決翻譯中遇到的形式與內容的問題,才能以譯介中華文化為己任,孜孜追求,不懈努力。第二,要有堅實的語言基本功。翻譯中的語言基本功指的是源語及目的語兩種語言的詞匯知識、語法結構知識、句子理解能力、語言典故等的掌握與了解等,語言基本功與翻譯的關系就如同地基與大廈的關系:沒有牢固的地基,便無法構筑堅固的大廈;沒有扎實的語言功底,便無法正確理解原文,更不用說準確表達原文意思。因此,譯者語言基本功的重要性再怎樣強調都不為過。第三,要有廣博的文化知識。翻譯家即雜學家,各方面的知識都要涉獵,一方面因為我們平時所接觸的翻譯材料,常常會涉及到各行各業的方方面面,如果譯者不具備相關學科的基本的知識是不能保證質量地完成翻譯任務的,另一方面,由于我們所處的信息時代,全球一體化步伐加快,語言學科和文化學科蓬勃發展,各門學科相互滲透、相互影響,譯者多學習一些語言學、文化學、傳播學、社會學、哲學等方面的知識對提高譯文質量極為重要。當然,對于中譯外的譯者而言,相關領域的科學文化知識應該是包括源語國家和目標語國家的,正如奈達曾說:“對于真正成功的翻譯而言,熟悉兩種文化甚至比掌握兩種語言更為重要,因為詞語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義。”[11]
筆者認為,圍繞人才培養目標制定的培養規劃應該注意以下幾點:理論教學與實踐相結合;中國文化、少數民族文化與外國文化學習相結合;國內培養與國外學習相結合。這樣才能培養出具有扎實的語言功底、廣博的文化知識和敏銳的感受能力的翻譯人才,才能保證少數民族文化外譯和傳播的質量和效果。受篇幅所限,關于外譯人才職業化培養將另文專論。
四、結語
在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的今天,中譯外是增強我國國際話語權、擴大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一個必不可少的媒介。挖掘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的經典,研究其對外翻譯和傳播策略是歷史賦予翻譯工作者的使命。培養高素質的翻譯人才是解決民族文化外譯的根本所在。
[1]趙啟正.跨越文化障礙更好地向世界說明中國[EB/OL].http://www.cccf.china.cn,2012.
[2]王岳川.發現東方與中國文化輸出[J].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02(3).
[3]王銀川.非文學翻譯:翻譯教材建設和翻譯教學的思維轉向[J].外語界,2009(2).
[4]王滬寧.作為國家實力的文化:軟權力[J].復旦學報,1993(3).
[5]劉延東.推進文化改革發展,增強我國國際話語權[N].人民日報,2011-11-01.
[6]龔放,王運來,袁李來,等.南大逸事[C].沈陽:遼海出版社,2000.
[7]馬紅軍.為賽珍珠的“誤譯”正名[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3(5).
[8]Spivak,G.C.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
[9]Lawrence Venuti.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London:Routledge,1995.
[10]Christiane Nord.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11]Nida,E.A.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s in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