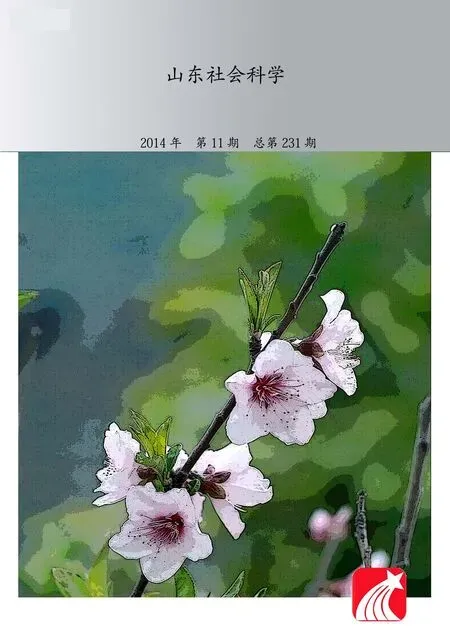論生命人格與文藝創作
楊守森
(山東師范大學 文學院 ,山東 濟南 250014)
在心理學界,“人格”一語,常見以下兩種更具主導性與普遍性的看法:一是指一個人的“先天傾向,沖動,趨向,欲求,和本能,以及由經驗而獲得的傾向和趨向的總和”*陳仲庚、張雨新編著:《人格心理學》,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2頁。。據此而有內傾型人格與外傾型人格,完美型人格、成就型人格、理智型人格、活躍型人格之類劃分。二是延續了拉丁文的面具(persona)本義,指一個人在公共場合中表現出來的文化形態的外在自我,據此而又有政治人格、道德人格、法律人格、審美人格之分。政治人格指的是一個人與政治觀念、政治立場相關的個性表現;道德人格指的是一個人在品行與操守方面的行為模式;審美人格指的是一個人超越現實、向往美的個性情懷;法律人格指的是一個人在一定法律關系中的主體資格。本文所要論及的生命人格,與側重于社會文化層面的政治人格、道德人格、法律人格、審美人格以及更具現代心理學意義的含混“總和”之人格不同,指的是一個人更見本真性與內在性的自我,即從根本上來說,是基于身體機制、遺傳素質、生命本能而形成的人格特征。這樣的生命人格,與人類的文學藝術活動之間,無疑有著更為密切的關聯。透過這一視角,不僅有助于我們更為深入地分析探討作家、藝術家的風格與成就,亦會有助于我們進一步弄清何以“文若其人”以及又常常“文不若其人”之類相關問題。
一、文學藝術家的生命人格
世上的人,有的優柔寡斷,有的雷厲風行;有的沉默寡言,有的風風火火;有的灑脫不羈,有的謹小慎微;有的易于激動,有的老成持重等等,表現出來的生命人格是不一樣的。這些生命人格,有的更適于文學藝術活動,有的則更適于其他方面。比如我們很難想象“見花流淚,見月傷心”的林黛玉那樣一種生命人格者,會成為一名習慣于動刀動剪的外科醫生;也很難想象性格暴躁、動不動就掄動板斧的李逵那樣一種生命人格者,會成為吟風弄月的詩人。
與人類的其他活動大不相同,文藝創作,更需要飛揚的才思、敏銳的感覺、燃燒的激情、活躍的想象,而這些素質,雖亦可經由學習訓練、環境影響而增強,但從根本上來說,則更賴于一個人不期然而然的生命人格。由中外文學藝術史上那些卓有成就的詩人、作家、藝術家可見,這類生命人格,最常見的是以下特征:
一是敏感多情,想象活躍。面對生活現實與自然萬物,人們的感受程度,以及為外物所激發而產生的情感與想象的活躍程度是有很大差別的。比如同是花開葉落,在常人眼里,不過是尋常的自然景觀,而一位詩人則會激動不已,會生出奇思異想,會如同陸機所說的“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文賦》)。對于詩人與常人的這一區別,美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羅伯特·N.威爾遜亦曾有過這樣切實的判斷:詩人對事物會有超出常人的“敏感性、強度、意識和激情”,“詩人必須有一種對人和自然事物強烈的好奇心,對這個世界有一種強烈的依戀,以至于其經驗的饜足點遠遠高于大多數人”。[注][美]阿恩海姆等著:《藝術的心理世界》,周憲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39-240頁。這樣的生命人格特征,自然不只見于詩歌創作,在其他藝術門類中同樣如此,如麥田、果園之類,實在不過是尋常的鄉村風景,而經由凡·高之筆,即大不一樣了,會令人心跳眼熱、情感洶涌,會成為西方美術史上的經典之作。由這類畫作可知,凡·高亦正是以藝術家特有的敏感、好奇與獨特想象力,捕捉到并表現出了尋常的鄉村風景中所隱含著的生命的狂野與躁動之類難以窮盡的奧妙。同是面對鳥獸蟲魚,一般人可能習焉不察、漫不經心,一位畫家,則會如同八大山人那樣,從其眼神與體態中體驗到生命的喜怒哀樂,生出悲天憫人的情懷;同是生命壓抑,許多人會逆來順受,一位作家,則會如同寫出了《變形記》、《城堡》之類作品的卡夫卡那樣,感受到人被異化為非人的痛苦,想象出別一番可怕的人間圖景。正是由于更為敏感于物事變遷、人間冷暖、生命痛苦,作家、藝術家才會更具關愛萬物的情懷,才會對現實與人生有著更為完滿的企盼,才會對真善美有著較常人更為執著的追求,才使其作品擁有獨到的人性深度與藝術魅力。
二是厭惡喧囂,甘于孤獨。與敏感于物事變遷、人間冷暖、現實壓抑,以及時常沉溺于想象世界相關,優秀的作家、藝術家,多是厭惡喧囂、甘于孤獨,甚至看上去不無抑郁之病狀者。他們,正是在孤獨中,傾聽到了自我生命的沉吟,洞徹到了大千世界的奧妙,創作出了獨具個性的作品。事實上,一位不甘寂寞、熱衷于群體交際、八面玲瓏、到處應酬的人,是難得有心理余暇品味人生、玄思宇宙,進入一個清靜澄明的藝術世界的。海明威即曾這樣深有體會地說過:“寫作,在最成功的時候,是一種孤寂的生涯。作家的組織固然可以排遣他們的孤獨,但是我懷疑它們未必能夠促進作家的創作。一個在稠人廣眾之中成長起來的作家,自然可以免除孤苦寂寥之慮,但他的作品往往流于平庸。”[注]《海明威談創作》,三聯書店1985年版,第25頁。然,就外在行為而言,社會上沒有誰能完全與世隔絕,故而一位作家、藝術家的真正孤獨,尚不能僅就外在行為而論,而更為關鍵的是要看內在心靈,即是否有著鄙棄世俗、厭惡喧囂的心理趨向。在中外文學藝術史上,諸如但丁、貝多芬、高更、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司馬遷、曹雪芹這樣一些成就輝煌的作家、藝術家,莫不是這樣有著孤獨心靈的生命人格者。
三是自由不羈,率性而為。美國認知與教育心理學家戴維·N.帕金斯曾將藝術家與科學家的人格進行了如下比較,認為“創造性的藝術家是一些不關心道德形象的放浪形骸者;而創造性的科學家則是象牙塔中冷靜果斷的居民”[注][美]阿恩海姆等著:《藝術的心理世界》,周憲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46頁。。其論也許不無偏頗,但在詩人、作家、藝術家的生平資料中,我們的確可以更多地看到不同于恪守禮儀、時常自我克制的道德人格者,實際上也不同于巧于周旋、善于審時度勢的政治人格者,或長于理性研判、冷靜沉著的科學人格等其他文化形態的人格者。他們,常常是無所顧忌,順其心性,特立獨行。會像中國古代詩人嵇康那樣敢于“薄名教,任自然”;會像李白那樣目空一切,“天子呼來不上船”; 會如同李贄所說的常見“絕假純真”之“童心”;會像英國詩人拜倫那樣宣稱“不自由毋寧死亡!”(《盧德派之歌》)。我們生活的現實世界總是不完滿的,人生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作家、藝術家的獨特價值之一正在于:通過赤誠率性、灑脫不羈、敢于沖破既有規范的詩歌意境及其他形態的藝術形象創造,讓讀者在想象世界中得以情感的宣泄、心靈的撫慰,以及生命自由與人性解放的滿足。
四是沖淡曠達,超逸高邁。與一般人格不同,優秀的詩人、作家、藝術家,在敏感于花開花落、物事紛擾,乃至人間苦難的同時,又會如同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所說的那樣,能夠“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會以中國古代哲學家莊子所說的“與天為徒”的心境面對,會以德國哲學家叔本華所說的“宇宙眼”視之。他們,會像雨果、托爾斯泰那樣,面對人間的丑陋與邪惡,不只是憤怒與仇恨,亦會以超逸的心態去包容世界,會用冉阿讓、聶赫留朵夫這樣一些在他們心目中亦不乏“善根”的人物去溫暖世界;會像沈從文那樣,同是面對戰亂與殺戮的人間,在小說中,不是站在某一立場著力于渲染仇恨,以求進一步激發階級的、民族的仇恨,而是以高邁的視野,注重用文學筆墨建立供奉“人性”的“希臘小廟”,力圖通過對“愛、自由與美”之類的追求,來化解人間的紛爭與仇恨。會像楊絳、孫犁那樣,同樣是寫“文革”期間的苦難,在其《干校六記》、《雞缸》、《王婉》等小說中,讓我們體悟到的是另一種不同于“傷痕文學”的沖淡曠達的人生意味。
上述分列的生命人格特征,在不同作家、藝術家的具體生命結構中,所占的比重自然并不相同,某一方面可能更具主導性,從而形成了李白不同于杜甫、雨果不同于托爾斯泰這樣一種生命個性與創作個性的差異,但在某一具體作家、藝術家身上,這諸多方面的生命人格特征,又是相互關聯、交互并存的。其中,敏感,即類乎生命底色,為所有作家、藝術家所共有。如果缺失了敏感,一個人也就缺失了成為作家、藝術家的基本質素。敏感與孤獨,又是相伴而生的,一位敏感者往往易致孤獨,一位孤獨者亦往往更為敏感。孤獨與率性、超逸亦具有內在相通性,實質上,率性與超逸,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孤獨的特異表現形態。
與主要基于文化教養、環境熏陶與自我追求而形成的政治人格、道德人格等其他文化形態的人格相比,作家、藝術家生命人格的形成,雖亦與環境影響及個人的文化追求有一定關系,但決定性的因素,是源于一個人遺傳性、先天性的命理機制,是涌流于血脈中的一種生命氣質,或如美國生物學家帕客(G.H.Parkir)曾指出的:這樣的個體人格,“如感覺的敏鈍,行動的遲速,氣質的特性,如憂郁或爽快的脾氣,無能,寡斷,誠實,節儉與可愛等,嚴格說來便都是大腦的機能。”[注]轉引自《陳立心理科學論著選》,杭州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48頁。這樣的個體生命機能,雖有可能因外在環境的壓抑而潛隱,但恐是難以從某一生命個體中完全清除的;或可因外在影響與主觀追求而強化,但恐也是難以無中生有的。正如民諺所謂“山好改,性難移”。比如一位率性人格者,可能會因時勢迫壓或利欲誘惑而有所收斂,卻是難以從骨子里徹底改變的。這樣一種情況,在作家、藝術家那兒,是廣為可見的。舉個例子來說,如在李白的一生中,既有過窮困潦倒之時,亦曾得享過宮廷的榮華,但不論在何處境中,李白終究還是那個仙風道骨、飄逸瀟灑、“一生好入名山游”(《廬山謠》)的李白。同樣,一位對事物缺乏敏感者,一位不甘寂寞者,一位心胸狹窄者,你想通過諸如教育之類的方式讓其變得敏感,變得孤獨,變得超逸曠達,也是不大可能的。
二、生命人格的順應與堅守
感覺敏銳、甘于孤獨、赤誠率性、超逸曠達之類的生命人格特征,當然不只為作家、藝術家所獨有,亦可見之于其他社會群體的成員。但從事其他活動者,因其職業與謀生原因,則不能不盡力予以自我克制。比如一位政治家,為了國家或黨派利益,或其他政治目的,有時不能不委曲求全,不能不韜光養晦,甚至不得不口是心非,不得不鐵血心腸,因而是無法孤獨、難以率性,也難以超逸高邁的。這就是為什么歷史上許多文學成就顯赫的詩人,大多在官場上郁郁不得志的重要原因。另如以建立并力倡道德規范為使命的倫理學家,以研判人間公正為使命的法學家,以窮究宇宙萬物之理為使命的科學家,以及工、農、兵、學、商諸色人等,也是很難像文學藝術家那樣孤獨、狂放、超逸的。而對于一位作家、藝術家而言,如果背離了敏感、孤獨、率性、超逸之類生命人格特征,也就等于放棄了自己的藝術生命。
從人類的文學藝術實踐來看,一位作家、藝術家,只有順應自己的生命人格,才能在作品流露中出更為本真的生命情懷,從而使之更為真切動人,也使之更具個性生命的質感與活力。但丁、莎士比亞、曹雪芹、蒲松齡、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福克納、貝多芬、凡·高、畢加索這樣一些文學藝術大師,無一不是憑依其敏感、孤獨之類的生命人格,才更為深切地感觸到人類社會的律動,體悟到了人生的幸與不幸,洞察到了大千世界的紛紜奧妙,從而創造出了《神曲》、《哈姆雷特》、《紅樓夢》、《命運交響曲》、《向日葵》、《格列尼卡》等一部部扣人心弦的小說、一首首撼人肺腑的樂曲、一幅幅動人心魄的繪畫。表面上內向沉默,而骨子里桀驁不馴,早在童年時代就已顯露出反叛個性,就敢于在課堂上當面質疑老師的中國當代作家莫言,亦正是因其順應了自己的生命個性,敢于訴諸“猶如孫悟空在鐵扇公主肚子里拳打腳踢翻跟頭,折騰個天昏地暗日月無光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口吐蓮花頭罩金光手揮五弦目送驚鴻穿云裂石倒海翻江蝎子窩里捅一棍”[注]《幾位青年軍人的文學思考》,《文學評論》1986年第2期。的狂放筆墨,才寫出了激情洶涌、風姿卓異的《紅高粱》、《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豐乳肥臀》、《蛙》等一系列世界聞名之作的。
特別值得深思的是:一位順應自己生命人格的作家、藝術家,有時甚至會“無意插柳柳成蔭”,在不經意中獲得創作的成功。中國當代作家畢飛宇,以小說語言的鮮明個性,尤其是極具張力的反諷韻味為人稱道,有不少學者已從修辭角度予以分析探討。實際上,當我們聯系到畢飛宇大學時代曾崇尚留長發的詩人,曾拒絕接受第七屆華語文學傳媒獎,以及他自己說過的“對一些人我從不妥協”之類性情來看,[注]姜廣平:《“我們是一條船上的”——畢飛宇訪談錄》,《花城》2001年第4期。其小說語言特征的形成,恐決非主要是作者有意為之的創作技術層面的修辭問題,在更深層次上,亦恰是畢飛宇順應了自己敏感、超逸以及骨子里的“狂放”之類生命人格特征的結果。個中奧妙,還是畢飛宇本人說得更為切中肯綮:“我惟一能做的,就是盡我的可能把我的生命人格注入語言,永遠不要當語言的奴才。”[注]林建法主編:《2002年文學批評》,春風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頁。這樣一種傾注了自我生命人格,而非主要賴于修辭訓練的語言,自然也就會從根底里與眾不同。另如被視為美國現代先鋒藝術大師的杜尚,自己大概也沒想過要創造什么先鋒藝術。長期留學美國的西方藝術史學者王瑞蕓女士曾有過如下有說服力的論析:“杜尚是一個對藝術對人生真的看開了、放下了的人。他是把這個眼光真正貫徹到他人生中去的人。他一生活得無滯無礙,如行云流水,視富貴功名如糞土。”[注]王瑞蕓:《變人生為藝術》,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頁。他將一個小便池當作自己的作品,“等于是用他自己的生活、生命本身提醒了我們這樣一個重要事實:藝術被限制在一幅畫或一個雕塑中是一種狹隘。他把藝術放大為做人,放大為人生”;用杜尚自己的話說,那只不過是“做我認為有趣的事罷了”[注]王瑞蕓:《變人生為藝術》,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頁。。杜尚之所以為人看重、名聲大振,關鍵原因亦正在于:此一順應自己生命人格、率性而為的反藝術的 “藝術活動”,本身就呈現了特定的生命意義。更為重要的是,巧合天緣,所作所為恰好隱含了時代所向往的藝術反叛欲望。正因如此,我們會看到,在杜尚成名之后,有不少自視為先鋒的效顰者,競相追隨,卻難以如杜尚那樣為人看重了。其原因又正如王瑞蕓女士這樣論及的,那些追隨者,“與杜尚徹底的反藝術是兩碼事。雖然這些人手里出來的作品都打著反藝術的旗號,但他們搶著進博物館的心情比誰都來得迫切”[注]王瑞蕓:《變人生為藝術》,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頁。。顯然,這樣一種缺少了生命人格的本源動力、而別有他求的外在模仿者,自然也就難有多少獨到的藝術創造價值了。
一位作家、藝術家,也只有堅守自己的生命人格,才能保持其創作生命力。唐代詩人李白洶涌的創作活力與文學成就,即與其堅守了狂放不羈的生命人格有關。試想一下,受到玄宗召見、成了翰林供奉之后的李白,如果如世俗之人那樣,受寵若驚,對玄宗感恩戴德,變得唯唯諾諾,中國文學史上大概也就沒有偉大的詩人李白了。中外文學史上不少作家的創作成就與藝術高度,亦均是基于這樣一種對自我生命人格的堅守。如美國當代小說家品欽,在1973年因一部《萬有引力之虹》成名之后,竟仿佛一下子從人間消失了,再也不肯露面,“沒讓人照過一張相,人們也不知道他目前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也不知道他還寫不寫小說”[注]袁可嘉等選編:《外國現代派作家選》(下冊),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第738頁。。人們后來知道,品欽當然還在寫小說,是在力避世俗紛擾、甘于孤獨中繼續埋頭他的創作,是在不為人知的近20年間,又悄然完成了《葡萄園》(1990年)、《梅森和迪克遜》(1997年)、《抵抗白晝》(2006年)、《性本惡》(2009年)等長篇小說。正是這樣一位品欽,才有了更為輝煌的創作成就,才進一步成為許多讀者與批評家心目中更為杰出的美國當代小說家。中國當代作家孫犁,之所以在晚年仍能文思泉涌,寫出了一大批諸如《雞缸》、《女相士》、《高蹺能手》、《亡人逸事》、《鄉里舊聞》等標志著新的藝術高度、境界高超、深受讀者喜愛的小說、散文,亦是與其厭見擾攘、畏聞惡聲、甘于孤獨的人格堅守有關的。我們知道,晚年的孫犁,“常常閉門謝客,從不主動結交官場人物,遠離人事糾葛,不參加文學圈子里的各種會議、活動,也不歡迎作者到自己家里來,愿意保持一種單純的文字之交為好,甚至家里長期不安裝電話”[注]趙天琪:《我所知道的晚年孫犁》,《縱橫》2005年第7期。。孫犁的這樣一種堅守,無關乎政治、道德,而正乃一位作家、藝術家所需要的對生命人格的堅守。與孫犁不同,我們會看到,在中國當代文壇上,另有不少詩人、作家,稍有成就之后,即熱衷于拋頭露面,孜孜于官位、榮譽、頭銜,結果只能是:除了徒增些虛名之外,創作方面已看不到有什么作為了。
三、“文品”、“藝品”與“人品”
在我們既有的文藝理論中,一直特別尊崇“文若其人”之說,并相信“文品”、“藝品”與“人品”之間存在著密切關聯。西人的代表性論斷是古羅馬朗吉弩斯“崇高是偉大心靈的回聲”;中國文論中則有諸如郭若虛所說的“人品既已高矣,氣韻不能不高,生動不得不至”,文征明所說的“人品不高,落墨無法”,清人薛雪所說的“著作以人品為先,文章次之”(《一瓢詩話》)等等。此外,法國人布封講過的“風格即人”,也常在此意義上受到推崇。
這類現已得到了文藝理論界普遍認可的看法,論據當然是充分的,也大致合乎文藝創作的實際。一名鼠竊狗盜之徒、心靈齷齪之輩,即使舞文弄墨,一般說來,是不大可能寫出值得肯定的作品的。但深究起來,這類將“人品”與“文品”、“藝品”完全扯在一起的看法,又是有問題的,在我國古代文論中,即早已不乏異議。宋人吳處厚在《青箱雜記》中即有是論:“世或見人文章鋪張仁義道德,便謂之君子,及花草月露,便謂之邪人,茲亦不盡也。”清人魏禧亦曾道及:“古人能事已備,有格可肖,有法可學,忠孝仁義有其文,智能勇功有其文。日夕揣摩,大奸能為大忠之文,至拙能襲至巧之語。雖孟子知言,亦不能以文觀人。”[注]轉引自錢鍾書:《談藝錄》,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61頁。在中外文學藝術史上,這類“人品”與“文品”、“藝品”并不統一的例子可謂不勝枚舉。讀者如果了解潘岳“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晉書·潘岳傳》)之類品行,大概就很難相信“絕意乎寵榮之事”,“覽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閑居賦》)之類文字會出于這樣一位“趨世利”者之手。宋詩中有一首《夏日登車蓋亭》:“紙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其超然淡遠之境界,令人神往。但這首詩的作者是曾經出任過宰相的蔡確,在《宋史》中是被置于“奸臣”之列的,其傳中載有“以賄聞”、“既相,屬興羅織之獄”之類劣跡。宋代另一位在書法方面有著很高藝術成就的宰相蔡京,也是以貪瀆弄權而聞名史冊的。在外國作家、藝術家中,如西班牙著名畫家畢加索,是以生活放蕩、濫情縱欲著稱的,一生中,不知有多少女性因他而陷入了悲慘命運。即如海明威這樣一位偉大作家,也不無品行方面的虧欠:慣于撒謊,5歲時,他就謊稱自已降服過一匹脫韁的烈馬;他曾欺騙父母與女電影演員梅·馬什訂了婚,事實上他只是在電影《一個國家的誕生》中看到過這位演員;他曾煞費苦心地編造了自己在芝加哥充當職業拳擊手的故事,說他的鼻子被打破,但他仍能繼續還擊;他曾謊稱在戰場上被機槍子彈擊倒兩次,被0.45厘米口徑的子彈擊中32次。[注]《海明威:深淵》,載[英]保羅·約翰遜:《知識分子》,楊正潤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面對此類事例,我們又如何理解“人品”與“文品”、“藝品”之間的關系呢?
為了進一步探明此類問題,這兒有必要首先弄清何謂“人品”?又何謂“文品”與“藝品”?在我們已有的理論中,“人品”通常是就腐敗墮落、不仁不義、媚顏卑膝之類的道德人格,或濫用公權、陷害好人、獨裁專制之類的政治人格而言的。而“文品”、“藝品”就比較復雜了,至少常見兩方面所指:一是指作品的格調氣度,二是指作品的精神內涵。就前者而言,與“人品”自然是沒什么必然關聯的。錢鍾書先生曾正確地指出:“其言之格調,則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風,不能盡變成澄淡,豪邁人之筆性,不能盡變為謹嚴。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注]錢鍾書:《談藝錄》,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63頁。錢先生所強調的“在此不在彼”,意思即是:所謂“文如其人”,只是就作者“豪邁”、“狷急”之類的性格特點與文章的相關格調之間的關聯而言的,不涉其他。而這“豪邁”、“狷急”之類性格特點,是無關政治,也無關道德的。就作品的精神內涵而言,有許多作品,比如一首山水詩、一幅花鳥畫、一件書法作品,也是不一定有什么道德與政治內涵的,對于這類的詩人、書畫家,又何談其“文品”、“藝品”?確有許多作品,尤其是表現社會現實生活的作品,是會有道德內涵或政治訴求的,但在真正優秀的作品中,亦必會同時充滿著人生感悟、生命沖動之類的復雜意緒,對于這樣一些內涵復雜的作品,當然也不宜僅以道德或政治內涵的“人品”尺度去對應考量。對此,莫言有一個看法倒是很值得進一步深思:“作家的人品與文品沒有完全直接的關系,一些道德敗壞的小人寫出的作品說不準是精品,而一些道德完善的君子寫出的作品卻會很爛。”[注]莫言:《作家和他的文學創作》,《文史哲》2003年第2期。
與道德或政治層面的“人品”視角相比,由生命人格著眼,或許能夠更為科學地認識作者與作品之間的關聯。文藝作品的某種風貌,肯定是源于作者生命人格的相關特征。如果就此而言,布封曾經強調的“風格即人”是對的。比如只有狂放不羈如李白者,才能寫出“黃河之水天上來”這樣豪放氣勢的詩篇;只有超逸如王維者,筆下才多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這樣的淡遠情致;只有敏感細膩、多情善感如李清照者,詞中才會多見“被翻紅浪”、“綠肥紅瘦”之類的婉約意象。在某一具體詩人、作家身上,由于既會有生命人格的主導特征,又會有交互并存的其他特征,故而豪放如李白者,也有過“床前明月光”這樣的柔情之作;超逸如王維者,也寫出過“試拂鐵衣如雪色,聊持寶劍動星文”這樣的壯懷激烈之作;敏感細膩如李清照者,也留下了粗獷雄健的“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一詩。對于上述現象 ,從“人品”角度,恐是難以說得通的,因為這狂放、超逸、細膩、敏感多情,以及上述錢鍾書先生所說的與“格調”相一致的“狷急人”、“豪邁人”之類,顯然更屬于與天性氣質更為相關的生命人格特征,而非社會文化性質的“人品”特征。
而諸如“狂放”、“超逸”、“敏感”、“ 細膩”之類的生命人格特征,自然不可能唯“人品”高尚者才會具有,亦會隱潛于許多人身上。由于筆情墨趣的誘導,或生活變故、自然風光等其他外在因素的激發,即使一些道德人格低下或政治人格有虧的人,在賦詩作文、寫字繪畫時,亦有可能超越自己的道德人格與政治人格,而順應其潛在的向往生命自由、掙脫利欲束縛之類的人格趨向,使之創作出境界高超的作品。對諸如存在政治人格或道德人格缺失的中國歷史上的潘岳、蔡確、蔡京,西班牙的畢加索、美國的海明威這樣一些人的文學藝術成就,或正可作如是觀。如潘岳雖有“拜路塵”之類的獻媚丑行,骨子里實亦不乏與一般人相通的厭恨塵世紛爭之意,辭官歸隱期間,恬淡的鄉野風情,又必會使之進一步強盛,在此期間寫出《閑居賦》之類作品,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亦可謂是其生命人格的自然體現。蔡確也是在被貶出朝廷之后,由山光水色激活了超逸情懷,才寫出了那首意緒淡遠的《夏日登車蓋亭》的。蔡京雖系權奸,但作為政治人物,原本就不乏“豪健”、“沉著”之類的生命人格氣度,當投注于書藝時,自然也就成了值得肯定的格調。至于畢加索的濫情縱欲、海明威的慣于撒謊,從文化人格的角度看是道德虧欠,而從生命人格的角度看,則又恰是有利于其創作成功的率性、超逸之類特征的體現。
正是經由對潘岳、蔡確、蔡京、畢加索、海明威這樣一些個案的分析,我們會進一步意識到,在探討“人品”對“文品”、“藝品”的影響時,不應將“人品”簡單地道德化或政治化,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人品問題“決不能認為是一個倫理道德問題,而應該是一個氣度問題。因此,人品的高下從根本上看取決于氣度的大小。換言之,只要氣度大,則無論大奸大惡還是大慈大悲,其人品必高,發于繪畫,其畫品也必高;如果氣度小,則無論小奸小惡還是小慈小悲,其人品必下,發于繪畫,其畫品也必下”[注]徐建融:《“揚州八怪”批判》,《文藝研究》1993年第6期。。正因如此,我們在評價相關作家作品時,也就不宜簡單化地因人廢文、因人廢藝。
在我們的理論中,另一值得進一步深思的相關問題是:不少學者認為,只有具備審美人格的作家、藝術家,才能創作出具有審美價值的作品。而事實上,許多創作出審美作品的詩人、作家、藝術家本人,抑郁終生,生活得并不“審美”,也就很難說他們擁有多大程度的超出常人的獨特審美人格。例如創作了許多美麗童話的安徒生,在現實生活中,就常常處于病態的苦悶與恐懼之中。因神經過敏,無論走到哪兒,都會覺得有人在蔑視他、侮辱他或暗算他。在充滿陰郁和絕望的信件中,他曾時常悲嘆他那可憐的身體——“虛弱”、“發燒”、“頭暈目眩”、“筋疲力盡”。因為時刻擔心被人活埋,他曾在睡覺的床頭上寫了一張條幅:“我睡著時看上去象死了似的!”[注][丹麥]歐林·尼爾森:《漢斯·克里斯琴·安徒生》,郭德華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8年,第73頁。貝多芬也這樣說過:“我過著一種悲慘的生活。兩年以來我躲避著一切交際,因為我不可能與人說話。我聾了。要是我干著別的職業,也許還可以;但在我的行當里這是可怕的遭遇啊。我的敵人們又將怎么說,他們的數目又是相當可觀。……我簡直痛苦難忍。……我時常詛咒我的生命。”他甚至寫下遺囑,準備自殺。[注]羅曼·羅蘭:《貝多芬傳》,載《傅譯傳記五種》,三聯書店1983年版,第134頁。如果我們僅從審美人格角度解釋諸如安徒生、貝多芬這樣一些作家、藝術家的藝術成就,恐也是不無牽強的。而從生命人格角度,會更易說得通:正因極度敏感而驚恐于人生痛苦,正因憤世嫉俗而自甘于孤獨,正因向往自由而渴望率真之類的生命人格,安徒生才想象出了那一個個安逸美好的童話世界,貝多芬才創作出了氣勢磅礴、喧騰著不屈生命激情的《熱情奏鳴曲》、《命運交響曲》等不朽樂章。
四、生命人格與藝術成就
由于側重于從道德或政治角度看待“人品”,故而人們對作家、藝術家文化形態的道德人格、政治人格等,往往有著更高的期許,譬如希望成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社會的良知”、“時代的代言人”等等。一些有成就的作家、藝術家,亦往往被作為人格楷模、偉大旗手予以褒揚與推崇。
在作家、藝術家群體中,道德品行高尚者當然是大有人在的,但也確有不少影響頗大的作家、藝術家,是說不上多么圣潔、多么高尚的,甚或是不無卑鄙低俗之劣跡丑行的。如以道德標準衡量,法國小說作家莫泊桑即惡習十足。他逛妓院,與各種女人鬼混,甚至有段時間與其他四位朋友同時共享一個女人。他曾公然宣稱:“我的朋友,床鋪就是我們的一生,我們生于斯,愛于斯,死于斯。”托爾斯泰亦不無齷齪與卑劣:曾誘奸過家中的仆人,曾遺棄了為他生了兒子的情婦。[注][美]歐文·華萊士:《名人隱私錄》,王金鈴譯,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版。深為世人喜愛的著名喜劇表演藝術家卓別林,品行亦夠得上“骯臟”:一味喜歡蹂躪含苞欲放的處女,曾為美國新聞界指責為“淫徒”。另如前述畢加索的生活放蕩、海明威的慣于撒謊等等。以政治人格來看,富有報國激情、時代責任感,或勇于反抗社會黑暗的斗士型作家、藝術家也是累累可見的。如中國古代的屈原、杜甫、白居易,現代的魯迅,前蘇聯的高爾基,英國的詩人拜倫、小說家喬治·奧威爾等等。但亦有許多有成就的作家、藝術家,并不怎么關心政治,或刻意遠離政治、避開政治、超越政治的,如中國古代的李清照、曹雪芹,現代的沈從文、徐志摩、張愛玲,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俄裔美國作家納博科夫、2013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加拿大女作家艾麗斯·門羅等等。更有甚者,依據一定的政治尺度,有些作家、藝術家,曾有過為世人詬病的污點,如巴爾扎克加入過保皇黨;1999年獲貝爾文學獎的德國小說家格拉斯曾信奉納粹觀念,并長期隱瞞了自己的納粹軍人歷史;身為宋太祖趙匡胤第11世孫的趙孟頫仕過元;周作人出任過偽職等等。
但上述那些道德人格有所虧欠,以及說不上政治人格,甚或有過政治污點的作家、藝術家,其創作成就似乎并未因此而大受影響;相反,有不少政治人格獲得頗高評價的詩人、作家、藝術家,藝術成就亦未必一定突出。如享有“英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創始人”之聲譽的“憲章派”代表詩人厄內斯特·瓊斯,被恩格斯稱贊為“德國無產階級第一個和最重要的詩人”的維爾特、日本著名無產階級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度頗受推崇的革命作家蔣光赤等等。有不少追求道德純正、恪守道德規范者,在賦詩作文時,也會緣其本原性生命人格的自我克制,而影響其創作質量。如宋代理學家朱熹、陸九淵、張栻、真德秀、魏了翁等人,雖也寫過不少詩歌,但大多給人枯燥之感,少有真正耐讀耐品之佳作。在我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我們還可以看到這樣一種現象:不少作家,在經由先進思想的教育改造之后,雖然道德人格提純了,政治人格提升了,藝術水平反倒下降了,如艾青、曹禺、丁玲等等。
正是透過上述現象,我們會發現,與“人品”關系密切的政治人格、道德人格,與一位作家、藝術家的成就之間,似乎并無必然聯系。而生命人格則不同了,一位作家、藝術家,如果缺失了敏感多情、想象活躍、甘于孤獨、率性而為之類的生命人格,是難以創作出優秀作品的。
與常人相同,一位作家、藝術家,無論如何偉大,亦終究是血肉之軀,亦會有源于本能的七情六欲,因而其整體人格不可能是完美的。而正因其不完美,才更具人之為人的生命活力與情感熱度,其作品也才會更為切近人性,更能呈現人生的斑斕多姿。如果苛求他們神圣化,期望他們承載更多超文學超藝術的使命,不僅不切實際,且勢必會壓抑其生命活力,遏制其作品中的情采與意緒,影響其創作成就。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一位作家、藝術家,原本就不應是時刻聽命于某些外在要求的政治工具,或處處循規蹈矩的道德奴隸,而更應是順其心性,敢于放任自我生命、勇于擴張自我生命者。
當然,我們承認作家、藝術家人格的不完美,強調放任生命、擴張生命,并不意味著可以縱容作惡,可以容忍無恥,可以躲避崇高。作家、藝術家,在順應并堅守諸如敏感、孤獨、率性、超逸之類更有益于優秀作品產生的生命人格的同時,還是要高度重視人品修養,至少要守住公平正義、仁慈善良之類的政治與道德底線。因為文學藝術,畢竟是引領人類精神文明的燈塔,畢竟具有推動人類不斷走向完美的力量;因為德藝雙馨,畢竟是人們更為向往的藝術人格標竿;因為從文學藝術的欣賞接受史來看,一個人的文學藝術成就無論多高,如果在政治或道德方面劣跡斑斑,亦會如宋代的蔡京那樣,難以為人們從心理上接受,而影響其應有的藝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