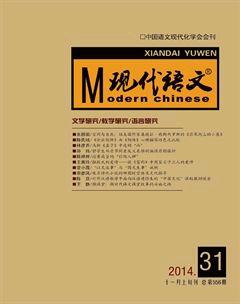論黃庭堅(jiān)的“引陶入禪”
摘 要:蘇軾和黃庭堅(jiān)作為北宋文壇領(lǐng)袖和宋代江西詩派的宗師,都深受東晉隱逸詩人陶淵明的影響。他們自身精深的禪學(xué)修為使其在論陶詩之時(shí)引援佛禪,亦為后代評論者“引陶入禪”[36]開啟了先河。
關(guān)鍵詞:黃庭堅(jiān) 陶淵明 蘇軾 引陶入禪
一直以來,儒道兩家學(xué)說對陶淵明思想與詩文創(chuàng)作的巨大影響已被學(xué)術(shù)界所認(rèn)可,不容置疑。但陶淵明是否接受佛學(xué)思想、其詩文創(chuàng)作是否受到佛學(xué)的影響,卻難以確定。眾說紛紜。陳寅恪是其中持否定意見的代表,《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guān)系》云:“陶集中詩文實(shí)未見贊同或反對能仁教義之單詞只句。”[1](P348)又說:“夫淵明既有如是創(chuàng)辟之勝解,自可以安身立命,無須乞靈于西土遠(yuǎn)來之學(xué)說。”[1](P315)并且說:“陶令絕對未受遠(yuǎn)公佛教之影響。”[1](P356)到了近代,認(rèn)為陶淵明受到佛學(xué)影響的學(xué)者漸多,以朱光潛、李澤厚、趙樸初等人為代表。葉嘉瑩先生也說:“陶淵明雖然,沒有正式皈依、信奉佛教,但在他的詩里卻反映出濃厚的佛教的空觀思想。”[2](P18)如“人生似幻化,終當(dāng)歸空無。”[3](《歸園田居其四》)“結(jié)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yuǎn)地自偏。”[3](《飲酒 其五》)所謂“遠(yuǎn)離”,在小乘佛學(xué)中指遠(yuǎn)離聚居的熱鬧之處,而到空寂的山林、墳地僻靜之地進(jìn)行修煉,目的在于擺脫世俗紛擾。大乘般若學(xué)認(rèn)為世間等同于世間,因此“不應(yīng)取法,不應(yīng)取非法”[4](《金剛經(jīng)》)。只要心地“遠(yuǎn)離”,不妨身處俗塵。《維摩詰經(jīng)》中說:“蚑行喘息人物之土,則是菩薩佛國。”“眾生之類,是菩薩佛土”。[5](P30)至于當(dāng)代,關(guān)于陶淵明的思想的論述成果斐然,在此就不贅言。[37]
陳公三語,其中第二語亦即對淵明與佛教之關(guān)系的根本判斷,概括得比較準(zhǔn)確。但第一語及第三語,則有待商榷及補(bǔ)充。而通過后代學(xué)者在這兩點(diǎn)上的研究可知陶淵明在思想方法上,還是受到了大乘般若學(xué)的影響。以佛解陶,由來已久,至今不絕。雖然陶詩從唐朝開始逐漸受到重視,在宋代確立經(jīng)典地位,得到宋人的普遍承認(rèn),陶淵明從此成為最受人喜愛的詩人之一。但“引陶入禪”的現(xiàn)象卻是從蘇軾開始濫觴,之后被葛立方等人推向極致。蘇軾在論陶詩時(shí)直接引用佛理,分析陶詩中的佛學(xué)影響,指出陶詩文中的許多詩句合乎佛理,開啟了從陶淵明詩文中指實(shí)合乎佛理之詩句做法的先河。蘇軾結(jié)合禪宗的“中觀”和般若空觀,賦予陶詩以不同的禪學(xué)韻味。蘇軾將陶淵明的詩作納入禪學(xué)的軌道,除了陶淵明自身思想不可避免地受佛教思想濡染之外,大概還因?yàn)樘K軾認(rèn)為成佛的關(guān)鍵在于“明心見性”,而非是否事佛。“淵明形神自我,樂天身心相物。而今月下三人,他日當(dāng)成幾佛。”[6](《劉景文家藏樂天身心問答三首戲書一絕其后》)蘇軾所謂成佛,是禪宗的“見性成佛”,“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4](《壇經(jīng)》)。蘇軾的學(xué)生,江西詩派之宗黃庭堅(jiān)在論陶時(shí)也有“引陶入禪”的傾向。
一、黃庭堅(jiān)的“引陶入禪”
黃庭堅(jiān)作為宋代另一位在詩歌地位上與蘇軾相提并論的詩人,在深受陶淵明影響的同時(shí),也將禪宗《楞嚴(yán)經(jīng)》和“法眼”等理論自覺地運(yùn)用到關(guān)于陶詩的詩論中。在參禪修道方面,蘇軾以親近云門宗為主,黃庭堅(jiān)則傾向臨濟(jì)宗,他曾入黃龍派嫡傳弟子晦堂祖心禪師及祖心得弟子的師門下,自稱“是僧有發(fā),似俗無空,作夢中夢,見身外身”[7]。“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于為詩也。至于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于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寧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為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fā)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dāng)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1](《題意可詩后》,《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六)道人曰云云出自《楞嚴(yán)經(jīng)》:“譬如琴瑟琵琶,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fā)。汝與眾生亦復(fù)如是,寶覺真心,各各圓滿,如我按指,海印發(fā)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又偈云:“聲無既無滅,聲有亦非生。生滅二緣離,是則常真實(shí)。”[8]這段話是主要宣揚(yáng)如來藏思想的,即常住、妙明、不動(dòng)、周圓與神妙真如:常住是不去不來;不動(dòng)是不生不滅;妙明是寂而常照;周圓是周遍圓滿無所不包;妙真如是真如能生萬法,能生一切妙有。“海印即佛心常住三昧,按指發(fā)光,動(dòng)成妙用也。”另一種解釋是“以按指喻舉心,以發(fā)光喻塵勞起也。正以不具妙智,故但發(fā)塵勞,不發(fā)妙用,正合無妙指不發(fā)妙音也。海印者應(yīng)是佛手印文,不指佛心三昧。舉心塵起,若克取前文,實(shí)即傾奪而為色空耳。”[9](《楞嚴(yán)正脈》卷九)“妙指喻觀行也!然汝與眾生寶覺真心各各圓滿與我無異,如我按指則海印發(fā)光,汝暫舉心則塵勞先起者,何也?良由愛念小乘,不肯勤求,得少為足耳!”[10](《楞嚴(yán)經(jīng)通議》第四卷)山谷引用這段話是喻淵明之詩為“海印”“妙音”,只有具備“妙指”才得窺見一斑。雖是論詩,卻也禪意盎然。
禪宗的“眼”有兩義,一指“句眼”,指語言文字中的微妙處;二指具眼人,黃庭堅(jiān)認(rèn)為只有具眼者才知句中眼。此眼又稱“法眼”“道眼”,華嚴(yán)宗稱其為“法界觀”,禪宗稱為“正法眼”,其根本精神是萬法平等視之,圓融無礙。這兩種含義的“眼”其實(shí)是統(tǒng)一的,只有具眼人才能明取句中眼。按照錢鐘書先生的說法,禪家的“句中有眼”喻“要旨妙道”。[11](P330)黃庭堅(jiān)常以“法眼”來觀照萬物,對于詩歌創(chuàng)作,更提出了“句中有眼”的詩歌理論。所謂“無俗不真”,是就事物的本體性空而言,禪宗認(rèn)為世間萬法都虛空不實(shí),在本來的意義上是真實(shí)平等的。其思想就來源于“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的華嚴(yán)法界觀以及禪宗的“平常心是道”。塵世百相,譬如眾生,如作白骨觀。在禪悟的境界里“無俗不真”,沒有真假的分別。“法眼”“世眼”,也即是“真諦”“世諦”。尤與大乘中觀學(xué)派的“真俗二諦說”頗有相通之處。此派學(xué)說由鳩摩羅什開始系統(tǒng)介紹進(jìn)入我國,成為各派佛教立宗的重要根據(jù)。俗諦又稱“世諦”“世俗諦”;“真諦”又稱“勝義諦”“第一義諦”。真諦是依佛教的道理提出的學(xué)說,是超越一切言語的般若正智,真諦不能用語言直接描述,只能用特殊的方式體悟,佛、菩薩為了把人們導(dǎo)向真諦,不得不借助世俗的語言和觀念,這世俗的語言只是方便說,佛陀隨順世間說的道理稱俗諦,俗諦就是禪宗的指月的手指。縱觀學(xué)派認(rèn)為因緣所生諸法,自性皆空,世人不懂此理,誤以為真實(shí)。這種世俗以為正確的道理,謂之“俗諦”;佛教圣賢發(fā)現(xiàn)世俗認(rèn)識之“顛倒”,懂得緣起性空的道理,以此種道理為真實(shí),稱為“真諦”。此二諦雖有高下之分,但均是缺一不可的“真理”。龍樹《中論》云:“第一義(諦)皆因言說(方得顯示);言說是世俗(諦)。是故若不依世俗,第一義則不可說”,即強(qiáng)調(diào)“真諦”必依賴于“俗諦”而顯示,要從“俗”中求“真”。隋僧吉藏《二諦義》卷上云:“真俗義,何者?俗非真則不俗,真非俗則不真。非真則不俗,俗不礙真;非俗則不真,真不礙俗。俗不礙事,俗以為真義;真不礙俗,真以為俗義也。”這就把真俗二諦彼此依存、互為前提條件的關(guān)系發(fā)揮得更為淋漓盡致。此派佛教學(xué)說旨在借助“二諦”來調(diào)和入世間和出世間的對立,但也在斷定世俗世界和世俗認(rèn)識的虛幻性的同時(shí),又從另一角度來肯定它們的真實(shí)性,為佛教之深入世俗生活提供理論根據(jù)。這種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深深地為宋代士人所習(xí)染。[12](P33-47)黃庭堅(jiān)運(yùn)用禪宗“法眼”“真諦”“俗諦”的概念來評論陶淵明的詩,黃庭堅(jiān)認(rèn)為,以“法眼”來看陶淵明詩,其拙與放之處正是其“愚不可及”之處,事實(shí)上,正如蘇軾把讀詩比成參禪一樣,黃庭堅(jiān)也將詩歌的“句中有韻”比作禪家的“句中有眼”,而這種比喻或類比本身就顯示出詩人具有圓融無礙的“法眼”。山谷從對佛家中觀學(xué)派的體認(rèn)和發(fā)揮中,深刻地把握陶詩“與一丘一壑者共之”的真不離俗、即真即俗的自然契合之境,在“真諦”與“俗諦”間,權(quán)借語言的表述,轉(zhuǎn)達(dá)出了語言之外的真如本體,讓人感到意象欲出、造化已奇的禪性。正是這一點(diǎn),才使陶翁高出庾信,而不是簡單地追求“不使語俗”。更重要的是陶淵明自身胸懷霽月,不為斗米折腰、和光同塵,并從卑俗低微的塵世生活中尋求真諦,因此才能“免俗”。
黃庭堅(jiān)進(jìn)一步融合臨濟(jì)宗參話頭、文字禪等修持方法,將“以禪喻詩”的觀點(diǎn)運(yùn)用于詩歌理論當(dāng)中,并由江西詩派繼承與發(fā)揚(yáng),主導(dǎo)宋詩的發(fā)展路線。黃庭堅(jiān)反對工巧,強(qiáng)調(diào)生拙。其借用一些禪宗思想和禪門話頭來論述陶淵明的詩歌,后來的吳可、楊萬里乃至嚴(yán)羽的以禪論詩也是如此,其內(nèi)涵大致與莊學(xué)甚至儒學(xué)不無共通之處。
二、蘇黃“引陶入禪”比較
第一,“云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3](《歸去來辭》)是千古傳誦的名句。同樣是化用“云無心以出岫”一典,中唐以前,多帶有飄泊無定、被文人尤其是漢魏文人用以感嘆自身命運(yùn)的“云”意象被蘇軾和黃庭堅(jiān)分別賦予了佛家“莫起分別心”和“無念為宗”的禪意:
陰晴朝暮幾回新,已向虛空付此身。出本無心歸亦好,白云還似望云人。[6](《望云樓》)
是身如浮云,安得限南北。出岫本無心,既雨歸亦得。[6](《送小本禪師赴法云》)白云出山初無心,棲鳥何必戀山林。[6](《贈(zèng)曇秀》)片云會(huì)得無心否?東西南北只一天。孤云出岫豈求伴,錫杖凌空自要飛。[6](《蜀僧明操思?xì)w龍丘子書壁》)
在蘇大學(xué)士的詩中,“出岫”與“知還”,都統(tǒng)一到“人雖有南北,佛法本無南北”[4](《壇經(jīng)》)這個(gè)大前提下,無論出入進(jìn)退,貴在返本歸真,也就是歸于“自性本來清凈”。其次,淵明的“無心”之境,被南宗的“無心”禪法巧妙地解釋或者混而為一。惠能謂“有道者得,無心者通”。惠能五世法孫希運(yùn)更是力主“但能無心,便是究竟”,“無心者無一切心也。真如之體,內(nèi)如木石,不動(dòng)不搖;外如虛空,不塞不礙;無能所,無方所,無相貌,無得失。”[13](P18-31)禪宗之無心的涵義與般若經(jīng)典有密切的關(guān)系,無心表示般若空觀的體證,是基于佛教緣起性空而得之精神的提升與解脫。老莊之無心與道之體現(xiàn)有關(guān),道具有創(chuàng)生的、形而上的主宰地位,人須去除一切主觀的偏執(zhí),讓心處于虛明之狀態(tài),才能體現(xiàn)道之存在意義,同時(shí)達(dá)成主體的精神自由。郭象之無心觀與其獨(dú)特之自然、自生自化之理論有內(nèi)在的聯(lián)系。與老莊之偏重工夫論意義之無心相比,郭象之無心觀具有更豐富的內(nèi)涵,反映出魏晉思想之特色。基本上,禪宗與道家之無心均表達(dá)精神之自由,不受外在環(huán)境與主觀意見之影響,故在相當(dāng)范圍內(nèi),兩者有所交集。但嚴(yán)格而言,雙方各有其理論依據(jù)。東坡禪悅詩中用“無心”之典時(shí),其內(nèi)涵與上述理論相似;但與淵明的本意相比較,則貌合神離,相去甚遠(yuǎn)矣。如果說,淵明筆下的無心之境是為了獲得一個(gè)超越的精神境界而“守拙歸園田”,那么,東坡禪悅詩中的無心之境就是“當(dāng)知直心,求菩薩凈土”。
同蘇軾一樣,黃庭堅(jiān)在詩作中也借用《歸去來兮辭》中“云無心以出岫”一語:“水之為物,甚寒而極清。郁為堅(jiān)冰,得溫而釋,遍利諸生。云之為物,無心而出岫穴。風(fēng)休雨息,反一無跡。……萬法本閑,而人自擾擾爾。”[7](《清閑處士頌》)“殊不知云無心而出岫。水盈科而或流。遇高山而必止。至大海而方休。”詩中兼用儒家“夫水,大遍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14](《荀子·宥坐》)的典故,釋家也有“為利眾生,受諸菩提”之說。詩的結(jié)尾正有“正所謂萬境本閑,唯心自鬧,一心不生,萬法俱息”[15](《印光法師文鈔后編》)的禪宗“無念為宗”的思想。“知見一切法,心不得染著,是為無念。”“無念為宗”這一原則的確立,最早見于《神會(huì)語錄》。其中有曰:“無念者,無何法?是念者,念何法?”答曰:“無者,無有二法;念者,唯念真如。……所言念者,是真如之用;真如者,即是念之體。以是義故,立無念為宗。”[16](《神會(huì)語錄》)在《壇經(jīng)》看來,所謂“無念”,就是“于念而不念”,具體地說,就是“于一切境上不染名為無念。于自念上離境,不于法上生念。”“流水鳴無意,白云出無心,水得平淡處,渺渺不厭深。”[7](《以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為韻寄李子先》)葛兆光先生曾專門探討了“云”這一意象在中唐時(shí)因?yàn)槎U宗影響而發(fā)生的變化:自中唐始,由于受佛教及禪宗的影響,人們的觀物方式發(fā)生了變化,“云”由外在的自然物象轉(zhuǎn)化為悠然自在的禪意象征,自此而與心靈融為一體。[17](P77-86)而在蘇軾和黃庭堅(jiān)筆下的“出岫之云”更帶有了悠然自在的禪意象征的意義,契合隨緣任運(yùn)、無心自在的生活態(tài)度及其所追求的境界。在黃庭堅(jiān)的詩中,“云”由原先隱者的象征,轉(zhuǎn)而摻雜了作為悠閑自在的禪意象征,從而追求一種渾然天成、不煩繩削而自合的境界。
第二,蘇軾云:“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xiǎn)過之,而溫麗精深不及也。所貴乎枯澹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shí)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二也。”[1](《評韓柳詩》)又謂:“吾于詩人,無所甚好,獨(dú)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zhì)而實(shí)綺,癯而實(shí)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1](《與蘇轍書》)“佛所言說,皆應(yīng)信順。譬如食蜜,中邊皆甜。吾經(jīng)亦爾。”[18](《四十二章經(jīng)》)《四十二章經(jīng)》相傳為中國第一部漢譯佛經(jīng),在宋代有真宗、守遂等注本,流傳頗廣。佛經(jīng)原意告誡信眾,研修佛學(xué)不應(yīng)有小乘、大乘的分別心,應(yīng)要“中邊皆甜”。蘇軾在這里化用這一佛典,依照“中邊”即“中觀”的觀點(diǎn),則俗與雅、故與新、枯與膏、澹與美均為相即相徹的對立統(tǒng)一的概念,也就是說,這些對立概念之間并非只有一種非此即彼的選擇,而完全可以并且應(yīng)該統(tǒng)一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圓融境界。“質(zhì)而實(shí)綺,癯而實(shí)腴”意為其外“質(zhì)”而“癯”,其中“綺”且“腴”。蘇軾用佛經(jīng)中的人食五味來比喻對陶詩的品評,一般人對一種純粹的味道容易分辨,但要分辨“中邊”之殊異的詩中三昧就不易了。而“枯澹”的藝術(shù)風(fēng)格,正是“以俗為雅”的最高審美追求。僧肇《鳩摩羅什法師誄并序》形容法師的精神境界說:“融冶常道,盡重玄之妙;閑雅悟俗,窮名教之美。”也正是冥同玄遠(yuǎn)與世俗的平淡自然之美。[12](P33-47)蘇軾認(rèn)為詩之韻味得自詩人內(nèi)心的空靜,“欲令詩句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群動(dòng),空故納萬鏡。”[6](《送參寥師》)還認(rèn)為心如止水才能更好地反照外物,“能如水鏡以一含萬,則書與詩當(dāng)益奇。”[19](《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敘》)空靜說的提出,一方面繼承了道家“滌除玄覽”的“虛靜”說,另一方面借用了禪宗大乘般若學(xué)的空觀和動(dòng)靜觀。心靈空靈澄澈,便可洞察機(jī)微、統(tǒng)攝三千、包羅萬象。縱然煙水掩目,亦可飛澗撥紋。這種空靜境界,“真空妙有”禪家“悟境”本就是微言妙諦、語淡蘊(yùn)深的詩家“化境”。蘇軾所極為推崇的陶詩的“枯淡”,實(shí)際上也是空靜境界的具體體現(xiàn)。他晚年仰慕陶淵明的平淡美處,達(dá)到了“至其得志,亦不甚愧淵明”[1](《與蘇轍書》)的境地。
蘇、黃都推崇陶淵明至華無文的平淡詩歌風(fēng)格。蘇軾評陶詩曰“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shí)美”[1](《評韓柳詩》),黃庭堅(jiān)則欣賞淵明的大巧若拙“至于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于檢括者輒病其放。”[1](《題意可詩后》)事實(shí)上,“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1](《題意可詩后》)正是黃庭堅(jiān)早期的藝術(shù)風(fēng)格,“黃氏中年提倡法度,重鍛煉,到了晚年則有努力回歸自然平淡的傾向,與其晚年崇陶一致,但不是否定法度,也不是法度的更新,而是法度運(yùn)用得更加自由了。”[20](P248)
從表面上看,蘇、黃的“引陶入禪”都顯示了重視詩歌的平淡的價(jià)值取向,但兩者實(shí)則不同。蘇軾大抵重禪悟,“然其詩質(zhì)而實(shí)綺,癯而實(shí)腴”[1]。《與蘇轍書》這種“質(zhì)而實(shí)綺”的禪悟具體表現(xiàn)在蘇軾對于陶淵明《飲酒》一詩的評論:“‘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因采菊而見山,境與意會(huì),此句最有妙處。近歲俗本皆作‘望南山,則此一篇神氣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1](《題淵明飲酒詩后》)在這一評論中,蘇軾點(diǎn)出了陶詩“意與境會(huì)”的特點(diǎn),也就是陶詩的“腴”。同時(shí),蘇軾又指出,陶詩中“見”,不能改作“望”;因?yàn)椋耙姟笔桥既慌d會(huì),“望”則“主觀追求”,人物精神風(fēng)神表現(xiàn)不同,又指出“古人用意深微”。這就使“樸字見色,平字見奇”,突出了陶詩“綺”的一面。黃庭堅(jiān)大抵偏重律法:“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38]由于以上的差別,因此,雖然同是追求枯淡藝術(shù)風(fēng)格,有學(xué)者概括為:蘇軾的態(tài)度是,順應(yīng)心靈的感受,遵循自然的極則,不經(jīng)意而達(dá)到平淡,主張從自由出發(fā)而不違法度,所謂“如風(fēng)吹水,自成文理”。黃庭堅(jiān)的態(tài)度是,既要經(jīng)過斧鑿,又不要人看出斧鑿痕,通過人工鍛煉達(dá)到平淡,主張從法度出發(fā)而最終獲得自由,所謂“得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兩人不僅態(tài)度迥然不同,而且蘇的法度主要是指一種“理”,客體的審美特征和主體的情感尺度;黃的法度主要是指“法”或者“律”。一種藝術(shù)形式方面的規(guī)范。蘇軾提倡的平淡,是性靈妙悟,天機(jī)自發(fā),沖口而出,揮筆而就,如清亮的山泉,隨山石曲折。黃庭堅(jiān)提倡的平淡,是覃思苦想,慘淡經(jīng)營,有如熬得太久的雞湯,以至于清淡中有幾絲焦味。[21](P94-95)蘇軾所追尋的是一種“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的未經(jīng)規(guī)范的自然狀態(tài),而黃庭堅(jiān)所崇尚的則是經(jīng)過不斷錘煉而形成的“不煩繩削而自合”的從規(guī)范到超越規(guī)范的狀態(tài)。
第三,黃庭堅(jiān)和蘇軾對于“無弦琴”這一典故的接受也不盡相同,前者將其和頓悟真如的境界聯(lián)系起來,而后者則在此基礎(chǔ)上提出了更高的境界。南朝梁蕭統(tǒng)《陶淵明傳》:“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弦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1](《陶靖節(jié)傳》)“陶淵明作《無弦琴》詩云:‘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聲。蘇子曰:淵明非達(dá)者也。五音六律,不害為達(dá),茍為不然,無琴可也,何弦乎?”[1](《劉陶說》)“我今不飲非不飲,心月皎皎長孤圓。有時(shí)客至亦為酌,琴雖未去聊忘弦。”[22](《謝蘇自之惠酒》)東坡對阮籍、劉伶等人以其狂傲怪誕濁世形態(tài),以酒求名求高頗不以為然。而東坡引莊子之言,以為全于酒未若全于天。無有一物,心境便入澄澈;火宅本空,塵身不困牢城。《傳燈錄》:“心月孤圓,光吞萬象。”[23](《景德傳燈錄卷七盤山寶積章》)在這里,東坡用無弦琴的典故表達(dá)了禪宗里一種“花落還開,流水不斷,華枝春滿,天心月圓,大千同我,無憂無煩”的境界。“列子御風(fēng)殊不惡,猶被莊生譏數(shù)數(shù)。步兵飲酒中散琴,于此得全非至樂。樂全居士全于天,維摩丈室空翛然。平生痛飲今不飲,無琴不獨(dú)琴無弦。”[6](《張安道樂全堂》)在《謝蘇自之惠酒》詩的基礎(chǔ)上,蘇軾不但否定了“弦”,更進(jìn)一步否定了“琴”。六祖慧能有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4](《壇經(jīng)》)心體為“本無”。蘇軾將禪宗的“空觀”和莊子的“無待”思想相結(jié)合,相較于淵明,這種不借助萬有而期望心靈直接悟達(dá)本體究竟的思悟方式更加接近于禪宗,而與玄學(xué)為遠(yuǎn)。“以手指月,而指非月”,在禪宗看來,法界萬有無非是一張以月為徽,以風(fēng)為弦的古琴,能夠撫弄這樣的無弦琴,自是深得真空妙有、無生而生之禪悟真諦。禪宗的“無相之相即實(shí)相”,“無音之音為大音”,和老子所云“大音希聲”有殊途同歸之意。然而不同的是,莊子的“無待”是以無限的自然絕對立場消滅個(gè)體的自我意識,以達(dá)到“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而禪宗正相反,特別是以慧能為首的南禪宗倡導(dǎo)本體的一元論,自困唯心,自渡唯心,此心有本,一瞬歸程。無弦之琴彈奏的不是世間的靡靡無常之音,而是諸法實(shí)相,不生不滅,不來不去之音。陶淵明以無弦琴會(huì)友,是因“無弦琴本身就具有意蘊(yùn)的自足性,無須與更多的意象組合就產(chǎn)生與玄學(xué)相通的深妙意味。……陶淵明借助無弦琴體悟人生真諦的做法是對玄學(xué)‘得意忘言思悟方式的詩性化繼承,無弦琴所寄托的意趣與玄學(xué)之‘無(‘意),無弦琴形象與玄學(xué)的‘言、象取得了對應(yīng)關(guān)系。”[24](P187-190)但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的“得意忘言”“得意忘象”的玄學(xué)本末體用說在魏晉時(shí)期引發(fā)的“重本輕末,崇無賤有”的風(fēng)尚,更導(dǎo)致“有”“無”絕對對立的思想方法危機(jī)。般若實(shí)相觀的出現(xiàn)及其與《涅槃》學(xué)相結(jié)合的流布從某種程度是化解的這個(gè)問題,般若實(shí)相學(xué)認(rèn)為,作為宇宙本體的“真諦”,是獨(dú)立于名教之外,“非文言所能辯者”。它既有非無,又亦有亦無;并非“有相”,亦非“無相”。[25](P127-138)
從唐代開始,禪宗語錄便多次談及“無弦琴”這一話頭,如龐居士贊馬祖道一時(shí)說:“一等沒弦琴,唯師彈得妙。”[26]《古尊宿語錄》還有“風(fēng)前一弄無弦曲,會(huì)有叢林人賞音。只如燈燈相續(xù),心心相印,血脈不斷處,作么生行履,還體悉得么?”[27](《宏智禪師廣錄》卷四)凡此,有學(xué)者認(rèn)為無弦琴則被認(rèn)為是禪意的代名詞。[28](P96)“三十年來無孔竅,幾回得眼還迷照。一見桃花參學(xué)了。呈法要,無弦琴上單于調(diào)。”[29](《漁家傲》)黃庭堅(jiān)以引禪典入詞,將唐末靈云志勤禪師的開悟偈“三十年來尋劍客,幾逢花發(fā)幾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30]與淵明“無弦琴”典故結(jié)合,以此作比,來闡述修行悟道至法無法的禪理:琴有弦,所奏音調(diào)總有一定限制,每一根弦都是對一個(gè)范圍中的聲音的執(zhí)著,只有全部執(zhí)著都能放下時(shí),那才是徹底的大自在;唯其無弦,方能奏出廣大無限之調(diào),以此倡導(dǎo)一種縱橫自在、純?nèi)伪救坏木辰纭l`云三十年來蒙昧混沌,幾番出入于迷悟之間。最后一見桃花,終于參悟。以無弦琴作喻比之至法無法的禪理:縱橫自在,純?nèi)伪救唬庆`云參悟的境界。靈云為求悟,歷經(jīng)曲折,虛度半生,所以我輩應(yīng)以靈云為鑒,趁著年少及早悟道。道遍一切處,流水、行云無不是悟道的機(jī)緣,何必執(zhí)著于桃花。在詞中黃庭堅(jiān)以“無弦琴”和靈云禪師的“桃花”作為對立意象,在黃看來,靈云三十年的蹉跎,尚有“漸”的痕跡,而我輩追尋的則是“無弦琴上單于調(diào)”的悟道至高境界。頓悟說禪宗在參悟“真如”時(shí)主張頓悟見性,禪家有一個(gè)基本思想就是佛即本心,無須外求。悟也就要“自身自性自度”。黃庭堅(jiān)追求的就是這樣一種在靜默關(guān)照時(shí)“忽然撞見來時(shí)路”的瞬間感悟:“凌云一笑見桃花,三十年來始到家。從此春風(fēng)春雨后,亂隨流水到天涯。”[7](《題王居士所藏王友畫桃杏花二首(之一)》)“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7](《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會(huì)心,為之作詠》)“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陽樓上對君山”[7](《雨中登岳陽樓望君山二首》之一)。這種佛祖“拈花一笑”式的超然頓悟卓越風(fēng)姿,指的就是在瞬間頓悟時(shí)對心境相合,手心相應(yīng)的自然境界的期望與追求,借助于內(nèi)心的默領(lǐng)神會(huì)去化解胸中的學(xué)問和見識,為詩創(chuàng)造“機(jī)緣”,而使詩出于自然。[31](P14)山谷在《送陳蕭縣》用翻案法遞用陶淵明“無弦琴”的典故。翻案法禪家轉(zhuǎn)語,即翻進(jìn)一層,北宗禪神秀主漸悟:“時(shí)時(shí)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南宗禪反其意而言:“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后人把這種方法用于做詩上,稱為翻案法。翻案法的運(yùn)用在唐詩中初露端倪,而在宋詩中已蔚成風(fēng)氣禪宗講求翻案的逆向思考手法,啟發(fā)黃庭堅(jiān)詩歌理論“以故為新”“以俗為雅”的觀點(diǎn)。黃庭堅(jiān)的詩利用禪宗典籍提供的大量的典故和俗語,將這些典故和俗語與禪宗的翻案法相結(jié)合,化用前人的詩句。黃庭堅(jiān)受禪宗翻案法的啟迪,提出“以故為新”“以俗為雅”的創(chuàng)作觀,“以故為新”“以俗為雅”與禪宗參究公案、話頭別出心裁的觀點(diǎn),頗有暗合道妙之處。在《送陳蕭縣》中,“無弦琴”成為貫穿整首詩的線索。第一次“陶令無弦之琴”主要指志趣相投的默契友情,第二次“乃知不必徽弦具”之琴主要喻指朋友以德化民,如春雨潤物,潛移默化,其功也大;第三次“此中亦有無弦意”主要喻指擺脫俗累的閑適雅趣。此典三用三新,疊用疊奇,而又互相關(guān)聯(lián),實(shí)為陶淵明“無弦琴”接受史中的創(chuàng)舉。[32](P324-325)黃庭堅(jiān)還常常將《莊子》中“匠石斫鼻”的典故與淵明“無弦琴”相提并論:“贈(zèng)君以匠石斫泥之利器,淵明無弦之素琴。”在黃庭堅(jiān)看來“斫鼻”不如“無弦”:“斫鼻昔常爾,絕弦知者希。”匠石斫鼻雖然心手相應(yīng),神無比,但終究“有數(shù)”,而不能象 “無弦之琴”一樣做到“無功”。[33](P150)黃庭堅(jiān)還用“拾遺句中有眼,彭澤意在無弦”[7](《贈(zèng)高子勉》)來概括他最贊賞的詩人杜甫和陶淵的創(chuàng)作特征。任淵注云:“老杜之詩眼在句中,如彭澤之琴,意在無弦外。”[7]這個(gè)注解并不能完全闡釋黃庭堅(jiān)的這句話,可以說,杜詩和陶詩分別代表著萬象森列和大象無形的兩種“至有”和“至無”的境界。而黃庭堅(jiān)又將淵明的“無弦”之意與宋代“文字禪”中“不立文字,不離文字”的“印心說”聯(lián)系起來。
而蘇軾對于無弦琴的解讀正如前文所述,在陶淵明的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否定了“琴”,將無弦琴和“緣起性空,自在枯榮”的般若禪境聯(lián)系在一起。再者,蘇軾還將陶典與夢境結(jié)合在一起,表達(dá)了“人生如夢”般若空觀和前世今生的因果宿命論:“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予自杭州還朝,宿吳淞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予,彈之有異聲,就視,琴頗損,而有十三弦。予方嘆惜不已,殊曰:‘雖損,尚可修。曰:‘奈十三弦何?殊不答,誦詩云:‘度數(shù)形名本偶然,破琴今有十三弦。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予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既覺而忘之。明日晝寢復(fù)夢,殊來理前語,再誦其詩,方驚覺而殊適至,意其非夢也。問之殊,蓋不知。”[6](《破琴詩序》)
三、小結(jié)
和陶淵明的詩歌相比,蘇黃二人都創(chuàng)造性地融入了禪宗的思想旨趣,將儒釋道三家的思想旨趣作為解決身心矛盾的詩性源泉。但從蘇黃兩人對“無弦琴”和“云無心以出岫”的不同化用,可以看出兩人不同的禪悅觀。所謂禪悅,是指在參禪學(xué)佛的活動(dòng)中得到心靈的愉悅。宋代文人用儒家思想來解決將個(gè)人價(jià)值寄托于社會(huì)責(zé)任的政治道德問題,也就是“世間法”,而禪宗思想則是用來的解決個(gè)人存在的自然本性和社會(huì)性的矛盾問題,也就是“出世法”。兩者相互結(jié)合,或進(jìn)或退,總能堅(jiān)守住一片心靈最后的凈土。禪悅思想為古代文人提供了一個(gè)保持心理平衡和人格完整的退避之地。在蘇軾和黃庭堅(jiān)的繞路說禪的背后是不同的禪悅思想的折射:般若與如來藏。[34](P28)無論是“陰晴朝暮幾回新,已向虛空付此身”[6](《望云樓》) 還是“無弦則無琴,何必勞撫玩”[6](《和頓教授見寄》)都強(qiáng)調(diào)禪宗的般若空觀:“緣起性空,自在枯榮”,“無生無滅,緣合謂生,緣離謂滅”,虛而不實(shí)就是事物本身的真實(shí)性狀,宇宙萬物都是地、火、風(fēng)、水依因緣聚合而生滅的幻象這個(gè)世界實(shí)際上是無生無滅的,幻化的只是人心而已。黃州之貶、惠州之難是詩人思想莊禪化的大轉(zhuǎn)折。他和陶而不似陶,“自用本色”,以禪宗的空觀取代了老莊的委運(yùn)乘化:“百年六十化,念念竟非是。是身如虛空,誰受譽(yù)與毀?”[6](《和陶飲酒二十首》其六)“感子至意,托辭西風(fēng)。吾生一塵,寓形空中。”[6](《和陶答龐參軍六首》其六)“對弈未終,摧然斧柯。再游蘭亭,默數(shù)永和。夢幻去來,誰少誰多?彈指太息,浮云幾何?”[6](《和陶停云四首》其四)“萬劫互起滅,百年一踟躕。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6](《和陶和劉柴桑》)正是通過對陶詩的禪意的個(gè)性解讀,成為蘇軾超越世俗悲情的精神支柱:“但應(yīng)此心無所住,造物雖馳如余何?”[6](《百步洪二首》)將陶詩的樂觀精神同宋代士人超越悲情的精神融合起來,塑造出善于處窮的陶淵明這一形象,是蘇軾在陶淵明接受史上的又一大貢獻(xiàn)。[32](P324-325)
而對黃庭堅(jiān)來說,他是臨濟(jì)宗黃龍派的法嗣,曾以黃龍派的參禪手段為禪修方法,打破疑情,體悟到心是幻法,勘破心念的虛幻,體會(huì)到心性本體(真如)清凈、寂靜的特質(zhì),并以般若思想為指導(dǎo)進(jìn)行禪觀實(shí)踐,通過對自我身心進(jìn)行深入觀照,以期達(dá)到般若思想“畢竟空”的境界。[35](P28-46)山谷將詩品之詣,歸結(jié)于人品,又將陶淵明高妙的人品稱為:“淵明風(fēng)流”“樂易陶彭澤,憂思庾義城。風(fēng)流掃地盡,詩句識馀情。”[7](《和答李子真讀陶庾詩》)“風(fēng)流豈落正始后”[7](《次的子高讀淵明傳》),“俗里光塵合,胸中涇渭分”[7](《次韻答王眘中》),“胸次九流清似鏡,人間萬事醉如泥。”[7](《戲效禪月作遠(yuǎn)公詠》)黃庭堅(jiān)受真如的禪悅思想的影響,較注重于心性修養(yǎng),能跳脫世俗煩惱而淡泊自持,將禪法厚植于生命實(shí)踐當(dāng)中。在黃庭堅(jiān)看來,士大夫只有擁有了安身立命之本——內(nèi)在的不受污染的清凈心,才能摒除利欲之心,憂患之念,在他看來,只有保持不受緇磷的清凈之心,才能真正實(shí)現(xiàn)儒家的政治倫理主張,治世必須首先治心。而在這一點(diǎn)的相同,確實(shí)使得他與陶淵明有了神交之契。黃庭堅(jiān)所說的“心”,從宇宙觀上說,等于真如本體;從解脫論上說,又是純粹的主觀心性。這樣,他就像一個(gè)超脫世俗、冷眼旁觀世間靈魂沉浮的修行者,而不時(shí)生出慈悲拯救之心。由于保持著對真如之心自我完善的追求,黃庭堅(jiān)達(dá)到一種挺立道德實(shí)體的心性誠明的儒者氣象與超然物外的清靜胸襟的佛道妙悟相結(jié)合的境界。這使他在面對官場的拘牽、政敵的迫害時(shí)仍能以一種寵辱不驚的態(tài)度泰然置之。當(dāng)然,在蘇軾的“和陶詩”中也仍有表現(xiàn)“如來藏”禪悅觀的例子,如“夢求亡楚弓,笑解適越冠。忽然返自照,識我本來顏。歸路在腳底。”[6](《和陶東方有一士》)蘇軾自敘曾在仕途的波浪中迷失“本來顏”。“如來藏”本來澄明湛寂,自性清凈心,心性隨緣起染,生滅流轉(zhuǎn)。“如來藏”一似不動(dòng)的水,被“無明”之風(fēng)所吹拂,遂成為生滅心的動(dòng)水。
繼蘇黃之后,宋代又有不少文人在論陶詩時(shí)提及陶詩與禪宗的關(guān)系,最典型的要屬葛立方,他將陶淵明譽(yù)為“第一達(dá)摩”,將蘇軾的“引陶入禪”推向極端。究其原因,除了宋代文人禪修的環(huán)境因素,一定程度上取決于蘇、黃兩家的“引陶入禪。”因?yàn)樘K、黃作為北宋文壇的領(lǐng)袖人物,他們的理論往往直接影響著宋代詩歌理論的發(fā)展,甚至影響后世。因此,研究蘇、黃詩“引陶入禪”的過程及異同,對于研究和解釋整個(gè)宋代甚至后代的陶淵明接受過程中的某些現(xiàn)象,具有重要意義。
注釋:
[1]北京師范大學(xué)中文系,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文學(xué)史教研室:《陶淵明資料匯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又后文所引古人論陶語,悉出于此,不復(fù)注出。
[2]葉嘉瑩:《葉嘉瑩說陶淵明飲酒及擬古詩》,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
[3]陶潛著,龔斌校:《陶淵明集校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4]陳秋平,尚榮:《金剛經(jīng)?心經(jīng)?壇經(jīng)》,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
[5]張晶:《禪與唐宋詩學(xué)》,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3年版。
[6]蘇軾:《蘇軾詩集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7]黃庭堅(jiān):《山谷詩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8]參見《嚴(yán)經(jīng)》,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
[9]真鑒:《大佛頂首楞嚴(yán)經(jīng)正脈疏》,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36年版。
[10]張永儉:《憨山大師法匯初集》,香港佛經(jīng)流通處,1997年版。
[11]錢鐘書:《談藝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30頁。
[12]王水照:《文體丕變與宋代文學(xué)新貌》,中國文學(xué)研究(長沙),1996年,第4期,第33頁,第47頁。
[13]魏啟鵬:《蘇詩禪味八題》,《東坡詩論叢蘇軾研究論文第二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頁,第39頁。
[14]荀況:《荀子》,北京 : 中華書局, 2007年版。
[15]印光:《印光法師文鈔續(xù)編》,臺北:財(cái)團(tuán)法人佛陀教育, 2000年版。
[16]刑東風(fēng)釋:《神會(huì)語錄》,臺灣:佛光出版社,1996年版。
[17]葛兆光:《禪意的“云”:唐詩中的一個(gè)語詞分析》,文學(xué)遺產(chǎn),1990年,第3期,第77,86頁。
[18]佛教:《四十二章經(jīng)》,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
[19]蘇軾:《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
[20]錢志熙:《黃庭堅(jiān)詩學(xué)體系研究》,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版,第248頁。
[21]周裕鍇:《蘇軾黃庭堅(jiān)詩歌理論之比較》,文學(xué)評論,1983年,第4期,第94-95頁。
[22]潘永因:《宋稗類鈔》,北京:書目文獻(xiàn)出版社,1985年版。
[23]道原:《景德傳燈錄譯注》,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版。
[24]李劍鋒:《陶淵明及其詩文淵源研究》,濟(jì)南:齊魯書社,2002年版,第187頁,第190頁。
[25]高華平:《凡俗與神圣——佛道文化視野下的漢唐之間的文學(xué)》,湖南:岳麓書社,2008年版,第127頁,第138頁。
[26]賾藏主:《古尊宿語錄》,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版。
[27]參見《禪宗語錄輯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8]李小榮:《論陶淵明“無弦琴”故事的兩種類型及其寓意之異同》,福建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1年,總163期,第3期,第96頁。
[29]黃庭堅(jiān):《山谷詞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30]參見《禪偈百則》,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
[31]郝愛麗:《論禪宗對黃庭堅(jiān)詩歌的影響》,語文學(xué)刊,2011年,第11期,第14頁。
[32]李劍鋒:《元前陶淵明接受史》,山東:齊魯書社,2002年版,第324頁,第325頁。
[33]陳志平:《“箭鋒”之喻與黃庭堅(jiān)的詩學(xué)》,廣東社會(huì)科學(xué),2006年版,第2期,第150頁。
[34]周裕鍇:《夢幻與真如——蘇、黃的禪悅傾向與其詩歌意象之關(guān)系》,2003年版,第3期,第68頁,第75頁。
[35]孫海燕:《觀化與閱世:黃庭堅(jiān)在佛禪思想影響下形成的獨(dú)特觀物方式》,中國詩歌研究動(dòng)態(tài),2009年版,第1期,第28頁,第46頁。
[36]“引陶入禪”指在論陶詩時(shí)引援佛理,或在運(yùn)用陶典時(shí)引入禪宗的意涵。如“集題為《飲酒》本二十首,悠然‘望南山句,‘望字不誤,不望南山,何由知其佳耶?無故改古以伸其謬見,此宋人之病也。‘此還有真意句,‘此還當(dāng)不誤。觀注引狐死首丘說之,則還仍即上飛鳥之還也。或作中,殆非。真意與上心遠(yuǎn)相應(yīng),且既目為真意矣,豈忘言之謂乎。或者遂引陶入禪,則毋寧遠(yuǎn)援蒙吏矣。”(黃侃《文選平點(diǎn)》,中華書局2006年重輯本,頁345-346)
[37]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極多:如專論陶公與道家、道教文化者則有吳國富《陶淵明與道家文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專論其與佛教關(guān)系者則有丁永忠《陶詩佛音辯》成都:(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1997年)。李君的論文《陶淵明與佛教關(guān)系略論》(《九江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5年第4期),對陶淵明最終沒有追隨廬山慧遠(yuǎn)佛教集團(tuán)的原因作了全面的論述;鄧小軍《陶淵明與廬山佛教之關(guān)系——兼論<桃花源記并詩>》(《中國文化》,2001年第21期)詳細(xì)闡述了淵明與廬山佛教之間的思想論爭。
[38]按:提倡“句中有眼”也是山谷注重律法的表現(xiàn)。
(陳婷婷 暨南大學(xué)文學(xué)院 510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