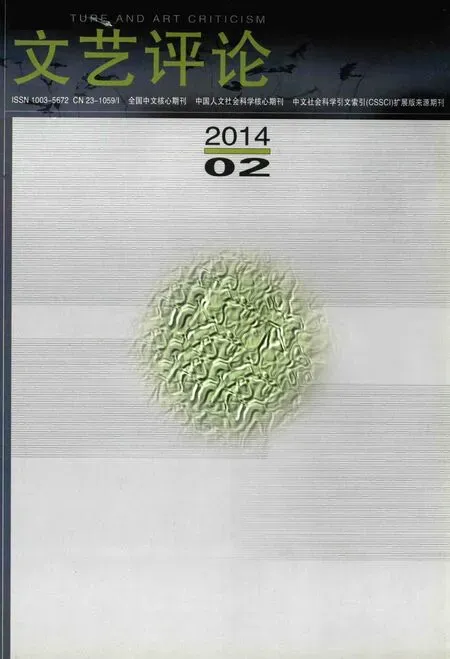癲疾與八大山人的怪誕繪畫
陳玉強(qiáng)
八大山人(1626—1705),姓朱名耷,明太祖朱元璋第17子寧獻(xiàn)王朱權(quán)的九世孫,清初文人畫大師,明亡后,出家為僧,后患癲疾。八大山人瘋癲之前,畫風(fēng)省凈恬淡;瘋癲之后,畫風(fēng)漸趨狂怪,開始出現(xiàn)怪魚、怪鳥等怪誕圖像。癲疾影響了八大山人的繪畫創(chuàng)作,對(duì)此,美國(guó)學(xué)者高居翰已有論述①,但對(duì)癲疾影響八大山人繪畫的機(jī)制,未有深入探討。本文以傳統(tǒng)中醫(yī)學(xué)及現(xiàn)代精神病癥狀學(xué)為視角,分析八大山人癲疾的癥狀,進(jìn)而探究癲疾對(duì)其繪畫的影響機(jī)制,有助于詮釋八大山人怪誕畫風(fēng)的成因。
一、八大山人癲疾的癥狀
從現(xiàn)有史料看,八大山人曾于1678年、1680年兩次癲疾發(fā)作②。八大山人第一次患癲疾的情況,裘璉作于康熙十八年(1679)夏天的《釋超則詩(shī)序》有記載:“又二三年,予再游臨川,聞雪個(gè)病顛,歸老奉新。予疑其有托而云然。”③根據(jù)汪世清的考證,裘璉再游臨川是在已未(1679)春天,這時(shí)聽聞八大山人病癲的消息。八大山人病癲必在戊午(1678)初夏以后,已未(1679)年初以前,約言之,在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④。但裘璉對(duì)八大山人病癲的傳聞,持懷疑態(tài)度,他認(rèn)為八大山人可能是佯狂;他對(duì)八大山人癲疾的癥狀也沒有描述。
1680年,八大山人在臨川第兩次癲疾發(fā)作。邵長(zhǎng)蘅《八大山人傳》記載道:
臨川令胡君亦堂聞其名,延之官舍。年余,意忽忽不自得,遂發(fā)狂疾,忽大笑、忽痛哭竟日。一夕,裂其浮屠服焚之,走還會(huì)城。獨(dú)身猖佯市肆間,常戴布帽,曳長(zhǎng)領(lǐng)袍,履穿踵決,拂袖蹁躚行,市中兒隨觀嘩笑,人莫識(shí)也。某侄某識(shí)之,留止其家。久之,疾良已。⑤
邵長(zhǎng)蘅《八大山人傳》是他在北蘭寺會(huì)晤八大山人后所寫。此次“發(fā)狂疾”是八大山人向邵長(zhǎng)蘅親述,具有較高的可信度。邵長(zhǎng)蘅詳細(xì)描述了八大山人在臨川突發(fā)癲疾的癥狀:哭笑不止,踄跔踴躍,撕燒僧服,出走遠(yuǎn)行,披長(zhǎng)領(lǐng)袍,穿破爛鞋,鼓腹高歌,蹁躚起舞。從現(xiàn)代精神病癥狀學(xué)分析,八大山人出現(xiàn)了精神病患者的行為障礙,比如衣裳倒錯(cuò)癥、儀表不整、破壞行為、沖動(dòng)行為、出走、漫游癥⑥。
傳統(tǒng)中醫(yī)學(xué)對(duì)于癲疾的研究由來已久,《黃帝內(nèi)經(jīng)》所論癲疾的證類頗多,歸其大類,約為三證:陽(yáng)盛癲狂證、陽(yáng)虛癲狂證、氣逆癲癇證。《靈樞經(jīng)·癲狂》謂癲疾“喜忘,苦怒,善恐”,“狂言、驚、善笑、好歌樂、妄行不休”;《素問·陽(yáng)明脈解篇》又謂癲疾“病甚則棄衣而走”,《素問·厥論篇》“癲疾欲走呼”,這些癥狀描述與八大山人的病情是吻合的。傳統(tǒng)中醫(yī)學(xué)認(rèn)為有火盛陽(yáng)亢病性特點(diǎn)的癲疾,就是陽(yáng)盛癲狂證。《素問·至真要大論篇》:“諸躁狂越,皆屬于火。”《古今醫(yī)統(tǒng)大全·癲狂門》:“癲狂之病,總為心火所乘,神不守舍,一言盡矣。”作為明宗室遺民,八大山人憎恨清廷,汨浡郁結(jié),火盛陽(yáng)亢,無法排解。從其癲疾癥狀看,八大山人當(dāng)是患上了陽(yáng)盛癲狂證。
八大山人的兩次癲疾,都很快治愈。然而,癲疾依然對(duì)他的生活帶來了許多不良影響。由于癲疾,八大山人出現(xiàn)了語言功能障礙。傳統(tǒng)中醫(yī)學(xué)認(rèn)為瘖啞是由于陽(yáng)氣入中所致。《素問·脈解篇》:“所謂入中為瘖者,陽(yáng)盛已衰故為瘖也。”王冰注曰:“陽(yáng)氣盛入中而薄于胞腎,則胞絡(luò)腎絡(luò)氣不通,故瘖也。胞之脈系于腎,腎之脈俠舌本,故瘖不能言也。”八大山人患陽(yáng)盛癲狂證,陽(yáng)氣入中,又致瘖啞。有學(xué)者認(rèn)為八大山人患有遺傳性啞疾,這種說法不正確。陳鼎《八大山人傳》記載八大山人:“父某,亦工書畫,名噪江右,然喑啞不能言。甲申國(guó)亡,父隨卒。人屋承父志,亦喑啞。”⑦陳鼎認(rèn)為八大山人有遺傳性啞疾,但陳鼎晚生一百余年,未見過八大山人,他所據(jù)的傳聞并不可信。1677年秋天,八大山人到進(jìn)賢介岡菊莊拜會(huì)饒宇樸,為《個(gè)山小像》求跋。饒宇樸的跋記載八大山人:“丁巳秋,攜小影重訪菊莊,語予曰:‘兄此后直以貫休、齊己目我矣!’”時(shí)年八大山人52歲,語言功能正常。但1680年八大山人第二次癲疾發(fā)作后,他的語言功能受到影響。1690年邵長(zhǎng)蘅作《八大山人傳》,記載他與八大山人“夜宿寺中,剪燭談,山人癢不自禁,輒作手語勢(shì),已乃索筆書幾上相酬答”⑧,此時(shí)八大山人已有明顯的語言功能障礙,不得不借助手語與筆書。
二、從癲疾到佯狂
八大山人究竟是患癲疾還是佯狂,已有的研究各執(zhí)一詞⑨。從現(xiàn)有史料看,八大山人1678年那次癲疾存疑,但1680年患癲疾,則確定無疑。疾愈后,八大山人為避禍又裝瘋佯狂。龍科寶《八大山人畫記》記載八大山人“既而蓄辮發(fā),往往憤世佯狂”⑩,蓄辮發(fā)還俗是八大山人第二次癲疾痊愈之后的事情;而龍科寶與八大山人有過交往,他的說法有較高的可信度。這表明八大山人疾愈后,依然佯狂。
所謂佯狂就是裝瘋。1682年,八大山人《春甕》詩(shī):“若曰甕頭春,甕頭春未見。有客豫章門,佯狂語飛燕。”?八大山人遇見不愿意交談的人,就裝瘋佯狂與天空中飛行的燕子說話。八大山人之所以佯狂,與他的自身處境有關(guān)系,他是明朝宗室遺民,有亡國(guó)喪家之痛,不滿清廷,又無力反抗,只能佯狂避世。1682年,八大山人《畢甕》詩(shī):“深房有高甕,把酌無閑時(shí)。焉得無閑時(shí),翻令吏部疑。”?八大山人之所以喜歡醉酒,是因?yàn)樗虑逍褧r(shí)遭受官府懷疑。可見,八大山人佯狂避世是為了避免清廷的懷疑與迫害。正如邵長(zhǎng)蘅《八大山人傳》所言:“山人胸次汨浡郁結(jié),別有不能自解之故,如巨石窒泉,如濕絮之遏火,無可如何,乃忽狂忽喑,隱約玩世,而或者目之曰狂士,曰高人,淺之乎知山人也。”?
八大山人佯狂有不得已的苦衷,并非樂事,但佯狂必然會(huì)使他回憶起曾經(jīng)病癲時(shí)的精神狀態(tài)。如果八大山人不患癲疾,他縱然佯狂也無法體驗(yàn)病癲時(shí)的精神狀態(tài);如果八大山人患癲疾一直不愈,他也無法進(jìn)行繪畫創(chuàng)作。由癲疾到佯狂,令八大山人在較為理性狀態(tài)下體驗(yàn)曾經(jīng)的瘋癲狀態(tài),對(duì)他的繪畫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八大山人的題識(shí)、鈐印映證了瘋癲體驗(yàn)對(duì)他繪畫創(chuàng)作的影響。1677年,八大山人《梅花冊(cè)》中出現(xiàn)了“掣顛”印章,在《個(gè)山小像》戊午(1678年)中秋后二日自題下也鈐有“掣顛”的白文長(zhǎng)方形印。從語源上看,“掣顛”是禪語。《五燈會(huì)元》曰:“師掣手便去。臨濟(jì)一日與河陽(yáng)木塔長(zhǎng)老同在僧堂內(nèi)坐,正說師每日在街市掣風(fēng)掣顛。”?“掣”解為“抽”,所謂“師掣手便去”,即師抽手便去。可知,八大山人所謂“掣顛”,就是抽顛,表明他的畫作與癲疾存在關(guān)聯(lián)。“掣顛”并非制止瘋癲,而是駕馭瘋癲為藝術(shù)創(chuàng)作服務(wù)。1701年,八大山人題石濤《蘭花》曰:“苦瓜子掣風(fēng)掣顛,一至于此哉!”?所謂“掣風(fēng)掣顛”意謂抽風(fēng)抽顛,是稱贊石濤畫作的狂怪風(fēng)格。“掣顛”不無禪宗的影響,也與八大山人的癲疾有聯(lián)系,他正是借助瘋癲體驗(yàn),對(duì)繪畫創(chuàng)作進(jìn)行了徹底的變革。
八大山人經(jīng)常以酒為引,沉入瘋癲體驗(yàn)中,然后繪畫。龍科寶《八大山人畫記》親眼看到八大山人痛飲后繪畫,“旁有客乘其余興,以箋索之,立揮與斗啄一雙雞,又漸狂矣”?。邵長(zhǎng)蘅《八大山人傳》提到八大山人喜飲酒后作畫:“飲酒不能盡二升,然喜飲。貧士或市人屠沽邀山人飲,輒往,往飲輒醉,醉后墨沈淋漓,亦不甚愛惜。”?陳鼎《八大山人傳》評(píng)曰:“山人果顛也乎哉,何其筆墨雄豪也!余嘗閱山人詩(shī)畫,大有唐宋人氣魄。至于書法,則胎骨于晉魏矣。問其鄉(xiāng)人,皆曰得之醉后。嗚呼!其醉可及也,其顛不可及也。”?借助于瘋癲體驗(yàn),八大山人創(chuàng)作了一系列意味深遠(yuǎn)的怪誕繪畫,在清代文人畫中獨(dú)樹一幟。
三、瘋癲體驗(yàn)對(duì)八大山人繪畫的影響
瘋癲是人類極端、邊界的精神狀態(tài),瘋癲之中不可能進(jìn)行真正的繪畫創(chuàng)作;瘋癲體驗(yàn)則是對(duì)曾經(jīng)瘋癲經(jīng)歷的回憶與假想,卻有助于激發(fā)畫家的想象力。福柯認(rèn)為瘋癲體驗(yàn)為藝術(shù)創(chuàng)作提供了最好的想象?,杰米森描述了瘋癲體驗(yàn)帶來的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八大山人經(jīng)歷瘋癲后,創(chuàng)作了大量風(fēng)格怪誕的作品,這并非孤立的文藝現(xiàn)象。1888年,荷蘭畫家凡高(1853—1890)在瘋癲中割下了右耳,此后他的畫作《星夜》(1889)、《絲柏》(1889)、《絲柏與群星》(1890)、《群鴉亂飛的麥田》(1890)以扭曲旋轉(zhuǎn)的星云、夸大變異的星光、橙黃如桔的月亮、墨綠如焰的柏樹,構(gòu)成了迥異于現(xiàn)實(shí)的幻象。凡高是在發(fā)病間隙作畫,八大山人則是病愈后佯狂作畫,瘋癲體驗(yàn)對(duì)于他們的藝術(shù)想象有著重要的意義。
精神病癥狀學(xué)的研究表明,瘋癲者描述外物不循常理,他們對(duì)物體的幻想在數(shù)量、大小、形狀、空間及時(shí)間關(guān)系上會(huì)發(fā)生改變?。八大山人在佯狂中形成瘋癲體驗(yàn),激發(fā)了想象力,創(chuàng)造出一系列改變形狀、大小及空間關(guān)系而又獨(dú)具審美意蘊(yùn)的藝術(shù)形象。
第一,八大山人筆下的動(dòng)物形象產(chǎn)生了形體異化。1684年《個(gè)山雜畫冊(cè)》中的兔?,形狀怪誕,兔身似驢似馬又似牛,兔眼則像熊貓眼,除了兩只聳立的耳朵還表明兔子的屬性外,兔身無一處似兔。這種“兔非其兔”呈現(xiàn)出一種異化感,似乎是八大山人“人非其人”、自身異化的一種象征。作為明宗室遺民,八大山人的身份不容于清廷,他是一個(gè)異類。異化主題在八大山人的畫作中頻頻出現(xiàn)。《魚軸》中,魚身似山,宛如石化,右上角有題名“稚震”的跋:“此等筆墨,近世罕有,人莫能識(shí),不意在徐青藤后復(fù)有一徐先生在也。”?徐渭也曾患有癲疾,且畫風(fēng)狂怪,稚震評(píng)八大山人乃隔世之徐渭,正著眼于此。然而細(xì)加品味,兩人畫風(fēng)又有區(qū)別:徐渭畫作狂放恣肆,迸發(fā)出難以扼制的激情;八大山人則背負(fù)了更多的憤世嫉俗之情和國(guó)破家亡之痛,他的畫作更為安靜、內(nèi)斂,多以變形夸張的手法,在花木鳥獸身上融進(jìn)主觀的象征性蘊(yùn)含。比如八大山人對(duì)動(dòng)物形象的石化表現(xiàn),頗為多見。《鳥石圖頁(yè)》?中,立于巖石上的鳥與巖石融為一體,而巖石又似展翅之鳥,鳥與巖石形成了有意味的比照。《貓石圖軸》?中,兩只貓分臥于一高一低的石頭上,貓身與石頭融為一體,只剩下匍匐于石上的貓首依稀可見。這種石化不是天人合一式的靜穆自在,而是強(qiáng)迫性的異化,透露出荒誕與無奈。
鄭板橋《靳秋田索畫》曾經(jīng)比較過八大山人與石濤的畫風(fēng):“然八大名滿天下,石濤名不出吾揚(yáng)州,何哉?八大純用減筆,而石濤微茸耳。”?八大山人名聲勝過石濤,因?yàn)榍罢呤褂谩皽p筆”,而后者“微茸”。所謂“減筆”是對(duì)事物自然面貌的有意刪減,形成“有意味的形式”。八大山人1693年《書畫冊(cè)》中有一幅竹石圖?,畫中只有幾片無枝的竹葉,石頭一片墨色,不可辨識(shí),款題“涉事”。無枝的竹葉似乎隱喻八大山人失國(guó)喪家的無根心態(tài),黑不可辨的石頭似乎象征烏云般的政治環(huán)境。《鳥石圖頁(yè)》?中,一條魚碩大無比,瞪眼向人,最為怪異的是魚鰭、魚尾用墨筆暈成,一片模糊。乍一看,這條魚好像從尾部開始燃燒,化成一團(tuán)墨汁消融于水中。這條魚的殘敗,體現(xiàn)出八大山人繪畫的異化主題,因?yàn)轸~之不能容于水,好比八大山人不能容于清廷。
第二,八大山人畫作改變了事物的大小關(guān)系。他擅長(zhǎng)利用不恰當(dāng)?shù)谋壤齺黼[喻現(xiàn)實(shí)的不合理。1695年《魚鳥圖軸》?中,巖上一只瞪眼鳥,巖下兩條一大一小的瞪眼魚,大魚占到整幅畫寬,與巖石不成比例,似乎象征著世界的荒誕與不協(xié)調(diào)。1700年《椿鹿圖軸》?中,巖石比鹿的身體還要小,鹿立于其上,兩眼瞪大,不知所措,似乎隱喻著八大山人明宗室遺民身份難以立足的尷尬。1694年《書畫冊(cè)》中有一幅竹石圖?,危巖之下的幾棵竹子矮小如同小草,壓彎身姿,似乎象征清廷的壓迫與八大山人的弱勢(shì)。八大山人畫水仙?,宛如巨樹,碩大無比,占據(jù)整幅畫面,高大遠(yuǎn)遠(yuǎn)超過其后的山巒;畫“靈芝”?孤零零地立于畫中,巨大無比;畫“玉蘭”?也占滿整幅畫面。水仙、靈芝、玉蘭這些植物在中國(guó)古代象征著士人傲岸的精神,八大山人放大比例的描繪,是他主體精神高揚(yáng)的象征和狂傲性格的隱喻。
第三,八大山人畫作改變了事物的空間關(guān)系。1689年《竹荷魚詩(shī)畫冊(cè)》,四條魚在空中飛行,題識(shí)曰:“從來?yè)Q酒金魚子,戶牖平分是一端。畫水可憐三五片,潯陽(yáng)干過兩重山。”?畫中連“三五片”水都沒有,魚飛行空中,極為荒誕,有著極深的寓意。國(guó)破家亡的八大山人正如同這條離水之魚,被懸置于空中。1689年《瓜月圖軸》,本在天上的月亮卻被放置在地上與西瓜并排,題識(shí):“昭光餅子一面,月圓西瓜上時(shí),個(gè)個(gè)指月餅子,驢年瓜熟為期。”?將月亮喻為餅子,與西瓜并列,這種空間關(guān)系十分怪異。
第四,八大山人畫作存在不恰當(dāng)?shù)氖挛锝M合。“鷹蟹圖”?中,一只鷹立于巖上俯視巖下的一只蟹,蟹則張螯向鷹,這種對(duì)抗與搭配荒誕無比,似乎象征著八大山人與環(huán)境的不協(xié)調(diào)與不妥協(xié)。1694年《晚安冊(cè)》中的瓶花圖?,瓶身滿是裂紋,如同僧人的百衲衣,瓶子尚不知存在多久,插于瓶中的枝葉更是前景不妙,正所謂“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上述畫作對(duì)事物常規(guī)形狀、大小、空間關(guān)系等的改變,體現(xiàn)出八大山人獨(dú)特的藝術(shù)想象力,而藝術(shù)想象力的激發(fā)又與他的瘋癲體驗(yàn)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可以說,沒有佯狂而致的瘋癲體驗(yàn)就不會(huì)產(chǎn)生八大山人晚年的怪誕繪畫。
八大山人疾愈后的畫作雖然狂怪,但充滿冷靜與隱喻。他將瘋癲體驗(yàn)融入繪畫圖像中,圖像的意蘊(yùn)則是他的理性體現(xiàn)。瘋癲體驗(yàn)對(duì)于時(shí)空、形態(tài)的改變有助于八大山人在繪畫中展現(xiàn)他一貫的異化主題。1693年魚鳥圖卷中,兩只鳥立于石上,一條魚則在天空游弋。畫中有八大山人的三段題識(shí),左下角的題識(shí)為:“東海之魚善化,其一曰黃雀,秋月為雀,冬化入海為魚;其一曰青鳩,夏化為鳩,余月復(fù)入海為魚。凡化魚之雀皆以肫,以此證知漆園吏之所謂鯤化為鵬。”?八大山人認(rèn)為魚、鳥互相異化,夏天魚化為青鳩,秋天魚化為黃雀,其他月份鳥又入海為魚。另外兩段題識(shí),一段是說沈約因?yàn)椴W(xué)而得“隱囊”的稱呼,八大山人“品意”而作此畫;另一段題識(shí)則解釋了八大山人畫作中所題“涉事”二字的由來。王二畫石、大戴畫牛求形似,而八大山人的畫只曰“涉事”,強(qiáng)調(diào)圖像的指涉性和象征性。這三段題識(shí)證明了八大山人畫作中的圖像大都是有所指涉、有所象征的,這也是我們解讀八大山人畫作意蘊(yùn)的邏輯起點(diǎn)。正因?yàn)榘舜笊饺苏J(rèn)為魚和鳥存在互相轉(zhuǎn)化的情況,所以他的魚鳥畫就別具意味。八大山人的魚鳥圖大都是巖上鳥與巖下魚的對(duì)望,不同時(shí)空、不同形態(tài)的魚鳥共居一處,互相瞪視,宛如前生與今世的對(duì)望,荒誕而有哲理。
結(jié)語
八大山人罹患癲疾,痊愈后,為避禍又裝瘋佯狂。佯狂是對(duì)瘋癲的戲劇性模擬,導(dǎo)致對(duì)事物的正常形狀、大小及時(shí)空關(guān)系的扭曲性體驗(yàn),這對(duì)于繪畫結(jié)構(gòu)外物的方式有著積極意義。八大山人筆下怪誕的動(dòng)植物改變了其自然屬性,本質(zhì)上是一種幻象,是他的觀念載體、本質(zhì)體現(xiàn)及靈魂隱喻,蘊(yùn)含著他對(duì)意識(shí)形態(tài)的指控。福柯說:“藝術(shù)作品與瘋癲共同誕生和變成現(xiàn)實(shí)的時(shí)刻,也就是世界開始發(fā)現(xiàn)自己受到那個(gè)藝術(shù)作品的指責(zé),并對(duì)那個(gè)作品的性質(zhì)負(fù)有責(zé)任的時(shí)候。”?八大山人的怪誕繪畫可以看作是他對(duì)清廷的指控,是“一種似乎被世界所湮沒的、揭示世界的荒誕的、只能用病態(tài)來表現(xiàn)自己的作品”?。明朝的覆滅及清廷對(duì)明宗室遺民的迫害,對(duì)八大山人的內(nèi)心產(chǎn)生了難以磨滅的消極影響,其怪誕繪畫的圖像喻義、結(jié)構(gòu)方式有著反意識(shí)形態(tài)的意義,故而不能把八大山人畫作中的怪誕圖像視為精神病的涂鴉。
八大山人經(jīng)歷瘋癲后,滿腔苦澀、悲憤與孤寂,在藝術(shù)領(lǐng)域里得到了釋放,瘋癲體驗(yàn)與意識(shí)形態(tài)指控融為一體,形成了八大山人狂放不羈、冷縱怪異的畫風(fēng),從而將清代文人畫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