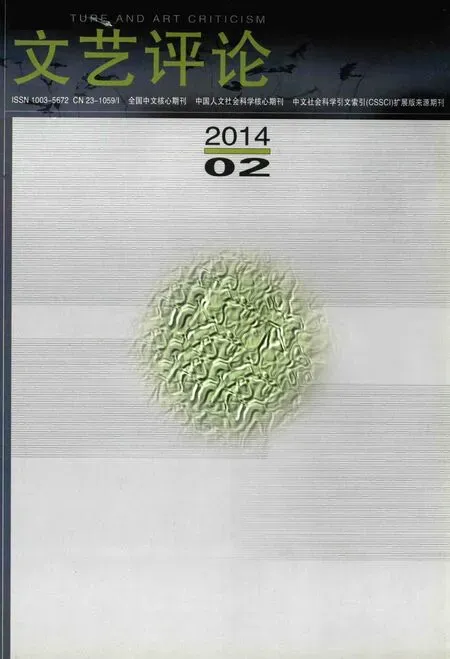論董仲舒與漢代以《詩》決獄
張華林 宦書亮
董仲舒首次運用的“以《詩》決獄”是對其“以《詩》為法”《詩》學觀的落實,而其“以《詩》為法”的《詩》學觀則是在其《春秋》學基礎上提出來的。在董仲舒的影響下,“以《詩》決獄”被漢代學者反復使用,從而成為漢代極具特色的用《詩》方式之一。
但學界對“以《詩》決獄”并未給予應有的重視。目前所能見到的相關成果,只有劉立志的《漢人引詩決獄芻議》①一文,該文主要從秦漢時期儒法合流的角度對此進行了探討,而對于董仲舒之“以《詩》決獄”觀生成的內在經學因素與流布情況卻未作全面論述。
本文主要從經學角度討論董仲舒“以《詩》決獄”這一用《詩》方式的生成原因和漢人對此用《詩》方式的延續情況。
一、以《春秋》為法
董仲舒是《春秋》學大師。他認為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為后王確立王道大法。其言曰:“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萬事,見素王之文焉。”“《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為左右,以成文采。……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前者言孔子以《春秋》來體現其“素王”之文法;后者言《春秋》記載了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其中布滿了孔子的王法。
《春秋》既是孔子受命所作的王道大法,故董仲舒提出以《春秋》為法的觀點:“孔子……是非二百四十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宋伯姬疑禮而死于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春秋》賢而舉之,以為天下法。”前一條材料說孔子著《春秋》“以為天下儀表”,也即是以《春秋》為天下法;后一條材料則是對此觀點的細化:他認為《春秋》乃以伯姬和齊桓公的行為為天下之法則,以為天下人所取法。兩條材料所表達的皆是以《春秋》為法則的觀點。
不但如此,董仲舒還將“以《春秋》為法”的精神貫徹于現實生活中,其具有代表性的行為便是他對各種案件的審理也依據《春秋》“大義”來作出判決,此即“《春秋》決獄”。據《漢書·藝文志》,董仲舒著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后漢書·應劭列傳》則言:“故膠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這《春秋決獄》可能就是《漢志》所說的《公羊董仲舒治獄》,惜其多已亡佚,今僅存數條佚文。茲列一條以見其例。據《太平御覽》卷六載董仲舒《春秋決獄》佚文曰:
甲父乙與丙爭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也,當梟首。"議曰:"臣愚以父子,至親也,聞其斗,莫不有怵悵之心。扶伏而救之,非所以欲詬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於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也,不當坐。
在此案中,董仲舒以為父子至親,子甲執杖救父乙而導致誤傷乙,但其動機非傷父,乃救父。故據“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的《春秋》“大義”和《春秋》赦免許世子止因進藥其父而誤致“弒君”的行為,認為也應赦免甲之罪。可見董仲舒“以《春秋》決獄”即是依據《春秋》或“大義”來對相關案件作出斷決,也即“以《春秋》為法”。
董仲舒不僅要求以《春秋》為法,他還進而要求以六藝為法。他在元光元年的對策中還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董仲舒認為六藝之科即是孔子之術,而“六藝”獨尊,即可實現“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此即認為“六藝”與“統紀”、“法度”有關,乃民之所宜效法者。這便是認為六藝皆可為天下法。而《詩》是“六藝”之一,故亦可法。
正是在這種經學背景下,董仲舒提出了“以《詩》為天下法”的觀點,并有了“以《詩》決獄”的具體實踐。
二、“以《詩》為法”與以《詩》決獄
(一)董仲舒“以《詩》為法”的提出
董仲舒在其《春秋》學的影響下,在《春秋繁露·祭義篇》中首次提出了“以《詩》為法”的觀點。其文云:
《詩》曰:“嗟爾君子,毋恒安息。靜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為天下法矣,何謂不法哉?其辭直而重,有再嘆之,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尚不省,何其忘哉!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
董仲舒首先認為君子應該以真誠而恭敬的態度去對待祭祀;然后引用孔子之言進一步說明孔圣人也是如此;而鬼神是公正無私的,那些公而無私的人是會受到鬼神的福佑。他認為《小雅·小明》之“嗟爾君子,毋恒安息。靜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就體現了這點。此言君子不應長久的貪圖安逸,當恭謹地對待自己的職事,好與正直者交往,這樣就會得到神靈的福佑。然后董仲舒進一步闡述道:“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這就將詩義由君子交往的具體的某個“正直”之人延伸為更具普遍意義的“正直”的處世態度,而且說這就是人們應該遵守的法則。在此基礎上,董仲舒進而提出了“以《詩》為天下法”《詩》學觀。這里可以從兩個層次來理解:一是就其所引詩句而言,認為此詩所體現的正直的處世態度,不僅應該是君子的法則,而且應該是天下人的法則。另一層面則是說,不僅當以此詩為天下之法則,而且應該是以《詩三百》為天下之法則。
同時他也表達了對人們不以《詩》為法的疑惑與不滿。從這種疑惑與不滿的論述中,我們可以進一步確認“以《詩》為天下法”是董仲舒的創見。然后董仲舒從《詩》的語言特征和表達形式方面肯定了《詩》中必有大義存焉,是值得天下效法的。
另,“以《詩》為天下法”之“下”字,據有些版本作“子”。②由于此字直接關系著對董仲舒《詩經》學的理解,所以不可不辨。本文認為當作“下”,而不是“子”。考辯如下:
該段文字主要討論的是君子的言行,而《春秋繁露》中的“君子”一詞,主要指那些樂于“循理”而行的有德之士③,它與“賢”近,又曰“賢人君子”,其為政,則可“三卿之位”;它是一個集合名詞,具有涵涉社會各個階層的成員的可能性,但《春秋繁露》中絕無以“君子”指“天子”者。而《小明》一詩,《毛詩序》說它講的是“大夫悔仕于亂世也”,三家《詩》無異議。其中“嗟爾君子”一句,鄭玄《毛詩箋》云:“謂其友未仕者也。”即此“君子”為“未仕者”,乃大夫之友,皆與“天子”無涉。且“天子”二字也無法涵涉前面君子、孔子、圣人等內容,這在行文上無法與前面的內容形成邏輯關系。在接下來對“以《詩》為天下法”的重要性的闡述里,董仲舒云:“有再嘆之,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尚不省,何其忘哉。”如果是就“天子”言,這里恐怕不當稱“人”。
此外,《春秋繁露》中還有與“為天下法”相同或類似句子。如《楚莊王》篇之“宋伯姬恐不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春秋》賢而舉之,以為天下法”;又“孔子……是非二百四十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為天下儀表”即是為“天下法”。此外,《尚書緯》也有類似說法。如“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④,“可以為世法”即“為天下法”。而遍檢董仲舒以及《史記》、《漢書》等漢人著作,無“為天子法”句式。所以此句當作“以《詩》為天下法”,而不當作“以《詩》為天子法”;“子”乃“下”之訛。故有的學者將此說成是“以《詩》為天子法”是不準確的。
由此可知,董仲舒在中國《詩》學史上首次提出了“以《詩》為天下法”的觀點(本文簡稱為“以《詩》為法”),要求將《詩經》作為天下人言行的法則、典范。此一《詩》學觀點的提出,將《詩》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天下法”。
(二)董仲舒以《詩》決獄
董仲舒不僅提出了“以《詩》為法”這一觀點,還有進一步的具體運用,如“以《詩》決獄”。這見載于董仲舒的《春秋決事》,其文曰:
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之以為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春秋》之義,父為子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⑤
在此案件中,甲乙關系是關鍵點。乙乃棄兒,非甲親子,于是甲乙兩者間的父子關系在法理上便有可商酌之處。對此問題的處理,董仲舒依據《詩經·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負之”一句,認為螟蛉之子為蜾蠃所養而為蜾蠃之子;然后據此斷定作為他人棄子的乙為甲所養大成人,則自然為甲之子。如此,甲乙父子關系因《詩》而得以明確。甲之隱匿義子的行為動機便有了經典的依據,從而具有了合法性。再依據《春秋》“父為子隱”的原則,董仲舒肯定了甲隱匿乙的行為之合法性。
從這一處理案件的過程可以看出,董仲舒是以《詩經》作為認定甲乙父子關系的依據與法則,這便是“以《詩》為法”,即將《詩》作為處理現實事務的法則與典范。這與后面緊接著以《春秋》為法,作出斷案是同樣用法。而“詔:不當坐”一句,表明漢武帝對董仲舒這種以《詩》為法、用《詩經》來作為處理現實政治事務的法則的肯定。于此可以看到,這種以《詩經》為法則,甚至將其當作法律來處理現實政治事務的情況,與此前的用《詩》方式有明顯的不同,其意義不可忽視。而且如前所言,《春秋決獄》載有二百三十二事,可以想見董仲舒以《詩》決獄或許不止一次。而且這些內容受到了漢武帝等朝野的肯定而被作為治獄之典范來對待的。這必將對“以《詩》決獄”的用《詩》方式之傳播產生影響,此后陸續出現的以《詩》決獄現象應該就是源于此。
三、漢人對董仲舒以《詩》決獄的延續
(一)漢代學者對“以《詩》為法”的接受
董仲舒提出的以《詩》為法的觀點得到了司馬遷等兩漢學者的認可。
如董仲舒弟子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說:“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于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于后世。”司馬遷認為六藝皆是孔子為后世所制作的“儀法”、“統紀”,也即王道大法,所以可以六藝為天下法。此即董仲舒所謂的以六藝為法。
具體就《詩》之可“法”性而言,司馬遷有更明晰的論述。其文曰:
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以備王道,成六藝。
此“王道”,即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所說的“《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中的“王法”,也即前面所說的“儀法”、王道大法。此言孔子之時詩有三千多篇,孔子選取相關的作品,去除其重復,按“禮義”標準選擇相關作品,然后依據歷史先后順序進行排列,從而使《詩》具有了王道大法的功能。此即以《詩》為法。
對于漢成帝常常召見言祭祀與方術者,延續了董仲舒災異之學的谷永上疏成帝說這些人是“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此即以“五經”為“法”;《漢書》揚雄說《詩》乃“法度所存”,并說“詩人之賦麗以則”,“詩人之賦”即《詩》中作品,“則”,法也,此言《詩》可法則,與其所說的《詩》乃“法度所存”同義。
受董仲舒思想影響的讖緯,也延續了他“以《詩》為法”、以六藝為法的觀點。如《春秋演孔圖》說孔子“作法五經,運之天地,稽之圖像,質于三王,施之四海”,此言包括《詩》在內的“五經”乃孔子為天下所作之“法”。還有鄭玄亦反復強調“以《詩》為法”。他在《詩譜序》中言及詩的功能時說:“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剌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即言《詩》具有“法”“戒”之功效。鄭玄釋“雅”曰:“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為后世法。”此言詩人作《雅》詩的目的在于為后世法。等等。
由上論述可見,自董仲舒“以《詩》為法”的《詩》學觀提出后,在其“儒宗”地位的影響下,不論是《魯詩》學者(司馬遷、劉向)、《齊詩》學者(班彪)、《毛詩》兼《韓詩》學者(鄭玄),以及無法確知《詩》派對揚雄、讖緯《詩》學等等皆認可并積極提倡董仲舒的“以《詩》為法”。因此可以說“以《詩》為法”已成為漢人在《詩經》學上的一種共識。
(二)漢人對“以《詩》決獄”的運用
隨著董仲舒“以《詩》為法”的被廣泛接受,他提出的“以《詩》決獄”也被漢人廣泛的接受與運用。
如劉向稱《詩》以斷陳湯、甘延壽之獄。據《漢書》卷七十《陳湯傳》載,陳湯、甘延壽矯制發兵斬單于,而中書令石顯、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等人對陳湯、甘延壽立大功不賞而反欲因其矯制而治罪,元帝無主見,故久議不決。對此,劉向上疏稱《小雅·采芑》詩文,說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而今陳湯、甘延壽之功,雖周宣之方叔、吉甫也無法與之相比;又稱《小雅·六月》詩文說吉甫之歸,周厚賜之;而今陳湯、甘延壽之功遠超方叔、吉甫,不但不如吉甫受祉之報,反而久挫于刀筆之前。因此應立即解除其罪,赦免其過。結果是元帝納劉向之議,赦免了陳、甘二人,并議封賞之事。
由上述可見,劉向在議陳、甘二人功過之時,主要依據《采芑》、《六月》二詩中關于方叔、吉甫的功勞與周宣王對二人的獎勵行為,提出陳、甘二人也應受到方叔、吉甫的待遇,元帝則接受了劉向的論斷。這便是“以《詩》為法”之據《詩》斷獄。
據《漢書·文三王傳》載:
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傅致難明之事……污蔑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于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圣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于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為宗室刷污亂之恥,甚得治親之誼。”
有司奏請誅梁王立,其罪在于梁王與其姑園子有奸情。對此,谷永稱《大雅·行葦》之詩文以辯之。而《毛詩序》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即此詩乃言和睦宗族之事。對于所引詩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毛傳》曰:“戚戚,內相親也。肆,陳也。”鄭《箋》云:“莫,無也。具猶俱也。爾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
《毛傳》《鄭箋》所言與《序》一致,即此詩乃言王與族人相親相愛、和睦共處之情形。而谷永稱此詩句,也在于明確并強調成帝與梁王間乃族親、公族關系。將梁王之事與同宗的天子關聯起來,然后在“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圣德之風化”的基礎上,論定梁王立之無罪。從而達到為梁王開脫罪責,免于治罪的目的。這種先稱《詩》文以明確梁王與天子的宗族關系,再以《春秋》為親者隱諱的經義斷之無罪。其方式與董仲舒以《詩》治獄如出一轍。
此外,《漢書》卷八十三《朱博傳》載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認為傅晏“干亂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職為亂階,宜與博、玄同罪,罪皆不道”。其“職為亂階”出于《小雅·巧言》,鄭玄《箋》云:“此人主為亂作階,言亂由之來也。”龔勝等當取其“為亂作階”義,言傅晏乃亂之所由,屬漢律之“造意”、“首惡”之罪,于法當誅,故言“罪皆不道”。此乃直接稱《詩》定其罪。
由以上對漢代以《詩》斷獄案例的分析,可以得到如下認識:
第一,從《詩經》所起作用的方式看,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以《詩》文為標準來判定某種定罪是否成立,如劉向、昌邑王條等;二是依據《詩經》來為罪行的判決建立某種條件,使這種條件成為斷罪之依據,如董仲舒和谷永條。
第二,所涉案件,包括天子之廢立事件(昌邑王),涉及王公大臣之生死事件(梁王、匡衡、傅晏等等),以及一般平民之案件等,皆與以《詩》決獄有關。由此可見出其在漢代的使用層面極為廣泛。
第三,漢代以《詩》決獄現存材料,主要集中在西漢武、宣、元、成、哀時期,東漢此類用《詩》方式較少。
第四,“以《詩》決獄”一方面促進《詩經》在整個社會階層中傳播,另一方面則促進《詩經》的法典化,使《詩》由經典向法典的轉化,進而使《詩》兼具經典與法典的特性與功能。這極大地提高了《詩經》在漢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