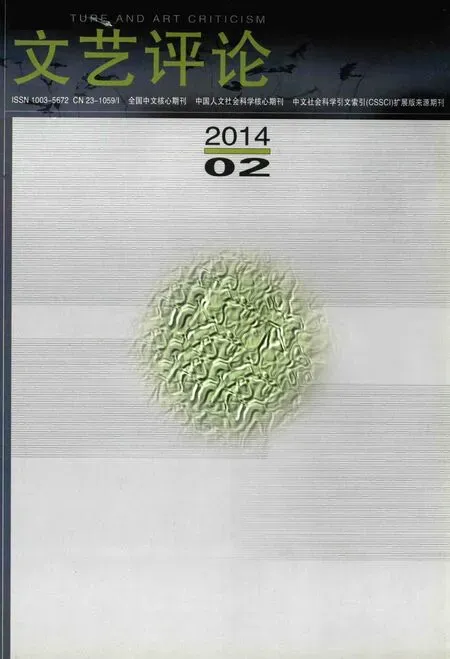從脫離到返本:新詩與古典詩歌格律
李 丹
對新詩格律問題的探討是一個老話題,研究成果也相對豐富。多數研究從新詩自身的角度進行,有探討其發展演變歷程的①,有專門研究某一時期格律理論的②,有針對某一派別的格律理論進行梳理的③,也有研究某位詩論家的格律理論的④,還有對格律和自由兩種詩體進行比較的⑤,此外,也有談及傳統文化與新詩格律問題⑥以及繼承傳統詩律以建構新詩格律的⑦,但未見研究古典詩詞格律與新詩格律之間繼承與演變關系的;針對這一狀況,本文嘗試進行探討。
一
永明聲律論的出現,標志著古代漢語藝術運用規則的成立,它既有總原則,力求文字聲音富于變化,以構成音調的錯綜和諧;在具體運用中,又有四聲八病的規定。永明聲律論對發掘漢語詩歌的音韻美產生重要的促進作用,到唐代已演變為一套完備的格律規則。近體詩可以作為中國古典詩詞格律的典型,這里將其分為聲音與體式兩個方面來說明,其中聲音方面的規則有:一是葉韻。要求一韻到底,除首句外,偶句末字須押同一韻部的韻。押韻是構成詩歌音樂性的關鍵環節,在詩行固定位置出現相同的韻腳,可以加強節奏,使詩歌在聲音層面形成一個整體。二是平仄。這是詩句詞語聲調安排的規則,將四聲二元化,把平上去入四聲分為平聲和仄聲;詩中多以兩字為一組,其平仄或交錯或相對或相粘,一句之內平仄相間,兩句之間平仄相對,兩聯之間平仄相粘,末字除外。律詩的平仄及其變化的規則還有避免孤平、三平調或三仄腳,首句末字可平可仄可入韻可不入韻即“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等。“在格律詩中,重要的是二、四、六等偶字亦即音組的落點上必須相同,只要這些字的聲調一致,便是粘合了。所謂粘,其功用在于使全詩聯與聯之間緊密聯結在一起,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兩聯之間緊相嚙合,整體感得到強化。”“這樣一種規則,表面上看是相對立的,但實際上卻是利用平仄二元對立的性質,既使上下兩句間因差異各具不同的音調特性,又通過二者的中和與更高層次上的類似獲得一種整體感。可見,充分利用平仄二元之間既相異又互補的特點是格律詩音樂性的奧妙所在。”⑧正由于其排列的精妙,故自唐代定型后,持續了千年之久。
體式方面的要求表現在,一是對仗。以律詩為例,全詩由八句組成,每兩句為一聯,共四聯,依次稱為首聯、頷聯、頸聯、尾聯,每一聯中,上句為出句,下句為對句,一般要求中間二聯對仗:出句與對句同一位置所用字詞,其詞性、色彩、方位等要同類相應,而意義則要相反相成。“就唐詩中的對仗來說,它大致有幾個規則:一是詞性要相同或相近,名詞對名詞,形容詞對形容詞;二是上下兩句的句法結構要相同或相近;三是偶對字詞的平仄要相對——平仄的對立不僅不會造成偶對的不和諧,反而突出了各自或高或低或長或短的聲音特性,由此獲得一種超越對立的統一。”⑨較常見的對仗有流水對、借對、交錯對、當句對等,從分類的精細程度就可看出近體詩的對仗要求極為工巧。作為一種并置的方式,對仗在詩句語言線性進展的流程中設置出一塊或并列、或對反的停留空間,以強化時間流動中的空間排列,達到拓展內容的目的。在杜甫、李商隱等大家的筆下,對仗不僅僅是體式方面的外在要求,而是為貌似簡短的律詩辟出一方容納開闊境界的領域。“進一步來看,詩中的對仗還有一種特殊的功用,那就是擴展、改變作者的思維方向,增加詩歌的意義內涵。……表面看只是一種技巧,實際上卻是由于對仗的原因,而使得詩人在寫作時不由自主地、必然地向與之相反的一個方向和物體靠攏,由此改變了人的思維習慣或思維方向。……由于整個思維方向的改變,就大大擴展了空間場景,增加了詩句的情感張力,并在未寫的中間地帶留給讀者廣闊的想象余地。”⑩二是篇制。這是關于詩篇字數的規定,分為絕句、律詩、排律,絕句為四句二十字或二十八字,律詩為八句四十字或五十六字,排律可更長。將絕句、律詩的體量限制在相對狹小的范圍內,有利于激發詩人選用最恰切的字詞和飽含情思的語句,以集中地傳情達意。近體詩的五、七言,是依音節而定的,一個字構成一個音節;詩句停頓點也是固定的。以此構成詩篇體式層面的節奏。
概括地說,近體詩的格律規則對于發揮古代漢語的聲音與意義功能達到相當高的程度。有學者認為,“從整體來看,格律詩的最大特點在于對立統一。對立,指聲調之平仄、詩句之對偶,在兩句之間都是兩兩相反相對的;統一,既指由這種對立形成的一種互補結構,也指聯與聯之間的緊相粘合與全詩的整體和諧。這是由對立形成的統一,也是整體統一中的對立,對立與統一,便是格律詩形成的基本法則。”?近體詩格律規則有利于促成詩歌這一文體自身特性的突出,并造就了漢語詩歌的巔峰,魯迅就曾說,“我以為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這當然是就近體詩范圍而言的。
二
直到20世紀初,中國詩歌仍在沿用近體詩規則,實際上,這種古典用語系統與日常口語之間已出現頗大的距離,難以準確地表達隨著社會生活的變化而出現的新事物、新現象、新感受,可以說,謹嚴的古典格律束縛了新的社會文化條件下的創造力,使詩歌創作成為刻板的古典形式應用。此時,赴域外的學習經歷使得中國留學生接受西方文學觀念的影響,尤其歐洲國別文學的產生和發展規律,促使先行者思考相應的問題;新詩的誕生便是這一影響的產物。1916年,胡適在美國首先提倡擺脫古典詩詞格律的束縛,旨在打破古人設定的形式規則對今人詩作的制約。與此相并列的另一條線索是在日本留學的郭沫若于五四運動前后創作的新詩,以情感內容決定詩歌的形式。它們都力圖以自由的體式取代傳統的格律。
1.“自然的音節”說。于認識到傳統詩詞格律強大的規范力量,胡適革新主張的第一步是摒除古典格律的影響,他倡導的“不更做文言詩詞”,而作“長短不一的白話詩”?,就是針對傳統格律而言的。他認為,“五七言八句的律詩決不能容豐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絕句決不能寫精密的觀察,長短一定的七言、五言決不能委婉達出高深的理想與復雜的感情。”?所謂“詩體的大解放”,“就是把從前一切束縛自由的枷鎖鐐銬,一切打破: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話怎么說,就怎么說。”?在此意義上,胡適倡導的是自由詩。
在“詩體的大解放”倡導之下,古典詩詞格律中的平仄、對仗、篇制等規矩都被拋卻,只剩下用韻這一項要素。除韻腳問題外,胡適還注重新詩“音節上的試驗”,他曾專門討論“雙聲”、“疊韻”、“齊齒”對“增加音節上的美感”的認識,認為“凡能充分表現詩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輕重,自然高下的,便是詩的最好音節。”?“詩的音節全靠兩個重要分子:一是語氣的自然節奏,二是每句內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諧”?。在實踐的基礎上,胡適將“自然的音節”?理論總結為
兩個重要問題,一個是用韻,即他所謂的“音”,主要表現為韻腳,新詩押韻比較自由,可以一韻到底,也可以一節一轉韻,還可以采用交韻、抱韻、隨韻等;另一個是音節,即他所謂的“節”,是新詩格律理論探討的關鍵所在,涉及詩行詞語停頓的問題。胡適將傳統詩句以“言”為計量單位轉化成現代漢語詩歌以“節”為計量單位。盡管提出了“節”的概念,也就是關系到新詩節奏的問題,但由于胡適順從口語的習慣,重視白話而不重視詩歌藝術,導致初期新詩呈現散文化傾向。不過“音節”概念的提出,對新詩格律理論建設具有奠基的作用,后來聞一多的“音尺”,葉公超、孫大雨的“音組”,朱光潛的“頓”,林庚的“節奏音組”,鄭敏的“字群的組合”?等概念,都是在胡適“節”的概念基礎上的探討。
五四時期還有一些討論傳統格律問題的意見,如劉半農提出廢除律詩、排律,“更造他種詩體”?的觀點,皆是對古典詩詞格律的擺脫。
2.“自然流露”說。自由詩這一源自西方的概念,是相對于古典格律詩而言的;自由,指其形式的不受囿限,并不是不要形式,而是不要傳統的格律形式。自由體的形式由內容決定,即由內容形成韻律,或曰“思想韻律”?。思想韻律依循情感的起伏,可以采用重復、排比等方式。詩人兼詩論家艾略特說:“好的自由詩基本上是一種對比較為人熟知的英語詩節奏形式的逃避”?。可見,不論中西,現代詩的成立都需要經過脫離古典詩歌格律的過程。
郭沫若接受西方自由體式的影響,大膽跳出中國古典詩歌的傳統套路,提倡依據內容跌宕起伏的自由詩。他說:“我也是最厭惡形式的人”,“總覺得以‘自然流露’的為上乘”?,這種自然流露觀的準則是要體現內在的節奏或內在的韻律。“詩之精神在其內在的韻律”,“內在的韻律便是‘情緒的自然消漲’。”?并進而認為,“詩=(直覺+情調+想象)+(適當的文字)”,“詩不是‘做’出來的,是‘寫’出來的。”?這種自然流露說還包含直接“摹擬我們底心情”的意味,由情感控制詩的進程。在此理論導引下,崇奉形式絕端自由的郭沫若任情緒像脫韁之馬盡情馳騁,而不注重打磨,以致造成某些詩作藝術粗糙的弊端。
陸志韋在1923年出版的《渡河·自序》中指出,“破四聲”、“舍平仄而采抑揚”,抑制新詩的“放蕩”,創造有節奏的“自由詩”?,一定程度是針對郭沫若自由體觀點而言的。抗戰期間出版的《詩論》代表艾青對自由詩理論的推進,他注重節奏與旋律,而不注重格律,更不迷信形式,“節奏與旋律是情感與理性之間的調節,是一種奔放與約束之間的調協。”?艾青將胡適的白話入詩觀念提升為散文入詩的觀念,將郭沫若對情緒的宣泄引向對情感內在節奏的把握,從而將初期新詩的散文化擢升至自由詩的散文美,并將自由詩的形式藝術定位在制造韻律上。
三
盡管新詩脫離古典詩詞格律的束縛而得以成立,但自由詩隨之產生了散文化和藝術粗糙的弊病?,也就是說,新詩對傳統詩詞格律的規定拋棄得太多了。對此,聞一多強調新詩的節奏理論。這是對詩歌格律的重新認識,實際上構成對漢語詩詞格律傳統的歸返。在新詩格律建構中,聞一多、葉公超、孫大雨等人主要圍繞詩行的頓數問題展開,這就與傳統格律里的篇制問題相關聯。
1.“音尺”說。作為新格律派的綱領性文件,《詩的格律》一文提出“音尺”的概念,這是英語詩格律術語foot的中文翻譯,聞一多借來用以稱謂新詩的節奏單位。他認為新詩的音尺主要分為“二字尺”或“三字尺”,以《死水》為例,每一詩行為四個音尺,或由兩個二字尺和兩個三字尺組成,或由三個二字尺和一個三字尺組成,音尺在詩行里等時地流動,整首詩的節奏就得以突顯。這里,聞一多將傳統詩歌的等音計量轉化為現代漢語詩歌的等頓計量,由傳統的“幾言”轉化為“幾個音尺”(幾頓),奠定了新詩格律中通過控制節奏來控制詩行長度的基礎。
基于“音尺”計量單位的確定,聞一多還提出“句的均齊”的觀點,這是依據音尺數相等而形成的詩行之整齊。如果說古典格律的五、七言是在文言的基礎上對詩歌句式、字數要求的話,那么聞一多對新詩行的要求與前者的思路是一致的,卻更適合新詩的組句特點。進一步地,他提出“節的勻稱”的觀點,這是在句式均齊的基礎上形成的詩節之整齊。
整齊的字句是調和的音節必然產生出來的現象。絕對的調和音節,字句必定整齊。
這樣講來,字數整齊的關系可大了,因為從這一點表面上的形式,可以證明詩的內在的精神——節奏的存在與否。?
由于對格律規則的循環應用,一邊說“沒有音尺,也就沒有句的均齊;沒有格式,也就沒有節的勻稱”,一邊說“字數整齊的關系可大了”,這樣就忽視了詩行音尺數相等與字數相等的差別,因此他提出的“字數整齊”產生了絕對劃一的詩句長度問題,違背了新詩行按音尺數(頓數)計量的法則。
盡管如此,聞一多格律理論的進步性在于,解決了新詩行停頓次數整齊所產生的節奏問題,比胡適“自然的音節”觀點更突出了新詩的格律。
2.“音組”說。在聞一多之后,葉公超也發表了關于新詩格律的觀點,他認為,“格律是任何詩的必需條件,惟有在合適的格律里我們的情緒才能得到一種最有力量的傳達形式;沒有格律,我們的情緒只是散漫的、單調的、無組織的,所以格律根本不是束縛情緒的東西,而是根據詩人內在的要求而形成的。假使詩人有自由的話,那必然就是探索適應于內在的要求的格律的自由,恰如歌德所說的,只有格律能給我們自由。”?他提出新詩是“說話的節奏”和“音組”的概念,“在文言里,尤其在文言詩里,單個字的勢力比較大,但在說話的時候,詞語的勢力比較大,故新詩的節奏單位多半是由二個乃至四個或五個字的詞語組織成功的,而不復是單音的了,雖然復音的語詞中還夾著少數的單音。……中國語言的音組(即語詞的字音)是很短的,大概五個字的音組已是不多聽見的。在每個音組里,至少有一個略微長而重,或重而高,或長而重而高的音。……我們只有大致相等的音組和音組上下的停逗做我們新詩的節奏基礎。”?這里的“音組”概念的提出,原則上與聞一多的“音尺”概念是一致的,但葉公超強調新詩行音組數相等而詩句長度可能不等的自由,這是對聞一多格律理論的推進。
孫大雨對新詩格律的貢獻在于界定了音組的概念,他認為詩的節奏總是相當整齊有度的,因而總可以分析成為規律化的音組,音組是由久暫顯得相同或相似的一個個單位組成的:
這些相似但又不盡相同的單位川流不息而來,接連幾個單位(通常以二至六為度)以成行,積聚幾行以成節段,在時間里秩序井然而又變化不絕地進行著,使作者聽者都感覺到內容和意義風格之間有一脈活力推動著,活躍著:這就是韻文所有而散文所沒有的“音組”。?
至此,在新詩格律建構里,由音組的流動形成的節奏,其性質、功用被清晰地揭示出來。由于古典格律要求每句字數相等,故整首詩的停頓點是一致的,而新詩則因現代漢語組詞字數不一的緣故,詩行并不一定整齊;如果能在整首詩內形成音組(頓)有節奏的流動,則詩歌的音樂性就得以產生。
對新詩格律的探討既是對詩歌格律本源的回歸,也是在忠實于新詩節奏特點的情況下對傳統格律的發展,等頓計量與等音計量的區別,構成新詩格律與古典詩詞格律在篇制問題上的差異。
四
從上文分析可知,不論是要破除舊格律套路的自由體,還是要建立新形式的格律體,實際上都圍繞著這樣兩個共同的問題:一個是用韻;一個是節奏,即音節、音尺、音組、頓等。對于前者,理論與創作都不存在歧義;對于后者,關于詩歌節奏的原則問題也沒有爭議,凡是詩歌就應該有節奏,而在是否應像近體詩一樣,其節奏應有形式上的定型要求這一點存在分歧,格律派一直在尋找新詩行的節奏規則,即固定的詩行模式,只是至今仍未確定下來;而自由派則反對規定一種形式作為新詩的主要形式,他們將詩句節奏樣式的決定權留給詩人自己。這樣,問題的焦點就在于,不論古今,也不論自由體還是格律體,都遵循著詩歌語言的運作規律,也就是發揮漢語言的音樂性,只是由于現代漢語不同于古代漢語,新詩人應該像音樂家那樣創造讀者喜愛的節奏,以口語的節奏代替傳統格律,把詩歌從機械呆板的節奏中解放出來,將凝固的古典格律轉變為自然靈活、富于彈性的現代節奏。就是說,新詩行的停頓樣式是不定的,每首詩的詩行頓數也是不定的,盡管四頓可能是最常用的,但其他頓數的出現也是有可能的。這樣新格律的多樣化并存狀態,一方面成為新詩的一種現代性表現;另一方面又與自由體的節奏論相靠攏,即使兩者仍存在嚴格與寬松的區別。一言以蔽之,盡管自由體、格律體的名稱不同,而實質上兩者探索的是同一個問題。
關于新詩格律與自由的問題,曾在1950年代出現集中的討論,如何其芳界定的現代格律詩,“每行的頓數有規律,每頓所占時間大致相等,而且有規律地押韻”?;卞之琳也認可以頓作為新詩格律的計量單位,并認為“詩經、楚辭、古詩、近體詩等都可以用頓來分析它們的格律基礎”?,這是用新詩格律計量單位衡量古典詩歌,這一反觀說明新詩格律衡量尺度是有效的;此前用古典格律衡量新詩往往遇到阻礙,那么這種反證法的運用,也是一種對新詩格律可行性的論證。當代自由詩創作的流行,一定程度說明其符合現代漢語詩歌節奏多元化的要求,正如徐訏所說,“詩詞的節奏和韻律,應該是語言的節奏與韻律,所謂語言的節奏與韻律實是生命生活節奏與韻律,一個人的走路有節奏韻律,呼吸有節奏韻律,血液循環有節奏韻律,消化工程有節奏韻律,這是生命的節奏韻律。生命的節奏韻律,一方面可說人人相同,另一方面也可說人人不同,……在詩歌方面,五言也好,七言也好,一方面,它們的節奏與韻律相同,另一方面講,每個詩人都有個別的節奏與韻律。”?將詩行節奏韻律的頓挫起伏交由創作處理,就是令每首詩都能獲得適合自己節奏韻律的表達方式。還有一種調和格律與自由兩派的觀點出現,即“精煉,大體整齊,押韻”?的提法,這貌似一種折中,實際上希望對兩派理論優長進行調諧,既要克服格律派的刻板,也要克服自由派的放蕩。總之,不論兩派調和與否,它們都將節奏韻律視為新詩的必要條件。
新詩格律問題仍處在探索過程之中,如果說新詩還沒有形成固定的格律,也許意味著新詩格律并不像古典格律那樣是單一的,而是多樣化的,即基本格律原則是應該有的,而在具體創作中則可以變通處理。就新詩格律與古典格律的關系而言,所謂脫離古典詩詞格律,是由古今漢語的差異造成的;所謂歸返格律精神,是由詩歌的文體性質決定的。一方面,古典詩詞的格律精神與節奏規律可以作為建構新詩格律規則的參照基礎,另一方面,新詩格律的建構可以也應該超越古典模式。在新詩格律建構中,古典詩詞格律規則發生不同的變化:用韻仍是一項重要的因素,且現代漢語詩句的押韻較古典詩詞寬泛,故應用較廣。由于多音節詞的出現,難于按近體詩的要求進行平仄搭配,但可以將其轉化為聲調上的差異排列,抑揚起伏而非單調劃一就能展示聲音上的錯落協調之美。因為構詞方式與古代漢語的差異,盡管不排除有對仗的詩句,但難于絕對地要求形式上的對仗,而對偶思維的功能往往應用于新詩內容之中,轉化為一種詩意表現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