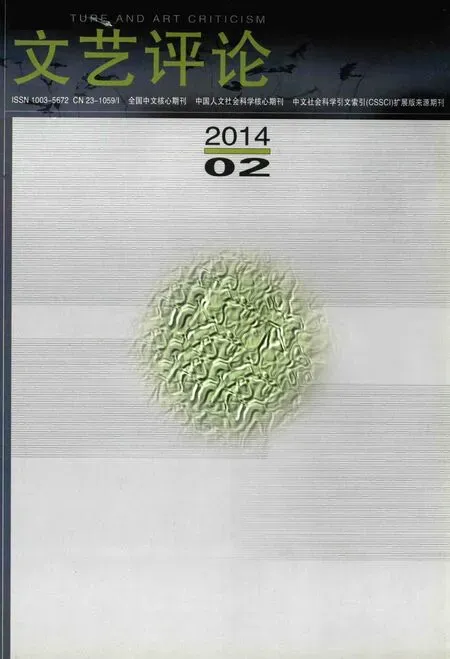明清樂論的客觀化趨向探析
韓 偉
明清樂論尤其是明代樂論與宋代樂論有相似之處,但又存在自身特點。就相似處言之,在理學的大背景下都表現出一定的維護儒家樂統的傾向,這一點在以王守仁、王夫之為代表的理學家樂論中表現明顯,他們仍然十分推崇儒家中和之德對音樂的指導意義,仍然推崇雅樂而否定新聲,對儒家的“中和”、“雅正”、“德行”等理想推崇備至,從而形成了理學家樂論與具有進步色彩的民間樂論分庭抗禮之勢。可以說,王守仁、王夫之等人的樂論也體現了正統文人及道學家樂論內在的自足性,同時這種自足性也帶有天然的封閉性,從而與音樂實踐的距離越來越遠。就明清樂論的自身特點而言,由于世俗化的逐步擴展加之市民社會的逐漸形成,便使宋代就已經十分繁榮的通俗文化進一步深化,相形之下,傳統儒家藝術觀念中的政治性、倫理性和神秘性傾向開始受到挑戰,此種背景下明清樂論亦表現出鮮明的客觀化傾向。我們認為,這一點是明清樂論區別于前代樂論的重要特質。
一、明清樂論的“主情”色彩
就主情而言,首先應提及者是李贄。李贄對“情”的重視事實上是其“童心說”的副產品,并將其與“性”放在一起,他反對前后七子的復古思想,主張在創作中要遵循“最初一念之本心”,表達自己的真實性情,崇尚自然真情。在《焚書·讀律膚說》中他指出:“蓋聲色之來,發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牽合矯強而致乎?故自然發于情性,則自然止乎禮義,非情性之外復有禮義可止也。”①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樂論從先秦時期開始就對與“情”相關的“性”十分關注,這一點在以《樂記》為代表的儒家樂論中表現十分明顯,《樂記》嘗言“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推崇人之本性,但這種“性”則是具備儒家之“德”的內涵的,與今天意義上的“性情”概念并不完全相同,所以《樂記》所言之“性”、“情”不同于李贄所言之“性”、“情”,雖然在宋代理學家樂論中也提到了“情”,但其與“性”相似仍是在“天理”的框架下言說的。而李贄所言之“性情”則是自然之情,甚至也不排除“欲”的成分。對真實情性的重視,在李贄琴論中也表現明顯:“《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人邪惡,歸于正道,故謂之琴。’余謂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②此處李贄對傳統琴論觀提出挑戰,《白虎通》中的琴論思想代表了漢代以來對琴樂的普遍認識,賦予琴鮮明的政治色彩和道德內涵,認為其是禁止淫邪思想產生的重要工具。對此,李贄的觀點十分鮮明,他更多的是將其看成表達人內在情感的工具。
可以說,李贄的這種認識在明中葉以后是具有非常強大的號召力的。比如湯顯祖便從戲曲創作角度談到了情的重要性,“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③。而公安三袁則從歌詩角度表達他們對“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理解,袁宏道嘗言:“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閭閻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不效顰漢、魏,不學步于盛唐,任性而發,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欲,是可喜也。”④明清時期,對“情”的重視,除了上述諸人的樂論之外,還有張琦、李開先、馮夢龍等人,他們的基本立場與李贄、湯顯祖、袁宏道等人較為相似,限于篇幅不贅述。
二、明清樂論的“尚俗”取向
明清樂論的客觀化潮流的第二個表現是尚俗。所謂尚俗,是說明清樂論表現出鮮明的雅俗通變立場,甚至認為俗樂是雅樂的基礎。事實上,這種現象在宋代朱熹、鄭樵等人的樂論中就曾有所表現⑤,但直到明清兩代,俗樂的地位才被正式確立下來。俗樂由于能夠自由地表達真情實感,加之形式上很少受到束縛,所以在明清時期獲得了蓬勃發展。在樂論中,與上述“主情”傾向一致,這一時期的樂論對俗樂多持肯定贊賞的態度,本書認為對俗樂的重視李贄、馮夢龍、李漁代表了逐漸深化的三個階段。李贄樂論亦如前述,對自然情性的重視使得其對民間音樂更為推崇。下面重點談一下馮夢龍和李漁。明代中期以后的很多文人普遍持“真詩只在民間”(李開先語)的看法,此種背景下馮夢龍對民歌十分推崇,并輯有《山歌》、《掛枝兒》等民歌集,其對俗樂的看法在《山歌》一書的序言中有明確的展現:
桑間濮上,《國風》刺之,尼父錄焉,以是為真情而不可廢也。山歌雖俚甚矣,獨非《鄭》《衛》之遺與?且今雖季世,而但有假詩文,無假山歌,則以山歌不與詩文爭名,故不屑假。茍其不屑假,而藉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今人想見上古之陳于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于民間者如此,倘亦論世之林云爾。若夫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其功于《掛枝兒》等,故錄《掛枝詞》而次及《山歌》。⑥
由此可見,馮夢龍認為山歌與詩文同等重要,而且與李贄、湯顯祖等人相似,其推崇山歌的深層原因仍是源于真情,并希望能夠“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在馮夢龍眼中鄭衛之音、桑間濮上之曲與山歌相似,在各自的時代都起到同樣的作用。無疑,這種看法是具有進步性的。
馮夢龍之后,清代戲曲理論家李漁對俗樂的認識又有所深入,這也是明清俗樂理論發展的第三個階段。李漁在《答同席諸子》一文中談到欣賞歌舞的感受時他說“然胸中所見,自謂簾內之絲,勝于堂上之竹;堂上之竹,又勝于階下之肉”⑦,表明他肯定“絲勝于竹,竹勝于肉”。可以說,李漁的這一認識是對傳統樂論中“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觀念的反叛,承認了世俗樂器的重要性,其中原因一方面在于,絲竹的樂聲雖屬于人為,與天然的肉聲不同,但絲竹之聲卻帶有更大的不確定性和含混性,因此會帶給欣賞者更大的想象空間,這一點是肉聲稍顯遜色的地方,而這種想象空間恰是藝術的生命,正因如此李漁主張“即不如離,近不如遠;和盤托出,不若使人想象于無窮耳”⑧。另一方面的原因則與李漁的鮮明民間立場密不可分,自明代李贄開始,經過馮夢龍,到李漁這里,文人對民間文藝越發推崇,而絲竹等樂器恰是演奏民間音樂的主要工具,所以李漁對絲竹的肯定恰可反映出其對通俗音樂的基本態度。與其對民間藝術的態度一致,他對具有鮮明民間特點的戲曲和填詞都較為肯定:“文字之最豪宕,最風雅,作之最健人脾胃者,莫過填詞一種。……惟于制曲填詞之頃,非但郁藉以舒,慍為之解,且嘗僭作兩間最樂之人,覺富貴榮華,其受用不過如此。”⑨
除此之外,在對待古樂與新聲這對一直以來的矛盾藝術方面,李漁的觀點也較為透脫,在他看來,古樂與新聲并無明確界限,大可不必機械地拘于固有成見,“聽古樂而思臥,聽新樂而忘倦。古樂不必《簫韶》,《琵琶》、《幽閨》等曲,即今之古樂也”⑩。即是說,只要能表現人的真實情感無論是古樂還是新聲都是值得肯定的音樂。
李漁對待古樂與新聲的這一態度,在清代音樂研究者中較為普遍。這一點在毛奇齡、李塨、江永等人的樂論中有較為集中的表現。毛奇齡認為雅樂、俗樂并無價值論層面的區別,他對歷來備受推崇的雅樂有自己的看法:“古樂有貞淫而無雅俗。自唐分雅樂、俗樂、番樂三等,而近世論樂者動輒以俗樂為譏。殊不知唐時分部之意原非貴雅而賤俗也,以番樂難習,俗樂稍易,最下不足學則雅樂耳。故考伎分等反重番樂,其能習番樂者,即賜之坐,名坐部伎。其不能番樂則降習俗樂,不坐而立,名立部伎。若俗樂不能則于是斥習雅樂,不齒于眾,雅樂之賤如此。”?在他看來,雅樂的價值和難度絕不比俗樂和番樂大,前世帝王往往也用俗樂和番樂祭祀郊廟、侍奉祖先,俗樂只要內容上真純自然,雅俗的界限是不存在的。對此,清代的另一名學者李塨便一陣見血地指出:“天地元音今古中外只此一轍,辭有淫正,腔分雅靡,而音調必無二致。”?由此可見隨著通俗文藝在明清兩代的盛行,理論層面的雅與俗、古與今、中與外之間的巨大鴻溝被最大限度地填平了。
與毛奇齡、李塨的立場相似,江永在《律呂新論》中也以通變的態度看待古樂與新聲,且其觀點更為辯證,在《俗樂可求雅樂》中他說:
俗樂以合、四、一、上、勾、尺、工、凡、六、五,十字為譜,十二律與四清聲皆在其中,隨其調之高下而進退焉。所謂雅樂亦當不出乎此,為雅樂者必深明乎俗樂之理,而后可求雅樂。即不能肄習于此者亦必于俗樂,工之稍知義理者,參合而圖之,未有徒考器數、虛談聲律而能成樂者也。宋世制樂諸賢,唯劉幾知俗樂,常與伶人善笛者游,其余諸君子既未嘗肄其事,又鄙伶工為賤伎不足與謀,則亦安能深知樂中之曲折哉?判雅俗為二途,學士大夫不與伶工相習,此亦從來作樂者之通患也。?
由此可見,在江永眼中欲求雅樂,則必須先明俗樂之理,甚至要向士大夫所不齒的伶工賤隸學習,實際上江永已經將雅俗的界限取消掉,大俗即為大雅。而這一簡單的道理則一直被正統文人所摒棄,自宋代以后僅有劉幾等有限的幾位音樂理論家能明白這一點。江永除了在雅樂與俗樂方面的觀點較為靈活之外,對樂器、律準的看法也是如此,在《樂器不必泥古》篇中他說:“聲寓于器,器不古雅則聲亦隨之。然天下事,今不如古者固多,古不如今者亦不少。古之笙用匏,今之笙用木,匏音劣于木,則亦何必拘于用匏而謂八音不可缺一乎?……后世諸部樂器中,擇其善者用之可也。”?在《度量權衡不必泥古》中他亦認為古代律準以黃鐘為根據,較為固定,因為度量的標準是統一的。而后世度量衡則很難統一,相應黃鐘管的長度便很難確定,此種背景下各音的高度自然出入較大。鑒于此,他認為律準與樂器相似,都不必泥古不化。可以說,江永的上述思想是十分辯證的,這也是其樂論的基本指導思想,其在《聲音自有流變》中便明確指出:“若不察乎流變之理,而欲高言復古,是猶以人心不安之禮強人以必行也,豈所謂知時識勢者哉!”由此,其“通變”思想可見一斑。
三、明清樂論的“去神秘性”
明清樂論客觀化潮流的第三個表現是去神秘性。中國古代樂論的去神秘化過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雖然魏晉時期出現了嵇康《聲無哀樂論》這樣的樂論名篇,但從總體而言先秦的天道觀、漢代的五行思想乃至宋明的天理觀,都使得古代樂論帶有天然的神秘性色彩。明代總體而言雖然在心學的影響之下更加強調主體真實性情的作用,但樂論中的神秘性因素仍時有表現,即便是在陽明心學中較為自由的泰州學派的代表李贄處,也有這種影子。其在《焚書·征途與共后語》?中明確提到了“聲音之道可與禪通”的觀點,認為音樂創作和欣賞都與禪悟有相通之處,“所謂音在于是,偶觸而即得者,不可以學人為也”。很顯然,雖然如上文所述李贄樂論中有若干進步之處,但仍有神秘化的影子,所不同的是其更多的是從禪宗的角度來看待音樂的。
而明清樂論在整體上畢竟是以去神秘化為主的,李贄作為開端性的人物雖不徹底,但畢竟對后來者有“導夫先路”之功。在清代的毛奇齡和李塨的樂論中,可以更鮮明地看到對神秘化樂論的摒棄。毛奇齡在《竟山樂錄》中有如下言論:
故凡為樂書者多畫一元兩儀、三才五行、十二辰、六十四卦、三百六十五度之圖,斐然成文而又暢為之說,以引證諸黃鐘、太簇、陰陽、生死、上下、順逆、增減,以及時氣、卦位、歷數之學,鑿鑿配合者,則其書必可廢。何者?使觀其書而樂由以明,五聲由以著,六律、十二律皆由之而曉然以晰,則傳之可也;乃畢力求之,窮竟篇帙,而按之聲而聲茫然,按之律而律茫然,則雖欲不廢而何待已?故未求聲而求器,未求器而求數,未求數而先求之度量衡之銖、兩、絲、黍、百、千、萬、億之璅璅,是皆亡樂之具。……然后知遷、固以后京房、鄭玄、張華、荀勖、范鎮、房庶、王樸、李照、陳旸,以及近代之韓尚書、鄭恭王、楊主事輩,凡言鑄鐘均弦、造器算數,皆欺人之學,不足道也。?
在毛奇齡的這段話中有幾點值得注意:首先,他承認“人聲”的重要性,并將其看做音樂之根本,即“樂以聲為主,樂之聲以人聲為主”是也。其次,對漢以后中國樂論中的神秘化和倫理化色彩提出質疑,認為從圣王、天地、五行等角度討論音樂是古代樂論的最大弊端,這種做法往往會使音樂淪為某種倫理思想或哲學思想的附屬品,而喪失了自身的獨立性,所以毛奇齡稱這種做法“與聲律之事絕不相關”。再次,他也對歷來的“以尺定律”的機械做法提出質疑,所謂“以尺定律”是與“以律定尺”截然相反的定準方式,前者重視古制,往往以史料中的記載為準,而后者則以實際音聲和諧為準,所以“以尺定律”便是以先入為主的方式確定固定的標準,這一標準多出于前代樂書或本朝的音樂制度,然后確定律準,進而確定各音的高低。對于“以尺定律”還是“以律定尺”的問題,漢代以后一直爭論不休,尤以宋代最為激烈,李照、胡瑗、陳旸、房庶、范鎮等人都曾參與其中。今天看來,“以律定尺”當更為科學,更為符合音樂的自身規律。毛奇齡所批判的“未求聲而求器,未求器而求數,未求數而先求之度量衡”便屬于這一范圍。可以說,毛奇齡的觀點代表了明清以來樂論漸趨客觀化、科學化的潮流,這已是明清樂論尤其是清代樂論較之前代神秘化樂論的重要進步,為近代樂論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受毛奇齡影響,他的學生李塨在《學樂錄》中也持類似觀點:“今中華實學陵替,西洋人入呈其歷法算法,與先王度數大端皆同,所謂天地一本,人性同然,不知足而為屨必不為蕢者也,乃于樂獨謂今古參商,而傳習利用之音為夷樂俗樂,亦大誤矣。”?在他看來,包括西洋樂在內的一切音樂并無本質區別,甚至中華音樂與西洋音樂其“度數大端皆同”,這一方面表明西洋音樂此時已經進入國人視野,并對本土音樂產生了影響。另一方面也可表明隨著西洋樂的普及,中國傳統文人表現出相對接受的態度,可以說這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也是本土樂論逐漸客觀化的鮮明標志。另外,李塨在《學樂錄》中也記載了毛奇齡否定神秘化樂論的言論:“塨問曰:‘五聲配五行、十二律配十二月皆秦漢以后牽掣之論,圣經未有也。今扭合之終不確,且滋紛無益也,不如一概巳之。’河右答曰:‘是’。”?這段話中的“河右”便是毛奇齡的號,李塨曾從學于毛奇齡,并對其思想較為認同,其《學樂錄》自序云:“塨學樂河右先生一年余矣,雖窺涯岸,未盡精微也。”?由此不難看出,李塨是深受毛奇齡影響的,而上述對西洋樂的態度、對神秘化樂論的否定恰可充分地說明這一點。
當然,明清樂論中仍無法決然摒棄掉傳統樂論倫理化、政治化甚至是神秘化的色彩,在很多人尤其是明代道學家的樂論中這種情況仍十分明顯,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明清尊奉傳統樂論一系雖然仍對《樂記》等樂論經典十分推崇,但其直接承續的對象則是以周敦頤為代表的宋代新儒家樂論,較突出的例子便是往往以周敦頤的“淡和”思想為指導討論音樂問題,如明末琴家徐上瀛在《溪山琴況》中曾提出古琴美學的二十四況,其中前九況為:和、靜、清、遠、古、淡、恬、逸、雅,便蘊含著宋代理學之“淡和”的因素,蔡仲德先生說:“前九況的精神……歸納為‘清和’、‘和靜’、‘清淡’,不如歸納為‘淡和’之為宜。”?清人汪烜在《樂經律呂通解》卷一《樂記或問》中也有如下文字:“曰:‘五聲皆亂,便不成聲矣。然則鄭衛之音不和律乎?’曰:‘不如此說。樂貴淡和,八風從律,其律便自淡和。不和固不是正樂,不淡亦不是正樂。’”?甚至上文提到的較具通變意識的江永也有類似觀點:“故古樂難復,亦無容強復,但當于今樂中去其粗厲高急、繁促淫蕩諸聲,節奏紆徐,曲調和雅,稍近乎周子之所謂淡者焉,則所以歡暢神人、移風易俗者在此矣。”?事實上,對周敦頤“淡和”樂論思想的接受僅是明清樂論接受宋代樂論的一個縮影,經宋代新儒家改造過的傳統儒家樂論由于其更貼近現實社會、更符合新的審美傾向,被明清兩代樂論廣泛接受。正因如此,我們可以認為,雖然明清兩代樂論已經表現出鮮明的主情、尚俗、去神秘性的客觀化色彩,但仍然無法決然拋開固有的文化“模子”,仍帶有一定的不徹底性,但不管怎樣,明清時期較之前代樂論畢竟在客觀化層面有所突破,這一點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