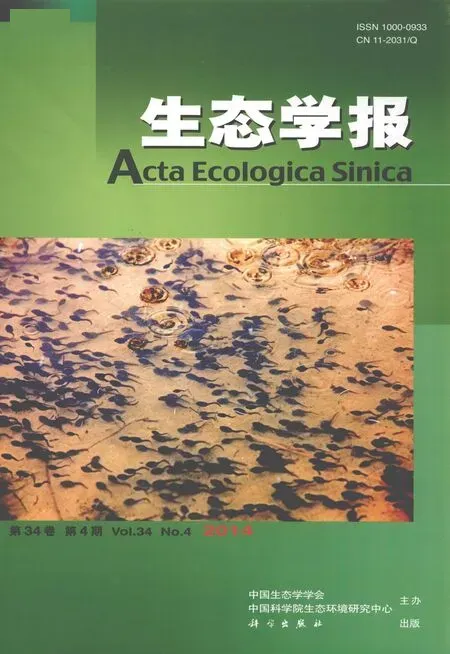三工河流域琵琶柴群落特征與土壤因子的相關分析
趙學春,來利明, 朱林海,王健健, 王永吉,周繼華,姜聯合,魯洪斌,趙春強,鄭元潤,*
(1. 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北京 100093; 2. 中國科學院大學,北京 100049;3. 青城山-都江堰旅游景區管理局, 都江堰 611843)
三工河流域琵琶柴群落特征與土壤因子的相關分析
趙學春1,2,來利明1, 朱林海1,王健健1,2, 王永吉1,2,周繼華1,2,姜聯合1,魯洪斌3,趙春強3,鄭元潤1,*
(1. 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北京 100093; 2. 中國科學院大學,北京 100049;3. 青城山-都江堰旅游景區管理局, 都江堰 611843)
琵琶柴(Reaumuriasoongorica)是我國荒漠地區分布最廣的地帶性植被類型之一,對維系荒漠地區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具有重要作用。以三工河流域兩個琵琶柴群落為對象,在2010年主要生長季節(6—10月),通過群落和土壤調查,采用土鉆法、土柱法、地上收割法對兩個琵琶柴群落的土壤性質、生物多樣性、細根生物量、地上生物量、生物多樣性與土壤性質的關系進行研究,結果表明:兩個琵琶柴群落在冠幅、蓋度、多度和物種多樣性等方面均存在顯著差異。在0—100 cm土壤層內,兩個群落土壤電導率、pH值、容重、含水量存在顯著差異。除土壤容重外,群落2各個土壤因子的值均大于群落1,并隨土壤深度的增加表現出類似的趨勢。兩個群落物種多樣性指數、地上生物量、細根生物量存在顯著差異,從6月到10月呈現先下降再上升的趨勢。由于7、8月群落1有大量夏雨型短命植物和類短命草本植物的出現,Shannon-Wiener多樣性指數、Pielou均勻度指數急劇降低,Simpson指數表現出相反的變化趨勢。群落2土壤電導率和pH值較高,草本植物鮮有出現,多樣性指數和均勻度指數變化均較為平緩。兩個群落的Sorenson相似性系數較低,群落差異明顯。相關和回歸分析表明土壤環境因子是導致兩個琵琶柴群落特征、生物多樣性和生物量不同的主要因素。較高的土壤含水量可以增加琵琶群落的生物多樣性,較高的土壤容重抑制琵琶柴群落細根的生長,輕度的干旱脅迫促進地上生物量的積累,一定濃度的土壤pH值和土壤鹽分可以促進琵琶柴群落細根的生長。
干旱區; 琵琶柴群落; 生物多樣性; 生物量; 土壤因子
植物群落與環境因子的關系是生態學研究的熱點問題[1- 2],氣候、土壤及微環境條件的變化可在不同尺度上顯著影響植物群落的結構和功能。即使在同一植被帶內,由于環境因子的變化,也可造成類似的植物群落在結構和功能上的顯著變化。關于植被大尺度格局與氣候及土壤關系的研究很多, Woodward和Williams研究了全球和區域水平氣候和植物分布的關系[3]。Ariza和Tielb?rger分析了植物-環境關系及其隨環境尺度的變化[4]。Kramer等探討了空間尺度對1年生植物分布的作用和決定機制[5]。就荒漠地區而言,Schlesinger等分析了荒漠地區土壤環境對植物結構和功能的影響,認為土壤條件決定植物的生長發育與分布[6]。Ma等認為土壤鹽分和水分制約植物群落的形成和演替[7],Sperry和Hacke[8]及Li等[9]研究了植物在干旱生境下生理和形態上產生的適應性反應。但在氣候相同、土壤條件類似的區域內,微環境條件變化對自然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影響的研究較少。
琵琶柴(Reaumuriasoongorica)為檉柳科(Tamaricaceae)紅砂屬(Reaumuria)小灌木,廣泛分布于我國西北荒漠地區,為我國荒漠地區分布最廣的地帶性植被類型之一,從鄂爾多斯西部、阿拉善、河西走廊、柴達木盆地、北山、噶順戈壁到塔里木盆地和準噶爾盆地,形成面積巨大的鹽柴類荒漠。琵琶柴亦是新疆阜康三工河流域的典型建群種和優勢種,具有極強的抗干旱、耐鹽堿特性[10],對土壤鹽堿化改良、植被恢復以及維持荒漠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具有重要意義。
琵琶柴為泌鹽植物,植物群落的建成除受到植物本身各種生物學特性影響外, 同時深受環境因子的影響。水分是影響荒漠地區植物生長發育的關鍵因子[7],是琵琶柴群落發生、發展和演化的決定因素[9]。土壤含鹽量亦是影響琵琶柴群落組成的重要因素[11],影響著鹽生植物群落的豐富度和多樣性。
野外調查中發現,在三工河流域琵琶柴群落典型分布區內,兩個相距較近,地形、地貌類似的琵琶柴群落在冠幅、蓋度、密度、多度、生物量及物種多樣性之間存在著很大變化,引起這種變化的原因是什么?本文旨在通過野外調查,比較分析兩個琵琶柴群落的結構和功能及其相應的環境因子,探討其結構和功能變化的機理,對深入理解琵琶柴群落與環境的關系,理解微環境變化對植物群落的影響機制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可為更加有效地管理天然琵琶柴群落,恢復退化琵琶柴群落提供科學基礎。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研究地點位于新疆天山中段北坡準噶爾盆地南緣的三工河流域,地理坐標為87°43′—88°44′E, 43°45′—45°29′N,整個流域南高北低, 由東南向西北傾斜,流域面積1670 km2。研究區域為典型的溫帶荒漠氣候,夏季炎熱而冬季寒冷,降水少而蒸發量大。年平均氣溫6.6 ℃,最高氣溫42.6 ℃,最低氣溫-41.6 ℃,7月份平均氣溫25.6 ℃,1月份平均氣溫-17 ℃;年均降水量164 mm,年蒸發量1780—2453 mm,冬季平均積雪厚度29 cm,無霜期174 d。
研究區域土壤成土母質以沖積物為主,土壤類型為典型荒漠鹽堿土,pH值均大于8.5,土壤生物過程較弱,有機碳含量較低 (<4.0 g/kg)。地帶性植被為荒漠植被,其中以檉柳科(Tamaricaceae)琵琶柴屬(Reaumuria)、檉柳屬(Tamarix),藜科(Chenopodiaceae)梭梭屬(Haloxylon)、豬毛菜屬(Salsola)、堿蓬屬(Suaeda),蒺藜科(Zygophyllaceae)白刺屬(Nitraria)、霸王屬(Sarcozygium)為重要建群種。其中,琵琶柴荒漠植被是北疆最典型的植被類型之一。
1.2 樣地設置與野外觀測
在研究區選取兩個分布距離較近,但外貌結構具有顯著差別的琵琶柴群落,基本情況見表1。

表1 兩個琵琶柴群落的基本情況
于2010年主要生長季(6—10月)每月月初,在兩個琵琶柴群落內分別設置3個25 m×25 m 的樣方,記錄樣方內的物種數目及每個物種的個體數、冠幅、多度、高度、蓋度等。在每個25 m×25 m的樣方內設置3個5 m×5 m的樣方,刈割植物地上部分,測定地上生物量。采用土柱法測定細根生物量,在每個5 m×5 m的樣方內設置3個50 cm×50 cm的采樣點,每隔10 cm挖取土樣,直到鮮有根系為止。將土壤樣品帶回實驗室,置于細篩之上用水沖洗,同時去除其它雜質,僅留直徑小于2 mm的細根。在每個25 m×25 m 的樣方內,隨機選取3個樣點進行土壤樣品采集,采樣時去掉地表凋落物,用土鉆依次鉆取0—5 cm、5—10 cm、10—20 cm、20—30 cm、30—40 cm、40—50 cm、50—100 cm處的土壤樣品各約300 g,用于分析土壤pH值、電導率等指標;在每個樣點內挖掘土壤剖面,用土壤環刀每隔10 cm分層采集用于測定土壤容重和含水量的樣品,同時用Em50測定土壤溫度。
1.3 室內分析
用于測定土壤容重的樣品在105 ℃烘干至恒重,同時測定土壤含水量。用于測定其他指標的土壤樣品,置于干燥陰涼處風干,挑去其中根系、未分解的有機質,過100目土壤篩。分別采用pH計和DDSJ- 308型電導儀測定土壤pH值和電導率。將琵琶柴地上生物量和細根生物量于65 ℃條件下烘干至恒重,測定干重。
1.4 數據分析
采用t檢驗法,比較兩個琵琶柴群落特征及其土壤含水量、pH值、容重、電導率、土壤溫度、地上生物量和細根生物量的差異。
采用以下公式計算琵琶柴群落的物種多樣性:
(1)物種數目 s
(2) Shannon-Wiener多樣性指數
H=-∑PilgPi
(3)Simpson指數
(i為1,2,3,…,s)
(4) Pielou均勻度指數
J=(-∑PivlnPiv)/lns
(5)Sorenson相似性系數
式中,s為物種總數,N為全部物種個體總數;H為香農-維納多樣性指數,Pi為抽樣個體屬于某一物種的概率;Sd為Simpson指數,ni為第i個物種的個體數,N為全部物種個體總數;J為Pielou均勻度指數,Piv為ni的相對重要值(相對高度+相對蓋度);Cs為Sorenson相似性系數,j為兩群落或樣地共有的種數,a為群落1的物種數,b為群落2的物種數。
數據分析檢驗均在SPSS16.0中完成。
2 結果
2.1 琵琶柴群落特征
兩個琵琶柴群落物種數均較少,群落1為8種,包括琵琶柴和梭梭2個基本種,全年均存在于群落之中;豬毛菜和大花駱蹄瓣(Zygophyllumpotaninii)2種夏雨型短命植物,出現在夏雨較為集中的6—8月;二色補血草(Limoniumbicolor)、兜藜(Panderiaturkestanica)、角果藜和鹽地堿蓬(Suaedasalsa)4 種類短命草本植物,其中二色補血草、角果藜、兜藜出現在初春至9月,鹽地堿蓬出現于6月中旬至生長季結束。群落2物種數為4種,包括琵琶柴、小果白刺、梭梭3種基本種,豬毛菜1種夏雨型短命植物,類短命植物未出現于群落之中。群落結構簡單,僅有灌木層和草本層。蓋度較小,群落1為25%,群落2為35%。
由圖1可見,在主要生長季節兩個琵琶柴群落的冠幅、蓋度、高度隨琵琶柴的生長大致呈遞增趨勢,10月份或有微量降低。兩個琵琶柴群落除植株高度無明顯差異外,密度、冠幅、蓋度、多度均存在顯著差異。

圖1 兩個琵琶柴群落的植冠面積、蓋度、多度、高度(平均值±標準誤差)Fig.1 Crown area, coverage, abundance and height of Reaumuria soongorica communities (mean ± SE)不同字母表示在相同時間下兩個群落指標存在顯著差異
群落1和2平均地上生物量分別為100.20、140.25 g/m2,平均細根生物量分別為35.92、105.13 g/m2(圖2),差異顯著,并表現出明顯的季節變化。兩個琵琶柴群落生物量變化規律相似,6月份最低,隨后逐漸升高,在9月初達到峰值,隨后急劇下降;群落1地上生物量與細根生物量變化均較群落2變化緩慢。

圖2 兩個琵琶柴群落地上生物量、細根生物量季節變化(平均值±標準誤差)Fig.2 Seasonal variations of aboveground biomass and fine root biomass of Reaumuria soongorica communities (mean ± SE)不同字母表示在相同時間下兩個群落指標存在顯著差異
由圖3可見,兩個琵琶柴群落的物種數目相對較低,群落1的物種數目明顯大于群落2。季節變化趨勢一致,6月最低,隨后逐漸升高,8月達到最大,之后逐漸下降。
就Shannon-Wiener指數而言,群落1明顯高于群落2,群落1的指數值由6月的0.67下降到8月的0.43,9月后有所增加,10月再次下降。群落2指數值從6月份到10月份變化趨勢平緩。
對于Simpson指數,除6月外,群落1指數值均大于群落2。季節變化與Shannon-Wiener多樣性指數變化趨勢相反。
兩個群落Pielou均勻度指數季節變化趨勢與Shannon-Wiener指數幾乎一致,不同之處是除6月外,群落1指數值均比群落2低。

圖3 兩個琵琶柴群落物種多樣性季節變化(平均值±標準誤差)Fig.3 Seasonal variations of species diversity of Reaumuria soongorica communities (mean±SE)不同字母表示在相同時間下兩個群落指標存在顯著差異
兩個琵琶柴群落的Sorenson相似性系數較低且季節波動大,平均值僅為0.21,從6月的0.25降低至8月的0.16,之后在10月增加到0.20。
2.2 土壤理化性質
兩個群落1 m內的土壤pH值隨深度的增加表現為先增大后減小的趨勢。群落1的pH值變化范圍為8.3—9.0,平均大小為8.73;群落2的pH值范圍變化為9.1—9.7,平均大小為9.32。
群落2土壤發生高強度鹽脹反應,表層(0—10 cm)疏松,土壤容重較小,僅為0.9 g/cm3, 隨土壤深度增加,表現出逐漸增大的趨勢。群落1土壤表現出一定的板結現象,表層土壤容重較大,隨土壤深度的增加土壤容重先降低后逐漸增加,超過40 cm以后容重增加趨勢變緩。
群落1的土壤含水量明顯低于群落2,從表層的0.79%增加到1 m處的7.04%,表層土壤含水量較低,約為1%,超過20 cm后逐漸達到6%以上,30 cm以后增加不明顯。群落2表層土壤含水量亦較低,但達到2%左右,深度超過10 cm后達到6%,40 cm深度時達到12%,其后增加不明顯。

圖4 琵琶柴群落不同層次土壤電導率、pH值、容重和含水量 (平均值±標準誤差)Fig.4 Soil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pH, bulk density, soil water content of two Reaumuria soongorica communities (mean±SE) in different soil layers不同字母表示在相同時間下兩個群落指標存在顯著差異
2.3 物種多樣性與土壤因子的關系
表2顯示了群落1各多樣性指數與土壤因子的關系。Shannon指數、Pielou均勻度指數均隨土壤含水量增加而增加,隨土壤電導率和土壤pH值的增大而減小,Simpson指數表現出相反的變化趨勢。此外,僅Shannon指數與土壤容重的擬合達到了顯著水平,生物多樣性指數與土壤溫度的關系不顯著。
表3顯示了群落2各多樣性指數與土壤因子的關系。其中僅Pielou均勻度指數隨土壤容重、土壤電導率和土壤pH值的增加而減小,Simpson指數隨土壤容重和土壤電導率的增加而增大,其它多樣性指數與土壤因子之間不存在顯著關系。

表2 群落1多樣性指數與土壤含水量、容重、電導率、pH值、容重的回歸方程
*P< 0.05; **P< 0.01

表3 群落2多樣性指數與土壤含水量、容重、電導率、pH值、容重的回歸方程
*P< 0.05; **P< 0.01
由表4可見,pH值、土壤含水量進入群落1 Shannon指數、Pielou指數、Simpson指數與土壤因子的逐步回歸方程中。pH值進入群落2 Pielou指數與土壤因子的逐步回歸方程;電導率、土壤含水量進入Simpson指數與土壤因子的逐步回歸方程。

表4 多樣性指數與影響因素的逐步回歸分析
W:土壤含水量(%); pH: 土壤pH;E:土壤電導率(ms/cm)
2.4 細根生物量與土壤因子的關系
由圖5可見,群落1細根生物量與土壤容重關系顯著。群落2細根生物量與土壤容重關系不顯著。
陣頭規定,家鄉宗教廟會時,青年必須趕回家鄉參加子弟陣頭的訓練和表演。這一傳統相當于“春節”,是人們繁忙之余順應親人或族群團聚的精神寄托,在于合家團聚、祭祀祈福;“九天”成立職業陣頭團體一方面是滿足社會需求,另一方面是求生存求發展。吳明認為傳統體育從文化的功能上來說是一種“文化資源”,一種可支配的資源,是會給人們帶來效益的[11]。如果一個傳統在生活中不能發揮任何作用,人們也不會遵從,自然就會消亡。
群落1細根生物量隨電導率的增加而逐漸增加,在電導率3.6 ms/cm處達到峰值后緩慢下降。群落2表現出完全不同的規律,細根生物量隨電導率增加近直線增加。
群落1細根生物量隨pH值增加先增加后下降,在pH值為9.10時達到最大。群落2細根生物量在可見pH值范圍內,隨pH值的增加而增加,但增加速率逐漸變慢。

圖5 兩個琵琶柴群落細根生物量與土壤容重、電導率、pH的回歸方程Fig.5 Regression equations of fine root biomass and soil bulk density, soil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soil pH
由表5可見,pH、電導率進入群落1細根生物量逐步回歸方程。土壤pH值、土壤電導率和土壤含水量進入了與群落2細根生物量逐步回歸方程中。
2.5 地上生物量與土壤因子的關系
由圖6可見,群落1地上生物量與土壤含水量關系顯著,隨土壤含水量的增加逐漸增加,在含水量為6.09%達到最大值后地上生物量開始下降。群落2地上生物量與土壤含水量關系不顯著。群落1和群落2地上生物量與土壤容重關系均顯著,隨土壤容重的增加地上生物量不斷增大。群落1和群落2地上生物量均隨電導率的增加先增大后逐漸降低。

表5 細根生物量與影響因素的逐步回歸分析
Fr: 細根生物量(g/m2);W: 土壤含水量(%); pH: 土壤pH;E: 土壤電導率(ms/cm)

圖6 兩個琵琶柴群落細根生物量與土壤含水量、土壤容重、電導率、pH值的回歸方程Fig.6 Regression equations of fine root biomass and soil water content, soil bulk density, soil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soil pH
群落1地上生物量與土壤pH值關系不顯著,群落2地上生物量隨土壤pH值的增加逐漸增加,在pH值9.42時達到最大值后開始下降。
由表6可見,pH值、土壤溫度和土壤含水量進入群落1地上生物量逐步回歸方程。群落2僅有土壤容重進入地上生物量逐步回歸方程中。

表6 地上生物量與影響因素的逐步回歸分析
B: 地上生物量(g/m2);W: 土壤含水量(%); pH: 土壤pH;R: 土壤容重(g/cm3)
3 討論
3.1 琵琶柴群落物種多樣性
物種多樣性是度量生態系統結構、功能的主要指標[12],其大小影響著群落的生產力和生態系統穩定性[13]。氣候變化、人類干擾、極端環境、環境異質性和生物間的相互作用決定著植物群落組成和多樣性變化[14]。
本研究中群落1與群落2的多樣性指標在時間和空間尺度上均表現出較大的差異,主要與群落1 7、8月份有大量夏雨型短命草本植物出現,群落2此類植物鮮有出現相關。因此,豬毛菜、大花駱駝瓣、角果藜、二色補血草等夏雨型草本植物在7、8月的大量出現導致群落1的物種數目、Simpson指數顯著增加,Shannon-Wiener指數、Pielou均勻度指數、Sorenson相似性系數顯著降低。群落1中6月和9、10月草本植物的種類、個體總數雖不及7、8月多,但均勻度較大,Shannon-Wiener指數亦較大。Simpson指數表現出與Shannon-Wiener指數相反的趨勢。
群落2因其土壤表面蓬松和高鹽高堿的影響,限制了其它植物種子的萌發,夏雨型草本植物僅有極少量豬毛菜出現,對多樣性指數的影響較小。群落2較群落1組成簡單且植物個體總數少,受物種數目和個體總數的共同影響,Pielou均勻度指數在整個生長季節均較群落1大。受均勻度、物種數目和個體總數的共同影響,群落2 Shannon-Wiener指數在整個生長季呈平緩下降趨勢,Simpson指數呈平緩上升趨勢。
研究區域海拔變化較小,氣候條件、人類活動干擾類似,表現為土壤環境條件對更多物種生存的限制,特別是土壤水鹽的空間異質性是限制本地區植物群落分布的主要原因。琵琶柴群落物種Shannon-Wiener多樣性和Pielou均勻度隨土壤電導率和pH值的增大顯著降低,這與顧雪峰關于土壤鹽漬化是限制阜康綠洲植物群落分布和生物多樣性主要原因的結論類似[15]。因此,可以認為由于土壤鹽堿化程度較高,土壤鹽分含量和土壤pH值限制了三工河流域琵琶柴群落生物多樣性的發展,決定著種群繁衍和群落演替。
3.2 琵琶柴生物量
生物量是評價生態系統功能的重要參數之一,生物量對研究生態系統的碳循環和營養物質分配具有重要意義[16]。一般而言,荒漠生態系統由于受極端環境的影響,植物群落物種多樣性小、植被分布稀疏、蓋度小、生物量較低。本文中琵琶柴群落1和群落2地上生物量的平均值分別為100.20、140.25 g/m2,大于趙成義、劉速報道的55.55、63.63 g/株的結果[17- 18],但小于馬茂華報道的295.6 g/m2[19]。琵琶柴群落1和群落2細根生物量平均為35.92、105.13 g/m2小于Jackson等報道的全球荒漠生態系統細根生物量(270 g/m2)[20],這可能與本文琵琶柴群落分布于極端干旱區有關,但本文結果與裴志琴等報道的琵琶柴群落細根生物量(54.51 g/m2)[21]接近。
造成植物生物量不同的直接原因是降水、溫度、光照、海拔高度、土壤等因素,本實驗中兩個植物群落除了土壤性質差異之外,其它環境因子基本一致,因此土壤因子是造成琵琶柴細根生物量不同的主要原因。細根生物量是生物量的重要組成部分[22],對土壤因子的變化響應靈敏,其生長對整個群落生物量的影響十分明顯[23]。本文結果表明細根生物量與土壤容重、pH值和電導率具有顯著的相關性,與土壤含水量和土壤溫度相關性不明顯。琵琶柴群落1和群落2的平均土壤容重分別為1.36、1.21 g/cm3,由于群落1具有較大的土壤容重,降低了土壤孔隙度和氧氣含量,導致土壤微生物、有機質等含量減少,限制了植物根系的伸展,降低了水分和養分的利用效率。因此,導致細根生物量降低。
琵琶柴為耐鹽堿植物,通過Na+和K+含量的增加而調節滲透勢以適應土壤鹽度的增加[10]。何玉惠認為琵琶柴可以在高鹽堿條件下生長良好[24],并具有極強的抗鹽、抗干旱能力[19],耐鹽能力越強的鹽生植物,其根際的鹽分富集程度也更大[25]。周航宇采用150mmol/L的鹽溶液處理琵琶柴后,地上部分干重增加18%[10],表明適當的鹽分處理可以促進琵琶柴植株地上部分的生長。譚會娟等發現100—150 mmol/L的NaCl可以顯著促進琵琶柴愈傷組織的生長[26]。楊成龍等認為Na+和CI-具有促進鹽生植物的生長和地上部分器官肉質化的作用[27]。一些學者在霸王(Zygophyllumxanthoxylum)、細葉濱藜(Atriplexgmelini)和鹽地堿蓬(Suaedasalsa)等一些鹽生植物中也發現了類似的現象[7,28]。因此適當濃度的土壤鹽堿可以促進琵琶柴細根的生長和生物量的增加,群落2因其具有較高的鹽分含量和pH值,促進作用較群落1更為明顯,其機理仍需進一步研究。
綜上所述,干旱區琵琶柴群落受土壤環境條件的影響,物種種類少、結構簡單,生物多樣性低,較高的土壤含水量可以增加琵琶柴群落生物多樣性,土壤鹽堿化是影響植物群落和生物多樣性的主要因素;土壤容重、pH值和土壤鹽分含量是造成兩個琵琶柴群落生長和多樣性差異的主要因素,較高的土壤容重抑制琵琶柴群落根系的生長,輕度的干旱脅迫促進地上生物量的積累,一定濃度的土壤pH值和土壤鹽分可以促進琵琶柴根系的生長和生物量的增加。
[1] Grime J P, Brown V K, Thompson K, Masters G J, Hillier S H, Clarke I P, Askew A P, Corker D, Kielty J P. The response of two contrasting limestone grasslands to simulated climate change. Science, 2000, 289(5480): 762- 765.
[2] Brooker R W. Plant-plant interaction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New Phytologist, 2006, 171(2): 271- 284.
[3] Woodward E I, Williams B G. Climate and plant distribution at global and local scales. Vegetatio, 1987, 69(1/3): 189- 197.
[4] Ariza C, Tielb?rger K.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studying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plant-plant interactions along environmental gradients. Functional Ecology, 2011, 25(4): 932- 942.
[5] Kramer H A C, Montgomery D M, Eckhart V M, Geber M A. Environmental and dispersal controls of an annual plant′s distribution: how similar are patterns and apparent processes at two spatial scales?. Plant Ecology, 2011, 212(11): 1887- 1899.
[6] Schlesinger W H, Pilmanis A M. Plant-soil interactions in deserts. Biogeochemistry, 1998, 42(1/2): 169- 187.
[7] Ma Q, Yue L J, Zhang J L, Wu G Q, Wang S M. Sodium chloride improves photosynthesis and water status in the succulent xerophyteZygophyllumxanthoxylum. Tree Physiology, 2011, 32(1): 4- 13.
[8] Sperry J S, Hacke U G. Desert shrub water relations with respect to soil characteristics and plant functional type. Functional Ecology, 2002, 16(3): 367- 378.
[9] Li Y, Cohen Y, Fuchs M, Wallach R, Cohen S, Fuchs M. On quantifying soil water deficit of a partially wetted root zone by the response of canopy or leaf conductance. 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 2004, 6(1): 21- 38.
[10] Zhou H Y, Bao A K, Du B Q, Wang S M. The 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how eremophyteReaumuriasoongoricaresponses to severe NaCl stress. Pratacultural Science, 2012, 29(1): 71- 75.
[11] Zhang B, Meng B, Hao J X, Ding W H. Heterogeneity of soil moisture and salt Contents and its eco-environmental effects in oasis-desert belt in arid zone-Taking Zhangye oasi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Heihe River as a case study. Journal of Desert Research, 2006, 26(1): 81- 84.
[12] Tylianakis J M, Tscharntke T, Klein A M. Diversity, ecosystem function, and stability of parasitoid-host interactions across a tropical habitat gradient. Ecology, 2006, 87(12): 3047- 3057.
[13] Tilman D.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ethics of biodiversity. Nature, 2000, 405(6783): 208- 211.
[14] He J S, Chen W L. A review of gradient changes in species diversity of land plant communities. Acta Ecologica Sinica, 1997, 17(1): 91- 99.
[15] Song C Y, Guo K, Liu G H. Relationships between plant community`s species diversity and soil factors on Otingdag sandy land. Chinese Journal of Ecology, 2008, 27(1): 8- 13.
[16] Potter C S. Terrestrial biomass and the effects of deforestation on the global carbon cycle. BioScience, 1999, 49(10): 769- 778.
[17] Zhao C Y, Song Y D, Wang Y C, Jiang P A. Estimation of aboveground biomass of desert plants.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2004, 15(1): 49- 52.
[18] Liu S, Liu X Y. The estimating model of upper plant weight onReaumuriasoongoricasemishrub. Arid Zone Research, 1996, 13(1): 36- 41.
[19] Ma M H, Kong L S. The bio-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Reaumuriasoongoricaon the border of oasis at Hutubi, Xinjiang. Acta Phytoecologica Sinica, 1998, 22(3): 237- 224.
[20] Jackson R B, Mooney H A, Schulze E D. A global budget for fine root biomass, surface area, and nutrient content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997, 94(4): 7362- 7366.
[21] Pei Z Q, Zhou Y, Zheng Y R, Xiao C W. Contribution of fine root turnover to the soil organic carbon cycling in aReaumuriasoongoricacommunity in an arid ecosystem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Plant Ecology, 2011, 35(11): 1182- 1191.
[22] Lukac M, Godbold D L. Fine root biomass and turnover in southern taiga estimated by root inclusion nets. Plant and Soil, 2010, 331(1/2): 505- 513.
[23] King J S, Albaugh T J, Allen H L, Buford M, Strain B R, Dougherty P. Below-ground carbon input to soil is controlled by nutrient availability and fine root dynamics in loblolly pine. New Phytologist, 2002, 154(2): 389- 398
[24] He Y H, Liu X P, Xie Z K. Effects ofReaumuriasoongoricaon its underlying soil properties and herb plant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Journal of Ecology, 2011, 30(11): 2432- 2436.
[25] Yi L P, Ma J, Li Y. Soil salt and nutrient concentration in the rhizosphere of desert halophytes.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07, 27(9): 3565- 3571.
[26] Tan H J, Jia R L, Liu Y B, Zhao X, Li X R. Characters of ions accumulation inReaumuriasoongoricacallus under salt stress. Journal of Desert Research, 2010, 30(6): 1305- 1310.
[27] Yang C L, Duan R J, Li R M, Hu X W, Fu S P, Guo J C. The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alt-tolerance inSesuviumportulacastrumL..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0, 30(17): 4617- 4627.
[28] Bajji M, Kinet J M, Lutts S. Salt stress effects on roots and leaves ofAtriplexhalimusL.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callus cultures. Plant Science, 1998, 137(2): 137- 142.
參考文獻:
[10] 周航宇, 包愛科, 杜寶強, 王鎖民. 荒漠植物紅砂響應高濃度NaCl的生理機制. 草業科學, 2012, 29(1): 71- 75.
[11] 張勃, 孟寶, 郝建秀, 丁文暉. 干旱區綠洲- 荒漠帶土壤水鹽異質性及生態環境效應研究——以黑河中游張掖綠洲為例. 中國沙漠, 2006, 26(1): 81- 84.
[14] 賀金生, 陳偉烈. 陸地植物群落物種多樣性的梯度變化特征. 生態學報, 1997, 17(1): 91- 99.
[15] 宋創業, 郭柯, 劉高煥. 渾善達克沙地植物群落物種多樣性與土壤因子的關系. 生態學雜志, 2008, 27(1): 8- 13.
[17] 趙成義, 宋郁東, 王玉潮, 蔣平安. 幾種荒漠植物地上生物量估算的初步研究. 應用生態學報, 2004, 15(1): 49- 52.
[18] 劉速, 劉曉云. 琵琶柴 (Reaumuriasoongorica) 地上植物量的估測模型. 干旱區研究, 1996, 13(1): 36- 41.
[19] 馬茂華, 孔令韶. 新疆呼圖壁綠洲外緣的琵琶柴生物生態學特性研究. 植物生態學報, 1998, 22(3): 237- 244.
[21] 裴智琴, 周勇, 鄭元潤, 肖春旺. 干旱區琵琶柴群落細根周轉對土壤有機碳循環的貢獻. 植物生態學報, 2011, 35(11): 1182- 1191.
[24] 何玉惠, 劉新平, 謝忠奎. 紅砂灌叢對土壤和草本植物特征的影響. 生態學雜志, 2011, 30(11): 2432- 2436.
[25] 弋良朋, 馬健, 李彥. 荒漠鹽生植物根際土壤鹽分和養分特征. 生態學報, 2007, 27(9): 3565- 3571.
[26] 譚會娟, 賈榮亮, 劉玉冰, 趙昕, 李新榮. NaCl脅迫下紅砂愈傷組織中主要離子累積特征的研究. 中國沙漠, 2010, 30(6): 1305- 1310.
[27] 楊成龍, 段瑞軍, 李瑞梅, 胡新文, 符少萍, 郭建春. 鹽生植物海馬齒耐鹽的生理特性. 生態學報, 2010, 30(17): 4617- 4627.
Correlation between characteristics ofReaumuriasoongaricacommunities and soil factors in the Sangong River basin
ZHAO Xuechun1,2, LAI Liming1, ZHU Linhai1, WANG Jianjian1,2,WANG Yongji1,2, ZHOU Jihua1, 2, JIANG Lianhe1, LU Hongbing4, ZHAO Chunqiang4, ZHENG Yuanrun1,*
1InstituteofBotany,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100093,China2Universityof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100049,China3QingchengMountain-DujiangyanScenicSpotsAuthority,Dujiangyan611843,China
Reaumuriasoongaricai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distributed plant species in arid regions of China and ha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desert ecosystem. On the basis of field data, including the species composition, number of species, plant height, coverage and abundance, and selected soil properties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pH, bulk density and moisture content), the fine root biomass and aboveground biomass of twoR.soongaricacommunities in the Sangong River basin were investigated over the course of the main growing season (from June to October) of 2010. In addition, by calculation of derivative biodiversity indices comprising Pielou′s evenness index, Simpson′s dominance index, the Shannon-Wiener diversity index, and Sorenson′s similarity index,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ine root biomass, biodiversity and soil properties of the two communitie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rown area, coverage, abundance, species number, Pielou′s evenness index, Simpson′s dominance index, Shannon-Wiener diversity index, aboveground biomass, fine root biomass, and the soil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pH, bulk density and moisture content in the 0—100 cm soil layer of twoR.soongaricacommunitie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Except for soil bulk density, the values of all soil properties of Community 2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Community 1, and showed similar trends with increment in soil depth. Except for species number and Simpson′s dominance index, the other biodiversity indices decreased initially and thereafter increased from June to October, whereas the aboveground biomass and fine root biomass increased initially and thereafter decreased from June to October. Owing to the appeara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summer rain-dependent herbs in July and August in Community 1, the Shannon-Wiener diversity index and Pielou′s evenness index showed sharp reductions over the growing season, whereas Simpson′s dominance index showed the opposite trend. Compared with Community 1, Community 2 had higher soil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and soil pH, and few summer rain-dependent herbs, and therefore the Shannon-Wiener diversity index, Pielou′s evenness index and Simpson′s dominance index changed only moderately. In addition, Sorenson′s similarity coefficient was small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communities was significant.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oil properties were determinants of the differences in biodiversity and biomass of the two communities. High soil moisture content increased biodiversity, high soil bulk density inhibited fine root growth, and certain soil pH and soil salt contents promoted fine root growth inR.soongaricacommunities. We concluded that soil salt content and soil pH a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restrict biodiversity,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growth ofR.soongaricain the Sangong River basin. Differences in microenvironments, especially in soil characteristics, could induce strong differences in two communities with identical dominant species in the same climatic zone. These findings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e for management of naturalR.soongaricacommunities and rehabilitation of degraded communities, as well as for improvement of soil salinization in arid regions of China.
arid region;Reaumuriasoongoricacommunity; biodiversity; biomass; soil factor
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資助項目(2009CB825103)
2012- 10- 07;
2013- 03- 14
10.5846/stxb201210071379
*通訊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E-mail: zhengyr@ibcas.ac.cn
趙學春,來利明, 朱林海,王健健, 王永吉,周繼華,姜聯合,魯洪斌,趙春強,鄭元潤.三工河流域琵琶柴群落特征與土壤因子的相關分析.生態學報,2014,34(4):878- 889.
Zhao X C, Lai L M, Zhu L H, Wang J J,Wang Y J, Zhou J H, Jiang L H, Lu H B, Zhao C Q, Zheng Y R.Correlation between characteristics ofReaumuriasoongaricacommunities and soil factors in the Sangong River basin.Acta Ecologica Sinica,2014,34(4):878- 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