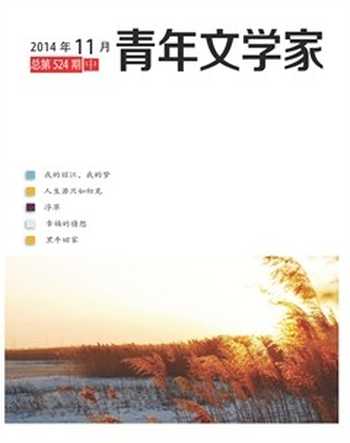福斯特小說中女性知識分子在文化聯結中的努力與困境
摘 ?要:愛德華·摩根·福斯特(1879—1970)是20世紀英國著名作家之一,其小說的特點之一就是將旅行中的英國知識分子置身于不同的“文化語境”中,不同文化間的聯結是他作品的主題之一,其中女性知識分子在文化聯結中的作用和處境又是他關注的重心。小說《霍華德莊園》和《印度之行》中女性知識分子在文化聯結陷入兩難處境:努力探索卻面臨困境。
關鍵詞:福斯特;女性知識分子;文化聯結;困境
作者簡介:何雙(1979-),女,江西分宜人,碩士,講師,研究方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工作單位:南昌大學科學技術學院。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4)-32-0-03
福斯特是愛德華時代的小說家,他的作品主要發表于愛德華時代,并對這個時代進行了觀察與思考。工業文明的沖擊使得“愛德華時代”處于動蕩之中,知識分子精英對象牙塔外的種種變化不可能無動于衷,誠如福斯特所言:“我不能把自己關在藝術之宮或哲學之塔里,而無視人世間的瘋狂與悲慘。”[1]
福斯特以跨文化視角在多部作品中探討了文化聯結主題。這種聯結愿望的達成常常又是以“婚姻”為載體的,正如文學評論家安妮·賴特明確指出,福斯特小說中的婚姻不是停留在表面,而是具有象征意味的一種尺度。在這“聯結”愿望的實現過程中女性知識分子有著非凡的地位和作用。他在作品中主要描述了女性在婚姻中的選擇與取舍,呈現了她們在文化聯結中努力探索和困難處境。
一
在《霍華茲別墅》中福斯特呈現了現代文明的尷尬處境:物質創造與精神生產的矛盾,工商業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沖突。
姐姐瑪格麗特是達成文化聯結愿望的使者。小說通過瑪格麗特和威爾科克斯的結合來體現這種聯結的實現,他們一個代表文化人,一個代表實業人。瑪格麗特清醒地認識到文化人的優越生活條件來自實業人的艱辛勞作,是實業人的物質創造奠定了文化人精神享受的基礎,文化人對此應該予以正視,而非對實業人嗤之以鼻。
在與亨利的交往中,瑪格麗特認識到物質與精神、金錢與文化間相互依賴的關系,決心把二者結合起來,試圖借助婚姻來企圖來彌補亨利身上的弱點:雖有“健全的頭腦”但道德上并非如此,而是膚淺、狹隘、缺乏想象力和同情心。他需要同情心和理解力,需要擁有精神層面來實現心靈的完整和人格的完善;同時瑪格麗特認為這也能給自己的生活輸入一些新鮮的空氣,那就是實業人士的能干精明!
顯然差別存在于瑪格麗特和亨利之間,鴻溝也存在于文化世界與失業世界間,而且妹妹海倫極力反對反對姐姐和亨利的結合,可是瑪格麗特終于跨出了“溝通”或“聯結”至關重要的、直面現實的第一步。
聯結的道路是艱難的。不僅瑪格麗特與亨利的婚姻遭到極大的反對,而且婚后兩人之間也并非沒有抵牾,亨利與瑪格麗特分屬不同的世界:生意人與文化人。自信又充滿活力的亨利雖然有著很多文化人所沒有的優點,但始終不能夠進入到瑪格麗特的精神世界中。瑪格麗特非常積極地投入到雙方的溝通中,為了能夠更接近亨利,精神世界遠遠豐富于亨利的瑪格麗特為了和丈夫取得一致的觀點,她常常隱藏真正的看法和壓抑自己的本性。即便如此,瑪格麗特努力追求的和諧并沒有收到相對的回應,亨利對他人的冷漠和自私自利也沒有因為瑪格麗特對他的寬恕和溫良而有所改善,連懷有身孕的海倫在莊園過夜他都不允許,瑪格麗特的努力最終也只是徒勞,彼此的分歧既來自不同理想和價值觀的矛盾,也來自男女不平等的社會傳統與現實。
《圣經》種下了西方社會男權中心的種子,認為女人是隸屬男人的,不僅體力不如男人,智力也要低于男人,她們的角色只是妻子和母親。男尊女卑是顛簸不破的“真理”,而且這種看法滲透了人們認識的意識深處。阿爾弗雷德·特尼森(Alfred Lord Tennyson)在其詩作《公主》中說:“男人耕作,女人炊煮;男人持劍,女人拿針;男人有腦,女人有心;男人發令,女人服從。”[2]維多利亞時代英國政治生活中雖然女王高居王位,但她作為女性發出的聲音卻十分微弱,因為活躍在政治舞臺的都是男性。在家庭生活中,丈夫是一家之主,妻子從屬于丈夫,妻子唯丈夫之命是從。即便是經歷了從19實際下半葉開始的爭取女性地位和權力的婦女運動,女性的地位和命運很大程度上有了改變,但是傳統的男權家長制社會卻動用一切手段來強化男性的地位,處處壓制女性,為此男子盡力剝奪女子的思維,要她們以為婦女應該是沒有個性、沒有自我的,更不可能有自己獨立的思想,而要達到和男性思想的交流溝通則是奢談。
瑪格麗特作為一位知識女性,她有自己獨特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信念,甚至精神境界要高于亨利,然而作為妻子的她按男權社會的要求是要絕對的從意識和靈魂層面完全服從丈夫,而不只是在形式上取得一致。試問作為妻子的瑪格麗特怎么能希冀通過“婚姻”來聯結自己和丈夫之間的世界?即便不存在文化與價值觀方面的差異,她也會遭到來自亨利所代表的男權文化的抵制。
瑪格麗特和海倫最終冰釋前嫌和好如初,她們重新審視了所發生的一切,最后善良的瑪格麗特決定繼續維持她和亨利的婚姻。有人認為福斯特所希望的“聯結”只是一種形式的慰藉卻沒有實質意義,也缺乏說服力。
在形式上終于保住了但在實質上顯然不能讓人信服。然而筆者認為瑪格麗特的妥協并不意味著是對文化藝術傳統的背叛,也非女性對男性的屈從,而是作為女性知識分子以其責任意識架起實業文化與人文文化、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聯結中付出的艱辛努力和面臨的艱難。
二
《印度之行》將人物置于更廣泛的國際政治背景,展示的是英國宗主國文化與印度殖民地文化間的沖突,作品以印度為背景,在這個宗教、種族、語言、文化復雜多元的國家展現了兩位英國女性為東西方文化的“聯結”、人與人真誠的“溝通”所做的努力與遭遇的困難。
殖民文化和印度文化間的沖突,作品以印度這個地域廣闊,宗教、種族、語言、文化多元化的國家為背景,表現了兩位英國女性試圖跨越東西方之間文化的鴻溝,為實現人與人之間真誠的“聯結”和文化的“聯結”而做的努力。
出身英國中產階級的阿黛受過正統的英國教育,具有人文主義意識,長得不漂亮,不夠有魅力,而且具有較強的自我意識和思考精神,嚴肅對待人生,并不把婚姻當成一種生活的手段,為此,從男權社會的標準來看,她并不符合英國淑女的標準,甚至可以說是男權社會的異類。
阿黛拉來印度是為了和未婚夫朗尼結婚,她和朗尼在英國已經訂了婚,彼此相處也很不錯。小說中作家將他們的關系放在印度,一個更為多元化、更為復雜的跨文化背景中,他們的關系會如何?阿黛拉將會如何面對異質的印度呢?
從小說的敘述中我們發現,福斯特以其敏銳的洞察力揭示了社會中女性低下的地位的社會現實。在英屬印度,英國殖民者尤其是男性他們根本無視印度女性的存在,她們只是作為母親和妻子存在于家庭中,在社會政治場合中,她們的存在毫無意義。雖然從種族角度而言,英國女性享有印度女性不可能擁有的特權,英國女性所面臨的處境比印度女性也好不了多少。
在馬拉巴洞穴事件中,阿黛拉是受害者,但大家卻把同情的目光投給朗尼,當他走進俱樂部時,所有俱樂部成員除菲爾丁之外居然都起立表示對他的理解和遺憾之情。作品這樣寫道:
Miss Quested was only a victim, but young Heaslop was a martyr, he was the recipient of all ?the evil intended against them by the country they had tried to serve. [3] (P192)
細心的讀者顯然清楚作者運用一種反諷語氣對俱樂部成員的心理進行描述。這句話中運用非常關鍵的兩個詞“only”和“martyr”準確地指出了男權社會中女性的地位。“only”一詞絕妙地淡化了阿黛拉作為事件受害者應得的理解和支持,并將其痛苦也忽視了。而“martyr”(受難者)一詞將最大受害者給了阿黛拉的未婚夫朗尼。可見,在男權社會中,女性只是作為男性的私有財產而存在,只是男性的附屬品。當女性受到傷害,人們只是覺得男性的財產受到了侵犯,而并不關注女性作為人被傷害,無視她們的感情、權力、身心被侵犯的感覺。
在英屬殖民地印度,女性也常常被認為是只需服從命令為英國殖民者統治服務的工具。當阿黛拉在法庭上于眾目睽睽之下撤回了對阿齊茲的起訴后,作者這樣寫道:
The Superintendent gazes at his witness as if she was a broken machine. [3] (P232)
我們看到在英國殖民者起訴阿齊茲的案件中,案件的重要“證人”阿黛拉被看做是“a broken machine”只是一臺“機器”,毫無自己意志和思想,只要按照英國殖民者既定計劃,聽從他們的意志和命令運行,就能達到他們以控告和懲罰印度人來加強他們的統治地位和優越感的目的。
當馬拉巴事件之后,作為殖民地的最高官員,特頓先生宣稱他要保護他們的女性,他這么做也只是為了顯示其所謂的男子氣概,他內心的真實想法卻是:……“After all, its our women who make everything more difficult out here” was his inmost thought. [3] (P217)
特頓作為英國男性,他的紳士教養讓他去保護女性,但在這個保護女性的紳士風度之下卻是他內心里對她們的怨恨。他恨女性的原因是因為她們并不情愿成為男性保護的對象,在他看來,阿黛拉就是這樣一個不愿生活在男性設定的圈子里而按自己意愿說話做事的女性。他甚至認為英國人與印度人之間糟糕的關系以及印度混亂的狀況阿黛拉是始作俑者,必須負責。
可見,在這種情況下,身處異質文化中,阿黛拉要去熟悉并了解印度這片陌生的土地以及這片土地上的東方文化,并試圖打通相異文化的融通,她所面臨的困難遠遠比瑪格麗特要大得多。面對英國夫人們對本地人的冷漠和歧視,善良的阿黛拉感到焦慮:“我聽說,一年之后我們都會變得粗暴起來。”她拒絕其同胞對她進行殖民意識同化:“我沒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我絕不應該變成這樣一種人。”“我要與我的環境對抗,去避免成為她們一類的人。”[4] (P165)當然,阿黛拉畢竟生活在英國殖民者之中,多少受本國人對印度人偏見和不信任思想的影響,因此她并沒有完全做好接收異質文化的心理準備,這也就成了她產生錯覺的心理因素。因此在游覽馬拉巴山洞時,她對阿齊茲產生了誤解,并狀告阿齊茲侵犯了她,導致了后果嚴重的“馬拉巴山洞事件”。但阿黛拉憑著自己的良知和勇敢在真相正義和謊言欺詐之間做了選擇,撤銷了對阿齊茲的起訴,哪怕是擔著被當作叛國者的危險。最終也取消了與朗尼的婚約。朗尼以印度執政官的身份來到印度之后,性格發生了很大變化,他自以為是和專橫無理,嫣然以大英帝國的忠誠衛士身份帶著種族偏見對待印度人。阿黛拉則愿意和印度人友好相處,真誠相待。文化價值觀上的巨大差異是兩人通向婚姻之路失敗的重要原因。
馬拉巴山洞事件是阿黛拉小姐的一次自我探索和自我成長,事件發生后她意識到“自我”的存在,主體意識的覺醒使她不再對婚姻抱有幻想,更不想因為婚姻使自己的自我附屬于男性的自我。徘徊在民主自由思想和殖民主義思想之間的她,最后撤銷了對阿齊茲的指控,避免了成為英印殖民者的幫兇,沒有成為英印文化交流的障礙。
阿黛拉解除了與羅尼的婚姻,成長為一個獨立的人,既沒有淪為男性的附屬,也沒有成為英印殖民者的幫兇。盡管在之后的日子里,她不是足夠堅強,但她敢于坦誠女性的不足和脆弱,直面壓力和誤解,按自己的思想奔向與過去不同的生活,她再也不是作為男性的附屬而存在,而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她自己而存在。作為一個男性作家,福斯特大膽地突破了傳統男性拯救女性的模式,女性自己能夠拯救自己。
至此我們發現一個問題:阿黛拉借助婚姻力量聯結不同文化的努力最終放棄的行為似乎與采取“聯姻之路”為求文化聯結這一目的相背離,其實不然,“聯姻之路”的取而又棄一方面反映了作家在不放棄聯結努力的同時對采取何種方式所產生的困惑,另一方面也說明了阿黛拉較之露茜和瑪格麗特的成熟和進步,反映了作家更深沉的思考。福斯特并不因為自己是男性作家就避諱呈現女性的自我斗爭,他并不害怕這樣會改變自己的自我意識。
福斯特常常將其作品中女性置于不同文化語境之中,描寫她們在為不同文化架起聯結橋梁途中的積極探索和努力追求,并試圖以“婚姻”為載體達成聯結愿望。評論界對福斯特以“婚姻”為媒介的文化聯結觀看法不一,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或肯定,或否定,或支持,或反對,我們對其聯結觀并沒有定論。難能可貴的是福斯特面對爭議,面對困惑,他沒有知難而退。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作家,福斯特努力的探尋著不同文化的“聯結之路”,并對女性知識分子在這聯結之路中的努力給予充分肯定,對其在聯結之途中的困境傾注莫大關注,給我們以無限的思考和警醒。
參考文獻:
[1]英國文學指南[M].鵜鶘書社.1978.
[2]陸偉芳.對19世紀英國婦女運動的理論考察婦女[J].研究論叢.2003(2).
[3] Forster,E·M.A passage to India[M].London:Penguin.1984.
[4](英)E·M·福斯特.楊自儉 譯.印度之行[M].上海:譯林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