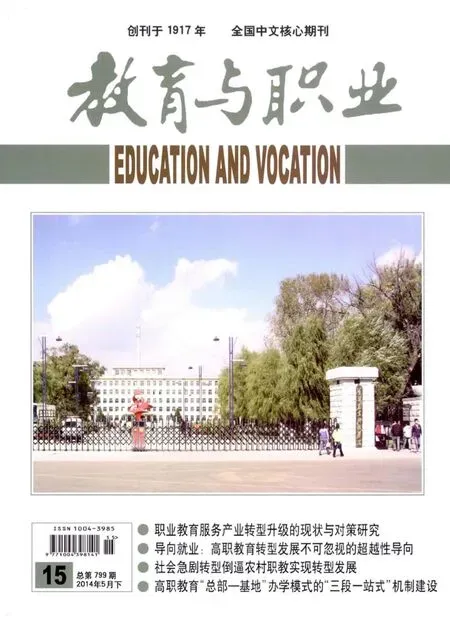符號化社會定義下的高校學生工作初探
2014-04-17 13:58:37徐保華
教育與職業
2014年15期
徐保華
一、符號化社會的二重解讀與高等教育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論述了人類社會從人與人的依賴轉為人對物的依賴、從而相對獲得獨立性的過程。毋庸置疑,我們已經處于一個社會生活高度符號化的時代,無論是社會管理、文化傳承還是消費行為、精神訴求乃至產品制造都被標上了特定的物質或精神符號。各種文化符號以意識形態的方式悄悄潛入大眾的生活中,維護著社會的發展,而人類個體就在與這些符號的碰撞中尋求認可,既有被世俗符號認同的渴望,又有被其定義的痛苦。
不同的理論家對符號化社會的看法不一。在悲觀的理論家眼中,社會符號被看作人的對立面規定著人的種種行為。比如鮑德里亞用符號編碼解釋和批判了人對物的這種消費性依賴,認為“符號的系統生產”在消費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人類在物的消費中不斷被符號腐蝕而異化。所以有必要對個體“進行消費培訓、進行面向消費的社會馴化”。而卡西爾在《人論》中的看法則相對樂觀,他認為“符號化的思維和符號化的行為是人類社會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只有把人定義為符號的動物,“我們才能指明人的獨特之處,也才能理解對人開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這里的符號被看作人類成長和進步的依托,人在社會符號中具有絕對主體地位,能主動借助符號構建語言、神話、宗教、藝術、科學和歷史的文化世界。
符號化社會的二重解讀為當下的高校學生教育工作提供了理論視角和借鑒思路。……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大科技·百科新說(2021年6期)2021-09-12 02:37:27
幼兒園(2021年6期)2021-07-28 07:42:14
好孩子畫報(2020年5期)2020-06-27 14:08:05
文苑(2020年4期)2020-05-30 12:35:30
小學生學習指導(低年級)(2019年11期)2019-11-25 07:31:48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6期)2019-07-24 08:13:50
小學生作文(中高年級適用)(2018年3期)2018-04-18 01:24:47
小學生導刊(2017年13期)2017-06-15 20:29:38
奧秘(2015年2期)2015-09-10 07:22:44
少兒科學周刊·少年版(2015年4期)2015-07-07 21: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