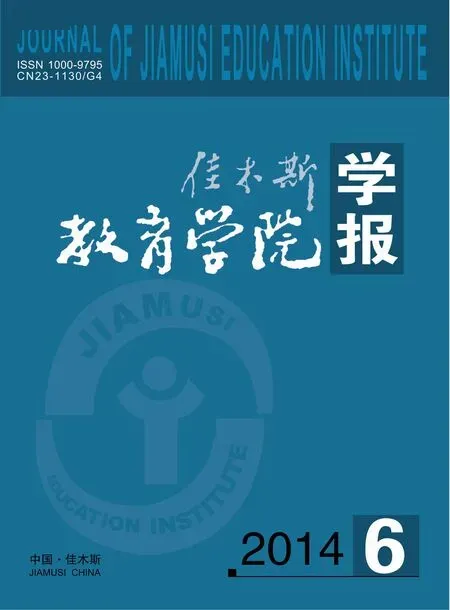《呼蘭河傳》中的視點反諷的三重表達
張宇男
(黑龍江大學研究生院 黑龍江哈爾濱 155800)
《呼蘭河傳》中的視點反諷的三重表達
張宇男
(黑龍江大學研究生院 黑龍江哈爾濱 155800)
本文以《呼蘭河傳》為個案,并通過雙重視點、視角干預等方面分析未能引起研究者重視的蕭紅的反諷性敘事。
視點反諷;兒童視角;視點干預
當代學者在關于蕭紅《呼蘭河傳》的研究上一直是圍繞著茅盾的序言“這是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凄婉的歌謠”做詮釋,將注意力更多的放在她的身世與創作關系,例如:自傳體、童年回憶錄、寂寞說,還有散文化的小說結構、兒童視角等方面上,并認為這是蕭紅在即將離世時對遙遠故鄉的溫情回想,是她理想中家園景觀的一種寄托。
然而,就我個人的閱讀體驗而言,初讀《呼蘭河傳》體會的是作者對風俗畫的描寫,是對故鄉的眷戀;再度體會到作者求而不得、思而不往的無奈與寂寞;三度體會到了通過反諷敘事而表達的作者理性批判的態度。1940年創作完成的《呼蘭河傳》正是因為它敘事的反諷性而常讀常新,也正是因為它的耐讀,才成為了蕭紅(1911—1942)個人最重要的代表作,而且也是20世紀中國現代小說史上的一部經典。
理性的批判與情感的懷戀之間的交織,批判不是最終的目的,對讀者靈魂的詩意觸動才是蕭紅的反諷修辭的旨歸。蕭紅在《呼蘭河傳》中是以“同是天涯淪落人”的身份,對病態的民族文化心理和丑陋的靈魂做了文化批判。
一、關于反諷的界定
反諷是小說中最常見的微觀修辭技巧,具有意婉旨微而又深刻有力、耐人尋味的特點。但因為至今還是一種發展中的技巧和方法,因而很難對它做精準的界定和理論把握。
綜合趙毅衡、李建軍等學者的界定,以及對于文本的反復體味,對于“反諷”我也做了自己的判定,認為:反諷是在旨意上較嘲諷柔和,又比嘲諷更趨于暗示、婉轉的一種間接性諷刺手法。它是讓作者的態度不做直面抒發但通過某些線索又能使讀者朦朧的體悟到作者批判態度,并通過潛在的反諷消解顯在的主題意向并形成一種張力性修辭、敘事手法。它包括回避直接陳述、言意悖反、需要讀者參與等特點。
于是,下文就將繼續闡述敘述者是怎樣在表層結構的下面流露深層內涵的。
二、成人、兒童的雙視角敘事
視點反諷在于視點的特異性,即“敘事通過異常、獨特的視角展開,從而具有了勘測普通視角無法觀照的殊異風景的能力。視點反諷依靠的就是異敘述者的異常敘述。”例如:一個小孩子看到的事情完全不同于成人,一個瘋子、傻子、甚至動物的特殊視點展開的敘述肯定偏離正常的敘事,這就會形成反諷。簡單地說,敘述者就是作者在文本中的心靈投影。
成人視角比較好理解,比如文章中第一章第三節中,描寫了眾多人的死亡,人們看見這樣的人,既有惻隱之心但又覺得這樣的人太多可憐不過來,于是又冷漠了。人們的生老病死就像四季的春生秋落一樣,默默的交替著,惹不起半點漣漪。讀者的閱讀期待是本以為在這樣的死亡面前,敘述者的態度應該是悲憫、同情、憤慨的,然而《呼蘭河傳》中的成人視角敘述卻是類似零度敘事一樣不動聲色的、平靜的、可觀的,于是在讀者的閱讀期待和實際敘述中產生了錯位,生成離間效果,這本身就是一種諷刺。
而兒童視角的運用,在《呼蘭河傳》中則是一個亮點。所謂“兒童視角”,簡而言之,就是用童眼觀看世界,用童言言說世界,用童心感受世界。
蕭紅通過兒童視角,在天真和疑惑的發問中,完成了對成人世界的拷問。他們為什么輕生重死,對別人的死能夠有看熱鬧那樣輕松的態度,卻又對給死人扎紙人那么熱衷?走出文本,身為讀者的我們會感到,這種情境恰如《皇帝的新衣》中說出皇帝什么衣服也沒有穿的小孩。“我”是如此直白地說出了我的困惑,我不明白為什么如此明了的事實在大人那里卻很是不清楚,甚至在“瘟豬問題”、“小團圓媳婦生病”問題上,他們也不愿意讓一個孩童幫他們找出真相。
例如,第五章的描述中,大家都爭先恐后的湊熱鬧去看小團圓媳婦,兒童視角的“我”自然也央求祖父帶我去。在小團圓媳婦的故事里,女童是惟一與眾不同的觀眾,“與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沒有什么好看的,團圓媳婦在那兒?我也看不見,經人家指指點點的,我才看見了。不是什么媳婦,而是一個小姑娘。”可見,在兒童視角對于“小團圓媳婦”這一身份的消解,“我”認為她是小姑娘不是什么媳婦。
在《呼蘭河傳》中,作者蕭紅將自己裂變成成人敘述者和兒童敘述者兩個敘事人,也就用兒童視角和成人視角的雙重敘述方式,使文本呈現出一種復調的詩學意蘊。兒童視角因其立場的邊緣性、情感經歷的原始性,她所感受的世界與所做的情感評價都將與小說呈現出來的客觀現實之間存在著一定的距離。又為了避免讀者將作品當作非反諷故事來閱讀,作者在再現童年生活的過程中又適時地介入了成年人的身份來干預兒童視角的敘述。
三、敘述視角的干預
作者的反諷性的敘述還體現在敘述視角干預、越界上。文中在塑造小團圓媳婦的婆婆這一人物形象時,就有明顯的視角越界。
例如,來個云游真人要給小團圓媳婦抽帖,婆婆想“這倒也簡單、容易,想趕快抽一帖出來看看,命定是死是活,多半也可以看出來個大概。”當聽到每帖十吊錢的時候,她的心理經過了用十吊錢買豆腐、養口豬、買雞等等的“發財夢”的如意算盤。
但是,前文已經闡述過,小說從第三章開始,敘述視角就由全知視角轉換為童年的“我”,即兒童視角。按常規來說,抽帖時婆婆的心理活動,作為局外人、作為看客的第一人稱敘述者“我”是無法知道的,更無從知曉她從前養雞的艱辛。那么顯而易見,此時的敘事策略,就有從第一人稱的限制視角向第三人稱全知視角的侵入,因為只有第三人稱全知視角才有這種洞察別人心理活動的權力和能力,通過這樣的視角干預,有利于作者更為深入地剖析人物的內在心理。
反諷以委婉隱幽為主要敘事風格,通過巧妙的暗示,把事實的真相或自已的態度暗含在似是而非的假象以及含混的陳述之中,讓讀者透過表象去領會其中的深層含義。
四、反諷性評述
雖說小說是虛構的藝術,是由作者虛構的敘述者,闡述的一個虛構的真實。然而,在《呼蘭河傳》中,我們隨處可見作者的聲音。那些看似漫不經心的只言片語暴露了作者的蹤跡、泄露了作者的態度傾向。例如:
第一章第二節,先有一個哲理性總論:“一年四季,春暖花開、秋雨、冬雪,也不過是隨著季節穿起棉衣來,脫下單衣去地過著。生老病死也都是一聲不響地默默地辦理。”(P104)作者蕭紅以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輪換,來對應人的生老病死的生命輪回,以一種最為簡單、粗礪的形式傳達出鄉村不過是毫無意義的“生死場”,沒有變化,沒有希望,有的只是人的生存的悲哀和生命的荒涼,進而直指人性的荒蕪和靈魂的死寂。
“荒涼”這個詞在第二章中頻繁出現,并且是從該章第二節到結尾第五節的每一節的開頭,可想而知,“荒涼”這個詞所要傳達的深意是必須引起讀者重視的。那么試問,一個整天在后花園中玩耍,黏在祖父身后的小女孩,如何能夠感受到當時的家是荒涼、是空虛的?那么文中的這些聲音又是由誰發出的呢?顯然這是出自作者之口,是作者時不時的跳出虛構的敘述人身份而發表作者自己的評論。出現作者聲音的原因,究竟是一種敘事策略還是作者的繾綣之情難以自掩的一種體現?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就這種現象本身而言還是非常耐人尋味的。
錢理群說:“這樣的批判性的審視,顯然不屬于前述兒童的眼光;這是成年人的敘述對兒童視角的一種干預,讓讀者身入其中,又出于其外,這‘進(入)’、‘出’,‘內’、‘外’之間的就形成了一種張力。”
其實,作者運用反諷并非要掩蓋自己真正的意思,相反,它是以一種更隱蔽更高明的方法來吸引讀者的閱讀興趣,帶領我們積極追尋自己的真實意旨,以享受更多的閱讀樂趣。在議論中所流露出的作者情緒,并非是要控制故事的發展或走向,而是一種介入的方式,是一種模棱兩可的敘事態度,是隱含作者對所敘之事的反諷。
[1]陳振華.小說反諷敘事:基于中國新時期的研究[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3.
Shallow discussion the hulan river "the irony of the triple expression of viewpoint
Zhang Yu-nan
(Graduate School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155800, China)
This paper takes the hulan river as a case, and through the double point of view, the respect such as Angle of intervention analysis failed to sexual narrative irony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researchers of xiao hong.
Viewpoint of irony; Children's perspective; A viewpoint intervention
I207.4
A
1000-9795(2014)06-0105-02
[責任編輯:董 維]
2014-03-11
張宇男(1989-),女,河南洛陽人,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方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