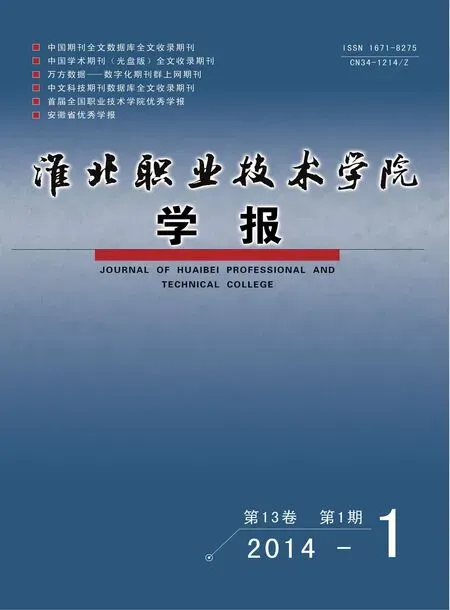關于“中華宗教詩學”概念的提出及思考
張兆勇,李群喜
(淮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安徽淮北 235000)
·文學藝術與歷史文化研究·
關于“中華宗教詩學”概念的提出及思考
張兆勇,李群喜
(淮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安徽淮北 235000)
“中華宗教詩學”指幾千年來以詩承傳的中華根本性民族精神:憂患、知恥、奮進、慎思。這種宗教的根本性在于它既不同于佛教,亦不同于道教,與儒家道統(tǒng)亦有區(qū)別。而宗教詩學指士人把詩作作為他特殊的傳導方式和批評方式,它應從先秦孔子“刪詩之旨”即很成熟,此后各代均有自己變現(xiàn),宋代士人又對之進行了內涵與方式的再完善。
問題域;本根;綿綿一息;圣證
所謂“中華宗教詩學”是指幾千年來以詩承傳的中華根本性民族精神及對之的研究。從宗教角度說,它既不同于道教,亦不同于佛教;從道統(tǒng)角度說,它與儒家道統(tǒng)既有聯(lián)系,亦有區(qū)別。它有著別樣潛行與生命力。
其實,這不是新鮮概念或命題。因為與之相關的幾個概念幾乎也是二十世紀西方文化反思的主旋律,例如:文化本質、人的本質、人的家園、人行為的動因、人生價值標尺等。西方既重新審視了這些與宗教的關系、重審了宗教的意義,也重審了詩的意義,詩之于宗教的關系等。
于是,越來越多的西方學人在他們的思路中往往將文化——宗教——詩聯(lián)系在一起,從文化角度或更精細地從宗教,依著宗教心理狀態(tài)、宗教的途徑來定位詩的價值,詩之于人生本質的意義。總之,依此種方式研究詩是二十世紀學人普遍的興趣點。
假如我們將此稱為“宗教詩學”問題域,那么這個思路框架、架構取向能否挪移至中華,從而展開對中華詩壇考察,對中華詩的宗教意義展開探尋?這實在是一個卓有探尋意義的問題。
前些年拜讀過張志剛先生的《宗教文化學導論》[1],他斷言宗教與文化聯(lián)系研究已經(jīng)到了展開研究的時候了。在我們看來“展開研究”除了要借鑒二十世紀西方學人的思路,還應考察在我國五千多年中華文化里宗教與詩的關系,我們的前人對此的傾訴暨對此豐厚不懈的實踐成就。關于此,至少可以從以下問題展開:
什么是中華本根的宗教精神?詩在展衍本根宗教時其角色定位,其特色何為?
中國大量詩論對此是怎樣表述的?它們的展衍、啟示、遮蔽應有什么樣的呈現(xiàn)?而先后所起的道、釋對照之又應歸屬為什么性質?中國詩論所體現(xiàn)的宗教性在釋、道這里又有哪些展衍與分工?它們與中華本根宗教承傳有哪些不同?在筆者看來,所有這些均應是“展開研究”關乎中華“宗教詩學”的問題域。
一
不必諱言,以“宗教詩學”命名引發(fā)當前中國傳統(tǒng)詩學研究易產生許多領會上的歧意。就當前的學術界看,在不同的領會歧途均已有學人研究且有豐碩之果。
首先,在文獻層面,指關于宗教人(包括佛教、道教信仰者)所創(chuàng)作詩的文獻整理,宗教人的身世研究。這些在學界一直均是熱門話題。
其次,在關乎宗教的詩歌藝術價值評估方面,包括對不同身份的詩人所創(chuàng)作的涉及宗教(包括對佛、道甚或其它教派)的詩進行整理、評估。這也是學人研究的熱點。
再次,在理論層面,指針對以宗教思維、宗教方式、宗教價值趨向來指認、定性、升華詩的特征、規(guī)律、審美評估等理論的研究。尤其在于,假如我們把詩的定義泛化一些,這一理論研究范圍實際上涵蓋了畫論、樂論、書論、詩詞曲論等的遺產。
其實,筆者想要說的是,宗教在中國當然包括道教、佛教,誠如許多學人所概括的那樣: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神傳衍雖有眾多因素,但不能離開有一根本性的宗教意識支撐。①二十世紀以來西方不同層面上的學人均分別承認了文化與宗教的依存性,②宗教對科學的原動力,③我想對一個民族來說可能更是指這種宗教。
而對中華來說,這一根本性宗教顯然不能就是道教或佛教。這一根本性宗教是什么?它的方式、思維方法、價值趨向,怎樣引領著詩學、凝聚詩性精神,怎樣滲透于詩學?顯然所謂“宗教詩學”其更本質、更值得探尋的問題應在于此。如此說來,所提出“宗教詩學”者,若把它作為理論命題,那么其所涉獵至少有兩個層面上的問題。首先即關于道教的、關于佛教的、關于道統(tǒng)的俚清。除此還有更深更重要的層面,即民族宗教精神的開掘。而對于“中華宗教詩學”來說,只有兩方面綜合才能是它的合理架構,尤其是第一個層面中儒、釋與道統(tǒng)三方面研究結合在其相比中見出各自的特點,才能突顯出另一層面的民族真精神,從而把握宗教詩學的真命脈。
二
從中國學術史上,我們知道從宋代起中國士人在談論自己綿綿一息的中華民族精神內質時喜歡就三個命題展衍它們時而單線、時而交錯的思維軌跡。它們是:
①所謂十六字的心傳,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大禹·謨》)
②所謂天人合一觀念:“萬物負陰而抱陽,充氣以為和也。”(《老子·四十二章》)“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盡心上》)
③孔子的感慨:“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
針對于此,我們發(fā)現(xiàn)有這樣一些特點能概括宋代以來士人對這三個命題的深沉關切:
①宋代士人越來越滋生維護其自覺的立場。所謂從宋代開始,并非說以前沒有,而是指宋代的士人越來越以自覺而呈其特征,越來越以自覺去以養(yǎng)護。其表現(xiàn)出的敬仰、誠信、從容等心理狀況,尤其見出對此大宗教的至誠。對于此,如果將張載的“四為”姑稱為儒者宗教“四句偈”,④那么大程《識仁篇》⑤又經(jīng)典闡發(fā)了什么樣才能是真正的仁者,尤有宗教意味。
②宋代士人進一步突顯其以“道心”并加以充實其內含,進一步努力將三個命題加以熔煉,以作為支撐其框架。經(jīng)過熔煉宋人發(fā)現(xiàn)天地精神作為“道心”主要取其勁健、寬容、自強與厚載。而我人的態(tài)度:憂患,崇仰,安穩(wěn),宋代士人發(fā)現(xiàn)華夏詩人的魅力在于經(jīng)常以其獨特唯一表現(xiàn)對其感受。此也應說是詩的魅力,或云詩之宗教性。
③宋代士人普遍是用濃郁的還原思維將天、地、人溝通,并以此作為“道心”的背景。從而在這個意義上進一步總結陳述“道心”的人文審美特征,比如:無言、蕭散、外枯中膏等人文特質,從而使其主體化。
我們不難感受到宋代學人在展開這些思路時所由衷流溢的是其敬畏、崇仰、優(yōu)游、自信的心態(tài)。而這正好才是大宗教的情懷。如果說,宋代士人將這種心態(tài)深深地扎到先秦儒道先哲,實現(xiàn)著所謂儒道互補;扎到了禪門,使后人能反觀他們透亮靈澈的心愫,那么這種心愫最終又實現(xiàn)在生活中、在藝術創(chuàng)造中的軟著陸。這也是宋代士人的創(chuàng)造性。在此完全可結論為:宗教文化化、文化世俗化、世俗詩化。終于在宋代道學這里宇宙之間僅存唯一一種懷著感激的人生態(tài)度,此即宗教心態(tài)。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張載《西銘》(即《正蒙·乾稱》首段)以精湛命題,千古一息,往上通達著《論語》上太多的箴言,所謂“君子和而不同”(《子路》)所謂“道之將行也與,命也。”(《憲問》)“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
在本文中,我想要表達的是對“人心惟危”根本性的憂患應看成是中華這些心態(tài)最本然的宗教意念背景。只有把宗教詩學定位到此,定位為關于此的詩性精神的承傳上,才能理順、彰顯它的魅力,體悟到它“無待”的生命特質。
從詩史上看,事實上亦是如此。從孔子的刪詩之旨,到漢樂府的不絕如縷,再到《古詩十九首》的驚心動魄,此后各代一直在倡言道統(tǒng),追問道心,各代的那種深悲極樂,所謂“流水淡,路茫茫,憑高目斷,鴻雁來時,無限思量。”(晏殊《訴衷情》)那種義無反顧,那種悲壯,所謂“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晏殊《浣溪沙》詞)總之,宋代人想要感動人的和能夠感動人的差不多均在于此。而把握中華宗教理應到此查詢與守候,比如說從北宋末開始,廣大士人雖既已忿憤著江西詩派的過于文字、議論、典故,但南宋朝士人始終沒擺脫敬佩山谷及追隨者所承傳的刻意性。尤其敬佩這種承傳的刻意以至于詩的“活拔拔”,其原因即在山谷將生活悟道為詩,能以至于高絕。
在我們看來,山谷詩的魅力恰在于是真正以此貫徹了華夏真宗教和憑其尖新、忌俗觸及著中華宗教詩學所應涉及范圍,應是體驗與關涉、宗教與詩學、心靈與物化的完美實例,這應是受到景仰的原因。
所可慰藉的是對這一宗教的關切,對此宗教詩性的挖掘以及詩學意識構建,歷史上從來沒斷線過,而是“金線暗隨鴛鴦浴”,尤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五祖法演語)像歷史上的鐘嶸,陳子昂,李、杜,韓、柳,張戒,一直到王船山等,他們均是維護著詩性精神的典范,正是有這些學人的卓越成就,才使中華詩學有濃郁的宗教性。在這一點上,船山是后起的,也是一個卓越的終結者。從他的《畺齋詩話》到三本詩的評選均在貫徹著對詩性精神的找尋與維護,⑥從中能感到他找尋的艱辛,獲得的深刻孤獨。
綜上看來,宗教詩學實際是非常廣義的概念。它理應跨越中國的道教、佛教,但它更包涵著儒教的中華根本性宗教。就這一點來說,結合歷代學人的心靈感悟,本文或可以做如下總結以作為本綱要的總結。
1.中華學人曾成功地利用道教概括過他們對詩、詩人的把握,比如司空圖、白玉蟾、朱權等。
2.中國學人也曾成功地利用佛教概括過對為詩的領會,如中晚唐以皎然為代表的系列僧人,宋代以后以禪喻詩、以禪喻畫,所編織的太復雜的詩道與佛禪的關系。
3.相比之下,中國學人更是在華夏民族根本性宗教的意義上體現(xiàn)著宗教的心態(tài)。并以此心態(tài)創(chuàng)造了、建立起與詩的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從而表現(xiàn)出中華士人的最根本志趣。這也正好在這個意義上,完好地保持著刪詩的尊嚴,體現(xiàn)著詩——宗教的綿綿一息。
而所謂建立“中華宗教詩學”同時兼顧著三個層面,即是洞徹關于宗教的定義,關于詩的宗教定位,關于歷史上儒釋道三家分擔的角色。如果說要營造中華宗教詩學,顯然三個層面要同時兼顧。而它的價值與意義在于,只有如此才能將關于“中華宗教詩學”命題以立體思維落實到它的主題思維,它的真背景上,才顯得不空洞,才能在立體思維的相映之中建立起關于中華的宗教詩學理論來。
三
以下筆者想按照這個思路試著將中國漢代以來關于詩學名著作粗略的排隊如下:
首先,具道教傾向的有:
(1)《列子》(2)《高士傳》(晉皇甫謐)(3)《抱樸子》(晉葛洪)(4)《二十四詩品》(唐司空圖)(5)白玉蟾(南宋)(6)《太和正音譜》(明朱權)。
其次,具佛教傾向的有:
(1)宗炳《畫山水序》(六家七宗的支道林、慧遠均具有影響力的相呼應篇什)(2)王維(皎然、齊己、貫休、遍照金剛諸篇,均可與王維媲美并全面鋪開了佛學詩觀)(3)五祖法演(4)趙孟頫(5)董其昌(6)王漁洋。
再次,傾向于玄學的有:
(1)竹林七賢諸篇(2)陸機《文賦》(3)鐘嶸《詩品》(4)劉義慶《世說新語》、劉邵《人物志》(5)謝靈運《與諸生辯道書》(6)昭明太子《文選序》。
第四,傾向于儒家的有:
(1)《詩大序》(《琴操》與之相近)(2)陳子昂《修竹篇序》(3)李、杜風雅論諸篇(4)韓、柳、劉道統(tǒng)諸篇(5)柳(開)、石(介)、胡(瑗)道統(tǒng)呼吁與歐陽修的再倡導(6)蘇、黃道學(7)從陳師道到呂本中、南宋四大家的江西詩派之論(劉克莊、蔡正孫、方回的江西再論)(8)嚴羽“第一義諦”與張炎“騷雅”(9)朱子“道心”,范成大《梅》《菊》二譜品質探(10)明人“正統(tǒng)”爭議(11)王陽明為詩心路(12)清儒在詩上、詞上對本真前赴后繼的求解(13)龔自珍《夜坐》:“春夜傷心坐畫屏,不如放眼入青冥。”
龔自珍《己亥雜詩》:“陶潛酷似臥龍豪,萬古潯陽松菊高。莫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騷。”
上面列舉應是對中國《詩大序》以后詩學名著的大概羅列。在我們看來,第一類傾向于道家者,主要是指在這些著作中從不同側面反復描摹了道家羽化的風度與風范。他們的描摹經(jīng)常被用來作為詩人心期的境界與感覺,因而有引導詩人的文論意義。當然關于此可以追蹤至《老》《莊》,但像上述這些所起的是更具明確意義的道教中介推進,并且各有其特點,自然不能忽視。
第二類傾向于佛學的,如果不整理一下,還覺得佛禪與中華文論的滋長很密切,但真的整理就不難看出,佛禪對中國文論影響其實很小、很少。它差不多又可分三個系列:
一者,即宗炳等對佛影、傳神論的引鑒。二者,貫休、齊己、遍照等的登堂入室思維。三者,即以王維為開山或被推為開山,以禪悅、禪照、禪境來隱喻詩作、詩境、詩韻。從董其昌到王漁洋,他們又創(chuàng)造性將上述幾方面結合一起,尤其是引司空圖、嚴羽的加入充實及引中唐即有的登堂入室思維成為一個有影響的詩論支派,這一派的影響還表現(xiàn)在對繪畫的批評上,促成詩畫批評聯(lián)璧。
和道家、釋家相比,儒家顯然泱泱大觀。但要摸清儒教的真面目,正要將其放到以下幾個層面上:
首先,從《詩大序》以來,風雅、道統(tǒng)與政治性的膠著倡論往往是風沙俱下。雖表現(xiàn)著儒家的浩然豪氣,卻忽略了在細部舒展的內在性及審美情操,因此往往不能最終導致心與心的相溝通。
其次,是從玄學層面。它的建設性在于是“人的自覺”后對《詩大序》的形而上的再擴展,要么從建設,要么從梳理,要么從整理維護。一句話,玄學走完了一條曲折的以“玄對山水”“目擊道存”的體道之路,從中雖體現(xiàn)著儒者精神,但內涵缺充實。
再次,自北宋道學以來,道學學人幾經(jīng)努力,找準主體抒情切入角度,找準了敬畏的靈性儲備,找準了歷史上此敬畏之心傳播的綿綿一息。他們既按照這個思路對中華詩人進行精確分析,也有意識在這個意義上有意做大、做強以體現(xiàn)自己的時代精神。
到此,筆者想要說的是,若要建立“中華宗教詩學”,首先要在不同層面上將中華文論諸篇還原它本來的意義,還原它所處的歷史環(huán)節(jié)。其次本著中華宗教找到它們在詩論上的變化與所藏。特別是能以領會孔子的以“興、觀、群、怨”展開的刪詩之為作為思維背景。
其實,關于“宗教詩學”確立歷代學人在理論層面已篳路藍縷,是他們發(fā)現(xiàn)同時他們自己亦在傳遞、秉賦中華詩教的正脈。比如,阮籍《樂論》,鐘嶸《詩品序》,李、杜的風騷論,蘇、黃“韻味”,張戒的杜甫情結,最終以朱子“道心”到王船山“圣證”說:以上即是試列舉一些略其印跡。
而從詩的創(chuàng)作層面說,《古詩十九首》、曹子建、陶淵明、老杜、韋應物又是被學人反復推碑的精華。筆者最后想說,在學人眼里并不是其他詩人不好,而是說上述更是圣證。他們具更純真的憂患意識,他們更顯活潑自在的生命情結和生命境界。這個境界從心的層面叫“道心”,從人格層面叫“外枯中膏”,從與自然交融角度叫“蕭散”。顯然,中華宗教詩學研究最終應定位于此,聚焦于此。學人體悟到此即體悟到關于宗教詩學的“圣證”。
注釋:
①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海森伯說:“宗教是倫理學的基礎,而倫理學則是生活的先決條件。”愛因斯坦也認為科學只能斷言“是什么”,而不能斷言“應當是什么”。
②美籍德國神學家蒂利希認為“宗教是文化的本體,文化是宗教的形式。”
③德國物理學家普朗克云:“人需要自然科學是為了認識世界,人需要宗教則是為了行動。”愛因斯坦說:“在我們這個唯物論的時代,只有嚴肅的科學工作者才是深信宗教的人。”
④即著名的張載“四為”。見《張載集·張子語錄》卷中。
⑤即“學者須先識仁。”見《二程遺書》卷上。
⑥即王船山《古詩評選》《唐詩評選》《明詩評選》。在三書中的不同之處,他對從《古詩十九首》、曹植、杜甫、韋應物等的詩性承傳做了艱苦搜尋。
[1] 張志剛.宗教文化學導論[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責任編輯:張彩云
I207.2 I207.99
A
1671-8275(2014)01-0024-03
2013-12-23
張兆勇(1965-),男,安徽五河人,淮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與傳統(tǒng)文化。李群喜(1988-),男,安徽太湖人,淮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文藝學專業(yè)2012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