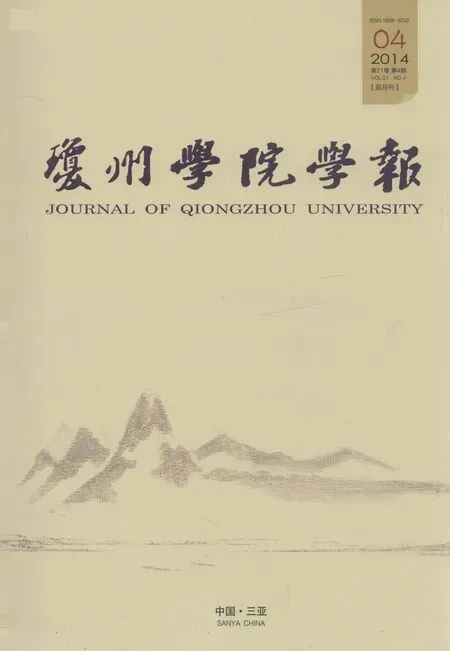整體的流變的大文學史觀
木 齋
揮手之間,來美國普渡大學已然約略百日,寓舍于普渡村。學術之余,每日晨夕,種地澆水,過上了“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的生活。此地治安甚好,往往不需荷鋤,只是攜著剛剛采摘的瓜果菜蔬,在夕陽暮色中穿越荒蕪蔓草,緩步而歸。悠然之間,時時感悟人生,細細反思學術,亦時有所得。以老邁駑鈍之軀,晨曦閑暇,三月之間,瓜果菜蔬,可以供給一家數口之需,而余之古詩研究,嘔心瀝血,迄今已十年矣,緣何收獲甚微?或云:先生所云過矣,自數年前《社會科學研究》首開專欄討論以來,以古詩研究為中心討論之專欄,凡幾近十種,論文近百篇,且正有星火燎原、方興未艾之勢,影響不可說不大,成果不可謂不豐,緣何仍有此嘆?
平心而論,余之所得,皆源自于嘔心瀝血,昌黎《進學解》曾描述其學問之甘苦:“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余之探索歷程,有過之而無不及矣!其所論證,皆無空言,而文學史的闡發,不僅依然故我,而且,在某些學者眼中,這種顛覆性研究,無異于異端邪說。余雖在海外,依然能感受到某種黑暗濃重的霧霾,在深深地,而且是日益深重地壓迫而來。
我深深感到,學術研究再難也不難,只要有正確的方法論,學術難題無不可破譯。學術之難,其難在于接受。每個學者在長時期的學術歷程中,均已形成自身的一套方法論,并由之產生的學術理念和觀點,面對顛覆性成果,不能接受,這是自然的現象。而年輕一代的學人,由于觀念尚未凝固,反而容易接受新的理念。某些學者,特別是專治漢魏六朝一段反而不能接受的學者,與我和宇文所安先生等發出不同聲音的學者而言,其根本的分歧,正在于我們用的是不同的方法論,采用不同的語言系統,由此產生了讀不懂,或是字面讀懂,內在涵義不能相通的情況。與此相反,一些年輕學者,反而顯示出來更為敏捷的思維,寫出了非常之多的優秀篇章,令我為之欣喜。
近日在普渡大學,手頭資料匱乏,有閑暇網上閑看,偶然看到這樣一篇短文,文章并未屬名,似乎是聽我講授過課程的學生,文章寫得真實、具體、細致、生動,特別是寫出了接受新觀念的過程。由于沒有署名,也就不能提前通告引述,但也正由于為無署名之文,方才更為真實,更為不具功利性。文章轉引如下:
以往十幾年做學生,我總結出這樣的經驗,一堂課開始時老師如果告訴我們這節課講述的題目,那么在將題目寫在黑板上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等著老師把以形成共識的觀點平鋪直敘地講給我們聽,而我需要做的就是盡量把我聽到的東西都記在筆記上,如果對自己要求高一些的話,就需要一遍一遍的看筆記,把老師說過的東西理解記憶,于是,類似的東西日積月累,便形成了我的基本知識儲備。但是,一遇到木齋先生,我在聽過幾堂課之后,發現我的確應該轉變思維方式了:
在木齋的一門《聲詩曲詞發展史》的課堂上,我連續好幾次被自己的思維帶跑,這里只簡述其中一個環節。開始,木齋跟我們講“研究詞的起源,不能不清楚中國古代音樂的發展史……”,這一論點我很贊同,詞本來就是古代的流行歌曲,為了研究詞的起源,清楚當時時代的音樂發展狀況,實在太有必要了。于是,我欣欣然地往下聽,老師這樣說中國古代音樂發展演進的大概過程是:雅樂——清商樂——燕樂三大階段,雅樂產生了詩經,清商樂產生樂府五言詩,燕樂產生詞等等,我聽到這里大為興奮,通過對文學的了解,再通過音樂和文學之間密不可分的聯系,一下子覺得古代音樂發展史也光榮的進入了我的知識儲備,并且脈絡清晰、簡單易懂,就飛快地記著筆記。當我享受不求甚解的輕松時,老師一下子話鋒一轉,舉出大堆的史料對該說法提出疑問,在我看來沒有絲毫紕漏的一條觀點,竟然被老師分析出七個疑點:如,唐代之前是否有燕樂存在,如果有,那與唐代的燕樂區別在哪?外來的胡樂怎樣影響了中原本土音樂,并且如何影響古代各個時期主流音樂的發展?等等,我停筆一想,的確是這樣的,這七個問題沒有一個是不需要回答的,沒有一個是沒有意義的,傳統觀點認為,燕樂產生詞體。而此燕樂的解釋是唐代入了中原宮廷的胡樂,而在先秦周代,也存在一種音樂叫燕樂,此燕樂和彼燕樂的區別在哪?既然共用一個名稱,那后世在概念的流傳中是否有很多被混淆的地方?這樣說來,我們一直真誠信奉的詞體起源問題并不是個簡單的問題,要回答它,需要厘清的概念太多太多了。受限要對很多現象的名稱有個清晰的界定,界定概念是非常不容易的,要在種種有限的線索中嚴謹的思考、推論,在這個過程當中,也許會有很多被前人遺漏的線索被發現,為什么當時我只知道把結論記下來,這些很實際的問題卻沒有思考?這時候,我回想起剛才接觸以上結論時思想意識里的“點頭哈腰”,不禁一陣臉紅。后來在老師的一一論述下,這些問題都一一厘清,古代的音樂史,其發展面貌同樣是立體的,縱橫交錯的,在復雜的脈絡里有主流,也有分支,分支在新的社會綜合因素的作用下會轉化成主流,以往的主流也許會退居支流,只是很多年后,會在吸收很多外來因素之后重新變成主流,但這絕對不是歷史的倒退,而是否定之否定的提升。我們明明在哲學的方法論里清楚這樣的原理和方法論,可是在學習的時候卻還是希望歷史是單線的、平面的、遞進的簡單程式化方程,好便于記憶和傳播。但是,可怕的是,學術問題是環環相扣的,我們了解音樂發展史的目的是為了追尋詞體起源,而不是去找證據證明自己已知的結論。
打個比方來說一說我聽課的情況吧,我所了解到的基本知識,就好比幾塊形態各異的積木,傳統的文學史告訴我們,這些全部積木搭起來,一定是個這種形狀的房子,于是我就在找合適的積木搭,當我正為自己找到了合適的積木搭好固定的房子而皆大歡喜時,木齋告訴我,你遺漏了很多的積木,于是,我的心情可想而知,哭笑不得之后,我應該如何處理遺漏的積木呢? 按套路來說,我應該將已搭好的房子拆掉,重新認真地搭一個全新的房子,可是,這時候惰性會干擾我,不求甚解的習慣會勸說我,我很有可能偷偷地把那兩塊遺漏的積木丟掉,以求得毀尸滅跡,好保留我曾經“精心”搭建的成果。
以上假設有很多不恰當的地方,因為,就我現在的學識,根本不具備親自搭積木的本事,只能看著老師演示,自己憑著印象和記憶模仿。好在木齋對學術的敬畏之心,不允許我有“毀尸滅跡”的行為,更好在木齋為我們演示搭積木的過程,總是絲絲入扣,不遺漏每個細節,如果學生真心想看個清楚,那么一定就能看清楚。除非,我已經陷入了對已有“成果”的迷信和執拗。
這堂課后我清楚了古代音樂發展史的基本概況,作為一個全新的知識進入我的儲備。但這是次要的,因為所謂基本概況已是木齋先生經過推理得出的結論,懂得一個關于音樂史的更加接近歷史真實的結論對于一個古代文學的在讀碩士來說,當然也是不錯的收獲,但不是最大的收獲,更大的收獲是以老師對待傳統結論的質疑態度對比我在課堂上表現出的幾次對已成套路的觀點的迷信引發了我的反思。我一直以為,迷信跟我這樣一個有著重點大學生文憑的人是無關的,可是,我遺憾地發現面對學術,我是個如此迷信的人。迷信,就是迷迷糊糊的相信,不去思考也不去分析,就直接接受別人的結論,這樣說來,我才意識到,我以前一直都是個迷信的人。一個把傳統結論當作金科玉律的人。當務之急,就是需要破除迷信,達到“靈魂”覺醒。①此所引無署名文章《學術真理的宣教士——木齋學生所感(一)學術迷信的破除》,發表網址為:http://muzhai.blog.sohu.com/132503406.html,發表于2009年9月23日。按:本文轉引時,對文章中少數明顯的錯誤進行了修改。
正如上文作者所言:“如果學生真心想看個清楚,那么一定就能看清楚。除非,我已經陷入了對已有‘成果’迷信和執拗。”將其中的“學生”更改為“讀者”,就正適合當下古詩問題的狀況。當下之一些學者,如果說讀不懂,應該不是實情,但面對需要將自己苦心經營一生的房子拆毀重新搭建,這不僅僅需要理解的能力,更需要學術的勇氣和作為知識者的襟懷和良知。而作為方法論的具體分歧,很多學者都已經給予詳細闡發,那就是需要重回整體的、流變的大文學史觀來解讀文學史上的課題。關于這一點,筆者在此前的反思論文中,已經有過較為詳細的論證,在此就不能贅述。好在我已經讀到不少在這種大文學史觀方法論下寫出的優秀論文,此次發表的兩篇,一篇論證宮廷文學侍從在先秦漢魏階段的文學史地位,意圖闡發建安文學侍從的特殊功用;另外一篇由王立博士撰寫的《論“古詩”類五言詩及樂府詩在傳播中的變異》,兩篇大作俱佳,將所研究論題置身于文學史、文化史、傳播史的大背景之下加以考察,自然不難新見迭出,文采斐然。因為,文學史現象原本就是在文學史、文化史等多重背景綜合之下的產物,唯有將其置身于或說是還原于同等或是相似的視角之下,才有可能接近歷史真相的真實。
寫到這里,情尤未已,以一首小詩作結吧。
也許/我只是一只/螢火蟲/在暗夜/飛動/在無邊的暗夜/發出/微弱的歌聲
也許/我只是一只/螢火蟲/用生命的熱血/照映/那渴望者的/光明
也許/我只是一只/螢火蟲/在宇宙的萬古/洪荒中/瞬間/消失/無影無形
但我/還是一只/螢火蟲/一只撲向光焰的/螢火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