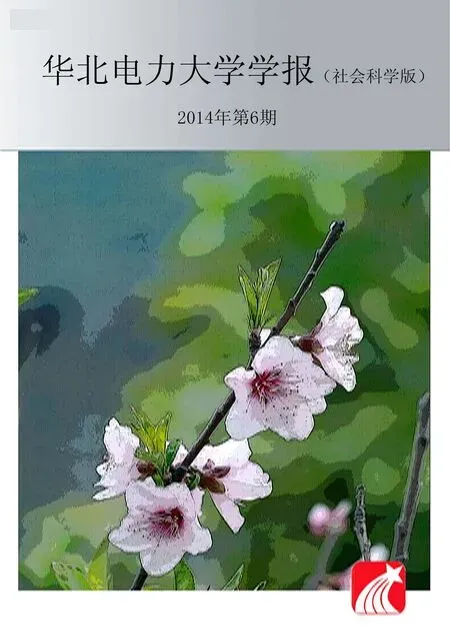對政府公開虛假信息行為的司法審查
王 鵬
(清華大學 法學院,北京 100084)
一、問題的提出
案例一:2009年,南京市的胡某以當地國土資源局發布的某地塊出讓、轉讓、變更及對土地登記等信息為虛假信息為由,請求法院判決發布政府虛假信息的行政行為違法,但法院以起訴針對的信息不明確、不具體為由,駁回了起訴①。
案例二:2011年,曹某訴上海市浦東新區規劃和土地管理局,要求公開選址意見書和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等政府文件一案中,原告認為該局公開的制作于2000年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是虛假文件,因為其簽發單位是2001年才出現的“上海市南匯區規劃管理局”。對這一可能直接決定案件結果的訴求,法院雖然稱該局“不應該提供其他虛假信息”,但并未進一步直接審查其真實性,僅以程序瑕疵為由撤消了相關《告知書》②。
案例三:2014年4月10日,蘭州市發生自來水苯超標事件。但蘭州市政府、甘肅省環保廳等部門在隨后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卻稱,苯超標時間為4月11日。此外,在之后疾控中心發布的實時水質信息監測報告中,僅包含苯含量數據,對《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2006規定的其它一百余項數據均未檢測,影響了信息的真實性和權威性。之后,5位蘭州市民到當地法院起訴自來水公司,被以不符合《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公益訴訟原告資格為由駁回。
上述案例表明,在信息公開實踐中,由于種種原因,政府可能存在公開虛假信息的行為。這里所提的“虛假信息”,根據學界的觀點,是指由政府發布的、與真實信息相反的、不具有“及時”、“準確”、“明確”、“客觀”以及“完整”等要素的信息。
遺憾的是,當前對政府發布虛假信息行為的救濟方式僅有行政救濟,缺少司法的審查和救濟。以“信息公開”和“虛假”(或“過錯”、“責任”、“錯誤”)檢索“北大法寶”網站,能得到2部部門規章和83部地方政府公布的規范性文件,這些文件對政府公開虛假信息行為的規定有三個特點:一是處理方式主要為行政處分,包括責令改正、警告、記過、記大過、降級、撤職以及開除等,此外還包括責令改正、通報批評等;二是處罰對象主要是虛假信息公開的相關責任人,對政府部門的責任沒有規定;三是沒有提及法院對虛假信息的審查和救濟。如果以與“虛假”相反的“準確”、“及時”等詞匯檢索相關法律,在去除重復和無意義的規范后,能得到7部法律規范①由于這一方面的地方文件全部重復中央文件表述,因此本文只列舉檢索發現的7項法律和中央政府法規規章,包括:《突發事件應對法》、《傳染病防治法》、《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應急管理工作的意見》、《衛生部關于做好貫徹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工作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運輸部施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辦法》和《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這些規范規定了政府信息公開的及時準確等正面要求,其中《突發事件應對法》等還規定了違反這些要求的法律責任,但這些規定過于籠統,難以在實踐中操作,而且缺乏法院審查方面的規定。此外,信息公開的總“綱領”《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簡稱《條例》)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政府信息公開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簡稱《規定》)對政府公開的虛假信息能否進行司法審查也模棱兩可。《條例》第9條、13條、33條和35條對政府信息公開的范圍、申請資格和責任的規定,《規定》第1條和第2條關于受案范圍的規定由于較為抽象,在政府信息司法實踐中引起了較多爭議,使虛假信息的發布行為成為司法審查的“灰色地帶”。另外與法律規范類似,在司法實踐中法院也往往難以發揮對虛假信息的審查作用。由于法律規定的模糊及舉證困難等原因,法院對政府明顯錯誤的信息有兩種處理方式:一是將虛假信息認定為未公開信息,二是對行政訴訟原告請求進行真實性審查的訴求不予回應。
然而,現實中法院對政府公布虛假信息行為不予審查的做法,并不代表不應該對其進行司法審查。哲學家休謨認為“是”(實然)與“應該”不能混同,否則“就會推翻一切通俗的道德學體系[1]”。只有在系統全面的分析應然和實然之間區別的基礎上,認清實然的特性,并結合具體情形,才能創造合適條件,使實然向應然轉化。從虛假信息的危害性、司法的作用和“有權利必有救濟”原則來看,法院對政府虛假信息的審查有一定的必要性。當然,由于上述我國法律規范的問題和司法的特性,法院對政府虛假信息的審查存在一定的障礙,因此法院審查應遵循一定的界限和標準,以達到司法謙抑和權利保護之間的平衡。
二、司法救濟的必要性和障礙
如上文所說,除行政機關內部救濟方式外,由法院對政府公開虛假信息的行為進行審查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具體來講,法院對政府此種行為進行審查既符合法治政府的要求,又避免了行政機關“自力救濟”的無效性,而且還有利于維護公民的合法權利,“實現人民群眾對政府工作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2]”。
(一)司法救濟的必要性
首先這是建設法治政府的必要條件。法治政府應該是“有限有為的政府”和“誠信負責的政府[3]”。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法治社會的健全,政府發布的信息逐漸成為對公民和社會至關重要的“公共產品”。而且由于政府在收集和處理信息方面天然的優勢,其發布的信息往往較個人信息有更高的可信度和真實性。但這也是一把“雙刃劍”,由于政府處于信息壟斷的地位,其可能在發布信息時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公開虛假信息,這在“政府公司化”[4]傾向嚴重的今天表現尤為突出。在這種“政府失靈”的情況下,僅靠政府自我調整是不可能有效規制其行為的,因此有必要引入獨立的第三方——法院,對其行為進行監督。另外從信賴保護原則看,法治政府要求政府要有“信用”與“信賴”,是“誠實政府”[5],也就是說如果人民對政府存有“信賴利益”,其利益就應受到司法的保護或救濟。可見,法治政府信息公開的初衷和基本目的就在于提供真實可靠的信息,這是信息公開的前提條件和題中之義,任何違反這一原則的行為都應當受到法院的外部監督和審查。
其次是行政救濟方式的低效率。盡管當前在規范層面已經對政府公開虛假信息的行為進行了規制,但無論是從實踐中,還是在理論上,這種單一行政控制方式的低效率都已經有所顯示。在現實層面,盡管存在眾多規范地方政府信息公開質量的文件,但當前地方政府依然存在大量公開虛假信息的行為,以“政府信息”和“虛假”(或“錯誤”、“虛假信息”、“不真實”等同義詞)檢索中國知網“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全文,能得到近800條結果,其中大多數都是關于虛假政府信息的報道。在理論層面,任何沒有外部監督的權力都會導致其低效甚至腐敗,“為了遏制行政權的惡和保護個人權益不受強勢行政權的非法侵害,只有通過外在力量來控制和制約行政權[6]”。同時,行政監督的低效也導致了行政違法成本的降低,出現“發布錯誤信息-行政自我規制低效-違法成本低-發布錯誤信息”的惡性循環。因此,對政府公開信息質量的控制,需要引入外在監督機制,主要是社會力量和法院。對于前者,根據《條例》第33條,社會力量對政府不履行信息公開義務的監督方式是向有關行政機關舉報,這樣在繞了“信息錯誤-舉報-行政內部監督”這樣的一個大圈子后,又回到了行政自我規制的范疇。由法院對政府虛假信息進行審查,則能夠避免這種尷尬。
再次是保護公民合法權利的需要。政府公布虛假信息是對公民知情權、監督權等權利的直接侵害。我國信息公開的立法體現了對權利保護范圍不斷擴大的取向:《行政訴訟法》第11條不僅規定了法院受理“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的案件,還有“受理法律、法規規定可以提起訴訟的其他行政案件”這一兜底條款,而《條例》33條則將法院受案范圍拓展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在政府信息公開工作中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行政行為,體現了“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與“法定性和實踐性相結合[7]18-19”等原則。此外,“有權利必有救濟”,政府虛假信息可能會對公民權利產生不利影響,在行政機關不能提供有效救濟的情況下,根據“司法最終”原理,應由法院提供最后的救濟途徑。印度 在 其 2005《信 息 法 案 》(The Right to Information Act)第18條(1)(a)中就指出,公民可就其認為的不完整、誤導或虛假的信息(incomplete,misleading or false information)提出申訴(complaint)①The Right to Information Act,2005[EB/OL].http://righttoinformation.gov.in/webactrti.htm.。
(二)司法審查的障礙
1.司法理念障礙
這里主要涉及到對“司法謙抑性”和審查效果的理解。有研究者從法院和行政機關分工的角度指出,“行政管理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和時效性,法律授予其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間,這是司法機關無法替代的。[8]”而政府公開信息的正確與否應該屬于行政機關自我判定的范疇,而并非法院所應涉足之領域。法院對政府虛假信息的審查將導致“司法能動主義[9]”,使法院權力過度擴張。另外從審查效果看,由于政府公開虛假信息行為并非一種典型的具體行政行為,而是更多的表現為行政事實行為,不會產生法律上的效果,因此法院對這種行為的審查缺乏法律依據。
2.受案范圍障礙
從受案范圍來看,當前法律和規范的相關規定較為模糊。《條例》第33條和《規定》第1條關于受案范圍的規定都沒有明確的將政府公開虛假信息的行為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保護范圍狹窄。盡管《規定》第1條第(二)款將信息公開的適當形式納入受案范圍、第(四)款規定與“自身相關的政府信息”不準確的可以提起訴訟,但這兩個條款僅是錯誤信息的一個表現形式,而且根據《條例》第25條,這里“自身相關”的內涵較為狹窄:一方面,僅限于“稅費繳納、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等內容[7]29。另一方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第6款,“不產生實際影響”的行為不屬于受案范圍。二是上述兩規范僅將訴訟范圍限于“具體行政行為”,在這種語境下,對于多表現為行政事實行為的虛假政府信息公開行為很難納入訴訟的范圍。為此有學者認為這是由于我國沒有將行政訴訟類型化,只有全面建立“客觀訴訟”和“主觀訴訟”制度[10],對《行政訴訟法》、《規定》及《條例》等法律規范進行徹底改造,才能解決這一問題。但對當前存在的政府公開虛假信息問題,沒有提出具體可行的路徑和策略。
3.制度構建障礙
還有研究者認為,盡管有必要對政府公開虛假信息的行為進行審查,但即便克服了上述兩個障礙,法院在實踐操作中依然存在眾多問題,包括:政府信息有較強專業性和科學性,法院難以判定其真偽;證據問題,包括舉證責任分配、調查舉證、證據證明力以及證據判定標準等問題;錯誤信息與國家秘密等的平衡問題;審查標準問題;判決形式問題;對相對人的賠償(補償)問題等等。
這三個障礙是相互關聯的,只有在解決障礙一與二的基礎上,才能考慮障礙三,從理論和實踐看,障礙二是關鍵問題,受到了最多的討論和關注。由于司法理念和受案范圍對制度構建在方向、框架和理念上有根本性影響,因此本文擬首先討論前兩個障礙,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具體制度的構建問題。
三、障礙的克服:司法理念與受案范圍
(一)對司法理念的再認識
如上所述,當前認為司法機關不宜審查行政機關虛假信息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對司法地位的考慮和對審查效果的擔憂。從司法的地位來看,其應保持謙抑性,但這種謙抑性并不是對行政權一味的退讓。以美國為例,其最高法院對謙抑性的理解就隨著時代和案件的變化而變化,甚至出現了以“忽視先例”、“法官造法”以及“結果導向”為特征的“司法能動主義”(Judicial Activism)傾向[11]。但應注意的是這種司法的主動性不是無限的,美國最高院提出了多種限制的標準,如在“俄亥俄林業公司訴塞拉俱樂部”(Ohio Forestry Ass'n,Inc.v.Sierra Club)①118S.Ct 1665,1668(1998).案中,在處理司法權與行政權關系問題上最高院提出了法院受理案件的三個標準:延遲審查的危害、司法審查是否對行政權構成了不當干預以及事實情況是否有利于司法審查[12]。可見,司法的謙抑理念并不代表其對政府行為的過度退縮,只要遵守法定的標準,法院就能達到謙抑性和審查權擴張之間的平衡。在審查效果上,盡管對虛假信息的判定需要一定專業知識,但一方面,法院可引入第三方專家證人,以提高對專業知識的判定能力;更重要的是,由于是“程序決定了法治與態意的人治之間的基本區別[13]”,法院對虛假信息的審查必然包含程序合法性問題,而現實中,如本文的三個案例,行政機關發布的錯誤信息往往是由于未遵守法定程序,因此法院能夠通過對程序的控制達到控制信息質量的目的。
(二)受案范圍的明確
法院對政府虛假信息審查的受案范圍是理論和實踐中討論的關鍵問題,從筆者搜集到的幾十篇重要文獻和著作看,幾乎都涉及到法院受案范圍的研究。這些成果可分為兩類②限于篇幅,這里不再一一列舉學者觀點,具體內容可參見本文所引注釋和參考文獻。:一類是將訴訟類型化作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途徑,另一類是主張“細分”虛假信息的種類,盡量將“合適”的政府行為納入法院的審查。筆者認為,當前解決政府公開虛假信息的基本思路是保證法的穩定性和變動性的統一,因此應綜合這兩種認識,對公開虛假信息的行為進行分類,使當前法律能最大限度的容納一部分此類行為,并根據法理和國外經驗對法規范進行修改,以實現法院對虛假信息的全面審查。從我國《行政訴訟法》和《條例》、《規定》體現出的“與公民利益直接相關”的精神來看,公民對公開虛假信息行為的訴訟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主觀訴訟,即虛假信息與公民有直接利害關系,另一類是客觀訴訟,即虛假信息與公共利益有直接關系。但鑒于問題的復雜性,需要對這兩類訴訟作進一步細分。
1.主觀訴訟與法院審查
主觀訴訟強調的是法院對利害關系人訴求的直接回應,“法院審判須更強調回應原告的訴訟請求[14]”。從實踐看,關于虛假信息的主觀訴訟所針對的對象主要有兩種:單純發布虛假信息的行為和作為具體行政行為組成部分的發布虛假信息的行為。
在主觀訴訟視角中,法院可對單純發布虛假信息的行為直接進行審查。根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第11條、《條例》第13條、《規定》第1條第四款和第5條的規定:a.如果行政機關依申請公開的的信息不準確,則利益相關人在提供了“更正申請以及政府信息與其自身相關且記錄不準確的事實根據”后,能夠向法院提起訴訟。b.如果行政機關主動公開的信息不準確(包括因情態發展而導致的不準確),且其內容確實關涉特定第三人利益的,該第三人得依上述證據規定,提出對該信息的審查權。國外在這一方面也有類似的規定,如澳大利亞的《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1982)第五部分“對個人信息的修正 和 注 釋”(Amendment and Annotation of Personal Records)第48條(a)款就規定公民可就政府公開的與其相關的“不完善、不正確、過時或誤導”(incomplete,incorrect,out of date or misleading)的信息提出更正,并可提起訴訟。借鑒其經驗,我國法院應該對“準確”一詞的外延做擴大解釋,使其能與虛假信息的外延重合,將不完整、有涂改的信息都作“不準確”解釋。這也就意味著,在主觀訴訟方面法院可在不改變法律規范的情況下,對虛假信息行使較為完整的審查權。
在政府公開虛假信息的行為屬于具體行政行為組成部分的情況下,由于公開虛假信息行為被政府的一項具體行政行為所包容,會出現兩種情形:a.公民以虛假信息作為起訴對象。由于此時虛假信息僅是具體行政行為的一部分,從節約訴訟成本和訴訟實效性考慮,法院應不予受理或駁回此訴求。如在“夏國芳等224人訴北侖區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開案①(2006)甫鎮行初字第22號。”中,原告以政府主動公開信息的行為違法為由,而非征地行為違法,提起訴訟,對此法院認為既然原告明知公告內容,其訴求“無實際意義,也沒有必要”。b.公民以具體行政行為為起訴對象。根據《行政訴訟法》第11條,人民法院有權對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審查,據此法院應以行政行為違法作為主要案由,并附帶審查信息的真實性,并將其作為行政行為是否違法的判定標準之一。如經審查確認為虛假信息,則法院可判決具體行政行為違法或無效。
2.客觀訴訟與法院審查
與主觀訴訟相比,客觀訴訟較為復雜,需要平衡法律規定和法理、現實之間的沖突。一方面法律和司法解釋之所以沒有明確賦予法院審查權,是因為這類訴訟“帶有公益訴訟的性質,這在目前的《行政訴訟法》的架構之下是較難突破的[15]”;但另一方面如上所述,法院對虛假信息的審查確有其必要性。為維護二者平衡,防止出現“囚徒困境”,“折中”無疑是最好的選擇。具體思路是:首先嘗試將客觀訴訟“迂回轉化”為主觀訴訟;對無法轉化的,發揮立法和司法裁量的作用,將其逐步納入訴訟范圍。
(1)將客觀訴訟轉化為主觀訴訟
根據法律和規范,客觀訴訟轉化為主觀訴訟的關鍵在于對“合法權益”的認定。《條例》第6條規定,行政機關發現可能影響社會穩定、擾亂社會管理秩序的虛假信息,應當發布準確信息予以澄清,這構成了政府法定義務的一部分。而根據《規定》第3條,公民在“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主動公開政府信息義務”的情況下,可提起訴訟。同時根據《行政訴訟法》第11條第(八)款“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的”和《規定》第1條第(五)款“認為行政機關在政府信息公開工作中的其他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的規定,對于政府公開的虛假信息,如果公民認為侵害了其合法權益,可向法院提起訴訟。此外應該注意的是,這里的合法權益有兩層含義:一是法定性,即公民“應當證明其與被訴的行政行為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②京高法發[2009]150號:《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行政審判適用法律問題的解答》。”;二是直接性,即利益(或損失)與虛假信息的公布在法律上有直接的因果關系。之所以需加這樣的限制,是因為“權利是一種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主張[16]”,即便在較為重視公民知情權的美國,其 《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也規定,公眾請求公開起訴時,限于受到不利影響的人[17]。在司法裁判中,法院首先應考慮能否將客觀訴訟轉化為主觀訴訟,以盡量在當前法律的范圍內實現對虛假信息的審查。
(2)立法明確客觀訴訟的范圍
立法擴大客觀訴訟的范圍有其必要性。“從現有政府信息公開專門法律規范內容來看,其主要立法目的是反腐倡廉和推進民主政治建設,保障知情權”[18]。“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確定應當以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訴權為原則,不能僅僅因行政行為的分類就將某些類型的行政行為排除在司法審查范圍之外。[19]”我國臺灣學者也同樣認為,對于行政行為,無論是具體行政行為還是行政事實行為,只要其導致了不利后果,相對人就對此有“結果除去請求權[20]”。而且擴大范圍并不意味著“濫訴”的出現,因為在中國“訴訟是要成本的,沒事找事或以訴訟為樂的情況,極難出現。[21]”
但受案范圍的擴大并不是沒有限制的。首先,受案范圍的擴大應與社會現實相適應。在1989年制定《行政訴訟法》過程中,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漢斌指出:由于觀念更新、不習慣、不適應以及承受力等問題,“對受案范圍現在還不宜規定太寬,而應逐漸擴大,以利于行政訴訟制度的推行。[22]”這一論斷在當前我國司法資源緊張且司法機關地位較低的情況下依然成立。其次,即便是在法治發達的國家或地區,法院對具有公益訴訟性質的客觀訴訟也不是一概受理的,“客觀訴訟是否應為司法審判權的范圍,亦在國外引起爭論[23]”。境外對客觀訴訟的限制主要有兩類:一是以“公益代表”替代公民行使訴權;二是以單行法律確立公民或檢察官訴權。前者如在德國,根據其《行政法院法》第35條第1款和第36條第1款,公益檢察官(或代表人)參與體現公益的客觀訴訟,民眾則無此權利。后者如在美國和我國臺灣地區。美國最高法院早在1943年就于“紐約州聯合工業公司訴伊斯卡案”①134F.2d694(2dCir.1943).(Associated Industries of New York State,Inc.v.Ickes)中指出,國會“有權以法律指定其他當事人作為私人檢察總長(Private Attorney General),主張公共利益”;《聯邦行政程序法》(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第702條也確立了“申請保護的利益可能屬于有關法律或憲法所保護的利益[24]”這一標準。可見,美國對客觀訴訟范圍的規定是原則性的,必須經過單行法的進一步規定方可實施,如美國通過《清潔空氣法》、《清潔水法》及“緬因州人民聯盟訴馬尼科洛公司案”②471F.3d277.(Maine People’sAlliance v.Mallinckrodt,Inc.)等司法判例進一步建立的環境公益訴訟制度。與美國相似,我國臺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第9條在賦予公民公益訴訟權的同時,附加了一個但書:“但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使該規定成為銜接其他單行法(如“空氣污染防治法”第74條第1款)的原則性規定。
因此,我國未來相關立法應考慮現實情況,并借鑒國外經驗,在原則上規定公民和檢察機關有權提起客觀訴訟的前提下,在單行法(或部門法)中分門別類的授予公民或檢察機關對政府虛假信息提起客觀訴訟的權利。首先應修改《行政訴訟法》第11條,將公民提起客觀訴訟的權利納入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因為根據《立法法》第8條,訴訟制度必須由法律規定,受案范圍作為訴訟制度的組成部分,必須首先由《行政訴訟法》進行規定。在此基礎上修改《條例》第33條和《規定》第1條,規定公民可對虛假信息提起訴訟,但具體應由法律規定。之后修改單行法,在特定領域將行政機關公開虛假信息的行為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從維持法律體系完整性的目標和國外實踐來看,當前可在《突發事件應對法》、《傳染病防治法》和環境性立法(如《環境保護法》和《大氣污染防治法》)中首先確立對政府虛假信息的審查。之所以是這三類法律,是因為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前兩部法律已經有了較為完整的信息公開責任體系,而且突發事件和傳染性帶有緊迫性,對政府虛假信息的審查既能最大限度保持法體系的完整,又能維護社會穩定和政府公信力。環境性立法之所以需要建立這一機制,是因為從西方法治發達國家的實踐來看,其客觀訴訟基本上都包含了環境保護的內容,因而有豐富的經驗可資借鑒。
(3)司法裁量權
對虛假信息的審查需要法院司法裁量權的運用。政府信息公開訴訟是一種“新型”、“特殊的訴訟類型[25]”,僅靠規制傳統行政行為的《行政訴訟法》來確定受案范圍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時,規定信息公開的《條例》作為行政機關制定的行政法規,根據“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原則,不得規定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圍。因此在立法和行政機關均有局限性和滯后性的情況下,對政府虛假信息的審查就需要發揮法院的裁量作用。例如在美國環境公益訴訟中,其最高法院就發揮了積極作用,其在“聯邦電訊委員會訴桑德斯兄弟無線電廣播站案”③309U.S.470(1940).(FCC v.Sanders Brothers Radio Station)、“數據處理服務公司訴坎普案①397U.S.150(1970).”(Data Processing Service Organizations,Inc.v.Camp)、“塞拉俱樂部訴莫頓案②405U.S.727(1972).”(Sierra Club v.Morton)及“盧堅訴野生動物聯合會案③496U.S.871(1990).”(Lujan v.National Wildlife Federation)等系列案件中,在尊重法律規定的前提下,對法律權利、損害認定及原告資格等進行了一系列解釋,促進了環境客觀訴訟制度的構建。當前我國法院也應積極運用其司法裁量權,在處理政府公開虛假信息的案件中,應特別注意四個方面:首先,在原告資格認定方面,法院應該對當事人權益受損程度、訴求針對行政行為的性質及證據是否能初步證明信息虛假等方面進行主動審查,以明確原告資格,防止“濫訴”的發生;其次,將虛假信息造成相對人信賴利益損失的情形納入主觀訴訟的范圍,作為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對待;再次,區分政府公開虛假信息行為和不公開信息的行為,因為二者在行為方式和法律責任上都有所差別,不能同等對待。最后,最高院可考慮發布審理虛假信息的指導性案例,以期對下級法院的審判活動形成更為細致的指導。
四、障礙的克服:制度構建
司法理念和受案范圍是進行制度構建的前提。在明確了政府公開虛假信息受案范圍的基礎上,應進一步探討法院在處理這類案件中的制度構建,以完善相應的審查機制。具體來說,在審判實踐中主要有四個方面需要明確和完善,即審查標準、舉證責任、判決形式以及賠償(補償)責任。
(一)審查標準
在審理政府公開虛假信息的案件中,法院應該堅持合法性審查原則。盡管無論是在大陸法系還是在英美法系國家,其法院均有權對行政行為的合理性進行審查,如“美國的憲法至少為司法審查對行政機關是否濫用自由裁量權提供了保障[26]”,但一方面,從作為上位法的《行政訴訟法》的基本架構看,除行政處罰“明顯不當”外,法院僅能審查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即便是進行合理性審查的國家,法院也較為謹慎,常常“只在其特長范圍內就法律問題進行裁決”,“并不闡釋合理的具體涵義[27]”。因此我國法院對公開虛假信息的行為進行合法性才是較為穩妥的選擇。具體來說,根據《行政訴訟法》第5條和第54條,法院應審查行政機關在公布虛假信息時有沒有出現適用法律、法規錯誤、違反法定程序、超越職權以及濫用職權等行為。另外,根據《條例》第6條,《規定》第1條第1款第(四)項的規定,法院有權對公開信息的及時性和準確性進行審查;根據《條例》第二章、第三章,法院有權對政府主動公開信息的“范圍、方式和程序 ”等內容進行審查。法院在審查虛假信息的過程中應依照上述規定,對實體和程序等內容進行審查。
在合法性審查過程中,法院對虛假信息的審查可能與反信息公開④即阻止行政機關公開某信息的行為。發生沖突。這里又可分為兩種情形:一是虛假信息與第三人利益相關。根據《條例》第23條,行政機關不得隨意公開公民的個人隱私或商業秘密,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產生公民權利之間的博弈,如知情權與隱私權,對此恰當的做法是通知相關第三人,允許其作為利害關系人參加信息真實性訴訟,或者允許其作為原告,單獨提起反信息公開訴訟。二是虛假信息與國家秘密等相關。在這一方面與《條例》形成博弈關系的法律主要有:《保守國家秘密法》第2條、第9條、第13條和第20條,《檔案法》第2條、第13條、第16條、第19條和第20條。盡管這些法律“都是上世紀制定的,有些規定與政務信息公開原則有沖突[28]”,但其位階較高,在司法實踐中不宜隨意改變,對此類信息,應主要通過政府的內部監督保證其真實性,法院也可通過不公開審理的方式,盡量保證對此類信息的審查權。
另外,在單行法(或部門法)專門規定了客觀訴訟情形下,法院應當對虛假信息有更嚴格的界定標準。這是因為這類法律規范的對象都具有較強的危害,虛假信息可能導致極為不利的后果。對此法院審查可考慮兩個方面:一是信息的社會效果,“突發事件信息公開需要對社會效果的考量[29]”,對引起了社會恐慌的信息,如果其較為模糊,法院應該認定為虛假信息。二是信息的針對性,對于行政機關發布的技術性過強且內容混亂復雜的信息,如果其沒有通俗的文字對信息內容進行講解或說明,法院可認定其為虛假信息。
(二)舉證責任
在政府公開虛假信息的情況下,根據《行政訴訟法》舉證責任的規定,結合《條例》和《規定》的內容,原告需要提供的證據包括:(依申請的情況下)證明申請信息屬于公開的范圍并且符合法定條件,被告提供的信息內容,其與公開信息的利害關系,初步證明虛假信息的證據資料等。被告的舉證責任包括:遵守了信息公開法定程序和期限的證明;公開信息屬于法定公開的范圍;證明信息正確性的相關材料,包括信息公開的方式、時間與載體等。
(三)判決形式
1.原告請求確認政府信息為虛假信息。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法院經查明發現政府信息為真實信息,則應判決駁回原告訴訟請求;如果法院查明信息確實為虛假信息,則可發布確認判決,并可同時責令行政機關限期重新公開信息。對于重新公開信息真偽有爭議的,仍可提起行政訴訟。
2.原告以信息虛假為由,請求撤銷政府公開虛假信息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法院查明信息為真實信息,則應駁回原告訴求;如果法院查明信息為假,則可據此撤銷該行政行為,并可要求政府限期重新發布信息;如果法院查明信息為真,但公開行為在程序等其他方面違法,根據《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54條第一款規定的“全案審理原則”,法院仍應依程序錯誤等理由撤銷該行政行為。此外對于上文提到的,在公開虛假信息行為是一個具體行政行為組成部分的情況下,法院應審查該具體行政行為,對原告單獨的提出的審查該虛假信息的訴請不予受理或直接裁定駁回。
(四)賠償(補償)責任
對公開虛假信息行為的賠償要求可按照《國家賠償法》和《行政訴訟法》的規定進行。從條件來看,虛假信息應對申請人造成了現實的、確定的損害,二者必須有直接的因果關系,而且這種損害不能是間接地或預期的損害。從申請機關來看,根據《行政訴訟法》第67條,公民可在提起行政訴訟時一并提出賠償申請,或者先向行政機關提出,對其決定不服的,再行提起賠償訴訟。
如果政府由于客觀原因發布了虛假信息,則應根據公平、合理、及時與公開等原則[30]對受害人進行補償。“政府公開的信息總會受到一系列外部條件的影響,因此其真實性并不能絕對得到保證[31]”。由于社會信息復雜多變且內容極其龐大,政府在收集整理過程中,由于認識本身的局限性,難免會出現公開虛假信息的情況。如果相對人出于對政府的信任而為某種行為并造成了損害,其對政府的“信賴利益”應當得到法律的保護。在這種情況下,行政機關應通過公平原則和正當法律程序,對相對人予以補償,以彌補其合法權利因政府行為而導致的特別損害。
[1](英)休謨.人性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510.
[2]曹康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讀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7.
[3]馬懷德.法治政府特征及建設途徑[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8(2).
[4]劉志彪.我國地方政府公司化傾向與債務風險:形成機制與化解策略[J].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3(5).
[5]馬懷德.行政程序法立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86.
[6]崔卓蘭,盧護鋒.行政自制之途徑探尋[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8(1).
[7]江必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政府信息公開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理解與適用[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
[8]傅國云.行政公訴的法理與制度建構[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2).
[9]李輝.司法能動主義與司法克制主義的比較分析[J].法律方法,2009(1).
[10]鄧劍光.論政府信息真實性爭議及其解決機制的完善[J].政治與法律,2009(6).
[11]Keen D.Kmiec,The Origin and Current Meanings of“Judicial Activism”[J],92California .L .Rev.2004:1463-1475.
[12]Lingsay J.Nichols,The NMF’s National Standard Guidelines:Why Judicial Deference May Be Inevitable?[J]91 Calif.L.Rev,2003:1405-1406.
[13]Justice William O.Douglas’s Comment in Joint Anti-Fascist Refugee Comm.V.Mcgrath[M],se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s Reports,The Lawyers Cooperative Publishing Company,1951:858.
[14]薛剛凌,楊欣.論我國行政訴訟構造[J].行政法學研究,2013(4).
[15]李廣宇.政府信息公開司法解釋讀本[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66.
[16](美)史蒂芬·霍爾姆斯,凱斯·R·桑坦斯.權利的成本:為什么自由依賴于稅[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13-14.
[17]王名揚.美國行政法[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1995:1007.
[18]王萬華.知情權與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91.
[19]黃學賢,梁玥.政府信息公開訴訟受案范圍研究[J].法學評論,2010(2).
[20]翁岳生.行政法[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903.
[21]劉善春.行政訴訟原理及名案解析[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483.
[22]王漢斌.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草案)》的說明[J].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89(7).
[23]李仁淼.司法權的觀念(上)[M].臺北:元照出版公司,2002:921.
[24]Glen O.Robinson,Ernest Gellhorn,Harold H.Bruff,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 (2ndEdition)[M].St Paul:West Academic Publishing,1995:217.
[25]劉穎.挑戰或機遇:政府信息公開訴訟對我國行政審判的理論及實踐意義[J].法律適用,2009(4).
[26]William F.Fax,Jr.Understanding of Administrative Law[M].Philadelphia:Matthew Bender &Co,2011:391.
[27]Christopher F. Edley, Administrative Law:Rethinking Judicial Control of Bureaucracy[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96.
[28]莫于川.經由陽光政府走向法治政府[J].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7).
[29]何翠鳳.論突發事件信息公開的真實性原則及其例外[C].北京: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2009:524-531.
[30]鄭全新.論我國實定法行政補償的基本原則[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4(2).
[31]趙春雷.論政府信息公開中公眾的體驗及其改善路徑[J].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