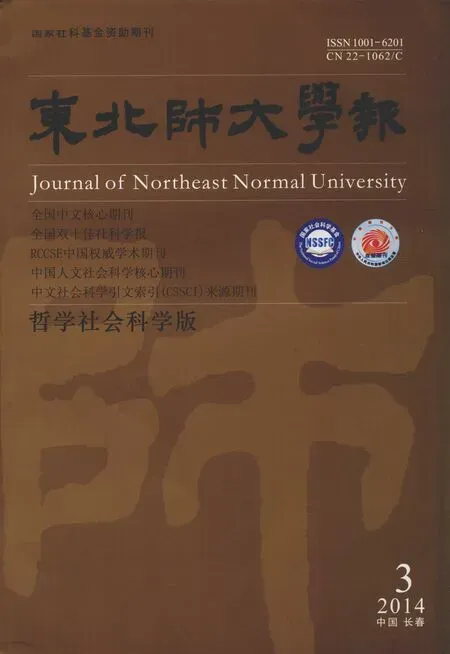論清末文學教育的轉型
19世紀的鴉片戰爭,不僅破壞了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結構,同時還對國人封閉僵化的思維觀念與行為模式造成了巨大的沖擊。隨著社會性質的轉變,儒家文化思想漸漸失去了信仰與崇拜的光環,依附于封建制度的舊式教育成為了當時知識分子主要攻擊的對象。此后,興“博學”之實用科目,教“濟世”之文學,育“時務”之新人才成為了文學教育改革的重點。
一
中國傳統的文學教育在科舉選士的“指揮”下,逐漸形成了八股“作”文與經義“述”學的交織,教育中的文學性和教育意義幾乎被“有妨舉業”的衡量標準遮蔽。再加之清朝中葉以來的文化高壓政策,知識分子與生俱來的憂患意識與犯言直諫的品格投向了內斂沉悶的學術考校。然而,這種治學之風隨著帝制末外敵入侵發生變化:戰敗,變法;國難,新政。為了挽救封建政權,洋務運動、維新變法為近代知識分子打開了一扇革新的大門。一批先覺者由質疑走向了反思,試圖從興新學入手,通過教育的革新舉措有計劃地挽救清廷的頹勢。但此時的革新更多的是創造之意,雖有革除舊蔽的實際做法,如改八股為策論、辦京師同文館,但在文學教育領域奉行的則是一種“有限抽離”的策略。
吉登斯曾經在《現代性與自我認同》的討論中提道,“前現代社會以一種松散的形式組織起來的活動模式,隨著現代性的出現,變得更為專門化,更為精確。”[1]19然而,其中還有一種更為內在的關聯,“即社會關系從地方性的場景中‘挖出來’(lifting out)并使社會關系的在無限的時空地帶中‘再聯接’”[1]19。對于“抽離”,吉登斯強調的是一種傳統社會發展的動力之一,它是理性思考的外化過程。事實上,清末的封建社會也處于“抽離”的階段。此時文學被知識分子從各種社會關系中“挖”了出來,成為教育革新的對象。并且在19世紀末中、西文化傳統互動中,摻雜了社會轉型、現實需要、思想進化等多種因素的“再聯接”:一方面,它借鑒了西方現代學術體制、非原發的價值觀、思維方式后,構成了文學教育轉型的試驗場;另一方面,為了維系封建統治秩序,文學教育在轉型中保留了一部分傳統文化思想。在這兩方面的影響下,清末文學教育開啟了現代性的探索。
首先,中國古代的統治集團是在“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倫理教化中培養國家需要的人才。而包含著經、史、諸子學等繁雜內容的文學,不過是教育的手段而并非目的,它不是成為舉業的“附屬產品”,就是成為“修身立德”的人生標簽。雖然,清末的治學活動遺傳了學海堂、詁經精舍“實事求是”的學風,但這種內容混雜、外延模糊的“泛文學”教育已然不符合晚清救亡的需要。從另外一種角度看,清末又處于中西思想碰撞的大時代,當“具有想象力與創造力的題材”[2]與傳統的典章子集相遇時,知識結構、思維方式等方面的強烈反差,也成為了文學教育轉型的巨大推手。
其次,文學教育的轉型離不開制度的保障。清末的治學雖然囿于儒家的經典內容,但當它們遭遇“欲取儒學的地位而代之”[3]的文化殖民活動后,文學在自我保護機制的驅使下,開始從國家制度層面思考“濟時用”的文學革新。1902年,“文學科”一詞出現在清廷頒布的學堂章程中,隨后在《奏定大學堂章程》中,“中國文學門”劃出了“四書五經”“程朱理學”等內容,設文學研究法、說文學、音韻學、歷代文章流別等七門主課以及四庫集部提要、各種紀事本末、西國文學史等九門補助課。自此,文學教育的合法地位得到官方話語的肯定。但是,清政府在《奏定學務綱要》中又特別指出,經籍古書有益德性,有助封建統治,所以學堂內不得廢止。這就決定了清末文學教育的轉型不可能是徹底的新生,它只能是以漸進的方式,協調文學與傳統制度、社會、國家之間的關系,并以學術研究的姿態參與清末的自救行動。
二
作為一種審美意識活動,清末的文學教育只能選擇抽離的方式把握人與社會、古典與現代的復雜關系。大體上說,中國古代的文學教育主要是培養倫理型人才。而清末在西方知識觀、價值觀的沖擊下,在“啟民智”的訴求下,文學教育開始了一番對世界重新理解和把握的活動。其中,知識分子采取了一種溫和的改良方式,雖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文學在情感、知識、價值觀等方面的效度,卻逐漸拉開了文學教育與封建制度的關系。
其一,言辭方面的探索,即“言文合一”的主張促進了白話文學的發展,間接地推動了清末文學教育的轉型。傳統的文學以詩文典籍為主,“文言分離”保證了書面文的高雅、古樸。但清末的民族危機亟須便于認知、理解、記憶、應用的文學表達方式出現。因此,在裘廷梁、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的倡導下,“言文合一”的白話通俗文體進入了文學創作的視野。特別是19世紀末,迫于外交、商貿、翻譯的需要,歐化的語體帶著新思想、新知識、新詞匯進入了新式學堂。這種借鑒西方語言、句式,又接近民眾生活的表達拓寬了文學教育的空間,加快了文學革新的進程。周作人就認為,早期對《圣經》的中文譯介就對近代文學發揮了不小的作用。胡適更是指出,“歐化的白話文方才能夠應付新時代的新需要。歐化的白話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語言的細密的結構,使我們的文字能夠傳達復雜的思想,曲折的理論。”[4]因此,在社會需要的情況下,“言文分離”、排斥俚俗的文學開始新的嘗試。如,早期黃遵憲嘗試在詩歌創作中引入民間俗語,并提出了明白暢曉的文學變革設想。陳榮袞則認為只有白話文才能救亡圖存,因而積極地創辦白話報刊,編寫白話文課本。再有,無錫三等公學以淺近通俗的文字編寫了《蒙學讀本》,意在傳遞普通知識,養成立憲國民之道德。直到1904年,《奏訂初等小學堂章程》規定,“使識日用常見之字,解日用淺近之文理,……并當使之以俗語敘事,及日用簡短書信,以開他日自己作文之先路。”[5]但是,這種較為接近日常生活的言辭探索,還處于由傳統向現代的過渡,其與“五四”時期的白話文學仍存在區別。
其二,新文體功能的凸顯,即新小說、戲劇、詩歌的創作為清末文學教育的轉型提供了直接的文學來源。經由不同文學體裁與主題的閱讀和接受,有助于豐富讀者的情感體驗、提高智識、獲得審美愉悅。但清末的學術研究鉆精、考校八股,很少涉獵科舉以外的文學作品。鑒于這種僵化、功利的治學風氣,一種切合實用,又能傳播智識的文體迅速成為知識分子思考的重點。如,梁啟超在湖南時務學堂的《學約》中提出了“傳世之文”和“覺世之文”的分類。他力主一種“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6]的寫作。1902年《新民叢報》刊載《新小說》雜志的廣告,強調小說文體具有的“曲折透達,淋漓盡致,描人群之情狀,批天地之窾奧”[7]特質,并指出“本報文言俗語參用”的體例。另外,在翻譯文學的影響下,西方文學創作的藝術手法、描寫方式、審美標準等都參與到清末文學的轉型中。古文雖美,但此時新文體的出現與流行打破了傳統詩文歌賦的權威感。這種通俗易懂的體裁,強烈的語言感染力及文白夾雜的言說形式,以社會群體為啟智對象,在一定程度上沖破了桐城文法、“同光”詩作的局限,為文學教育開辟了新的天地。此外,1905年科舉停罷,俗語和官話進入了文學科的視野,加快了文學教育內容的轉變。盡管此時詩歌、小說的創作還有依托古人的痕跡,《新中國未來記》《九命奇冤》還稱不上白話文學的新生,但它們的確為文學教育的蛻變打下了基礎。
除了以上兩種途徑之外,清末文學教育還在學科化的建構中展開了自我轉型的探索。近代教育系統的完善與發展,需要更嚴謹的學科劃分以及專業的學術研究。但是,中國古代的文學教育并不是依照“性質的類別而組織成各自獨立的系統”[8]。它更近似于一種學術“大拼盤”。余英時先生將這種情況歸為“邏輯知識論意識”的缺失。然而19世紀末西方科學思想的輸入,傳統分齋而治的詞章記誦、八股訓練,轉向了初、中、高以及大學堂各有側重的文學認識活動。雖然,此時的文學教育仍然以古書經籍為主,但它畢竟邁開了學科獨立探索的第一步,推動了內容混雜、外延模糊“泛文學”朝著專業化、精細化的學術系統轉型。特別是文學教科書的編寫與應用,加快了清末文學教育轉型的步伐。最初從模仿教會學校課本開始,知識分子在異質文化的對接中逐漸完成了文學教科書獨立編纂的工作。這一階段比較完備的課本主要有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最新教科書”,以及劉師培編輯的《中國文學教科書》。他們的編寫是對舊式學堂內經書、文選的告別,在內容編排上由字、音、義入手,從簡到繁。前者的編寫以通俗語體配上插圖,后者以文言體例為主,側重小學的研究。而在大學堂內有林傳甲、黃人的文學史講義,這兩本著述在文學界定、文體分類及研究方法方面有許多創新的思考。但是,清末文學教育的轉型畢竟站在了封建殘垣之上,雖然在開通智識和學科建構方面有所突破,它的本質仍然指向益德教化的封建立場。
三
總體來說,清末文學教育的轉型是在封建體制內對思想啟蒙的呼喚,它雖比不上新文化運動來得猛烈,但其借助異質文化碰撞的契機,還是對傳統文教進行了一番形制的拆解。盡管在這一拆解過程中,政治指向與價值觀沒有得到徹底的改變,但文學與傳統秩序建立的親密關系已經在革新的教育語境中出現裂痕。儒家文化的權威性受到了學科化文學建構的沖擊。白話文和新文體被知識分子從封建秩序中“挖”了出來,并與思想啟蒙聯接在一起。這種帝制末的文學轉型,是對固有范式與規則的反抗,不僅為文學教育現代性發生開辟了教育的空間,也為新文學傳播搭建了一個思想的平臺。
[1]吉登斯,趙旭東,方文.現代性與自我認同:現代晚期的自我與社會[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2]李春.文學翻譯如何進入文學革命——“Literature”概念的譯介與文學革命的發生[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1):85.
[3]李清悚,顧岳中.帝國主義在上海的教育侵略活動資料簡編[G].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7.
[4]胡適.新文學的建設理論[M]//蔡元培.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集:再版.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4:42.
[5]奏訂初等小學堂章程[G]//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璩鑫圭,唐良炎.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205.
[6]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88.
[7]新小說報社.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N].新民叢報,1902-07-15(14).
[8]余英時.意識形態與學術思想[M]//沈志佳.余英時文集:第4卷.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