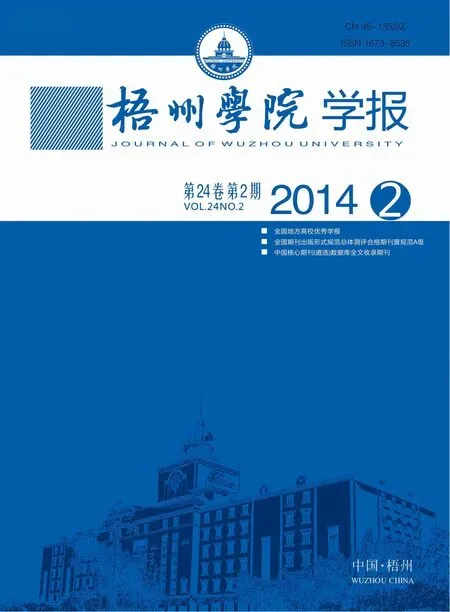從中國視角看文化產業的“西方經驗”
李江
(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廣西桂林 541004)
從中國視角看文化產業的“西方經驗”
李江
(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廣西桂林 541004)
文化產業的“西方經驗”包含著兩個不可分割的部分:一是系統完備的理論認識,二是豐富的產業經驗。理論認識是更多地側重于學術層面上的批判性研究,產業經驗則更多地關注實用性的產業手段的運用。總體上處于自然經濟狀態的中國文化產業如果要為進一步跨國經營做準備,就有必要在全面把握西方文化產業的社會歷史條件、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政策、文化產業基礎、發展方式以及社會貢獻的基礎上,更好地兼顧西方文化產業理論和產業化經驗。
文化產業;西方經驗;文化產業理論;產業化經驗
一、西方文化產業理論的發展
從思想背景和理論影響來看,法蘭克福學派、伯明翰學派以及技術媒介學派對西方文化產業理論研究的形成和發展,都做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
(一)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產業理論
法蘭克福學派深入研究過文化工業的機制、特點、作用和影響。對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提出了很多富于警策性的見解,令人目眩地打開了一條與其他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有所不同的批判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新思路。
跟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中生產力進步和人的解放邏輯不同,阿多諾深刻地繼承和發揚了一種方法論上以及基本立場上的批判傳統,對文化產業保持了一種清醒而不妥協的批判姿態,集中而不是目標寬泛地探討了文化產業的相關問題,并把這些思考轉換成了認知表述,從而使他揭示的文化產業的相關認識系統而又深入。根據阿多諾的觀察,文化產業明顯不同于自發生長的大眾文化。“在文化工業的所有部門中,為了大眾的消費而制作的、在很大程度上決定這一消費本質的產品,多少是按計劃而生產的。各個個別的部分在結構上都是相似的,或者至少是相互適應的,把自己組織為一個幾乎沒有裂隙的系統。做到這一點是借助了當代的技術能力以及經濟和行政上的集中化。”[1]在阿多諾看來,文化產業是由文化生產商控制、按照嚴格的生產程序、為滿足利潤欲望和消費欲望而興起的產業。生產的標準化導致文化產品的同質化,創造方式決定了產品的特點,這也就是文化產品為什么不具備真正藝術品那種真實的風格以及豐富的韻味的原因。文化產品具備的只是獨特而新穎的虛假性,它帶給消費者的并不是由衷的心滿意足,而是一種充分而虛假的快感。雖然人們普遍認為,作為娛樂形式,對消費者而言,現代文化產品相對無害,在很大程度上文化產業化是對消費者要求的一種民主化反應,但西奧多·阿多諾堅持認為文化工業是一種破壞性力量,文化工業培養的是空虛、平庸和順從。如果忽視文化工業的性質,就是屈從于它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是腐敗的和操縱性的,它鞏固了市場和商品拜物教的統治。它同樣是使人順從和使人頭腦麻木,強迫人們普遍接受資本主義秩序。文化工業經營各種謊言,而不是真理。經營各種虛假需求和虛假解決辦法,而不是現實的需求和現實的解決辦法。它‘僅僅在表面上’解決各種問題,不是按照在現實世界中應當解決它們的那樣去做。它提供解決各種問題的偽裝,而不是實質,把對各種虛假需求的虛假滿足當做對各種現實問題的現實解決辦法的替代物。在這樣做時,它把大眾的意識接管了。”[2]72霍克海默和阿多諾不僅跟其他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邏輯和理論特征不同,而且實際上跟法蘭克福學派的本雅明之間分歧也很大。其他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是以西方工業文明為基礎,來開展他們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諾不同,從《啟蒙辯證法》到《否定辯證法》,他們采取的是拒絕工業文明進步的思路。同樣,本雅明是一個技術樂觀主義者,而阿多諾不是。阿多諾一直在堅定地預警,提示人們注意新技術中的經濟動機和意識形態動機。如果忽視商品拜物教和意識形態利益之間的關系,人類就將很難擺脫發展中的危機。他語重心長地寫道:“文化工業總體的作用是反啟蒙的,如霍克海默和我所評論的。其中,啟蒙即先進的技術的統治,它完成了大眾騙術,變成了約束意識的手段。它妨礙自主、獨立、為了自己而自覺做出判斷和決定的個體的發展。它阻止時代生產力所允許的、人類為之準備著的解放。”[2]65通過對文化工業生產過程和生產特點的觀察,阿多諾注意到經過標準化的過程,文化產品具有了所有商品的共同形式。“文化工業雖然無可否認地反思過它所針對的成千上萬的人們有意識和無意識的狀況,但大眾卻不是主要的,而是次要的,他們是被算計的對象,是機器的附件。與文化工業要我們相信的不一樣,消費者不是國王,不是消費的主體,而是消費的客體。”[2]72文化工業把文化變成了娛樂,這樣的娛樂再造了虛假的幸福感,壓制了消費者的思考,防范了人們對現實的否定以及解放沖動。在這里,阿多諾明確地指認出文化工業在生產方式上的標準化和同質化的的特點和后果,更不隱諱文化工業對消費者的意識或思想的管控,他把消費者設想為“文化呆子”。聯系商品社會中文化產業的拜物性,阿多諾認為進入文化產業過程產出的文化商品,生產的目的就是為了在市場流通環節中交換或銷售。它是商品,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藝術品,已經失去文化的某些本性。既然不是藝術品,那么它主要是為了迎合消費需求而不是或不能滿足真正的精神需求或靈魂的需求。嚴格說來,藝術創作是自由的精神創造。藝術讓靈魂飛升,完成對人類的精神表現或精神引領。在產業化時代,把藝術文化的創造視為輕而易舉的行為,把藝術文化作品的鑒賞理解為一種易如反掌的娛樂。這種認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滋生享樂主義的溫床,并因此不可避免地導致審美能力的萎頓、批判能力的退化、反思能力的閑置。
法蘭克福學派敏銳地注意到當文化產業服務于有組織的資本時所暴露出來的問題以及必然會引發的后遺癥。從更深層次的現實來看,阿多諾具有一種類似于宗教救贖那樣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因此在他看來,藝術文化一旦屈從于產業秩序,放棄作為文化藝術品的“以太”(ether)那樣的精神之光,那么人類的心靈將萬劫不復。所以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阿多諾對日益發達的資本主義文化工業還保持著堅定的抵抗和批判的姿態。在很大程度上,阿多諾敵視的或堅決拒絕的不僅僅是資本主義文化工業,還具體針對工具理性向人的社會生活的擴展。張一兵曾經敏銳地注意到阿多諾在《否定的辯證法》中那個準確概括現代技術社會特征的概念:“被管理的世界。”在闡釋這個概念所表征的“工具理性的進步就是人類文化的鏟除”時,張一兵做出了這樣的聯想:“這也是啟蒙思想無意識自反性更具象的方面。我認為這一批判性指認對于中國學界面對‘科學管理’體制長期以來的無反思性的受動狀態,一定是一種強勁的震撼。”[3]
值得注意的是,阿多諾在完成對文化工業和技術社會的批判時,也巧妙地發現文化產業在物化社會和意識方面并不是萬能的,文化工業意識形態存在著某種虛弱的一面。在警惕技術主義和商品拜物教的同時,阿多諾相信藝術并不是凝滯不變的,而是會在運動中完成自我調節的“變數”。在他看來,新的文化、新的藝術,也就是他所說的“尚無人知的審美形式”有可能產生于這種與技術統治之間的許多密切關聯中。從這些表述來看,阿多諾既不悲觀,也不守舊,更不僵化。在《電影的透明性》中,阿多諾明確地宣稱:“文化產業的意識形態本身在操縱大眾的嘗試中,已經變得與它想要控制的社會一樣內在地含有了對抗性。文化產業的意識形態含有自己的謊言的解毒劑。”[4]由此看來,深邃而辯證的阿多諾在批判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文化工業時留下的大量言論對中國正在方興未艾的文化產業而言,其意義就絕不是單一的。對接受者或借鑒者而言,對此不能斷章取義,把握其表層含義和具體細節是必不可少的環節,但更重要的是把握其具體論斷之下的深層思想。不能只是刻板地援引阿多諾的理論文本,而是更全面更自主地接受。中國文化產業和后工業社會的西方發達國家在發展潛力、發展規模、發展節奏和發展趨勢等方面的情況都大不相同。對中國文化產業而言,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和國際影響的逐步擴大,發展文化產業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可能性都變得越來越堅定,也愈來愈明確。無論是內需,還是外需,都顯得越來越迫切。這就是說,中國的文化產業在這種情況下不僅要積極回應國內需求,而且還要千方百計地參與和主導激烈的國際競爭。從適應國際需求和確保國家文化安全的角度來看,文化產業有秩序地良性地發展,也許比單純的宣傳更能有效地完成意識形態的使命。相對而言,媒介傳播比一般意義上的宣傳在效果上更深入,也更內在。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這也許是文化產業最基本的現實國際職能。不過有必要注意的是,文化產業也是一種雙刃的兵器。如果不充分尊重文化規律和產業發展的規律,不能有效處理文化與經濟之間的緊張關系,那么從中產生的問題有可能會遠遠超過發展制造業引發的環境污染以及在大中型企業重組時國有資產的流失。
法蘭克福學派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文化工業所做的研究及其論斷,作為前車之覆,對我們提供的是至關重要的警醒。無論是國家層面的產業戰略或決策,還是企業層面的可行性戰略制訂、資源整合的方式、商業模式的調整,實際上都需要認真關注價值觀的作用。如果價值觀體系的效能得到充分發揮,社會必將穩步發展。這也許是我們在解讀阿多諾時獲得的主要收獲。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馬里亞諾·格龍多納(Mariano Grondona)教授認為,一個國家必須具備做出正確決策的價值觀體系,才能實現持續的、迅速的發展。他提出:“價值觀有兩大類:一類是內在的,一類是工具主義性的。內在的價值觀是指我們不計個人得失而均予遵循的價值觀。例如,愛國主義作為一種價值觀,要求人們做出犧牲,有時就個人得失而言,它是‘不利的’。然而自古以來,千百萬人都為捍衛祖國而獻出了生命。相形之下,工具主義性的價值觀是指那種因為它直接對我們有利,我們才予以遵循的價值觀。假定一國致力于經濟增長,為此而強調努力工作、提高生產率和進行投資。倘若有利于發展的決策所追求的只是一種經濟上的工具主義性價值觀,所以要發財致富,那么人們富到一定程度時,努力就會減退。”[5]實際上,從馬里亞諾·格龍多納對價值觀體系的特點和作用的闡釋中,恰好包含著阿多諾和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文化工業中指出的那些主要問題的原因。工具主義價值觀的暫時性并不足以推動經濟和社會的持續發展。作為工具,一旦實現它的使用價值,人們也就不會再充分注意它的作用。但馬里亞諾·格龍多納所說的那種“內在的價值觀”就大不相同,它不會隨階段性任務的完成而失去作用。如果說因為經濟發展的自相矛盾之處,經濟價值觀并不足以保證經濟的持續發展,而內在價值觀與此相比最大的不同之處就在于,它可以引領人們,使人們不至于誤入歧途。
(二)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產業理論
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以雷蒙德·威廉斯和理查德·霍加特等理論家為代表,在文化立場、文化態度、文化研究方法以及文化理論認識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從《文化與社會》、《漫長的革命》、《馬克思與文學》等著述來看,雷蒙德·威廉斯對文化的理解非常寬泛。他提出過一個著名的命題,即“文化是整個生活方式”。這就是說,僅僅把“文化”局限在觀念或價值體系方面來理解,或局限在某些部分的生活或個別的生活方式來認識,都是存在著偏頗的。高雅文化是文化,低俗文化也是。嚴肅文化是文化,大眾文學也是。從存在形態上看,文化有可能已經凝結為概念化的范疇,也有可能彌散在或滲透于日常行為和經驗之中。雷蒙德·威廉斯甚至認為,從價值層面看,這些文化形態沒有也不應該有高下優劣之分,因為這些復雜多樣的文化形式共同構成了人類生存或成長的條件。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產業理論在如下幾個方面形成了自己的認識重點和認識特點。
第一,伯明翰學派也堅持文化產業研究的社會批判性,但跟法蘭克福學派有所不同的是,伯明翰學派更重視把大眾文化作為文化產業形式來開展嚴肅的研究。由于消解了精英與大眾、高雅與低俗之間的對立,所以伯明翰學派在他們的理論工作中敞開了消費者的創造性以及發生在消費中的生產性閱讀或闡釋是怎樣改變生產者的初衷或某種預先設定。這就是說,文化產品一旦進入傳播或消費環節,它就具備了或體現出某種不以生產者的意志為轉移的特性。
無論是斯圖亞特·霍爾、霍加特、湯普森,還是雷蒙德·威廉斯、托尼·本內特,在他們對“大眾”“人民”“流行文化”等概念的闡述中,都是試圖彰顯某種“文化平民主義”或“文化民粹主義”。對“大眾”“人民”的關注,對“大眾文化”的觀察,有助于推動對文化研究中真實而具體的消費情況的研究,在密切注意有選擇的消費行為、生產性的接受行為與文化產品的生產者的原有意圖之間的差異時,還可以更細致地探尋接受中或消費中的吸收、抵抗、協商、曲解等各種具體的情況。那些批評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產業理論研究的“大眾”視角的意見則認為,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產業研究視野狹隘,完全有可能把研究工作引入一種不加批判的解釋模式中。吉姆·麥圭根這樣寫道:“我贊成理解和評價各種日常意義的愿望,但是這樣一種愿望,會產生對于塑造普通民眾間接體驗的物質生活景況和權力關系的不恰當解釋。”[2]278對伯明翰學派持批評意見的人們認為,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產業理論研究缺乏一種必要的批判力量。實際上,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產業理論研究更明顯的價值主要還是體現在它的意識形態立場上,也許將其視作一種政治策略比將其視為一種文化產業理論更符合實際。在各種文化產業理論中,真正切實的受眾研究或許正是從伯明翰學派開始。雖然看起來迄今為止他們只是替消費者代言,或者替消費者立言,還沒有朗聲向消費者發言,但顯而易見的是,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產業理論研究并不僅僅像大多數文化理論那樣,只是把文化消費當作經濟行為或生產行為,重點在于消費者行為研究,而不在于消費者心理和消費過程,伯明翰學派還關注消費的文化本性。在對文化產業的本體認知中,雖然他們也注意到產業手段以及產業方法,但他們更重視文化目的。由于他們不會把目的當手段,也不至于把手段當目的,所以可以希望以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產業理論研究成果來實施某些認識糾偏。
第二,伯明翰學派把文化產業理論研究從關注生產過程向關注消費過程的位移,在現在看來不僅僅是一種研究重心的轉移,而且更是對某種消費主體性的強調。伯明翰學派在研究中注意到,文化產業的消費者并不像法蘭克福學派斷言的那樣,完全是一批空虛、平庸、不動腦筋、經不住誘惑的上當受騙者。伯明翰學派認為,把消費者設想為受控于大眾媒介和它所傳播的文化內容,完全被文化產業所算計,這樣的判斷并不完全符合事實,至少是過分夸大了權力對文化生產的控制,夸大到這些因素的力量足以決定文化消費模式的地步了,那就明顯地出現偏差了。斯圖亞特·霍爾指出:“在傳統媒介研究中,受眾總是以受影響的形象出現,一直是廣播組織以及廣告機構調查的需要。而我們要用一種更活泛、主動的受動概念代替了這些過于簡單的概念。在這些概念中,讀解、媒介信息如何被編碼、編了碼的文本的重要性和不同的受眾的解碼之間的關系都是活泛的。”[6]斯圖亞特·霍爾等對閱讀策略或大眾解碼策略的研究,強調了受眾在消費行為中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可以表明伯明翰學派并不否認民眾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的某種弱勢處境,但與此同時他們把理論興趣集中在對符號權力的研究方面,其主要目的在于說明社會權力雖然很強大,但符號權力卻是受眾可以大顯身手的領域。他們可以通過對文化產品的解碼,來實現預期的對媒介權力意識形態的抵抗、顛覆或者重構。更重要的是,伯明翰學派對文化產品在消費過程中的意義改變、意義追加、意義歪曲、意義挪用等解碼行為的細致研究,一方面豐富和擴展了人們對文化消費的特點和意義的認識,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人們更全面更科學地認識生產和消費之間的辯證關系。
伯明翰學派重視文化那種作為社會經驗的屬性。在雷蒙德·威廉斯看來,文化存在于日常行為和經驗之中,是一種和真實的生活緊密相關的“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其物質性和實踐性意味著文化創造是凝結群體智慧的方式,它是民主的、開放的、動態的,也是充滿活力的。也就是說,由于創造和消費的廣泛性,文化的意義也許正在于某種難以壟斷的、無法預測的、不斷更新的同時也是前景廣闊的形式。這些形形色色的創造意義的形式,充分體現出不可忽略的創造過程的某些“共同性”,或類似消費過程中那種共享的“民主性”以及參與者自我成長的某種“家園感”。消費模式對文化生產具有某種至關重要的決定性,不過對文化消費模式的研究僅僅停留于對消費行為的關注,那就太表面也太淺近了。從這方面來看,伯明翰學派的研究顯得深入得多。
(三)媒介技術學派的文化產業理論
媒介技術學派在解魅作為訊息的媒介對人的感知方式、感知系統以及認識和心理的深刻影響方面,以其獨特的認識貢獻,啟發人們更及時更準確地關注新技術與文化產業之間的相互關系。電腦、信息技術、多媒體技術、互聯網以及通訊技術在為文化產業提供便利的同時,也迅速地引發了文化產業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的變化。媒介技術學派以技術演變為基礎和認識線索,廣泛吸納新的理論資源,建構起富有闡釋力和前瞻性的理論體系。
赫伯特·馬歇爾·麥克盧漢是研究媒介技術理論的先驅。由于對媒介技術在人類認識活動中發揮中介作用的機制、方式和效果的研究,他開創的麥克盧漢主義或麥克盧漢學派在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研究領域獲得過很好的評價。他提出的“媒介訊息論”“冷媒介與熱媒介”“媒介環境學”等論斷產生過廣泛的影響。麥克盧漢至為關切的媒介技術對社會和心理的影響,迄今為止仍然是媒介技術研究中一個廣受關注的重要理論問題,讓人們對媒介技術變革不得不保持足夠的重視。
作為傳播學先驅,麥克盧漢理論體系的前提就是“媒介訊息論”。在他看來,媒介之所以能影響人,是因為它能把需要傳通的東西處理成了能讓受眾接受的“訊息”。對“訊息”的理解,可以彰顯他的“媒介訊息論”的要旨。他認為,單純的信息,是一種不帶訊息(message)的媒介。“任何媒介或技術的‘訊息’,是由它引入的人間事物的尺度變化、速度變化和模式變化。”“‘媒介即是訊息’,因為對人的組合與行動的尺度和形態,媒介是發揮著塑造和控制的作用。”[7]228在很大程度上,麥克盧漢早年從事英美文學教學的經歷使他在用語上也體現出某種散文風格,這種非連續性并置的方式適合深度研究的表達,也增加了理解的難度。“媒介即訊息”至少包含著三種相互聯系的含義:一,訊息的樣式或規格必須適合傳媒的要求,便于讓受眾接受。二,媒介的性質是第一位的,遠勝于傳播的內容。三,理解媒介就意味著理解其影響。麥克盧漢認為,媒介的性質,其重要性遠遠超過交流的內容。因此,他更重視研究媒介的性質,因為媒介成分和內容的研究絕不可能揭示媒介影響的動力學。
麥克盧漢對媒介冷熱屬性的研究,其目的正在于深究媒介對人的感官的影響。在他看來,“熱媒介”清晰度高,媒介感知者不需要深度介入,也不需要進一步地大量補充信息。如電視、電話、象形文字、卡通片、手抄本、口語等。“冷媒介”與此不同,其信息清晰度低,信息接受者必須深度卷入,并補充信息。麥克盧漢把這一類媒介稱之為“冷媒介”,如電影、照片、印刷品、拼音文字等,并進一步就媒介的“冷熱”特性闡述了自己的見解。他指出,因為“熱媒介”可以提供充分而清晰的信息,所以可以剝奪信息接受者深度卷入的機會,那么信息接受者的感官機能降低。“冷媒介”邀請信息接受者深度卷入,那就需要感官提高感覺機能。麥克盧漢對媒介冷熱屬性模式的識別或者區分,其實已經暗含著對信息接受者的某種“分眾”處理。顯然,“冷媒介”適合媒介與精英階層的信息交流,“熱媒介”則可以大量用于社會中的普通受眾。在媒介與受眾之間的雙向互動或伺服中,麥克盧漢認為由于人的中樞神經系統的自我保護機制,新技術對社會的影響和對心理的影響已經可以讓接受者渾然不覺。對信息接受者而言,那已經是一種隱形的環境,就像“魚到了岸上才知道水的存在”[7]70。當新技術內化時,就會很快發生文化的新型轉換。
從媒介史或媒介變革的角度,麥克盧漢樂觀地預言,電子媒介時代將通過感知系統的重塑,人將會成為感官平衡、具有整體思維能力、能夠整體把握世界的“部落人”。在原始部落時代,人們的視覺、聽覺、嗅覺、觸覺以及味覺都可以接受信息,感知方式是整體的、直觀的。在那個“口語媒介”時代,不憑借文本,也不發生感知方式的分割。書面媒介時代是由視覺感知主導的時代,拼音文字把信息進行視角編碼,人類的眼睛在訊息感知中代替了耳朵,感官平衡被打破。在感知方式上人成了殘缺的人。電子媒介縮小了地球空間,成了“地球村”,由于感知方式在更高層次上的“返祖”,在信息接受中感官平衡,人也許可以成為人格健全的人。這是新媒介帶給人類的最振奮人心的福祉。
麥克盧漢對新媒介的環境作用的重視,使他有機會具體地探究媒介是怎樣影響人的感知、感情、認識和價值的。他認為:“環境的首要特征是隱而不顯、難以覺察的。這似乎是種系發育過程的必然結果。每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都成為此前一切階段的環境。然而我們直覺到過去的階段,或者說只覺察到環境的內容。”[7]412媒介形式對人的感知、認識、思考、理解,其方式有所不同,而且外在于人的感知方式。環境是可以避開人的感知的,并用一種奇怪的力量傳播著關鍵而主導的訊息。既然新媒介就是一種新環境,新媒介傳播的訊息又是根據新媒介的規范完成的新編碼,那么在媒介與人的互動中,就必須重視具有主導性的新媒介的變革。媒介史從口語到書寫、從書寫到印刷、從印刷到電子媒介的轉化表明,只有在媒介技術和人的回應能力之間保持某種必不可少的平衡,現代社會才有值得期待的未來,人類才有健康的精神生活。文化創造或文化生產的積極作用和建設意義在這里可以獲得集中的體現。
從總體上看,媒介技術是麥克盧漢認識現實的視角。圍繞媒介技術建構起來的認識體系,以富于歷史性和反思性的闡述方式表達了具有啟示性的文化民主觀。也許,他并不完全是一個技術還原論者或技術決定論者。其理論認識的宏觀性表明,麥克盧漢主義不像布迪厄的媒介批判理論和波德里亞的“仿真”理論那樣,更多直接而具體地面對文化生產現實或文化產業現實,因此,它也因為這種理論和現實之間的間距而顯得要全面得多,也顯得更深刻。
二、西方發達國家文化產業實踐的基本經驗
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產業理論研究體現的是學術研究的成果,理性、完整、全面,具有戰略認識的宏觀性和前瞻性。從策略層面看,跟文化產業實踐之間距離遙遠,缺乏直接的可操作性。這也許是由理論研究和實踐運作在目標和效用之間的差異所決定的。
中國文化產業當前具有良好的政策支持和發展環境,正處在加強學習和積蓄力量的重要階段。自從2008年納入國家產業振興計劃,文化產業被確定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之后,現在的狀態也并沒有急流猛進,一路高歌,而是“盡可能地從容前行,不斷調整發展方式,完善管理方式,在人才培養、金融支持和研發資金等方面積累經驗”[8]。這種現實要求中國文化產業在面對西方經驗時要更有整體性、前瞻性地借鑒,更有針對性和科學性地利用。在此之前,中國文化產業重視投資,但忽略消費對產業的推動力量,大量民間資本被閑置而沒有發揮出應有的效益。在管理方面采取的分業發展和行業分層管理也暴露出管理理念滯后的問題。所以,面對西方經驗,我們不僅要重視西方發達國家在文化產業理論方面的豐厚積累,更要認真學習他們在發展文化產業方面的實踐經驗。如果我們不充分注意以產業鏈結構為核心的從理論到實踐的經驗整合,就有可能難以實現跨越式發展的目標。
具體地看,由于西方各國文化產業基礎不同,所以在政策支持方式、產業發展方式以及產業管理方式等方面采取的措施也有所不同。美國重視電影業和旅游業,他們的電影業、家庭電視、錄制音樂等娛樂也獲得了充分發展,所以其體制、市場、產值的成長都具有自己的獨特性。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重視美國電影公司在國際市場上的業績,希望并鼓勵那些海外子公司在銷售方面充分發展市場開拓能力。美國的旅游業是零售業中第三大零售產業,在支持和解決就業方面,功勛卓著。德國政府在政策上大力支持戲劇業和電影業,并千方百計增加經費投入。德國公共劇院和私人劇院基本上不為經費問題發愁,因為各州以及地方政府把公共娛樂支出的百分之六十三都投給了劇院。政府專門設置電影促進署來推動電影業的發展,媒體公司和國際電影集團負責在影片制作和電影院基礎設施建設或改造方面投資支持。這些措施不僅支持了國內電影生產,也加強了德國電影業和歐洲電影業以及國際電影界的合作。瑞典跟美國和德國的情況不同,瑞典政府在文化環境建設、文化旅游以及群眾文化活動等三個方面做出過許多努力,但在經費投入方面并不太多。在瑞典,廣播、電視、書刊、音像以及報業都是文化產業,所以就要按市場機制來運作,也就是需要消費者來投資了[9]。瑞典政府在文化建設方面的投資主要用于交響樂團、博物館、圖書館以及歷史文化遺址保護等方面,這里體現的也許是一種立足文化國情、腳踏實地、量力而行的指導思想。
從以上歐美諸國的情況來看,共同之處在于:一、政府在戰略層面上的政策支持,具有主導性和推動作用。二、文化產業在發展過程中并不體現為面面俱到或平均使用力氣,而是有重點、分主次、立足實際地被引導。三、依法管理文化產業,廣泛利用民營資本來推動產業化。四、在滿足國內需求的同時,加強了國際產業合作,組建跨國公司,有助于有效把握機會,利用對方的市場、渠道、機制,既可以保持一定的產業發展規模,又可以充分發揮靈活性。作為具體的文化企業或企業負責人,在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不一定要急于經營跨國公司,但從確保國家文化利益和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角度來看,今天中國文化產業的跨國經營,勢在必行。
[1]Theodor Adorno:Culture industry reconsidered[J].New German Critique6,Fall1975.
[2][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納蒂.通俗文化理論導論[M].閻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72.
[3]張一兵.無調式的辯證想象[M].北京:三聯書店2001:32.
[4]阿多諾.美學理論[M].王柯平,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6.
[5][美]塞繆爾·亨廷頓,等.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M].程克雄,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81.
[6]StuartHall,Dorothy Hobson,Andrew lowe and paulwillis (eds.)culture,Media,Language[M].London:Hutchinson and Co.(publishers)Ltd,1980:117.
[7][加]埃里克·麥克盧漢.麥克盧漢精粹[M].何道寬,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228.
[8]李思屈,等.中國文化產業政策及其實施效果[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3(3).
[9]陳忱.文化產業的思考與對話[M].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6:41.
On the“W estern Experience”in Cultural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
Li Jiang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chool,GuangxiNorm al University,Guilin 541004,China)
The“western experience”in cultural industry consists of two inseparable parts:one is systematical knowledge of theory and another is rich practical experience.The systematical knowledge of theory ismainly about critical research atan academic level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often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practical industrial approaches.If Chinese cultural industry which is still in a natural state needs to prepare the experience for furthermultinationalmanagement,it necessary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social factors of the western cultural industry and the cultural industry policies,bases,developingmodes and social contribution of the western advanced countries so as tomake better use of the theories and experience in the western cultural industry.
Cultural industry;Western experience;Theory of cultural industry;Experience of industrialization
G114
A
1673-8535(2014)02-0037-08
李江(1964-),男,重慶市人,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學博士,研究方向:現代文化和文化產業理論。
(責任編輯:覃華巧)
2014-01-12